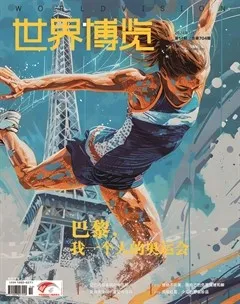时间褶皱

特德·姜的科幻小说《你一生的故事》(电影《降临》原著小说)里,讲到关于语言和时间的一种理论:语言决定认知,如果谁掌握了非线性逻辑的语言,便能感受到非线性的时间。当时间离散分布,我们所谓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将会并置或散乱分布在眼前。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同时看见当下、未来和过去。一个人不但可以体验到像本杰明·巴顿那样的返老还童,逆向生长,还可以早早看见自己子女年老时的模样,将生命体验和情感关系彻底颠覆。
于当下日常的我们而言,这种理论设想终究只能在小说或影视里呈现。不过,我们可以真切感知的,是历史留下的印痕。在南方工业小城一隅,站在一座上世纪九十年代兴建,如今已画上“拆”字和“危险勿近”的仿苏州园林小公园里,一抬头,可以看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炼钢铁时期留下的巨型水塔,其上已爬了三十年的爬山虎,正在郁郁苍苍地逼近峰顶。
如果爬山虎愿意,可将整个工厂区尽收眼底。幼儿园里,有旧时砖砌的迷宫和地道。子弟中学没有草皮的大操场历经风雨。最庞大的是第一代商品房宿舍,重重翻修粉饰,也遮不住楼角顽强的青苔。大烟囱那边,是仍在生产钢铁制品的厂区,厂区周边,有当年的运动馆、广场和医院。还有偌大一片空地无人打理,已然杂花生树、芳草萋萋,但却照样是广场舞圣地。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短短数年之内,一座座在战火中衰颓的商业城市变成了工业重镇,为富国强兵源源不断地输送“血液”,堪称国家的“装备基地”。待到春风满地,改革到来,计划转市场,转型、破产和下岗潮接踵而来,自然草木趁乱疯长,人造万物渐显老迈。









历史大风起兮,时间起了褶皱。工厂区或工厂子弟的身份概念淡去,制度更迭,留下不少尴尬自处的事与人。一个十年再一个十年,早就规划着要拆的旧房子,始终人不去楼不空,子弟小学旧址上新起楼盘却险些烂尾。新鲜的标语和涂鸦抹在老墙上,是对过往的闯入——当然,也许带有那么一些修正和否定。上一番浪潮席卷留下的残迹尚未消失,潮头已经速退却了。恍恍惚,惶惶然,几代人走到了拐点。
散步在如此的时空,不免心生怀古之情。但作为外来者,好奇这些旧物和老人,其实是对新经验的兴奋。弃置的巨型水塔,像历史纪念碑,越老越牢,意义越发坚实不可撼动。可随便找个年轻人问,却说不清道不明——“从小就在那儿”,“爬山虎比我还老呢”。
已然是破败园林的小公园,即便在正午,也有几分森森的鬼气,像聊斋里的场景,处在闹市路口,却人迹罕至,仿佛是个什么象征。
成年人对时间的感知,对过往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童年记忆的理解,一旦纪念碑和象征被拆除或翻新,时间的褶皱展平,一些记忆便永远消失,有些感觉就没了。到那时,从褶皱里活过来的老人,也许对记忆不再那么确定,就像流浪在宿舍、公园里的野猫,问今是何世,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责编:常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