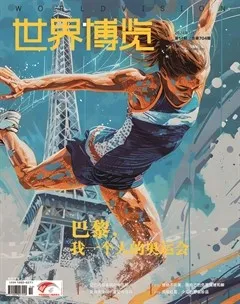\"正名\"问题中的语言人类学:对语言,我们期待什么,又害怕什么?

“正名”一词出自《论语·子路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正名”的基本含义是,要让事物的名和事物的本来面目相称,名实相符,才符合天地间的秩序。事物的名本是因事物的自然属性由人们约定俗成的,但事物之名一经确定,却又能对事物本身和其所处的环境发生影响。
在任何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社会语境下,“正名”都会涉及深远的政治内涵,其中大致会涉及这几个方面:1.所正之名本身的语意;2.是谁被赋予了正名的权力和意愿;3.为何人们会在正名的过程中感受到可以理解和分享的意义,但同时却又随时会恐惧和无法确定所正之名的真实性,以及自身想要正名之情是否虚妄。这三个方面恰恰都是语言人类学过去一百多年的研究传统中深入探讨的方向。
舌语:是对神的赞美,还是恶魔的诱惑?
语言人类学是人类学学科中一个非常小众的分支。研究语言人类学的学者们需要打下三个方面的基础:1.普通语言学;2.语言哲学;3. 在普通人类学研究中,对研究群体的语言和他们运用语言的方式以及相关的语言意识形态,语言使用的社会、政治、历史环境进行参与式观察。
举个例子,如果要对“正名”做一个语言人类学研究,那么可分为三部分:1.研究者首先需要了解汉语中“言”和“语”,以及“声”和“音”的分野,要知道为事物赋名在“语”和“声”,出自自然而未经思辨的情感与朴素的认识;然而为事物正名则需要“音”和“言”,皆有非常深远的历史、文化、哲学和政治背景;2.前文提到“正名”涉及的三个方面主要在语言哲学的范畴内,探讨的不仅是特定的内容(比如“正名”),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特定内容的讨论,理解人类对语言本身的认识:我们想要通过语言得到什么?我们又害怕语言会带来什么影响和后果?3.通过参与式观察或文献研究分析具体情境下的“正名”的例子。这里说的都是理论假设和推演,然而非常近似的研究已经在语言人类学领域出现过,就是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尼古拉斯·哈克尼斯对宗教典籍与仪式中“舌语”(glossalalia)的研究。

19世纪西欧的《圣经》学者们把古希腊文中的“舌头”和“说话”的两个词根合并为“glossolalia”一词,来描述《哥林多前书》14章中第6和第23节记载的现象,即在祷告时由圣灵发出的语言。因为赞美神的话语如泉源般涌出,快到来不及成型为言语,所以成为一种由舌头摆动发出的对神的赞美。长期以来,许多信徒们认为这是超自然力触发的言语方式。
哈克尼斯教授对舌语在韩国传播的研究,扎根于他对语言人类学长期的观察与研究兴趣,所以他关心的问题是:从人们对舌语的态度可以看出,我们希望语言能做到什么,我们又害怕语言会反映出哪些人们能感受到却不愿意承认和深入剖析的东西。在他的研究案例中,有失恋时用舌语祷告的女高中生,有出国在外跟同乡一起用舌语祷告时感受到慰藉的博士生,有天然会用舌语却不愿意使用的公职人员,有极为虔诚却无论如何无法用舌语祷告的主妇,有被舌语迷惑的教堂歌手和乐师,也有被舌语恫吓而害怕成为恶魔诱惑对象的普通教徒们。
韩国近代历史中,基督教的极大盛行和传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可以说基督教信仰与新时代的国家主义被捆绑到了一起,被人们寄予了摆脱愚昧和被殖民的往昔,迎来经济兴盛、社会纯洁美好的意涵与想象。舌语就像这一信仰在韩国的文化实践的缩影。在韩国,固然虔诚的基督教徒人数众多,但更大数量的人们并未能完全不设防地全盘接受这一在历史上并无根基的信仰,更像是徘徊在恐惧中:既希盼自己的基督教信仰能反映出国家社会兴盛美好的盛景,但同时却又迷惘于这一切是否只是虚妄的想象。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韩国流行起两个祷告形式非常激情澎湃的教会分支,舌语由此系统地进入韩国基督徒团体(数量巨大)的视野。但从一开始,“释义”的问题就一直存在。无法释义的言语虽被信徒们承认为出自圣灵之口,但人们总是很容易对说出和听到自己无法释义的言语产生不信任,于是总是试图在某种维度上解释它。也有许多人把它看作一种仪式中暂时性出现的非下意识的心理状态,有助于在与他人一起祷告时产生一种亲密而激情的精神上的联系。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非同小可:到底是谁在说话,说的人和听者能否区分那是来自圣灵对神的赞美,还是来自恶魔的诱惑,让人产生虚妄的激情和无意义的幻觉?有许多天然就能用舌语祷告的信徒们不愿意使用舌语,就是出于对被虚妄的激情占据的恐惧。
可以释义,才能正名?
哈克尼斯教授的田野观察与基于语言哲学的讨论基本止于此。作为人类学家,他不需要回答这些问题,他更重要的角色是写好这些问题怎样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造成了个体与群体的情感与困境,人们又是如何诠释这些想法,把它们内化为某种道德指南和情感寄托的。除此之外,他还对舌语做了系统的录音,并作出了基于声学的图像分析,把其声学上的特征与变化跟其具体使用的情境与社会意义联系在一起,希望能够在释义之外,对舌语的特征做出科学的描述。由此他探讨的层面又深了一点:语言中,声与言语在释义层面的贡献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因为到现在为止,人们对释义的理解往往停留在言语的层面。
哈克尼斯教授的研究涉及了许多关于对语言本质理解的层面,为什么人们想要言语能够释义?为什么人们害怕无法释义的言语可能带来的虚妄的会占据心灵的激情?这就回到了开头说到的正名。我们认为惟有在言语可以释义的时候,才能为事物正名。惟有在事物得以正名的时候,天地间(人类社会)的秩序才得以实现,以及为人们所认识和维系。帝王将相的正名对政治制度的影响早已被广泛讨论过,为飞禽走兽、四季时日、七情六欲、亲疏贵贱正名,又何尝没有贯穿我们的整个文学史和哲学史呢?
(责编:刘婕)

哈佛大学研究现代韩国经济和社会的人类学教授尼古拉斯·哈克尼斯。

语言人类学家们对语言相对论(language relativities)研究有相当久远的传统,关于言语释义对心智和认知的影响有相当多的哲学讨论,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考虑读美国学者约翰·李维特(John Leavitt)的《语言相对论》(Language Relativities)一书。
qpeyKwKPufq7d5MW5VyqDhR/azc2eM+LBHPiY8mUtfg=
“舌语”,一直以来都引发着人们的好奇心以及神学界激烈的争论。有人将其称颂为“超自然的天赋”,认为它是超越语言的神秘表达,也有人谴责其为“符号学的炼金术”,认为它是胡言乱语,毫无意义。这种分歧的核心是舌语与语言之间令人费解的关系。哈克尼斯在《舌语和语言的问题》一书中调查了舌语在韩国不同教派和教会中的广泛应用情况,展现出韩国舌语的风行处于众多交织甚至相互竞争的社会力量、宗教遗产及精神愿景中,本书分析了在世界范围不断传播的福音派最神秘的实践之一,并推动了我们对语言的力量及其局限性的理解。

《首尔之歌:韩国基督徒声与言的人类学》是对韩国声音的人类学研究,在韩国,西方的歌剧、艺术歌曲和合唱音乐在基督教福音派中风行。根据在韩国的教堂、音乐厅和音乐学校的田野调查,哈克尼斯认为欧洲古典风格的声音已经成为韩国基督教繁荣的象征。韩国基督徒对此种声音特质的养成反映了信仰带来的社会变迁,本书解决了声音人类学中的疑问,并跨越诸多学科,发展出一种创新的符号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