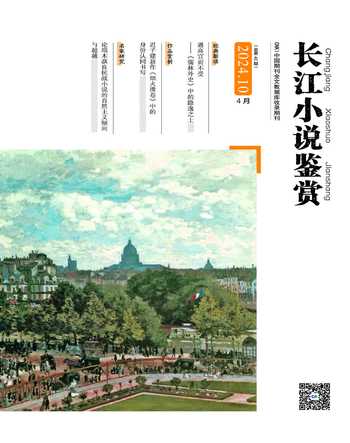《金锁记》中的异化策略及跨文化传播困境
张瑜
[摘 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多次掀起张爱玲研究狂潮,其翻译风格引发众多学者热烈讨论。译本The Golden Cangue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在保留民族文化差异性基础上向读者输送异国情调,展现了张爱玲对异化翻译策略的熟练运用。本文以《金锁记》自译本The Golden Cangue为例,从词汇翻译入手,分析他者化的语言风格实则体现张爱玲坚守中国本位文化立场。同时,本文着重指出该翻译策略以忽视市场需求为代价,势必使译本陷入跨文化传播困境。
[关键词] 张爱玲 《金锁记》 The Golden Cangue 异化 跨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 H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4)10-0103-05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进行双语创作并致力于海外传播的优秀作家之一。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开始在上海发表作品,以傅雷、谭正壁为代表的学者开始了对张爱玲以及张爱玲作品的风格研究;20世纪60—80年代,夏志清首次将张爱玲写入文学史;20世纪80—90年代,随着《中国现代小说史》传入中国大陆,张爱玲吸引了大批学者视线。如今,对张爱玲其人其作的研究不知凡几,大致有文本分析、翻译、影视传播等角度。研究者结合现代西方文艺理论,在材料选择、理论运用、研究视野方面都更为开阔纯熟。目前,关于其自译本的陌生化翻译研究已屡见不鲜,但对其遭遇的跨文化传播困境分析还略显不足。本文将立足前人成果,从异化翻译策略入手,探讨《金锁记》自译本The Golden Cangue中体现的中国本位文化立场,以及试析其遭遇跨文化传播困境之成因。
张爱玲渴望在美国实现自己的文学梦,但除语言障碍外,作品和读者间还有无法跨越的政治因素。种种原因使《金锁记》自译本The Rouge of The North反响平平。现实境遇使张爱玲译作心态发生变化,《海上花》和《红楼梦》的翻译确证了她与中国文化的情感重建过程。经夏志清鼓励,她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将《金锁记》重译为The Golden Cangue。该翻译理论由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提出,他将翻译策略细化为“归化”(domestication)和“异化”(foreignization)。前者指译者接受目的语国家文化价值观,对外国文本的民族中心主义进行还原。后者则突出源语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将读者送到国外体验异域风情。The Golden Cangue正是异化策略的完美体现。
张爱玲选择以原作美学风格为主重译《金锁记》为The Golden Cangue,对解构英美文化霸权具有积极意义。然而,一味以异化为主颠覆目的语用语规范,极大缩小了阅读群体,或许在不经意间沦为文化殖民主义者的同谋。张爱玲坚持译者主体性的翻译理念忽视出版社、读者的阅读偏好,使译本销量低迷,同样也容易陷入传播困境。
一、他者化的语言风格
异化翻译策略要求译者从事翻译活动时保留源语语言材料,欢迎不通顺或艰涩难懂的语句,以便给接受者提供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在此理念下,张爱玲忠于原作,竭力保留源语文化意象再现源文异域性。
1.颜色词
张爱玲一向喜爱浓郁的色彩词。《我的天才梦》中,她写道:“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1]英汉两种语言隶属不同的文化体系,颜色词受所属文化影响。故而,译者须掌握颜色词背后的隐喻义,方能展开翻译活动。《金锁记》原文包含诸多颜色词,“青”成为高频出场词汇之一,其有特殊的文化底蕴。“青”与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相配,作为五色之一归入五行图式,表五行生万物之义。《汉语词典》中把“青”归纳为:蓝色或绿色;黑色。作为世代中国人的记忆,张爱玲在The Golden Cangue的译本里根据语境需要将其灵活译为蓝、绿、黑三色,力求再现原文意趣。
原文:天是森冷的蟹壳青。[2]
译文:The sky was a cold bleak crab-shell blue.[3]
原文:竹根青窄袖长袍。[2]
译文:Narrow-sleeved gown of bamboo-root green. [3]
英语体系里并无与“青”对应的英文单词,部分学者便以“Cyan”代指,现今国际颜色对照表沿用了该译法。但张爱玲却将“青”细分为“蟹壳青”“竹根青”,并分别译作“crab-shell blue”“bamboo-root green”。“无论是原料来源还是实际颜色的波长,青色与欧洲的蓝色都是最为接近的颜色。”[4]青色也被归为蓝色色彩大类。因此,张爱玲将“青”与“blue”对应,具有一定根据。此外,“青”作形容词时也指青灰色的皮肤和忧郁情绪等。原文“蟹壳青”前用“冷寂”一词勾勒黎明时分天空诡谲之色,又承接上文嬷嬷对两个小丫头的斥责,从形式和内容上共同型构了天地的压抑深沉。译文中,“冷寂”译为“cold bleak”,再借助“blue”凸显了当时凄冷、阴郁的环境。但“蟹壳青”总体偏深灰绿色,视觉效果上与“light blue”“light steel blue”近似。“竹根青”指竹子的绿色,类似于英文颜色词中的“olive”“dark olive green”。张爱玲在颜色方面精益求精,但过渡雕琢反而不易于英语读者理解。与张爱玲的翻译理念相反,金凯筠在《倾城之恋》译本Love in a Fallen City中直接选用现有的英语颜色词以提高读者阅读体验。如“土崖缺口处露出森森绿树,露出蓝绿色的海”[2]中“蓝绿色”一词,金凯筠并未多做纠结直接以“aquamarine”替换,增加了译文流畅度。
2.成语和俗语
成语和俗语是中国特色文化现象,作者为保留《金锁记》原文中成语、俗语的文化意蕴,多采取直译汉语意象。
原文:她那小长挂子脸便往下一沉。[2]
译文:her narrow little face fell to its full length like a scroll. [3]
因婚礼操办的过于匆忙失了排场是兰仙的一大憾事,七巧故意重提,自然引起兰仙不快。形容兰仙的“小长挂子脸”时,张爱玲按汉语语序直译,再辅以“its full length like a scroll”阐释,形象刻画出兰仙“长”而“窄”的面部特征。语言风格呈现出强烈的异域色彩。
原文:七巧听了,心头火起,跺了跺脚,喃喃呐呐骂道:“敢情你装不知道就算了!皇帝还有草鞋亲呢!这会子有这么势利的,当初何必三媒六聘地把我抬过来?”[2]
译文:Fire leaped up in Chi-chiao as she heard this.She stamped her feet and muttered on her way downstairs,“So—just going to pretend you dont know.If you are going to be so snobbish,why did you bother to carry me here in a sedan chair complete with three matchmakers and six wedding gifts?” [3]
“三媒六聘”属于汉语特有词汇,表现了我国悠久的婚礼制度文化。 张爱玲为传播中国婚姻习俗,选择将其意译为“three matchmakers and six wedding gifts”。虽然该译法向目的与读者传递了源语文化礼仪,但不免将中国婚礼制度简单化。且“三媒六聘”还包含兴师动众之意,汉语虚数“三”“六”被译成实数,丧失了成语的实际意与隐喻意。
3.中国特色文化
“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5] 长期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宗法观念,将庞大的亲属体系按血缘、姻亲关系划分为宗亲、外亲和妻亲三类。《金锁记》中姜家作为典型的联合家庭,人物称呼极为复杂。如小说中宗亲长子称“长房大爷”,其配偶为“大奶奶”玳珍,待字闺中的云泽称“姑娘”,七巧的兄长曹大年被丫鬟们唤作“舅爷”等。反之,西方家庭更多属于核心家庭模式。英语中的亲属称谓无法囊括原文复杂的人际关系,故译者需施用补偿策略,在保证原作基础上辅助读者理解词义。如在汉语语境里,“老太太”是对老年妇女的尊称,亦是宗法家族中权力与孝道的象征。“大奶奶”处权力次阶。张爱玲在翻译这组词时均用“mistress”指代,增“old”“eldest”以示二者年龄之分。但“mistress”在英语语境里常用作“情人”,难免使英语读者感到困惑。
原文:季泽是个结实的小伙子,偏于胖的一方面,脑后拖着一根三脱油松大辫,生的天圆地方,鲜红的腮颊……[2]
译文:A robust youth,tending toward plumpness,Chiang Chi-tse sported a big shiny three-strand pigtail loosely plaited,down his neck. He had the classic domed forehead and squarish lower face,bright chubby red checks.[3]
本例中张爱玲采用复杂的翻译方式增译“三脱油松大辫”。她用“sport down”描绘辫子在脑后的运动状态,用形容词“shiny”将辫子上闪亮的油膏具象化,舍弃了英语惯用的“behind his head”,而用“neck”替代。张爱玲如此苛责自己的原因在于大辫子成为清朝时期封建贵族的地位象征,晚清以来,辫子又被视为“未开化”的标志。《金锁记》所述时代为民国晚期,季泽的“三脱油松大辫”实则隐含封建贵族沉溺旧梦之意。译者选用异化策略将翻译复杂化,可见其良苦用心。此外,“天圆地方”的译文,也是作者异化策略下的语言产物。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用异化译法可以使译作充分体现异国文化特色,增强语言的生命力,进而实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看似简单的翻译活动,译者实际上需要解决不同语言符号系统的等值交换,面对不同的文化体系,担当跨文化交流的重任。”[6]张爱玲在美国时,竭力在两种异质文化间搭建沟通桥梁。但以异化策略为主的翻译观念过于强调忠实原文,反而平添读者阅读负担。
二、 跨文化传播困境
作为西方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思潮,接受美学从读者和作品的相互关系中研究文学作品的接受过程,将读者视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读者在阅读中发挥的能动作用。受到该理论影响,翻译研究也开始重视读者在翻译活动中的重要作用。翻译与跨文化传播本质上具有目的性,目标的实现一定是以目的地语读者的期待视域符合。张爱玲坚持其译作理念,忽视读者了解中国的阅读需求,使其译本在海外遭受冷遇,不利于其作品在海外的传播。
1.译者的主体意识
《金锁记》及其译本没能在美国市场打开销路,很大程度上归结于张爱玲的主体意识。她谢绝他人代笔,坚持直译,甚少采用英美俚语以免造成化华为夷的印象。强烈的陌生化效果降低了译文可读性,使《金锁记》异域传播受制。在讨论中国文学、文化外译问题时,译者需以读者为锚点,认识到客体作为主体功能的引导者和行为效果的检验者,在译作的传播与接受中不容忽视。尤其是弱势语向强势语输入源语文化色彩时,译者更需重视目的语读者阅读习惯、偏好和审美趣味,以便本国文化走出去。张爱玲早期Chinese life and fashion一文,以读者为导向兼顾文化交融和读者背景,运用大量英文典故和隐喻,符合在亚洲居住的白人的阅读期待,因而获得较大关注。然而美国投稿失败的经历,让张爱玲自译时偏向输入本国文化色彩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读者的接受能力。
张爱玲有自译作品的习惯。虽然其英语水平毋庸置疑,但毕竟不是母语,在口语和成语的运用上始终吃亏。宋淇就曾指出:“中国人在美国用英文同这么多的英语作家争一日之短长,很容易碰壁。”[7]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编辑Karen Mitchell认为张爱玲的译文虽好,但人物对白听起来并不自然。可见,张爱玲译文风格书面气过足而口语化稍弱。刘绍铭和欧阳桢在《爱玲说》中详细论述了The Golden Cangue存在的语文习惯问题。如七巧颤声道:“一个人,身子第一要紧。你瞧你二哥弄的那样儿,还成个人吗?”[2]译文则是这么翻译的:Her voice trembled.“Health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anybody. Look at your Second Brother,the way he gets,is he still a person?”[3]该句中“is he still a person”不符合阅读习惯,且“person”属于社会性角度,“human”则是从人的生物性和精神性出发,符合七巧的丈夫是个患了痨病、全身不能动弹的人物形象。故此句应改作“is he still a human being anymore?”更为适宜。
张爱玲在美期间,基本只与台北的皇冠出版社有稳定合作,其作品在国外出版社极难出版。后续由金凯筠翻译的《倾世之恋》却得到精英刊物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青睐顺利出刊。金凯筠作为美国汉学家,熟稔西方读者阅读习惯。就译本题目而言,金凯筠将《倾世之恋》译为Love in a Fallen City简单易懂,而张爱玲的自译本The Golden Cangue中Cangue选自法语词汇,特指中国用来体罚和公开羞辱的刑具,二者相比,后者更为抽象复杂。此外,The Golden Cangue中的句式严格对应原文,往往冗长烦琐,而Love in a Fallen City则以读者为导向删繁就简,不拘泥原文句法。
原文:她梳洗完了,刚跨出房门,一个侯守在外面的仆欧,看见了她,便去敲范柳原的门。[2]
重译:She washed and dressed,and walked out the door. There was a porter waiting outside. Seeing her,he immediately knocked at Liuyuans door.[8]
原文该句是典型的短句结构,金凯筠初译时遵循张爱玲的译文风格,按照原文句式翻译,但在重译本中她将一个长句拆分为三个句子,删除了诸多副词、动词,留下最简练的信息,使译文读起来简洁明快。此外,The Golden Cangue中人名采取韦式拼音法,而金凯筠在重译本里选择音随人名的灵活译法,利于凸显人物关系。如“金蝉”译为“Jin zhan”。总的来说,作为母语使用者的金凯筠比张爱玲更熟悉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且坚持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策略令其译本更利于海外传播。
一个要走向世界的作家必须要学会适应新的文学环境。彼时张爱玲虽远离中国,但她的创作灵感仍停留在她在上海的时候。隐居生涯让她未能接纳新的文化环境。且受赞助者夏志清影响,张爱玲的译作理念抱有鲜明意识形态和诗学特征。译本虽保留了原文本的文化特性,也极易陷入个人主义和作者中心论。正如谢天振所说,译者作为跨语言、跨文化交流的载体,需明确任何文化输出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是面对强势文化环境,“其实牵涉到一个民族接受外来文化、文学的规律问题:它需要一个接受过程”[9]。
2.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
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向来喜爱赋予中国神秘颓废的气质形象,为其构筑特殊的异域风情。张爱玲批判西方这种狭隘的阅读兴趣,提出“想象力需要空间,它需要距离与宽松的环境”[7]。与赛珍珠不同,张爱玲想要写的是“一种更贴近自己人生的文学”[7],她关注腐败的封建家庭制度和吃人的礼教,无意展示乱世下中国传统乡村生活和普通小农家庭的精神世界。然而美国中产阶级读者早已习惯赛珍珠所写的中国形象,他们希望了解中国当时的社会风貌。张爱玲笔下的旧中国儿女难以引发英语读者同情,又因其描写的内容与西方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相悖,所以接受度不高。Sciban在她的论文里写道:“Sometimes the life-like portraits of the characters in her stories shock the reader, such as Cao Qi-qiao in‘The Golden Cangue.”[10]张爱玲对民族文学的远离也是她迟迟未进入世界文学经典的重要原因。在2006—2015年的MLA经典文章的索引条目中,张爱玲被评为次要作者,仅被引用90次,而鲁迅则被评为主要作者,引用达247次[11]。
此外,20世纪50年代美国女性主义思潮迎来高潮。韩素音紧跟社会思潮刻画出一批独立自主的新型女性形象。如在《无鸟的夏天》中拥有独立人格的助产士人物群像就契合了美国女性主义风潮。而张爱玲的The Golden Cangue中的女性人物更具思辨性,七巧兼具受害者与压迫者双重身份,是“现实狡猾的求生存者,而不是用来祭祀的活牌位”[12]。而这种卑微求生者的形象自然不符合当时美国女性主义思潮下流行的大胆离开家庭的英雄女性形象。林语堂是能兼顾中西文化、突出中国文化形象的译者,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国吾民》)中,他将中国哲学、宗教思想融合一体,从性格、心灵、思想、生活等方面表现中国人的生活情趣和闲适哲学。林语堂对经典儒学和抒情文本的译著满足了世界大战后西方人的精神需求。敏锐的读者意识、出版商的准确定位,使其作品在海外广泛传播。反观张爱玲,其作品从选材、人物形象、翻译策略来看,均不符合西方市场的阅读期待。曾有西方编辑认为:“所有的人物都令人起反感。我们曾经出过几部日本小说,都是微妙的,不像这样squalid。”[13]张爱玲作品文字艰深、人际关系复杂以及用词陌生化,往往让西方读者难以捉摸作者之意,这些负面因素使张爱玲作品在西方世界的流传受阻。
三、结语
张爱玲在《金锁记》自译本The Golden Cangue中坚持异化策略,保留原作的中国文学特色,无论是文本选择还是对文化负载词的处理,都体现了其“渲染东方色彩为主、兼顾英语读者接受为辅”的译作理念,对西方读者固有的价值观和阅读习惯施加了民族偏差压力。张爱玲曾这样描述自己的译作理念:“我一向有个感觉,对东方特别喜爱的人,他们所喜欢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13] 而此种翻译理念并不能让作品真正“走出去”。当时的英语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译介尚处于萌芽阶段,“还没有形成一支较强、较成熟的译介队伍,更缺乏一个接受中国文学文化的较成熟的接受群体”[14]。面对“文化缺省”的难题,The Golden Cangue中以“我为中心”的翻译思想难以融入目的语文化语境,海外传播速度迟缓反而阻塞两国文化交流与传播。译者翻译时应适当投其所好,“不能只基于我们自身的文化传播需要,还得关注接受方的需要。只有关注接受方那里真正需要的东西,才能真正地‘走进去并开花结果”[15]。
参考文献
[1] 张爱玲.流言[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2] 张爱玲.传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3] Lau L S M,Hsia C T,Lee L O F .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las,1919—1949[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1.
[4] 包岩.青色极简史[M].北京: 现代出版社,2022.
[5] 黎昌抱.英汉亲属称谓词国俗差异研究[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1(2).
[6] 许钧.译者、读者与阅读空间[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6(1).
[7] 张爱玲.张爱玲往来书信集:纸短情长[M].台北:皇冠出版社,2020.
[8] Chang E.Love in the Fallen City[M].KingsburyK S,translated.New York: New York review books,2007.
[9] 谢天振.换个视角看翻译——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谈起[J].东方翻译,2013(1).
[10] Sciban S. Eileen Chang's “Love in the Fallen City”:translation and anaylsis[D]. Edmonton:University of Alberta,1985.
[11] Hoyan H F C.“Include Me Out”:Reading Eileen Chang as a World Literature Author[J]. Ex-position,2019(41).
[12] 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M].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13] 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
[14] 谢天振.历史的启示——从中西翻译史看当前的文化外译问题[J].东方翻译,2017(2).
[15] 梁新军.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困境与出路——《国家译介行为论:英文版〈中国文学〉的翻译、出版与接受》读札 [J].中国比较文学,2023(2).
(特约编辑 刘梦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