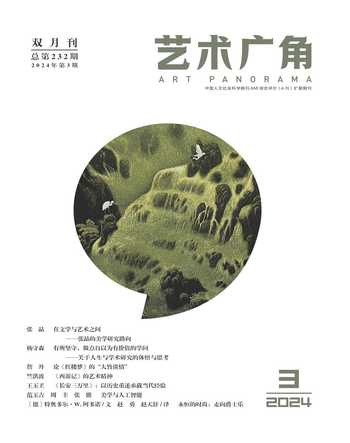《长安三万里》:以历史重述承载当代经验
摘 要 2023年的国产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以回望盛唐的怀旧姿态重写诗人李白与高适的人生历程,作品中存在三重错位:盛唐既是延绵至今的民族自豪感来源,也是一个永远无法回归的怀旧乌托邦;从盛唐到安史之乱的王朝兴衰,与诗人们的人生顺逆并不同步;高蹈出尘的诗仙李白,与汲汲于世功的俗人李白两个形象同时并存。这三重错位为《长安三万里》带来广阔的表意空间,也凸显出今日中国的文化症候——对可能性的怀旧向往与对确定性的现世追求悖论般地并存于我们的时代。
关键词 动画;唐诗;李白;高适
一、回望盛唐:挽歌与赞歌的并行
2023年暑期上映的国产动画《长安三万里》以高适和李白相互交织的人生故事,揭开安史之乱前后,大唐长安的诗意空间。动画中的大唐美得恣意张扬,不负盛世之名。美人舟上拓枝舞,巾帼月下剑生风,胡姬酒肆连诗句,进士探花赠佳人。唯美而恢宏的镜头带着抒情性的节奏,将每一个中国人自牙牙学语时便熟读背诵的唐诗中得来的盛唐一梦化作银幕里的虚拟现实。故事中的高适与李白也都是盛唐哺育的诗人,有着独属于盛唐的强健体魄与诗意灵魂。两人陌路初遇,就携手击杀盗马贼,高适一杆银枪救了李白一命,从此相伴而行,成至交好友。他们文能提笔赋诗,武能上马杀敌,与后世想象中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截然不同。王维、岑参、王昌龄等盛唐诗人亦带着他们的名篇佳作悉数登场,复现出那个“人人都会写诗”的传奇时代中“斗酒诗百篇”的热闹场面。动画中的人物形象设计参考了教科书中常用的诗人画像,以及唐代绘画作品中的身形和服饰,力求唤醒观众的亲切感与熟稔,让他们相信作品中呈现的,就是自己在教科书上见过、在背诵《唐诗三百首》时想象过的盛唐人物与盛世长安。
故事是由安史之乱后的高适回忆、讲述的,带着对一去不返的开元盛世的无限追怀。曾经把酒言欢的诗人们如今或身死战乱、或潦倒飘零,一代诗人的落幕与盛世的终结相互印证,显得格外悲凉。
以中晚唐的回溯性视角遥望盛唐,是叙事的通例,似乎不如此,便不能见盛唐之盛。陈凯歌导演的电影《妖猫传》中的主人公白乐天以出生于代宗大历年间的诗人白居易为原型,以一起牵扯到三十年前杨贵妃之死的妖猫案为主线,在藩镇割据的中唐聆听盛唐余响。白乐天带着一身不合时宜的盛唐之气,举止狷狂、情感丰沛,像一个生错了年代的落寞灵魂。白乐天对寻访盛唐的执念,毫不亚于少年白龙对杨贵妃三十年不肯醒的痴梦。但他只能在杂草丛生的荒屋中搜索陈年旧迹,在幻术中看一眼太液池曾经的金碧辉煌、人声鼎沸。在这场幻术中,不断变换位置的摄影机如同白乐天贪婪的回望之眸,尽情掠取“开元天宝盛长安”最恢宏壮丽的风华而不知餍足,不肯为具体的一人、一事而片刻聚焦、流连。盛世风流云散,只留无限遗恨蜷曲于妖猫诡异而逼仄的身躯中,引人怅惘。
网络游戏《剑侠情缘网络版叁》(以下简称《剑网三》)2013年的资料片“安史之乱”给玩家带来的震撼与《长安三万里》所要达成的效果更加接近。《剑网三》的主线故事始于大唐天宝四载,这一年杨玉环被封为杨贵妃,安禄山奉诏入朝面圣。在游戏中,长安是三大主城之一,玩家常常要在这里进行物品交易、完成日常任务等,是许多玩家最熟悉的游戏区域。“安史之乱”资料片更新后,主城长安骤然变成了战乱长安,曾经井井有条的街市、商客云来的店铺、巍峨富丽的殿堂宫宇都残破颓败,玩家能在这里接到的任务大多变成了救济灾民、收集物资、击杀流寇兵匪、搬运伤员与尸体。玩家在逐个完成这些任务的过程中,回想“老长安”的和平与热闹,便尤为深刻地感受到“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王朝兴衰之叹自古便是诗词文赋中的常见主题,但这些诞生于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以来的作品不约而同地以回望的视角抒写盛唐,与其说是在延续兴衰之叹,倒不如说是借故事中人物之口,表达着今人的怀旧乡愁。自2015年前后起,从“民国热”到一批“70后”“80后”导演拍摄的伤痛青春片中的青春怀旧,再到“东北文艺复兴”所引发的对20世纪90年代的集体回忆与“港风热”,“怀旧”始终是流行文艺的重要主题。怀旧故事混杂着对同时代个体间相似童年经验的追忆,以及对过往历史时代的回溯性重构。相比于历史细节之真实,怀旧故事总是更重视当下情绪之真实,那些被当下所召唤的历史时空,往往被建构为开放的、传奇性的、充满各种历史可能性的激动人心的时刻,而叙事者总是一个怀旧的后世灵魂,在对过去的向往中包裹着一点难以言说的遗憾和落寞。
《长安三万里》的盛唐叙事亦当如是观,追忆盛唐的并非安史之乱后的高适,而是今日的创作者与观众。取自明代诗人陈子龙诗句的标题“长安三万里”实际上已经悄悄拉远了追忆者与盛唐的历史距离,故事中的高适在风雪边塞叙说盛唐一代诗人命运时,言辞也不似当世之言,倒更像后世断语。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在一定程度上冷却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的民族主义高热,贫穷青年白手起家成商业巨擘的商业传奇似乎也已远去,人们逐渐适应社会发展“新常态”。上升通道的窄化压缩了人生的机遇与可能,未来似乎不再那么充满诱惑力,人们回望过去,追怀已然逝去的辉煌与未曾被开启的可能,在文艺作品中一遍遍地梦回长安。
但当《长安三万里》聚焦于我们烂熟于心的盛唐诗歌,当故事终章高适说出那句“诗在,长安就在”,故事里的长安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复兴这一时代议题的典型意象,在观众那里,它不可避免地召唤出对于中国文化传承的民族自豪感,于是崛起中的当代中国又成为盛唐的延续。盛唐既是往事不可追,又是精魂今犹在,这两重彼此矛盾的情感投射框定了《长安三万里》的表意空间:是挽歌亦是赞歌;是叹不能躬逢盛事,亦是身处其中、与有荣焉。或许这也就是为什么,《长安三万里》没有像《妖猫传》那样彻底选择一个到中唐才出生的主人公,而是选择了生于盛唐的高适来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
二、历史书写:时代与人生的交错
《长安三万里》中,李白与高适持续一生的人生交集几乎总是以十年为单位,分离是常态,相聚的次数屈指可数。这固然是对没有飞机与手机的时代,四处游历的诗人们真实交游状态的展现,同时也是创作者有意剪裁的结果。两人的每次相聚都标志着上一个人生阶段的结束和下一个人生阶段的开启,不同的人生状态与生命感悟,在每一个重逢时刻得到集中表达。由此,作品不再聚焦于某个具体事件中的风云际会和人物决断,而是将目光投向数十年间两位诗人的命运流变。
高适与李白都有着盛唐所孕育的灵魂,但他们的人生轨迹却并未与盛唐同命运。他们都没能于盛唐一展抱负、在政治领域成就事功。出场时踌躇满志的李白,初出茅庐便受了打击,出身商贾之家的他不仅无缘科举,亦在行卷时被拒之门外;后虽因诗名而供奉翰林,但也并不被重用。高适的入仕之路同样坎坷,甚至勉强以杀人之枪作娱人之舞,委曲求全至此,依然未能得玉真公主青眼;后得哥舒翰赏识,也只能入幕为掌书记,仍无法实现上阵杀敌的夙愿。作品还虚构了一个裴旻将军之女裴十二,剑法独得裴家真传,却只因是女儿身便无法建功立业。繁华而开放的盛唐,似乎对他们格外吝啬,在他们身上,显现出保守而僵硬的一面。
李白与高适、杜甫、丹丘生、岑夫子等人在水边饮酒,作《将进酒》的场景,是《长安三万里》的一出重头戏,伴随着慷慨激昂的吟诵,画面逐渐从人间上升至天阙,众人乘鲲鹏直上云霄,俯瞰银河,与白玉京仙家共饮。尽管整段情节在画面表现上略显生涩,鲲鹏、仙人等传统意象在具象化时显得有点“中西合璧”、不够地道,但仍有着不错的感染力。相比于画面表现,或许这一段落更出色之处,在于道出了《将进酒》的豪迈与浪漫背后,无尽的落寞与失意。“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旷达底下,是怀才不遇的不甘与悲愤;“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亦不过是断念于仕途时的自我安慰。李白最好的诗,总写于他人生失意的中途。
高适则要到知天命之年,才入河西幕府;待安史之乱爆发,山河破碎、盛唐终焉,玄宗西逃、永王叛乱,才有了施展拳脚的机会。他出任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出兵讨伐永王,此后一直颇受重用。在《旧唐书》中得到“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的评价。
国家不幸诗家幸、一将功成万骨枯,李白与高适相互交错的人生命途,与唐王朝之兴衰构成微妙的错位。或许恰恰是因为《长安三万里》中的盛唐,既是对已经逝去的理想盛世的追怀与想象,也寄寓着对今日中国的观照与期许,所以如此美好又如此充满遗憾,所以故事中的个体经历才如此与家国命运密切相关却又与历史盛衰微妙错位。《长安三万里》有意识地通过情节与人物提供了这些彼此矛盾的情绪与思考,体现出国产动画电影中少见的复杂性。
全长168分钟的影片是一段节奏整严但意指崎岖的旅程,并没有任何一种明确的主题或立场可以统摄全篇。少年意气与中年蹉跎、满腔豪情与壮志难酬,所有的人生得失都在高适老迈而沧桑的讲述中酝酿成厚重却又缥缈的人生况味。随后情节一转,高适卸下奄奄一息的伪装,变为老骥伏枥依然志在千里的威风将军,千里奔袭、奠定胜局。李白也因高适请托郭子仪代为求情而得到赦免,一叶轻舟过白帝城时依然像少年一样自由而畅快。似乎故事就将收束在这个虽然世事艰难,可毕竟天道酬勤的高昂情绪中。但高适的独白再次使行动转入沉思,藩镇之乱中的大唐依然前路难明,一场胜利并不能扭转历史的走向,在漫长的时间之流中似乎个人的一生功业都显得无足轻重。功成名就的快意蒙上虚无的阴影,被蹉跎的岁月又似乎染上诗意;高适最看重的是手中的枪,流传于世的却是笔下的诗;“诗在,长安就在”终究意味着,除了诗,没有什么能超脱岁月的束缚成为永恒。
不以历史之沧桑否定短暂人生的精彩与超越性力量,却也不赋予英雄人物改写历史走向的超能力;肯定个体身上不可磨灭的时代印记,却又不使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简单同构。事功或诗情,一意进取或纵情欢乐,《长安三万里》并不决然地肯定什么或否定什么,或者说它对这一切的评价都显出一种有意为之的含混和暧昧。这种观影经验与读史颇为相似,事件的连缀看似随意且充满偶然,其实已然经由史家或创作者之手划定了潜在的表意空间。它邀请每一位观者携带独属于自己的当下经验卷入精心剪裁之后的关于前人旧事的片语只言,做出判断,并完成独属于自己的意义重组。
对于国产动画电影而言,这种对观众的信任更显得难能可贵。它或许意味着国产商业动画电影正在摆脱动画是专属于儿童的艺术形式的刻板印象,摆脱以直白台词解释作品主题、以密集的喜剧情节和动作戏吸引观众注意力的创作惯例,重新寻找作者个人表达与大众喜闻乐见之间的平衡点。
三、重写高适:“考公人”与“做题家”的历史化身
《长安三万里》的叙事有意模仿了史书的节奏与笔调,但并非真的严格遵照史实创作故事,也并未沿用最通行、最大众化的历史叙事逻辑与历史评价。李白与高适的形象,都渗透着当代人的历史想象和现实经验。
作品选取了高适,而非观众更加熟悉的李白为第一主人公和故事的讲述者。李白救郭子仪的故事变作李白与高适同救郭子仪,后来郭子仪为李白求情则改为高适暗中写信请郭子仪为李白求情;松州之战战胜吐蕃的主要功臣也从严武变作高适。这些对史实的改写,增加了李白与高适的交集,但体现出的高适人物形象倒并不与历史记载有太大龃龉。
作品对高适的最大改写,在于性格刻画。故事中的高适勤奋刻苦、重信守诺、不善言辞、果敢仁义,颇有些“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君子之风,与李白的浪漫恣意“不着调”恰成对照。但据历史文献记载,时人对高适的评价却并非如此。电影中反复出现的诗集《河岳英灵集》评价高适“性拓落,不拘小节,耻预常科”,《旧唐书》中说他“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然言过其术,为大臣所轻”。
这个不拘小节、不屑于以常规科举途径入仕、喜欢侃侃而谈王霸大略却又常常言过其术的高适,显然不是电影中那个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实干家。但电影中的高适形象却又是最容易被当代观众理解的。踏实、努力、可靠、重事功,尊重世间的秩序规矩与常情常理,肯从基层做起,走正途、不放纵,亦能在不挑战底线的事情上变通妥协。对于和平安稳但经济增速放缓的当下社会而言,这样的人生选择是最安全、最稳妥的。当稳定与否成为人们未来规划中的重要考量,“做题家”与“考公人”人格就有了无与伦比的正当性。
这表现出与2013年陈可辛导演的电影《中国合伙人》截然不同的气质。在《中国合伙人》中,天地无限广阔,哪怕是一穷二白的平民青年,只要敢闯敢拼,就能拥有无限可能。但在《长安三万里》中,相比于可能性,高适更渴望确定性,充满不确定性的宦游生活不如家乡的耕读日常更令人安心,安史之乱固然是他人生中的重大机遇,但他对这一机遇态度暧昧。类似的叙事变迁在当代流行文艺中普遍存在,比如今天仙侠剧中的主人公,往往不再是李逍遥(《仙剑奇侠传1》)那样彻头彻尾的草根少年,而是生来拥有高贵血脉和无匹神力的神君。赤裸降生的李逍遥固然拥有无穷的可能,神君也固然要被传统、血脉与责任所束缚,但传统、血脉与责任是束缚也是保障,神君们活得总比李逍遥更“安全”。
人们一方面在回望盛唐的故事中,被那个充满无穷可能性的时代所感召,另一方面又极端抗拒缺乏确定性的现世人生。就如同概率科学讨论一切“可能的情况”,但任何一种“可能的情况”都与现实无关;当代流行文艺中的“无限可能”也不过是一种不指涉现实的“理念实体”,[1]并因此具有审美能量,一旦它触达具体的现实人生,就迅速变质为匮乏的噩梦。在《长安三万里》中,作为背景环境的盛唐长安可以拥有无限可能,供人遥想、缅怀、赞叹,但方便观众带入的男主人公高适却必须拥有一个追求确定性的“考公人”人格,才能被理解、认同、喜爱。
创作者让这样一个适应于今日社会的高适在安史之乱的大变局中仍能抓住机遇,成为盛唐诗人功业最卓著者,无疑暗合于当代观众的成功学逻辑,满足了观众对于商业片叙事之“爽”的需求。
四、诗仙在世:历史与当下的互动
在《长安三万里》中,李白是高适的反面,他同样追求政治上的成功,但太过理想主义,恃才傲物,不拘小节,行事过分张扬随性,睥睨世俗,缺乏真正的政治眼光,稍有不满便纵酒以自昏秽。作为一个诗人,他的天真是他的天赋;但作为一个求功名者,他的幼稚是他的致命弱点。尽管《长安三万里》中的一些地方存在突然跳转到上帝视角或李白视角的叙事瑕疵,但整体来讲整部作品都是固定使用高适的视角来讲故事的。因而高适的形象和人生故事是连贯的,人物逻辑是流畅的。但李白的经历总是以碎片化的方式呈现,观众能看到的,只是高适眼中的李白,而这数十年间,高适与李白总是聚少离多。碎片化的李白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李白,或者说,通过将李白的故事讲述为一系列并不连贯的碎片,作品试图掩盖故事中的李白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李白形象的拼合体这一事实。
一方面,李白是观众从小便熟悉、崇拜的诗仙李太白,他的恃才放旷、荒诞不经皆是因为他天生与众不同,有着不世的诗才与最浪漫不拘的灵魂,他的纵酒与欢歌皆是美的、纯粹的,不染凡俗尘埃。另一方面,李白又是一个汲汲于事功而在政治上幼稚愚蠢的俗人,浮躁、任性、眼高于顶,他与诗人们的宴饮酬唱充满了浮夸而矫情的互相吹捧,像极了今天种种推不脱、逃不掉的商业应酬,让“正经人”高适频频皱眉。李白会入赘,也会摧眉折腰事权贵,给永王大写赞歌,只是终究不得其法,故而一事无成。挺着啤酒肚、喝得醉醺醺的李白,着实俗得不像一位谪仙,一点都不浪漫。
《长安三万里》对历史的文学性重述实际上包含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出于文学性考量,对史实进行直接修改,比如让高适参与李白救郭子仪的历史事件,这就是纯粹的艺术虚构,围绕《长安三万里》所产生的争议也往往在这一层面展开;另一个维度或许更为重要,那就是基于不同的观念和经验,对相同的史实做出不同的历史解释。克罗齐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强调“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观点,提出“当代史固然是直接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被称为非当代史的历史也是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因为,显而易见,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的”。[1]这一观点提示我们,任何历史解释都有其不可避免的当代性和主观性,而且这种当代性和主观性并非纯粹的“错误”或“冗余”,这种历史研究中贯穿的现实的精神生活,恰恰是历史研究的重要价值所在。在文学性的历史叙事中,对于史观的自觉选择更显得尤为重要,决定着作品关涉现实的方式与程度。
按照中小学文史课程中的一般讲述,诗仙李白是中国古代最伟大、成就最高的浪漫主义诗人。这是按照西方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文学流派、文学思潮概念,创造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叙事框架,并在这一能够与西方对接的文学史讲述中,塑造中国古典时代的文化英雄,证明中国古典文学拥有不输于任何民族与文明的伟大成就。而实际上李白的“浪漫主义”当然不是雪莱或华兹华斯的“浪漫主义”,“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终究只是一种具有当代意义的历史叙事,而不是过去曾经发生过的现实本身。为了在大众普及教育中完成这种历史叙事,李白的形象被或多或少地按照“浪漫主义”的标准提纯了,相比于他对仕途的热望,人们更热衷于讲述他令高力士脱靴的狂放高傲与蔑视权贵;相比于他的婚姻与家庭生活,人们更津津乐道他与诗人杜甫的结识与交游。
诗仙李白的浪漫形象实在过于深入人心,无论如何也无法舍弃。但与此同时,当循规蹈矩的高适成为最理所当然的正面主人公,这个时代实际上已经很难再去想象一位诗仙李白,很难为他的人生选择提供正当性——像李白那样活着是错误的,这是一个不能明言的时代共识。于是,《长安三万里》提供了另外一个关于李白的历史叙事,一个更具当下视角、更符合日常经验、更加世俗化的李白形象。正如新历史主义小说诞生于对革命历史小说的不满,同时关联着新时期以来意识形态的松动;挺着啤酒肚的世俗李白也诞生于对诗仙李白的厌倦,同时关联着对纯粹崇高的质疑。在《长安三万里》中世俗李白与诗仙李白这两种对立的历史叙事不断争夺着故事的主导权。
如果说历史兴衰与个体命运的错位是《长安三万里》的亮点,那么两种李白形象的扞格便是作品的症候。“90后”以降的当代中国青年一代,是兼具“宏大叙事尴尬症”与“宏大叙事稀缺症”的一代,这构成影响当前流行文化叙事形态的重要前提。一方面,他们并未走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解崇高”的文学倾向,面对完全正面的历史故事与纯粹崇高的历史人物时,会有一种因袭而来的不适与怀疑;另一方面,由于这一文学倾向在他们实际成长起来的历史时期中已基本不再具有反抗性的意义,所以他们对于文艺作品中宏大叙事缺位的切身经验又造就了对纯粹崇高的渴望。在这一意义上,世俗李白与诗仙李白缺一不可。对于诗仙李白宏伟诗句的极尽描摹,勾连起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有效抚慰“宏大叙事稀缺症”;而世俗李白时时戳破诗仙李白的光环,则是应对“宏大叙事尴尬症”的良方。只不过这双重李白本该以更加连贯顺畅的方式在作品中得到呈现,《长安三万里》中如此明显的断裂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高适是统合的,而李白是分裂的,观众可以毫无顾虑地认同高适,但面对李白时却有着又憧憬羡慕、又避之唯恐不及的复杂心情——就如同故事中的高适总在期待与李白重逢,每次相见又总是匆匆失望离场。故事中的长安终究不是盛唐的长安,而是今日中国的镜像;每一个人物身上负载的,终究不是历史的真实,而是今人的想象,在想象的极限处,断裂便显现出来。
好在《长安三万里》并没有真的像寻常升级爽文那样,让高适一路顺风顺水、走上人生巅峰。即便在他显达之时,也仍有颇多艰难和不得已。或许高适也曾在人生沉浮的尽头扪心自问,这样的活法是否就是最好的活法、唯一的正途?又或者,千年之后,当盛唐长安只在诗中留存,他曾拥有的一切是否真的那么重要?历史的沧桑与轻微的虚无感冲淡了做出价值评判的紧迫性,这使得李白的分裂尚能在故事的框架之中被容宥,也使得李白不仅承担了反衬高适正面形象的作用,还有可能成为反思高适人生选择的参照系。
五、结语
“梦到长安三万里,海风吹断碛西头。”长安三万里,是诗人们的事功之志与政治现实之间的距离,是诗与史的距离,也是今与古的距离。河图演唱的网络古风歌曲《不见长安》有这样的歌词:
我忽然开始疯狂想念 故事里的长安
我日夜兼程跋山涉水 山水路漫漫
……
我渐渐开始每晚梦到 故事里的长安
长安城有人歌诗三百 歌尽了悲欢
……
这重重楼阁浩浩殿堂 都不是我想象
我心中曾有画卷一幅 画着它模样
无论是“故事中的长安”“画卷中的长安”还是“梦中的长安”都是诗的长安,而非真实的长安。诗中长安是幻想与现实的交叠,是在不同的时代一遍遍吟诵同一个名字,却向其中灌注不同的具身经验和问题意识。
《长安三万里》写就的,是属于今人的诗中长安,带着独属于今天的浪漫与局促、骄傲与忧思;既是对时代症候的无意识显影,亦是带着今天的问题意识向历史寻找启迪。《长安三万里》并不完美,特别是或许未能找到最适宜的视觉形式,3D形象不够“中国”,水墨2D场景又失之过简。但在这个人人都迫切地寻求人生答案的充满焦虑的社会中,《长安三万里》却有意识地容纳了暧昧、复杂与矛盾,有意识地放弃设置故事的唯一正解——又或者没有答案,未尝不是一种回答。
【作者简介】
王玉玊: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任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