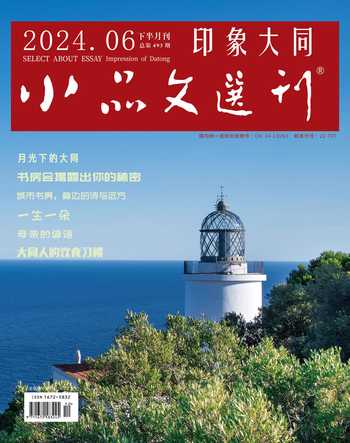坐享其成
大漠

姑父没文化,他狡辩的功夫无人能敌,一犯起浑来,村干部都躲着他,用当地的话说“穷横穷横的”。就因为他能干一手好活,别人干不了的他都能做到极致。
我从哈尔滨到海城车站再见到他时,他还是壮汉。下半夜赶着毛驴车来城里接我,飞也似的颠簸在从城里到乡村的搓衣板路上,把我的胃都快从嘴里颠出来。夜幕沿着风的方向流动,到了柳镇村口才听见了第一声不知谁家的公鸡撕裂般的鸣叫。
天亮我才注意到,院有两个猪圈,石头墙。肉猪四五只单独一房,两只母猪在另一个大圈间隔着,各搂着一窝猪崽子,猪崽子们在母猪肚子底下撕纽扣。
黄狗拴着绳子,瞪着眼睛看着对面干草垛边的三只奶羊和溜达鸡,溜达鸭。被虫嗑掉的青枣东一个西一个散落在地上,馈赠给蚂蚁啃食。蟋蟀在阴凉瓦砾处细声细气地叫着,有几垄草莓七扭八歪,青的纷纷探出头,红的已经熟透。只有那挂驴车静静地吊着驴套躺在那,像一个打盹的老人。
猪圈矮墙堆着松塔,树轱辘,木头柈子。一排柳树杉树十几年前栽的,有碗口粗。等大小,二小俩儿子将来结婚盖房子就地取材,大梁椽子檩子都有了,勤快人家都这样大院门前栽树,院里种菜,剪枝拔尖,伺弄的茂盛翠绿。
我与姑姑、姑父有着不一样的情感,据母亲说,我出生时正值母亲在生产队当队长,没有奶水,姑姑正好大我几个月生下大女儿小凤,于是怀里抱俩吃奶,吃不饱时姑父每人再喂些糊糊,就这样来内蒙古前我是他们喂活的。
一家人除了忙乎大田作物,院子自留地果树蔬菜家禽,厢房里有台扎草袋子机和一堆农具,孩子放学回来,谁闲了吃饭之前再编一摞草袋子,够五百个到家里来收一次,挣点现钱补贴家用。二小不到十岁,负责放羊,这小子鬼精,偷偷把奶羊放到生产队玉米地里,吃玉米吃黄豆秧子,吃饱了,回来挤两盆奶,全喂小猪崽子,补充羊奶的小猪长得飞快,圆咕噜滚儿,二十几只小猪个把月到大集上能卖上几个好钱。
说白了,人每天所有的劳作都是为了糊口,凡是长嘴的都要吃食。猪羊鸡鸭鹅狗哪个不喂饱哪个都叫唤个没完。西边有一片公社的大田开阔地,收完麦子麦茬还在地里杵着。不知谁造谣,说从长白山有一个白须老头,也有人说是白狐仙,一路跟踪到大柳树下不见了。当地人很迷信,于是一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十里八乡的村民,沈阳,海城,鞍山的城里人有开车的,有坐火车的,陆陆续续拿着贡品到大柳树下空地,跪地祭拜,求仙人赐药治病。折柳取叶,风尘泥沙称之为天降灵药。树枝上挂满了红布条,村里立刻有人卖贡品,卖红布条的。远远望去火树飞花。天蒙蒙亮就一排一排人跪地烧香,烧的遍地狼烟,贡品到处都是。
灵不灵验,天知地知。
姑父家在村子最西头,从后墙篱笆门就能看到,一览无余。白天踩点,夜里九点以后等人散去,姑父一家开始套驴车,大筐小筐,麻袋,全员出动。姑父说“扯犊鳖子的人啥时候都有,仙人吃不了,扔在野地里糟蹋粮食,犯罪啊”,于是每到夜晚,一车一车地往回拉,让猪驴牲畜可劲造,啃水果,啃馒头,直到累的牙痛,哼哼唧唧睡去。所有的泔水缸里都泡满了,满院子晒。福兮祸兮,管不了那么多,就不信那个邪。
世上的怪事多的去了,你信它就在你心里折腾,不信啥也不是。姑父属于天老大地老二,爱谁谁。家里院里照顾好,老婆孩子为中心,外面蛮横不讲理,有便宜占就行。下了场院,去给驴割草,顺便在养鱼池塘顺两条鱼,一根稻草穿透鱼嘴,挂在铁锹上,扛回家。
在社里粉条厂,把一捆子没晒好的粉条,围在腰间,小布衫一搭,回家猪肉炖粉条,酸菜血肠是他的拿手菜。
到了上秋,做小豆切糕,赶着毛驴车挨个村庄卖。倒腾粮食,这个换那个,那个换这个,没人知道他的弯弯肠子,究竟怎么绕成弯弯绕。
1975年东北海城大地震,我父母心急如焚,寄了衣物和钱,姑父来过一次内蒙,之后通讯也是断断续续,一直到渺无音讯,岁月和时间都老了。
选自“阵地”
- 小品文选刊·印象大同的其它文章
- 你需要什么话来“励志”
- 书房会揭露出你的秘密
- 校出一个错字
- 如何让孩子放下手机捧起书籍?
- 君子
- 一生一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