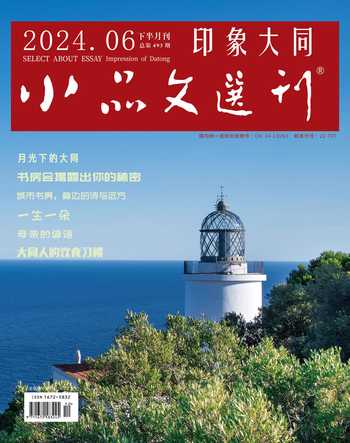一生一朵
苇杭

甫开眼,透过风痕雨迹的玻璃窗,辄见美丽的白云天——说庸常也庸常、说神奇也神奇,随你怎么想:开启这平凡而又平常的一天,坐拥24小时的“豪奢”。这在天文学上有个别致的叫法,“一个太阳日”。真是令人耳目一新,仿若与太阳肩并肩。可否就此得寸进尺,把这海波也似的青空、悠悠往复的白云,作为这个“太阳日”热情迎接我的前导队?——脑回路果然比较清奇,与阿Q有得一拼,遂得大欢喜。一骨碌从榻上爬起,打开窗,与晨风撞了个满怀。风中有庭树、秋花的露气烟光,点缀以珍珠、碎钻也似的虫鸣鸟唱——世界还可以比这再好一点吗?
无限时空中,所谓漫长的人类史,较之天地日月、河流山川,也无非是电光石火;而饱经沧桑的人世百年,置于历史长河,无疑又是沧海一粟、蜉蝣天地。遂令人愈发珍视眼前的一切:一缕扑面的清风、一片芳草地、一角白云天;衡门之下可栖迟,手中一卷,夜眠七尺,乌黑的漆碗里沏着白月亮;早起灶间的紫砂煲“炊金煮玉”,玉米金黄,稻谷流脂,一粥一饭,烟火人间……桩桩件件,都是充满平和喜乐的“小确幸”。
不是一大早就发神经,而是昨天去了墓园扫墓,再一次直面生死,便有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大悲大喜及“潮汐”过后的沉静与反思。
毕竟,中元节近了。
墓里的先人,是我家先生的祖父母,我未曾谋面的祖公祖婆。肃立,行礼,相当于向长辈请安,问好。擦拭墓碑上的灰尘,亦等同于为老人“洒扫庭除”。而后,摆好供果,恭恭敬敬上一炷香。
祭如在。
一直阴沉的天,飘起雨来。
在墓前撑起伞,注视着雨伞下的香火。
香火暗红。一会儿,香灰就寸许长。香烟袅袅,先是笔直,随着香灰无声地“坍塌”,香烟也改了“路径”,四散而去。
二人轮番执伞,倾着身子,遮着祭台,直到一炷香燃烬。
不知不觉间,如丝如缕的小雨,停了。
收了伞,视线从祭台移开,沿山坡瞭望,但见墓碑林立,亦如城区一栋栋密密麻麻的“鸽子笼”……转身回望对面的青山隐隐碧水迢迢,不知墓中人还能感知云起云飞,暮霭朝晖否……回来的路上,想起远在故土父母的坟茔,不知弟弟哪天去祭扫……到家后,便微信他。反馈道,早几日就去了,一切安好,勿念……然后告知今日刚刚送走二姨家的表弟天贵儿,才进屋一小会儿云云……
一下子,我便愣在那儿了!
天贵儿刚刚四十出头的年纪,病了也就一年多的光景……虽然晓得这病的凶险,凶多吉少,但听到噩耗还是吓了一跳……想起与表弟的最后一面,还是两年前的春天,在母亲的葬礼上。那时,他看起来还很健康,跑前跑后,没少帮忙。其后不久就听说病了,在北京做的手术。费用自然是一大把,好在二姨家的兄弟姊妹多,平时也很抱团,遇事相互照拂,大家出手好歹凑够了手术费。我虽未曾到京或回乡探视,也微信转去了一点心意,以示慰安。……孰料转瞬间,就轮到送别正值壮年的他了……真是人生苦短,世事无常,素日司空见惯的一切,随时随地都可能成为永诀。譬如,今早的晴空与流云,拂过的叶露与花香,杂乱无章却生机无限的鸟雀喧喧,于刚刚故去如天贵儿者,永不可得……
生命所为何来,如此匆匆忙忙,如时钟的秒针,马不停蹄,日夜兼程,奔向那未知的前途与万古不易之目的地。汉语真是奇妙啊,充满哲思。原来“目的地”,便是“墓的地”。发音完全相同,岂是偶然?
早晨的时光,寸阴寸金,容不得思想的野马自由驰骋。赶紧“勒紧缰绳”,入洗手间盥洗、晨妆。涂护肤水、乳液;眉笔轻拈,淡扫双眉,亦如远山长;旋出唇膏,双唇轻染,亦如樱瓣如玫红如烈焰。生命,是一团火吗?有光有热,我们拿什么来助燃?
疫情以来,单位原则上要求零公交出行,我这公交一族,便改骑共享单车。每日出门,则抱着晨练的心情,迎着日出或风雨,奔驰在车流人海。遂不以为苦。
照例在指定停车点交了车。步行,穿过桥洞,路过临近的小学校。秋风倏来,唰啦啦落了一地干枯的叶子,脚下一阵脆响。遂止步。侧身仰望身旁这一排高大的白杨树。树冠仍是夏日枝繁叶茂的样子,虽未见十分秋意,但足下分明落叶渐多,毕竟处暑已过,白露在望。在寒地冰城,总是率先感知秋的气息。三三两两的小孩子,貌似一年级新生,小脸上罩着大口罩,在背包罗伞的家长悉心护佑下,雀跃着涌入校门。再一次驻足。目送这一波一波的孩子蹦蹦跳跳的小身影,在秋意渐浓的萧瑟里,体味着活泼泼的生之欢乐。
等转过街角,忽见旁侧高高的铁栅栏上爬满牵牛花心形的叶子,枝枝蔓蔓,左盘右旋,沛然而下,如绿色的瀑流,朵朵烟蓝的牵牛花,掩映其中,大好。好到,如孔夫子的“不知老之将至”。这盛开的牵牛花是“不知秋之将至”了,且是寒地的肃杀之秋。掏出手机,左拍,右拍,上拍,下拍,试图留住这刹那芳华。
牵牛花,亦名“朝颜”,这名字未免动诗人愁怀。日本俳句有“牵牛花,一朵深渊色”,说的就是这种烟蓝的牵牛花儿。岛国人的审美总是很独特,如“物哀”、“细柔”、“枝折”、“侘寂”……听听这名色,就如和歌与俳句,携了岛国的缤纷落樱,粉泪簌簌。烟蓝的牵牛花,是一朵——“深渊色”?此刻,我不是正凝视这美得骇人的“深渊”吗?干嘛要凝视呢,是打算跳下去吗,跳下去,则别有洞天,如费长房之追随壶公?
实则,凝视时,我们已不知不觉在其中了。被侵染,被吸附,被旋舞,被塑型……深渊色,美得玄幻,深不可测,如天之蓝,海之深。“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说这话时药山惟俨是面色凝重,还是云淡风轻?
我却只撷了这一朵,“深渊色”。在庚子年初秋这一日。彼此凝视。花非花,我非我;我亦花,花亦我。
没有宋国的漆园吏格调高、口气大。他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而我眼下、手中,就这一朵。那就与这一朵“合而为一”吧。
一生一朵。
日本江户时期的美学家本居宣长说,“知物哀的人,目之所及、耳之所闻,心便有所感,即便是对荣枯盛衰的草木也是如此。”又援引《源氏物语》中的一句话:“秋日到来,令人更加知物哀。”
缘何手中这一朵“朝颜”,而有了寂色?原来“我们最甜美的诗歌,表达的是最悲哀的思绪”,故而“朝颜”有寂色,是面对神放置在人类面前的巨大的沙漏——大自然律动性的、周期性的死亡警示的必然反映。
不知不觉,我用“寂色”,悄悄置换了“深渊色”。
毕竟,一生,一朵。
选自《新散文观察论坛》
- 小品文选刊·印象大同的其它文章
- 你需要什么话来“励志”
- 书房会揭露出你的秘密
- 校出一个错字
- 如何让孩子放下手机捧起书籍?
- 坐享其成
- 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