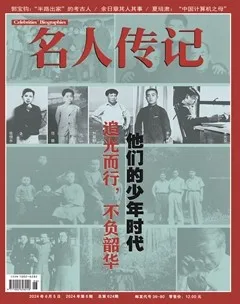张伯苓:炸不毁的南开精神
康艳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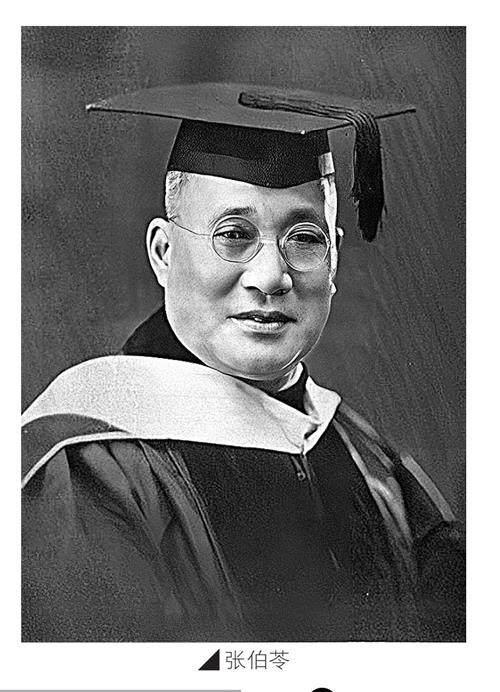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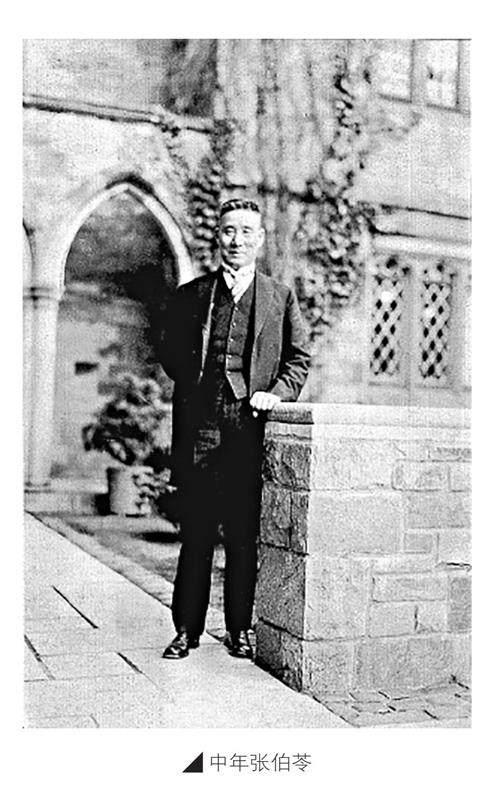
“四十多年以来,我好像一块石头,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向前滚,不敢作片刻停留。南开在最困难的时候,八里台笼罩在愁云惨雾中,甚至每个小树好像在向我哭,我也还咬紧牙关未停一步。一块石头只需不断地滚,至少沾不上苔霉;我深信石头愈滚愈圆,路也愈走愈宽的。”这位自比一块石头,不敢作片刻停留的人,就是南开大学的创始人张伯苓。
“你们讨厌得好!”
1927年,针对日本觊觎我国东北的“大陆政策”,身为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苓认识到加深了解与研究东北问题对祖国的重要性,他亲赴东北考察,所到之处无不目睹“日人经营满蒙之精进与野心”。忧心之下,他感慨说:“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博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机。”1928年初,他亲自筹划成立了“满蒙研究会”(后改名为“东北研究会”),三次组织教授和学生到东北实地调查,搜集了大量资料,深入进行东北问题的学术研究工作。张伯苓还专门组织力量编写《东北经济地理》一书,普及东北的相关知识,并将其作为南开的必修课。有人评价说:“这本教材无疑义地是当时国内有关东北地理有限著作之中最好的一部……以扼要的科学知识和大量的统计数字教导学生加深了解何以东北对祖国是那样重要、神圣。”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被日军侵占,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张伯苓召开全体师生大会,当众发表了题为《东北事件与吾人应持之态度》的演讲,慷慨激昂,语重心长,勉励南开学子抱为国奋斗“至死不腐之志,将问题观察透彻,认识清楚,沉着精进,从事准备工作”。他还让人在校园内挂出这样一副对联:“莫自馁,莫因循,多难可以兴邦;要沉着,要强毅,立志必复失土。”不久,“天津抗日救国会”“天津中等以上学校抗日联合会”等群众组织纷纷成立,张伯苓出任领导职位,多次发表演讲,动员社会各界投入抗日救亡。作为南开的校长,他还当众宣布了这样几条规定:凡东北籍的学生,生活费一律减免,学费缓交;凡因战乱而流亡关内的东北大学的学生,南开一律向其敞开大门,以助完成学业。这一期间,他先后接纳了七十八名流亡关内的东北大学生免费借读。
1933年山海关抗战时,张伯苓亲笔写信给前方将士曰“努力杀敌,为国争光”,以鼓励他们继续战斗的决心和意志。之后他又派遣四名师生,携带一千条毛巾、一千块肥皂、三百斤糖果,奔赴前线以示慰劳。
1934年秋,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河北体育场隆重开幕。伴随着雄壮的乐曲,一千多名体育健儿迈着矫健的步伐进入会场,运动员向近三万名观众频频挥手,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当东北选手入场时,南开大学与南开中学的数百名学生面对主席台用手旗打出了“毋忘国耻”“收复失地”等标语,并齐声高唱《努力奋斗之歌》:“众英豪精神焕发,时时不忘山河碎,北方健儿齐努力,收复失地靠自己。”深受鼓舞和感染的观众立刻群情激奋,掌声和口号声此起彼伏。在这爱国热情的浪潮中,大会“嘉宾”——日本驻天津最高长官梅津美治郎再也坐不住了,他向张伯苓提出“抗议”。张伯苓义正词严地回答道:“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爱国活动,这是学生们的自由,外国人无权干涉!”恼羞成怒的梅津美治郎愤而退席。第二天,日本驻华大使也向南京外交部提出“抗议”,南京政府命张伯苓严格约束学生的“轨外行动”。张伯苓不得不将啦啦队队长找来,“严厉”地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你们讨厌!”“你们讨厌得好!”“下回还那么讨厌!”“要更巧妙地讨厌!”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进一步伸向了华北,其在天津的指挥部,就设在距离南开大学、南开中学仅一箭之遥的海光寺。这年的开学典礼上,张伯苓望了望近在咫尺的日军指挥部,满怀激愤地问了三个问题:“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顿时激起全场的一致共鸣,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道:“是!”“爱!”“愿意!”洪亮的声音在秀山堂的大厅中久久回响……
“吃天津萝卜也不消化”
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的抗日爱国行为使其成为日本侵略者的眼中钉、肉中刺,日方开始寻衅恐吓,企图阻止师生们的抗日行为。他们组成各种各样的“参观团”,甚至包括和尚、尼姑在内,跑到校园内肆意捣乱,干扰正常的教学秩序。日本驻军则以军事演习为名,将装甲车开到学校的大门口,把校园当成他们的打靶场。他们还公然宣称:“只要你们取缔抗日,我们就不再来了!”
当看到恐吓行为没有效果后,自1937年7月29日凌晨起,侵华日军悍然对南开大学实施轰炸,日本侵略者以猛烈炮火轰炸各教学楼和师生宿舍,30日又派出飞行第六大队以“九二式五十千瓦弹”轮番轰炸。学校图书馆、南楼教学楼、西楼教师宿舍、学生宿舍及部分校舍被炸毁,校门前的自来水管被炸断,水满弹坑。为达到全部毁灭南开之目的,轰炸后,日方又派出骑兵百余名、汽车数辆,满载煤油,到处放火,南开校内秀山堂、思源堂两处教堂楼、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火光之中,张伯苓半生心血化为一片废墟。
日军在轰炸南开学校后广播说“反日大本营南开学校被毁”。1938年4月号的《亚细亚》月刊也刊登消息:因为南开学校是天津“造成反日情绪与反日活动中心”,所以日方“非炸毁(南开)不可”。
数十年心血毁于一旦,张伯苓并没有被日军的野蛮行径所打垮,他在面对记者采访时慷慨陈词:“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故本人对于此次南开物质上所遭受之损失,绝不挂怀,更当本创校一贯精神,而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
张伯苓的“南开精神”感染了很多人,以至后来老舍和曹禺特意写了一首幽默诙谐的诗歌称颂他:“看这股子劲儿,/哼!这真是股子劲儿!/他永不悲观,永不绝望,/天大的困难,他不皱眉头,/而慢条斯理的横打鼻梁!//就是这股劲儿,/教小日本恨上了他。/哼!小鬼儿们说:‘有这个老头子,/我们吃天津萝卜也不消化!……”
“我早就把他许给国家了”
当抗日烽火燃遍华夏大地之时,南开在校师生中许多人投笔从戎,在杀敌的疆场上“我以我血荐轩辕”。其中就包括张伯苓的第四子张锡祜。张锡祜在父亲抗日爱国思想感召之下,投考了中央航校。1934年,在张锡祜的毕业典礼上,张伯苓代表全体学生家长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勉励中央航校的毕业生要驾驶战机,飞向蓝天,英勇杀敌,保卫家园。毕业后,张锡祜担任空军第二十分队队长及中尉队员,时刻严格训练,为有朝一日奔赴抗日前线而准备着。
1937年1月10日,张锡祜与未婚妻张乐民在南京订婚。刚订完婚,他就接到命令开赴战场。作为中国空军飞行员,张锡祜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保家卫国的战斗。8月2日,他连夜写了一封家书,知道自己这次上战场会凶多吉少,早已做好为国捐躯准备的他,劝慰父亲:“儿昨整理行装,发现二物足以告禀于大人者,其一即去年十月间大人于四川致儿之手谕,其中有引孝经句:‘阵中无勇非孝也!儿虽不敏不能奉双亲以终老,然亦不敢为我中华之罪人!遗臭万年有辱我张氏之门庭!此次出征,生死早置度外,望大人勿以儿之胆量为念!”
得知儿子即将上战场的消息,张伯苓向学生讲话时还兴奋地说:“前几天我接到四儿子的来信……我不因为儿子赴前线作战,凶多吉少而悲伤,我反而觉得非常高兴。这正是中国空军历史上光荣的第一页,但愿他们能把这一页写好!”
8月14日,淞沪抗战的硝烟笼罩着上海。张锡祜驾驶飞机,奉命从江西吉安飞赴南京对日作战。当时气象测报不良,不适宜飞行,但张锡祜报国心切,急于歼敌,冒险飞行,终因天气恶劣,傍晚飞回南昌的途中,在临川上空遇雷雨失事殉国,年仅二十五岁。噩耗传到重庆,张伯苓内心悲痛万分。但他无悔于自己的选择,他对三子张锡祚说:“我早就把他许给国家了,遗憾的是,他还没有给国家立功。”沉默半晌,他又说道:“我本人出身水师,现在老了,我常常以不能杀敌报国为恨。如今我的儿子为国捐躯,我也就没有遗憾了。”
“南开中学是世界近现代史上笃笃实实最爱国的学校”
早在1935年,张伯苓就从日军的恶劣行径中洞察到,平津地区早晚会成为日本的侵略目标,南开也不能幸免。有此“先见之明”的他,为南开寻找到了新的“根据地”——重庆。在重庆郊区沙坪坝,他购买了四百多亩土地,筹建南渝中学(1938年改称重庆南开中学)。
抗战全面爆发后,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张伯苓爱国情怀的言传身教之下,在南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引导之下,南开人始终以爱国为己任,走在抗日战线的前列。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很多南开的同学要求投笔从戎赴陕北投奔革命根据地,张伯苓都会从中予以联络,或者让他们持函去曾家岩五十号或红岩村直接面见周恩来,或者直接写信往陕北推荐:“兹有南开校友杨作舟君原任所得税事务处湖北办事处收发主任,近以国家危急,拟投笔杀敌,赴陕北工作。用特专函介绍,即请酌为委用为荷。”“兹有南开校友罗君沛霖愿到贵军作无线电设计制造及修理工作。……为人聪颖干练,学力极佳。爰驰书介绍希酌予任用是幸。”“兹有南开大学毕业生傅大龄君,曾担任母校物理助教数年,人极诚笃,作事努力。现拟赴陕投效,俾积极参加救国工作。苓特为介绍,即望赐予接洽,并酌量委派工作,是所至盼。”……
抗战胜利后,1947年1月5日,在南京的南开校友为张伯苓一行举办茶话会,南开校友会南京分会召集人、中央通讯社唐际清在致辞中说:“据我所知,抗日战争胜利后,在被立案惩处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是战前南开学校毕业生。虽然这个发现暂时也许不宜公诸报端,但是凡我南开校友理应为此自豪。”3月19日,张伯苓回到天津,南开校友、时任天津市市长杜建时也向张伯苓报喜:平津二市被立案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战前南开毕业生。张伯苓笑答:“这比接受任何勋章都让我高兴。”
南开的毕业生中非但没有一个汉奸,反而出现了众多抗日英雄,对此,世界著名历史学家、美国科学与艺术学院院士何炳棣撰文评价说:“南开中学是世界近现代史上笃笃实实最爱国的学校!”当然,这与校长张伯苓的爱国主义教育密不可分。这位让“日本人吃萝卜也不消化”的校长的南开精神和爱国情怀,广为传颂,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