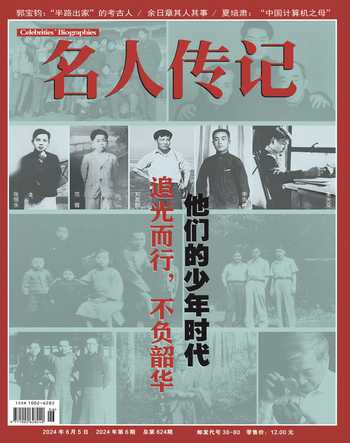费孝通和他的三位外国老师
孙守让



费孝通(1910—2005)是我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主要奠基人。他年轻的时候“转益多师”——求师中国学者,也取法外国学者,这使他不仅懂得中国,而且通晓西方学术,成为一位具有全球视野的学者。
1930年,费孝通由东吴大学医预科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吴文藻凭借其良好的海外关系,积极推行“请进来,派出去”的人才培养方略,邀请国外社会学、人类学名家来华讲学,并连续推荐多名优秀学生到国外留学进修。于是,费孝通获得了跟随外国学者学习的机会。
因祸得福,成为派克的学生
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派克(E.Park,亦作帕克)是费孝通的第一位外国老师。
派克生于1864年,从小生活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镇上。由于当地的教育条件不好,派克十岁时才开始上小学。小时候,派克学习成绩不好,在仅有十三名学生的班级里名列第十。父亲很失望,不准备再让他读书了。倔强的派克愤然离家,靠劳动自食其力。1883年,他考入密歇根大学,曾师从实用主义学者杜威博士。起初,派克想做一名工程师,但杜威的实用主义学说改变了他一生的志趣,他决心成为一名能够了解人的思想和行为的社会人类学家。1898年,已经做了十一年记者的派克放弃记者职业,进入哈佛大学读书。一年后,派克携家人来到德国,并于次年进入德国的一所大学学习社会学。他深入农民之中,深刻了解德国基层民众的基本生活,完成了相关论文。1903年,派克回到美国,在哈佛大学当助教。此后,他结识了美国黑人领袖布克·华盛顿,两人一起完成了若干关于黑人问题的著作。五十岁那年,派克接受著名社会学家托马斯的邀请,进入最早创立社会学系的芝加哥大学工作。1918年之后,随着托马斯学术影响力的消失,派克开始占据社会学芝加哥学派掌门人的位置。
1932年8月,吴文藻邀请派克到燕京大学讲学。原本,费孝通应在1932年夏天毕业,但是那段时间,他受风寒病倒,很快转为肺炎,在医院住院达一个多月。期末考试结束后,学校注册科通知他,尽管他平时各科成绩都非常优秀,但是根据学校的规定,由于他请病假超过了规定的期限,他在整个学年中所修的学分将全部作废,如果要拿毕业证,必须重修一年。这个结局当然是令人非常遗憾的,但是费孝通却因祸得福,正好碰上派克来讲学。派克来燕京大学教书不是临时讲学,而是正式开课,学生学完课程后可以得到学分。作为四年级学生,费孝通选了派克的课,不仅要按时去上课,还要按照老师的要求完成各项作业。
派克是社会学的泰斗级学者,当时已经六十八岁,满头白发,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师生都对他敬仰有加。他在燕京大学开了两门课程:“集合行为”和“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费孝通说,派克的“社会学研究的方法”是大学期间最令他振奋的课程,因为派克在第一堂课上就先声夺人:“在这门课程里我不是来教你们怎样念书,而是教你们怎样写书。”派克的授课,不仅激发了同学们的学术兴趣,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社会学前进的方向。
芝加哥社会学派以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进行研究而著名,学生们走出课堂,投身真实、生动、丰富的现实生活,把整个社会当作实验室。这种“田野作业”的方法在燕大社会学系得到了很好的实施,派克带领学生们到城市贫民窟,到前门外的“八大胡同”,甚至到监狱中调查研究。费孝通第一次在监狱给犯人进行人体测量和观察,看到有的人浑身上下都是黑点,得知那是扎针吸毒的疤痕,感到触目惊心。费孝通回忆说,派克曾对学生们说,要了解中国,老北平平民社会的典型区域——天桥,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点,里面什么都有。在派克的指导下,学生们通过调查研究,写出了《北平的慈善机关》《北平粥厂之研究》《娼妓制度之研究》等多篇高质量的社会调查报告。
派克鼓励同学们要大胆假设,然后用在生活中观察到的事实对假设进行检验,再得出答案。他特别反对早年间在美国乡镇小学里通行的学习方式——死记硬背。也许是知道当时的中国教育也时兴这一套,所以在第一节课上,他就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这种学习方式。派克的教学在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进而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形成了“派克热”。面对派克为他们打开的世界,费孝通领悟到,不是每个人都像自己一样生活,过去自己寄身的生活圈子太小,实际的社会生活开阔得多。
1932年12月,派克结束教学,返回美国,社会学系的师生们在临湖轩为他召开欢送会。离别之际,派克表示希望同学们展开生动活泼的社会学研究,为中国社会学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学生们编辑、出版了一部《派克社会学论文集》送给他做纪念。在这本书的序言中,燕大师生高度评价了派克带来的影响:“我们今日之所以起始追求学问的意义和本相,可说完全是先生所启发的。”派克也写了临别赠言《论中国》,回报燕大师生的盛情和厚意。
四十七年后的1979年4月,费孝通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访美代表团到哈佛大学参访,见到了派克的弟子休斯,两人一起谈了很多关于派克的事情。临别时,休斯将自己撰写的《派克:一个社会学家的传记》一书送给费孝通。晚年,费孝通觉得中国的社会学需要重新补课,于是又认真地复习派克的社会学学说,这部传记也成为他放在案头经常翻阅的著作。费孝通认为,当年学习派克的学说是他一生社会学研究的源头,让他受益无穷,而派克的学说有很强的生命力,重温派克的社会学,对于我们“重建社会学”是非常必要的。20世纪90年代,费孝通撰写的《温习派克社会学札记》在《万象》杂志上连载,在社会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经史禄国引领,开启体质人类学研究
在早年的中国学术界,社会学和人类学是没有明确界限的,学习社会学的同时也应学习人类学。吴文藻在燕大社会学系的学生中挑选了若干名去学习人类学,费孝通便是被选中的学生之一。那时,我国的人类学学科还处于草创阶段,人类学学者极少,但是在燕大隔壁的清华大学却有一位闻名世界的人类学家——俄罗斯人史禄国(Shirokogorov)。
史禄国出生于1887年,1910年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人类学院,回国后在圣彼得堡大学和帝国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二十六岁时当选为帝国科学院院士。史禄国是通古斯(鄂温克族人的别称)研究方面的权威,1912年至1917年间,曾在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中国的蒙古和满洲地区进行考察。然而,由于英语表达能力比较差,与同时代的人类学家相比,他的学术影响力并不是很大。
史禄国对苏联的十月革命不够理解,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所疏远和冷落,于是不得不远走海参崴,在海参崴远东大学任教。1922年,史禄国流落中国,在圣约翰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辅仁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因不熟悉汉语,无法进行社会调查,他便从事人体测量方面的工作。在史语所工作期间,不善处理人际关系的史禄国工作并不顺利,后经所长傅斯年推荐,于1930年进入清华大学任教。其存世的人类学著作中,和中国相关的有《华北人类学》《华东和广东的人类学》《中国人的身体发育过程》等三部,费孝通称这三部著作在中国体质人类学史上的地位为“空谷足音,无人后继”。
1933年,经过吴文藻斡旋,史禄国接收费孝通做自己的研究生。史禄国在清华大学生物馆借用了一间实验室,实验室的两张桌子上堆满了零散的人体骨头,桌子旁还竖立着一具人体骨骼模型。这些是史禄国为刚刚进入体质人类学领域学习的费孝通准备的基础研究材料。
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只有史禄国和费孝通两人,史禄国的主要工作是撰写《通古斯人的心态》这部著作,做实验的主要是费孝通。在指导费孝通做研究时,史禄国不是手把手、耳提面命式的,而是安排布置一定的任务后,放手由费孝通自己去完成。每天傍晚,史禄国总要去实验室一趟,查阅费孝通收集的各种统计资料,如果发现费孝通工作中的错误,他就会在纸上写下“重做”二字。经过两年的学习,费孝通撰写了论文《朝鲜人的体质分析》,还完成了对驻扎在清河的士兵的人体测量及体质分析的工作。
史禄国认为人体测量是人类学研究的方式之一,因为人是活生生的。他告诉费孝通,要通过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在混合的人群里分辨出不同的类型,并告知采取怎样的态度才能使测量者和被测量者之间达到心灵契合等。史禄国不仅教导费孝通分析人体的显性形态,更指导他从人的生理层面出发,来探讨人的社会行为产生的心理机制。
1935年7月,费孝通完成了第一个阶段的学习。为了给出国留学做好准备,经史禄国建议、吴文藻联络和协调,费孝通决定和妻子兼同学的王同惠一起,赴广西进行题为“广西省人种及特种民族社会组织及其他文化特征研究”的社会调查。行前,史禄国为费孝通购买了一台德国产的不用胶卷而用胶板的照相机,以确保费孝通能够顺利完成此次调查任务。知道广西山区有一种专门叮人的旱蚂蟥,史禄国还为他俩定制了长筒皮靴。
9月18日,费孝通和王同惠到达广西南宁,随后进入大瑶山展开调查。12月16日薄暮时分,在从古陈村转移到罗运村的途中,费孝通误踏当地村民设置的捕猎野兽的机关,机关带动石头压住了费孝通的腰腿和左脚。费孝通受伤,左脚脚踝也错了位。情急之下,王同惠先挪开压在费孝通身上的石块,然后独自走出森林向村民求助,然而,途中不慎坠崖,落水而亡。七天后,村民们发现了王同惠的遗体。费孝通则在受伤后的第二天被当地瑶族同胞发现,获救。事后,费孝通说,如果没有史禄国为他准备的这双皮靴,他的左腿会报废,甚至有可能和妻子一样,无法活着走出大瑶山。
1936年,费孝通根据在广西的调查写出的《广西省象县东南乡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由北平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撰写的社会学和民族学专著。而自1935年分别,费孝通与史禄国便再也没有见过面。1939年,史禄国逝世,享年五十二岁。
抗战时期,许多文化科研机构将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运往了内地,在运输过程中,车辆和船只常遭遇日军轰炸。费孝通存放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的两篇关于朝鲜人和中国人体质分析的毕业论文,因遭日机轰炸随船沉入江底。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费孝通亦遭当局通缉,只得匆匆携眷离开昆明。他在广西大瑶山所测量的人体数据等资料因不方便携带被留在了昆明,最终不知下落。20世纪50年代,费孝通被错划为右派,丧失了二十年宝贵的科研时间,他不得不放弃人类学的研究,这让他感到非常遗憾。
20世纪80年代,苏联为史禄国平反,承认他是通古斯研究方面的权威。史禄国的理论、方法对费孝通影响至深,费孝通晚年在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所运用的“类别”“模式”等概念,都是从史禄国那儿“拿来”的;费孝通在民族学方面创立的“多元一体论”,也获益于史禄国的体质人类学理论。
在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
1936年,吴文藻赴美国和英国遍访当地的社会学家,为其学生出国留学寻求合适的导师。同年夏天,费孝通从清华大学毕业,得到公费留学的机会,被吴文藻安排到英国留学,后师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
马林诺夫斯基1884年生于波兰,父亲是著名语言学家。大学毕业后,他先后留学德国和英国,1914年由伦敦大学资助到澳洲开展调查研究,1927年担任伦敦大学所属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马林诺夫斯基门徒众多,经常指派学生到非洲进行人类学调查。不到十年的时间,他所创立的功能学派的声势便压倒了其他派别,他本人更是该学派的一面大旗。与一般的人类学调查不同,马林诺夫斯基主张人类学学者要重视社区调查,调查者要想获得对某个方面的了解,必须从这一方面与其他方面的联系来探索穷究。
当时,欧洲流行一种名为“习明纳尔”(seminar)的教育形式,即专题讨论。马林诺夫斯基每个星期五都要组织一次这样的学术讨论会,参会的既有他的朋友、同事和学生,也有来自其他国家的人类学家,大家一起交流人类学研究的前沿信息,这门课程因此得名“今天的人类学”。会上交流的内容,不仅是课堂上没有讲的、教科书上没有写的,有些甚至是大部分人类学学者从来没有想到的。经过交流与讨论,与会人员的学术视野更为开阔,研究问题更有广度和深度。
马林诺夫斯基经常与朋友讨论学问,当感到讨论的某个问题可能对某个学生有启发时,他总会招来这名学生,让其参与讨论。他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沉浸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之中,即使学生暂时听不懂老师们在讨论什么,单是感受这种氛围也会大有收获。
在一次“习明纳尔”上,费孝通第一次见到马林诺夫斯基。在费孝通眼中,马林诺夫斯基是一个高度近视、光头、瘦削的老头,看起来很精明。1936年9月,马林诺夫斯基曾经到美国参加哈佛大学建校三百周年的庆典。在那里,他遇见了代表燕京大学参加庆典的吴文藻。通过吴文藻的介绍,马林诺夫斯基得知费孝通当时已经到达了伦敦。只是后来费孝通第一次见到马林诺夫斯基时,两人没有来得及进行交流。
参加完哈佛三百周年校庆后,吴文藻于1936年底乘玛利亚皇后号轮船到达伦敦,先访问牛津大学,随后到访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他了解到,当时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博士弗思正担任费孝通的导师,他们已经就费孝通的博士论文进行了深入讨论,最终确定的题目是《中国农民的生活》。吴文藻向马林诺夫斯基建议,由他亲自指导费孝通。马林诺夫斯基接受了吴文藻的建议,对费孝通进行简单的考察后,决定亲自担任他的导师。
除了“习明纳尔”外,马林诺夫斯基还有一种新颖的教学方式,就是让学生到他家里围观他的“写作”。马林诺夫斯基高度近视,完全不能看书和执笔书写。写作时,秘书会在他身旁贴身服务,帮他读稿子。他闭着眼睛认真听,然后口述相关内容,秘书再将他所说的话记录下来。学生在旁边听他的口述,能够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他是如何思考的,文章是如何形成的,最终又是如何修改和定稿的。
费孝通在撰写博士毕业论文期间,每写完一章,就拿到马林诺夫斯基床前念给他听。马林诺夫斯基躺在床上,用白布蒙着眼睛,给人的感觉像是睡着了。不过即便这样,费孝通也丝毫不敢懈怠,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马林诺夫斯基就会从床上跳起来,大声地说文章哪一段说得不够,哪一段有错误,而且语言非常俏皮、尖锐。虽然费孝通觉得自己已经竭尽全力,但是马林诺夫斯基始终不能满意。当然,马林诺夫斯基还是希望费孝通能够顺利毕业的,因此指派了一位讲师对他的论文进行修改和补充。
1938年春天,为躲避战乱,马林诺夫斯基准备前往美国。行前,他催促费孝通尽快完成博士论文的写作。费孝通的博士论文答辩仪式是在马林诺夫斯基家里举行的,校方指派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后更名为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院长、著名波斯语专家丹尼森·罗斯爵士参加论文答辩。丹尼森·罗斯称赞费孝通在学术上有过人的才华,还说自己的夫人也认为其论文很有吸引力,一口气就看完了。答辩结束后,丹尼森·罗斯毫不犹豫地在学位答辩审定书上签了字,然后喝了一杯酒,便离开了。
那天,马林诺夫斯基留费孝通在家中共进晚餐,席间,他给一位出版商打电话,希望对方能出版费孝通的这篇博士论文。出版商开出条件,如果马林诺夫斯基为这本书写序,他就可以出版。马林诺夫斯基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这篇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交付出版时改题为《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这部著作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并将自己写序言所得的稿费五十英镑,作为礼物送给了费孝通。
费孝通将《江村经济》的校样校阅完毕后,便匆匆回国,投身由吴文藻主持、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合作建立的“社会学研究工作站”的工作中。他学习马林诺夫斯基的“习明纳尔”教学方法,经常组织学生们讨论问题。他还按照马林诺夫斯基的要求,继续进行“微型社区”的调查和研究,先后在“禄村”“易村”和“玉村”(分别指云南禄丰、易门、玉溪的三个村庄)三个调查基地进行田野调查,取得丰硕成果,1945年写成《云南三村》一书。
1980年,费孝通获得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他亲自前往美国丹佛参加了授奖仪式。费孝通对马林诺夫斯基这位社会人类学的缔造者非常怀念,在讲话中深情地表示,面对此情此景,“不由得我们不对这一位杰出的应用人类学的开路人表示敬爱和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