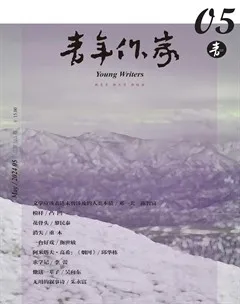换 季
衡世敏
一
镜子里,一颗颗凸起的红色斑点像是炸开的火星。我感受到身体瘙痒的疼痛。这疼痛像是儿时蹲在灶台边帮娘看火,无聊时将口袋里的花骨朵掏出,一颗颗扔进火里,几乎听不见声响,只有加柴时火星溅到手背上,才隐约感受到破裂的热度。又像是光脚踏进了蚁窝,蚂蚁一窝蜂上来吃我。小小的、锋利的上颚啃噬着我的皮。但它们惊讶地发现,我是一尊难以搬动的庞然大物。
药膏抹在红包上,带来刺痛的清凉。窗外出了太阳。大家一拥而出,在楼下的空地里站着,将自己反复晾晒。似乎这样便能驱散霉意,来迎接之后数周的卷土重来的雾霾。
我问志宇,要不要一起下楼晒太阳。
他专心致志地抓着什么,像在扑花蝴蝶。听到我的话,他转过头,语气乖巧又客气,显然在幼儿园里学到了不少东西。
“不用了,妈妈。”
“晒太阳才能长高。”我蹲下来,试图拉进和他的距离。
他黑色的眼睛滴溜溜地转,看上去像两颗清洗过的葡萄。怀志宇的时候,我还没有和他的父亲分手。下班之前,他会买一袋我最喜欢的紫葡萄,洗干净、剥皮,放在果盘里。他说自己很快就能把那边的事情处理好,我也就耐心地等待着。
志宇向后退了一步,甜甜地说:“我不想晒太阳,妈妈。”
他每唤我一声妈妈,我便觉得身上的红斑痒了一分。我有些失望地告诉他,妈妈要下楼晒太阳,让他乖乖呆在屋里。志宇虚握着拳头,点了点头。
楼下有很多老人和孩子。老人围成两桌,一桌打扑克,另一桌摸象棋,其他人围在旁边看,指手画脚;孩子在空地里疯跑,背上的毛巾落下来,像是没有剪断的脐带。我多么希望志宇也能像他们一样。中年人站在台阶附近,三三两两谈论着。我听见他们谈论股票、孩子和周一的油价。于是,我想要走远一些。
“志宇妈妈——”相熟的太太喊道。
我只能停下脚步,加入她们的谈话。
“你也下来晒太阳?”
“是啊,成都可真是太潮了。”
“可不是,”她露出担忧的神色,“我真担心自己以后患上肺癌。哎,活不久了,能活到七十岁就很不错喽。”
“能活到退休的年纪就很好了。”
“志宇妈妈,你最近很忙吧?我侄子说刚刚一诊完。”
我挤出一个短促的笑容:“还好,班里的孩子都很乖。”
她沉默了片刻,又扭头和旁边的太太说起话。她们都是全职妈妈,共同话题有很多。孩子的衣服,孩子的食物,周末带孩子去哪里玩……我静静地听着,又想起志宇来。他一个人在楼上,可能不小心撞倒客厅的茶几,或者踩着小板凳拿橱柜的零食却踩空摔下来。一想到这样的可能性,我便不自觉地紧张起来。
太阳很好,我告诉自己,多晒太阳对换季时的皮肤病有好处。但是阳光却像是医院里的照灯,让我觉得自己躺在了另一张麻醉床上。志宇会没事的,我只是下楼十分钟。我反复在心里念叨。我的胳膊开始颤抖,我用一只手抓住了另一只,两只胳膊一同震动起来。我的头发丝开始震颤,连带着五官和五脏六腑。
“志宇妈妈,你怎么了?”
“我要回家。”我急匆匆地甩下这一句,就往电梯走去。
有人小声嘟囔着:“这又是怎么了?”
相熟的太太好心解释道:“单亲妈妈,压力一定很大吧。”
用钥匙拧开锁孔的瞬间,我看见志宇惊诧的神色。他站在玄关,鞋穿了一半,手里捏着玻璃瓶,里面装着黑色的沫状物。这是他的宝贝,平日里总是揣着,不轻易拿出来。三岁的时候,我送了他一个许愿瓶。他将里面的星星掏出来,说愿望归我,瓶子是他的。我笑他这么小就有想法了。之后又将家里的鱼缸找出来放星星。以前里面养了两条金鱼,现在它盛满了星星。
我问他去哪里,他说自己想要下楼晒太阳。
“你这孩子,”我嗔怪道,“刚刚和我一起下去不就好了。”
他露出甜甜的笑容,把玻璃瓶往后藏了藏:“突然想了。”
小孩子的想法像夏天的雨,随时都在变化。我给他垫上一张毛巾,叮嘱他,和其他孩子玩游戏时跑慢一些。志宇犹豫了,说自己不和他们玩。
“为什么?”我担心志宇在幼儿园也不合群。
志宇支支吾吾地说:“他们说,我不能和他们一起玩。”
“为什么呀?”
“因为我是没有爸的孩子。”
小孩子哪知道这些,分明是大人教的。我想起女人们亲切的脸庞,心跳得快极了,似乎脉搏都要跳出来了。她们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向我问好呢,每一次谈话时,她们是不是都在心里偷笑着我?我又盘算起搬家的事。这是志宇的父亲选的房子。最开始,他和我一起住,我们计划结婚之后将这里买下来;后来我怀孕了,他不再过来,只帮我交租金。再后来,便是我一个人承担了。志宇不喜欢这里,我也不喜欢这里。很早之前,我便想搬去另一处地方。但是有什么东西,将我困在了这里。
是什么?我看着门渐渐合上,志宇的身影消失在视野里。耳边传来了嗡嗡声,我一个巴掌呼过去,没有打着;再换一个方向,依旧是空的。这个季节怎么会有蚊子。嗡嗡环绕在我耳边,持久又延绵。我觉得心烦,便从包里抽出作业本开始批改。
高三学生的字迹,透着疲软和怨恨。
成年的前一年,似乎要将前十八年的善意与忍耐都耗尽。先前和班里学生不错的师生关系,也在这几个月里迅速激化。他们开始给我取各种难听的绰号,在一遍遍对我的咒骂里完成作业。钉成册的试卷,每周一换的草稿本,每天早上七点开始的早读,总有无数的脑袋低下,像一片倒伏的麦田。我将他们叫醒,到后面罚站。他们眼里的睡意变成抱怨,眼里充满着无能为力的怨恨。
有一天,跑完操后,我的班长对我说:“老师,你可真讨厌。”说这话时,她是笑着的,似乎在开玩笑。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经常这样开玩笑。
但是这一次,我从她的眼中看见了怨恨。
又过了一天,她对我说:“老师,我要退学。”
我习以为常地放下习题册,捏了捏被眼睛架痛的鼻梁。这样的学生见了太多,几乎每一天,都有学生告诉我,自己抑郁了。有人请假出去看病,有人说,把作业免掉一天。最后他们都灰溜溜地从办公室离开。最后我告诉他们,明天下午考理综。
我问:“为什么呢?”
她答:“我怀孕了。”
她的语气如此平静,就像是一个被癌症折磨了许多年最后头发秃秃地躺在床上的病人。我望向她的肚子,那里是少女的平坦,不像我,空落落的袋子拴在腹部,我时常觉得子宫里感受不到其它东西。那里真的会孕育一个生命吗?
办公室里没有其他老师。另一个年轻老师在走廊上答疑,其他的在休息室午睡。我却如同一个小偷一样,左顾右盼,最后干巴巴地说:“梓涵,你不要瞎说。”
梓涵走过去,将半敞开的门关上了。
她走过来看着我,像是面对着一堆未解的数学公式,神色沉静又茫然。她摸了摸小腹,似乎又变得不确定起来。办公室里的温度下降,空调自动启动,发出轰鸣声。空气中也散发着干燥的气息,我回过神来,看着她的神色又恢复了确定。似乎在我走神的几秒钟内,她便找到了自己的答案。快速,精准,像每一个高三的孩子。
我艰难地开口,“梓涵,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知道,老师。”她用黑白分明的眼睛看着我。
像是说谎的表情。
我沉下心来,宽慰道:“老师知道现在压力很大。再忍一忍,只有半年的时间了。等你上了大学,一切都会变好的。”
她似乎在疑惑,为什么我不相信她。最后她向我请假,希望自己可以出去走一走。
我露出为难的神色:“这几天要评讲一诊试卷。补习只剩下两周了。两周后你就有七天的假期。那时候,你想去哪里都是可以的。”
我使劲地安抚她,像是在进行一场演说,希望打动她的心。
她点了点头,离开了办公室,没有忘记关上门。
轻轻的,几乎听不见什么声响。梓涵她总是很沉稳,让她带着同学们早读和自习,我也很放心。每学期结束的时候,我都会送她一本书,感谢她的努力。
这学期送什么书好呢?我的笔停留在字母A上。笔尖渗透出红色的墨水,像是一滴硕大的眼泪,将A染得通红,我不敢去擦,只能用纸巾一点点地稀释。红色依旧在那里。黑色的字迹被染得面目全非,就像是胸口烙印的红字。
只是一会儿的功夫,屋外的阳光已经黯淡下来。
我放下笔,走到窗边,试图在楼下众多黑色的身影中找到志宇。可是哪里也没有。我在视野之内,从左往右又数了一遍,还是没有。就当我焦急地准备下楼时,却看见志宇在门外专心致志地倒腾着玻璃瓶。他的手上捏着一个微小的东西,倘若不是他翘起的指尖,我根本注意不到他的手中还有东西。
我问:“志宇,你在干什么呀?”
志宇扬起局促又讨好的笑容,将手背到身后。
我拉下脸,说:“把手伸出来。”
志宇依旧不肯。我只好绕过去,一把抓住他的手。他的指尖捏着一只蚊子。没有了翅膀和细腿,只有小小的、却胀鼓鼓的肚子和头。我看向志宇的宝物。玻璃瓶的底部放着一层黑乎乎的东西——我原本以为是泥土,现在才发现全是残肢。
志宇不知所措,但是他仍在笑。
他走过来,拉着我的衣袖,让我不要生气。但是他的另一只手,仍没有松开那只蚊子的尸体。紧紧地攥着,眼睛盯着我手中的玻璃瓶。
二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我总是走神。我将昏昏欲睡的学生点起来背课文,心里想着志宇是什么时候变成这副模样的。刚生下志宇的时候,没有人来医院看我。妈曾经劝我先将孩子打掉,以后再要一个也不迟;但是我不肯,因为下一个孩子便不是志宇了。临产前一个月,我和志宇的父亲分了手。他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听起来既陌生又亲切。我想哭,但是嘴里的咒骂阻止了眼泪落下。他一声不吭地听着我的指责,接受了我的分手,依旧用温柔又令人信服的语气叫我好好休息。
忙音响起的一刻,我意识到自己只有志宇了。
分娩后,伤口依旧疼。失效后的麻药似乎放大了所有的感官。我时常觉得志宇没了呼吸声,挣扎着偏头看时,又发现志宇睡得安详。乳房很胀,志宇喝不下奶的时候,乳头像是堵塞的水管,我几乎能听见身体的呜咽声。护士送来了吸奶器。我的动作不灵活,又担心志宇万一想喝奶了自己却没有奶水,总是在愧疚中弄得满头大汗。幸好志宇一直都很好养活。他安静地闭着眼睛,没了刚抱出来时血淋淋的模样。他的皮肤很白,眼睛很大,像是年画中的福娃。
“老师?”
“嗯?”
我如梦初醒地回过神,发现自己走到了教室的正中央。被点起来的男孩看着我,脸上带着不好意思和担忧,桌面上的课本大打开。他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我的神色,似乎在等待我纠正错误。可是刚才,我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我只能清了清嗓子,让他坐下,又叫他背熟一些,下次就不能蒙混过关了。我听见了哧哧的笑声,像是锯齿摩擦着地板。但是大家都用课本挡住了脸,我只能看见他们来不及洗头而泛光的头顶。
很不舒服,这笑声如同半夜三更听见门被推开的摩擦声一样恐怖。我走上讲台,让所有人打开练习册,站在较高的地方打量着他们的神色。蜡黄的脸,低垂的眼睛,耷拉的青色眼圈,只有鼻尖那颗硕大、冒着红光的痘告诉我,他们还年轻。
唯一不同的是梓涵的脸。她注视着窗外,神色专注而从容,嘴角还有来不及放下的弧度——刚刚的笑声是她发出的吗?我不由地战栗了一下。
梓涵转过头,将手轻轻地放在了小腹上。
我像是被家乡的滚雷赶上了,银白色的火雷在我的脚底炸开。我瞪大眼睛,细细辨认她脸上的神情。我怀志宇的时候也是这副模样吗?不,不是。那时候的我和冷静毫不沾边。我辞去了工作,因为没有办法忍受任何消息的震动;我总是神经质地查看预产期,不断地打字又删去,将十根指头都咬得残缺不齐。望向镜子时,我恍惚觉得自己怀的不是孩子,而是一场灾难。但是这一切,都在那通电话后终结了。
“梓涵。”我情不自禁地叫道。
“到。”她站起来,像是一棵挺拔的白杨。
我只能说:“你讲一下第七题该怎么做吧。”
“老师,第七题不是家庭作业。”
“那你现看吧,给同学们讲讲思路。”
我的脸火辣辣地烧起来。我看见第二排的男生冲同桌挤眉弄眼,似乎在说班长怎么惹我不高兴了。他们只有当了老师才知道,这个位置连角落的蛛网都看得清楚。梓涵的声音很恬静,几乎不是在讲解题目,而是在朗读诗歌。我无法将她和分娩联系起来。她像是所有长辈都会喜欢的孩子,我也不例外。每当我听见班里同学们窃窃私语时,总是忍不住劝他们多多体谅别人的不容易——但是,他们显然把梓涵当作了我的走狗。
他们是这样说的,带着爽朗、明媚得如阳光一样的笑声,在走廊的栏杆边抱怨着我这个不近人情的老师,以及和我素来走得很近的班长。
“她怎么什么都看不顺眼。”
“更年期的女人。”
“她看上去不像是四十岁的样子呀。”
他们轻松地说:“早更了呗。”
最初听到这话的时候我很难过,但想着自己始终是老师,高三的学生压力很大,于是装作什么都没有听到,沿着另一个方向离开了。回到家后,我忍不住抱住志宇,反复告诉他要讲礼貌,要尊重别人。志宇似乎没有听明白,安静又天真地看着我,不能理解我的难处。他快要六岁了,已经没有了襁褓里的奶气,看上去是个俏生生的男孩了。
他长得像我,和我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这大概是我唯一的慰藉。我问他记住了吗,他一板一眼地重复道:“记住了。”
课间的时候,我把梓涵叫到了办公室。教室里传来阴阳怪气的声响,有人学着太监尖细的嗓音喊道:“恭送班长——”我佯怒地转过头,他们又嘘了声,低头做起题目。几个一分钟前冲出教室小解的学生,又飞速地绕回了自己的座位。我突然想起隔壁的班主任对我抱怨,说这半年的尿液都比往常深一些。她说屁股上鼓起一个脓包,平日里只能侧着坐,就连内裤也必须穿宽松的。他们也有同样的烦恼吗?我扫过书桌上的水杯,还有地面上零零散散的矿泉水瓶。班里最刻苦的孩子买回了1L的矿泉水,他说这样可以喝一天,不用频繁地到走廊另一端打水。可是这几分钟又有什么用呢?磨到现在,我也变得不确定。我只能一遍遍地告诉他们,再忍耐一段日子。
这般想着,火气便消了。高三这一年,对于老师和学生都是特别的记忆。志宇也习惯了六点钟睡眼惺忪地被我喊起来,顶着冷气站在幼儿园的铁门外,和哆嗦着前来开门的保安大叔道一声早安。自习要上到晚上十点半,虽然学校没有明确要求班主任要守班,但这已经成为了默认的传统。偶尔让隔壁班的老师帮忙看着,第二日年级组长便找了过来。三十多岁的人,依旧像做错了事的孩子般挨训。我只能趁晚饭的空隙到幼儿园接志宇。志宇坐在我身前,整个身子都躲在电瓶车的挡风罩里。一瞬间,我以为他又回到了我的身体里。
梓涵在笨重的办公桌前站着,我让她端一个凳子来。这是要长谈的架势。门板阻隔了走廊的喧闹和隔壁卫生间冲水的声音,热风冲破扇叶的阻挡,形成一股暖流,盘踞在屋内的天花板。我觉得眼前的梓涵很陌生。
“梓涵,你在想什么呀?”
“没有想什么,”她顿了顿,又加重了语气,“什么都没想。”
“上次你和老师说的……”
她漫不经心地望向我的眼睛:“老师,我说什么了?”
大抵是胡话吧。我嘘了声,心里也松了一口气。认为她就像是其他孩子那样,在高三觉得自己浑身不舒服,于是也想找个理由去看病。但记忆里的梓涵是会说谎话的人吗?我想起她每一次言辞确凿的汇报,不由地怀疑,先前她说的话又有哪些是真的呢?班里没有一个人完成的作业可能是我说漏了,梓涵也确定地告诉我,自己并没有听到布置的作业;寝室里大家都学习到很晚,所以宿舍阿姨让我去查手机的时候我也不太在意;还有每一次自主小测的成绩都很好看——可是为什么一诊会考得这么难看?
“梓涵,你告诉老师,你是不是在说谎?”
梓涵把头转向窗外:“哪件事情?”
“你说不是家庭作业的习题,宿舍里没有偷藏的手机,还有小测……”我一口气说出了自己的怨愤,但想到前几日梓涵确凿又坦然的神色,我又不知道该如何把最后一个问题问出口,“还有你上次说,自己怀孕了。”
第一次见到班里的同学时,大家都很踊跃,热情又害羞地围在我身边。军训的时候我买了两箱蜜雪冰城,他们欢呼着向我跑来,像是一片青翠的树林。去年元旦放假的前一天,本该举办的晚会被学校取消,我让他们关好门窗,偷偷带着同学们在晚自习看恐怖片。有男孩把薯片撒了一地,被邻桌女生笑骂着拍了一巴掌。这似乎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
“梓涵,你说话呀。”
我看着她淡漠的脸,心都揪了起来。
“我不记得了,老师。”
“怎么会不记得呢?你前几天才说过嘞。”
“我真的,”她的声音如此平静,像是暴风雨间的喘息,带着令我头晕目眩的力量,“不记得了。可能是需要背诵的东西太多了。”
她在怨我。
这个想法让我一哆嗦。我似乎觉得自己站在空地里。浑身湿透,等待着下一场雨噼里啪啦地砸下。嗡嗡的声音围绕在我的耳边。蚊子,该死的蚊子,怎么没有冻死它们!
“梓涵,”我竭力控制自己的手,不去追逐嗡嗡的声音,“再忍耐一段时间,等到六月份结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们现在不理解,以后就会知道老师的苦心了。”
这是掏心窝子的话。妈的收入不多,大部分都投入了我的教育。在我没有犯浑之前,她总是向邻居夸耀,自己看男人的眼光虽然不行,但是很会养孩子。她从小就告诉我,只能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我走出了那个散发着猪饲料味的县城。在乐山师专读了四年,又到四川师范大学念了三年的硕士,最后通过校招到了郫都教书。妈以为我会留在成都市区。我告诉她郫都属于大成都,社区里的人都说自己是成都人。但是妈只是冷哼了一声,说:
“和我们这个地方又有啥子区别。”
她从来不肯体谅我,总是怨我不够努力。要是再勤奋一些,我肯定能过得更好,她总是这么说。记忆里的妈一直带着焦躁的神色辗转在小卖铺、批发商和家里,每次的考试她都觉得我有上升的空间。她将自己用不着的胸罩丢给我,我的整个青春期都是在钢圈勒着胸脯的闷痛中度过的。有一次,我实在是受不了,便偷偷将内衣脱了下来。走廊上不小心和疯玩的男孩撞了满怀,乳头便颤巍巍地立起来。我羞得几乎哭出来,只能耷拉着肩膀,用垂下的衣物来掩饰自己的异样。回家后我对妈说,我想要一件合身的内衣。她白了我一眼,继续核算着账本,说:“你要穿给谁看啊。”
后来,妈不再做小卖铺的生意,开始跟着相似年纪的大妈跳广场舞。她纹了眉,买了新手机,学会了看直播。最后一次见她时,她兴冲冲地要帮我涂红色指甲油。这样的妈让我生出落泪的冲动。虽然那瓶指甲油,最后炸在了我的脚边。
“梓涵,”我沉下声音,“你想去一趟医院吗?”
“我不相信医生。”
“那你相信老师吗?”
“我也不相信。”她执拗地摇着脑袋。
这个年纪的孩子只相信自己。我屏住呼吸,无言地看着她。蚊子的声音又来了。像是深夜里的轰炸机,缠绕在我的耳边。嗡嗡嗡,嗡嗡嗡。我觉得身上的红斑更痒了,痒得让我抑制不住地用衣服的布料摩擦了一下瘙痒的部位。但是片刻的缓解后,却是更令人难以忍耐的刺痛,仿佛一连串的干咳。火星在我的身体里炸开,这红斑就是它的遗骸。
“老师,你怎么了?”梓涵似乎带着关切,又像是随口一问。
“换季的皮肤病。”我嘟囔道。
“是呀,春节就要来了。”
梓涵的话让我生出些许希望。我说:“梓涵,你看,这四季轮回也是这样。你现在觉得很难熬,但是一眨眼就过去了。或许等你反应过来,就是夏天了。”
她反而笑了出来,脸上流露出大人的模样。
“老师,我们不喜欢听这些。”
“那你们喜欢听什么?”
“我靠呀,卧槽呀,累死人了。”梓涵轻快地说。
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梓涵说的是脏话。想要开口说她两句,又觉得这不是自己该管的东西了。我端起桌上的水杯,靠近嘴边才发现已经空了,只能装模做样地抿了两口。我将抽屉里的糖果分了一些给她,这本来是给志宇打发时间时吃的。最后,我找不到东西可以给她了,竟阴差阳错冒了一句:
“这蚊子可真讨人厌呀。”
“老师,哪里有蚊子?”
“就是在这里,”我随意比画了一下,“绕着我们飞。”
梓涵流露出疑惑的神色,抿了抿嘴唇,似乎带上了一丝怜悯,最后点了点头:“那我帮您把它打死吧,老师。”
她举起两只手,张开手掌,在我的眼前快速地一拍。
啪——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
那个每天买1L矿泉水的男孩走了进来,手里拿着阅读题和便利贴。见我们这般面对面坐着,连忙往外面退去,说自己另外找个时间来。我担心自己耽误了他问题,忙说已经谈完了,让梓涵先回教室。梓涵从容地站起来,往门外走去。
“梓涵——”
她转过头,平静地望着我。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叫住她,只好说:“谢谢你。”
她露出一个真心又嘲弄的笑容,轻轻地关上了门。
蚊子的声音真的消失了。似乎梓涵变戏似的一拍,真的将那可恶的蚊子打死了。男孩将作业本摊在桌上,绿色的荧光笔将第二遍还是做错的题目圈了出来。这是我教给他们的小窍门。他像是激光枪般“突突”,一连吐出了好多字,我听得头晕目眩,只好把教师用书翻出来,对着解析讲。他似乎理解了,又似乎没有,但是将我圈出来的关键字都抄了下来。
“你,你知道梓涵最近经历了什么吗?”
他推了推眼镜,臃肿的身体在空调房里被捂出了汗,鼻尖上的痘亮晶晶的。他似乎惊讶于我的问题,也不想多说,支支吾吾:“没什么吧,能有什么呀。”
“真的没有什么吗?”
“啊,这个……”
“你如实告诉老师,老师不会说出去的。”
他似乎下定决心一般,飞快地往门口走去。走了几步,又带着恼怒和不高兴的神色,似乎我打探了班里的私事,让他为难了一般:
“她妈妈,给她找了一个新爸爸。”
他顿了顿,嘴角似乎带了点笑容,又拼命压制住,最后像钩子一样往下压去:“她妈妈还怀孕了,似乎要给她生个小弟弟。”
我觉得蚊子的声音从体内升起,嗡嗡嗡,嗡嗡嗡。这一回我终于明白了,这不是什么冬天没有死透的蚊子,而是红斑的瘙痒。
“你是从哪里知道这些的?”
“周五她妈来接她放学,大家都在说。”
三
晚自习结束的时候,我回到办公室找志宇。他坐在笨重的桌前,安静地看着画本。见我进来,他立刻用脆生生的声音对我说:
“妈妈,你辛苦了。”
志宇,我的志宇。倘若放在往日,我定会抱住他,在他的发旋处落下一吻。但是此刻我只觉得身体痒得似乎要烧起来,巨大的轰鸣声在体内响起。我想起医生的话,他让我放平心情,不要太焦虑,这湿疹自然而然就好了。我让他多开一些药,又不放心地问:“这病会传染吗?家里还有孩子。”他安抚道:“不会的,这主要是你自己内分泌失调。”
药,药。我焦急地想要从包里找出药膏,却发现里面的东西变了位置。
“志宇,”我觉得头晕目眩,“你翻了我的包吗?”
志宇眨了眨眼睛,笃定地摇脑袋。
我几乎要站不住了,红斑火烧火燎地疼:“志宇,妈妈给你说过什么,不要撒谎!”
“我没有想翻乱你的东西,妈妈,”志宇小声地说,听起来也很委屈,“我只是想把我的玻璃瓶找回来。当时说好了,星星送给你,玻璃瓶归我。”
“可不是让你用来装那些东西的!”
“那妈妈把玻璃瓶放哪里了呢?”
“我扔了!我扔了!你找不到了!”我终于忍受不了地尖叫起来,我几乎觉得志宇肢解的每一只蚊子都在我体内生了卵,嗡嗡嗡地叫起来。
它在报复我,它在报复我!
他在报复我,他就是一场灾难!
志宇安静地看着我,沉默不语。一时间,办公室里只有空调的轰鸣声。
我终于回过神来,意识到自己失态了,想要走过去拉住志宇的手,告诉他,刚刚是妈妈做得不对,是妈妈没有控制住自己的脾气。
志宇甩开了我的手。他尖叫道,用我在幼儿园门外听到的那些孩子们充满童真的声音脆生生、欢快地喊道:
“去你妈的,去你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