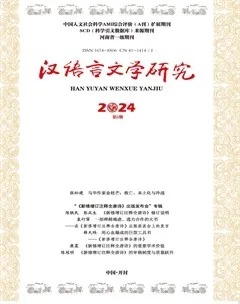论张枣诗歌中悖论的建构及美学反思
鲁登 赵海霞
摘 要:张枣诗歌的语言体现了“轻甜”“圆润”“婉转”的特点,同时又聚焦于悖论的表达,即言说的悖论。通过词与物的关系、语言与存在的关系、“生与死”的问题、中西反思和对中西传统文化资源的汲取,他完成了悖论内涵的建构和美学特质的体现。他主动选择“元诗”这一诗歌形态,放弃对明晰意义的追求,通过一个隐喻的语言花园,来达到叩问苍穹、克服言说危机的目的。元诗,是张枣悖论美学的最高呈现。这种写作风格的形成,与诗人的教育背景、审美追求、时代遭遇有关,家族的精英意识、楚文化的滋养、少年写诗的氛围和青年德国之旅的体验,是张枣悖论表达的外在文化环境,生死、中西之间主体自身的复杂和矛盾,是其悖论表达的内在美学原则。
关键词:张枣;悖论;文化渊源;美学;元诗
作为“第三代”诗人的杰出代表,张枣以其别具特色的诗歌显示出中国当代诗坛发展的潜力和可能性。近年来,张枣其人及其诗歌价值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围绕其诗歌意象、手法、观念、技巧、“元诗”理论及美学理想等诸方面展开探讨。这些探讨不仅拘囿于张枣本身,更体现出新诗自身发展过程中的自我质询、评判、衡量和探索,以及当代诗坛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诗写作受到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决定性影响的反思。受到重视的同时,张枣的诗歌风格独特的表现,以及开放性与不确定性之间,他的诗歌表达深处的特点和文化渊源等问题,人们的认识还不够充分,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察。回到其创作,张枣的诗歌语言体现出一种“悖论”的典型表达,这种表达具象化为诗歌的风格,又内化为深层的结构,涉及作者对生命的追问、古今的反思、文化的熔接和诗歌美学的构建,即诗歌直觉和逻辑的并存。
一、“悖论”的基本内涵
在逻辑学上,悖论指的是:在表面上显示为是同一个的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着两个对立的结论,而这两个结论都能自圆其说。而在文学上,“因为文学既具有现实一面又具有反现实的一面,这种等值因素并存于同一体内的范式,就是悖论。”①布鲁克斯更强调,“诗人表达真理只能依靠悖论”。②在论鲁迅《野草》时,张枣谈到了“言说的悖论”。鲁迅关于“言说的悖论”的观点,也可以认为是张枣的观点,张枣诗歌创作中,悖论通过隐喻集中体现,呈现为一种文学的结构。
首先,“言说的悖论,就是生存的悖论,言路即生路,对言说危机的克服,就是对生存危机的克服,对自我的分裂和丧失、对受损主体的修复,只有通过一个绝对隐喻的丰美勃发的诗歌语言花园,才可能完成”。③利科认为,隐喻的内核即是悖论。因为隐喻在通过想象建立异质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联系时,却无法否认他们的异质的本质。张枣绝大多数诗歌的难解,就在于它们每一首都是“丰美勃发的隐喻花园”。
张枣诗歌中的典型意象,比如鹤、虎、天鹅,典型词汇比如袅娜、颤袅、蠕袅,以及他诗歌中的典型动词,比如“忍”“克制”“憋住”等,似乎有意通过丰美勃发的诗歌语言花园,去修复诗人自我的分裂和丧失,如意象“天鹅”是温柔、缓和的,而动作“忍”、“克制”却包含着一种紧张。不少研究者把张枣的诗歌风格归为“轻甜”①、“圆润”、“婉转”②,这却是心理上的自我压抑和诗歌美学上的有意识的追求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应当忽视他的诗歌风格中的这一悖论特性。
其次,如学者廖昌胤所说,悖论也是一种文学的结构,它通过相互对立、差异、非同一、矛盾、冲突的词语并置,用以揭示现实世界的诸多矛盾关系。如张枣诗中的典型的自相矛盾的表达:“雨外看雨”“似乎森林不在森林中”。而有关身体的分裂、分身术,以及主体与它的属性或部分的分离则有“替死亡当侦探的影子”“身子分成好几瓣”“而我们还在等着我们”和“自己还不是自己”等。
第三,张枣诗歌风格的“暴力”以及诗歌风格的优雅,都离不开他早年的经历。巴赫金认为,作品风格的一个关键要素——语调,和作者对它讲述、描述的对象的态度有关。③
张枣的家世和生平对张枣对创作对象的态度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一,张枣家族是湘军将领之后,他的高祖张庆云,是当年随左宗棠征西的大将之一,张庆云的家族在晚清民国期间一直很显赫,其中出了不少人物。“张枣有家学,从小背古典诗词,……他用长沙话背屈原的《离骚》、《橘颂》等……”④加之,少年时,张枣在家乡当时成立的“向阳院”就开始尝试写诗。其二,张枣父亲的伯父是军人起家,张家有习武传统。“我从小学外语”——张枣的父亲毕业于北师大俄语系,他的家庭有良好的外语学习的氛围——此先天外语学习的条件。其三,张家高祖张庆云曾被派去镇压白莲教起义,偶然从白莲教的人手里得到了一些医术秘方,并流传了下来。深厚的家庭背景使张枣对他的家族产生了类似杜甫对他的家族的感情:“吾祖诗冠古。”这是张枣在诗歌创作中流露出的强烈的精英意识的来源。“向阳院”的教学模式学的是小靳庄。大家都写诗的氛围,使得写诗成为张枣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他身上少了同时代很多诗人都有的焦灼感、竞争意识和影响的焦虑。他的写作的最开始是从容自在的,以上因素促成了张枣诗歌风格“轻甜”“圆润”“婉转”所显露的一种整体上的优雅形态。同时,张枣“从小就对暴力不太陌生,对暴力有审美倾向”,“记得有一次,我和爸爸正在五一路散步,就看见在一个交通亭里有很多人用皮鞭围打一个人”,“张枣是个军事迷”。⑤
因此,在他的创作中,存在着两种相互矛盾、冲突又对立统一的力量,既有精英意识和童年氛围造就的从容,又有诗人自称的“某种很霸道的东西”,这两股力量的融合形成了“一种极端的温柔、下定决心的温柔”。⑥笔者把这种“下定决心的温柔”理解成为一种内化了的温柔、优雅的力量,一种用以对抗暴力的态度。这也就是他所说的他的诗的paradox——悖论,精英的责任和写作的从容,暴力霸道和内化了的优雅温柔,即张枣诗歌“悖论”的基本内涵所在。
二、“悖论”的形态建构
在张枣的诗歌题材中,悖论的形态呈现为两点:一是显露于复归诗歌传统时,写作中“无用”和“有用”价值取向的内在冲突,二是显露于为了“发明语言”去国离家与设身处地的现实,却使诗人“失语”的矛盾。
首先,张枣诗歌中的悖论建构在“复归传统”之上,而这个传统又包括了两种并非完全没有冲突的传统:《诗经》的现实主义和《离骚》的浪漫主义。张枣认为,人必须在传统中写作,如果不在传统中写作,就免除不了最终被历史遗忘的命运。“在传统中写作”在张枣诗歌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于直接从古典散文、韵文、诗词中取材写作。张枣生于楚地,他自然而然地继承了屈原的浪漫传统,他想要创作的是一种无用的文学、一种浪费的文学。因此,当张枣面对稍早于他所处那个时代的朦胧诗时,他更能接受的是舒婷的抒情传统,而不喜欢北岛诗中的英雄主义。
譬如诗歌《楚王梦雨》,这首诗是对宋玉《高唐赋》《神女赋》中巫山云雨故事的互文性写作。《神女赋》写到楚襄王梦遇巫山神女的故事,《楚王梦雨》则对这个楚襄王求爱不得的故事进行了现代性改写。神女化身水滴赴约,“她的践约可能是澌澌潮湿的”,这是诗人的想象。张枣的诗歌取材巫山云雨故事,来自他对楚地巫文化的强烈认同,巫文化的神秘主义、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对宇宙本源的质疑及其人文精神,都对张枣的诗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源于张枣青年阶段在湖南与川渝两地生活、求学时所浸淫的那种氤氲的地方文化氛围。①
其次,即使是在对中国诗歌传统的扬弃与继承上,张枣也显露出自相矛盾之处。他从诗歌写作对“个人中心主义”的现代性的批判出发,回归儒家文化传统所建构的伦理道德体系,回归对人的日常生活的执着。②
《何人斯》直接取材于《诗经·小雅·何人斯》,并对其进行了以现代性为指向的改写。其一,诗的形式是现代的,但元素和题材都是古典的。比如诗中所出现的意象青苔、山丘、鲜桃等,充满古典气息,这种风格的意象贯穿了张枣几乎全部的百余首诗作。其二,虽然《何人斯》已将《诗经·小雅·何人斯》中略微凄怆的女子对变心的丈夫的怨情改写为并没有多少恨意的苦恋,但诗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对原诗的致敬,前者的前四节和后者的前四节在内容上相对应。其三,张枣的诗也数次取材于《易经》,如《十月之水》,全诗是“渐”卦内容的现代性改写。渐卦的六条爻辞主要是讲循序渐进的道理。为了阐述这个道理,爻辞中用了“女归”“妇孕”“飞鸿”作为例子,而张枣的诗中,“妇孕”和“飞鸿”的例子都被现代性地化用了。《十月之水》第一节的“机密的微风”与第一爻的“有言”在对应,“你和她行走于一根断弦”与第二爻之“饮食干干”(意谓男女双方已结婚,能够和乐地共享饮食)在相对应,第二节第三爻之“夫征不复”在相对应。第三节在内容上与渐卦爻辞对应最明显,“水鸟飞上了山”对应着“鸿渐于陵”,“而我的后代仍未显现在你里面”对应着“妇三岁不孕”,“我如此被封锁至再次的星占之后”暗示“夫征”得还,分离的男女最终得以重聚,这与第六爻之“吉”,也即循序渐进终于实现最终目标的意思也是对应的。
再次,张枣的诗歌中也埋藏着丰富的“西方资源”,这些西方资源不仅体现在西方文化的涵纳等,还体现在借鉴西方语言的修辞方式。在为了完成诗歌创作的美学目标而实施的“化欧化古”的行动中,某种情绪上强烈的不安感、方法论上的自相矛盾,还是不可避免地泄露在了表达情感的诗作之中。
一、张枣运用了西方语言的修辞方式,并化用到诗歌表达中。比如《而立之年》中,“我身上的逝者谈到下一次爱情时,试探地将两把亮匙贴卧在一起,头紧靠头”用来描述对“下一次爱情”的想象时,用“两片亮匙贴卧在一起,头靠紧头”表示恋人间亲密接触的动作,这源于英语词汇:spoon。这个单词表示恋人间头紧靠头、通过身体间的像两片勺子紧贴摩擦的方式进行的亲密举动。在中文语境中,读者会把这句诗当成是对亲密行为的一个比喻,但在英语中它不过是spoon的本意,至多也只能把它看作一个隐喻。深谙外语尤其是德语、俄语的人,也许一读张枣的诗,就能从修辞中发现张枣学习、效仿的对象,但是不懂外语的人,只好从内容,而不是从形式上去探索张枣的诗歌那些特别之处的来源。
二、张枣没有预料到的是,为了更好完成诗歌创作的美学目标而“流亡”到另一种语言中去之后,设身处地的现实与出国前怀揣仗剑远行、替天行道的那种情绪时设想的现实迥然不同。加之上世纪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时代氛围中诗歌抒情激情的消退,直接导致了张枣的好友,同样也是当代优秀抒情诗人的柏桦的暂时停笔,这样的时代氛围的变化,也同样影响到了张枣的写作。当张枣身在域外德国——比当时的中国发达得多的德国,也是现实的德国,是真正地置身在了“现代性”之中。
张枣出国后所遭遇的首先是一些十分现实的问题。其一,“在德国,没什么好吃的。他不喜欢吃西餐”(北岛语)。其二,生活节奏紧张,睡得马马虎虎。其三,经济拮据。其四,很可能还有性的压抑。“在德国,街上哪里有少女啊。”其五,一个中年男人为了承担照顾家庭的责任而背负的压力。“不过我感觉到你的另一面,一种属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男人的怅惘。”①其六,最重要的还是失去了朋友、知音的激发和回馈,失去掌声。种种问题给张枣带来的改变反映在诗歌中是对于祖国、对于自己过去曾生活过交游过的地方的怀念和对自己内心种种矛盾、痛苦的近乎露骨的表达。诗人把出国后自己所身处的地方叫做“假地方”,所流露的情绪是怅惘的。
矛盾在《祖国丛书》一诗中有鲜明的表达,诗中酒、樱桃核、破碎、月亮的脸、水之窗,都是柔美古典的,是诗人深深眷恋的祖国的事物。从眷恋的事物中“溢出”的带有象征意味的意象,意指眼前的这些事物还不是那最贴近心灵的真事物。诗人愿意过上这种域外陌生的但是饱含现代性的生活,毕竟出国是张枣为了实现个人理想的主动选择,但也可能仅仅是一瞬间的“消极性”附体之后的妄言。“人类还容忍我穿过大厅”,诗歌中抒情主体的形象一下就被从“人类”这个群里中剔除了出来,而丧失了合法的人的身份,虽然从诗句的表达形式来看,这个丧失是诗人自己主动的选择。这首诗中,饱含强烈现实感的诗句中所描绘的情景突然成为一个“疯人”眼中的幻象,这和诗人去国后的处境多么相似。时代的变迁导致知音稀缺产生的“孤寂感”。张枣的诗中数次出现了“信”这一意象,甚至生前出版的唯一一本诗集的名字,他都选择了“春秋来信”。《献给CR的一片钥匙》里那封“误投的航空信”和《春秋来信》里的那封信有着相似的思乡意味。一封误投的航空信不经意间竟成了救命稻草,不难从中把握写作者那种漂泊无根的心境。
三、“悖论”的主题建构
张枣诗歌中的重要主题“疾病”“死亡”,也包含着“生”与“死”自相矛盾、自相冲突的悖论。克尔凯郭尔曾区分美学、伦理和宗教的三种生活阶段或层面。其中,美学层面耽于纯粹的感性、肉欲,纯粹的自我反倒失去了个性。伦理层面则以普遍、公开的道德规范压抑了个性。个性的强势张扬应在宗教层面,以基督徒的激情去信仰生存的悖论,信仰荒谬,信仰上帝。“信仰正是这样的悖论,作为特殊性的单一个体高于普遍性,这一点在普遍性之前得到了确证,但它并不作为普通性的附属物,而是作为比普遍性更高的东西。”②
小时候接触的暴力事件、易患病的身体,使张枣很早就通过亲历获得了关于“疾病”和“死亡”的认知。这体现在诗歌中散落的诸多与疾病、医药、死亡有关的意象和表达,如“药方”(《祖父》)、“脉搏”(《望远镜》)、“喂药”(《入夜》)、“发烧畏寒”(《一个诗人的正午》)、“一片推敲宿疾的药片”(《第六种办法》)、“碘酒”(《空白练习曲》)等,以及“我病中的水果”(《秋天的戏剧》)、“死亡猜你的年纪”(《死亡的比喻》)等。
首先,张枣的诗歌中的“生”和“死”,既来自对自身肉身的脆弱所带来的生命易逝感的形而下的关注,也来自从存在主义出发对“时间与生命”“生与死”“人与神”问题的形而上的关切。而悖论就主要体现在这些形而上的追问之中。张枣在《四月诗选》前言中有言:“文学的根本问题是生与死的问题,世界的本质是反抗死亡,诗歌感人肺腑地挥霍死亡。”死亡并不是寄身在诗人的一个时时刻刻需要通过抚摸这样具体的方式去安慰、让它平静的小小魔鬼,而是他所有诗的一个叩问宇宙苍穹希求在自己的灵魂撞击出回声的抽象主题,一个哲学问题。对于置身实在的现代性的诗人来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生命意义的问题是诸问题中最急需回答的问题”。①严肃的诗人必须在写作中对这最急需回答的问题作出回答。
克尔凯郭尔阐释人的“生存悖论”时说,人的生存悖论在于人有了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最根本的恐惧是关于自身死亡的知识。在动物王国中唯独人受此特别的裁决”。②为了克服未知带来的恐惧,人有了求知的需要。但知识反过来又将诅咒加诸求知的人身上。这一诅咒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一旦人对某种事物有了认知就不可能再回到对某事物没有认知的状态。二是由于人不可能一次性对某事物形成全面的认知,因而为了克服不全面的认知所带来的恐惧人又会继续追求对该事物的认知。而人一旦形成了对“死亡”——这个人生在世最急需回答的问题有了第一次认知之后,为了克服“死亡”所带来的恐惧,就不得不寻根究底地向“死亡”的问题追问下去。
其次,张枣对“生”和“死”的思考还在于“死亡”是一种诅咒,是在死去的事物中寻找“生”的事物以求安慰的一次尝试。
“我知道化成一缕青烟的你/正怜悯着我,永在假的黎明无限沉沦。”(《与夜蛾谈牺牲》)诗人羡慕耶稣“一劳永逸”地用死“把所有的生和死全盘代替”,羡慕夜蛾能依从属于它的物种的命运的最高法则,扑火而亡,去往“真的黎明”。 这首诗是诗人二十几岁年纪创作的,在生命蓬勃的时刻,“死亡猜你的年纪,认为你这时还年轻”,“死亡说时间还充裕”。“蛾”意象,以及借这个意象——这个“遨游的小生物”展开的关于生死问题的玄思,在《卡夫卡致菲利丝》第七首中再次出现。“枯蛾紧揪着光/作最后的祷告,生死突然交触/我听见蛾们迷醉的舌头品尝/某个无限的开阔”,从生走向死的瞬间蛾们是迷醉的,这是自然法则赋予没有自我意识的依从者的幸福,而这种幸福在人这里是不存在的。“蛾们”品尝到了无限的开阔,而人这里却是无穷无尽的“局限”。
《哀歌》也谈及“死亡”。诗中,“死”是在死去的事物中寻找未死的事物以求安慰的一次尝试。如果把这首诗作为一首“挽歌”来读,它是以一种曲折的方式来哀悼某个人或者某些人,最后一句“死,是一件真事情”,就是一封信通过“喊”向“我”发出的召唤,让“我”好好地关切生命。在欧洲诗歌的历史长河里,哀歌的源头是形式要求严格的挽歌。即使在象征主义诗歌里,仍然有许多哀歌是悼念已死去的人的挽歌,而挽歌又具有招魂的性质。“设身处地地,谦卑地善待在他人的死中的自己之死”。③这个“喊”字,多么像“如果我哭喊,天使的队列里有谁能听见”里的“喊”(里尔克《杜伊诺哀歌》)。因此,这首诗里,“有人说,不,即便死了/那土豆里活着的惯性/还会长出小手呢”实是有挽歌性质的:在已经死去的人身上还存在着不死,“另一封信打开,你熟睡如橘”,是写一个人已经死去了,但是“有人剥开你的赤裸后说,他摸到了另一个你”,这一句也同样是在写“死”中的“生”。
再次,克尔凯郭尔提及的美学、伦理和宗教的三种层面中,个性的强势张扬应在宗教层面——以基督徒的激情去信仰生存的悖论。从这个层面来说,张枣的生存的悖论还体现在诗歌中对“神”的召唤和与“神”的对语。
张枣诗中的“神”很显然与基督教的“神”完全不同。这里所出现的神,都是张枣的观念中认为其崇高、伟大、神秘而他欲与之交谈的“诗神”。张枣的诗中多次出现“神”这个意象,如“神的望远镜像五月的一支歌谣”(《望远镜》),“神呵,呵气的神”(《孤独的猫眼之歌》)、“像圣人一刻都离不开神”。张枣曾谈到自己的诗歌写作所经历的三个阶段:第一是词是词、物是物的阶段,第二是词物浑然的阶段,第三是词语物又分开、主体重新出现、三者对峙的阶段,类似于悟禅的三个阶段。宗教超越伦理,信仰超越思考,张枣诗歌对“神”的呼唤和信仰目的在于诗歌的创作和现实人生,只有在现实人生中,在诗歌中,张枣才可以与其诗神对话。
张枣的诗中,为了与“神”对语,出现一个个腾空了自身的“空白”,如“这是一支空白练习曲”(《今年的云雀》)、“空白引领乌合的目光”(《空白练习曲》)、“空白之词蜂涌,给清晨蒙上肃杀的寒霜”(《跟茨维塔耶娃的对话》)。当张枣以为已将自己腾尽时,万物就都可以被纳入这些空白中。慧能说:“心量广大,就如虚空……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山河大地……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这时,被纳入人的心灵的空白之中的内容与形式,就都是来源于神了。不过这心灵,也必定是神所照亮的心灵,因此,可以把《空白练习曲》当成是张枣“叩问神迹”后从神那里听来的训诫,张枣作为天使,作为先知将它传达人间。但诗歌之神永远带走了诗人,张枣也真正一生与诗歌相伴,他的写作成为对生存和死亡命题的有力阐释。《空白练习曲》中,这些诗人腾空自身而产生的空白,以及为了照亮空白而形成的诗歌写作方式,牵引出张枣元诗理念中呈现出来的矛盾和张力。
四、元诗悖论及美学反思
关于张枣一再强调和实践的元诗理论,同样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悖论。尽管他一再通过诗句来实践一种言说,但还是一边显露出写作的焦虑,一边显露出这种理论本身的自相矛盾。但“这种张力其实是元诗的生机所在,其中可能的矛盾甚至蕴含着元诗概念的当代性”。①
首先,“元诗”一词内涵丰富,如同张枣的诗歌一样深邃神秘,元诗思维的形成,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状态,如同“荆棘之途”。张枣虽在博士论文中使用过德语metapoetische,但元诗是他在汉语论文中提出延伸的概念。元诗手法既体现在主题上的对诗与写作反思的直接表达,也暗藏于诗行间的意象选取和谋篇布局,也体现着诗人对创作潜意识的剖析和把握,以此揭开那“诗成于写作之前”的前写作状态的玄思谜题。因此,一首具有“元诗性”或“元诗倾向”的诗歌,即可在其内部找寻到有关诗歌秩序的本质表达。②《空白练习曲》第六首的整个滑冰的过程,是对元诗写作的“荆棘之途”的隐喻。“脱身于身畔的伟构”中的“伟构”同时隐喻静默事物的大混沌,“佯媚”这个词是形容女滑者采取的面对观众乌合目光的姿态:一种装出来的取悦人的媚态,也可以很好地比喻张枣的元诗写作姿态,表面上是有女性的委婉和媚态,不过都是佯装出来的。就如诗中“轻月虚照着体内的荆棘之途”这句诗本身质地的委婉与柔媚,也不过是伪装。男滑者最终是滑向了无法取消虚无的造型,那也就意味着,女滑者最终是回到了实在中。但不管是男滑者,还是女滑者,都是张枣自己。有可能女滑者是张枣对初出茅庐的自己的想象中的追忆,而男滑者才代表着这个写作阶段最真实的自己。关键意象“红飘巾”可能意味着词与物完美融合的一个象征物,但在这里,它似乎意味着对诗人的一个永恒的诅咒。《空白练习曲》第九首中“短暂啊,难忍如一滴热泪”的“短暂”一词,在张枣诗中以同样的慨然之姿反复出现。“短暂”这个词始终充满着不祥的意味、宿命的意味,最终也只有连击空白时诗人才存在着。
其次,诗歌为何能够“元”化,从元诗的美学逻辑来说,艺术表现的是创造。元诗既可以把诗歌创造原料表现为主题、结构、语言等形式,也可以作为一种元创作意识。通过元诗写作,张枣表达出对诗歌是什么这一命题的思考。他试图在面对生活诘难时回归本源,写作成为焦虑与辩解的过程。如果把《今年的云雀》看作是稍晚创作的《空白练习曲》元诗理论的一个理论框架,这种自相矛盾和不可解的悖论就体现得越发明显。
《今年的云雀》中,元诗理论相关的关键意象和表达的内涵可以与张枣其他诗作作互文性的解释。比如“但不似药片的那种敲”和“像一片推敲宿疾的药片”(《第六种办法》)。这首诗里最关键的象征性动作就是“敲”:“敲是回家?但家不应该含有羞怯和尴尬。”所以,需要敲的地方,就不是“家”。“但家应该是这儿,这儿”——这一句紧接着又把上一句的意思否定了。“随喊随开,敲。”一个只用“喊门”就能开门的地方是家,相反,一个需要“敲门”的地方,需要羞怯和尴尬地敲门的地方,是陌生的人家。药片的敲在于吻合,吻合某种疾病。空白练习曲之敲,则不屑于吻合某种臆想:对神之形式的臆想——溶解你我才能提纯的神之形式。空白练习曲的敲,只敲形象,形象即本质:自己的里面还是自己,短暂的里面还是短暂。这似乎意味着,“连击空白者”如果不是为了击中某个“中心”,而是为了击中经验中的各种形象,那么此人就永远不是在回家。当敲结束,形象地“化合”成为哑谜,谁也猜不透“你这云雀葬身何方”。敲这个动作的主体很可能就是“云雀”,在这里,歌唱着的人附身云雀之上,云雀歌唱犹如人之写诗。从“我站起”这里开始,诗人换了一口气,来揭秘云雀究竟葬身何方。“无边无限”的墙,是紧承诗的前半部分那些出现在“敲”之后的抽象客体之后的第一个真正的具体的实体。在前面,药片的敲,是比喻意义上的敲,虽然是具体的行为,但本身也被嵌套在一个比喻的诗语结构里,只有“我站起”,摸到了无边无限的墙,才是在这首诗里真实地发生了的行为。墙是无边无限的,没有可以通向墙的另一面的门,因此才有了给它戴墨镜这样一个近似于“刻舟求剑”的举动。“无门可入”只是诗人的一个比喻,云雀还是死于前面提到的矛盾之中,也即“随喊随开”和“敲”的矛盾。敲,似乎是歌唱者不能停止的行为,是其宿命,但敲,如果是不屑于吻合的敲,那它就永远不是回家,而是漂泊。这就是最根本的矛盾。有论者早就指出,元诗“一开始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诗学方案,它在提出诗学路线的同时也直言它的局限”。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欧阳江河对张枣诗歌的判断是对的,他并非一个象征主义者,只有印象主义者才会有这首元诗所表达的诗歌观念。
因此,作为张枣的诗歌理念,元诗立场是一个诗意内核,是诗歌审美的一个类型,是元诗模式下的诗歌走向超现实的维度。张枣从创作论出发,用它来考量汉诗发生的美学过程,但它同时也充满悖论,这是张枣的一种创作反思。《空白练习曲》第一首就有“从来没有地方,没有风,只有变迁栖居空间”。如果张枣并不认同象征主义的诗观,不认为在那些经验现象的背后真的有某种真理碎片的话,“只有变迁栖居空间”,就意味着在宇宙空间中并没有什么恒定不变的东西。现象并非恒定不变,而这些现象的背后,也没有什么恒定不变的真理。这就仿佛是以神之存在为前提的重重判断和推理,最后证明了神的不存在。所以对张枣来说,也许诗歌写作的意义,只在于揭示并直面这些内蕴冲动却不可解的悖论。对于这场勇敢的诗歌冒险的终局,诗人自己大概也是无能为力的。
结语
综上所述,张枣诗歌表达的悖论形态及语言风格得以建构与形成的原因不仅在于其家世与生平所造就的内在的用以对抗暴力的温柔秉性,也在于他诗歌创作的总体美学追求。张枣诗歌的悖论形态表现为俯拾即是的悖论式表达,在内容上则体现在对“时间与生命”“生与死”“人与神”等形而上问题的辩证式追问。张枣的诗在题材上中西合璧,但在“元诗”这一主动选择的诗歌形态中,放弃了对明晰的意义的呈现,而追求通过一个丰满的隐喻语言的花园,来达到叩问苍穹、克服言说危机的目的。但元诗路线的选择也是对“诗是什么”的一次强有力的本体论探寻。而通过对其元诗代表作的分析,可以发现诗人虽努力通过形象的表达建构其元诗理论大厦,其本体自身似乎也是一个矛盾重重的不可解的悖论。不过尽管如此,张枣的诗在代表一代诗人与“空白”对话的道路上,仍然为人们呈现诗歌本来应有的样子。
① 廖昌胤:《西方文论关键词:悖论》,《外国文学》2010年第5期。
② [美]布鲁克斯:《精致的瓮:诗歌结构研究》,郭乙瑶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③ 张枣:《张枣随笔选》,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版,第146—147页。
① 参见傅博:《轻与甜:论张枣诗歌的美学气质及其建构》,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5月,第6—11页。
② 参见敬文东:《味与诗——兼论张枣》,《南方文坛》2018年第5期。
③ 参见[苏]巴赫金:《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论社会学诗学问题》,李辉凡等译,《巴赫金全集》(第2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90—92页。
④ 颜炼军:《诗人的德国锁——论张枣其人其诗》,《北方论丛》2018年第3期。
⑤ 宋琳、柏桦:《亲爱的张枣》,江苏: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81页。
⑥ 张枣、颜炼军:《张枣随笔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1页。
论张枣诗歌中悖论的建构及美学反思
① 参见李双:《论“四川五君”诗歌的传统文化追求》,辽宁大学硕士论文,2019年5月,第19—20页。
② 阮纪正:《儒家文化传统与当代道德建构》,《哲学研究》1996年第4期。
① 宋琳、柏桦:《亲爱的张枣》,第66—82页。
② 刘程:《语言批判 维特根斯坦美学思想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论张枣诗歌中悖论的建构及美学反思
① [法]加缪:《西西弗神话》,杜小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12页。
② [美]厄内斯特·贝克儿:《死亡否认》,林和生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6页。
③ 宋琳、柏桦:《亲爱的张枣》,第165页。
① 王东东:《中国现代诗学中的元诗观念》,《扬子江文学评论》2022年第1期。
② 武钦诺:《张枣抒情诗中的元诗倾向研究》,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22年5月,第11页。
论张枣诗歌中悖论的建构及美学反思
① 李章斌:《走出语言自造的神话——从张枣的“元诗”说到当代新诗的“语言神话”》,《文艺研究》2021年第6期。
作者简介:鲁登,澳门科技大学2021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诗学、创意写作学;赵海霞,澳门科技大学国际学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与文化批评、创意写作、国际汉语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