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级森严的巴黎动物园:《高老头》中的动物性比喻体系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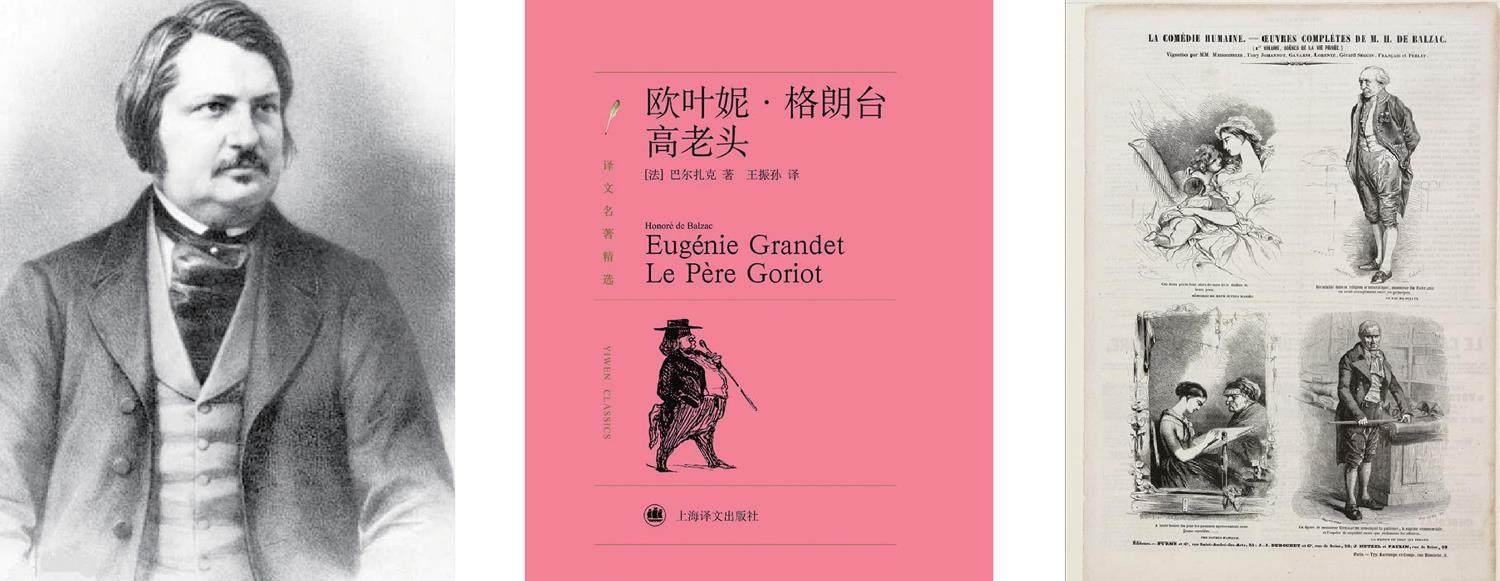

摘 要:在巴尔扎克的小说《高老头》中,作者使用了大量的动物比喻,即通过对小说中各种人物按照社会等级进行分类,并将不同的社会阶层表征为特定的动物类型。比喻方法可以分为临时性比喻和类型化比喻两种:前者是暂时性的,描绘小说人物在具体情境中的临时情态;后者则以标签的形式将社会各层级人物类型化,以自上而下的食物链模式构成一个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结构。在这种金字塔结构的内部,塔尖的社会阶层奴役着塔底的人,塔底的人挣扎着向塔尖攀爬,呈现出真实而生动的社会面貌。这种动物性比喻体系的运用,正是巴尔扎克在创作《人间喜剧》时的匠心独运之处。
关键词:高老头;动物性比喻;类型化;人间喜剧
据统计,巴尔扎克的小说《高老头》中存在着约50处动物性比喻修辞。这类比喻的喻体全部是动物,它们在人物描写中占据的篇幅虽不算多,却十分引人注目。其中,一部分比喻修辞是临时性的,它展示的是人物在具体情境中的某种样态。巴尔扎克依据人物当下的言行举止,将其比喻为最易联想到的动物。这种临时的比拟持续时间短暂,因而并不在本文的比喻体系研究范围之内。相较而言,更值得注意的是另一种类型化的比喻。这种比喻将不同社会地位和背景的人物固定地比作不同的动物,从而构建了一个分层的等级制度。这些不同层级的人物构成了一个严密的金字塔结构,从上至下依次排列,形成了所谓的“动物性比喻体系”。明确动物性比喻体系的分类,对不同类别进行梳理并加以分析,既要考虑到不同人物的身份与处境,又需要注意到巴尔扎克笔下的情感倾向。该体系的明晰对于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创作的整体构建研究之推进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一、动物比喻的自然环境
《高老头》中频繁出现的场所包括德·鲍赛昂子爵府与伏盖公寓两处。小说开篇,巴尔扎克便用较长的篇幅描写了伏盖公寓的样貌与居住其中性情各异的租客们。这座公寓属于刻薄而势利的伏盖太太,她的租客有沉默寡言的古杜尔夫人、唯唯诺诺的布瓦雷、行踪神秘的伏脱冷,以及小说的主人公高老头和大学生拉斯蒂涅克,等等。这些人聚集在肮脏破败的小公寓里,每天在餐桌上碰面并上演唇枪舌剑的场景,堪称真实的社会缩影。“巴黎就像新大陆的一片森林”,在这片森林里“打猎的种类很多,有的猎取陪嫁,有的猎取破产后的廉价处理物资,有的出卖良心”[1]268。弱肉强食的社会里,所有人都在用自以为合理的手段谋求钱财与地位。巴尔扎克将巴黎比作一片森林,在这座城市中生活着的人都是森林里的动物。这片森林似乎没有边界,每个人的野心与欲望都变为囚禁自己的隐形牢笼,一旦入场便难以逃脱。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是拥有牢笼的场域,内部被划分为供不同物种生存的栖息地。当我们阅读这部小说时,读者视角与文本内部世界产生互动,阅读小说的过程如同在全知视角中观看这座庞大的动物园,看各类人物轮番登场,演绎一出出堪称荒诞的戏剧。园子内部呈现出金字塔结构,顶端是以德·鲍赛昂夫人的府邸为代表的上流社会,这是“喧嚣纷繁的蜂窝”[1]414,金钱与欲望化身使人垂涎欲滴的蜜汁,塔底是肮脏破败的伏盖公寓,这是底层人民的生活区域。正如公寓后院里和睦相处的猪、鸡和兔子一般,租客们在泥潭似的环境中容忍着彼此,当他们在气味难闻的饭厅里坐着就像“马槽前的牲口那样”[1]244。年轻的主人公拉斯蒂涅克穿梭在两个区域之间,渴望着走向金字塔的顶端。这样的社会环境正是“动物性比喻体系”赖以存在的基础。由此,《高老头》便成了《人间喜剧》的序幕,它的创作开启了巴尔扎克整个文学大厦的建构。
二、动物比喻
在类型化的动物性比喻中,本体与喻体在性格或身份地位上均有相似之处,每一类比喻都具备特殊含义。本文根据本体差异,将与之对应的喻体分为三个层级,这些层级自上而下呈现出社会等级的金字塔结构。
(一)狮子、老虎和鹰——权力与地位的代表
例1:“可我们又偏偏是像狮子一样的血性人,胃口大得一天可以干出二十件蠢事来。”[1]250
例2:“我是懂法律的,我还能像老虎一样张牙舞爪呢。”[1]250
例3:“您知道您该干什么!好啦,我的小鹰。”[1]268
狮子、老虎和鹰都是金字塔顶端的生物,他们或是上流社会中有着封号的贵族,或是拥有巨额财产的商人。例1是伏脱冷对拉斯蒂涅克说的话。当这位心思深沉的逃犯看穿年轻大学生的心思,知晓后者想要通过某种途径往上爬的野心后,伏脱冷与其有了一段交谈。在这次言语的对峙中,伏脱冷将肮脏但现实的社会准则告知拉斯蒂涅克,试图说服其与自己合作谋求财路。拉斯蒂涅克对伏脱冷提出的建议并非毫无动摇。在他因为身份低微被人轻视时,在他没有多余的钱乘坐豪华马车时,在他沉溺赌场大肆挥霍从而欠下诸多债务后,这位大学生变成了伏脱冷口中嗜血的狮子,开始考虑是否要利用维克多莉娜对自己的感情来夺取她父亲的巨额遗产。即便最后计划未能成行,但拉斯蒂涅克见识了上流社会的纸醉金迷后,已然产生了对金钱和女人更深切的渴望。他希望能走向金字塔的顶端,成为自己人生中爱情和财产的绝对掌控者。伏脱冷再度拉拢大学生时,又将他比喻为“小鹰”,直白地挑明彼此的野心。此时的拉斯蒂涅克在上流社会的销金窟中一再停留,却屈辱地发觉这里没有属于自己的位置。他希望能拥有魔鬼般的力量,将上流社会的女人们抢到身边作为自己地位的象征,就“如同一只雄鹰在平原把一只尚在吮吸母乳的白色小山羊抓进它的巢穴”[1]250。
年轻时的面粉商高里奥先生也曾属于这一阶级,例2中张牙舞爪的“老虎”是高老头对意气风发的自己的回忆。当他有钱有势时,可以为两个十五岁的女儿置办马车,留下几百万的财产使她们对自己百依百顺。然而,高里奥先生对少女非分之想的纵容与迁就,导致阿纳斯塔西和苔尔费娜养成了奢侈放荡的习性。刚从商界隐退的高里奥先生,在搬入伏盖公寓之初,不仅能轻松承担每年一千二百法郎的膳宿费用,还能保持衣着打扮的高标准,享受公寓的最优质服务,甚至引来伏盖太太的觊觎。而当主人公拉斯蒂涅克来到这座公寓时,高老头已经破产,从一头威风凛凛的老虎变成了一条人人嫌弃的野狗。在《高老头》中,巴尔扎克对金字塔第一阶层的描绘大多都是通过底层人士的视角展开的,譬如高老头如何回忆年轻时的意气风发,拉斯蒂涅克在伏脱冷的讲述中想象上流社会的生活等。在子爵夫人的府邸,拉斯蒂涅克观察着社会最高阶层的人物们,渴望着取代他们,从一只受人压迫的家畜蜕变为他人望而生畏的林中走兽,也因此变得不择手段。
(二)马——被奴役的女性
例4:“按照德·隆克鲁尔侯爵的说法,她是一匹‘纯种马……‘纯种马‘名门闺秀等称呼取代了‘天使‘仙女,取代了花花公子们早已唾弃不用的古老的爱情神话。”[1]202
例5:“您只要把男男女女都看成是驿站的马,把他们骑得精疲力竭,每到一站您就可扔下不管,这样,您就能达到欲望的最高峰。”[1]241
例6:“既然做了父亲,就应该永远有钱,应该能驾驭女儿,就像会驾驭劣马一样。而现在我却要跪在她俩的脚下。”[1]398
在金字塔的顶端,还有一种很特殊的生物“马”。小说中,上流社会的女性都被称作一匹马,她们虽然也处于金字塔顶端,却被狮子、老虎和鹰所牢牢驾驭。这是一群为欲望所奴役的人群,她们追求巨额的财产,想要拥有优越的生活条件,也追求崇高的地位,渴望得到名利场上他人恭维与艳羡的目光。她们也追求爱情,又或是单纯的欲望,因为在这些人眼中拥有一个情夫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她们虚荣而软弱,正如例4所写,从前的花花公子称呼女人们为仙女或天使,如今上流社会的男性则将她们称为“纯种马”。上流社会的男性在享受女性给予的感情的同时也在驾驭着她们,考量对方是否值得自己持续投下筹码,一旦有更好的目标出现,他们便毫不犹豫地抛弃从前的女伴。在小说中,拉斯蒂涅克就曾目睹鲍赛昂夫人被抛弃后心灰意冷的境况。爱情早已不再单纯,它成为众人为自己谋取私利的绝佳手段。
拉斯蒂涅克初入上流社会时,在德·雷斯托夫人处吃了闭门羹,因此他又到德·鲍赛昂夫人那里寻求安慰。鲍赛昂夫人对主人公拉斯蒂涅克进行了人生中的第二次教育,她理所当然地告诉拉斯蒂涅克,应当把所有人都当作驿站的马,榨取每个人的现存价值以实现自己的欲望。当人们被骑得筋疲力尽时,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可以弃之脑后而寻求新的“马”。领会了新的社会法则后,拉斯蒂涅克将德·纽沁根夫人视为自己追寻的那匹马,他渴望得到这个女人的爱,因为一旦苔尔费娜对自己另眼相看,她周边所有的女人也都会迷上自己。显然,只要所有女人都觉得某一个人有能耐,她们身边的男人们也会跟着高看这个人一眼,这便是鲍赛昂夫人为拉斯蒂涅克指点的成功之路。拉斯蒂涅克也因而看清了社会的本质:法律与道德毫无约束力,金钱和地位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高老头临终时,拉斯蒂涅克陪伴在他身侧,听到高老头充满愤恨地斥责女儿们是劣马,后悔自己没有通过金钱驾驭她们。高老头的一生似乎又再一次印证了鲍赛昂子爵夫人对拉斯蒂涅克的“教诲”。
(三)驴子、狗和候鸟——平凡的大多数
例7:“其余两间是为‘候鸟准备的,这些穷苦的大学生……每月只出得起四十五法郎的膳宿费。”[1]183
例8:“这家伙似乎曾经是系在我们这个巨大的社会磨坊里的一头驴。”[1]185
例9:“难道我会像野狗一样死去吗?这就是我爱他们一辈子的报应,被她们抛弃。”[1]401
金字塔的第二阶层是各式各样的种群。这个层级的人们既没有钱也没有地位,仅仅是一群平凡的底层人民。贫苦的大学生们是种群庞大但居无定所的“候鸟”。他们之中,有的只想认真读书,找份安稳工作度过余生,有的逐渐被巴黎的繁华迷住双眼,拼命想挤进上流社会。值得一提的是,“候鸟”这一比喻暗示了这座金字塔中阶层的流动性。虽然等级森严,但并非没有上升的通道。拉斯蒂涅克这只候鸟就一直渴望着离开自己的栖息地,到上流社会闯荡一番,变成威风凛凛的走兽。而高老头的一生则是从金字塔的顶尖坠入塔底,这样的阶级跌落往往比攀升更易于实现。阶级的流动性暗示着无限的可能,能够最大程度地激发出每个人内心对金钱和权利的渴望。而不想高飞的候鸟逐渐定居下来,就变成了以布瓦雷先生为代表的可怜又可悲的底层群众,他们深受社会的压迫,像一头终日只知围着磨盘打转的任劳任怨的驴。
在这群人中最可叹的是高老头,他也是《高老头》这部小说中被比喻为“狗”的次数最多的人。曾经的高里奥先生身处意气风发的第一阶层,破产后的他却成为伏盖公寓里的受气包,人人都以取笑他为乐。伏盖太太用最恶毒的言语诅咒他,“愿他不得好死,孤零零的好像狗一样”[1]135。为了女儿们能拥有更好的生活,高老头一再缩减自己的开支,从一头意气风发的“老虎”变为孤苦伶仃的“野狗”,甚至被女婿们赶出家门,临死也未能见到女儿们最后一面。直到生命尽头,他才意识到自己悲剧的一生正是软弱与溺爱的报应。
(四)蝙蝠、臭虫和蜘蛛——互相残杀的世界
例10:“这只老蝙蝠,我一见她就心惊胆战。……这个面色苍白的老处女就像一条长长的蛀虫,能把房梁蛀空的。”[1]235
例11:“别人可以把他像臭虫一样掀死,他是扁平的,臭不可闻。”[1]250
例12:“你们就要相互吞食,就像一个瓶里的蜘蛛。”[1]268
在金字塔幽暗潮湿的角落里,生存着蝙蝠、臭虫和蜘蛛等生物。巴尔扎克将为了三千法郎出卖伏脱冷的米肖诺小姐比作“老蝙蝠”“蛀虫”和“毒蛇”,认为对金钱的渴求扭曲了她仅存的人性。而布瓦雷先生唯唯诺诺地做着米肖诺小姐的跟随者,遭到众人的鄙弃,也像一只臭虫般毫无尊严地离开了伏盖公寓。
事实上,在彼时的巴黎,每个人都是第三阶层的生物。正如伏脱冷和鲍赛昂子爵夫人对拉斯蒂涅克的规训所言,人与人的关系如同瓶子中的蜘蛛,将他们关在一起迟早会相互吞食。弱肉强食是森林中的生存法则。伏脱冷为获取金钱引诱拉斯蒂涅克走上不归路,拉斯蒂涅克和苔尔费娜之间真心与假意的相互利用,高老头的另一位女儿阿纳西为过上体面的生活不惜疯狂压榨自己的父亲,又在高老头失去价值时弃之如敝屣。每个人都在为金钱和权力奔走,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择手段。社会中并无真情,只有生物们互相残杀并吞食彼此的残酷景象。
三、《人间喜剧》的序幕
各种各样的动物聚集在巴黎这座庞大的动物园中,因各自身份与地位不同而构成了一个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结构。这种动物性比喻体系是否是巴尔扎克有意为之?他建构这样的比喻体系对《人间喜剧》的创作又有何意义?对于创作理念的追溯,从这位伟大作家的生平经历也可见一斑。
巴尔扎克的母亲出身资产阶级家庭,受到母亲的影响,金钱至上的观念自小便在巴尔扎克心里扎下了根。1816年,他进入巴黎大学索邦学院学习法律。读书期间,巴尔扎克进入事务所成为见习生。在见习过程中,他目睹了无数家庭的悲剧和被轻易抹去的罪行,这些都成为了他日后创作的养分。在1834年创作《高老头》时,巴尔扎克萌生出将自己所有作品组合成一个整体并描绘出完整社会风貌的设想。也正因此,《高老头》和《人间喜剧》的相关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前者的创作正式拉开了《人间喜剧》的序幕[2]。
在《人间喜剧》的序言中,巴尔扎克谈到自己的创作念头“来自人类和动物界之间的一番比较”[3]前言3。生物学家夏尔认为,“世上只有一种动物,造物主只采用了唯一的一种模式来创造一切有机生物,动物是一种本原,只为适应它所处的生长环境而采取各自不同的外在形式”[3]前言3。巴尔扎克接受了这种说法,随即联想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相似之处,如同生物学将动物划分类别一样,“社会也根据人类进行活动的不同环境,将人类划分成各种各样的人”[3]前言3。他在“序言”中提到生物学家布封以及其笔下展示动物界全貌的著作《自然史》,希望自己能同布封一样,用一部作品描绘人类社会的全貌。布封的《自然史》分为动物、植物、矿物、人类和自然的世代五个部分,其中描写动物的篇章分为家畜、野兽和禽类。这位生物学家对各类动物都做出了生动幽默的评价,譬如“马是一种舍己为人的动物;它能满足人类的一切要求;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不会拒绝主人的命令,尽一切力量为主人效力”[4]。诸如此类拟人化的描述,生动地突出了马这一种群的特性,仿佛是将动物当作人来写。巴尔扎克则反其道而行之,将人当作动物来写,把类型化的人物和具有相同品性的动物联系起来。可以认为,巴克扎克在创作《高老头》时已经在有意识地描绘着一个由动物性比喻体系建构起来的等级社会。这种创作上的实践也彰显出巴尔扎克对象征美学的追求[5]。
巴尔扎克认为,“动物之间相处很少有惨剧发生,它们你追我逐,不至于有什么错综复杂的情节,人与人之间也像动物一样互相角逐,但因为他们多少有一些智谋,就使斗争格外复杂起来”[3]前言3。也许,人类的本性并无善恶,又或者说,兽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阴暗面。而在彼时的法国社会,偏重金钱与名利的社会境况使人类兽性的一面得到了无限滋长,并最终使所有人都变得面目可憎。在巴黎动物园中,在这个森严的金字塔结构里,每个人都渴望成为狮子,却最终都变成了令人唾弃的臭虫。
参考文献:
[1]巴尔扎克.高老头[M].王振孙,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沈大力.“众庶的圣西门”——巴尔扎克作品色调辨证[J].外国文学,1999(4):87-89.
[3]巴尔扎克.人间喜剧[M].丁世中,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4]布封.自然史[M].桂金,译.北京:台海出版社,2017:15.
[5]彭冬林.巴尔扎克作品的象征美学向度[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13.
作者简介:牛清原,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俄苏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