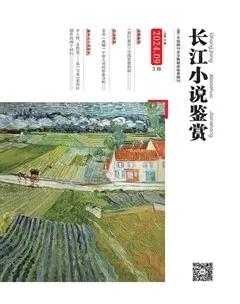传统志怪小说与电影的融合与变革
许嘤戈
[摘 要] 志怪小说作为中国特有的文学类型,体现着千百年来古人对于物质世界的朴素想象与探索。《山海经》《淮南子》《列子》等典籍中的神话传说,可以视为后世志怪小说的先声,而自东晋时期,干宝创作《搜神记》起,志怪小说便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忽略的一种文学形式。清代更是中国志怪小说的巅峰时期,诞生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与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志怪小说的创作范式与母题也逐渐形成——对周围事物进行“人化”,以“人、妖、情”作为主要内核。20世纪80年代志怪小说的瑰丽想象与凄美故事在影像世界中兴起,在20世纪90年代到达顶峰。小说作为比电影更早成熟的艺术形式,可以对电影带来引导与启发,志怪电影直接从志怪小说中汲取养分,加之以电影独有的艺术表达形式,最终形成独树一帜的电影风格。本文试从志怪小说和志怪电影的融合、发展过程中的题材同质与形式主义、当今的重构与突破三个方面来浅析志怪电影的发展。
【关键词】 志怪小说 志怪电影 集体无意识
[中图分类号] I24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2097-2881(2024)09-0105-04
一、历史传统下的发展与融合
电影作为造梦的艺术,与志怪小说对于世界的怪奇想象在形式上天然适配。志怪诞生于人们对自然现象、周遭事物的神秘化理解与精神释放,当人们无法用科学去解释事物时,往往会加之以一种神秘的诠释。在《电影:呈现画面的文学》中,萨斯皮格指出在小说作品中,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可以对电影形成启示[1],而且电影中的叙事也呈现小说情节的特征。而以古代文化为土壤的志怪小说,之所以能与新生的电影艺术相融合,也在于从古至今一些科学尚未解释的事物所形成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在《电影萌生的温床:论文学的启发与渗透》中,热奈特提出电影产生经历的四个阶段:成熟文学的产生、文学与电影的交汇、文学技巧与情节的启发、文学渗透电影[2]。志怪小说已经发展成较为成熟的文学形式,在志怪小说当中除了想象之外,还有对现实的讽刺不满以及对传统的美好人格的巩固铸造。志怪小说其中的故事情节之曲折离奇、想象之瑰丽多彩、内涵之广袤深邃,无疑滋养着志怪电影的诞生与发展。文学与电影要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在一定的时代中塑造人物与讲述故事,反映一个时代下的思潮。因此志怪小说与电影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过磨合与互通之后,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走向成熟。中国志怪小说当中的怪奇情节与想象,为电影供给不竭的养分,成就了中国志怪电影。志怪电影的成功,一方面是志怪小说的曲折情节,一方面则是猎奇的狂想展示在银幕世界中形成的奇观。《青蛇》中有地上穿梭的青白二蛇,《画皮》中有身披人皮的厉鬼,《画壁》中有进入奇异世界的书生,这些奇丽的情节与场景,不断刺激观众的观看欲望,满足其心理需求。
志怪小说与电影的融合,体现着民族集体无意识,以及中国美学的继承。中国志怪电影与西方魔幻电影虽都取材于民间想象,怪力乱神,但志怪小说之下是儒释道三教的交融,与“希腊—罗马文明”“希伯来—基督教文明”所构成的“双希文明”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思想内涵上,《指环王》中体现的是希伯来文化中的自我救赎、克服原罪与欲望;《诸神之战》则体现希腊文化中的多神论以及人化的神;但中国志怪电影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之下,始终描写“此岸”的故事,角色始终贯穿“忠孝仁义”。哪吒原型来源于佛教,《那拏天经》中记载了一位身着虎皮的千臂巨神,手中持有日月法器,常态为一头二臂的儿童,这便是哪吒的原型。经过民间故事不断地发展与完善,明清时期哪吒逐渐形成当今被我们熟知的故事,在哪吒的形象即故事本土化的过程中,人们给他赋予儒家思想的内核,哪吒为不连累父亲,拔剑自刎,则是“孝”的体现。除此志怪小说中不乏有情有义的妖,如聂小倩、婴宁等等,这些塑造出来的经典角色无一不体现着儒家文化的浸润。而白娘子、聂小倩这些动物修炼成人形,将动物人化的设定,也体现着中国独有的美学观念:对待世界的理解,人与自然界不是割裂的,人与万事万物也不是敌对的,是一种“大乐与天地同和”的和谐关系,所以动物可以修炼成人,而人与妖之间也会产生爱情,体现的则是中国美学中和谐共生的关系。全球化的影响使得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随着全球化的加深,西方文化的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扩大,传统文化面临着被西方文化同化的风险。年轻一代更容易接触到西方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认同感减弱,而志怪小说这一具有中国传统美学的文学类型与新兴艺术电影的结合,其所诞生出的志怪电影类型,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它可通过文化寻根来达到本民族的自我认同。
二、发展过程中的题材同质与形式主义
在志怪电影逐渐成熟的同时,其短板与弊端也逐渐呈现:过分依赖视觉奇观与题材的雷同不变,导致志怪电影在形式上随着科技的进步不断刺激与震撼观众的视觉,但是在内容上却过于单调,逐渐形成同质化内容与形式化视觉,甚至形成视觉符号吞并叙事主体的局面。
志怪小说一直以来的最大特点就是奇异的想象,在电影中则转化为一种视觉奇观,通过带有猎奇色彩的视觉场面来刺激观众的审美体验,志怪电影也成为当代“吸引力电影”的重要类型之一。《妖猫传》里竭力刻画唐宫夜宴的浮华、妖猫杀人的玄乎,旨在通过猎奇的场景“让电影回归视觉艺术本体论的层面”。但是过度追求、依赖视觉上的奇观同时也造成对电影主体的反噬,《阿修罗》中炫目的场景与拼凑的符号,将视觉奇观过度夸张,最终使得一个个拼凑起来的视觉符号吞并了电影主体。在《电影萌生的温床》中,热奈特指出,文学作品的情节所带来的“思想”和灵魂给读者所形成的冲击,是电影应该向文学作品所学习的[2]。而过分依赖视觉奇观以至于放弃与观众思想上的共振,无异于是志怪电影的自我阉割。
在内容情节方面,志怪电影题材的同质化是最大的困境。在《中国小说发展绪论》中,胡适将人妖相恋认为是志怪小说永恒的母题[3],但是在志怪小说的发展中,文学作品试图冲破此母题或者在此基础上可以有所创新。《聊斋志异》中除了人与妖凄美的爱情故事之外,也有《缪生》这样带有寓言式的劝诫故事;除了对于忠贞爱情的赞美之外,也有《曲绣》中为了存活而不得已吸尽恋人灵气的狐妖。但是在志怪电影中,最常出现的便是人与妖忠贞的爱情这样一成不变的题材。1987年的《倩女幽魂》中身为狐妖的聂小倩与宁采臣生死不渝,而到2015年的《钟馗伏魔》依旧是狐妖与人类忠贞不渝的爱情,情节内核并未产生丝毫变化,变化的只有视觉奇观,无非是一种“新瓶装旧酒”,如此同质化的题材也让观众产生对于志怪电影的审美疲劳。
志怪小说作为父权社会下的产物,在故事层面带有强烈的男性视角与性别倾向,志怪小说中出现的几乎都为“女性鬼”与“男性凡人”。在父权社会中,男性掌握着写作与阅读的权力,“引诱并且以身相许的女鬼”是具有吸引力的存在,女妖、女鬼既不是人,则不需产生道德观上的负担与谴责,而她们又是人化的存在,具有人的思想情感,便可以产生情感与肉体欢愉。在志怪电影中,男性视角下的女妖是主流存在,女性形象的塑造在男性视角下产生扭曲,一方面女妖引诱男人,一方面女妖又对主角忠贞不贰,女性角色连带猎奇场景一同,成为视角符号的存在。而在当代性别平等意识中,如何塑造女性形象无疑成为志怪电影创作过程中重点考虑的问题。
三、时代变化中的叙事调整与风格演变
在面对志怪电影对于同质化故事内核、人物塑造,以及过分追求视觉奇观的形式主义方面,可以通过热奈特对于探究文学与电影之间关系的理论来寻找突破。在《电影萌生的温床》中,他认为对于电影的启示文学主要体现在技巧与情节上。“没有不为了人物的情节”,人物与情节紧紧串联在一起,是文学与电影作品中最重要的创作核心,志怪电影的突破也必然是针对于题材同质、人物刻板、视觉形式的突破。
在题材选择方面,志怪电影可以更多从冷门志怪小说中进行汲取,或者结合当下时代背景进行创新。白娘子与许仙的故事,在商业上是占据极大优势的,作为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传说故事之一,每个人都对它有足够的了解,并且爱情也是十分受大众欢迎的题材类型。但是在一千多年的流传中,不管是古人对于故事雏形的完善与再次改编,还是如今众多电影、电视剧、小说对于《白蛇传》的再次创新,都将白娘子、小青、许仙、法海四个人之间的关系与可能发生的故事进行新的突破与创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白蛇传》在故事叙事方面已经达到了饱和,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将这个故事进行再度创新,但却保留故事原型,如何用“新瓶”装这样一杯“旧酒”,是十分考验电影的剧本创作的。《白蛇缘起》首先在故事设定层面做到了另辟蹊径,没有采取大家都选择的许仙与白娘子在西湖相遇的故事,而是讲述许仙与白娘子的“缘起”故事,即他们的前世故事。虽然这是一次大胆的创新,但是若把握不好故事方向仍称不上一部成功的电影。在故事创作中,编剧保留了《白娘子》故事中的母题——“爱情”,白娘子与许仙之间跨越人与妖界限的爱情,在此部电影中仍是故事的内核,只不过人物成了小白与许萱。志怪电影在时代的嬗变之中,唯有跳出之前已经成熟的传统志怪电影的创作题材,才能再次在银幕世界中焕发生机。
在性别平等意识的当下,传统志怪电影中典型的男性视角之下的女性鬼已然成为落后的人物形象存在,被扭曲的女性形象已经不符合当下观众的需求,在当下出现了具有酷儿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志怪电影。《画皮2》里小唯与公主之间暧昧复杂的情绪,虽有形象突破,但女性的身体仍然作为景观在志怪电影中处于被凝视、被观看的地位。在传统的人妖相恋的故事中,都是尽可能地将女妖人化,使女妖符合男性主角的生活与秩序,不管是无数个影视版本的《白蛇传》,还是故事相似的《倩女幽魂》,或者是发生在现代的《我的女友是九尾狐》,都是女妖来努力成为人。在《白蛇缘起》中,许萱因为爱情,选择了去成为一个和小白一样的妖,打破人与妖之间的等级差异,男性角色选择追随女性角色,这样的情节,是极为少见和吸引人的。
当下志怪的视觉奇观,逐渐受到西方魔幻电影的影响走向异质化,各种拼接的文化符号在志怪电影中屡见不鲜,反而丧失了中国传统美学的意境与韵味。志怪电影的巅峰时期,在视觉上未曾脱离中国传统美学,在电影《青蛇》中,徐克便以写意的方式来刻画法海的情欲。尽管当下的志怪电影逐渐脱离传统美学,但仍有坚守中国美学的存在。动画电影《白蛇:缘起》中宝青坊的木箱在组合之后如同中医的药柜,半空中浮动的孔明灯,颠倒的水面(在此水具有一种神秘感),国师出场之时,白色的战士形同排列整齐的千纸鹤,是折纸元素的一次运用。这些极具古典风格与美感的场景设计,为故事裹上了一层精美的外衣。在展现许宣与白蛇的情愫时借助水的倒影来映出主角,坐船渡河的许宣与白蛇倒映在水上,道馆的蒙蒙雨夜两人相拥在一起,“水”这个意象,本身具有一种神秘、朦胧和暧昧感,如同巫山雨云这个词一般。在两人的感情发展阶段,多次运用水的意象,浅显地来看是使画面更加具有美感,再深一层,便是水带给人的暧昧,是情愫的产生,欲望的强化。这些独具中国传统美学意境与韵味的志怪电影,通过艺术的形式来增强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感,从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这是我们处于同质化现象严重的现代社会中对于自己族群文明源头的探索与向往,是对自我主体的一种寻找与确认。志怪小说与电影结合,可以传承传统的民间神话传说,将其故事和人物形象通过电影的形式进行再现,让大众重新认识和了解传统传说,保持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时,通过现代化的转述,可以为传统神话传说注入新的元素和创新,使其更能与现代观众产生共鸣。同时,通过现代化的转述,还可以使传统神话传说更具有全球化的视野和吸引力,吸引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参与和欣赏。
四、结语
在当下,志怪电影的品质虽然参差不齐,但志怪文化的持续繁荣表明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以顺应时代的变化,并从中不断丰富自身。志怪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文人勇敢的隐喻和幻想拓展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版图,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古人们的瑰丽幻想提供了银幕空间,使其探索了一种在当今社会环境中仍然合乎逻辑的叙事。然而,志怪电影的影像只是隐喻的载体,其内核最终将转向人们面对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如何突破本土和外来之间的冲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心,构建独具中国美学的志怪故事,是当今志怪电影实现新的突破所面临的课题。
参考文献
[1] 萨斯皮格.电影:呈现画面的文学[M].//西方电影理论选粹(1901-2000)宗白新,选译.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2.
[2] Gérard Genette.The Warm Bed of Movies Coming:on The Enlightenment And Coming of Literature[M].Modern Movi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
[3] 胡适.中国小说发展绪论//胡适文集(第4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特约编辑 范 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