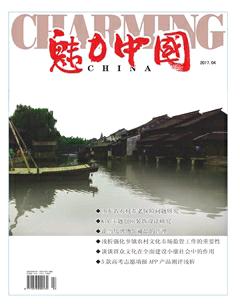试论中国武侠电影中的“武”与“侠”
张梅 李轶天
摘要:中国武侠电影自诞生以来就注定了其必须具备两个元素,即“武”与“侠”,武侠电影并非一蹴而就,它有着极深的文化渊源,其文化必源头便是中国的武侠文化和文学作品。对“武”与“侠”的认知和界定并非天然有之,它是伴随着武侠电影的发展和成熟而逐渐趋于正统的。下文笔者将试着对武侠电影进行一个概念上的简单界定,并将“武”与“侠”的历史源流、发展流变进行梳理与归纳。
关键词:武侠电影;集体无意识;侠文化
随着武侠片的发展及人们观念的变化,“侠”的形象越来越多元,武侠文化经历千百年始终占据老百姓内心一角的原因却是其表现的侠义主题给了生活在体制下的平民们一种精神安慰。
武侠世界必须有一个可供叙事的环境,即通常意义上的“江湖”。本文将武侠电影的范畴做出如下界定:从“武”(表现形式)与“侠”(内在精神)的关系出发,以“侠”为划分标准,以“武”为划分依据,以“江湖”为叙事环境,所谓武侠电影,是指在远离政权,自成规则的生存环境中,以武为主要方式宣扬侠义主题,讲述侠义故事的影片。
一、武侠电影之“侠”
“侠”字最初与“任”字通假,最早出现与《墨子·经上》篇中的“任”。但历来人们对“侠”的认知并不固定,韩非子在他的著作《五蠹》中,曾将侠归为对统治者存有威胁的一类,要求统治者将其“诛之”。
而西汉的司马迁与韩非子的观点却不同,他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写道:“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行,其信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游侠列传》记述了汉代著名侠士朱家、剧孟和郭解的行侠史实,司马迁在书中多次提到“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热情的赞扬了他们的高贵品德。《游侠列传》的出现不仅开创了一种史学的传说,即让历史上的真实出现的侠进入到了历史的记载中,同时开创了侠文学和侠文化的先河。
关于中国最早的武侠电影,有两种说法,其一是1920年任彭年导演、陈春生编剧的《车中盗》,其二为他的另一部影片《荒山得金》。其实无论是哪一部作品都表现了侠义主题,均以复仇为主线表现了惩奸除恶的铮铮侠骨之气。最具典型性的是五十年代在香港风靡的《黄飞鸿》系列,黄飞鸿这一英雄人物被刻画成了一个充满儒家风范“儒侠”。 黄飞鸿除了外在形象更具儒家风范外,其侠义指向也更具民族性,除了惩恶扬善、扶贫济弱、行医救人外,黄飞鸿的侠义精神更多的体现在其爱国救国的义举上。如果说传统的惩恶扬善是侠骨小义,那黄飞鸿系列所表现出的爱国情怀则是名族大义,所谓民族英雄侠之大者便是如此。
但说到真正将民族精神傳扬于世的则非70 年代的李小龙莫属,李小龙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功夫片正式形成并走向了世界舞台。与《黄飞鸿》系列不同的是,李小龙的形象不仅是传统的惩恶扬善的“侠”,或是怀有爱国情怀的“民族英雄”,更是走向世界显示国威的“时代英雄”。 虽然李小龙的影片永远在强调和表现个人英雄主义,但其实他的影片中也充满了富有时代感的自嘲精神。但将自嘲与武侠结合的最为精妙的非成龙莫属, 在1978 年的影片《醉拳》中,成龙一改黄飞鸿老成持重的形象,将其变成了活泼嬉闹的“问题少年”。而尊师重道的传统师徒关系也通过嬉笑怒骂的方式发生了转变。
二十世纪90年代以后的武侠电影也被称之为“新武侠电影”,将现代人的认知和思维以武侠的形式进行演绎和宣扬是其最突出的特点。在这一时期的武侠电影中很少看到对“侠”的歌颂或崇拜,取而代之的是对所谓正统侠道的讽刺与揶揄,传统的“侠”精神遭受到了来自多元化价值观取向的挑战,武侠的价值构成和严肃性受到了空前的颠覆。《鹿鼎记》(1998年)中的玩世不恭的武侠形象,《卧虎藏龙》(2000年)中对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认同,《英雄》(2002年)中对善恶观念的模糊界定,《武侠》(2011年)中对自我价值的认同,《太极1:从零开始》(2012年)中对武侠进行游戏化、趣味化的处理,这一切形式的背后,都透露出了一个讯息——“侠”精神的的重新整合消解了中国传统武侠的价值体系,使“侠”的含义得到了无限的延伸,但同时也不得不接受时代的考验。
二、武侠电影之“武”
“武”的艺术呈现是武侠电影中必不可少的视觉元素,也是判定武侠电影类型的重要标准。武侠电影中的“武”不仅具有审美表意功能更兼具叙事这一重要使命,其“武”也并不专指我国传统武术,它兼具戏剧、武术、舞蹈、杂技以及民俗元素等众多艺术元素。甚至随着门户的开放,武侠电影中的“武”更多的开始吸取其他民族的特色,逐渐呈现出一种全球化的包融性。
1.武与“技”。
“技”即技艺,强调技巧性和形式感,武侠电影中的“武”除具备攻击性外,创作者还会有意识的对其进行艺术加工使之具有观赏性,一个拔剑的姿势、一个挥刀的动作都能将武侠风格营造出来,即以传奇性铸就武侠性,以神怪斗法代替功夫技击。
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武侠电影开始大量聘用武术指导、动作导演等专业武术人员来设计和指导影片中的武斗,武戏的展现越来越具备攻击性和实战性。进入 21 世纪后,数码科技可谓开创了全新的武侠新样式,其动作设计更多的被电脑特技替代,如《功夫》、《七剑》等。其“武打”设计的形式感也从武侠电影诞生之初的粗浅神怪上升到了一个高峰。
2.武与“击”。
“击”即攻击、打击,强调格斗性与力度感,中国武侠电影中武戏的原形是中国武术。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期间,武侠电影的主战场从内地转到了香港,并得到了空前发展。这一时期,“真功夫”在武侠电影中开始出现并衍生出一种以格斗为主的技击美学。
70年代中后期,喜剧元素进入到武侠片并风靡一时,它是真功夫为寻求自身突破,成龙作品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作。80年代中后期,“现代江湖英雄片”勃然崛起,经典之作有吴宇森导演的《英雄本色》(1986年)、《纵横四海》(1991年)等。江湖英雄片具备了许多时尚元素,如新时代的车辆枪械,跨地域的异国风情及感人的兄弟情谊。
20世纪90年代开始,武侠电影逐渐倾向于以电影科技的发展来营造银幕视觉奇观。人物的武打动作越来越依赖摄影技术、剪辑和三维动画等电影技术的帮助,呈现出飘逸、唯美的形式化武打场面。“特技武打”成为这一时期武侠电影的主要特征,代表作有《新龙门客栈》(1992年)、《东方不败风云再起》(1993年)、《东邪西毒》(1994年)等。进入 21 世纪后,数码科技可谓开创了全新的武侠新样式,纯粹的武术真功夫已经不再为武侠电影所热衷,其动作设计更多的被电脑特技替代,数字技术的运用几乎完全渗透到了影片的各个叙事环节之中。如影片《天地英雄》(2003年)、《功夫》(2004年)、《神话》(2005年)等。
伴随着功夫展示的多元化进程,其暴力展示的视觉冲击随之不断加强,但展示暴力不是武侠电影的任务,那些一味渲染暴力而无实际劝诫意义的武侠片也必将随着历史的进程逐渐淡出观众的视野。创作者们如何在展示必要暴力的同时运用富有精神内涵的叙事主题或外在格斗动作的多变形式来消解暴力本身的残酷性成了武侠电影创作的重要使命和难题。
参考文献
[1]贾磊磊.中国武侠电影史[M].第一版.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4.
[2]徐南明.富澜.崔君衍.电影艺术词典[M].第一版.2005.12修订版. 69.
[3]汉许慎.说文解字[M].中华书局出版.2004.2.
[4]于果·明斯特伯格.电影:一次心理学研究[M].1916.
作者简介:
1.张梅,戏剧与影视学,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
2.李轶天,电影学,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