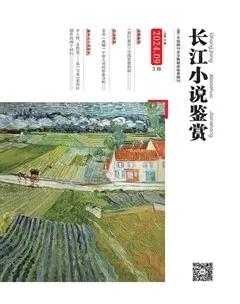家乡、历史、女性——张翎小说主题探究
徐静
[摘 要] 张翎,作为北美华文文学重要的作家之一,在加拿大旅居几十年。身在异国他乡,她用自己的小说创作表达了对家乡的追忆、对历史的回顾、对女性的关切。家乡藻溪、历史创伤、女性艰辛成为其创作的小说的三大主题,本文便对这些主题进行逐一分析。
【关键词】 张翎 家乡 历史 女性
[中图分类号] I24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2097-2881(2024)09-0066-04
张翎的小说聚焦于家乡、历史、女性这三大话题,她笔下的故土藻溪是充满原始生命力但也有些世俗的浙南小城,她对历史的叙述是为了让人们直面历史中的创伤和灾难,她塑造的女性在历史沉浮中、在故土、在他乡坚韧地生存,从她们身上,能看到藻溪的印记,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
一、对家乡的追忆
在张翎的小说中,我们常常能看到“藻溪”这个地名,许多故事也在此地展开。藻溪,温州苍南的一个小镇,是张翎母亲的故乡,承载着属于母亲的故土记忆。张翎曾在采访中提到,在她小时候,母亲和其他长辈们不停地给她讲述藻溪的种种趣事,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她笔下,藻溪是一个原始蓬勃且又饱经沧桑的浙南小镇,如同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纯粹善良,但也自私世俗。
1.原始纯粹的藻溪生命力
藻溪镇里有条“藻溪河”,《阵痛》开篇就提到这条河流不长也不宽,然而到了雨天,这条河流却成了翻脸的悍妇,湍急汹涌。依水而建的藻溪镇也被河水影响,充斥着奔流不息的原始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深深烙印在每一个藻溪人的基因中。《阵痛》中,上官吟春和月桂婶一起,带着刚出生的小桃,离开藻溪,来到温州城,改名换姓,在一间小小的卖热开水的铺子里将小桃抚养成人,“只要活着,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你什么都能看见”[1]。这种生命力让上官吟春成了勤奋嫂,让小桃于炮火中生下武生,武生在午夜马路上生下路得……
《雁过藻溪》中,末雁回到藻溪,安葬母亲的遗体。在藻溪的山水滋养下,她渐渐逃离了一直禁锢她的两座牢笼——母亲和丈夫的冷漠。藻溪的日子是一种藏了头掐了尾没有因缘不问结果没心没肺的日子,愚昧简单省心,甚至有些隐隐的快乐[2]。百川,是藻溪蓬勃原始生命力的集结者,他简单直白,不顾伦理道义,和末雁(后文知道他们两人是亲姑侄)发生男女关系。在和百川相处过程中,末雁沉睡几十年的生命力被唤醒,她可以和百川、灵灵,甚至和自己的前任越明开些世俗的玩笑,直面自己的欲望,她变得鲜活起来了。“末雁说完了,就暗暗吃了一惊,没想到自己如此木讷的个性,到了藻溪,换了个地界,竟也变得伶牙俐齿起来。”[2]“越明,你去死吧,你老婆离老,还有几里路呢。”[2]
蓬勃原始的生命力镌刻在藻溪人骨子里,即使远离家乡几十年,但只要一回到家乡,这种生命力就会被唤醒,人们互相帮助,善良简单,有着独属于浙南小镇的温情味道。“月桂婶是下街的一个寡妇……上街下街谁家有事,都喊她过来帮忙——也算是接济的意思。”[1]
2.自私落后的藻溪世俗性
与其他小镇居民一样,藻溪人或多或少带有着世俗气息,也有自私落后的一面。
《雁过藻溪》中,末雁的母亲黄信月,原本是藻溪大户人家的千金,从藻溪一路逃到温州。但当信月嫁给温州城的大官宋达文后,藻溪乡人却来寻求信月的帮助,无论是看病、找工作这种一家一户的事情,还是需要化肥农药灾款的大事情,他们带着乡下的特产,怯懦地敲响信月家的后门,希望这个曾经被全乡人伤害过的女人能够不计前嫌,让他们得到一些实际好处。
《阵痛》中也有这种世俗落后性。上官吟春误以为自己怀的是日本人的孩子,投河自杀,婆婆吕氏为了救她和肚子里的孩子,先是找了道姑喊魂念经,然后才派人去叫郎中;除此之外,吕氏十分渴望一个男孙,吕氏第一次见到上官吟春的时候,她紧盯着的是上官吟春的腰臀,衡量着吟春的生育能力;吕氏可以忍受男孙生于乱世的简陋,但绝不能接受吟春肚子里的是个女孩。
藻溪人身上的世俗性、落后性受到历史、传统、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毋庸置疑,他们的确有令人可恨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可悲。
二、对历史的回顾
张翎的小说常常直面历史,揭示在历史沉浮中,人们(尤其是女性)最真实的、悲惨的生活状态,这也形成了她小说主题的一大特色——创伤叙事。回顾历史,我们总会自觉而不自觉地躲避那些血泪、挣扎、苦难,而张翎以一种可贵的勇气向历史发问,透过小说背后,我们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能看到坚韧的人。
《金山》可以说是一部海外劳工的百年奋斗史,以艾米和欧阳云安的现代对话,再现了方氏一家从晚清到土改时期经历的历史风云,时代洪流的每一次涨潮都精准淹没了方家。方元昌因过度吸食鸦片而死,15岁的方得法一夜之间承担养家的责任,成了金山客,漂洋过海挣钱财,但金山并不是遍地金银,金山伯也只在家乡风光,对于金山来说,这些天朝子民是最廉价的黄种劳工,是“猪仔”苦力。他们忍受着海水的颠簸、封闭污浊的空间,背井离乡,开启了艰辛的人生新篇章。方得法不是个例,《金山》也不是虚构伪造。在晚清,曾有成千上万的华工前往北美洲淘金、修建铁路,他们变卖土地家产,筹措船费,拿着薄弱的工资,承担最危险的工作。太平洋铁路的每一个枕木下,都沉睡着一个中国劳工的亡魂。他们不懂得修建铁路是为了什么,能带来什么,他们只知道,等铁路完工后,他们就可以得到一大笔工钱,寄回家乡,如果钱够的话,还能荣归故里,娶妻、买田、盖房。但当最后一颗道钉敲进枕木,加拿大政府揭开了排华反华行动的序幕。《华人入境条例》的颁发,人头税的增长,禁止华工亲属来加拿大……多少华工永埋在大洋东岸,孤魂无法安宁。
他们在大洋彼岸吃尽了苦头,用筋肉、血泪换来的银票一点点抠出来,将自己的思念和牵挂植根于银票里,寄到此岸。然而时代变迁,日月更新,那头吃了苦,这头也不得歇,他们的家人在此岸也无法生存。他们的家人还是会经历战争、饥荒,甚至因为家里有个金山客,成了别人的眼中钉。《金山》里,有专门盯金山客家人的土匪,六指和锦河便曾被土匪劫走,变卖田产,东拼西凑才被赎回。[6]
张翎的其他小说中也有对战争、“文革”等历史事件的描写,《阵痛》中,人物命运起伏,是时代交接更替的结果。赵梦痕,资本家的大小姐,家境优渥,摩登时尚,她从象牙塔里跌落,成为一名女工。抗战,南下干部的儿子,他的父亲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也十分风光,然而到了“文革”,也被审查打倒。更不必说勤奋嫂、小桃这种普通人,他们只能顺着历史的洪流,听从历史的安排。
这些被历史裹挟着的人们,并不都只无奈地被历史推着行走,也有挺立潮头,想要改写历史的前进方向。《金山》中的欧阳先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作为一名教书先生,热衷国事,批评时政,后来参与戊戌变法。作为欧阳先生的弟子,阿法也用自己的力量,试图改写历史。在听完梁启超先生的演讲后,他停止了如日中天的洗衣馆生意,卖了两个衣馆,把绝大部分的钱捐给了北美的保皇党派,希望大清国能够再次兴起。“大清国若是略为强壮些,你我何必抛下爷娘妻子,出走这洋番之地,整日遭人算计讹诈。”[3]他的儿子锦山,也从卖菜得来的钱中,时不时搜取一点,捐给革命。在他们身上,我们能够感知到人们对时代的反抗,但历史的车轮即使偏颇,最终还是会回到应有的轨迹中。
历史是一堆灰烬,但在灰烬之中仍有余温。张翎的小说,在对创伤的揭露下,让我们看到了个体在历史中的生命轨迹,这是值得被记住的温热。
三、对女性的关切
张翎深受家族女性生命韧性的影响,因此,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她自然而然更了解女性,更关注女性,更同情女性。在她的小说中,如《金山》《阵痛》,常常以一个女性的成长历程为起点,衍生出几代女性不同的成长故事,每一代女性都有着自己的困境和艰辛。
第一代女性是以麦氏和吕氏为代表的婆辈。作为封建时代的典型女性,她们遵守三从四德,始终维护男权社会的核心利益。丈夫在世时,她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为丈夫生出儿子、养活儿子。因此,麦氏为了治好放得善的病,将年仅13岁的女儿阿桃低价卖给了别家做婢女。丈夫死后,她们便成了家庭中的权威,她们的重心和依靠全部转接到儿子身上,“大先生是吕氏手里的一只风筝,吕氏让他飞多远就是多远,一寸不多,一寸不少”。[1]对于以吕氏和麦氏代表的婆辈来说,她们的困境就是家庭男性的缺失。方得善死后,麦氏只剩下阿法这一个儿子,但阿法远在金山,几十年才能回趟家,麦氏带着对阿法的挂念熬完了自己的生命,而她死后,阿法也没有机会来坟前祭拜。同样,吕氏和她的儿子——大先生聚少离多,她死前也记挂着大先生,除此之外,她还挂念着未出生的孙子。事与愿违,大先生死在吕氏面前,吟春肚子里的是个女孩。
第二代女性是以六指和上官吟春为代表的母辈。她们从一个稚嫩的少女,转变成了博大的、坚韧的母辈。她们的困境分为两个部分,一方面,她们要忍受来自婆婆的压迫,丈夫的无情。六指伺候麦氏28年,为了照顾麦氏,她和阿法不得不分离在大洋两岸,在麦氏病重的时候,剜下自己的肉滋补麦氏。而阿法却在大洋对岸找到了新欢知己——金山云,甚至想把她带回开平,“阿贤是好人,不会容不下你”[3];吟春一开始就作为替代品被大先生关注,在吕氏仔仔细细打量过她的腰臀之后,被迎娶进了陶家,进入陶家之后,吕氏迫切地想要一个孙子,逼迫吟春扛起陶家的未来。至于大先生,当他误以为吟春怀的是日本人的孩子之后,他怪罪吟春,说她是贱人,肚子里的孩子是贼种。另一方面,丈夫长期在外,她们的肩膀压上了养家的重担。六指嫁入方家时,她意识到从此刻起,她的命就不再是她一个人的了,而是要剁得细细碎碎,和方家所有人的命擀在一起,再也分不出你的我的他的了。[3]六指也的确将整个生命献给了方家,生育三个儿女,抚养成人,为麦氏送终,守护着得贤居。吟春在大先生病倒之后,也明白了从今往后,她再也没有指望了,只能一个人跪着爬着,一毫一寸地,把塌了的天再慢慢扛回去。[1]她带着小桃,成为了勤奋嫂,改名换姓来到了温州,在一间老虎灶中把陶家唯一的后人抚养长大。
第三代女性是以区燕云、猫眼、小桃为代表的年轻女辈,她们的困境主要是和丈夫之间的尴尬情感。区氏,是六指为锦河挑选的妻子,但锦河并不想和自己的妻子隔着山海,他心中最合适的妻子人选是阿喜,可亨德森太太拆破了这桩姻缘,他只能和区氏结婚,让阿法早日抱上孙子。区氏只和锦河生活过几个月,之后便再也没有见过锦河。猫眼,作为锦山的妻子,和锦山也并不是两情相悦。她从番摊馆逃出来,将锦山作为救赎,紧紧抓住。锦山也只能好心收留她,“这一个男人从一开始就没有喜欢过她,却为了不叫她在街上饿死冻死”[3],即使当猫眼成了方家的主要经济来源,锦山仍时不时提到她的过去,在梦中呼唤的依旧是桑丹丝。小桃,爱上了留学中国的越南学生——黄文灿。但黄文灿最终必须回到千疮百孔的家乡,怀着身孕的小桃只好嫁给她喜欢但又不喜欢的宋志成。
第四代女性是以延龄、武生为代表的更年轻的女辈。对于她们来说,家庭是最大的困境。延龄从小生活在父母的争吵下,对那个拮据的家庭十分厌恶,因此她不断地出逃家庭,在陌生的城市中感受自己的生命,然而,她的每一次逃离都以失败告终,最终带着艾米回到了没有祖父和母亲的家。武生,在得知自己的导师——布夏教授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黄文灿之后,无法接受她的生命是个遮天蔽日的谎言,和小桃大吵了一架,在杜克的宽慰下慢慢接受了这个事实。
四代女性都有着各自的隐晦和心酸,但不同代际的女性无法相互理解,反而彼此对抗,呈现出一种僵持的关系。麦氏和吕氏压榨着六指和吟春,麦氏认为六指有六个指头,是晦气的象征,是六指抢占了阿法;吕氏则盯着吟春早日怀上儿子,让陶家后继有人。六指、吟春也和年轻女辈们僵持着。六指也像麦氏压迫过自己那样对待区氏和猫眼。她不承认曾经是妓女的猫眼是锦山的媳妇,即使在阿法破产、锦山受伤、锦河从军后,寄回开平的银票都是猫眼挣来的。六指也包办了锦河和区氏的婚姻,然而对木讷的区氏极其不满意。勤奋嫂和小桃也有着对抗,勤奋嫂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小桃身上,当小桃没交算术作业时,勤奋嫂扇了小桃的脸,同样,小桃无法理解母亲的艰难和节省,因为“老虎灶西施”这个称号给年少的她带来了很多苦楚,被排挤在班级之外,在招生考试的面试环节,被考官们讥笑。在第三代女性和第四代女性之间也能看到这种僵持关系,得知身世的武生责怪小桃的欺骗,想对小桃嚷“我没有求你生我”[1];猫眼顾不上青年时期延龄的自尊心和冲动,延龄也无法体悟猫眼养活一家人的难处,延龄出逃家庭,没见到猫眼的最后一面;猫眼望着延龄的房间,叫一声延龄之后便撒手人寰。
张翎笔下的女性带着独属于自己的酸辛,孤独地、艰苦地活在家乡,活在异国他乡。
四、结语
张翎的小说主题紧紧围绕着家乡、历史、女性这三个大主题。在加拿大几十年,她积攒的故土记忆排山倒海涌泄出来[4],在书写家乡时,张翎也重新来到了她记忆中的温州藻溪。对家乡的追忆离不开对历史的回顾,战争、“文革”这些历史创伤也深刻影响着浙南小城。回顾历史时,张翎的视野不仅仅局限于故土,她的写作疆域拓展到了广州,描写了两百年前的华工生存境遇。对故土的追忆,对历史的回顾都是通过女性展露出来,女性用不同于男性的姿态迎接着历史,用更坚忍的态度反抗灾难和创伤。自诩字匠的张翎,用她的文字锻造着历史长河中的隐秘角落,用女性的形象呈现出灾难和创伤,重塑自己精神上的故土。
参考文献
[1] 张翎.阵痛[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
[2] 张翎.雁过藻溪[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 张翎.金山[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4] 张翎.张翎作品集:长篇小说卷(全六册)[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21.
[5] 阮丹丹.情感·创伤·女性:论张翎的小说追问[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5).
[6] 陈姻吟.张翎小说《金山》中的华工书写[J].新纪实,2022(10).
(特约编辑 范 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