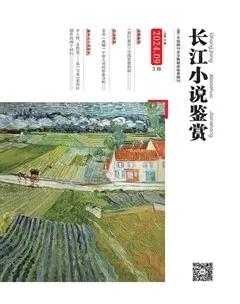老舍《离婚》中张大哥的形象分析
张钰
[摘 要] 张大哥是小说《离婚》中最具有小市民性格代表性的人物,他深谙旧社会规范秩序,万事都奉行敷衍妥协的生命哲学。经历了儿子被捕、惨遭敲诈等事情,他怯懦、无能、没有与强权斗争的勇气。在事情解决后,也没有对黑暗的社会提出质疑,反而重新迎合强权。老舍创作的核心思想是对小市民自身弱点和缺陷的深度剖析和多方面思考,在对人物形象进行塑造的背后是对造成这种性格的社会形态和文化环境的反思和批判。剖析张大哥的人物形象对于理解小市民的困境书写有着极大帮助。本文重点分析《离婚》中的张大哥形象,从“热心妥帖的好人哲学”“自私敷衍的庸人善意”“平庸怯懦的悲剧底色”三个部分来研究张大哥这一形象行为的深层逻辑。
【关键词】 老舍 《离婚》 人情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4)09-0031-04
李长之曾经比较鲁迅和老舍,认为“同是讽刺,鲁迅的是挖苦,而老舍的乃是幽默。鲁迅能热骂,老舍却会俏皮”[1]。不同于前者的毒辣讽刺,老舍的文字和故事都带有温情和宽厚。由于出身市井,老舍能够以平等体贴的姿态去客观地观察底层市民,把握和洞察老百姓的复杂心理。因此他笔下的角色,国民劣根性的讽刺和可贵品质的讴歌通常同时存在。《离婚》是老舍本人最为满意的作品,创作仅用了七十余天,一气呵成,结构精巧,语言凝炼,精彩纷呈。它的问世标志着老舍创作的成熟。这部小说塑造了许多鲜活生动的人物,洞悉了时局变动中知识分子的彷徨和愁闷,引起无数人的共鸣。其中作者主要塑造的张大哥形象具有极其深刻的复杂性,他是旧社会市井人情和腐败官僚机构下诞生的典型,是新旧交界时期保留着看似讲究传统美德实则极度局限苟且的老派市民。张大哥复杂形象下蕴含的人生哲理,对现如今的我们仍大有启迪。
一、热心妥帖的好人哲学
在小说开头,老舍这样给张大哥定性:“张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你总以为他的父亲也得管他叫大哥;他的‘大哥味儿就这么足。”[2]张大哥爱好做媒和反对离婚,他博学,不走极端,统领着一众人物,是北平生活圈中的核心角色。张大哥的每根神经都能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他极善于与人交际,奔走斡旋、溜须拍马都信手拈来。他的生活经验与百科全书具有同样性质,什么都懂什么都会,走到哪人缘都好,到处都有人脉和朋友。因此哪怕他的学问和资格并不如其他科员,在财政办中也属“伟人”级别的,既体面又富态。
张大哥是个热心肠的人,不仅不坏,甚至说得上善良。当他敏锐捕捉到同事老李为离婚事情犯愁时,便热情邀请他去家里吃涮羊肉。他并不认同老李心中追求的诗意,认为他应该将老婆孩子接到城里来,自己的老婆自己教,再多陪陪孩子们,死心塌地做好小职员,一生便很是完美了。为了打消老李的顾虑,劝解老李不离婚,张大哥热心地为老李奔波操劳,“老李,你只须下乡走一遭,其余的全交给我啦!租房子,预备家具,全有我呢……你打算都买什么?来,开个单子;钱,我先给垫上”[2]。一阵安排下来,老李不再言语。张大哥并不是只嘴上指点的假把式,他替老李寻好了新租的房,离电车站近,离市场近,清净整洁,又在心中细细过了一遍家具如何摆放,请了裱糊匠去糊好窗户顺道打扫卫生。
老李接乡下老婆孩子来到了北平,在财政办小赵眼中是可以戏弄老李的大好机会。他借口让老李请吃饭,将李太太和小孩忽悠到西餐厅,故意看他们出洋相。因着冬季里的便宜煤是小赵假公济私送的,张大哥没有出面制止小赵的轻薄无礼,但他也没有冷眼旁观老李一家的窘迫笨拙。当老李一家遭受小赵刁难时,张大哥也在恰当的时机替李太太解围,应付小赵等人的嘲弄,细心周到。尽管张大哥无法理解老李的内在矛盾,但却是真心诚挚地关心老李一家。当李太太带着两个小孩进北平时,张大哥夸赞她能干利落,又夸两个小孩聪明。在饭局结束后,又善意地宽慰李太太,告诉她小赵的本性恶劣,与他计较就是和自己过不去。
无论何时何地,饭桌上、酒局中,张大哥总是游刃有余,他擅长帮助他人,也乐于发表高见。每日觥筹交错,迎来送往,朋友遍布天下。作为市民阶层的中流砥柱,他通常扮演着指点那些刚刚完成阶级跃升小年轻的“人生导师”。他用言行教育着年轻人,如何适应社会的规则,如何游走在新旧的夹缝当中为自己谋得利益。张大哥并不渴求着高权势和高地位,恰恰相反,他认为自己是生活的智者,懂得知足、温良、与世无争,是一个清清白白、本本分分的老百姓。他对自己所持有的“优等百姓”身份有着强烈的优越感,并且将它视为每个人生活的最佳方案。这点体现在他对儿子的期求当中:“张大哥对于儿子的希望不大——北平人对儿子的希望都不大——只盼他成为下得去的,有模有样的,有一官半职的,有家有室的,一个中等人。科长就稍嫌过了点劲,中学的教职员又嫌低一点;局子里的科员,税关上的办事员,县衙门的收发主任——最远的是通县——恰好不高不低的正合适。大学——不管什么样的大学——毕业,而后闹个科员,名利兼收,理想的儿子。”[2]安稳妥当地活着,万事求中庸的生活哲学是张大哥一以贯之的智慧,但这种智慧说到底只是充斥着庸俗气的小聪明,当黑暗席卷而来,这些小聪明就毫无用武之地。
二、自私敷衍的庸人善意
先展现人物的光亮一面,再叫他出丑,是老舍极为擅长的。张大哥其实并不像外人看上去那样的体面,引以为傲的人生智慧和热心肠实际上是“敷衍上糊弄下”的灰色行径。
张大哥热心助人,做媒时自诩是显微镜兼天平,保准双方都满意,但是在用天平衡量的时候,他只在乎“年龄,长像,家道,性格,八字”,却对更为重要的内在思想和情感不屑一顾,对自由婚姻更是嗤之以鼻。旁人求他帮忙,他也尽力去斡旋。二妹妹的丈夫考了假的医师证,又用石膏开药害死了人。行骗害人被抓本是为社会除去一害,张大哥却不分黑白,仅因为二妹妹的婚事是他做媒,便要负责到底。先是安抚二妹妹情绪,又义不容辞替妹夫奔走,不仅托人说情放了庸医,甚至认为只要过些时日再度行医就行了。靠送人情获取医师证,又靠送人情摆脱牢狱之灾,不过是将事态敷衍过去,再装作无事发生重新开始。老舍借老李之口揭示道:以热心帮助人说,张大哥确是有可取之处,但若以他的办法说,他确实可恨。在这种社会里,老李继而一想,这种可恨的办法也许就是最好的。
在经济上,张大哥收入稳定,在社会认可度上,张大哥是公认的好媒人。尽管生活不奢华,比不过上流社会,却也远远好于下层的无产者们饥寒交迫居无定所。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物质基础滋养下,小市民阶层极易产生满足感。稳定的生活状态,使他们产生一种宁静安全的幻觉,而与他们地位相应的知识水平,又使他们易于接受封建文化思想的渲染,来完成对自我的训化。在这样一个靠人情便能打通的腐朽社会中,张大哥的良善是迎合社会的第一次自我规训,但他的善意只能继续保持社会的黑暗。确切地说,他将自己打磨成社会所需求的模样,这种环境下产生的善意在庸人手中已经成为病态,看似是张大哥作为长者帮助年轻人渡过难关,实际上他是代表着统治阶级去驯化更多的民众,教导他们属于旧时代的规章秩序。张大哥虽然生活在现代社会里,但是仍然信奉着传统的道德观念,保有着封建宗法下的阶级思想。他没有向上跨越阶层的冒险精神,而是盼望着自己目前稳定的生活没有波动,战战兢兢地维护着眼前的完美生活。在黑暗的政治社会下,他们选择主动取悦官场上位者,靠送人情、拉关系来加深与上位者的联系,以此求得保住自己的地位。对他人的规训,不过是渴望借此笼络到更多的志同道合的人,与他结成利益联盟,从而来巩固自己阶层的私利[3]。正因如此,张大哥的善意是有预设条件的,他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施以援手,当老李和小赵有冲突时,他先等小赵达到嘲弄目的后,再出于善意提点李太太,他配合小赵的举动在老李看来,比小赵的戏耍更加可恶。
在异化程序中,是非混淆、黑白颠倒,不透明的行政制度和司法制度长期捂住了民众的眼睛,让普通民众误认为自己似乎乐意生活在黑暗里,偶尔出现的光明,使得这种封闭制度下获利的人们难以忍受,不得不闭上眼睛。
三、平庸怯懦的悲剧底色
行事中庸、明哲保身不仅是老舍笔下旧市民所秉承的,也是几千年来很多中国人奉为信条的人生哲学。这一基本思想看似朴素睿智、真知灼见,实际上掩饰了平庸、守旧、愚昧、自私的普遍人性[4]。
张大哥帮助老李有一部分原因是他对老李深表同情,因为他认为老李是乡下人,生在乡下是极其不幸的。有趣的是,在他看来除了北平外都是乡下。由市民阶层文化教养出来的偏见,使他持有北平中心论的优越感,并将人分成了三六九等。他本身是瞧不上老李这类阶级的人物的,尽管他们不是坏人,甚至说得上是热心肠,但庸人的善意只能使社会的黑暗继续下去。只有当黑暗敲响他们自己的大门,他才半梦半醒地意识到自己与他们瞧不起的那些阶层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市民阶层的政治冷漠是必然,张大哥从不过问政治,他的政治态度就是没有政治态度。“不论对什么人,他都不说一句伤人的话,因为在他看来,骂一句人都是有负于礼教的。对于革命党,他必定永远留着神,躲着走,非到革命党做了官,他是决不送礼的。”张大哥的智慧和善意都是一种在政治夹缝中尽可能平安无事的生存方式,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偏偏这样一个绕着政治走的人,他的儿子却陷入了政治危机。张大哥的儿子张天真不知道为什么竟以“共产党嫌疑”被逮捕了,用尽人脉和关系,查不出缘由也不知道被哪个机关带走,张大哥筋疲力尽,恨不得哭死,四处托关系,但那些平日里同阶层交好的科员处长都对他避之不及,曾经花大力气维系的良好人脉关系,不过都是些镜花水月,无法为他提供任何帮助。小科员们连说“几张纸”都有改成“几篇纸”的必要,“张”字犯禁,大家都后悔曾经认识了这么一个人。正如奥维德所说“一旦乌云笼罩你的头顶,你就孑然一身了”。为别人帮了一辈子忙的、平时谁也不肯得罪的张大哥,在儿子因有共产党之嫌被抓走之后,只有老李一个人为他不安。在张大哥病后,老李决心为张大哥做些什么,问遍科员都没人肯帮忙,只能腆着脸向同科室的小赵求助,将自己当作“浮士德”抵押给小赵,求他替张大哥奔走。小赵答应放天真出狱,却借机要求张大哥将女儿秀真嫁给他。小赵风评不好,平日里是替科长太太做些上不得台面的脏事,张大哥不愿意为了儿子把女儿推进火炉,便提出用半生心血攒下的房屋和钱财与小赵做交易。小赵一面收了张大哥的一所房屋和老李的二百五十元,一面装作和秀真情投意合引诱少女,准备来个财色双收。“秀真笛耳,已经到了手;你的二百五十元,咱正花着;张大哥的房子,不久也过来!”[2]倘若没有丁二爷碰巧得知秀真与小赵谈恋爱,不忍心自己看着长大的秀真落入虎口,为报答恩情刺杀小赵,恐怕张大哥难以解脱这个困境。
在经历强权霸凌后,张大哥没有走出封建宗法的灰色阴影,又不敢和那个圈子里的高位者作斗争,他只能继续沿着原先的路径走下去,再次依附于权势。怯懦驯顺的思想让张大哥没有意识到官僚制度和统治阶层的不合理,恰恰相反,他更加在意强权依附,并由此生出自信,认为只要自己熟知了里面的套路和门道,再野蛮的强权也能与之周旋。然而说到底,他所能尽的最大能力也不过是延续先前的敷衍哲学罢了[5]。
老舍安排这个一辈子在市民社会中左右逢源的张大哥,在突然来临的意外中失去了生活的平衡,被他曾经如鱼得水游走的灰色制度狠狠击垮。这样的情节设计使得张大哥的地位实现翻转,在遭受小赵这类真正和统治阶级有所利益勾连的人的倾轧之时,张大哥不再担任“导师”“大哥”这类高高在上的提携人的角色,而是变为了被束缚住的羔羊,任人宰割。当被强权压迫时,张大哥怒斥命运的不公,哀叹道:“活着为儿女奔忙:儿女完了,我随着他们死。我不能孤孤单单地活到七老八十,没味儿!”他甚至不敢去反抗强权。几个月的愁苦和担惊受怕使张大哥变了样,头发白了许多,脸上灰黄,连背也躬了些。而危机散尽后,张大哥又对小赵的高抬贵手感恩戴德,全然忘记小赵敲竹杆时的丑恶嘴脸,反而将小赵看作放出天真的大恩人,要请他首座吃饭。自认倒霉,只求息事宁人,这将小市民阶层妥协、怯懦、自私的性格暴露无遗。
天真回家后,张大哥马上恢复了原先的模样,请吃饭、送人情、替人做媒,三两下解决了二妹妹的事。不仅重新回到财政所任职,还再次被人奉为座上宾,仿佛又是最开始的大哥形象,但他花白的头发和弓着的背清楚地暗示着他只是重操旧业,再次套上了社会为他定好的模具,在里面蜷缩着贫乏的灵魂。财政所的众人在结局恢复一团和气,关系比之前更加融洽,这让老李觉得索然无味。在社会动荡、思想碰撞的年代,形成固定思维的张大哥们规避了个性化的思考,规避了对新事物的探索,为了维持现状,他们放逐了自己的内在生命体验,同时也放逐了原本可以丰满的灵魂。在自私利己、敷衍中庸的逻辑使然下,他们迎合社会,以一种非自立状态与非本真状态的方式存在,并且锁住通向“诗意”的大门。贫瘠的灵魂难以滋养精神追求,这既无益于社会,也困住了自己。
四、结语
在小说《离婚》中,老舍着眼于他最熟悉的北平市民阶层,融合灰色悲剧,联通腐朽的官僚政治和黑暗的人情往来,创作出张大哥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张大哥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淳朴的温良、热心、讲礼节,又在异化社会的挤压下变得因循苟且、自私愚昧。又由这样一个人物引领着一众闹离婚的中年夫妻,在零碎琐事间揭露出以小市民阶级为代表的国民性的弱点。在道德式微的异化世界里,具有棱角的生命力在无形中被扼杀,只有敷衍才是唯一的出路。民众明明身在其中被规则秩序剥削,却觉得这样是正确的。财政办里,勤恳做事的老李被众人瞧不起,排挤在圈子外,反而是热衷于做媒的张大哥混得风生水起,工友等虚伪庸碌之辈对张大哥不仅没有意见,反而上赶着伺候,如此他们便也能靠张大媒人娶个合适的媳妇。有才华学识的人无法迎合混沌的社会秩序,个人的努力受到打压,毫无用武之地,浑水摸鱼的糊涂虫仅依靠旧式社会法则就能在台面上张牙舞爪。如此病态社会下的异化文化和价值取向造成人的异化,长期受到它的熏染便造成了人性的扭曲与畸变。
时至今日,张大哥并没有随着时代改变而消失,无数普通人仍困在其中。社会上依旧存在着千千万万个“张大哥”,高谈阔论,好为导师,实则妥协保守,精神贫瘠。甚至人们自省时,也能在自己身上窥探到“小市民”的影子。检视灵魂,警醒悲剧重演,老舍的文字为我们审视社会和自身提供了新的探索出路。
参考文献
[1] 李长之.李长之批评文集[M].郜元宝,李书,编.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
[2] 老舍.离婚[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18.
[3] 吴小美.市民社会灰色人物的灰色悲剧——评老舍的长篇小说《离婚》[J].兰州大学学报,1984(1).
[4] 司小同.为赋深意巧言辞——谈老舍《离婚》的错位艺术[J].名作欣赏,2009(6).
[5] 于永凤.几乎无事的悲剧——老舍小说《离婚》的“小市民性格”解读[J].名作欣赏,2010(5).
(特约编辑 杨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