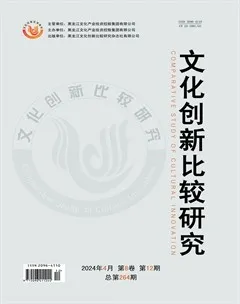他者视域下《啊,拓荒者!》中女性移民身份重构分析研究
康春雪 杨素珍 李欣玥 卢灿 盛睿航
基金项目:云南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资助“‘他者视域下薇拉·凯瑟作品中女性移民身份重构分析研究——以‘草原三部曲为例”(项目编号:202310673055)。
作者简介: 康春雪(2003,2-),女,河北沧州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通信作者:杨素珍(1966,4-),女,云南会泽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美国西部文学,英语教学,通信邮箱:sarahy424@163.com。
摘要:薇拉·凯瑟是美国第一位描写西部拓荒时代的女作家,被誉为20世纪美国最杰出的作家之一。该文以“他者”视角深入探究其代表作《啊,拓荒者!》中女性移民身份的重构过程。运用文本分析法,深入探讨乡村异化、父权束缚及移民排斥等议题对女性移民身份的影响,展现她们所面临的“他者”身份困境,以及从“他者”到“自我”的身份转变过程。这一转变过程涉及摆脱“他者”身份的束缚、解构种族与性别的限制、实现身份的重建,并克服文化冲突,最终实现文化交融。该文旨在丰富薇拉·凯瑟作品研究,并为美国女性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持。
关键词:《啊,拓荒者!》;薇拉·凯瑟;女性;移民;他者;身份重构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110(2024)04(c)-0015-05
A Study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Female Immigrant Identities in
O Pione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ther
KANG Chunxue, YANG Suzhen, LI Xinyue, LU Can, SHENG Ruihang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500, China)
Abstract: Willa Cather, the first American female writer to depict the Western frontier era, is hailed as one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authors of the 20th century.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female immigrant identities in her seminal work, O Pione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ther". Employing textual analysis, it explores the impact of issues such as rural alienation, patriarchal constraints, and immigrant exclusion on female immigrant identities. The novel portrays their predicament as "others" and their transformation from this status to selfhood. This transformative process involves breaking free from the shackles of "the other," deconstructing racial and gender limitations, reconstructing identity, and overcoming cultural conflicts to ultimately achieve cultural fusion.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nrich the study of Willa Cather's works and provide new perspectives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American women's literature.
Key words: O Pioneers!; Willa Cather; Women; Immigrants; The other;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薇拉·凯瑟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文学史上与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等齐名的著名作家[1]。她以其细腻的笔触和深刻的洞察力,将美国西部拓荒时代的故事娓娓道来。在她的作品中,女性形象常常扮演着重要角色,她们身上所展现的移民身份重构历程,不仅是个体的成长史,更是时代的缩影。本文从“他者”这一独特视角出发,以薇拉·凯瑟代表作《啊,拓荒者!》为例,分析作品中女性在城市化语境下的乡村“他者”身份、父权制建构下的女性“他者”身份和美国文化背景下的移民“他者”身份,探究女性移民摆脱“他者”身份困境、重构身份,以及克服文化冲突并实现文化交融的过程及其重要意义。
1 “他者”视域解构
“他者”的概念起源于西方哲学,是指自身以外的一切人、事、物,“他者”的对立面是“自我”(“同者”)[2]。“他者”视域指的是从“自我”以外的一切人与事物的角度来看待世界和自我。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创立了20世纪重要的哲学流派——“现象学”,并定义“他者”为人与人关系中的主体间性的概念基础[3]。
“他者”视域强调了不同个体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并提倡尊重和包容不同文化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多样性。“他者”视域可以帮助我们跳出自我中心的局限,开拓我们的认知,建立更加多元包容的世界观。通过采用“他者”视域,我们可以学会以平等、开放和尊重的态度去看待和处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
2 城市化语境下的乡村“他者”
十九世纪末,美国城市化进程正值加速之际,大量人口从乡村涌入城市,以寻求更好的生活机会。这一时代变革的巨轮,带来了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与城市文明的崛起,而乡村,似乎在这股潮流中逐渐沦为边缘的“他者”。然而,薇拉·凯瑟的《啊,拓荒者!》一书却为我们呈现了一位与众不同的乡村女性——亚历山德拉·伯格森。作为一名乡村拓荒者,她在城市化浪潮中选择了坚守乡村,与土地为伴,成了城市化语境下独特的乡村“他者”。
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市和乡村存在对立和冲突的前提下,小说在处理文明与荒野的关系时并非“一刀切”,而是展现出一种相对矛盾的态势。城市化的浪潮并未因亚历山德拉的坚守而停下脚步,尽管主人公深爱着荒野与土地,但她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城市文明的影响。她认为,城市生活代表着自由的行动和灵活的思想,而长期在乡村中劳作则可能使人的头脑变得愚笨、四肢变得僵化。因此,当她的弟弟艾米需要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做出抉择时,亚历山德拉希望自己的弟弟可以离开这片固守的土地,去城市中寻找更广阔的天空。所以,她决定将弟弟艾米送进州里的大学学习,由此可以看出,在艾米的培养问题上,亚历山德拉希望他能够脱离土地的羁绊,成长为一个拥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现代人。当艾米从墨西哥归来后,亚历山德拉也由衷地感到欣慰,并说道:“总算有一个能适应外面的世界,没有拴在犁耙上,有着与土地无关的、自己的个性。”因此,可以看出,艾米的成长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亚历山德拉的期望与梦想,这其中既包含着她对于城市生活的向往,也暗含其对于现代文明的追求。由此不难看出,作者在处理亚历山德拉关于文明与荒野关系上的矛盾态度:一方面对于土地和荒野有着深深的眷恋,另一方面又渴望投身于现代文明的洪流之中。
虽然在小说中乡村和城市之间存在着对立冲突关系,但毋庸置疑的是,作者基本出发点和最终价值归宿仍是热爱土地、回归自然的生态追求。具体来说,虽然亚历山德拉对于城市文明有着一定的向往,但在她的内心深处,她始终清楚自己与土地之间的深厚情感纽带。她明白,自己是土地的一部分,只有在这片土地上,她才能找到真正的归属感与自我认同。因此,尽管在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职业多样化和社交活动成为主流趋势,但亚历山德拉却仍然选择坚守乡村,回归荒野,承担起家族农场的管理重任。诚然,这种选择使她在城市日新月异的变革中,成了一个乡村“他者”,使她错过了在城市中的种种便利和机会,甚至在社会交往中处于边缘地位。然而,正是这种边缘地位及“他者”身份促使她更加关注土地与荒野,在与土地的亲密接触中,她逐渐发现了自己的价值与意义,收获了来自土地的馈赠与认同,最终完成由“他者”到“主体”的转变。
《啊,拓荒者!》中,以亚历山德拉为代表的美国西部拓荒者在边疆地区不懈奋斗的过程中,土地不仅培养了人们坚毅的性格,也锻炼了人们聪慧的头脑。以亚历山德拉为例,她不仅满怀对于土地的热爱与眷恋之情,更为重要的是她有着足够的毅力、决心和智慧改造这片土地。凭借着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亚历山德拉创造性地成为全村第一个种植麦子的人,并在连续三年丰收后成功带领大家一起种植。当人们纷纷抛售土地时,亚历山德拉却反其道而行之,筹措资金购买了尽可能多的土地,甚至不惜抵押自己的宅邸,因此,亚历山德拉很快便从挣扎在温饱线边缘的农民一跃成为当地最富有的农场主,而这一切都是基于她在长期与土地打交道的过程中积攒下来的知识与丰富的经验。因此,是土地赋予了他们无穷的创造力,培育了他们坚韧的品格,造就了他们机敏的头脑,孕育了他们宽广的胸襟。它犹如一位无私的母亲,毫无保留地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赋予亚历山德拉以包容万物的胸怀与美德,事实证明,亚历山德拉也的确是这么做的。当家庭陷入困境之时,她毅然牺牲自己的爱情,为了家人和土地,勇敢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不知不觉中,亚历山德拉早已不再是城市化语境下弱小透明的乡村“他者”,而是在与土地的朝夕相处中逐步建立起自尊自信,打破“他者”身份束缚,实现自我意识重塑,并逐渐成长为像大地母亲一样具有博大胸襟和无限智慧的独特自我。一方面,这片土地见证了亚历山德拉们的勇敢开拓,记载了他们的青春岁月,塑造了他们不朽的拓荒精神;另一方面,他们深深地热爱着边疆的土地,生命因脚下的土地而绚丽多彩。
尽管亚历山德拉在城市化语境下成了一个乡村“他者”,但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身份认同和抗争,她始终坚信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是正确的,并努力在乡村中创造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通过辛勤劳动、科学经营和社区参与,她逐渐赢得了周围人的尊重和认可,并在长期与土地打交道的过程中重新认识自己,认识土地,最终实现从“他者”到“主体”的身份转变。
3 父权制建构下的女性“他者”
十九世纪末的美国西部是一个以男性为主导、以冒险、探索和征服为中心的社会。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社会将妇女的位置规划在家庭内部,而妇女承担的主要角色为“妻子”“母亲”[4]。在《啊,拓荒者!》中,女性被塑造为“他者”的存在,其身份深受父权制建构的制约,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经历着种种困惑、依赖和痛苦。
小说的主人公亚历山德拉·伯格森,便是这一时代背景下的典型女性形象。她幼时随父亲来到内布拉斯加州原始荒野,父亲去世后,她继承家业,在极端贫困的境况下,艰苦奋斗,面对一系列挫折和打击:三年大旱、庄稼歉收、经济危机,周围的人纷纷放弃土地向城市逃亡;家境有所好转时,两个大弟弟为争夺家产阻挠她结婚;她悉心培养的小弟弟大学毕业后又死于情杀。但她没有动摇,而是凭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信心,用勤劳和智慧,用具有远见的计划和科学的管理方法,征服了桀骜不驯的荒山野岭,使之变成千里沃野。然而,尽管她在经济上取得了独立,但在情感和社会地位上,仍然无法摆脱父权制的束缚和影响。
从家庭的角度来看,亚历山德拉从小就展现出了勇敢和独立的品质。然而,这些特质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并不被看好,反而被视为与女性角色不符。因此,她被迫用男性化的方式来武装自己,以在这个社会中立足。她自己也承认:“可能我从来没有柔软过;但可以肯定的是,不是我自己选择成为这种女孩的。如果一直砍葡萄树,它会慢慢地变硬,就像树一样了。”亚历山德拉与传统女性不同的原因是,为了能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世界里取得一席之地,她不得不表现得像男性一样强壮,有男子气概[5]。她的内心也充满了矛盾和挣扎,她渴望被接纳和认可,但又不得不面对社会对女性的偏见和歧视。
虽然亚历山德拉具备独立自主的潜力,她却一直生活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中,并受制于周围人的期望和决策。弟弟对她未来婚姻的强制和影响,使得她在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时几乎没有自主权,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人生。在此过程中,她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个人渴望,成为一个被他人塑造和控制的“他者”。前期,亚历山德拉在父权制建构的婚姻制度中被描绘成一个虚弱被动的女性,通过这样的描绘,小说呈现了父权制度对婚姻的压迫性和女性无权发言的现实。然而,亚历山德拉并非一个完全被动的角色。她是一个勇敢、坚毅的女性,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野心。她内心深处渴望着独立和自由,不愿被父权制所束缚。在成长的过程中,她逐渐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和能力,开始勇敢追求梦想。在家人阻挠自己与卡尔结婚后,亚历山德拉坚持自己的选择,在四十岁时与卡尔结婚,这是她对父权制的一次反抗和挑战。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对女性的传统期望往往是为了家庭的贤妻良母,而不是追求个人事业和梦想的独立个体。这种期望限制了女性的发展空间,使她们在社会中处于从属和依附的地位。尽管亚历山德拉勇敢聪明并且渴望冒险,但她无法追寻她真正想要的独立和自由,女性身份及父权制建构使得她无法在这个时代中建立起远离男权文化的乌托邦。亚历山德拉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完美人物。作为女人,她有天分和直觉,也同样有其固执保守的一面。“分界线之神”的男性品质暗示亚力山德拉并未彻底摆脱传统女性角色的柔弱形象,但两者开启的分界线又表明农场已经成为女性生育力的事实象征[6]。她重新审视人生选择,并认识到父权制所造成的束缚和限制。最初,亚历山德拉的自主权和个人意愿在父权压制下没有发言权,她的女性身份和社会地位限制了她追求独立和自由的可能性。但她和土地最终实现和解,脱下重担,奔向属于自己的自由。亚历山德拉这一形象呈现了父权制建构对女性的压迫和束缚,同时也表达了对女性解放和自主权的呼吁。
除了亚历山德拉之外,小说中还出现了其他被父权制社会限制的女性,她们的一生也是被家庭和社会期望所束缚。麦丽同情自然动物,已成年的艾米枪杀了一只野鸭,麦丽伤心不已,被艾米恼怒地骂作“与伊瓦尔一样疯傻”。这一故事情节表明,女性难以拥有自主性和话语权,在父权制社会中正在被边缘化和忽视[7]。而麦丽的生活更是几乎完全围绕着男性,从依靠父亲转变为依附丈夫,她甚至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声音或追求自己的梦想[8]。麦丽的存在凸显了女性在父权制中的传统“他者”身份:她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做家庭和社区的附属物,在社会中被限制、压迫和塑造,女性的个人意愿和自主权被剥夺,成为依附和依从的存在。但她们尽力脱开牢笼要获得自由。
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常常被动地接受父权制度的支配,难以挣脱其中的桎梏。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压迫和束缚下,她们的内心涌现出强大的反抗意识和生存力量。在凯瑟的作品中,这种反抗精神得到了肯定和赞美,女性角色往往在面对困境时展现出了不屈的意志和坚强的毅力,最终实现了自我价值和身份的重构。因此,凯瑟通过描绘父权制度下女性“他者”的形象,呈现了关于性别平等和人权保障的深刻探讨,引发了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反思和探索。
4 美国文化背景下的移民“他者”
《啊,拓荒者!》一书介绍了瑞典移民家庭在美国西部拓荒岁月中的奋斗历程。在这部作品中,薇拉·凯瑟深入描绘了女性移民亚历山德拉与大自然博弈的坚韧不拔,以及她在面对新旧文化冲突时所展现的美好精神。作为移民家庭的一员,亚历山德拉不仅代表了那些身处异乡、努力适应新环境的移民个体,更成为美国文化背景下移民“他者”身份的典型写照。她的经历深刻揭示了移民在物质与精神层面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以及他们在追求文化适应过程中所展现的顽强与智慧。
亚历山德拉,这位瑞典移民的女儿,以其对美国西部土地的深情厚谊,成为作者笔下移民女性力量的化身。她的文化适应经历不仅是她个人成长的见证,更是作者对移民文化适应问题的深入思考与探索。作为美国文化背景下的移民“他者”,亚历山德拉既守护着过去的文化脉络,又积极适应着全新的文化环境。
亚历山德拉的家中,最惬意的屋子是厨房。这里不仅是她施展厨艺的舞台,更是她与瑞典姑娘们交流文化、分享生活的场所。她们在厨房里聊天、做饭,腌瓜果、做果酱,共同维系着那份来自故土的温暖与记忆。亚历山德拉还将过去老木屋里的简朴旧家具和家庭画像都放在自己的房子里。这些物品不仅承载着家族的历史与记忆,更成为她在新环境中坚守文化传统的象征。
在与其他移民女性的相处中,亚历山德拉同样展现了对故土文化的尊重与守护。她尊重李老太的生活习惯,不会嘲笑她的旧时习俗。相反,她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接纳并理解这些差异,使得她与李老太的相处模式处于一种轻松和谐的状态。当李老太在她家居住时,两人常常一起缝缝补补,分享着彼此的故事与经历。李老太滔滔不绝地讲她从瑞典报纸上看来的故事,不厌其详地叙述故事情节;讲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在戈特兰一个奶牛场时的生活[9]。这些故事与回忆,在亚历山德拉的倾听与理解中得到了传承与延续,使得故土文化在新的土地上焕发出新的光彩,曾经缺少文化归属感的漂泊者又重新找到自己扎根再生的地方。
面对美国文化的挑战与冲突,亚历山德拉并没有故步自封、停滞不前。相反,她以拓荒女性的创新精神,积极适应并调和着新旧文化之间的差异。父亲去世后,亚历山德拉独自扛起家庭的重担。三年后,村子遭遇了一场旱灾,而亚历山德拉凭借着对土地超乎常人的直觉,选择在其他村民离开分水岭时向银行贷款购买土地,这最终帮助她们一家渡过难关。在父亲去世16年后,昔日贫瘠的土地逐渐变得肥沃,慢慢获得丰硕的收成。土地不仅是亚历山德拉拓荒的直观体现,而且是亚历山德拉重新扎根美国文化土壤的意象呈现。她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生长,将自己的生命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
与亚历山德拉相比,她的三个弟弟在文化适应过程中则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罗和奥斯卡过度地“美国化”[10],他们对自己的瑞典血统和文化传统感到羞耻。罗与他的妻子尽管都是瑞典人,但基本上以英语交流为主,担心别人听到他们的瑞典话。同时为进一步融入美国社会,罗常常撇下他的农场不管,参加政治活动,希望转变自我身份而彻底融入美国社会。奥斯卡则因为自己的英语口音而感到自卑,他的妻子甚至以自己嫁给一个移民者为耻。他们的孩子们虽然有着瑞典血统,但却连瑞典话都听不懂。而最小的弟弟艾米则完全接受了美国教育,由于自小受美国文化氛围熏陶,他能够讲出一口流利的英语口语,外形也和美国孩童相差甚小,几乎是一个完全与故土失去联系的个体。这些彻底否认故土文化,过度“美国化”的行为与姐姐亚历山德拉形成了鲜明对比。三个弟弟对故国文化选择淡忘与忽视,彻底切断了与故土的本根联系,失去了厚植于内心的故土文化羁绊,成了真正的文化“他者”。
通过对亚历山德拉及其弟弟们文化适应过程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到移民在面对新文化时所面临的挑战与困境。一方面,他们需要努力适应新环境、新文化,融入主流社会;另一方面,他们又要保持对故土文化的尊重与守护,避免在文化适应过程中失去自我。这种平衡与调和的过程并非易事,需要移民个体具备足够的智慧和勇气。然而,正如亚历山德拉所展现的那样,移民在追求文化适应的过程中也可以实现文化的交融与共生。他们可以通过尊重与守护故土文化,同时积极适应新环境、新文化,实现自我身份的重构和文化认同的更新。这种文化交融与共生不仅丰富了移民个体的内心世界,也为美国多元文化的繁荣发展贡献了力量。
亚历山德拉的文化适应过程不仅是一部个人成长的史诗,更是关于文化交融与理解的壮丽篇章。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文化交流显得尤为重要。亚历山德拉的故事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更为人们展现了一个充满希望和可能的未来,让人们以开放的心态和包容的精神,去迎接这个多元文化的世界,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5 结束语
《啊,拓荒者!》展现了一个个生动的女性移民“他者”形象。在城市化语境、父权制度和美国文化的三重压力下,她们经历了种种挣扎和磨难,但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找到了自我,实现了身份的重构和文化的交融共生。在她们身上,我们看到乡村“他者”的挣扎与蜕变,父权制下女性“他者”的抗争与觉醒,以及美国文化背景下移民“他者”的融合与成长。通过对这些形象的深入剖析,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薇拉·凯瑟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更可以从中得到启示,为当代女性的自我认同和文化成长提供借鉴和启迪。
参考文献
[1] 张佳卉.薇拉·凯瑟小说《啊,拓荒者!》中的神话原型分析[J].语文建设,2015(5):33-34.
[2] 徐文雅.“他者”视域下的《我的安东尼亚》[J].江苏外语教学研究,2015(1):44-46.
[3] The Other[M].3rd ed.London: The New Fontana Dictionary of Modern Thought, 1999:620.
[4] 周婧.空间视域下《啊,拓荒者!》中女拓荒者身份建构研究:以亚历山德拉为例[J].新纪实,2021(19):60-62.
[5] 宋文,毕宙嫔.开创美国西部文明的拓荒女:评薇拉·凯瑟《啊,拓荒者!》[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72-75.
[6] 徐超超,张海榕.中美“移民线”地理景观书写:从《啊,拓荒者!》到《孔雀的叫喊》[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24,35(1):84-94.
[7] 周铭.从男性个人主义到女性环境主义的嬗变:威拉·凯瑟小说《啊,拓荒者!》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J].外国文学,2006(3):52-58.
[8] 张平,张晓霞.独立女性与依附女性:《啊,拓荒者!》的女性主义视角分析[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2):55-58.
[9] 薇拉·凯瑟.啊,拓荒者[M].资中筠,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10]许燕.《啊,拓荒者!》:“美国化”的灾难与成就[J].国外文学,2011,31(4):133-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