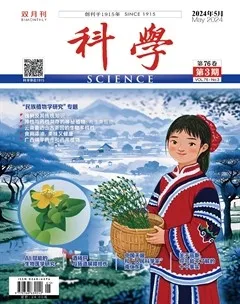神性与药性共存的神秘植物:寄生类植物
陈晴宇 程卓 龙春林

心情烦闷的宋代诗人连文凤放下笔墨,沿着进山的小路缓缓独行。四周草木葱茏,他忽见路旁的树上竟开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小花,景象十分奇异。连文凤站在树下仔细辨认,发现整棵树灿烂的白色柚花之下,还生出几枝红色的长管状红花——是寄生类植物!联想起南宋末期的风雨飘摇,以及仕途之坎坷多舛,连文凤恍然:自己又何尝不是一株脆弱的“寄生树”?他感慨道:“一朝失所托,早暮不相及。人生同此寄,百年一呼吸。”
对“微根不自立”的寄生类植物恨铁不成钢的连文凤可能怎么也想不到,在千年之后的广西传统药市上,寄生类植物已然成为当地重要的大宗药材,不仅能卖,还卖得特别多。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云贵高原东南边缘,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和热带季风气候,气候温暖,雨水丰富,地形多样,具有很高的生物多样性。被称作“山水小桂林、气候小昆明、药材大园林”的靖西市位于广西西南部,居住着壮、苗、汉等12个民族,其中壮族人口占99%以上,是全国典型的壮族人口聚居地。
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靖西市及周边城市的壮医、药农以及普通民众自发来到靖西端午药市,将采摘到的鲜药、自制的中成药集中摆摊出售。这种传统已延绵数个朝代,持续了700余年,售卖的常用药材多达400余种,其中不乏田七和七叶一枝花等名贵药材,还有本文谈及的桑寄生科和檀香科的寄生类植物,它们是其中生物量最大、出现最多的药用植物。
近乎“万能”的神性植物
全球寄生类植物约有4200种,占被子植物总数的1% [1]。与其他被子植物不同,因为根的退化或叶绿体不足,寄生类植物所需营养做不到“自给自足”,需要通过汲取寄主植物的营养而存活。根据它们能否进行光合作用,寄生类植物可分为全寄生型与半寄生型两大类。它们通过与寄主植物的根系或茎部相连,形成特殊的吸器结构,如吸盘、吸管或吸根,来吸取养分和水分。这些吸器结构形成运输营养物质的“生理桥梁”,让寄生植物无须自己进行光合作用和根系吸收,就能维持生存。特殊的生活方式使不同地区的人们多少都对寄生类植物心生敬意,认为这是汲取别人之所长补自己之所短的表现,并因此具有特殊的药效。在古罗马神话里,槲寄生(Viscum coloratum)指引着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度过了冥河。在欧洲神话中,嫉妒的洛基借槲寄生杀死了光明之神巴德尔。时至今日,欧洲凯尔特人认为寄生在栎树上的槲寄生是一种神圣植物,服用槲寄生可以吸收栎树的汁液,汲取栎树的力量[2];而英国人则相信在结果的槲寄生下亲吻的情侣可以共度余生,白头偕老——从古至今,寄生类植物身上总笼罩着一种“神性”色彩。
实际上,寄生类植物身上的这种神秘色彩与其良好的药效是分不开的,它们的确有神奇的功能。现代药理学研究已证明,寄生类植物大多具有药用价值,其提取物及单体化合物具有抗炎、抗肿瘤、抑菌、抗病毒、抗氧化、降血糖、降血压、抗骨质疏松、降脂等广泛的药理活性,是极具发展潜力的“六边形战士”。临床应用上,不同寄生类植物的应用重点不同,桑寄生属植物有显著的抗炎作用和较强的降压作用,常用于治疗高血压、妇科流产、心律失常及某些炎性反应[3,4];槲寄生属植物在降压和抗肿瘤方面有良好的表现,其相关制剂已广泛应用于治疗癌症,并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5];蛇菰属植物除了以上所述药理活性,还具有解酒保肝、抗疲劳和抗衰老等功效[6]。
那么寄生在不同的植物上,寄生类植物的药效会随之改变吗?答案是肯定的。不同科属间的次生代谢产物的差异同样呈现在寄生类植物身上,人们会偏好特定的寄生-寄主组合,追求更稳定、更安全的药效。例如,靖西民间认为生长在柚树、黄皮和桃树上的红花寄生(Scurrula parasitica)的药效最佳,桑树上的广寄生(Taxillus chinensis)、杉树上的鞘花(Macrosolen cochinchinensis)和樟树上的扁枝槲寄生(Viscum articulatum)等也同样是广西传统药市上极受欢迎的药材,而寄生在夹竹桃等有毒植物上的广寄生则因具有毒性,不能轻易入药。
寄生类植物可以选择的寄主植物通常是广谱性的,桑科、山茶科、壳斗科、芸香科、蔷薇科和豆科等多科植物都在它们的选择范围内。近年对广西境内桑寄生科植物的调查统计发现,其寄主植物可多达36科150多种[4]。不过,“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当桑寄生科植物在寄主身上生根发芽时,也得提防其他植物的“偷袭”——重寄生现象,即一种寄生物又被其他寄生物“套娃”寄生的现象。这种现象在细菌和昆虫领域中常见,而在被子植物的世界中,仅有檀香科重寄生属植物有此本领。至今,共描述了8种重寄生属植物,主要分布于中国南部和东南亚地区,其中我国分布有6种。研究发现,重寄生属植物的直接寄主有十几种,除扁序重寄生(Phacellaria compressa)偶尔会寄生在檀香科的多脉寄生藤(Dendrotrophe polyneura)上,其余寄主均为桑寄生科植物,其中又以钝果寄生属植物作为寄主的种类最多[7]。但无论是植物化学、药理活性,还是适应策略方面,当前重寄生属有关的研究都十分有限,需要进一步研究。
历史悠久的传统民族药

槲寄生与欧洲人的羁绊或许已不是新鲜事,但很少有人知道,我国古人早在秦汉时期便将寄生类植物写入药典。《神农本草经》是最早记录“桑寄生”的本草古籍:“桑上寄生……味苦,平,无毒……生川谷桑树上。”随着历史的发展,我们的祖先对寄生类植物的认识不断加深,从一开始客观记录“桑上寄生”的东汉起,张仲景就明确写下了其“根津所因处为异”的特点,认识到寄主种类对药效的影响。400年后,唐朝《新修本草》对其基源植物槲寄生作了初步记录,不仅对其外形、果熟期进行描述,还提及鸟类与其种子的合作关系[8]。到明清时期,寄生类植物的疗效归类趋于稳定,并对不同寄生类植物的优劣进行评价。
寄生类植物的利用历史悠久,分类的历史却不甚清晰,过去的大夫们是如何区分药效不同的“桑上寄生”的呢?没有林奈严谨的分类系统,不同本草中记载的特征又含糊不清,我们的老祖宗便选择了简单粗暴却又切实可行的方式——通过寄主植物区分。虽然现代药理学研究已经证明,不同寄主植物的确会影响单种寄生类植物的药效,但仅靠寄主植物分类的方式显然无法满足当下的利用需求。明朝以前,本草里记录的多是槲寄生及其近缘种的药用价值;明朝以后,李时珍明确记录了桑寄生及其近缘的锈毛寄生等植物,桑寄生科植物由此正式进入人们的视野里[9]。2020年,为规范不同药材的使用,《中国药典》明确规定中药材“桑寄生”的基原植物品种为广寄生(Taxillus chinensis),“槲寄生”的基原植物品种为槲寄生(Viscum coloratum)。由此,寄生类植物的神秘面纱正被一层层揭开。
广寄生是民间重要的药食两用植物,入药有补肝肾、强筋骨、祛风湿、安胎元等功效,用于治疗风湿痹痛、腰膝痠软、筋骨无力、崩漏经多、妊娠漏血、胎动不安、高血压等症。而在广东、广西等地,民间常用广寄生的枝梗、芽叶制作凉茶,也煮水熬汤或直接用开水泡当茶饮用。广西的不同民族长期以来将广寄生作为药食两用的保健饮料,据说有强身健体的作用,已成为当地的传统饮品。其中以梧州地区出产的广寄生茶最负盛名,系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传统保健茶品,并于1992年被列入中华传统食品保健茶类[10]。
寄生类植物的今生
抛开以上种种植物学知识和历史故事不谈,行走于端午药市之间,你依旧会被寄生类植物所吸引。你会发现当地民众对寄生类植物的认识虽朴素,却又充满智慧。在广西靖西端午药市上售卖的10种寄生类植物分别归属于桑寄生科、檀香科和蛇菰科。与史料记载相同,药市上的买卖双方依旧通过寄主植物来区分不同的寄生类植物,并以此区分他们的用途。考虑到寄生类植物的寄生特点,药市小贩通常选择直接将其整枝砍下,将寄生类植物与寄主植物共同售卖。他们对寄生类植物的生长习性了然于心,能明确说出不同寄生类植物的生长地点和采割季节,比如柚木寄生和枫树寄生多生长在半山腰以下的树林里,而扁枝槲寄生则需要到半山腰以上,甚至悬崖附近才能找到。
与史料记载不同的是,当问及实际操作时,当地人给出的答案比史料记载更加丰富且多元,还从侧面展现了当地的气候特点。为方便顾客快速挑选,药市小贩大多会在每种寄生类植物旁摆张纸条,写上寄主植物与治疗药效。当地人相信,湿热的天气会让人体内淤积湿气,进而招致内热、上火和风湿等疾病,因此在气候温暖且雨水丰富的广西,寄生类植物的主要功能是宣肺、化痰、止咳消炎和祛风除湿。此外,桑寄生科植物可用于补肝肾、强筋骨、预防流产,槲寄生属植物能用于治疗外伤、舒筋活络,而蛇菰属植物具有壮阳补肾、健脾理气、治疗腰痛和痔疮等病症的功效。民间药方里,除了传统的中药煎制方法,还可将寄生类植物做成药膳,比如将柚木寄生(即双花鞘花,Macrosolen bibracteolatus)与猪脚炖煮,可止咳化痰。

槲寄生属植物是端午药市中最容易辨认的寄生类植物之一,3~7厘米长的椭圆状披针形或长椭圆形叶与枝同为深绿色,远处看时,比起灌木更像一堆“绿色的杂草”,很难一下分清叶和枝的分界。或许是因为好认,几乎每一个卖寄生类药用植物的摊子上都有它,当地人叫它“柚寄生”“栎树寄生”“榕树寄生”,就是不叫它槲寄生。这也从侧面说明,槲寄生属的药理作用在靖西壮族内部的共识程度较高。回溯历史,槲寄生属植物确实声名显赫:古代欧洲人认为槲寄生不仅可以治疗癫痫,还可以增强妇女的生育能力,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则相信槲寄生可以解除多种毒药的毒性。在凯尔特的某些方言里,槲寄生叫作“栋树之水”。因为栎树本身象征着光明和太阳之力,而四季常青的槲寄生则象征植物不可摧毁的生命力和复苏能力,栎树上生长的槲寄生因此被视为上天的恩赐,或是表示这棵树被神选中。信仰万物有灵论的日本阿伊努人也赋予了槲寄生同样的特性[2]。
桑寄生科植物则是售卖量最大的寄生类植物,其中又以离瓣寄生(Helixanthera parasitica)和双花鞘花为甚。它们在广西境内分布广泛,寄主甚多:离瓣寄生最受欢迎的搭档是柚木、榕树和桂花,而双花鞘花的搭档则是八角、枫树和杉木,因此它们的别名就更多了。桑寄生科不同种之间枝叶的形态特征相似,但分辨难度比槲寄生的低——技巧是观察它们的花和果实。端午期间正值这些桑寄生科植物的花果期,这无形中又大大降低了药材误用的可能性。

与桑寄生科、檀香科相比,蛇菰科植物大多以干巴巴的形象出现在靖西药市上,看上去很像晒干的菌类。虽然长得像蘑菇,但蛇菰科植物是地地道道的被子植物,作为全寄生类植物,它们通常选择山茶科和壳斗科等植物作为寄主生活。当地人通常把它称作“公婆草”,用其煲汤炖鸡。相比之下,蛇菰科的售卖量最少,因此价值不菲。广西境内的端午药市上,我们只记载到疏花蛇菰和盾片蛇菰两种,而名气更大、资源更稀缺的红冬蛇菰只能在湖南江华县附近才能找到。早在多年前,红冬蛇菰就被列入我国的《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中,是一种十分稀有且珍贵的野生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