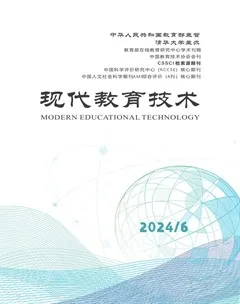培育智能时代的专家学习者



摘要:当前,鉴于专家学习者教育研究的既有范式使其陷入了困囿,以及智能时代学习型人才的培育缺少方向指引,从人工智能教育应用逻辑解构的新视角开展专家学习者培育研究,具有范式突破和实践参照的双重价值。为此,文章首先阐述了专家学习者概念的起源,解析了概念引入教育领域并身陷研究困囿的原因;然后,文章从智能技术介入、知识价值塑造、主体能力强化、学习场景改造四个维度对人工智能教育应用逻辑进行了解析;接着,文章归纳了智能时代专家学习者特征;最后,文章从重构学习设计路径、重拾知识学习取向和重立学习场景构向三个层面提出智能时代专家学习者的培育策略,以期在助力学习者有效投身智能环境下的学习活动的基础上,为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理论和实践提供靶向指引。
关键词:人工智能;专家学习者;能力培育;知识学习;学习素养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24)06—0035—10 【DOI】10.3969/j.issn.1009-8097.2024.06.004
一 研究缘起
专家学习者是指在学习这一专业领域具备特定专长、表现杰出的学习者[1]。由于不同时期的学习境脉存在较大差异,人们对学习的理解及所需的学习专长不尽相同,因此专家学习者的特征和培育方式始终处于动态的变化当中。本研究选择以人工智能教育应用逻辑的解构为立足点,通过洞悉智能时代专家学习者的特征,继而生成具有针对性的培育策略,不仅是教育领域突破专家学习者研究困囿的必要举措,也是培育智能社会所需学习型人才的有效途径。
1专家学习者概念的起源及教育引入
专家学习者概念的提出以及“学习”之所以能够被视为一种专业领域,得益于认知科学研究者的工作。20世纪90年代,当认知科学研究者在极力展示各领域专家独特的认知图景时,发现信息时代的来临让学习者处于一个快速更迭的境脉中,面对开放多元和复杂多变的世界,学习绩效已无法简单用知识掌握的多少来衡量,学习过程的多样性、变异性及其塑造的多种可能性,让学习同样能够被视为一种专业性、领域化的活动,故而推出了“专家学习者”概念,目的是为专家认知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增长点。进一步而言,认知科学研究者利用人工神经网络模拟专家学习者的学习行为和决策过程,继而构造仿生学习模型,以便让智能机器在某个领域能够重组已有知能,持续改进自身性能。
当前,金融危机频发、资源过度消耗、气候急剧变暖、物种数量锐减等一系列人类社会内部及其与自然之间的问题给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传统教育珍视的经典知识及其构建的社会能力难以应对这些挑战时,全球教育思想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学习理念的转变,即彻底抛弃“学习是一劳永逸”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通过普及终身学习理念以及打造学习型社会,让个体和社会都能够建立一个不断演进的知能体系,以此来推动人类社会突破困境。因此,专家学习者作为学习领域的“行家里手”,其概念一经推出就迅速进入教育学者的研究视野。具体而言,教育学者企图借助脑科学成果,对专家学习者的学习特征、学习技能、认知特点等方面进行洞悉,为人类学习素养的培育提供茎蔓可攀。
2专家学习者教育研究的困囿及突破
作为专家认知领域的研究对象,机器学习针对专家学习者的仿生能力不断提升。而作为教育领域的研究对象,专家学习者的研究境遇却大相径庭,在当下陷入了困囿。世纪之交,脑科学研究者发现了主控学习活动的三组脑功能网络(识别网络、策略网络和情感网络)[2],在国际教育届一度掀起专家学习者研究热潮,并推动一批以“通用学习设计”为代表的教育理念快速成型。但此后,专家学习者研究似乎走到了尽头,丧失了持续发展的生命力。更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技术进步与教育发展逐步形成共振,诸多致力于培育专家学习者的实践人员开始质疑已有的研究成果。例如,Mark等[3]在早期的研究中发现,影响在线学习者学习水平的首要因素为学习者态度和技术获取水平,并非之前专家学习者研究人员所指出的元认知监控等方面的能力;Mavrou等[4]通过调查美国推行的一些国家课程后发现,根据三组脑功能网络开发的“通用学习设计”三大教学原则未能有效融入课程教学,且专家学习者培育成效远低于预期。
这一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可归结为该领域的工作陷入了神经迷思和绝对主义泥潭。所谓“神经迷思”是指因曲解、误读或错误引用大脑及其功能信息而产生的迷思观念,并以此为教育或其他领域使用大脑研究成果提供依据与理由[5]。诸多脑科学家[6][7][8]指出,由于人类大脑结构的复杂性及其研究多层次、多水平的交叉性,导致神经生物学(脑科学)学科壁垒较强,其他领域容易简化或误读脑科学成果。此外,一些被广泛认可的脑科学假说有可能随着新证据出现,在大众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纠正。一系列神经迷思调查显示,各个国家的教育从业者均普遍持有不同程度的迷思观念,无论学科领域与学术水平如何都无法正确识别神经迷思与科学事实[9]。由此可见,当脑科学成果从实验室流向教育实践时,致力于借助其来研究和培育专家学习者的教育工作者或多或少存在神经迷思问题,继而对研究结论及教学改革产生负面影响。
绝对主义指的是由于专家学习者这一概念来源于认知科学领域,教育研究者遂将脑科学奉为指导各项工作的“圣经”,忽略其他视角和影响因素研究的积累。虽然说教育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脑科学,学习能力的培育需要遵循大脑工作的机制,但是教育作为一种影响人身心发展的社会实践活动,有自身运行发展的规律,其研究不应该只遵循脑科学研究的轨迹。然而,当前专家认知领域的教育研究者只是将脑科学作为学习品质刻画的“镜像”,并将其视为学习能力培育的唯一参照,势必会造成研究成果的单一性、片面性和孱弱性——这也是在脑科学研究取得重大突破之后的间歇期,专家学习者的教育研究会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
综上所述,教育工作者亟需开辟新的视角和路径开展专家学习者研究,不仅可以借助领域之间成果的相互校验,突破神经迷思困局,还可以形成多元研究趋向,摆脱绝对主义枷锁。当前人工智能成为影响教育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时专家学习者具备了全新特征。因此,从人工智能教育应用逻辑的解构入手开展专家学习者的培育研究,具有范式突破和实践参照的双重价值。
二 人工智能教育应用逻辑的解构
与其他技术不同的是,人工智能具有一定的认知水平和学习能力,并能够模拟人类大脑的功能进行信息处理、数据分析和决策建议,其让技术以全新的方式介入教育,彻底颠覆了以往技术在教育中的运用路线。因此,关注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首先应厘清技术介入的逻辑。同时,人工智能强大的知识发现和推理能力,开启了技术生产知识的先河,不仅带来了知识数量的指数级增长,更会因为其自带强化智力的属性重塑知识的价值。此外,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是对教育主体能力无法突破域限的外化延伸,以及对学习场景功能和结构的深度改造。故而,本研究将从智能技术介入、知识价值塑造、主体能力强化和学习场景改造四个维度对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逻辑进行解构。
1形式科学:智能技术介入的逻辑
人工智能研究包括符号主义、联结主义和行为主义三大范式。其中,符号主义将心智看作一种单纯的“计算心灵”,提倡基于逻辑推理的智能模拟方法,认为只要遵从物体定律就可以用某种符号描述认知过程,智能装置通过抽象运算即可实现智能行为,人工智能鼻祖“深蓝”和基于大数据知识工程的知识图谱是符号主义应用的典型代表;联结主义又被称为仿生学派,主张利用人工神经网络模仿人类大脑的工作原理,采用双向传播算法进行人工神经网络的训练和学习,当前经常谈论的深度神经网络就是一种典型的联结主义人工智能;而行为主义采用的是基于“感知-行动”的智能模拟方法,主张略去知识的表达与推理环节,利用智能机器与真实世界的交互进行学习,实现手段是采用信息数学模型模拟进化的遗传算法[10]。可见,无论关注抽象思维的符号主义,还是专注形象思维的联结主义,抑或热衷于感知思维的行为主义人工智能,都是建立在“计算主义”的强纲领之上。
从这个意义来说,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同样是一种计算,其对教育问题或教育现象进行数字处理,继而转化为计算(数学)问题,在算法的驱动和海量数据的供养下,通过人造处理系统和预测模型以固化形式进行结果的运算。因此,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过程深刻诠释了包括计算机领域在内的自然科学所推崇的形式科学逻辑。同样,邱德均[11]根据梳理的AlphaGo归纳学习进展,得出智能的核心推理是形式化;安涛[12]通过解析人工智能发展的本体论,认为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技术路线依然遵循形式科学的逻辑规则,并建立在数据、算法及计算的基础上。所谓形式科学是指对某一问题或对象做出程式化表述,并严格按照规定好的方式运行。形式科学的优势在于能够捕捉教育问题或教育现象的核心本质,将复杂混沌的事件和问题转化为计算机可掌控的对象。也就是说,人工智能之所以能够介入教育并在某些方面具有卓越能力,是因为其对复杂的教育进行了形式科学处理,并通过不断优化特定的算法集,统计出一种数据意义上最优的解决方案。
2尚智趋向:知识价值塑造的逻辑
知识价值讲的是知识学习的目的,或者说究竟为什么要学习与发展知识。鉴于知识是对客观世界比较可靠的认识成果,因此无论之前人们如何质疑和批判“为知识而教”和“为了知识而追求知识”的教育主张,通过学习来接受、存储前人已发现知识的大众信念从未减弱。相关学者为了迎合时代发展提出了回归论、建构主义等新型知识观,企图让教育的重心从“知识传授”走向“思维培养”,让学习者学习从“知识汲取”走向“转识成智”。但在现实的教育实践中,多数教育工作者施行这些理念的落脚点仍是为了便于让学习者获取知识,指向高级思维培养的知识活动同样成为学习者在完成知识的了解、记忆和内化这一闭环后的奢侈品。这并不能简单归结于教育实践者对知识价值产生的误解或者自身素养问题,而是学习者知识增长确实是重要的,也是能够真正抓得住的。因此,在当前教育实践中知识的价值容易被窄化为知识的浅层学习,可以说现代教育的困境是困在了“知识”中[13]。
智能时代的到来催生了新的知识生产方式:①智能体向知识生产主体靠近,自身同样具备了知识生产能力;②人机协同的智能模式扩大了知识生产机会。由此,新的知识生产方式将会加速知识容量的极度膨胀。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生成式信息获取服务的通用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取得突破,知识的检索将变得异常简单,因而学习者纯粹的知识获取将变得徒劳无益。此外,人工智能是不断汲取人类智慧来对待和理解世界的产物,人们倘若要在与其博弈和协同中占据主导地位,凭借的是自身的智力水平而绝非拥有的知识存量。因此,人工智能的教育普及让强调客观性和即成性的传统知识观遭遇挑战,而以生成性和情境性为特征的相对主义知识观或将真正成为主流。在此过程中,人们对知识的诉求也会从知识的本身转变为以高阶思维发展和复杂问题解决能力为核心的智力发展,从而在根本上帮助人们摆脱知识本位的枷锁。
3认知延展:主体能力强化的逻辑
从技术人类学的观点来看,如果说传统技术是对人类身体进行的延展,那么人工智能的显著特征就是对人类认知进行的延展。前者不言而喻,其观点受到了诸多学者的证实,如斯蒂格勒[14]对于“人-技术”存在结构的独特见解、Merleau-Ponty曾提到“盲人与拐杖”的典型例证[15],以及Ihde[16]关于技术与人之间四种关系的经典论述等。而人工智能对人类认知延展的观点源于Clark等[17]提出的延展认知假说,该假说认为人类的认知过程并不局限于颅骨和体肤的范围内,认知可以超越大脑,延展到身体之外的技术实体上。这种现象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①同等性,即外部实体和大脑组织发挥了同等作用;②动态耦合性,即外部实体与人体构成了即时性的动态互动系统。作为人类智能的物质进化载体,人工智能无须进行物理性连接就能与人脑神经系统存在功能上的耦合关系,其在教育中的应用事实上是作为一种延展认知技术。
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有两种演进路径:①协同路径。智能工具支持多轮对话或具备环境感知能力,教育主体能够与其沟通继而开展智能合作,完成复杂的学习任务,如回答复杂学科问题的计算知识引擎、感知学情提供个性化辅导的AI导师等。在协同路径下,教育主体与智能工具形成了“有机体智能”,面向任务时负责与外部物理世界建立双向交互。在这个动态的耦合系统中,外在智能工具是不可剔除的系统结构,成为智能环境下教育主体认知延展的典型形式。②独立路径。智能工具通过采集教育主体遗留的学习数据或痕迹,独立完成某些相对完整的任务,如借助记录的文本生成知识脉络的智能笔记程序、采集历史数据进行学习障碍诊断与反馈的智能分析师等。尽管独立路径下的智能工具没有与人类大脑进行直接的交互,但由于技术自身不具有意向性能力,其运转渗透了使用者所赋予的意识与功能归属,因此该类智能工具仍可视为教育主体认知的物理性延展,服务于大脑的认知活动[18]。作为当前极具变革性的延展认知技术,人工智能对教育主体认知能力的强化,让原本独立的个体认知拓展到了“人+技术”认知,从而大幅提升其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4虚拟交互:学习场景改造的逻辑
学习场景具有中介物的功能属性,是促进学习发生的间接支持条件,其担负的重要职责是帮助学习者感知学习对象,构建与世界之间的交往关系。智能学习场景要求学习者与智能机器之间可进行智慧沟通,鉴于后者运行的科学形式逻辑,其构建的资源和提供的服务都是数字化的表达,因此智能化学习场景本身就是一种虚拟与现实融合的场景,虚拟交互是学习者进行交往和感知对象的重要形式。人工智能改造学习场景的另一种手段是借助虚拟技术创设高质量的仿真环境,使学习者产生亲临真实环境的感受,能够沉浸式感知学习对象。可以说,通过人工智能强大的计算能力以及内容生产智能化的加持,虚拟技术真正达到了对现实世界的高度还原,不仅解决了虚拟世界模仿真实世界“样子像”的问题,还解决了“功能像”的难题,还原了“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概念的本意。
从词源来看,Virtual的含义为“虽不客观存在,但从功效来看相当于存在”[19]。例如,一般说Virtual Classroom,意为其在物理层面上不是教室,但实质上能够发挥教室的功能。因此,人工智能推动虚拟现实积极呈现功能意义上的“真实”,其与真实世界一样是学习场景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重要的是,以人机交互见长的人工智能为学习者提供了深度参与的接口,实现了虚拟现实媒介性质的反转。麦克卢汉[20]依据媒介能够提供信息的清晰度和受众接收的参与度等,将其划分为冷媒介和热媒介,其中冷媒介携带的信息量少且模糊,受众的参与需调动多种感官以及丰富的想象力,同时具有再创造的可能性,而热媒介的特性恰好相反。作为热媒介的虚拟现实所携带的丰富情境信息较好地促进了学习对象的理解,但其对受众感知器官的裹挟以及参与主动性的遮蔽,导致学习者广泛存在“人虽在场,身却缺席”的问题,而智能交互起到了关键的“降温”作用。学习者通过智能交互实现对虚拟对象的自然化操作,同时虚拟对象也针对操作形成自然化的反馈。这种自然化的交互状态是以身体经验为基础的具身学习,即学习者通过“体认”的方式建立对虚拟对象的知觉映像,达成与外部事物的实质性关联[21]。可以说,作为人工智能改造学习场景的逻辑,虚拟交互不仅是人机协同的根基,还彻底解决了以往技术所带来的“身-心”二元对立的问题。
三 智能时代专家学习者的特征解析
人工智能凭借巨大的技术优势,能够提供个性、精准和系统化的学习支持服务,然而学习是一扇只能由内向外开启的“心门”,即学习主体凭借心理动作对外部环境信息进行内部加工的过程。因此,智能时代的学习者不能以学习更加技术化为目的,而应该审视智能技术重塑的知识状态、学习机制和教育场景等,培养时代所需的学习专长,以便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规避技术理性陷阱,借助技术优势高质量投身学习活动。为了适应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四种逻辑并规避其带来的风险,智能时代的专家学习者理应具备以下特征:
①知识渊博且善于反思。该特征主要体现了专家学习者如何应对智能技术介入的形式科学逻辑,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智能技术教育介入的形式科学逻辑,使其远超人脑的运算力,刻画的学情以及提供的决策等学习服务更加高效、精准。然而,建立在“暴力计算”基础上的人工智能,由于算法的专有性和偏向性,可能会营造“信息茧房”,让学习者产生知识盲区。此外,人工智能对学习问题处理的程式化逻辑,极易使复杂的学习过程沦为简单的“照单抓药”,钝化学习者的思维并使其陷入“无思”,加剧标准化教育的泛滥。因此,“知识渊博且善于反思”成为智能时代专家学习者所需具备的首要品质。
为应对“信息茧房”威胁,智能时代专家学习者需要“知识广涉”,并善长“技术识别”。前者是指专家学习者能够广涉多领域知识,为智能环境下新知识的学习提供大量的背景性知识,打通新旧知识通道,以便建立知识之间的关系网络,全面评估新知识的价值;后者则关注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工具的迭代更新,理解不同类型人工智能运作的基础原理,能够正确识别其提供学习服务的特征尤其是局限性,继而有针对性地拓宽学习渠道。为了抵御“思维钝化”侵染,智能时代专家学习者还需善于“方向引领”和“学习调整”。前者是指专家学习者需要清楚自己的认知特点,结合所要达到的学习预期,为智能学习服务提供方向性的指引;后者则是专家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能够时刻反思自身学习特征与智能技术所创学习情境的相容性,并根据对认识对象的把握程度,实施监控和调整学习的路径,以克服技术程式化影响。
②以知养德且动机持久。该特征主要体现了专家学习者如何应对智能时代知识价值塑造的尚智趋向逻辑,具体内容如表2所示。智能时代知识价值塑造的尚智趋向,相较于只强调知识本身的学习无疑是一种进步,然而智育所占据的“独大”地位也会带来“知识与德性”疏远的问题。一方面,学习者对知识智力价值的崇拜,势必会挤占知识德性育人的空间;另一方面,学习者的智力借助外在的技术力量确实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但情感、意志、精神等德性因素在学习中的基础性作用将被长期忽视,从而导致学习本能的退化。由于“智力天生就不能理解生命”[22],知识的智力价值唯有通过联结其德性价值才能促进生命的整全发展,继而学习的意义才能全部显现。故而,“以知养德且动机持久”的学习专长,回应了智能时代学习领域的行家里手应该更像“智能机器”还是更像“人”的命题,成为智能时代专家学习者的第二个特征。
依据“以知养德且动机持久”特征的层次,其可划分为“立场守护”意识、“知识拣择”能力、“积极内化”素养和“发展驱动”功效四个维度。其中,“立场守护”指的是专家学习者持有契合智能时代的知识学习观,即面对智能时代知识的激增,纯粹的知识获取将变得徒劳无益,鉴于德性所处的境遇及价值,其应同时转化为德性成长的养料;“知识拣择”要求专家学习者拥有解构思维,知道如何拣择“有益”知识,化解智能时代暴增的知识生产量;“积极内化”是指专家学习者能够积极调动主观能动性,通过觉悟和体悟等方式将知识学习深化为审美旨趣、道德品质和价值观的培养;“发展驱动”则体现专家学习者对知识德性反哺功能的重视,为学习的推进提供不竭动力。
③善用策略且注重协同。该特征主要体现了专家学习者如何应对人工智能对学习主体能力强化的认知延展以及对学习场景改造的虚拟交互逻辑,具体内容如表3所示。人工智能对学习主体能力强化的认知延展逻辑,将学习者与技术工具之间的人机合作从一般性体力劳动拓展到了学习决策领域。进一步而言,人工智能通过精准的数据建模和算法,推送与学情相匹配的学习策略或资源,进而参与到具体的学习决策过程中,但复杂的学习任务或情境更需要学习者综合考量客观决策,利用相关经验对其合理优化和运用,从而实现人机合作的智慧生成。而人工智能对学习场景改造的虚拟交互逻辑,虽然让“虚拟化”客观实在成为促进学习发生的优良对象或环境,但其中更多体现的是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学习者之间及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被严重削弱,从而导致“数字化孤独”以及学习者社会适应能力的欠缺。因此,智能时代专家学习者的第三个特征为“善用策略且注重协同”。
面向复杂学习任务和情境的挑战,不管是由自身构建还是由人工智能提供的学习策略,专家学习者都应对其有深入的理解和把握:要能够做到“策略知悉”,即熟悉主动或被动提供的学习策略目标意图和使用细节;可以较好地实现“策略综合”,即在面对复杂的学习任务或情境时善于综合组织多种策略来创新问题的解决方案。此外,为了疏通学习者之间及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智能时代专家学习者理应具备良好的“团队协同”和“社会协同”能力,前者是指具有协作学习的意识和能力,能够在团队合作中积极担负协同认知的责任;后者则是要重视社会发展对个体发展提出的教育新要求,通过学习成为合格的社会公民。
四 智能时代专家学习者的培育
面对千差万别的学习者,依据传统教学的结构开展智能时代专家学习者的培育显然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任务。不过,人工智能的支持让教师不再受制于教学条件的束缚,能有效参与学习资源和策略的多样化设计,满足学习者学习的个性化需求,这为重构智能时代学习设计的路径,继而进行专家学习者培育奠定了基础。在此过程中,厘清知识学习的取向以及学习场景的构向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1从教学结构转向学习结构:重构智能时代学习设计的路径
当前教师在组织教学活动的过程中大多采用的是教学结构,即为了达成特定的教学目标,教师对可能影响教学过程的相关要素进行的系统组织与安排[23]。由于教学结构具有统一性和规定性,因此其常被视为一种稳定的结构。倘若让学习者以稳定的教学结构完成学习过程,不仅回避了学习者存在差异的这一现实,也忽视了智能时代专家学习者所珍视的知识广涉、学习调节、策略综合等能力的培养。学习结构则主张由学习者主持自己的学习行为,即学习者在教师和人工智能的支持下,根据学习目标的引导,自主设计学习进度,并选择合适的方式来完成自己的学习[24]。在学习结构中,教师和人工智能负责资源策略的供给以及学习的反馈等,通过给学习者适当的帮扶,使其建立一条适合自己认知的学习路径。在此过程中,学习者通过对自身认知的不断审视,逐步建立适合个性化学习所需的学习调节和策略综合能力,并会自主补充知识背景,满足知识理解的需要。这样一来,学习者的差异不再被粗暴地理解为学习能力的优劣,反而成为个体学习力增长的基石。
2从功利价值转向内外兼修:重识智能时代知识学习的取向
在知识遍地的智能时代,单纯的“育分”“应试”等功利性学习将走向穷途末路,否则我们终其一生培育的学习者只是具备了被智能机器淘汰的能力——知识的存储和提取。在人工智能科学逻辑的程式化规制下,知识学习的外化功能应重视不同学科知识对学习者学习素养养成的系统性支持,以便应对复杂的问题情境。这就要求教师充分利用智能学习空间,通过整合、渗透多学科知识,引导学习者解决劣构性问题,培养其探究意识和应对复杂问题情境的能力;就知识学习的内化功能而言,由于智能时代人们对于知识智力价值的崇拜严重腐蚀了教育的“精神气质”,因此该时期的学习比任何时候都有必要成为“人”的学习。针对专家学习者的培育,一方面需要教师打破传统“由外而内”的知识教学过程,通过外在情境的激发、人工智能的辅助、具象性知识的佐证,借助启发、引导、体悟等方式,指导学习者“由内而外”发现心中的真知本慧,促进其思想品质、道德观念等德性的成长;另一方面,需要教师善于利用人类历史沉淀下来的精神文化成果重塑学习者的学习取向,使其追求德性、自由及和谐的美好生活。
3从虚拟具身转向虚实共生:重立智能时代学习场景的构向
人工智能将学习者与数字世界直接联结,并通过其强大的交互能力,使学习者能够以虚拟方式高度感知学习对象,并获得与身处现实世界相同的知觉感受,从而达到虚拟具身的效果。然而,当前凭借人工智能构造的数字虚拟环境与现实世界只存在概念上的依赖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美国哲学家Lewis[25]所提出的“一种形而上学的可能世界”。换言之,数字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是镜像交映式的,它们之间不存在实质性的信息流动或者因果交互影响[26],其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阻碍了个体的社会化进程。智能时代的专家学习者不仅知道社会进步对个体发展的期待要求,更会通过学习将其转化为自身的现实品质。因此,智能时代学习场景的构建需要从虚拟具身转向虚实共生,通过虚拟世界与真实环境的无缝对接,将学习的实景模拟与真实应用、个人志向与社会需求、自身发展与集体角色、主观能动与社会规约等要素进行匹配,提高学习者的人际适应和协作能力,增强社会对其自身学习的影响,培育其适应未来社会的学习意识和能力。
五 结语
自从人工智能介入教育以来,学者就对其影响下的教学模式、学习方式、服务机制和教育伦理等进行了探究,虽有涉及学习专长及培育的描述,但总体上来看还不够深入。作为教育教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学习者尤其是专家学习者专题研究的阙如,导致人工智能教育研究无法聚焦,并弱化了理论成果的实践转化效果。本研究发挥靶向指引作用,当多数教育工作者能够将智能时代专家学习者的培育视为研究和实践的归旨、学习者可以普遍洞察其特征并成为学习的自治者时,“专家”这一修饰词即可去掉,届时人工智能才算真正对教育革命发挥了效用。
参考文献
[1]杨绪辉.从教学样式到学习范式:人工智能环境下学习的通用设计转化[J].中国电化教育,2021,(4):59-66.
[2]Rose D H, Strangman N .Universal Design for Learning: 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individual learning differences through a neurocognitive perspective.[J].Universal Acces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007,(4):381-391.
[3]Stark E, Lassiter A, Kuemper A. A brief examination of predictors of e-learning success for novice and expert learners[J]. Knowledge Management& E-Learning: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13,(3):269-277.
[4]Mavrou K, Symeonidou S. Employing the principles of universal design for learning to deconstruct the Greek-cypriot new national curriculu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clusive Education, 2014,(9):918-933.
[5][9]武志峰.神经科学知识在教育中的迷思与解蔽[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3):73-82.
[6]Devonshire I M, Dommett E J. Neuroscience: Viable applications in education?[J]. The Neuroscientist, 2010,(4):349-356.
[7]Jolles J, Groot R H M D, Dekkers H P J M, et al. Brain lessons: A contribu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debate on brain, learning and education,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an invitational conference organized by the Netherlands organisation for scientific research(NWO)[J]. Neuropsychology, 2006,(3):241-244.
[8]Bowers J S. The practical and principled problems with educational neuroscience[J]. Psychological Review, 2016,(5):600-612.
[10]刘晓力,孟伟.认识科学前沿中的哲学问题:身体,认知与世界[M].金城出版社,2014:32-36.
[11]邱德钧.智能的核心推理:归纳的形式化——AlphaGo归纳学习的进展[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173-184.
[12]安涛.“算计”与“解蔽”: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本质与价值批判[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0,(6):9-15.
[13]鲁子箫.知识的智育困境与德性本质——面向智能时代的思考[J].中国电化教育,2022,(12):44-52.
[14](法)贝尔纳·斯蒂格勒著.裴程译.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19.
[15]张尧均,杨大春.隐喻的身体: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研究[M].武汉:崇文书局,2023:113.
[16]Ihde D. Technics and Praxis: A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J].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s, 1980,(3):259-259.
[17]王永明.延展认知视域下教学认知边界的探讨与重建[J].电化教育研究,2022,(5):26-32.
[18]薛晨,赵星植.虚拟现实技术:新日常生活回归“以身为媒”[J].云南社会科学,2018,(5):179-184、188.
[19]刘铮.虚拟现实不具身吗?——以唐·伊德《技术中的身体》为例[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9,(1):88-93.
[20](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36.
[21]胡翰林,刘革平.从多态表征到置身参与:虚拟现实技术助力学科教学的价值路径[J].电化教育研究,2022,(1):79-85.
[22](法)亨利·柏格森著.高修娟译.创造进化论[M].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151.
[23][24]沈书生.从教学结构到学习结构:智慧学习设计方法取向[J].电化教育研究,2017,(8):99-104.
[25]曹易祥.大卫·刘易斯可能世界理论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2020:4-6.
[26]王晓阳.“虚实交融”还是“虚实交映”:元宇宙的形而上学图景刍议[OL].
Cultivating Expert Learners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ce
——Based on the Deconstruction of Application Logic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YANG Xu-Hui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 Huaian, Jiangsu, China 223300)
Abstract:At present, in view of the dilemma of the existing paradigm of expert learne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the lack of direction for the cultivation of learning talents in the intelligence era, the 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of expert learn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ogical deconstruction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 applications has the dual value of paradigm breakthrough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irstly, the paper elucidated the origin of the expert learners concept, analyzed the reasons why the concept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field of education and trapped in research. Then, the paper analyzed the application logic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 from four dimensions of the interven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the shaping of knowledge value, the strengthening of subject capaci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learning scenarios. Subsequently, the characteristics possessed by expert learners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ce were summarized. Finally, the cultivation strategies of expert learners in the intelligent era were proposed from three levels of reconstructing the learning design path, regaining knowledge learning orientation, and reconstructing learning scenarios, expecting to provide targeted guidance for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promoting learners to effectively engage in learning activities in intelligent environments.
Keywords: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pert learners; ability cultivation; knowledge learning; learning literacy
*基金项目:本文为2023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指向学习体系的AI双师课程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023SJZD052)、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学为中心的AI课堂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3JYB002)、江苏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2年度重点课题“从社会建构走向社会实在: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课程的重构研究”(项目编号:B/2022/01/16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杨绪辉,副院长,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信息化教学设计、智慧学习环境,邮箱为yitiaosan@126.com。
编辑: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