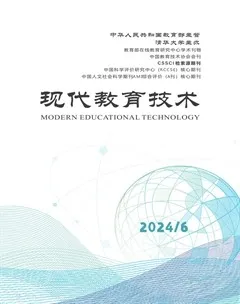破解“南国农之问”,助力新质教育
王竹立 宋肖芋
摘要:发展新质教育离不开大量新型学科建设,教育技术学作为教育学门类中的“新学科”,其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教育技术学科建设一直未摆脱“领域红红火火,学科停滞不前”的怪圈,对于如何破解这一“南国农之问”,教育技术学界长期未得其解。文章从数智时代新知识观视角,重新审视这一难题,认为其根源是错把教育技术学当作传统学科来建设,但教育技术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科,而是一种新兴的软学科。软学科是软知识的集合,特点是不稳定、更新迭代快。教育技术学中硬知识少而软知识多,其学术发展也受制于信息技术的更新速度,表现出阶段性的“信息化热”现象。因此,应从软学科特征出发,重新思考教育技术学的理论建设、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学科文化建设,探索建立新的价值体系与评价标准。此外,文章认为,教育技术学的不可替代性应表现在学科研究对象和基本研究范式两个方面。学科分化与重组是数智时代的大趋势,未来教育技术学有可能与传统教育学合二为一,诞生出新教育学。教育技术学科按照软学科思路进行建设,将为更多新学科建设提供有价值的经验和范例,从而推动新质教育发展。
关键词:教育技术学科建设;南国农之问;新知识观;软学科;新质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24)06—0005—09 【DOI】10.3969/j.issn.1009-8097.2024.06.001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新质人才,培养新质人才需要新质教育,开展新质教育需要新教育学理论体系作为指导,构建新教育学理论体系离不开新型教育学科建设[1]。教育技术学作为教育学中的新学科之一,与现代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关系最为密切,其学科建设中遭遇的“南国农之问”,在数智时代具有典型意义;深度剖析这一“标本”,对建设新型教育学科和新质教育中其他新学科的建设,均具有较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 “南国农之问”产生的背景
我国教育技术学科的起步最早可追溯至1936年提出的电化教育[2],期间经历了1993年更名为“教育技术学”并向其转型,至今已走过80余年。教育技术学科虽曾一度辉煌,形成包括本科、硕士和博士在内的完整人才培养体系[3],但好景不长,始终未逃出南国农先生在2011年底指出的“怪圈”:“当前我们国家的教育信息化可以说是红红火火。教育技术作为一个事业来说,它是红红火火、如日中天,但是作为一门学科来说,它正在逐渐衰弱,独立生存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小”,这个令人困惑的现象被后人概括为“南国农之问”[4]。笔者于2017年也曾发出“教育技术领域前景广阔、越来越好,但教育技术学科和专业前景堪忧,路越走越窄”的感叹[5]。之后仍不断有本专业的学者追问“中国教育技术学向何处去”,认为“无论从何种判断标准,都可以看出,教育技术学距离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并十分尖锐地质疑“教育技术学的‘不可替代性在哪里?”[6]此外,“随着媒体技术的不断更新换代,教育技术学逐渐进入了一个‘没有特色的特色型学科怪圈……由于近年来全国教育技术学发展面临的瓶颈,学科内部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不少教育技术学研究者、学习者、应用者对所从事的学科之价值、地位、前景缺少充分的信任”[7]。据笔者了解,部分学校的教育技术专业本科生中有不少是来自其他专业的调剂生,同时也有教育技术专业学生要求转到其他专业这种情况发生。
但也有人对此持不同的看法,如王运武等[8]认为“中国教育技术学科从无到有,从‘潜学科到‘显学科,从‘发展学科到‘发达学科,创造了学科发展史上的辉煌”。这里要区分“教育技术领域”和“教育技术学科”这两个不同的概念[9],很多人将教育技术领域的蓬勃发展误认为代表了教育技术学科的繁荣,事实上教育技术领域的发展难掩教育技术学科内在的尴尬境遇。在教育信息化事业越来越红火、国家对教育信息化越来越重视的今天,开设教育技术学科和专业的高等院校理应同步增长,社会对教育技术专业的人才需求也理应进一步上升,但事实却是全国开设教育技术学科和专业的学校数不增反减、部分学校招生人数连年降低甚至停招。2019年,全国有13所高校撤销教育技术学本科专业,位居全国撤销专业数量第二[10]。有研究表明,当前社会对教育技术学专业的毕业生需求转弱,教学技术学专业课程体系与社会需求之间匹配度不高,理论性课程偏多而实践性课程偏少,难以满足用人单位对教育技术学专业人才动手实践能力与信息技术水平的要求[11]。一方面是被奉为“制高点”和“突破口”的现代教育技术,一方面却是难孚众望的教育技术学科建设,这种“冰火两重天”的反常现象令人深思。新冠疫情发生以来,越来越多的非教育技术专业学者开始“跨界”关注教育技术问题、在教育技术领域实现“历史性会师”带来的教育技术学术繁荣[12],也反衬出本应成为主力军和中坚力量的教育技术学科自身的落寞。即使是王运武等[13]学者也不得不承认,教育技术学科扮演的常常是追随者而不是领跑者角色,他们指出“自从1993年电化教育更名为教育技术学以来,历经25年发展,其知晓度和认可度仍然较低。”其实,这种现象也并非我国所独有,美国著名教学设计专家Reigetuth[14]就曾感叹道:“我们教育技术人员发现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却处于边缘位置”。
二 教育技术学科建设停滞不前的根源
诸多直面现实的教育技术学界学者,一直希望破解教育技术学科发展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与教育技术领域蓬勃发展不相适应这一问题的成因,并为此提出了许多观点和建议。目前普遍接受的观点是,教育技术逻辑起点不明、学科定位不准,导致教育技术学缺乏独立的知识体系和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关于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和学科定位,有“教育”说、“技术”说、“教育/技术双重定位”说、“问题”说、“教育技术”说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5][16][17]。然而,这些早期的讨论并未给教育技术学科的窘境带来实质性变化,其根本原因在于,仍然将教育技术看作是一种经典意义上的学科,用传统学科的标准、规范去评估和要求教育技术。
真正意义上的一次突破来自陈丽教授团队[18],其在《“互联网+时代”教育技术学的学科定位与人才培养方向反思》中第一次将教育技术学科定位为“用新理念、新技术,破解教育问题,推动教育变革的创新实践领域”,将教育技术学科和教育技术领域直接画上等号。该文指出,教育技术学的产出不只是新知识、新理论和新方法,还有可能产出新媒体、新行业等,并主张教育技术学应向所有学科和方法开放。这就等于变相承认了教育技术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科。
笔者认为,破解“南国农之问”需要新思维。如果今天还在逻辑起点和学科定位上兜圈,还像传统学科一样建设教育技术学,恐怕教育技术学终会走向彻底衰落的一天。迄今为止,教育技术学是不是一个成熟的学科仍存在较大的争议[19]。美国教育技术发展了近百年,至今连一个统一的名称都没有[20]。学科是知识的门类,是对知识体系的划分,也是与该知识门类和体系相关的组织与机构的统称;学科也是教学的科目,分科教学指的就是按照学科分别开展教学。学科与专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专业是人才培养的平台,是综合多门学科知识形成的人才培养体系。学科建设最重要的使命是知识创造,而专业培养最重要的使命是人才培养。基于这个原因,以研究为导向的博士与硕士学位点按学科进行划分,而本科生按专业进行划分。
作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必须有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其内部一定有统一的概念体系、严密的逻辑结构和独特的研究方法。以人体生理学为例,人体生理学早已成为现代医学科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其专业名词的命名非常规范,需要经过权威专家的讨论并达成共识,一旦定下来就不能随意改变;极少存在两个名词意思重复或相近的现象,而且这些专业名词被其他学科广泛接受,成为普遍通用的专业名词。人体生理学教科书的内容都是按照总论、各论来撰写的,各论又是按照人体的器官系统来划分章节的,不同的教科书差别很小,教材的更新只是在原有结构体系上做内容或表述方式的少量改变。同时,人体生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所有的新知都来自实验,必须有设计严密的实验证据做支撑。而教育技术学中的命名则十分随意,任何一个学者都可以自己发明新名词、新概念,很多名词和概念意思相同或相近,给学习者带来了诸多的困难与不便。此外,这些名词并不一定会被其他学科接受和使用,甚至不被本专业其他学者使用,常常是“自说自话”“自娱自乐”。教育技术学没有统一的教科书,各学校常常使用自编的教材,不同的教材无论是体例还是内容都差别较大,很不规范。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也大多来自其他学科,缺少自己独有的理论,如教学设计来自教学论、教育传播理论来自传播学、计算机知识来自计算机科学、学习理论来自心理学和教育学等。教育技术学的研究方法也多与传统教育学研究方法雷同,有学者认为“系统科学方法”是教育技术学的基本研究方法[21],然而采用这种“系统科学方法”得出的研究成果常常大而空,并不能解决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被讥为“脱离实际、不接地气”[22]。时至今日,教育技术学科的社会认可度不高就是一个证明。
那么,教育技术学到底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教育技术学还不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不能按传统的学科标准和规范进行要求与建设,它属于一类全新的知识集合和知识类型,需要全新的学科思维和建设范式。正是因为一直以来误将教育技术学当作传统学科来建设,才使其发展的道路越走越窄,学科建设停滞不前。
三 从数智时代新知识观视角看教育技术学科建设
为了破解“南国农之问”,需要从知识观的视角重新审视教育技术学科建设。知识观是关于知识的本质、来源、结构和价值的理论观点,它对教育技术学的发展和应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网络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诞生与发展,导致知识的内涵、形态、范围和表征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先后出现了重构主义知识观、回归论知识观和数据驱动知识观等一系列新知识观[23]。知识的范围由原来仅限于经典著作中结构化、系统化的精加工信息,扩大到包含网络中尚未被充分结构化和系统化的各种信息、数据等;知识的表征形式由语言文字符号扩大到音视频、动漫、虚拟现实技术等新媒体、多媒体形式;知识的生产主体也由专家学者扩大到普通网民乃至智能机器。其中,最突出的变化是出现了软知识和硬知识的划分——软知识是指那些来源于实践,具有情境性、时效性和实用性的新知识雏形,是尚未被充分结构化、系统化的知识,是硬知识的前身;硬知识则是传统或经典意义上的知识,是那些经过专家学者加工整理,已经充分结构化、系统化,并被公众普遍接受的知识[24]。
软知识与硬知识最大的不同,就是是否具有稳定性。软知识的生成是一个不断更新迭代的过程,其价值具有情境性,往往因“情过境迁”而发生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软知识经历了不断淘汰、更新或重组等过程,可能会有一小部分最终趋于稳定,沉淀为硬知识。一旦成为硬知识,就较少会发生变化,硬知识是一个慢慢累积的过程,并非不断更替。当然,软知识和硬知识的区别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传统意义上的学科是一个具有较多硬知识的知识体系,越经典的学科,硬知识越多,相对而言,其知识更新速度也比较缓慢。以人体生理学为例,在其原有的体系内,知识更新速度已经很慢,需要向其他领域拓展,与其他学科发生交叉、重组,才可能出现较大突破。
网络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极大地加快了知识更新的速度,由此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软知识。这些软知识催生了一些新学科,这些新学科以软知识为主体,没有或仅有少量硬知识,可称为软学科。软学科是尚在形成过程中的新兴学科,很不稳定且缺少成熟的知识体系,也缺少专门的研究方法和范式,其内容构成也在不断更新迭代——教育技术学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
毋庸讳言,教育技术学并没有自己专属的核心理论[25],其主要理论构成大多来自对其他学科理论的拼凑和改造。教育技术学术的发展往往受制于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每当出现新的技术进步,就会掀起一阵教育技术学术研究和宣传推广热潮;当技术暂时停滞不前时,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则归于平淡与沉寂。我国早期电化教育是随着视听媒体技术的诞生发展起来的;网络与信息技术诞生后,电化教育开始向现代教育技术转型;人工智能的出现又开始了教育信息技术向教育智能技术的新拓展。正是由于技术不断进步,才推动教育技术学研究和实践不断向前发展。教育技术领域经历了计算机辅助教学热、数字资源建设热、网络教研热、电子书包热、数字故事热、微课热、慕课热、元宇宙热,直到最近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热等,无一不是由技术进步引发的。“江山代有热点出,各领风骚一两年”,对这种“信息化热”现象,教育技术学人大多心知肚明,但又心照不宣,对这一现象持批评与负面的观点,试图寻找一种稳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然而换一种角度来看,这不恰好证明教育技术学是一门软学科吗?由于软知识(包括新名词、新事物、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等)的不断更新迭代,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也在随之变化。教育技术专业教学内容的庞杂、不稳定、不统一,正是由软学科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决定的。那种试图用“回归传统、回归经典、回归基础”口号指导教育技术学人才培养的想法,恰恰是不了解教育技术学作为软学科的本质特征所致。按照这种指导思想培养出来的人才,更容易跟不上时代与技术的变化,其所学知识与技能往往因落后于时代而不受市场的欢迎与接纳[26]。唯有从承认教育技术学是一门软学科出发,才可能找到新出路。
四 教育技术学科到底应该如何建设
如果接受教育技术学是一门新型的软学科,就可以从全新的视角思考教育技术学科的建设。软学科是各类软知识的集合,教育技术学是一切同时包含教育和技术两个事物的软知识集合。无论是“教育中的技术”,还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抑或是“教育与技术的关系”等,都是教育技术学研究的对象与范围。由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教育技术学科建设问题。
1 理论建设
作为一门软学科,教育技术学尚未形成自己独有的理论体系。软知识是来自实践的知识,其与实践的关系相比硬知识更为密切。教育技术学理论也应来自教育教学实践或教育技术应用实践,同时借鉴周边学科如心理学、传播学、脑科学、学习科学、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技术等的最新成果,逐步建设符合本学科实际的知识和理论体系。
应明确教育技术学是一门实践性学科、技术应用型学科,形成一种由下至上的研究范式,即通过对教育教学实践、技术应用于教育的持续观察和审视,总结经验与教训,借助深度反思逐步提炼出阐释性理论。同时,应该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作为所有教育技术学人的座右铭,旗帜鲜明地反对崇尚空谈、玩弄概念的不良倾向,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技术不同于科学,其更注重实用性、可操作性。教育技术学唯有向社会提供具有实用性、可操作性的技术解决方案,才能赢得社会的认可。因此,教育技术学应摈弃“重理论、轻实践”的学院化倾向,走向教育信息化实践的广阔天地。
叶澜将教育理论分为学科基本理论和学科应用理论两个层次。他指出“基本理论研究者要想与时代对话,要想在一个变革的时代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有所作为,不能没有这样的面向时代变革实践的研究”[27]。对教育技术学研究而言,应该更多地侧重于应用理论层面。即使是从事基本理论研究,也应该将视野扩展到时代变革和教育实践领域。
教育技术学人应充分认识到时代和技术都处于快速变化之中,充分认识到软知识不是一次性生成的,而是不断更新迭代的,从而有勇气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和理论体系,做到与时俱进。教育技术类的期刊对教育技术的理论和实践均有导向作用,应该更多地向教育实践方面倾斜,多发开门见山、言简意赅、对信息化教育教学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和参考借鉴价值的文章,少发或不发脱离实际、言之无物、套话术语过多却缺少新意的玄文,少发或不发用貌似科学的方法证明一些常识性问题的“伪实证论文”,以帮助端正教育技术学界的学风与文风。
2 课程建设
教育技术学专业课程应充分体现前沿性、前瞻性、实用性、针对性,引导学生尽早接触领域前沿和最新技术,而不是重复学习过时的理论与技术。与一般的成熟学科不同,教育技术学没有多少高深的理论知识,无须过分强调经典和基础知识的学习,很多非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学者之所以能“跨界”研究教育技术问题,说明进入教育技术领域的“门槛”并不高。教育技术学应注重开发生成式课程,而不是既成式课程;教师应该和学生共同参与教育技术领域软知识的建构,而不是一味地传授硬知识。
对于相关学科如认知科学、学习科学、心理学、传媒学的经典知识,可以结合教育教学实际需要选择性学习,而且最好采用与最新知识和理论相联系的方式,开展研究和探究性学习,探索其发展演变过程,而不是简单地讲授与灌输,更不要求死记硬背。
教育技术学专业教师应面向其他学科和专业开设通识课、选修课,宣传教育信息化理论和知识,介绍新技术、新方法、新模式,同时解决自身教学工作量不足的问题;应努力说服师范院校和综合大学的管理者,将“教育技术导论”这类课程纳入教育学专业选修课或基础课,让所有有志于从事教育行业的学生进行学习。
课程教学应该采取最新的理念、技术与方法,让教育技术师生先做这些新理念、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实验“小白鼠”,从而获得第一手的经验和教训,才能在未来的工作中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不同学校的课程建设还应结合本地区和近期教育信息化的实际情况,开设一些具有实用性和针对性的课程,以满足社会对教育技术人才的需求。
3 师资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
教育技术学科应拥有两支师资队伍,一支是教育技术学专任教师队伍,一支是外聘教师队伍。其中,外聘教师队伍由教育信息化行业专家、人工智能专家、在线教育企业高管、技术开发专家、在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方面有建树的其他学科教师和熟练掌握某种最新技术的教师等构成。可采用“请进来”和“走出去”两种方式开展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活动。
教育技术人才培养可以按照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层次分别进行。有业内人士认为,美国没有本科层次的教育技术专业,因此我国也应考虑取消教育技术本科专业[28],笔者对此持不同看法。目前,我国中小学仍有信息技术教学和设备维护管理方面的人才需求,部分在线教育企业也需要本科层次的教育技术专业毕业生,因此仍应保留教育技术本科专业。同时,应鼓励其他专业尤其是师范类院校和教育学专业的本科生修读教育技术专业第二学位,并大力发展教育技术学硕士研究生培养,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教育信息化建设需要。至于博士研究生培养,笔者不主张盲目扩大,建议增加专业型研究生的招生比例,减少学术型研究生的招生数量,这也是后工业化时代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29]。
4学科文化建设
教育技术学科应该建立务实、开放、创新的学科文化,形成强调实践、求新求异、不断创新的学术氛围。教育技术学新知识的创生应遵循软知识生成的一般规律,即将众多个体的教育教学实践经验,通过网络的群智汇聚、人工智能的数据挖掘、专家学者的零存整取碎片重构,逐步形成以问题为中心的,具有一定结构化、系统化和普适性的知识体系,并在与实践的持续互动中不断修正、完善与更新迭代。构建软知识、软学科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创新、开拓的过程,要求教育技术人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较高的创新能力和良好的思维模式。同时,应将思维训练作为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之一,以提升师生的思维能力,并将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和包容性思维作为教育技术学科思维的核心。教育技术学研究还应该兼收并蓄、开拓进取,不能固步自封、画地为牢,将自己的研究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
5价值体系与评价体系的探索建立
任何一个新事物要得到认可,不仅需要做出实绩,还需要同时建立新的价值体系与评价标准。作为一个新型的软学科,教育技术学不能照搬传统的学科评价标准,而应建立适合自身的评价指标。为此,教育技术学应以服务教育信息化和数智化转型、推进教育教学变革、促进终身学习型社会建立为宗旨,在实际工作中体现自身的价值与不可替代性。在全球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教育技术学应承担理论支撑、技术引领、方法示范和成效检验等职责,并根据这些职责建立相应的评价体系。对教育技术学价值体系与评价体系的探索,不仅有利于其自身建设与发展,还能进一步推动其他软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五 教育技术学的不可替代性到底体现在哪里
如同软知识具有不确定性,软学科也同样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表现在缺少统一的学术名称、核心的知识体系、特有的研究方法等方面。然而,“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我们仍然需要某种确定性”[30],因为缺少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确定性”,就难以实现自身的不可替代性,教育技术学科就会面临生存危机。那么,作为一门新型的软学科,教育技术学的确定性应该在哪里呢?笔者认为,应该将教育技术学的确定性放在以下两个方面:
研究对象方面,前文已经讨论过,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对象可以比较宽泛,但不能离开“教育”和“技术”这两个要素。这两个要素必须同时存在,缺一不可。这里的技术,既可以是物质技术,也可以是观念技术。笔者不赞同将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对象限定为教学设计技术和课程开发技术的观点[31],也不完全赞同将教育技术学的研究重心从媒体技术、教学设计转向学习科学的主张[32],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只会使教育技术学研究的路越走越窄。笔者主张兼容并包,多方面发展,无论是研究教育与技术的关系、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基于技术的教育、基于技术的学习,还是技术与教育的互动以及技术与教育互动中产生的问题,都可以纳入教育技术学研究的范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教育技术专业人员,还是其他学科的专业人员都可以研究教育技术学问题,只不过教育技术专业人员应更侧重研究一些技术应用层面的问题。
研究范式方面,教育技术学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范式。这种范式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对与教育和技术共同相关的实践的持续观察与审视,借助网络的群智汇聚、专家学者的提炼加工和大数据的智能挖掘,生成一种情境性知识,并随着情境的不断变化对这些知识进行更新迭代,以保证知识的时效性和实用性。这要求教育技术学研究者具有对现实事物敏锐的洞察力,直面事实真相的自觉和勇气,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和整合各种概念与歧见的思维力。这种研究范式叫什么名称最合适有待商榷,对它的研究还处在初步探索阶段,需要今后进一步提炼和明确。这种新型的研究范式有望成为教育技术学研究的主流范式,它是教育技术学科知识创生的主要途径,使教育技术学人具有不同于一般教育学人的气质与风范,成为教育技术学不可替代的主要依据。我国教育技术学(电化教育学)的第一代领军人物孙明经、舒新城以及第二代领军人物南国农、萧树滋等先生就具有这种气质与风范,表现为一切从本土的实际出发,严谨治学、实事求是,以符合本国国情的方式解决本国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对外来的理论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而不是盲目地照搬崇拜[33]。遗憾的是,在教育国际化口号的带动下,第一代和第二代教育技术学人所具有的气质与风范,在当今部分教育技术学研究者中有所减少。一些教育技术学研究者喜欢从书本和文献出发,而不是从本土实践出发寻找研究课题;热衷于引进和介绍国外的理论与经验,却对出自本土的理论和经验视而不见;喜欢生造高大上的名词和口号,无法提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操作性建议;重视表面的科学形式,而违背真正的科学精神;乐于被资本和商业利用,却不愿为一线教师服务;只讲大而全的原则,而不提具体的步骤。凡此种种,皆是导致教育技术学科萎靡不振的原因。教育学中的其他学科研究者可以是单纯的理论家,只进行形而上的理论思辨;而教育技术学人则应该首先是实践家,然后才是理论家。只有这样,教育技术学才能成为理论与实践、教育与技术之间的“中介”和“桥梁”。
六 教育技术学将与传统教育学合二为一
传统教育学认为,教育是由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第一要素是教育者;第二要素是受教育者或教育对象;第三要素有不同的说法,如教育内容、教育媒介、学习环境或教育影响等。笔者认为,随着信息技术逐渐向教育领域渗透,教育技术已成为教育三要素的重要构成之一。今天,技术(包括媒介、方法等)与教育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离开了教育技术,教育将无从谈起。智能时代的教与学越来越呈现“人-机协作”乃至“人-机一体”的大趋势。一部教育史,可视为技术在教育中的发展史。
近年来,不仅有越来越多的非教育技术学专业学者“跨界”研究教育技术,也有越来越多的教育技术学者开始向传统教育学领域进军。例如,网络与智能时代新知识观的提出,就主要来自教育技术学者;联通主义和重构主义(新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也是由教育技术学领域的专家提出来的。在研究和实践领域,传统教育学与教育技术学都出现了交叉融合的现象。相信未来教育技术学有可能与传统教育学合二为一,诞生出新教育学,成为推动新质教育、培养新质人才的重要理论基础[34]。那时,“南国农之问”将自动化解。
当今世界已进入学科大分化、大重组时期,知识的快速更新迭代将导致越来越多新学科、交叉学科的诞生,传统的学科分类和建设范式面临新的挑战[35]。随着软知识重要性的上升、硬知识重要性的下降[36],一些硬学科逐渐退居幕后而软学科日益走到台前,软学科概念的提出和建设范式的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新质教育是相对传统教育而言的,发展新质教育离不开大量新型学科的建设,这些新型学科在发展初期大都属于软学科范畴。教育技术学科知识更新快、与其他学科交叉程度高、受技术进步影响大、研究方法开放多元等特点,是其他软学科所共有的。教育技术学科建设可以参照软学科思路先行先试,为未来更多软学科建设提供有价值的经验和范例。
参考文献
[1][34]王竹立.建构新教育学体系,发展新质教育——从数智时代新知识观入手[J].开放教育研究,2024,(3):15-23、36.
[2]南国农.我国电化教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展望[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0,(1):21-30.
[3]陈琳.中国教育技术学学科地位的世纪提升[J].中国电化教育,2007,(9):9-16.
[4][20][28]任友群,程佳铭,吴量.一流的学科建设何以可能?——从南国农之问看美国七所大学教育技术学科建设[J].电化教育研究,2012,(6):16-28.
[5][15][22]王竹立.衰落,还是兴盛?——关于教育技术学科前景的争鸣与反思[J].电化教育研究,2017,(1):5-14.
[6][19]李子运,李芒.中国教育技术学向何处去[J].中国电化教育,2018,(1):64-71.
[7]卢锋,方丽雅,黄宇星.一流学科建设背景下教育技术学学科发展:挑战、机遇与路径选择[J].中国远程教育,2022,(7):50-58.
[8][13]王运武,黄荣怀,杨萍,等.改革开放40年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的回顾与前瞻[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9,(3):18-27.
[9]李龙.教育技术领域·学科·专业[J].中国电化教育,2005,(12):5-10.
[10]胡钦太,陈娬,王妍莉.我国教育技术学人才培养现状与未来趋势——面向“十四五”的调研分析及建议[J].中国电化教育,2021,(1):66-72.
[11]聂赵育,胡卫星,赵苗苗,等.教育技术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分析——基于2017-2019年数据分析[J].中国教育信息化,2020,(15):7-13.
[12]李芒,段冬新.历史的会师点:教育技术的学术繁荣[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0,(2):3-19.
[14]Reigeluth C M.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t the crossroads: New mindsets and new directions[J]. 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1989,(1):67-80.
[16]南国农.教育技术学科究竟应该怎样定位[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3,(3):2-8.
[17][31]杨开城.教育技术学何以作为一门学科[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0,(6):20-23.
[18]陈丽,王志军,郑勤华.“互联网+时代”教育技术学的学科定位与人才培养方向反思[J].电化教育研究,2017,(10):5-11、22.
[21]李龙.教育技术学科的定位——二论教育技术学科的理论与实践[J].电化教育研究,2003,(11):18-22.
[23]王竹立,吴彦茹,王云.ChatGPT与教育变革——智能时代教育应如何转型[J].远程教育杂志,2023,(4):27-36.
[24]王竹立,吴彦茹,王云.数智时代的育人理念与人才培养模式[J].电化教育研究,2024,(2):13-19.
[25]陈明选,俞文韬.走在十字路口的教育技术研究——教育技术研究的反思与转型[J].电化教育研究,2017,(2):5-12、18.
[26][30]王竹立,吴彦茹.数智时代的知识管理:知识不确定性的挑战及应对策略[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4,(1):21-28.
[27]叶澜.思维在断裂处穿行——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系的再寻找[J].中国教育学刊,2001,(4):1-6.
[29][35]朱永东.新时代我国高校学科建设面临新挑战[J].中国高等教育,2020,(5):44-46.
[32][33]郑小军,杨满福.中国教育技术学科领军人物的历史回顾与展望——兼论第四代学科带头人的特征与使命[J].电化教育研究,2010,(7):29-34.
[36]王竹立.再论面向智能时代的新知识观——与何克抗教授商榷[J].远程教育杂志,2019,(2):45-54.
Cracking the “Nan Guonongs Question” to Boost New Quality Education
——How to Build the Discipline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WANFZhu-Li SONG Xiao-Yu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Taiyuan, Shanxi, China030031)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new-quality education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new disciplines. As a “new discipline” in the category of pedagogy, educational technology has certain typicality and representativeness in its construction experience and lessons. The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discipline has not got rid of the vicious circle of “the field is prosperous, the discipline is stagnant”. How to crack the “question of Nan Guonong”, has not been solved for a long time in the educational technology circ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knowledge in the age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his paper reexamined this problem and believed that the root cause lay in the mispercep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s a traditional discipline, but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s not yet a fully established discipline in the true sense, rather it was an emerging soft discipline. Soft disciplines are collections of soft knowledge, characterized by instability and rapid iteratio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with its preponderance of soft knowledge over hard knowledge, was constrained by the speed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updates, and exhibited the periodic phenomena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ever”.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rethink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teacher team construction, talent cultivation, and discipline culture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ft disciplines, and explored to the establish a new value system and evaluation criteria. In addition, it was believed in this paper that the irreplaceability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should be embodied in the two aspects of discipline research objects and fundamental research paradigms. Disciplinary differentiation and reorganization are significant trends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and in the future, educational technology has the potential to merge with traditional pedagogy to give birth to a new pedagogy. Constructing the discipline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ccording to the soft discipline approach will provide valuable experience and exampl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re new disciplines in the future, thus promoting the advancement of new quality education.
Keywords: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question of Nan Guonong; new knowledge paradigm; soft discipline; new quality education
作者简介:王竹立,特聘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网络和智能时代学习理论、创新教育,邮箱为WZL63@163.com。
编辑: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