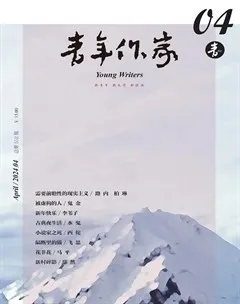花非花
铁花
我从一棵树的枝杈间看出去,一蓬一蓬金黄色的铁花正在小河上空炸开,轰轰烈烈,纷纷扬扬。这天是元宵节,我们一行八人从成都到青白江观花灯,被一盘围棋拖延了一点时间,到达现场时夜幕早已降临,打铁花这个重头戏也到了尾声。我还没来得及选个敞亮的地方观看,铁花就轰然凋谢了。沿河两岸的人声,也像那沸腾的铁汁在空气中迅速冷却,而花灯,依然是热流涌动,随波逐浪。
铁花,没错,打铁花。那是有着千余年历史的传统焰火表演。表演者将生铁熔化成的铁水抛洒起来,再用花棒轮番击打至高处,于是,燃烧的铁屑凌空绽放成漫天火星。
我的记忆深处突然蹿出来另外一份铁花,就像要把刚刚耽误的那部分补上去一样。我立即对七个人说了起来,刚开一个头就明白过来,自己原来是揣着铁花来看铁花。我在灯丛中边走边说,发现听我说话的往前走掉了两个。夜风微微有些寒意,我让花灯拂面而去,只管让铁花扑面而来。
我是从我十岁以后说起的。
那会儿,我刚从一场大病中站起来,就给自己的未来寻找出路了。我已经认准了自己不适合务农,就把身边的木匠、石匠、篾匠、面匠、箩子匠、杀猪匠等等排了一个队,然后给自己挑拣了一个角色,长大以后去当铁匠。我的病尚未痊愈,还需要不时上医院去打针,而从山村里的家到场镇上的医院,怎么也不会把铁匠铺绕开。每次经过那儿,我就想,其实我不用再往前走去医院,直接进去打铁好了。那快要掀翻屋顶的声响就不说了,光是那飞溅到了门外的铁的火星,就足以展示出一派热火朝天的工业景象,让我健壮起来,也让我豪迈起来。
我老早就知道,那铁的火星不是通常的火花,叫铁花。
终于,我有了一个机会,专门去了一趟铁匠铺。
我家的铁料已提前送到了铁匠铺,工钱也已付过,我的任务是在那个约定的日子,把打制好的镰刀拿回家。一个铁匠对我说,等一等。那正合我意,我在那之前只顾着去打针,并没有停下来看过打铁。铁匠铺建在一个高台上,面对着一个戏台,中间是一个宽大的院坝。戏台虽然很少演戏,但时不时会放电影,银幕一旦挂了上去,院坝立即寸土寸金,铁匠铺那个高台也就成了你争我夺的高地。打铁和看电影不会同时进行,要不,银幕上的战斗刚刚打响,突然被几个铁匠抄了后路,就把战略部署打乱了。
那会儿,院坝和戏台都空空荡荡,好戏全都在铁匠铺里。铁匠们分成了两组,两台风箱推拉出一样的呼呼大风,让煤炭燃烧起一样的熊熊大火。铁烧红了,上了铁砧。同样是铁的大锤和小锤,立即对那已经服软的铁进行锤打,扁了再直,直了再弯,弯了再长,长了再短。
我面对铁与火站定,把每一个铁匠都看成了自己打铁的身影。那也是一个个铁打的身影,正有铁花从肩头或是腿部迸溅出来。
铁匠们并不担心铁花会伤到一个孩子,因为他们知道,铁花飞起来时是烫人的,落下去时差不多就凉了。我理直气壮地站在那儿,注意到了,一个组打制的是镰刀,另一个组打制的是锄头。尽管锄头的铁花要茂盛一些,我却两眼紧盯着镰刀,我相信那就是我们家的镰刀。镰刀的铁花已经很小了,我却在心里念叨着再小一些再小一些,要不,铁花四散飞走,剩下来的镰刀也就小了。
淬火,伐齿。一把镰刀,就这样让人以铁的手段,把它的宿命敲定下来。
那个叫我等一等的铁匠,却不知从哪儿拿出一把冰冷的镰刀,交到我的手上。
这一把不是我的,我说,那一把才是我的。
铁匠铺里,好像没有人听见我说了话。铁花,依然那样泼洒着,发出水珠浇地的声音。
我不要这一把冷的。我在心里说,我要那一把热的。
锄头还在继续变形,镰刀之后又有镰刀跟上来。一块铁开始弯腰驼背,另一块铁已经脸青面黑。那个打铁的阵势,既像是在示范,又像是在示威。
我要我的镰刀!
我差点喊出声来,不过我忍住了。我拿着那把镰刀离开了铁匠铺,离开了那乱成一团的硬碰硬的声音。
那当然是一把新镰刀,却好像来路不明。无论割草还是割麦子,它都不如从前的镰刀听使唤。它那样子更像一个问号,问题一大堆。比如,它究竟是不是我们家提供的铁料打制的?如果不是,我们家的铁料去了哪里,成了谁家的镰刀?那个铁匠为什么要让我等一等?那是有意还是无意,好意还是恶意?如果是好意,他那是有意要让我先把手艺学起来,还是让我趁早把那份心收起来?那么,他真的看出我的志向来了吗?
一把镰刀撂翻的问题,差不多和它当初溅落的铁花一样多。
对了,那些铁花,最后都去了哪里呢?
不过,这些追问,并不完全是我当时发出来的,大都是我在今天才想出来的。但我在当时想到的也许远不止这些,谁知道呢?
我上初中以后,学校向学生公开征询各自的志向,铁匠已经在我的选项之外了。其原因主要是,我已经明白了“打铁还靠自身硬”这个道理。今天想来,对一块铁有了疑问,却没有穷追到底,那样一个孩子长大之后想必是做不好一个铁匠的。当然,对写作来说,也是这个道理。我在今天总也想不起来,自己当时是否就有了写作这个志向。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是有,也和当初想当铁匠一样,我并没有把它公布出来。
我刚满十五岁就回到生产队,和四个老人、两个中年人一起,经营集体的一个果园。果园藏在一条山沟里,我是会计兼记分员,那个起点可不低。每逢赶场,一支老中青的队伍,就会走向另一个更大更远的场镇。我们背着苹果、梨子、西瓜、南瓜、葱和蒜等等,去抢占一个临时摊位,早卖完早收摊。
那条路从深沟到场镇,中间还要再穿越一条深沟,最末一段横在场镇上方。每次走到那儿,我都愿意停一停。我站在高处,看见所有通往场镇的路上都是人,听见汇在一起的人声扩散不开,嗡嗡嗡嗡,哗哗哗哗,好像要让横竖几条街都悬浮起来。同时,有一片浩大的打铁声从我停脚的下方直升上来。我知道,那儿不是一个简单的铁匠铺,而是一个铁业社。光听响声就知道,远不止两个组,至少有两个连。那是梦里梦外的铁加在一起的巨大交响,好像让另一条路一起涌到了脚边。我的文学之路,好像就是踩着那个打铁的节奏出发,从那儿开的头。
这些年来,我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再听到过打铁声,镰刀和锄头这些农具恐怕全都走上了工厂的流水线。我说的场镇上那两个曾经的热闹处,那两处火热的地块,就算撒满了铁花的种子,如今也生长不出一个铁匠铺来了。但是,那份砸旧换新的铿锵,那份惊心夺目的绚烂,早已变成了经过锤打和淬火的文字,说生根就生根,说发芽就发芽,说开花就开花。
铁,它那一闪即逝的开花,成就了它一生一世的响亮和明亮。
我从前只领教过它的小打小闹,如今却在一窥之间,见识了它的大开大合。它骤冷骤热,随开随谢,仅用一个急匆匆的结尾,就不知点燃了多少人兴冲冲的开头。我试图替它做一个补充或一个注脚,结果发现,我给它弄出了另外一个版本。
我四下望望,一起来到这里的亲友大都没有走远,花灯的光彩好像让他们都进入了梦境。那个不慌不忙下围棋的朋友,此刻又迷上了熊猫组灯,老半天都叫不动他。我只好以一粒铁花的姿态,从一条遥远的深沟迸溅而出,降落到他的旁边。
灯花
老家安装了高杆路灯,一共五盏,我却是回去了才知道。母亲说,那也是个太阳能,不贵。我知道,父亲还在世时,家里就有了个太阳能热水器。细说起来,那太阳能路灯用的是感应开关,天暗就开,天亮就关。阴天呢?蓄电池好使,阴天夜里照样亮。
那天就是个阴天。我要看一看,太阳能路灯是怎样不分先后亮起来的。我曾经为了在一篇小说中把玉兰花落地的声音写得逼真,在一棵玉兰树下等了十来分钟,直到一朵玉兰花“啪”一声砸到头上。这次我不能再像一根杆子一样站在路边,等着看另外几根都比我高的杆子开灯。我要像以往那样,在黄昏时分绕着老家走上一圈。最好能看到路灯一一打开,然后,踩着以太阳的名义留给夜晚的那一路光亮,慢悠悠地走回去。
老家坐落在一个小山弯里,四周围合的道路早已硬化,既有坡路和平路,又有小路和大路。我先从一条小路爬坡上了一道小梁,也就上了一条大路。我看了看近处那一座山,山间早有一串路灯,要亮起来时山下才看得见。我看天色一时还不会黑下来,就突破了那个“一圈”,转身向右走出去一段,在一个果园边上停下来。那儿从前有一个院子,住了四户人家,我们家就在其中。现在院子已拆除多年,高低错落的地势也在复垦时被整理过。我早已说不准,哪一棵果树头顶盖过一片亮瓦,哪几片叶子底下搁过一盏灯。我说得准的是,我在那个院子长大,直到十六岁重新上学,去县城读了师范学校。
我在那儿站了一阵,才明白过来,那太阳能路灯好像触动了什么,使我回望起遥远的一粒灯火来了。
那是我十五岁的时候。
深秋,整个公社的人都在我们大队集结,参加水库建设会战。一个小道消息突然从此起彼伏的打夯号子声中溜出来,在人山人海中乱窜。我初中毕业已经四个月,也在水库工地参加劳动,却无从向人求证那个消息。父亲在外地任教,他把那个确切的消息急切地送回家来:招生考试制度恢复了,已经向全国发布。
我知道,我没有资格报考大学,但我凭着一张初中毕业证可以报考中专。当时,我们那个院子里住满了来修水库的民工,其中有我的校友,也都和我一样没被推荐读高中。他们和我一起报名之后,再也不到我住的木楼上去了。木楼顶上盖了一片亮瓦,西墙开了一扇小窗,靠窗有一张木桌和一盏煤油灯,摆布一个学习小组不在话下。他们对我说,谁不知道你是尖子生,就指望你脱下草鞋穿皮鞋,怎么还敢去影响你呢?
距离考试时间已经不足二十天,转眼就入冬了。白天,谁都要上水库工地,没法复习。夜里,不管多累我都会坐到煤油灯面前去,复习政治和数学。语文,我觉得自己用不着复习。母亲已经买回了足够的煤油,只对我说了一句,把灯点亮些。她知道我会心疼煤油,舍不得让灯芯往上冒一冒。民工队伍好像全都转入院子地下,没有一点动静,我只偶尔听到头顶亮瓦过风的声音。那扇小窗一直紧闭着,我和灯都不需要冷风。我更不需要看一看夜晚的模样,反正如同一个大得无边的锅底,连个灯花花都没有。
花花,是我们老家一带的方言。比如,给人帮工,回来抱怨主人家伙食不好,连个肉花花都没有。又比如,听说某处要放露天电影,夜里大老远赶过去,连个电影花花都没有。又比如,天阴着,连个太阳花花都没有……
花花,差不多就是渣渣。
灯花花都没有,就是说,一粒灯火都看不见。
事实上,当时农村已经有了一些起色,并不是都穷得连一盏灯都点不起了,但电灯依然还是一个遥远的梦。谁家有一盏带玻璃罩儿的煤油灯,那简直就是“轻奢”了。而我们自制的煤油灯,灯芯结出的一粒火苗,就像叶尖上的一粒露珠,呼吸重了它都会灭掉。那灯花花,只有被什么遮挡起来它才会有一点安全感,比如,一面没有裂缝的墙,一扇关得严实的门,一本打开并且站立的书。一粒灯火大不过露水,再被贴身拦截,别说远处,就是到了跟前,都不一定看得见。
民工队伍撤了,考试时间也近了。一天深夜,我被困在了一道几何题里,就抬头看了看亮瓦,知道月亮出来了。我有一个醒脑的办法,不要逻辑,胡思乱想。我想,灯火虽小,却也会让亮瓦晕出一块长方形的亮光,再由下到上泄露给月亮,并且会让整个天空都知道。地上的灯光连天上都看得见,为什么在地上看不见?我这样没来由地想一通,就狠下心来,让灯芯往上冒了冒,然后站起来,把小窗也打开了。那由我独占的一粒灯火,发出又大又亮的一团灯光,从窗口跳跃出去,让我看见了月色,也看见了霜。
我还看见,远处山上有个灯花花,一眨眼就不见了。
我没有多看外面,也没有把小窗关上。我好像需要一点其他亮光,月色、霜,另外的灯花花。还有,要是有人在远处能看到我的灯,也好。不一会儿,我就识破了几何图里一个梯形的真面目,再一次站起来,就好像踩在真正的梯子上了。我“更上一层楼”,好像立即就看得更远一些了。
我希望再看到那个灯花花,却落了空。
尽管夜里都下霜了,但在我的印象里,那是一个暖冬。如今,深夜开窗的那一幕在我的记忆里早已模糊,说不定只有“明月光”而没有“地上霜”。那灯花花,也可能是一个梦花花。但我却清楚地记得,考试那天,没有雨,没有雪,也没有风。考完我回到家中,继续下地干活,直到收到信封上写着我名字的一封信。那是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也是我平生收到的第一封信。
从此,我读书、教书并且写书,没有哪个夜晚离开过一盏灯。
我不知是在哪一本书上遇到了“灯花”,误以为就是那个所谓的“灯花花”。不过,我很快就弄明白了,灯花是灯芯燃烧时结成的花状物,从古至今都以它为吉兆,甚至把它和喜鹊相提并论。
灯花,它不是灯芯在火焰里的灰烬,而是灯火在亮度中的结晶。
我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前,却并没有听到“喜鹊噪”,也不知道还有什么“灯花报”。但我在十五岁那年一定见识过或含蓄或兴奋的灯花,只不过因为当时的懵懂无知,让它被忽略被遮蔽被埋没了。但“灯花”这个词却并没有缺席,它在那个梦断十年的暖冬,以喜结万家的温情,不时爆起爆落,乍开乍放。旮旮角角、星星点点、五湖四海、万水千山的灯花,连同那还有一口气的“灯花花”,汇成了一个时代的吉兆。
阳春三月,山那边吹过来的风暖意融融。山影已经凝重起来,我又向近处那一座山望过去,山间那一串路灯亮了。那个出资把一面空山点亮的老乡比我小几岁,也是我的朋友。他在老家上学时总是两头摸黑,在山间来来去去不知受过多少怕,当时就想,将来自己要是有了本事,一定要给那段山路把灯点上。他考上大学从山上走了出去,然后在重庆扎下根来,把事业做得风生水起。山城亮灯的时候,他大概会不时想起,家山也已经被点亮了。
我四下看看,远远近近好多人家都亮灯了。那一片一片灯光绽放的光彩,一层一层覆盖了我的那些记忆花花。我突然想起什么,赶紧朝小山弯看回去,还好,那高高举起的太阳能路灯还保持着一种低调,没有哪一盏亮起来。
我听见母亲大声叫着我的名字,她喊我回家吃夜饭了。
我在十六岁就算是离开老家了。四十几年过去,母亲喊我的声音还一直那样。我加快了脚步,但是,或许还在半路上,太阳就从老家门外的路灯里出来了。
稻花
那天下午,我登上了一辆从县城开往乡下的客车。客车要在一条破烂的公路上爬行三个多小时,我一点也不在意,因为我刚买了几本新书,其中一本是《百年孤独》。我到县城买书,没想到会在书店遇到这本如雷贯耳的外国小说。我年轻时有个习惯,会在书的扉页写上买下它的时间。所以,现在,我把它从书橱中取出,翻开就知道,那是1985年1月下旬的一天,星期天。
客车开动不久,我就拿起《百年孤独》,小心地打开来。
“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这个著名的开头,我已经从报刊上熟知,它就像一字不差的暗语,让我和大名鼎鼎的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接上了头。很快,磁铁在小说中出场了,客车好像也被吸了过去,和书里的“铁锅、铁盆、铁钳、小铁炉”一起乱滚起来。客车上爆出阵阵惊呼,好像夹杂着从书里跑出来的声音。我大概只读了两三页,就把书合上,公路上的坑洼也渐渐合上了。客车消停下来,我透过车窗,就看见外面的水田了。水田会在冬夜结冰,和我刚读到的“冰块”却不一样。我已经记不起来那天的水田有没有结冰,记忆里却留下了它们那亮晃晃的“孤独”面影。
不知过了多久,我渐渐回过神来。春节快要到了,要不了多久,水田就会插上稻秧,稻秧就会抽出稻穗,稻穗就会开出稻花……
车厢里挤满了人,还有年货。我却好像闻到了一缕香气,朴素,淡雅,夹着一点泥腥味。那香气,不知是来自我一时想到的稻花,还是来自我一直拿着的新书。
直到过了春节,我都没有再打开过那本书。我年轻时还有一个习惯,会在书的末页记下读完它的时间。我现在翻开书就知道,一共过了五个春节,我才在一个正月里第一次把它读完。
许多年之后,面对一本破旧不堪的《百年孤独》,我又一次回想起,我带着它乘坐客车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我在家乡中心小学任教,并且同步做起了文学梦,一有空闲就“爬格子”。我邮寄出去的那些稿件,要么原路返回,要么泥牛入海。1985年春天,整整五年过去了,我却连一个文学青年都算不上。所以,我在周末回家去,那步行只需十来分钟的一段路,也像文学之路一样别扭起来。
在家里,我就不一定坐得住了。天气已经暖和,水田开始嘈杂起来。我需要的创作素材并不在一间土墙屋里,而是在田间地头,因此,我拿着一本杂志出门了。杂志可以卷成一个筒,我就像拿着一件纸制工具去参加春耕。结果,我只是在远处听了听抽水机的响声,在近处看了看戽水或者耕田。我一副游手好闲的模样,既冷落着远道而来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又疏远着身边的责任田。
秧插上了,草也薅过了,稻田都已经转青了。满眼碧绿,文学在哪里?
那会儿,就是一份普通的文学报刊,也能让人感受到一个时代激情的涌动。我所在地区有一张公开发行的报纸,新推出来一个栏目“我的星期天”,还发出了征文启事。家里不需要我种责任田,除了读书和写作,我的星期天还能有什么呢?那就照实写来好了。我写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个青年应该有的简单模样,还搬出雨果和罗曼·罗兰以壮声色。我那时候要是也像后来那样对加西亚·马尔克斯顶礼膜拜,我一定会拿《百年孤独》来做文章,而不是只字未提。
那篇五百字的短文,很快就在报纸上刊登出来。
终于,我用了五年时间,写出了报纸上的一个“豆腐块”。那篇短文的标题里有一个“芽”字,我知道,就文学而言,我还只是一粒谷芽。我一点也不灰心,我相信自己也能成为一株秧苗,也能抽出一串稻穗,开出一溜稻花……
那篇短文,让我的钢笔字第一次变成了铅字,因为还标明了作者单位,所以,在接下来的夏天里,我接到了此生的第一个电话。那时候一个乡恐怕只有一部电话机,那个电话从县上打下来,到了第三天才被我接上。电话通知我,赶紧到县城报到。我回到家里,并没有急于通报电话的事,因为电话那一头并没有说让我去干什么,我也没问。我不会往坏处去想,却担心自己掩饰不住内心那一份莫名的得意,就趁着太阳还没有落山,到田埂上去走了走。
稻花,已经开了。
那从小到大闻熟了的稻田气息,扯着水,带着泥,从四周包围过来。我向稻田弯下了腰,轻轻地捋着稻穗,就怕伤着了稻花。稻花,那么微小,那么细弱,不像是稻穗开放出来,倒像是风把它们从别处吹送过来,被稻穗黏了上去。过些日子,一粒稻花不知会被放大多少倍,变成一粒稻谷。我双手捧着稻穗,就像抓到了好素材,我一松手就会把它弄丢了。事实上,我是在等稻花的香气在手上攒够了,才好让它变成新米一样的文字。我直起腰来,刚张开手,一阵微风就过来,把我轻握的那一把香气都带走了。
夜里,蛙声从稻花香里爆发出来,连篇累牍,颠三倒四,远远近近的稻田都在说梦话。我在梦里坐上了开往县城的客车,车轮轻松地绕过了一个又一个坑洼,满车的人鸦雀无声。车外,那水田依旧亮晃晃的,却也是蛙声一片。
不出所料,事情还真是因我那“豆腐块”而起。我一到县城,就领受了写一篇命题作文的任务。那是大会上的一个讲话,远比那“豆腐块”要长,要求半月之内完成。结果,不到三天,我就冒冒失失地交了卷。然后,我只好一直住在县上的招待所里等待,就像在等待一个分数,或者一个录取。那些多出来的时间,我大都给了书店。我在那里发现,原先摆放《百年孤独》那个地方,已经换上了别的书。
夏天就要过去了,我终于等来了一个接见,得到了一个当面的肯定。那几句话掷地有声,立即就让我刚冒出的一颗嫩芽,变成了一株绿秧。
接下来,我拿到了一纸调令。
1985年,我刚满23岁,就从乡下调进县城,以为从此再也不会为买书去坐客车和住旅馆了,却遭遇上了“刹住抽调教师之风”新规,很快又被调出县城。那一年,我坐了几趟颠簸的客车,再加上那一趟“过山车”,无须等到“许多年之后”,就好像把“孤独”和“魔幻”都体验过了。那不过是我人生的一个弯道,倒是让我一夜之间长大了十岁。我深以为憾的是,在我最需要一部伟大作品的日子里,《百年孤独》竟然被束之高阁。
我到了离县城稍近的学校,重新站上了讲台。过了一年,我就开始在刊物上发表小说了。我再一次打开了《百年孤独》,读了不上十页,它就让我知道,我自以为已经转青的秧苗,仍不过是个“芽”。
然而,随着我发表作品的增多,我从乡下进入城市的道路变得顺畅起来。我在小城市工作了几年,就来到了大城市。
几十年下来,作为一个作家,我写得最多的还是乡土,而不是城市。
前几年,我创作一首歌词,才写下两句,就意识到有什么被我省略了。
“梦里一颗露珠秧苗儿青,
梦外一只蜻蜓谷粒儿黄……”
秧苗在梦里转青,谷粒在梦外泛黄。人生如梦,那么,什么时候开花呢?
稻花,它怎么能够缺席呢?
结果,改来改去,稻花依然没能出位。它黏上一个句子,那句话好像就拖泥带水起来,当然,“稻花香里说丰年”除外。
还好,我把一只蜻蜓从梦里放了出去。
接下来,我看见了成群结队的红蜻蜓了。我一时不知道,那是回到了梦里,还是回到了年轻的记忆中……
稻田已经熟透,稻穗已经满足得昏了头,挨挨挤挤,搂搂抱抱,大概已经弄不清开花那回事了。那一团一团的红蜻蜓,起起落落,懒懒散散,兀自让稻田升起了暖色的轻烟。我看出来了,它们不是来标注季节的,而是来扮演花期的。它们要以爱情或是别的什么名义,完成一场别开生面的开花。它们降在了哪一片稻穗上,那一片金黄,就会绽放出鲜红的花朵……
【作者简介】马平,作家;生于1962年,四川苍溪人;著有长篇小说《草房山》《香车》《山谷芬芳》《塞影记》,小说集《热爱月亮》《小麦色的夏天》《双栅子街》《我看日出的地方我在夜里说话》《高腔》和散文集《我的语文》等。曾获四川文学奖、“中国好书”提名奖 、人民文学奖、川观文学奖;现居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