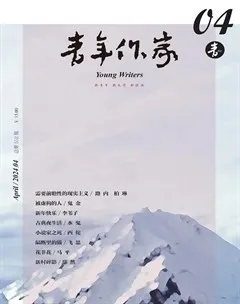新村碎影
天越来越暗,刚才还阳光明媚的天空,突然间变得灰黑起来,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和她身后的房屋全都笼罩在了阴影里。女孩抬起头来,惊异地望着天空,只见一片暗色的阴影移动着,飘向了太阳,遮盖上去,把日轮变成一束小小的环状银色光芒,把她的四周变得如黑夜。她大惊失色,呆望着环状的银色光芒,不知所措。她的身后,一扇门开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走了出来,对她说:“别怕,这是天狗吃日呢!”
那是我十二三岁时的事了,母亲对我说天狗吃日前,我正在门前的土路上踮着脚跳《白毛女》。
记忆里那个十多岁的女孩,穿着一双红色灯芯绒面料的布鞋,将身体的重心竭力落在由手工制作的厚厚的鞋底尖部,以鞋尖的硬度来支撑她的身体如芭蕾舞中的白毛女那般起舞。她的动作既不规范,也不老练,却自个儿边唱边跳,跳得如痴如醉。
母亲拉住了她的手,她和母亲都望着天空,直到太阳从黑色的阴影中跳了出来,她和她的母亲,还有身后的房屋重新置于阳光中。
就像《蝴蝶梦》中的女主角讲述她梦见自己回到了曼德里庄园一样,我也通过那个踮着脚起舞的女孩回到了我儿时生活过的地方,那地方叫大院坝。
那是一个如今只能在梦中才能够回去的地方。但它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新世纪的前十年,却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与蓉城那时的众多建筑一样,谱写着一个城市的历史。
每一座城市,都有它的历史。就像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对我而言,一个城市的历史,是由许许多多看得见的房屋建筑、桥梁道路、风土人情和看不见的精气神、消失的影像与消失的房屋、道路桥梁等组合而成的;一个人的历史,是由不同阶段的影像和发生在其身上的故事构成的。无数人的影像,汇集在其所在的城市,那些或消失或正在上演着的人生中的酸甜苦辣,融入到时代的大潮里,还有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尤其是历朝历代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留给这个城市的骄傲,组成这个城市的前世今生。
蓉城,在它的前世今生中,有一个已经消失的建筑群,叫太平南街新村,它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这座城市里众多由白墙、砖石、混凝土和木材与灰瓦建筑的房屋之一。或许,在那些如雨后破土而出的蘑菇似的建筑物中,它是很不起眼的,既无浣花溪杜甫住过的文化荣耀,亦无宽窄巷和少城的历史荣光,更无永陵王建墓的皇家贵气,不过是成都众多平民百姓的居住地,但它的影像,始终活动在那些消失了的印痕中,活动在我的魂牵梦绕里。
太平南街新村,是一个由好几个院坝和一排排房屋与土路组合而成的院落,我们叫它大院坝,它地处九眼桥汽车站通往三瓦窑靠近成都十二中学那条大马路的地段上,大院坝的深处紧接四川大学十四宿舍,它的前半部分,有一个不大的开阔地面,类似今天一个社区的小广场。这个“小广场”是生活在这个大院坝的人们聚在一起的热闹区域,在它还没有被高楼大厦覆盖前,曾经有过一段热闹的历史,是川大学生、教师,包括那时在川大教学或读书的外国人到此品茗聊天吃冷啖杯的好去处,大院坝的住户,许多都做起了这个“小广场”的生意。大院坝的“小广场”和其中的一些小院坝,渐渐成为了外来者的玩耍地。而更早前,在我少女时代,它是一个充满着人们油盐酱醋味而非商业味的场所。
最先,那个被大院坝的人们喊成小兰的我,与我的父母与弟妹就生活在门牌为“太平南街新12号”的小院坝里。
这个小院坝叫王家院子,它的女房东,是父亲的老乡——我们叫她大孃。大孃的男人王伯伯,1949年前是成都汇丰银行的经理,自然有钱,才能在太平南街新村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建成后,买下这个独户之家的院落。大院坝的独户小院不多,更多的是小院坝里生活着几户人家。
这些小院坝,完全不同于北方那些规整的四合院,讲究一种整齐的布局,而是显得随心所欲,建筑它们的设计者好像觉得一定要出新出奇才令人叫绝似的,整个建筑的设计有一种让人防不胜防的奇怪。“小广场”左边,是张家大院,张家大院门外有两个石狮子,黑色的大门和有些高的木条门槛,还有跨进门槛后不见院落只见照壁的设计使张家大院充满神秘感。尤其常有黑色的小轿车停在张家院门前,令上世纪六十年代还在读小学的我和生活在大院坝的伙伴们,对张家大院怀有敬畏之情。
太平南街新村建筑群,准确地讲,是由我正在讲述的这个大院坝和其它几个巷子与院落组成的。所以,这个大院坝只是新村建筑群里一个庞大杂乱的房屋罢了。
小时候,尽管大院坝有自己的水井,但我却更喜欢到外面培根路上的那口水井打水。打水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硬式的,即把水桶挂在竹竿上,双手握住竹竿慢慢移动,把水桶伸向井底,然后左右晃动竹竿,桶里装满了水后,再双手交替移动竹竿往上提,直到把水桶提出井口;一种是软式的,用麻绳捆了水桶送入井底打水,如果掌握不好力度和技巧,就很难把水桶装满提上来。所以,我还是更喜欢用竹竿打水。
还记得,我家的水桶随着我的年龄一点点变大。九岁时,最先去打水,父亲给我买了一对小木桶,还有一根比别人的小的扁担,用漆把它们涂成大红色。把红扁担扛在肩膀上,挑着红色的小木桶,我觉得可以用今日的“拉风”二字来形容当时的心情,很自豪得意呢。别人的水桶,比我大,桶是木头的本色,我就总有一种“过家家”的感觉。
这种“过家家”的新鲜感,随着水桶的变大就渐渐消失了。
当时,大院坝的人们用水有两种方式,洗菜淘米洗衣什么的,用井水;而煮饭喝水等入口的,则用自来水。自来水售水点设在大院坝外马路斜对面,紧靠如今也已消失的陶瓷厂旁边。一担水两分钱。从售水点到我家居住的新12号,有一千米的距离,所以,我得歇息几次,才能把自来水挑回家。而打井水的距离则近多了,三百来米吧。
随着年龄的增长,那种挑着红水桶“拉风”的感觉已消失殆尽,去井口打水,成为日常生活的必须,如人要吃饭一样寻常,但有一天,这种寻常的平静却被一个突如其来的意外打破了。当时十三岁的我,挑着已经不是红色而是比红色大一些的木桶来到水井旁的水泥地上,当我放下木桶和扁担抬起头时,正看到了母亲正走在培根路上。我知道母亲是去九眼桥汽车站旁的工厂上班的,但为了偷懒,还是向母亲叫道:“妈,你来帮我打水呀!”边叫边朝后退,在母亲大喊“不要后退,危险!”的同时,突然一脚踩空,整个身子落入了井口里。我本能地用双手紧紧抓住井口边沿,旁边一个打水的男人和吓得变了脸色的母亲赶到井边,二人一起把我拖了上来。脱离危情后,我“哇”地一声大哭起来,从此,再也不敢去水井打水了。
我实在吓破了胆。
幼铭姐的外婆——我们叫她胡婆婆,教给我母亲一个找回胆量的办法:喊魂。
母亲按照胡婆婆的吩咐,半夜时分,从新12号的大门走出,在夜深人静中沿着土路边走边叫:“小兰,你回来!”就这样喊着来到水井边,然后又蹲在井口,低头朝黑咕隆咚的井底叫着,要把自己女儿被吓破胆的魂从井底唤回来。母亲外出喊我的魂魄时,我还在熟梦中,对此浑然不知。
就这样连喊了三天的魂,我终于又挑着水桶走向了井边,但依然不敢在井口打水,每次都是跟着母亲,母亲从井里帮忙把水打上来,便匆忙上班去了,我则挑着水桶回家。
母亲上班后,家里的水缸没了水,我宁愿多走路挑着桶去陶瓷厂旁的售水点买水,也不愿一个人去井边打水了。
时至今日,那个被吓破胆的我,依然对井口心有余悸,如果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们还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们那样得靠井水过活的话,我相信自己还是不敢站在井边,把桶放入井里的。
多年后,母亲才告诉我为我喊魂的事。
现在想来,我知道不是父母狠心,让十岁前的我就去井口打水,而实属无奈。
那时候,父亲远在西藏昌都工作,母亲要上班,只好把我和弟弟妹妹托付给院子对面的邻居胡婆婆照看,从此,幼铭姐——一个原本与我家非亲非故的人,便成为我们再也离不开的亲人了,才十四岁的幼铭姐,承担起了照顾我们的任务。
胡婆婆是幼铭姐的外婆,一双小脚,走路颤巍巍的,老是穿着一件深蓝色中式斜开襟。胡婆婆儿孙满堂,与她的两个儿子——我们一个叫四叔、一个叫二叔两家人住在一起,幼铭姐的父母在外地工作,她和她的妹妹小铭姐由胡婆婆带着生活。可想而知,吃饭时再加上我们,堂屋里的那张大圆桌,总是被大家挤得满满的。
桌上的菜,自然十分简单,两三个炒素菜,还有一碗泡菜,固定的,难得吃上肉。后来,幼铭姐干脆带着我和弟妹另起炉灶,在我家做饭给我们吃,母亲上班是三班倒,夜班不在家,幼铭姐索性从胡婆婆家搬到了我家,带着我们过夜。
妹妹还未断奶,傍晚,哭闹不止时,幼铭姐就会背上我妹,带着我和弟弟,去厂里找母亲给妹妹喂奶。这时候,那个后来随太平南街新村一起消失的培根路和九眼桥汽车站,包括车站旁边母亲上班的工厂,便化作一帧帧影像在我眼前流动起来:
暮色中,一个左手有点残疾的少女,背着一个不到一岁的婴孩,右手牵着一个五岁的男孩走在前面,少女左手的残疾,是小时候得脑膜炎留下的后遗症。她的身后,跟着一个黑黑瘦瘦、看样子不过八九岁的女孩,他们沿着培根路,在路口右边的理发店停了下来,少女指着理发店门外那个发亮不停旋转的彩灯哄着背上哭闹的婴孩说:“妹妹,不哭哈,你看这转灯,好好看啊。”他们看着理发店,理发店里正在烫发和理发的人,也透过琉璃窗看着他们。然后,那个黑瘦的小女孩,转身抬眼看着街对面,她看到,街对面的诊所亮着灯,诊所不远处的那家百货小商店还没关门,营业着,而它旁边老马路口的那个蔬菜摊,则没了人影。蔬菜摊不远处,有一个白天人声鼎沸的茶铺,这时候也关了门。那个茶铺,兼搭着卖开水,白天,家里没有开水,来了客人时,母亲便让她提了温水瓶,来此花两分钱即可打一温水瓶开水回家。
她十分喜欢提着温水瓶到这个茶铺买开水,茶铺里,那些竹椅上总是坐满了人。跑堂的伙计提着长嘴茶壶,在桌椅间穿梭,肩膀上还搭着一条毛巾,动作娴熟地为客人倒茶添水。茶铺的一排炉子上,炭火熊熊,上面烧着一壶壶水,她交了钱,老板便高声叫着伙计过来帮她提了水壶装开水。
少女带头迈步,他们走过理发店旁边的农机厂大门和挨着大门排列开来的店铺,来到九眼桥汽车站,这里是人们前往三瓦窑、龙泉驿、华阳等地方的集散地,十分热闹,有糖果店、眼镜铺等。糖果店里,不同花色的糖果装在一个个玻璃罐里,玻璃罐排列着摆放在柜台上,柜台里则装着不同样式的糕点。煞是诱人。但糖果和糕点,都要凭票购买。
幼铭姐带着我和弟妹走进工厂,母亲在龙门刨刨床前埋头干活,我叫了声“妈”,母亲便来到我们身边,帮幼铭姐从背上解开绳带,抱了妹,坐到一旁,解扣为她喂奶。弟弟则兴奋地在那些车床、钳工台间跑来跑去,幼铭姐在后面追,把弟拉回母亲身边。吃了奶,妹睡着了,我和弟也睡眼蒙眬,幼铭姐用布带把妹又捆在她背上,带着我们在夜色中返回新12号。
新12号的大门,不像张家大门那样气派,甚至还没胡婆婆那边院子的大门大,是要小一些的本色双开门,从外表看,低调而不起眼。
在这个院子里,大孃和王伯伯还有他们的四个儿女住上房,我家住下房。所谓下房,是我的叫法,就是靠近木门的两间房子,房子在进门的右边,左边,有一块七八平方米的地方,被大孃建了一个竹条编成的养鸡棚,虽然这个鸡舍传出的味道破坏了这个院子的雅气,但大孃对母亲说,养的鸡,既可以吃它们的肉,又可以吃它们下的蛋。
从下房到上房,中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花园,里面种着各种花草,不知咋回事,现在说起这个花园时,总让我想到鲁迅笔下的百草园。一条小道从花园穿过,左边更多种的是菜,有葱、蒜、西红柿、辣椒什么的,右侧才是花草。左边靠近上房的地方,有一个厕所,分男厕女厕,还有一个坐式的马桶间,这个马桶间总是上锁,我们上厕所,都是在蹲式的厕所间。厕所后面有一条通道,通道的墙那边,是张家大院。沿着通道,可进入上房的后花园,这个花园要小得多。沿门右侧而出,五十米处,便是那个让我魂飞魄散的水井了。
如果从大孃家去这口井打水,要比我沿着新12号门外的土路前往近得多。但我的记忆里,从未走那儿打过水。
新村大院坝里,除了张家大院和王家院子有自己的厕所外,其他人都是上公厕,公厕坐落在大院坝外,我们叫它大马路的对面。
还记得有一年,父亲从西藏回来,早上起床去公厕解手,很久不回,母亲念叨说:“你爸解个手,这么长时间了,咋还不回来呢?”父亲回家后,母亲询问原由,我们才知:父亲的英拉格手表揣在裤兜里,在他解手时掉进了蹲坑里,用手捞不着,无奈,只能守在一旁,直到大院坝的熟人来解手,帮他找来火钳,才把手表夹了上来。
因为没有自己的厕所,每天下午四点过,是大院坝的住户倒马桶的时间。那个耳朵有些背——我们叫他聋子大爷的男人,总是准时来收集粪便,扯着嗓子在土路上吼着:“倒马桶啰!倒马桶啰!”聋子大爷还负责清除张家大院和王家院子的粪便。
这些粪便,是新村毗邻的农村浇地肥料的重要来源。当时,从川大十四宿舍到校园外,都是一片片的农田。
有趣的是,那个穿着绿色的制服、骑着绿色自行车的邮递员,则是上午出现在大院坝里,给人们送来邮件和报纸,他把自行车骑得飞快,在大院坝的土路上穿行。父亲从西藏寄来的信,还有每月寄来的钱,都通过他的投递交到我们手上。如果他叫:“孙家莲,有你的汇款!”恰巧母亲在家,就会拿出她找人刻制的那个有机玻璃的章子,在邮递员递来的签收单上盖章。我还记得那个小巧透明的印章上,雕刻有一朵红色花朵。那时有一句民谚:“车轮子一响,黄金万两。”虽是夸大之说,却也显示出了那个年代的物质匮乏。但因了父亲在西藏昌运司工作,能不时给我们带回一些当时在蓉城难得的牛羊肉和上海奶糖、白糖红糖、美加净牙膏等物品,我家的生活质量,显然比大院里我的小学同学和小伙伴们要好得多。
大院坝除了不时有黑色小轿车停在张家大院门外让我们感到的神秘,还不时有西藏昌运司解放牌汽车停在那个坝子里带给我和家人的喜悦。
这些糖果,除了自己吃,我还用它讨好大院坝的小伙伴们。没有糖果的时候,我就同要好的小学同学刘秀群、舒文伟在我家的厨房里用白糖制作糖饼,我们把白糖放进奶锅在蜂窝煤上烧化,将菜刀一面抹上清油,然后把融化后变成褐色的糖汁一一倒在刀面上,又用竹签插在这些糖饼上。冷却后,一个个糖饼就做好了。我的这两个小学好友,不住在大院里,她俩的家,就挨着我就读的太平南街小学,但她俩总是背了书包来找我,我们三个,再从我家走到学校。
刘秀群说,小时候,我和舒文伟,最喜欢去你们在太平南街的那个家了,至今还记得它的样子呢。
其实,不光她俩,小学的几个男同学,也被我家院子里的一棵桑树吸引着。
那棵桑树,靠近我家厨房,长得十分茂盛,会结许多桑果。桑果由青变红、由红变紫后,吃起来很甜,桑果解馋,桑叶养蚕玩,所以,几个男同学总是去找隔壁院子的小毛,小毛也是我的小学同学,趁我们不注意时,几个男生就在小毛家的院子那边摘桑果或桑叶。
那时,因为娱乐活动不多,我和大院的娟娟、小帆等女孩子,会在我家门外的土路上玩“跳房”,我们用白粉笔在路面画上一个个房间,房间里画上写字台、高低柜、桌椅、沙发等物件,还会在桌上画上收音机。总之,一句话,把七十年代我们知道的贵重物品,都通过手中的粉笔画在“跳房”的房间里。“跳房”时,我们还会用钢笔在各自的手腕上画上手表,显示我们的富有。有时候,高兴了,会在两条胳膊上画满大大小小的手表,有如今天的刺青般扯人眼目了。
这是我们的娱乐活动,带着对物质的追求,而另外的一种娱乐,则是跳舞和练功,则显示出一种对精神富足的向往了,好像我们肩负着一种崇高的使命似的。
比我和娟娟、小帆大几岁的两个女孩,在大院坝组织了一个宣传队,还买了一面红旗,上书“太平南街新村宣传队”,教我们跳《草原英雄小姐妹》《红军不怕远征难》等舞蹈,我同大院坝的一群女孩子一起,每天在那两个女孩子的带领下,在大院坝的那个“小广场”排练跳舞。有一次,两个女孩还把我们带到成都南光机械厂跳给工人们看,我们的宣传队进入工厂,工人们停下手中的活,聚在空地上看我们演出。我们的演出换来工人们的掌声,回家的路上,大家都十分开心。
母亲忙于上班,很少来看我们跳舞,有一次在大院坝排练时,母亲看到我不仅仰面下腰四肢着地,肚皮上还站了娟娟作造型,吓得大叫起来,生怕娟娟伤了我的腰。我却不以为然。
为了跳舞,我们还经常练功,不是在我家门外的土路上翻跟头,就是双手撑地,倒立于墙上。或把一条腿放在墙面,压腿或练下腰。娟娟能单手翻跟头,我怎么练也不如她,内心里很是嫉妒她漂亮的单手翻。
我在大院坝忙于跳舞时,幼铭姐便忙于做饭,如果母亲正好在家,就会走出木门大声叫道:“小兰,吃饭了!”母亲的声音又响亮又清脆,在大院坝总是传得很远。
八大样板戏上映后,母亲带着我和弟妹,还有幼铭姐,拿上小板凳,去成都工学院看坝坝电影。成都工学院当时位于如今十二中学斜对面的不远处,那时它的校外是一片农田。晚上我们去看工学院的坝坝电影时,必须穿过这片农田,电影散了,夜深人静,这段路便变得有些可怕。有母亲带着,倒是放心,母亲不在,走在这条路上,我总是提心吊胆。
除了看电影,八大样板戏的唱段也通过收音机广为流传,至今还记得,我在院子这边唱着《智斗》中阿庆嫂的唱段,隔壁我的小学同学的父亲就接唱起胡传奎和刁德一的唱段。一老一少,两边厢都唱得十分认真和投入。
夏天,宣传队的这些姐妹们,当然还有大院坝的男孩们,喜欢邀约着去川大游泳池或当时的河心村——如今的东湖去游泳。小时候我们称之为的河心村,其实是一个小水库,周围都是农田,而不是今日东湖公园的模样。去河心村游泳,不花一分钱,路上还能摘野果,自然十分开心。而去川大的游泳池游泳,五分钱一次,得办卡。
记忆中,应该是在大院坝的宣传队成立前的两三年的有段时间我们特别紧张,读小学的我看到大人们在大院的入口处垒起了沙袋,备战备荒,为的是防止外人入侵抢劫。为了自卫,大人们还组织了男青年守夜。父亲远在昌都,母亲要上班,家里没守夜的人,大院坝规定出不了人便出钱,母亲便按规矩出一点粮票和钱替代守夜。守夜者们还拿了铜锣做准备,告之大家锣声响起,大院的人都要起来保卫我们的家园。但我的印象中,铜锣一次也没敲响过,沙袋后来也撤除了。
外人的入侵未发生,倒是外乡人来表演了。有一天,三个外乡人带着一群动物来到了大院坝,在我们跳舞的地方即“小广场”演起了杂耍。杂耍的节目有猴子拉车背小狗等,最神奇的是黑白两色的狗熊走钢丝、过独桥。演完之后,一个外乡人手拿一铁皮盒向大家要钱,我把一个二分钱的镍币放到了外乡人的铁皮盒里。在我看来,二分钱不少呢,当时,四分钱可买一个冰棍了。
这是大院坝的热闹时刻,不分男女老少,都聚在了这个“小广场”上,而另一种热闹,是处理邻里纠纷。
曾在朋友圈看到一篇有关我们这个大院坝的回忆,说最惊艳的,是在消闲者想不到时,一扇木门里,突然走出一个让人心魂颤动的女孩,那种美若天仙出水芙蓉般的清纯亮丽,令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怀疑让人惊心动魂的女孩,怎么会生活在这样世俗嘈杂的院子里。
当时看到这篇东西时,我一点也不惊讶,只是笑写作者的少见多怪。现在想来,才感到有些不可思议。是的,从这个大院走出的女孩,大多十分好看,即便穿着朴素,也总是引人注目。如果那时有蓉城今日太古里的街拍,摄影师们一定会拍下她们的楚楚动人。
在这些逐渐长大的女孩中,有一个女孩子有着戴望舒诗里写的“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但她不是丁香,我们叫她黑牡丹。
记忆中,黑牡丹不在我们的宣传队里,她却比宣传队的女孩子们更漂亮,是杜甫《丽人行》中的“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的美,皮肤偏黑,被大家称为黑牡丹。她爱上了大院坝邻居家一个个头偏瘦却十分英俊的小伙子。她的父母不同意他俩相爱往来,她却执意孤行。无奈,父母在大院坝的“小广场”上,请来居委会劝解由此引起的纷争,我和宣传队的女孩子们都好奇地围观这场由爱引起的邻里风波。黑牡丹在这场风波中,成为大家瞩目的中心,无论父母怎么阻拦,她站在围观的人群中,态度坚决地说:“即使离家出走,出门讨饭,我也要跟着他,你们休想拆散我们!”那种决绝的态度,令那时还在上小学对爱情一头雾水的我,十分吃惊。
哦,爱情。
人世间,从古至今,有多少催人泪下的爱情,上演着痴男怨女的悲欢离合,蓉城历史上有名的女诗人薛涛,用“薛涛笺”,与相见恨晚的元稹互诉衷肠,吟唱出了“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欲问相思处,花开花落时”的绝唱。我不知道,那时候黑牡丹是否知晓,离我们大院坝不远处——坐落在九眼桥锦江河边的望江楼里,记录着薛涛与元稹抱憾终身的爱情故事,但我相信,时至今日,像黑牡丹那样对邻家少年一无所求的纯真的爱情,已稀世少见了。
那是一个物质匮乏却感情纯真的年代,那是一个糊里糊涂却激情燃烧的年代,那是一个只能在梦里见到却不能回去的年代……
若干年后的今天,当一切成为往事,当往事的发生地也已烟消云散不复存在时,我知道,除了我,还有从前在大院坝生活过的我的那些伙伴,他们的记忆里,一定会有一个或许不同于我的大院坝的影像,他们的影像,与我用文字记录出来的这些影像,组成了成都这座天府之国的影像片段。众多百姓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生活场景,连接着蓉城这座已经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文明足迹的前世今生,里面有邻里争吵、友谊和爱情,有着平凡百姓平凡人生里的柴米油盐、悲欢离合。
【作者简介】鄢然,本名鄢玉兰,作品发表于《中国作家》《作家》《钟山》《北京文学》《红岩》《四川文学》《青年作家》等刊。著有长篇小说《昨天的太阳是月亮》《角色无界》《残龙笔记》,中短篇小说集《灵魂出窍》,散文随笔集《半是藏雪,半是川土》等。曾获金芙蓉文学奖、巴蜀文艺奖、中国戏剧文学奖·论文一等奖、中国戏剧文学奖·剧本金奖等。现居成都。
——璧山区建立三级院坝会制度推进基层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