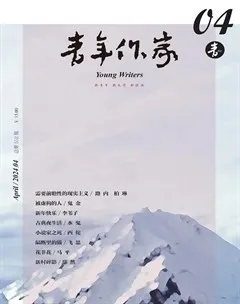戏台上下
一
十几岁时,有个晚上,我在一个同学家借宿,相谈至中夜,忽有哀鸣破空而来,犹如山风吹过巉岩上的古树,曲折、高亢,最后戛然而止于一缕啸叫。屋后是牛棚。我说,你家水牛叫声好长啊。
“是我爸。”同学说。
三个字堵得我半天不敢说话。人在睡梦中发出老牛的声音,是筋骨真的太痛了。
我也曾在田里插秧。日落时分,蚊蚋四起,收拾了扁担和秧架,走上田埂。手脚先是在泥水里泡得泛白,又被太阳晒黑,有的地方还脱了皮。这都不算什么,成天弓着腰在田里,最难的是腰酸腿疼。我个头高,弯腰更加不易。插秧要赶进度,不能老是直起腰来休息。老把式一上午都弓在田里,面朝泥水背朝天。十几岁时腰是柔韧的,上了年纪,种种受过的苦,就会从筋脉之间、骨头缝里溢出来,带来一个不安稳的晚年。
我知道农人的辛苦,不好意思插几行秧就直起腰休息。母亲安慰我说:“蛤蟆无颈伢无腰,老人家的骨头硬翘翘。”大家都是从柔嫩的腰开始,弯下去,弯下去,一辈子在水田里弯折,最后不就硬翘翘了嘛。
走上田埂,我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一阵晚风将我的帽子吹落,掉到人家插好的秧田里。风不认识帽子,使劲吹,田埂弯弯曲曲,等我赶过去时,一个瘦小的老头拿竹竿轻轻挑起草帽,戴到了自己的光脑袋上。我认识他,就住我家屋后,我喊他崇义伯。他放鸭子,手里时时拿着竹竿,用来赶鸭子,竹梢头系着塑料纸,沾了泥污,干净的帽子也污脏了,他也不计较,泥水顺着帽檐滴在他酱色的脖颈上。
“崇义伯,这是我的帽子。风把我的帽子吹到田里,我刚要过来捡,你先捡走了。”
“什么话!这是你的帽子?怎么会戴在我的头上?”
这是我的邻居,伯伯,长辈。我十四岁了,不是一个毛孩子由着他诓。
“我看到你捡起来戴在头上的,起先你没戴帽子。”
“你说是你的帽子,那你喊它一声吧。它答应了,我就还给你。”他叉着腰,站在田埂中间。
他叉腰的时候,竹竿掉在地上。我捡起竹竿就跑,“那你也叫一声竹竿吧,看它答应不答应。”
崇义伯气起来,把帽子往田里一扔。我跑去捡帽子,顺手将竹竿扔到田边的水塘里。
崇义伯只得走下水塘去抓竹竿,嘴里咕咕咕的,应该是在骂我。
正月,村里演戏,《铡美案》。崇义伯演那个有情有义的韩琪。戏里正演到秦香莲携子上京寻夫,陈世美不肯相认,派韩琪半夜追杀,而韩琪不忍心对苦难的母子下手。
“无故杀人天不容,左难右难难住我,把韩琪我夹在两难中……韩琪我心上主意定,一人死要救她三人生……”
韩琪不能空手而回,又不忍心屠杀无辜,最后被迫自刎。能以自己性命去换他人性命,韩琪是大义之人。扮演韩琪的崇义伯虽个头不高,在戏台上也吸引了许多人的眼光。我记得崇义伯的唱腔,浑厚中确有几分刚烈——台上有情有义的韩琪,台下在田埂上拿着竹竿放鸭子,捡了孩子帽子不肯归还的瘦小老头,我不知道要怎么把他们联系在一起。
多年以后,我从《世说新语》里读到孟嘉落帽的故事。九月初九重阳节那天,孟嘉与一群文武官员游览龙山,登高赏菊,山风吹落帽子,孟嘉浑然不觉,依然谈笑风生。有人捡回帽子,写了一张小字条压在帽子上,嘲弄孟嘉有失体面。孟嘉看到字条后,立即写成答词,文采斐然,四座叹服。
帽子被风吹落,留下一段佳话,又编成戏文《龙山宴》。而田埂上的我和崇义伯,斗嘴争抢,全无一点斯文。
戏台搭在稻田边上,看上去很近,其实很远。
二
宝荣叔家门口有一棵梓树。穿过村子的一条灰白的土路就在这棵梓树下面。树冠擎在他家院里,阴影落在我家窗前。
我们两家之间的这条土路很窄。但从洲上到西圩,多半要走这条路。
洲上,是武昌湖与长江之间的滩涂,土质肥沃,围湖造田后,除了水稻、棉花,还出产玉米、红芋。南北丘陵田地少的人家,就搬到洲上去定居。
西圩,是望江北部靠近怀宁的乡镇。乾隆年间,西圩出了个进士叫檀萃,与桐城派大家方苞齐名,名字被写进了国史。檀萃也喜欢戏剧,他力促徽班进京,在云南任上,还邀请故乡的“阳春部”到昆明演出。
我们村太小,没有进士,也没有出过举人。演戏却是人人都会的,小小戏台上,村民也能扮状元。
洲上和西圩,都是了不起的地方,我家处在连接两地的要冲,仿佛也沾染了光彩。这是小时候听大人说话得到的一点虚荣,其实那条路刚刚容两头牛并排。
我小时候坐在门前,看到的最远的地方就是黄家排,黄家排村口有高高的土坎,像山门一样,走过那道山门,不久就到了西圩。
我家门槛是一块淡青色的石条,我光屁股坐在上面,看过往的人:多是肩扛水车的、抬打稻机的、挑犁铧的、牵牛的;空手走的也会背着包袱,那是远路客。我得到最初的人生经验,就是人走在路上就得肩扛手提。
记忆最深刻的是洲上老人去世,往老家抬棺材。黑漆漆的棺材,头尾各以粗麻绳束一大铁环,大木棍穿过铁环,两头打横各拴一根扁担,四个壮劳力抬着。听说抬棺人在路上不能随便歇脚,他们像影子一样,默无一言,行走如飞。
有时候还能看到骑脚踏车的人,闪亮的钢圈,叮叮叮的铃声,使得村庄也响亮起来。雨天,门前的路被牛和人踩出很多脚窝,天晴了,人的脚窝很快被踩平,牛的蹄窝则深得多,让小路留下疤痕,脚踏车骑上去会颠簸。骑车的人却浑不在意,哪条路不是千疮百孔呢。
脚踏车离我太遥远了。我想要一辆手推车。手推车就一个车轮,碗口大,一根木头穿过轮轴,轮轴两边各钉一根长木棍,张开作喇叭形,两根木棍之间钉上木板,或者就用麻绳绑几道,就变成了我的“车厢”,可以坐在上面。那两根长木棍就是车把,小姑可以握着车把,推我在桃树下、无患子树下转圈。
这只是我的想法。很长时间,我都没有一辆这样的车子。
宝荣叔家的苦楝树枝太密,蓝盈盈的苦楝花遮住了厢房的窗户,他锯掉一根大枝,房里就敞亮了。半大不小的树枝不能打家具,他就将树枝截为两段,用了小半天时间,给我做了一辆手推车,“车厢”居然还是一整块旧木板。我躺在“车厢”里,云朵就在桃树叶上面,车把上还有苦楝花香。
我从未跟宝荣叔说过想要手推车,他怎么知道我这埋藏了很久的渴望。
宝荣叔有一天又做了一只小风车,迎着风跑动,花花绿绿的纸片就转起来。
“宝荣叔,你能让它一直转不停吗,不要跑。”
“我想想办法。”
他扛来一架竹梯,斜靠在梓树底下。梓树那时叶子正红。我喜欢一切有颜色的东西,树叶、花瓣、彩色的纸、蜡笔。梓树的果实包在黑色的壳里,用石头砸开,有圆溜溜的籽实。它不能吃,也没有香味,但看上去莹白,摸起来结实,是一种可爱的东西。在树下捡到那些落下的,我收存起来。树上的,我只能看着。宝荣叔现在爬到了树上。
“宝荣叔,你帮我摘一些树籽吧。”
他摇动树枝,掉下了很多梓树的白籽。我捡了又捡。
“莫捡了。快看树上。”
宝荣叔将那只小风车钉在树上,西圩的稻尖上吹来的风让它疯狂地转起来。我仰头看去,天蓝得有点刺眼,梓树叶真红啊,风车在树上转得太快了,还发出呼呼的声音。
“不用跑了,只要有风,它日日夜夜都会转。”宝荣叔说。
村里排演《铡美案》,宝荣叔是当仁不让的陈世美。他扮相俊美,没读过书,却天生一段风流气象。
而演秦香莲的是桃花婶。不是宝荣叔新结亲的美兰婶。
我们两家之间这条“官道”折向北是一片桃园。有一年春天,绵绵春雨后,桃园湿漉漉的空地上倒了一堆玻璃镜碎片。
玻璃镜在那时是奢侈品。只有结婚陪嫁才有。
我想起头天晚上,听见宝荣叔和美兰婶吵架。吵得很厉害。
三
正月,有小漳湖的远房亲戚来访。是儿女婚事遇到了一点麻烦,央我父亲代写一份诉状。父亲不置可否,殷勤劝以酒菜。我那时刚学写文章,看过俄国作家蒲宁的小说《乡村》,还有叶赛宁的乡村抒情诗,就把亲戚带来的诉状草稿拿起来认真看。
亲戚是男方,好容易说了一房媳妇,找了媒人,送了聘礼,双方照过面彼此满意,一切都按照乡村的节奏推进着。突然有一天,女方反悔了,要终止这门婚事。
男方的文字在陈述这段时语焉不详,指称混乱,“生要做你家人,死要做你家鬼”,谁要做谁家的鬼?
我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才摸清头绪。男方对女方很满意,女孩漂亮、热情、大方,是个裁缝;男孩个头不高,老实,学木匠刚出师,是个未来的手艺人。在乡下,这样的搭配不坏,两个人都不用在日头里讨生活,有希望过上殷实日子,皮肤不会晒得太黑,手脚不会被泥水泡得太粗糙。
据说女方反悔,是因为看上了一个泥瓦匠。泥瓦匠并不比木匠地位高,爬高上低,风吹日晒,还有风险。但这个泥瓦匠有点不同。他坐轮船去过上海。他有个亲戚在杨浦一家工厂里做领导。那里盖房子给的工钱远远高过乡下。
女方说钱财如粪土,反悔是因为这门婚事是媒人强为说合的,她还年轻,不想现在谈婚论嫁。
男方说这是借口,她就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她当初还对男孩说过“我生做你家人,死要做你家鬼”呢。
亲戚说,她还嫌我家孩子分不清布料,我们明明送了两块的确良布给她做褂子,两块腈纶做裤子,这个姑娘就是嫌弃咱,还说什么“粘胶、腈纶都分不清,我有的是涤纶、涤卡、维纶、丙纶、氨纶,还想糊弄我呢”——那都是人家的布料,你只是一个裁缝,分得清时兴的布料有什么了不起?你分得清木料吗?分得清泡桐、杉树和榆树板子吗?
我刚学过有机化学,对化学纤维也略知一二。那时大家穿的衣料主要是棉花纤维,吸汗,但易皱;讲究人家穿化纤衣服,挺括,但时尚。化学老师说,发达国家以棉布为时尚,我们在讲台下都瞪大了眼睛,他们傻啊。当时的乡下少年觉得化学纤维散发的文明气息远超村里的棉花。而赞美棉花、怀念村庄的散文,要到二十年后才出现。
我从蒲宁《米嘉的爱情》里得到一些有关男女恋情的认识,卡佳的移情别恋让米嘉痛不欲生,无论怎样转移都难以从这段悲伤的情感里解脱。这种浪漫的书写让我觉得自己应该、也能够帮帮这个陷在痛苦里的男孩。
于是,我用散文的笔法讲述这个故事,愤而向法律部门寻求支持。但写着写着,我发现这个情感悲剧与法律无关,最多帮男孩要回部分礼金。
礼金对于一个被抛弃的、伤心的男孩有意义吗?亲戚说,当然有意义,我们就是打算要回这笔钱,好给你表叔重说一门亲事。原来那个伤心欲绝的男孩还是我的表叔,我觉出了一些渺茫的责任,只是想到投入地讲述这样一个悲伤的故事,最终却是为了要回聘礼,又有些兴味索然。
女孩新喜欢上的男孩在上海做泥瓦匠,盖高楼。我那时从江边坐小火轮到贵池上学,见过很多开往上海的大轮,别说这个女孩,我也对遥远的上海怀着无限的憧憬。
我根据原稿和当事人的陈述,认真、清晰地记录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和男方的诉求。这是我的文字与现实生活第一次发生联系。我有一点点自豪。
这时父亲端上一盘汤圆,请客人吃。客人一再谦让说吃饱了,吃饱了。父亲也就不多客气,将白瓷盘轻轻搁在桌上,又拿烟给客人抽,香烟盒在烛台边上,正月里烛台都是点亮的,刚刚我在烛火下写诉状自我感动的氛围,也要算烛光一份。
好巧不巧,父亲拿香烟时,烛台突然倒下来,眼看就要栽进盛满汤圆的瓷盘,客人手疾眼快,伸手撩开,烛火稳稳落在刚写好的状纸上,眨眼功夫,那张薄薄的白纸化成了灰烬。
父亲说,不碍事,回头让我儿子重写。添酒回灯重开宴,父亲示意我回自己房里看书去。
我有点沮丧,也不好多说什么。
那天客人喝了很多,趴在桌上睡着了,早就忘记为何事而来。
送走客人,父亲以极少见的严肃口吻对我说:“一生一世,都不要写这种文字。”
我觉得有点奇怪,“这有什么,只是记录一下他说的事实。”
“你怎么知道他说的就是事实?”
“难不成他还来骗我们?”
“不是他存心骗我们,是他也未必讲得清事实。”父亲喝了一口酒,又补充道,“有囿于认知的无心之失,有利益纷争中的夸大其词,还有为泄私愤罗织罪名陷害对方的,也不少见。总之,这些文字,你不要碰。”
父亲趁着酒劲,跟我说了一大通话,大意是:个人抒发情志的文字,写写无妨;涉及他人利益或者名誉的,慎之又慎;至于讼师文案,坚决不要去碰。
“这么严重吗?”
父亲见过乡人家谱里记载的谆谆告诫,拿来警示我:“……奈何挟三寸之管,摇三寸之舌,当把持衙门之名,为士林所不齿,当途所贱恶,且丧心败德,近则身受其祸,远而子孙遭殃可畏哉,戒之。”
对我来说,这些告诫虽严正,也还是教条。但不久发生的另一件事,却彻底扭转了我的看法。
正月里,我也去小漳湖一带走亲戚,看同学,同学带我到他们的村子看戏,《小辞店》。这也是黄梅戏的经典曲目,戏里男女主角各自婚姻不幸,突破伦理相恋。三年后,男主角的忠孝节义战胜了儿女私情,毅然离开女主。女主柳凤英凄苦唱道:
我问客人妻房可有,扯谎的鬼耶,你说道无有妻子,在江湖上漂流。我看客为人忠厚,瞒公婆和丈夫私配鸾俦,实指望我们配夫妻天长地久,哥喂,未想到狠心人要将我抛丢。你好比那顺风的船扯篷就走,我比那波浪中无舵之舟;你好比春三月发青的杨柳,我比那路旁的草,我哪有日子出头;你好比那屋檐的水不得长久,天未晴路未干水就断流。哥去后奴好比风筝失手,哥去后妹妹好比雁落在孤洲;哥去后奴好比霜打杨柳,哥去后妹妹好比望月犀牛……
我被这唱词深深感动。是谁演得唱得这样好?我有点好奇,辗转打听,演柳凤英的竟是状纸里那个未过门就变心的“表婶”。
我在稻田里插秧,见过村民最深刻的辛苦,听过他们如牛的长号。我在村里的戏台下伫立,看他们在短暂的一场戏里扮演他人的人生。戏里的欣悦苦痛,忠烈侠义,跟乡野真实而粗粝的生活,很难说有什么关系。只是多年以后,我从稻田走到通衢,复杂的、多面的人和事,也还能从这里追溯出一点依稀的影子。
村里很久不唱戏了,崇义伯早已去世,宝荣叔垂垂老矣,那个差一点成了我表婶的女孩,我不知道她去了哪里。故乡现在以服装大县闻名全国,她是裁缝,以她的心性,应该早就过上了幸福生活。
【作者简介】冯渊,上海市语文特级教师,作品散见《上海文学》《解放军文艺》《散文·海外版》《长城》《安徽文学》等,出版有专著《仰望星空从仰望伟人开始》《冯渊上课》等十种;现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