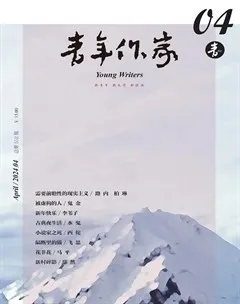晚钟
我写作只是想去努力接近一些事情的真相。
——保罗·乔尔达诺
一
蝉声开始高高低低地在树叶间起伏不停,我的心口也有一只蝉,吵得心跟着大陡坡似的起伏。
手机显示在7点50分,医院门口人流涨潮,我拉着家婆的手站在住院部的电梯口,她手心皮肤的褶皱里传来微凉,颤抖。身高不及我肩头的家婆,眼睛略带浑浊,无神、茫然地张望,好像不知怎的就来到了这里。
几天前,深夜临睡。突然听到家公大呼我先生的名字。
我从卧室冲出来,看到站在厕所里的家婆,她的脸上有难色,示意先生出去,让我进来。然后她将内裤拉下,浓黑的血从身下快速地滴下,地面一下子出现了一摊,浑浊的铁锈味扑面而来。
这是不祥的兆头,我朝先生喊了一声:“赶紧上医院。”
家里突然忙乱,开启了面目全非的生活。
我留在家中清理现场。眼前的浊血,来自已经绝经二十多年的身体,像利爪般扑来,气味怎么冲洗都挥不散,我打开窗户,外面无风,吹不进来。刚好前一天我来例假,女性的血色相涌而来,似乎连结在一起,但又不一样。我的经血,鲜红,充沛,表示身体正以潮汐般的规律正常运行。每缕鲜红,都是从一个女孩的成长一路流淌过来,是成长与身份的认证物,一次次参与少女、女人、母亲的确认,纠缠着女性的半生,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红亮旗帜。
现在,对于家婆来说,血色暗黑,带着破坏性、毁灭性的色彩。我只是一时不知这毁灭的火焰有多热烈,只知道她的生命,已设限。
她看着电梯数字跳动,也跟着念叨。另一只手半掩着嘴,压下声音问我:“我们要去哪?”
要去哪?我也有一刻的恍惚,几天来,从区级医院被拒收,到市级医院检查,拿到报告再找肿瘤医院,问诊过程波折不断。她的生命被魔手卡住,我恍惚地跟着种种确认行走。
我定一下神,按了6楼的电梯,找到了预约的医生,他是先生的学生推荐的。家婆的情况略为特殊:耳聋、驼背、有鼻咽癌史。医生没有进一步检查,坐下来对我说宫颈癌放疗的后期治疗难以忍受,以及家婆的情况,不建议放疗。我心头一凉,问有没有其他办法,他摆了摆手,我多问了一句:“不放疗,存活时间大概多久?”
他顿了顿,说:“2-3个月。”
原是抱着一丝希望而来,可是穿行的医务人员,我不知道有没有谁能延长她的生命线?我的手也是冰凉,牵着一个老人来到命运的审判台。
幸好,她耳背,听不到自己的限期。
我扶着家婆到等候区的椅子上,她早上空腹而来,已经饿得无精打采。小姑从保温壶中倒出白粥,她接过手,低着头,孩子般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她的神情,专注而认真。我看着对命运无所知的家婆,心里默数着她还有多少日子能吃得这么香。
小姑一下子崩溃了,眼泪跟着来。
为了存活的希望,我们又找了不少人。辗转到了中午,才有一名医生愿意收治家婆。他专注地倾听一个耳背的老人断断续续的叙述,然后根据病情快速做出了判断,安排放疗。
中午12:55分,家婆终于占有一张病床,在这间浅蓝色的病房中安顿下来。家婆躺在白色的床单上,嘴唇苍白,顶着乱成蓬松鸟巢的银发,疲惫不堪。
我看着入睡的她,仿佛在广袤的海面上,看着一艘白色的船只即将被蓝色的大海吞没,我们是海面上的救援者,尽力地营救。尽管只是让船只淹没的速度慢一点而已。
那天午后,坐在病房门口,看着门外往来的人,我才意识到这里仿佛是另一个时空。在这狭小的空间中,所有人都被快速地简单分类,这个时空之外的任何身份、职业,在这里都被滤去,仿佛一层层的外衣被剥落,只剩下医者、患者、陪护人(或者称为暂时健康者)的区分,人与人的关系在这个空间中重新排序。这几种身份也不是固定的,它在未来的某一刻,可能重新洗牌,这种新的排序让我心头一惊。
作为家属,当主治医生进入病房时,我们眼中的他身上仿佛自带发光体,迷茫、无助、苦恼的我们,一下子眼睛骤亮。
医生,成了我们唯一的稻草,但我害怕太深的期望和责任会把这根稻草压弯。
二
穿过花圃,桃红色的太阳花仰着头,与阳光交遇。头上的杧果树开始结果,从拇指大到鸡蛋般垂挂,一两颗还掠过我的头顶,自然的欢欣让我心头一亮。
我领着家婆到2号楼的地下放疗室门口,走下步梯,微凉的气息和外面截然不同,低温空调倏地让我打了一个寒颤。灯光亮得发白,白墙、白大褂,安静得没有气息。
等候区蓝色的椅子上,坐着几个不大作声的病人,在这里等候治疗的,多是生命有所失色的人,仿佛不久的将来,也会融入这一片安静的白色中。
放疗室里医生呼叫家婆的名字,换鞋的时候,她有点迟疑,我催促一下,牵着她走入通道,在通道边上的格子中,取下医生给她定制的白色模子,模子方便她治疗的时候固定位置。
放疗室里的温度很低,射线照进她的身体。她的腹部左侧,有一条红线描出了三角区,猩红。像极了一种刑罚,给她的身体画上烙印。
在疾病面前,人们只能快速地卸下在公众场合裸露身体的羞耻感。
医生示意我出去,身后的放疗室大门关上的时候,我不禁想起我的奶奶。
几个月前,90多岁的奶奶摔了一跤,髋骨折了。我去看望她,推开房门,刚好看到大伯母给奶奶擦洗身体。奶奶第一反应是拿过裤子盖在羞部,动作神速,她的脸上闪过一些不易觉察的微红。
那一刻,“羞耻”在奶奶身上还没有褪去,在我们孙辈面前,它仍是性别和辈分之间的暗示,即使活到性别可以模糊的年龄,在不涉及生命危机的节眼,羞耻感却近乎本能。
家婆一直是一个安静、少思的人,在这一次疾病面前,她在丈夫、子女看不见的背后,在暗夜里如何独自面对生命狙击手的子弹,我无从知道。只知道在我们面前,她无数次喃喃:
“这是没办法的事。”
我不知她是在安慰自己,还是在安慰家人,但暗夜里生长出的勇气,在面对生命的限期时胜过了羞耻感,却是我所料未及的。
如果说羞耻感是作为人的一种社会性,那么,在生命的自然性面前,它很快被“活命”的自然性后置。半个月之间,家婆的羞耻感,臣服于疾病之下,变得坦荡、自然。
我不由得想起多年前的夏天,躺在手术台上接受剖腹手术。麻醉之后,男麻醉师在监测心率。我的胸部敞开,因怀孕而胀大的乳房堆在胸前,男麻醉师在胸部轻压,安下监测器,有那么一刻,我想伸手去护住前胸,但动弹不得、无能为力。昏迷之前,我能感受到脸上的红潮没有被眩晕淹没,但那一刻,人类繁衍的责任远高于个体的羞耻感。
或许,在医院,不仅医务人员要去掉雌雄之别,病人也一样。唯有这样,人才回到生命本身。
三
家婆从身体到意识都开始远离我们,她开始跟我们划分疆界,无意识地站队到疾病的王国。
我回家的时候,家婆神秘兮兮地拉着我去看餐厅的一张椅子,说:“我只坐在这张椅子上。”仿佛在向我表明她的身份与决心。
那是家里最老的椅子,曾经在她眼中最不中用。而那张几年来一直是她使用的大红塑料餐椅,现在却被她移到角落里。我知道她在忌讳什么。
然后,她又拉着我的衣角到客厅,那张酸枝木单椅上,垫着她的一件棉衣,她拿起棉衣,翻来覆去给我看,“这是新衣服,我垫在椅子上,这样不会给家里带来晦气。”
我的心猛然下坠,看着她对身边日常用具的认领和区分。这不止是眼前的老人独有的行为,在偏远的农村,很多得了绝症的病人会自觉不祥,主动放弃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权利,给自己筑起墙堡。
我跟她说:“你还是坐原来的椅子,没事的,没什么需要改变。”可是,那张红椅子她再也没有坐过一次,客厅里,她都没再坐过其他位子。我难受地看着她在生命的边境彷徨,身体不断被挫伤,她的内心,在疾病面前也一点点地失去人的权利。
我想起苏桑·桑塔格所写的《疾病的隐喻》,她谈到疾病的隐喻具有时代性、社会性,作为一个癌症患者,她揭示道德评判使患者蒙受羞辱。但人对自身疾病带来的自我道德贬低的隐喻,在她的文字里几乎没有被提及,可能她自己早已剔除了这一点。可是我的家婆,她仍活在疾病带来的自我贬低中,关于疾病的隐喻一直还在。
这只是被摧毁的一部分。
我不知道是因为放疗的摧毁,还是因为一个人面对生命的无能为力,20次放疗疗程一结束,阿尔茨海默病迅速地将家婆卷入旋涡,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四五年前,这种病症开始造访她,但前几年间,它还拥有一个客人的礼貌,保持着远房亲戚的节奏,礼节性地拜访一下,然后快速地离开。带来的结果是家婆的记忆力缓慢地下坡:几年之间,她渐渐记不起子女的生日、生肖,去年她还摆弄过一只电饭锅,却怎么也想不出如何按键,幸好这些问题对于正常生活的影响不大。
但从医院回家,她开始认不出外甥女,记忆力垂直式下坠。
那天,外甥女进屋,她叫了一声“雁引”,雁引,是我的女儿。渐渐地,我们发现只要是身高与雁引相仿的孙侄辈,都是雁引。有时,几个小辈在家里,她望着她们,用手指认,可是她惊讶于有好几个雁引出现,茫然地不知道哪里出了错。后来,家婆最疼爱的小姑也被错认为雁引。
有一天在家里吃过晚饭,闲聊时,孩子们中的一个说:“奶奶最后一次记得我的时候,准确叫出我的名字。”另一个说:“奶奶也记得我是谁。”
大家哗地一声笑起来,我别过脸,回过神来时,看见孩子们的脸上有淡淡的泪痕。
疾病也瓦解了家婆原有的生活方式,她以病人的身份重新建立自己的作息。她的睡眠被阿尔茨海默病收割,每晚在上床与下床之间反复折腾——她睡不着,于是不断地敲我们的房门,要跟我重复确认某件事;上幼儿园的小女儿也因此兴奋不已,夜里也不肯睡,奶奶的敲门声成了她的游戏;半夜,家婆常轻拍家公的脸,直到家公醒来,惹来家公的不耐烦的呵责,可是,当家公半睡之间,又反复如此。先生不得已每晚陪她到半夜,在深夜的动静中,到处是她的身影,一家人的睡眠也被一并收割。
干扰一直存在,白天也无法逃脱。
以前,只要先生午睡,她在家中一定会轻声细语,甚至不让小辈打扰到他。现在,只要先生睡下,当孩子般缺少依赖的感觉开始袭击她,家婆就会一直在门口或床边唤醒他。家婆返回了自己的孩童时代。
回娘家时,我跟父亲谈及家婆的情况,他用老辈的说法向我解释:“我们潮汕有个词叫‘食老返童,就是说你家婆现在年老了,返回一个儿童的状态,你要去照顾她,经历上一辈自小养育你们时的难处。唯有这样,人才活得明白。”
后来,家婆确实像极了一个刚刚认识世界的孩子,当她偶有神志清醒的瞬间,认出了身边的某个人,大家便欢呼,这种辨认跟十来个月的婴儿开口叫人极其相似,她表现出来的一丁点常态都成了可贵的喜悦。
后来,我们之间已经无法对话,她常常喃喃不知所语,她面向更复杂、混乱的内心,我们不在同一平面上。
这个过程,我相信是生命的磨炼,既是她的,先生的,也是我的。不,是每一个人的。在时间河流中,只有见识了这些礁石,才能理解生活回荡着各种汹涌、奔突,才能修正我们对生活的认知。
身体的疾病不断抽干家婆的肌肉,神经上的阿尔茨海默病不断打击她的精神。我看着身神俱摧的家婆,看她犹如在黑暗的隧道摸索,触摸生命尽头的面目和玄机。
四
洗澡,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一个人生命羸弱之余的一种尊严,家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爱干净。
阿尔茨海默病使她变得简单,以前最关心的收衣服、扫地、家公换洗衣物等日常生活,现在都与她无关。她的世界缩小,个人化凸显得明显,只关心自己的生活,她的生活又简化成三件事:洗澡、吃饭、睡觉。
从确定病症之后,家姑俩和我帮她洗澡,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我们决定中午给她洗澡。时间在她那里变得模糊又清晰,每天早上,从见到我的第一眼,她就开始要求洗澡,仿佛这是开启一天的信号。有一天早上,道路挖水管导致水管破裂,正在抢修。早餐时,家婆开始纠缠洗澡。我解释水管在抢修,停水,要稍等。可是我发觉所有的语言对她而言是失效的。
她走过来拉着我的手到浴室,倾着前身,近乎哀求地说:“求求你,给我洗洗澡。”那种无助透出一种自我嫌弃。我心头一酸,跟先生说你带妈去屋后看看工人修水管吧,他扶着家婆下楼,可是对于一个阿尔茨海默症的病人来说,遗忘比记住容易得多,她只能简单地记住她的洗澡,其他不在她的考虑之内,当她上楼的时候,她再次发出哀求。
在家婆患病之前,我跟她谈不上亲密,只是日常间简单的交流。只有洗澡,成了我与家婆之间最隐秘的交集。
帮家婆洗澡,是最能直面一个躯体颓败直至接近终结的方式。起初,她能快速地除去衣服,她的皮肤白皙,七十来岁的身体不见斑点,驼背又将她后背的肌肤拉伸,看起来竟光滑得不似一个老年人的皮肤。但几天一小变、半月一大变,五个月后,她的身体已被不可见的气息吞噬,双腿变得伶仃起来。仿佛两条将枯的树枝支起一个耷拉的麻袋。只有驼的背才能支起她身体的厚度,她的乳房,像极了我早上在猪肉店里看到挂着的两个生猪肚,垂搭在她的腰间。
后来,她不再麻利,任你摆弄。她的肚皮缩成各种褶皱,每次清洗时,要一层一层的翻出缝隙里的污垢,因为瘦瘪,骨盆又显得特别突出,她的身体,越来越明显地现出一副骨骼的样貌。我面对这样的家婆,心里升起对身体的未来的唏嘘感。她的身后,镜子毫无保留地映照出她的身影,我挡了一下,怕她一转身,连她自己也认不出来自己。
这样的外相,是由什么内在隐秘的痛点主导而成的?在身体的内部,肉眼看不到的深处,与败坏有关的一切正在发生变化。眼见的常常只是表象。更多,未必看得到。在皮肉包裹之中,器官的败坏带来了一种类似鱼露的气味。
诗人里尔克在手记中谈过很多涉及死亡的话题,我想起其中的一则:“我们每个人的死都一直裹藏在我们自己的身体里,就像是一只水果里面裹藏着她的果核一样。”
五
那几天,家婆已经很难进食,她坐在餐厅,呆呆地,似乎与世事一点点抽离,脖子上围着幼儿围袋,每次喂她,汤汁总是从嘴角垂流下来,先生说一句:“吞下去。”她才稍有反应,茫然地咽下一点。一餐下来,其实并没有吞下多少。
先生看着家婆,眉头上的“川”字山峰迭起,语调也跟着提高,变成呵斥。他的内心充满无奈,矛盾,从前惟命是从的他开始会冒犯母亲:
“妈,吞下去!”
“跟你说吞下去!”
我在旁边看着他们,当年他带两个女儿时的耐心,似乎已经磨尽,这是我在过去十多年不曾见到的场景。
夜里,无眠。
先生突然倏地坐起身,狮子般发疯地用双手不停抓着头。
我吓了一跳,随即也坐直起来。
他的烦躁贴着头皮,快速地搓擦,一层一层的声音让我不安。
十多年来,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失控。
我拉下他的双手,问他:“你到底怎么啦?”
侧身开了灯,他抬起头,眼里的血丝与酒后的双眼一样,无力、彷徨地望着我,又夹杂着愤怒。
我让他靠在床背上,给他一个倾诉的姿势。
白天里温和的先生,此刻呈给我异样的形象。他开始断续地说:
“你知道吗?我感到绝望。我希望妈剩下的时间能过得舒坦一些,可是……”
“从前带女儿的时候,即使孩子淘气哭闹,心中会有希望,她们长大了就听话,是渐渐可以对话,明事理的将来。可妈,是没有希望的将来,是越来越糟糕的将来……”
他突然说不下去,看着我,生命中的无能为力明晃晃地呈现在面前,他无法回避。
我一直在想是什么导致了他的变化,一方面因为这种折磨还在后头,不知什么时候结束;另一方面,在困倦之时,还要战战兢兢地害怕来自母亲的折磨,而他想要许给母亲的舒坦也无法做到。
母亲,是一个人生命的根部,一个走向消逝的母亲,让子女仿佛植物根部离地。而不久的将来,他将生若浮萍。
他矛盾地活在中年,我在他这一刻的脆弱中,看到无数中年人的影子。
下了床,走到隔壁家婆的房间里,他熟练地撕下夜用卫生巾的胶纸,拿起家婆的内裤,垫在中间。我俩扶起家婆,慢慢地给她换上裤子。
抵达不惑的,不仅是先生,还有我。
我和闺蜜坐在庭院的芭蕉树下,初冬的阳光从树间流转,微风摇动,在墙上形成黑白般摇曳的光影,似梦似幻的跃动,与我半年来的生活相似,有些东西似影似真,灰扑扑地围着我的生活。
闺蜜点了我最喜欢吃的香芒鸡、冬阴功汤。这是半年来唯一的一次放松的聚会。她知道这半年是我事业与家庭最艰难时刻,它们密集地挤在一起,构成我整个夏秋的生活。
我们聊起近况,中年的她,也曾经历家人卧床多年的生活,她理解我的状态。
我说:“麻烦肯定不少,也烦心过。但有一天,在洗碗的时候,我看着手中的水流,那种一种日复一日的流逝突然打动了我。每个人都是流水的一瞬,照料家婆,会慢慢地意识到责任是其中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我从她身上看到作为人的共同命运,肉体衰老,精力耗尽,神经衰弱,没有一个人能逃脱。”
我看着芭蕉树下阴影的部分,日光虚薄,我其实还想说:“是必然的死,让人忍受其他时间未必能忍受的事物。”
我听见树间的蝉声,越来越明显。
我问闺蜜:“怎么现在还有蝉声?”
她错愕地看着我,说:“哪里有什么蝉声?”
哦,这种持续的嗡鸣声近期常常造访,有时白天,有时夜里,我开始觉得我的耳里住了一只蝉。直到现在,这只蝉仍然日夜不消停,我尝试过很多种医治方法,皆不奏效。
不惑之年,身体开始往下走,只有变坏的可能,没有更好。未来,只有更糟糕的在远方等着我们的身体。病弱之际的家婆,给我们提前预习了生命羸弱的N种可能中的一种。
我想起芒原在一首诗中说“身体里的晚钟一遍一遍地响起”。
六
出殡之后,我整理家婆的遗物。
阳台上,家婆离世那天晒着的衣服,还在风中飘着。我去阳台收拾,衣物上,还有她浓重的气味,物比人久,时间有那么一刻恍惚不定。
料理完家婆的后事,做完一场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法事,一生一世,来来去去,浓缩在一天之中。
亭台楼阁在火焰中纷飞,我跪在熊熊的烈火面前,热烈的火舌,吞噬的何止是这些。生命如纸,那样的轻飘、付于一炬,不足半个小时,她生命中存在的一切,都烟消云散。痛哭中,不止是一个人生命消逝的痛,更是生命被一层一层扒落,露出无遮拦的白骨般的真相。
祭拜的时候,先生握着我的手,死亡的手杖将我们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失去与存在,让中年的我们更加踏实地踩在大地上。
我是在家婆去世之后才看到电影《困在时间里的父亲》,由美国导演弗洛莱恩·泽勒执导,安东尼·霍普金斯和奥利维亚·科尔曼主演。在一个简单的故事中,讲述身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安东尼如何对身边的一切充满怀疑,以及作为家属的女儿无助的一面。
电影里的安东尼总是在找他的手表,执着于时间的安东尼,让时间分裂成几个世界。同样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家婆,也是一样的,我渐渐理解了她对洗澡的执念、对浴巾的寻找,与安东尼对手表的寻找如出一辙。病症让他们变得简单而固执,生活变成多个时间层面,但又减成越来越小的世界。那时家婆常常显露出茫然的表情,看着我,在脑海里搜索我的名字,然后又断片,分不清是在梦中还是在真实生活。
我看着她,仿佛洞见了一个人晚年生活的真实。有时会想,当一个人不再认识你的时候,她与你越来越没有感情纠葛,你会发现,两人之间的情感像一张纸上的痕迹一样越来越淡,可是,内心深处似乎有一根针,像针灸一样对着心脏提拉转动。
细想一下,《困在时间里的父亲》只是描述一种状态,而作为女儿的安妮,在棘手问题面前,矛盾、挣扎、无助,她其实也找不到方法。不应将阿尔茨海默病看作简单的身体疾病,我留意了一下,身边越来越多的老人,被这种病症束缚。或许,我们更应该将它看成现代生活必然要面对的社会的病症,而在找寻应对它的解法的路上,我们还是孩童。
美国医生阿图·葛文德写的《最好的告别》是我近期的读本,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关于衰老与死亡,你必须知道的常识”。作为由专业人士书写的有关晚年生活与如何面对死亡的告别的书籍,在这个时间点上,刚好适合我。
关于晚年、衰老、死亡,我在家婆病逝的历程中触及这些时,常感到措手不及,我发现没有书本经验和生活经验去应对。在葛文德医生的叙述中,这不是个人、或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整个人类的问题。是什么让我们在应对这个难题时缺少力量和经验?
古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在二十世纪初,如何面对衰老与死亡的这个问题少有人关注。现在一百年过去了,人类的平均寿命也达到70岁左右,这个难题依然少有人问津,葛文德也谈到“关于衰老、衰弱和濒死,我仍旧一无所知,教科书也几乎只字不提。这个过程如何演变,人们如何体验生命的终点,对周围人有什么影响——这些问题都无关宏旨。”葛文德由医者身份出发,又经历他父亲患病到离世的最后岁月,医者仁心、推己及人,写下一个现代医者的思考。
当家婆达到生命的临界点时,我们商量着要将她送去医院还是在家中接受死神的到来?每一种都有合适的理由。这个时候,我们是无法咨询家婆的意见的,她的世界偶有的清醒无法清晰地表达意愿。后来我们揣摩她的想法,家姑说:“家是她的一切,还是让妈在家中走吧。”读了《最好的告别》后,我庆幸当时我们做了正确的决定,没有将家婆送去医院。在最后一刻,我们常常忽略濒死者的需求,“她希望怎样?”这样的思考是缺乏的,反而考虑更多所谓的合理性。
只有在经历了这一仗之后,我才能体会另一个亲戚的最后时光,她生命的最后阶段在医院度过,听说那时一直嚷着回家,坐在病房外的楼梯口哭闹。但因为她的体弱,她的个人意志被消解为零,那时她的子女谈及,都说母亲疯了。她最后是在身体插满各种塑料管的情况下,离开人世。对于她的子女来说,已经尽孝。
家婆患病十一个月后,在家中离开人世。与死神相遇的几个钟头中,平静交锋,大口喘息之后,归于无声。
这一年的夏天,雁引跟我提过暑假想去朋友的中药店帮忙。我回过神,打量女儿,这个处于青春期的女孩,比我更早亲历生死,她的脸上有超过同龄人的成熟。“看着奶奶一路走到尽头,让我会更加关注身体的健康,如果有机会对身体多一点了解,那也是收获。”
在此之前,雁引也跟我一样,对身体的存在混沌无知,只是将它当成一件穿了很久,不需要每天换下的固定外衣。经历了家婆的病逝,我们对身体的各种变化敏感起来。
暑假的第一天晚上,我带着个头已经比我高的女儿,到朋友的中药店,开启了她的学徒生活。
【作者简介】余冰如,广东汕头人,生于1980年,作品散见《散文》《四川文学》《广州文艺》等刊,现居汕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