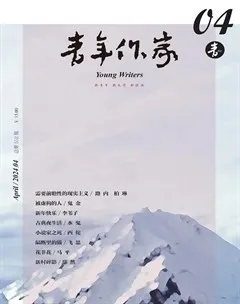古典夜生活
说书
要听俺细说他的来去,只是不知从何讲起,当真如百尺长的麻绳绞成一团,要解出个由头,顺出脉络,着实不容易。又都是些古久的事,难免时间错杂,张冠李戴了。
独独有一件事俺忘记不了。有一年,那时俺还是个小子,在面馆做帮工,拉风箱时常常发痴,想天子扮成平头百姓,落难与俺结识,称兄道弟,回京后赏俺一个芝麻官做做。
说偏了。有日一位说官话的人来到面馆,样子黑瘦,那就是日后大伙嘴里的大盗胡平亮了。真是人不可貌相,古话还是有几分道理的,我就是吃了这亏,不然当时就该大方请他一碗面条,施他一个人情,要晓得这类人是最讲恩情的,何至于我现在还在你们村吃这苦丁茶。茶不多了,再烧壶滚水,撮几指茶叶就够了。
若他只是在馆子里吃一碗面就走人,俺又怎能记得呢,那南来北往的食客成千上万,何以就记住了他呢?
什么?他在馆子里大开杀戒?胡说八道,那我现在还有性命在这跟你们讲古?
什么?我是鬼?小孩子净喜欢瞎想。闲话不表,言归正传。话说胡平亮那时到俺做帮工的面馆吃面,一碗接一碗,足足吃了有十二碗,手指都要数个来回。
不信?人家可是大盗胡平亮,岂是一般人饭量,不怪不怪。兴许他这本事能耐,连着可以十二天不吃不喝,吃一顿就能顶十二天。这样算起,俺说请他吃碗面,看样子是不成,十二碗,这哪请得起。
吃到第五碗时,厨子和俺都跑出来看,眼见他吃完了,又吩咐下一碗,俺就和厨子跑进去,忙手忙脚做完端出来摆在桌上,就又看他吃。胡平亮的面貌俺就此记住了。
如此过了些天,令胡平亮名声大震的那件事,想必你们也耳闻过,只是话传话,就像一口锅里煮的菜,任谁都来添加佐料,那还能不失味?俺是听一个打更的老头说,他说当时正是五鼓之后,打完收工时,街上有一些曙色,卖菜的已经支起摊子。
缉捕胡平亮的好手沿路访问,一直追到那儿,十来个人手持钢剑,围成一个圈儿,将他困在里面。大家齐喝一声,团成一块,又纷纷散开,又发一声喊,往里面刺去,忽而就倒了一半好手。剩下的再不敢近身,胡平亮退,他们就近,胡平亮近,他们就退,胡平亮哈哈大笑,捡起地上两个人,左手揪住一个人的腿,右手捏住一个人的胳膊,狂风卷地一样,打几个转,突然手一松,左手中的人撞向另两个人,顿时毙命。右手一松,又撞倒了俩人。
剩下的三个人远远躲开,胡平亮放出狠话,说:
“我准你们当中一个人活着回去传话,我要在此地住上一年半载,你们多派些人手来,让我舒展舒展筋骨。你们三个,是自己决出生死,还是由我出手挑选呢?”
这三人也是烈性子,二话不说举剑杀去,胡平亮几乎轻松几招就击败了他们。
留了谁的性命回去报信?那俺哪晓得,俺既不在场,又不会舞弄刀棒认识些捕手,谁能活命,都是老天爷可怜下来的。
你嫌弃俺尽扯胡平亮而不谈他?要讲他自然要从胡平亮讲起。话说大盗胡平亮杀了十来个差人,就踞在俺们城里不走,偶尔还出来逛街吃喝,富户人家吓得把银子都撅地埋了,有些避到邻县躲风。
那胡平亮这般高调,自然是要引他出来。他是谁,为何也到了俺们县城,这当中的恩怨,属实乱成团。
让俺理理,不错,胡平亮死后,有几个收尸的差人到俺做帮工的面馆吃面,是厨子告诉俺的,这话不假,那厨子说话直来直去,不会编造。
厨子揉面时耳听得来的。那几个官差吃面时高兴得禁不住口,就把话大声在面馆里说。原来那胡平亮原本是个正宗剑馆的弟子,据说还是首席,馆主看他甚重,又只有一个女儿,将来不但要把剑馆让与他,还要把女儿嫁给他。
若果真成了,那世上就少了一个大盗,多了一个剑馆传业的馆主,说不定日后也是一门的宗师。
坏就坏在朝廷有个武人得势,居然学读书人做下的千古基业,要像科举一般,层层选拔各地剑术名手。
消息传到各地剑馆,大家先是振奋,若是得了名次,这日后弟子必定源源不绝,继而又担忧选拔比试没得名次。
那胡平亮的师父原本是个秀才,没中举才跟人学的剑,听闻这消息,就把重担全压在了胡平亮肩上。
一时间各地突然许多农人横尸山野,原来是被这帮剑手用来试剑。朝廷颁布诏令,若是发现剑馆弟子试剑,除了绞杀试剑弟子,还要追责馆主,取消开馆资格。
风气虽然得到遏止,可仍有人在盛名之下,按捺不住,斩杀活人,磨练心志。
胡平亮终于还是走上邪路,准备在河边击杀一个卖鱼的老头,那时他正好路过,救下老头,解了胡平亮的剑,用渔网捆了押他去官府,路上渔民们大吹大打,路人不知怎么回事,问了就都佩服起来,也跟进人群,浩浩荡荡朝衙门走去。
他叫什么名字?这俺哪晓得。后来那胡平亮不知怎的从牢里逃脱,从此落草做了一个大盗,而后他听闻当初在河边捕他的人到了俺们县城,他也就来到俺们这里。
要寻人报仇,总得先掂量掂量自己的本事,列位可不要学胡平亮呀。再添几根柴火,把火烧结实,焖几个老皮红薯,待俺啜口茶,滋润滋润喉咙,讲讲胡平亮死的那晚。
俺永生也没法忘记那夜,大雪苍茫,四方为雪照耀,白的更白,黑的更黑。面馆老板借了亲戚家的驴,他家亲戚第二天早上要使,让俺晚上去还驴。俺就牵着驴,没顾前边,低头在雪地里一步一步走。雪地上突然溅了几道黑漆漆的东西,就跟在白纸上泼了几道浓墨一般。跟着又滚下一颗黑乎乎,南瓜一样的东西。俺抬头一看,只见面前立着两个黑黢黢的人影,一个冷冷站着,收了手中的剑,另一个把剑支在地上,身子没倒,却已没了头颅。
俺万分惊恐,却又呼喊不出,就跟溺水了一样。
虽然过去几十年了,那时候俺脸上的表情到现在也没变过,肉僵在脸上,几十年都没变过,脸上再没什么喜怒哀乐,永是这一副惊恐的面容。
哎。打起火把仔细瞧瞧俺,看看俺现在的这副鬼样子,你们就晓得他是多恐怖的一个角色了。
入室
客栈燃灯之后,七位旅客嫌时候尚早,无法拥被入睡,又没有娱乐,于是聚到一楼,集资买了两盘花生米、两盘蜜饯干果、两壶茶,坐那儿吃喝聊天。
聊新闻,也聊野史。客栈老板端茶上桌,说:
“聊归聊,你们的行李要看好,前几日咱这店就遭了毛贼,当中几位客官的损失可不小。”
内中一个肥头阔面的人说:
“你这店不有人守夜吗?”
老板说:
“那毛贼攀墙入室,灵活得像只猴子,守不住。”
另一个眉清目秀的读书人突然站起身,说:
“那我得上楼把我包袱拿下来。”
几个人见他上楼,于是也都一个个跟上去,楼道里响起一阵连环脚步声,踢踢踏踏,不多时大家抱着包袱下来,互相点头示笑,重新坐到一块。
话题抛到毛贼身上,老板却已藏身在柜台后,站在那儿噼里啪啦拨弄算盘,翻阅账簿,计算当月盈亏。几个人续接上老板引出的话,肥头阔面的人似乎颇有一番经历,就先开口说:
“我是个厨子,之前做事的酒楼,就出过一个毛贼,真是个好吃贼。他从不偷人钱财,每日待我们放工,就溜到灶房,看看有什么剩饭剩菜就偷去吃。”
“若是没遇到剩饭剩菜,他就自己起个小火,片些肉放锅里焖。有次灶房买了一坛甜酒,专门用来做汤的,他一碗一碗当水喝,喝多了醉在肉案下,第二天还没醒,被我们逮住之后……”
“稀松平常,稀松平常。”一个贩药材的毫不客气地打断厨子的话。
“偷些吃的算什么,我来说个采花大盗的故事。有一年我去松江卖药材,听几个同行说起当地一件新闻。有个采花大盗,不去掳劫女子,专门找些和自己身材一般成家立业的男人,摸清他们的住所,晚上再溜进他们的卧房,用迷药晕倒男人,放到床下,自己则摸到床上,趁着夜色,假装别人老公,挑逗他人妻子,暗中一言不发,有些妇人直到天亮醒来还蒙在鼓里,浑然没有觉察。”
几个人听完脸上有些异样,都不言语,这时候那个年轻读书人说:
“这可比偷些吃的要坏得很。我也说个和偷有关的故事吧。”
他不急不慢抓一把花生米,丢一颗到嘴里,扬了头,嘴巴微微翘起,凝神想了半天,大家等得不耐烦,突然他把头低下,非常高兴的样子,说:
“是这样一个事,有个人家里非常穷,白天要帮人扎灯笼,晚上才得空读书,可他舍不得灯油。”
坐在读书人对面的一个老头皱起眉毛,说:
“你是说他隔壁那户人家夜夜灯火通明,他就把自家墙壁挖了个洞,偷他家的光用来读书?”
读书人惊奇地说:
“你也听过这个?”
老头说:
“这算哪门子的偷。”
读书人很丧气,把头低了,吃起干果。
老头说:
“我也贡献一个,是和我自己有关的。”
他把袖子挽起,手臂上露出一个“贼”字,大家伸长脖子,头交头,盯着那个字看。那字是经火烧烫而成,年岁久远,一笔一画,跟蚯蚓一样。他褪回袖子,大家就散开脑袋,笔直地坐在桌前,要听老头讲。老头说:
“有一年冬天,天落大雪,那时我才二十岁,走到一个棚子下面,看到里面缩着一个妇人,抱着两个小孩,脚边架着一口小铁锅,下面只有一丁点的火,锅中煮着些雪,还没化掉。”
“他见我来,脸上有几分羞,见我要走,就突然站起来,乞求我弄点米送她,她好煮一锅给孩子吃。”
老头眼角流出几滴泪,擦了一把,又说:
“我真是善念一起,就遭了噩运。那时我自己没得一个铜板,却只因早上别人施舍了两个馒头,腹中还剩一点暖和,就想帮她寻点米,于是就到一家米店,趁老板不注意,抓了两把米,不料让旁边一个买米的人撞见,就当场吆喝老板,把我送到了官府,烙了这么个字到手上。”
厨子听完手在桌上一拍,叫骂道:
“抓你的那个人真是多管闲事!才两把米就要烙印刻字。”
读书人吸着鼻子,把手搭在老头手上,安慰说:
“你说我那个故事算不得偷,那你这个就更不算了。”
客栈老板盘算下来,这月挣得不少,心下欢喜,就从柜台里摸出一包牛肉干,走到众人桌边,小心揭去几层封纸,摊在桌上,说:
“我请客,吃。”
大家就不客气,七只手长短伸了,拈一块到手里,细细扯成丝吃。
八仙桌正好空一个位,老板填进去,里面一个卖曲的搂着一把古色二胡,说:
“肉有了,酒怎能少,我请大家吃酒,老板,来坛二锅头,再取八只碗。”
老板起身进厨房,出来时一手抱酒,一手托着八只叠在一块的碗。大家分了碗,卖曲的将酒满满倒了八碗,晃一晃坛子,声音浑厚,几乎要荡出来,还剩一大半。卖曲的放下酒坛,笑着说:
“这买卖实在,够吃了,够吃了。”
大家举碗碰了,深深浅浅抿一口,放下碗,抓起花生米吃。
卖曲的摸着自己的二胡,说:
“我这把二胡,虽不是名家打造,却是我父亲家传下来的信物,宝贝一样收着,靠它吃饭,哎。”
太息之间,想到自己的老父,他虽已亡故多年,却仍似幼时一样活在自己身边,舍不得让自己受寒挨饿。记起老父病入膏肓之时,惦念放心不下自己,唤到床边,说:
“儿啊,我没有什么家财留给你,你人又瘦,干活样样都比别人后,而今我是要走了,只这一把二胡,你要勤学苦练,往后兴许能混几顿饱饭。”
每每拉曲,念及父亲,仿佛曲中藏了父亲的魂,听者无不沉湎。
里面一个游历诸多名山,见识广博的游客说:
“想必你技法纯熟,不如拉一曲,让我们欣赏欣赏。”
卖曲的说:
“好,那就拉一个,献丑了。”
曲子一响,众人个个忆起旧事感伤。曲声结束,大家什么话也不说,空洞洞望着什么,酒一口接一口喝,不知什么时候,渐渐醉去。
首先醒来的是贩药材的商人,只觉大腿上少了些重量,一瞄,发现自己的包袱不在,大呼一声:
“不好,遭贼了!”
当中两个听到惊呼声,蒙眬中就去摸自己的包袱,摸空之后立刻清醒,就摇醒了另外几人。
大家吵吵嚷嚷,过了好阵子才发现八个人中少了一个,就是那位手上刺了“贼”字的老头。
大家的包袱悉数被盗去,连读书人包中那几本文选也没幸免,倒是卖曲人的那把二胡,没有损伤,摆在桌子正中,一点油水也没沾到。
灯笼
徐明在灯笼作坊做工,干到二更放工后,路上黑黢黢,提着灯笼更害怕,自己像是明晃晃的猎物,豺狼都潜伏在黑暗中。见到比夜更黑的一团东西,他就把灯笼凑上前,黄黄的光什么也没照出,仍旧是黑。
遇到比夜白点的一团灰,也把灯笼凑上前,还是黑。
前边亮起两点绿光,似两只发光的狗眼睛,停下,镇定后再走,才发现是两只灯笼。
灯笼挂在独轮车两边,车下垫了四根木头平衡,车上摆着一个炭火炉子,旁边放着一张小桌子,上面扣了两个铜盆,边上有几十个包好的饺子。
一个和他年岁一般的女子正坐在炉子旁烤火,见到有客人来,就起身说:
“下碗饺子吧。”
灯笼作坊里都是些大妈,徐明每日就是扎灯笼,糊灯笼,难得和年轻女子说上一句话,就说:
“那就下碗饺子吧。”
女子掩了炉子的门,炉子上架着一口锅,里面原本就热着的水滚了起来。女子下了饺子,问他:
“干饺还是汤饺?”
“汤饺。”
徐明坐在旁边的胡床上,端着碗先喝了口热汤,放下碗,说:
“你胆子真大,敢一个人晚上出来卖饺子。”
女子也不客气,说:
“那你还不是一样,敢一个人打灯笼闲逛。”
徐明话比平常多起来,说自己才放工,明天花船要游湖,订了很多灯笼,忙活不过来。女子说,花船游湖,这些天赶夜路的人多,她就在这里卖饺子。
人多?眼下分明只有徐明一个人。她又问徐明去不去看花船,徐明说他明天傍晚就收工,到时候会和家人去看。
突然起了一点冷风,徐明浑身一摆,他就把胡床搬到火炉旁,端着碗,边烤火边吃。女子嫌弃他挨自己太近,瞪了他一下,徐明说:
“我有点怕。”
“你怕什么。”
徐明也不知害怕什么,只见黑暗之中,走出一个中年男人来,徐明就顺手指过去,说:
“怕他。”
那男人走到摊子前,脸上的皮肉粗糙得看不出表情,他将手往饺子上一指,说:
“要干的。”
女子起身下饺子。徐明吃完一摸口袋,发现口袋破了一个洞,里面的铜板一个也不剩。徐明不是吃白食的人,脸皮薄,何况又是在一个面容姣好的女子面前,他想了下,说:
“灯笼你要吗?我钱掉了,就拿这个抵给你。”
女子看着徐明的灯笼,上面题了几行字,说:
“那就把灯笼给我吧,反正我也常用到。”
徐明见她爽快,觉着自己吃亏,说:
“那你得再找些钱给我。”
女子不乐意了,说:
“那可不行。”
徐明就提着灯笼,走到那个中年男人面前,低声问:
“灯笼,你要吗?”
男子点了下头,问了价钱,就当场付给徐明。徐明付完饺子钱,还剩一些,盘在手里,摸黑往住处走去。男子吃完,提了灯笼,也朝一片黑暗中走去。
第二日徐明去灯笼作坊做工,进门就听一声喊,拥出几个壮汉,将他打翻在地,五花大绑押到了衙门。就在昨天晚上,有人潜进本地一个富户,盗了几张古人的名家字画,杀了一个看守的家丁,尸体旁边弃着徐明的灯笼。那灯笼上有作坊的名号,徐明为了避免和别人的灯笼弄混,还添上了自己的名字。
徐明想到了那个摆摊卖饺子的女子可以作证,可自那天晚上过后,那个女子就再没到那里卖过饺子。
好美食的人怎能错过夜市,即便囊中羞涩,到了此地,见到满街的灯笼下,一个个摊子,卖油炸的、炭烤的、滚汤烫的,不禁抚着肚子,询问价钱,买上一点,又挪到下一个摊子消费,哪管明日的饭食计划。
京官杜建之办差途经此地,下车时正是夜市最热闹的时候。十年前他是本地的邑尉,掌一县治安,缉捕恶盗,刑罚甚力。相隔十年,回到发迹之地,感叹变化之大,记忆里已经全然没有印象。他穿着素衣,吩咐几位随从候在车旁,自己走走逛逛。
到了一个卖猪手粉的摊子前,他停下脚步,看着秋油炮制的猪手,就不自觉地坐下,点了一碗。
摊主是个不到三十的女子。她摆上一只大碗,里面蓄上汤,烫了米粉,用漏勺沥干残水,滑进碗中,再加上猪手和佐料,端到杜建之桌上,就又去招揽食客。
杜建之挑起团在一块的米粉,拉出一根齐额不断,韧劲十足,便问女子,是否用的庄田泉水。
女子答是,说自己就是庄田人。
那是十多年前的一件公案,庄田出了几个恶盗,杜建之带人前去缉拿。恶盗捉住后,用盐木枷锁了,带出庄田时,见路边有个卖粉的小馆子,一行人就顺路点了猪手粉吃。
杜建之乡音已改,夹杂几分京城官腔,说:
“十多年前,我去过庄田一回。”
女子得了空闲,说:
“听你口音,像是从京城过来的。”
杜建之说:
“是从京城过来的,不过原先在这里的。”
女子说:
“在京城做生意吗?”
杜建之啃光一块猪手,将骨头抛给一只正在寻食的黑狗,笑一下,说:
“在那边做些生意。你卖这个多久了?”
女子说:
“十年了。十年前我卖饺子的,后面就改卖猪手粉了。”
杜建之说:
“这里不怎么时兴吃饺子。”
女子回想往事,十年来的愧疚使她已经无所畏惧,说:
“倒也不是,吃的人还是有的,只因十年前有天晚上出摊卖饺子,遇到一个提灯笼的年轻人,没钱付我饺子钱,要把灯笼卖给我,我没要,后来他就卖给了另一个吃饺子的人。大概就是那个买了他灯笼的人闹出了一件命案,把那灯笼留在了命案现场,官府就把罪状全部推到了那个年轻人身上。”
女子又说:
“官府来我摆摊的地方找过我几回,我那几天跑去看花船游湖了,后来有人悄悄告诉我,我那时胆小,怕牵连进去,就没敢去作证。”
她叹一口气,说:
“哎,真是可怜,那个年轻人就这样稀里糊涂冤枉死掉了,听说当时负责那个案子的人,叫杜建之,已经升到京城去做官了。”
杜建之一呆,并不言语。
突然起了几股阴风,由黑漆漆的街巷入口扑来,吹得街上的灯笼都荡了起来。女子望着满街摇曳的灯笼,仿佛成百上千个提着灯笼的游魂,僵在原地茫然不知要往何处去。她说:
“看不出来吧,原先这里是一块法场,他就是在这里被处决的。”
法场一词,既是佛家的道场,亦是刑场。
月夜
极不待见的两个男人即将发生一场恶斗:他们在月光下手握一把反着冷光的柴刀,隔着一堆稻草,扬言要砍死对方。
这两个男人是邻居,一个叫天干,一个叫大雨。生天干那年遇到了旱灾,田中颗粒无收,于是他爷爷给他起名“天干”。次年大雨出生,正逢洪灾,他爷爷跟天干的爷爷是六子棋友,两个老家伙正在下棋,大雨的爷爷正为孙子的名字犯愁,天干的爷爷输了一盘棋后,就建议起名“大雨”。
六子棋在乡下非常盛行,不比象棋需要识字,也不像围棋煞费脑筋。简单,小孩子看看就会。方便,棋盘画在田间地头,棋子用棍子、石子都行。
天干和大雨光名字就相生相克,简直得了道家阴阳两极的精髓。
恶斗的起因非常简单。大雨家晒谷时,天干家散养的母鸡领着一群小鸡冲进谷场偷食,大雨家的狗追着一气咬死十来只小鸡。
咬死就咬死,那狗居然还叼着一只小鸡跑到天干家挑衅,天干认出是自家最可爱的那只,就摸起柴刀,砍伤了大雨家的狗。
那狗拖着腿,趔趄回家,大雨一见就炸了,誓言要为自家的狗复仇。
两个人吃完饭,手握柴刀,由小路逼到稻田,从黄昏僵持到月夜。
俩人都没娶妻,曾经相好的爷爷也都化成了山头的小丘。没有墓碑。
假设俩人现在已经成家,不知道媳妇是劝架还是帮腔。若是帮腔,极有可能在黄昏时就失掉了自己的男人。
俗话说月黑风高夜,正是杀人的时候,不过所指的是暗杀,如今是明斗。明斗在黄昏时,西边落日残阳,血红血红的,更容易冲昏头脑。
月亮当空,照得地上的一切都黑白分明。一只青蛙伏在稻草上,见证着两个男人的生死。它时不时鸣上几声,是在嘲笑和督促,引得两个男人都想将它劈成两块,但是谁也不敢动刀,只将捏出汗的手在刀把上擦擦。
他们为同一个理由反复争辩:
鸡偷谷,狗咬鸡,人打狗。
循环而稳定的三角关系,总之都说自己有理。
无法说服对方,就把陈年旧账摆出来算。先从近的开始,一样一样,直算到俩人还是孩童的时候。
彼此没有放松,反倒更加紧张了,今天晚上,总得弄死对方或者自己。月亮转移,就连那只青蛙也看不下去,跳下草堆,溜进了老鼠洞里。
山上下来一头不太大的野猪来田里觅食,希望能从稻草堆里翻出几株遗落的稻子。此时天干和大雨已经结束了争吵,两人立在那儿,像两个稻草人。野猪一路拱着田间的稻茬,什么也没翻到,气鼓鼓直往前边的稻草堆冲。俩人听见响动,野猪已经奔来。他们几乎马上达成共识,挥刀与野猪搏斗。
面对这种凶猛野兽,他们是害怕的,但拿刀与人斗,比拿刀砍野猪更加令人恐惧,对野猪的恐惧也就减了大半。之前的怒气得到发泄的机会,斫杀结下宿怨的死敌一样,把劲都用到了野猪身上。
那野猪大概是今天没寻到吃食,又眼瞎碰到两个拿刀的人,格外憋气,并不逃跑,冲完天干撞大雨,咬完大雨扯天干。
冲撞大雨时,天干就爬起来砍它后腿,野猪又调转头去咬天干,大雨就咬牙切齿,青蛙跳跃一般,砍向野猪的后腿。
野猪后腿虽然皮粗肉厚,怎奈今天俩人约仗前选了家中新买的柴刀,早已把柴刀磨了百来遍,无比锋利,砍肉斩骨不是大问题。
一场恶斗过后,野猪已经不能正常行走,两个男人也是伤痕累累,却感觉不到疼痛,把刀往野猪脖子上来回割。
野猪的号叫震天响地,惊得附近山上的鸟儿在稻田上掠来掠去,蛇在洞的深处盘成一团。
猪血像突破泥沙的泉水,流经两个人的手掌,有些烫手。两个人摁着野猪,浑身发冷,心下都想,今天要是被对方杀死,大概就跟现在的野猪一样。
野猪彻底失去温度,两个人才松了刀,瘫躺在地上,月亮还是那么白。损失十来只小鸡,伤了一条不听话的狗,因为屁股旁边的这头野猪得到了补偿。他们几乎不再怄气,接下来要讨论的是如何分肉。
一人一半,这一点不分歧。他们决定分头行动,一个去拿杀猪分肉的工具,另一个去拿装肉脱毛的行头。两个人往家走去,衣服都没换,拿到行李后往田中赶去。
他们在地上铺上稻草,将野猪翻到稻草上,又盖了些稻草到野猪身上,然后用火石点燃。几阵大火后,猪皮已经烧焦,毛发不存,分骨拆肉,连猪心都对半切了。
先是对峙,再是恶斗,后又干了屠户的活,晚饭俩人虽吃了几大碗,但蓄养的精锐折损殆尽,肚子憋得厉害,就割了大块五花肉,抹上家里带的盐,捡了些干柴,生一堆火,把肉丢在火里烧。猪油渗透出来,火势猛烈,盐激发出肉的香味,化成一道道油烟,诱得俩人的肚子紧缩。见时候到了,俩人立马用树枝拨出烧肉,抓把稻草垫在手里,吹弹肉上的柴灰,小口撕咬享受这场恶斗的战果。
大餐过后,月亮隐入灰雾之中,天边吐出银光,他们清理完田中的脏东西,趁着仅剩的一点夜色,各自扛着半头猪肉,溜回了家中。
天光大亮,他们没换衣服,连脸都没洗,穿街走巷,大家见了,莫不嫌弃又好奇,就问:
“真和天干打了?”
或问:
“真和大雨干仗了?”
两个人都点头,都不说话。
灯灭
倦意连绵,我躺靠在椅子上,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在萌芽舒展,待我看清了,哦,原来是一粒种子,但见它吐出嫩芽,弯弯曲曲长起来,藤蔓缠绕,枝条修长,片时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我顺树攀爬,周边的山河矮下去,再往上一看,雾霭蒙蒙,风一吹,现出一座大殿来。
还不及待我看清,铺天盖地的黑笼罩过来,不知何处有一个轻柔的声音在唤我,睁开眼睛,见我妻子站在油灯旁,她已把一件衣服披在我身上。
油灯旁有本翻开的当代名家文章选集,上面落了几点油,浸在几个字上。我须再费些神,把文章研究通透。
然而妻子说夜已经很深了。我说功名要紧,大考在即,于是又正襟危坐。妻子笑而不语,不知何时已贴在我身后,把一双纤长细嫩的手架在我肩上,穿过椅子,替我翻起书来。她哈出热气,说:
“我伴你读一会儿。”
热气几丝,落在我耳朵上,痒痒的,使我不得精神专心看书。
我捏住她的手,轻轻抬起,说:
“你去睡吧,等这灯油烧完,我就……”
“灯油烧完怕是已经四更天了。”
妻子嗔怪,随即夸我文章火候已到,不必这么劳苦,又说那功名富贵,不过流水云云。我说适才有一大梦,妻子绕到我身前,挨我腿上坐下,软软地拥在我身上,双手缠住我脖子,问我:
“什么大梦?”
梦还记得清晰,要是再过些时辰妻子问我,定然已经忘记。我便照着梦中所见,一一同她说了。
“原来是个南天一梦。”
“南天门口,兴许是预兆我这条鲤鱼,即将跨越龙门。”
“是呀,是呀。你不是鲤鱼,你是人,是我的人。”
妻子对我的梦似乎无甚兴趣,搂我更紧,几乎要与我重叠融合。
她的下巴搭在我肩上,双手箍住我双臂,我挣出双手,在脸上拍打,紧了紧脸,轻轻将她推开。
妻子捏住我的手,问我为何要抽打自己,又将手触在我脸上,似乎要寻出几根泛红的指印来。我说我没抽自己耳光,功名富贵要紧,得再看几页书。
“书是看不完的,何况夜已经很深了。”
屋外黑沉沉一片,窗户敞开,油灯的那点光亮,完全消融在黑夜中,往常能听到的鸟鸣虫叫,这会儿也寂静无声音可听。
起风了,可连风都哑了喉咙,只是吹,窗户虽动,却无拍击声音。妻子离开我,温热迅速流失。她掩了窗户,回身时我让出一半椅子,她坐下去,依在我身上。
我手指没入她的长发,像是进入了丝绸之物当中。得亏妻子嫁妆丰厚,才让我从粗麻布里挣脱出来,感受到丝绸的软滑,也让我闻到人体之外,脂粉的香气。
“我若不考取一个功名,实在愧对于你。”
妻子说:
“不打紧的,功名有则有,没有就没有。”
她突然仰起脸,说:
“你也不像个太在乎功名的人。”
这话一出,油灯下那本书上的文字,蝌蚪一样游动起来,怎么也看不清。
她又说:
“即便你没有考取,光是嫁妆就够我们吃喝一辈子,何况以后还有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孩子?他们在哪里?妻子看出我的疑惑,揽住我的手,从她的肚子上滑过去,说:
“现在没有,以后会有的。”
我闭住眼睛,想象着子女在屋中追赶打闹,妻子站在她们身后追赶。我睁开眼睛,眼角湿润,要不是遇到妻子,我怎能体验这人间的温情?
油灯微弱的光,总是能使人联想,使人话多,只是书上的文字,就看不大清,使人发昏。我睁了睁眼,将妻子搂在怀里,空出的手去翻书。
妻子嘴巴微翘,嘘了一声,白纸糊的窗户后扑闪着一只黑影,妻子起身打开窗户,一只金丝雀飞了进来,落在我的书上,对我叽叽叫唤。
我用手指抚着它光洁的羽毛,摇头笑着说:
“不懂,不懂。”
它瞬间明白我的意思,用喙在书上不停点着一个字,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妻子已经替我磨起墨,铺上一张白纸,将笔递给我,说:
“兴许是只神鸟,来给你透露考题。”
我浑浑噩噩接过笔,金丝雀在字上啄一下,我便在纸上照写一个,又见它用爪子抓起几页纸,翻页寻到一个字,我便又跟着写。
我一看抄写的文字,词句贯通,引经据典,真乃神鸟也,不仅断文识字,居然还熟读选集。金丝雀点完最后一个字,妻子伸出手,它扑棱一下飞到妻子的掌上,妻子说:
“这回你不必担心了吧,只要照着题目。”
我心下大欢喜,跪在地上,叩头拜谢。那鸟喳喳叫唤几声,妻子将手一抛,它飞过窗子,消失在一片阴沉沉的夜色当中。妻子又掩上窗户,勾魂夺魄似的朝我微笑,说:
“夜已经很深了,我们上床去睡吧。”
妻子扶我起身,油灯里的油已经见底,屋里昏沉,我们走到床边,坐在床沿。我把手触进被子里,里面还余着妻子睡过的体温。不远处的一只木炭炉子热着壶水,妻子正要起身打水,我轻轻按住,说:
“今夜就由我去吧。”
我提出墙角竖立着的木盆,倒上热水,用手指试探水温,又添了些冷水,端到妻子脚边,替她脱下鞋,将她的脚放进水中。
我紧挨妻子坐了,脱下鞋子,四只脚在水里游来划去。
水有些凉了,妻子附在我耳边呼吸,轻轻念着:
“夜已经很深了,我们睡吧。”
我脱下衣服,摸到腰间枯瘦的几层软皮,惊出魂似的急急趿上布鞋,跑到油灯旁,挑了下灯芯,捏在手中往身上照去,只见是一个老头的身躯。
我不过二十,肉身何以会这般衰败,问询妻子,只听她在床上应答:
“你已七十有一。”
五十载光阴弹指间流逝,而我犹如手中那盏油灯,只见它炸出几个火星,随我坍塌倒地,我也跟着一同熄灭在无尽的黑暗之中。
【作者简介】水鬼,湖南沅陵人,小说见于《花城》《天涯》《青年作家》《湖南文学》等刊,并被《小说月报》《长江文艺·好小说》转载。现居广东东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