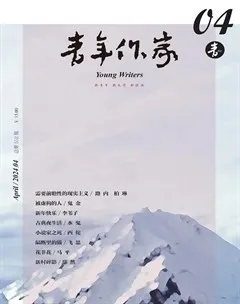失群的多利羊
高鹰生来就不适合做牧羊人。小时候看到爷爷每天牵着两头慵懒而没有生机的绵羊,他就开始拒绝牧羊人这个身份。
当高鹰看到爷爷为了羊群的发展壮大而绞尽脑汁地去村东头,找那头高高大大的公羊配种时,他轻蔑地对爷爷说:“现在已经不流行配种了,现在开始流行克隆,什么品种优质就发展什么品种。”他说话的派头像个经验十足的科学家一样。
“什么‘恐龙?你这个小屁孩从哪里听来的玩意?”爷爷并没有因为高鹰的话生气,微笑着问他。
高鹰把爷爷拉到他家的板壁墙边,指着那张开始泛黄的报纸说:“你看,这就是克隆羊,这上面说它有三个妈,又说它没妈,反正它是特别的羊,它应该是这世间唯一有名字的羊了!”
爷爷虚着眼睛跟着他认真地盯这张1998年的旧报纸,这张旧报纸是高鹰的父亲在2000年的时候以废品的价格论斤称重带回夹修沟的。跨世纪的这一年,他们打算用报纸来敷一下黢黑的板壁房。十多岁的高鹰对房子的翻新不感兴趣,他每天扒着浆糊未干的墙壁一看就是一天。
“真落后,这只羊都出生三年了我才听说。”他有些懊恼地摸着配图上那只昂首挺胸的羊,那是高鹰见过的唯一一只不拴绳索,不跟着羊群的羊,从它的眼里可以看出它对草并不依恋。
爷爷识字不多,没看几眼就没耐心看下去了。他摸着高鹰的脑袋说:“科学家有科学家的门道,农民有农民的门道,这两个没有关系。”爷爷转身走向他那两只萎靡不振的羊,继续为羊的配种而忙活。只有高鹰还意犹未尽。
这逼仄狭长的夹修沟,没有一块像样的土地。那些长在石缝里、荒土上的粮食,样子鬼鬼祟祟,不成体统。夹修沟的人大多养些牲口谋生。他们喜欢走一样的路,经常都是东家养了羊,西家也跟着养羊。夹修沟大多数人家养羊,所以爷爷为羊的发展心力交瘁,直到老死的时候也不过八只羊。父亲把那头因为一根绳子就耕了一辈子土地的老黄牛卖了,又买了一些羊来,壮大了羊群的队伍。
当大多数孩子还在山里的泥洼草莽中像猴子一样懵懂时,高鹰已经对这片土地充满了绝望。他从知道点世事开始,没有一天不想挣脱这一方土地,他心不甘情不愿地放羊的时候,也总是拿着一本书躲在树荫下,任由羊东奔西跑。那些获得短暂自由的羊群总在父亲的骂骂咧咧中回归羊圈。
后来他如愿离开了夹修沟,以为自己可以成为一只自由的羊,以云的方式在天空中生活。可现在又灰溜溜地回到夹修沟,这不得不说是一件猝不及防又无可奈何的事情。
“要不是爸爸突然死掉,我是绝对不会回到这里的。”他对年近七十念念叨叨的老母亲甩下这句话。
母亲一时哑口无言,坐在煤火边坚硬的床板上唉声叹气。
高鹰无法向母亲说出他内心的凄苦与煎熬,母亲也无法更深层地表达她对孩子的隐忧和最低的期许,他们一时都陷入了沉默。
窗外的风咻咻地拍打着窗户,年久失修的门也有点摇晃起来。高鹰从炉火边的矮凳上站起身,用胳膊把不太灵动的门抵上,又在窗柩上拉下拉线开灯,黄澄澄的灯泡像一个透明的葫芦,在镂空的板柱间昏沉沉地亮了起来。
“现在还早,不用这么早就开灯。”母亲那两只像灯泡一样昏黄的眼珠子浑浊地看着墙上那个挂钟,分明已经七点过了。夹修沟的天空本来就只有一线,这个时段外面早就昏黑了。
高鹰赌气似的又把拉线使劲地拉了一下,灯灭了。父母这种毫无原则的节俭让他感到生气。高鹰生气的何止是这一桩,就算生病了都舍不得药钱的态度才是高鹰最愤恨的。
他用力地拉开门,回过头咕哝一句:“不管怎么样,我把羊处理了就走。”
隔间的门吱呀一声,仿佛带着深深的怨气。高鹰躺在床上百无聊赖地看着他床头那张贴在板壁上的旧报纸,泛黄褶皱,字迹模糊得已经无法辨识。他立起身抹去配图上厚重的灰尘,那只羊的身体已经不见了,只剩下两只迷茫的眼睛。
“真可怜,在这世间没有一只像自己的羊!”高鹰自言自语地咕哝一句。
高鹰蒙头躲在被窝里,像躲避了一切混沌的世俗。这边母亲忧虑的脸在冒着蓝色火苗的炉火中越显越老。
有人说吃得了苦的人,后面有很多苦等着。当夹修沟的泥孩子还在树丛间愉快地蹦跶的时候,高鹰就带着几本卷边的书,一支只有手指头长的铅笔和几本皱巴巴的本子,去往五公里外的乡里读书。他每天走两趟,中午就吃几个冷土豆。冬天那种又冷又饿的经历,他这一辈子都不想回忆。
那些夹修沟里整天围着牲口转的孩子早把他当成了另类。他在县城里读书也历来孤僻,学校里的同学也把他当成了另类。他常常看《平凡的世界》以解脱精神上的苦闷,孙少平成了他唯一的知己和精神支柱,但他坚信他的命运一定会胜过孙少平。
他小心翼翼地挺到大学毕业,作为夹修沟最体面的读书人却一直没有找到村里人认为的体面工作。他端过盘子、做过墩子、卖过老鼠夹、送过外卖……直至三十三岁,他还在县城里开三轮卖水果。这些工作常人做可以,但是读书人去做就容易沦为笑柄。以前夹修沟的人说他是山窝窝的金凤凰,后来大家都觉得他是读书读傻了脑子,做的没有一件是光宗耀祖的事。
父亲死的前一天还给他打过电话。希望他能回到夹修沟给承包山林的老板当个会计,一个月2500元。父亲还让他接受一门亲事,是一位与他素未谋面的姑娘。
他不同意。父亲恼怒了,咳嗽着说:“整个夹修沟,就你活成了倒文不武的浪子,你看和你同年的人修房的修房,娶妻的娶妻,谁还像你这般窝囊。考试考不了也就算了,娶妻生子的人伦纲常你也读丢了,这辈子你当鳏公……”父亲急火攻心的咳嗽盖住了辱骂声。
他以往回到夹修沟遭受过很多冷眼,也感受到父母的不欢喜,但是从没有感受过父亲这样直白而裸露的侮辱。他也经历过考工作的漫长煎熬,他在密密匝匝的人群中接受一重又一重的筛选。他疲于一场场结局相似的奔赴。他宁愿选择洒脱与自如,比如卖老鼠药、苍蝇贴,他喜欢让自己的内心没有焦灼与紧迫的事。
父母一开始期待他西装革履地拎公文包,后来希望他循规蹈矩地回到夹修沟娶妻生子。父母对他从一开始说“没事”,到后来沉默了,直到他33岁,父母已经对他毫无耐心了。
“你爸爸不会说话了!”母亲哽咽的声音从电话传来时,他正在扔那些变坏的水果。多年的社会阅历让他明白只有及时跨越喜悲才能迎接第二天的生活。所以接到电话的时候,他已经全然不把父亲昨天辱骂他的难听话记在心上了。
他的父亲突然死掉了,留下了四十多只羊。将近七十的老母亲无法跟着羊满山吆喝,作为家中的独子,他不得不回到夹修沟继承这笔唯一厚重的家庭财产。他一直期待人生的变数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但他并不期待这样的家庭裂变。
高鹰想把羊群尽快处理掉,快快地收拾行李,离开夹修沟。在父亲潦草的葬礼上,夹修沟的人都在不怀好意地打听他目前的生活状况。其实他在县城里蹬三轮卖水果的事情早在夹修沟传开了。他们私下不知道冷嘲热讽过多少次,甚至还开始传播起高鹰气死父亲的流言。但是当着高鹰,他们对他没有找到体面的工作、三十多岁没有娶妻生子故作惊奇,进一步以广阔的胸襟安慰一番。
高鹰不曾觉得他做的某一份工作不体面,但是他无法坦然地接受他们的鄙薄,也不能冷脸回击,他终究也只是个有情绪的普通人。他只想早早地处理了那些一无是处的羊,然后逃离这块狭隘的土地。
但是还没联系到买主,就赶上冬天的早雪,断崖式的降温,他没有丝毫防备。没有羊群养殖经验的他忽略了母亲的叮嘱,没有给羊圈铺上保暖的枯草。四处漏风的羊圈灌满了冷风。第二天等他推开被白雪压着的木门时,那些羊踉踉跄跄。他给羊喂食的时候,羊咩咩地伸着头叫,却不抢食。有几只聪明的羊通过嗅觉找到了食盆,其余的都在傻傻乱叫。高鹰没耐性地伸长腿往羊屁股上踢,那些羊只在羊圈里乱窜,你踩我我踩你,就是找不到木门。他惊讶地发现这些羊一夜之间都瞎了。
高鹰扯开嗓子喊他的老母亲。老母亲以近七十年的人生阅历,也无法解释羊群集体失明的病症。高鹰觉得这不是什么吉利的事情,他没有心思继续养下去,就四处拨电话联系买主。来了几拨人,高鹰想把羊群尽快卖掉,但是买主看到这些瞎了眼睛的羊都摇头走了。有几个卖羊肉的老板倒是愿意要,只是给价低。况且也就只要一两只。高鹰只好垂头丧气地继续养着。
他想这些羊要是全部死了也好,就像他水果摊上的香蕉,要烂全部一起烂,扔掉也不可惜。可是它们只是瞎,又不死。他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他被困在家里,每天除了焦躁地喂羊也别无他法。为了把羊群尽早处理掉,他每天拿着手机在网上搜索治理羊瞎病的各种土方。他每天把羊夹在腿根,扯着羊的两只耳朵,他的老母亲哆哆嗦嗦地搬开羊的眼珠子往里面滴眼药水。天晴的时候,他把羊赶出来晒太阳,羊找不到路,他就推着羊的屁股走。
日子一天天过,他那些没卖完的水果早在他租的房子里长满了黑霉。房东给他打来电话,说他卖水果的三轮被收废品的偷走了。他只好临时去城里结算了房租,清理那些亏本的水果。继续回到夹修沟照看那群羊。
为了把羊群尽快处理掉,他不得不修整漏风的羊圈,给羊群准备新的饲料,他每天用他辛辛苦苦蹬三轮卖水果挣来的一点点积蓄,给羊买各种红红绿绿的眼药水,想尽一切办法治疗羊的眼病!
好不容易熬到了开春,羊的眼病才慢慢好转,他以为可以尽快离开夹修沟。他已经预备去租个铺面继续经营水果生意。他也打算把老母亲带离夹修沟,他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让老母亲在县城里安度晚年。可是那些羊又开始生起另一种病,嘴角起满水泡,哈喇子不停地流。一只传染一只,几乎都不吃不喝,才几天就瘦得皮包骨头了。有几只本来就瘦弱的羊,悲哀地叫了几声就死在了羊圈里。
他看着那几只僵直的羊,觉得他之前付出的心血又白费了,他的内心充满沮丧。他四处打听治疗这种疾病的办法,急慌慌地跑到县城里请教有经验的兽医,又匆匆忙忙地夹着大包小包的兽药回到夹修沟。
他又把那些虚弱哀号的羊夹在大腿根,掰开它们的烂嘴,让他的老母亲往羊嘴里灌药。可是县城的兽医经验并不一定比乡下的丰富,他花了几百块钱的药钱,羊病还是不见好转。
真他妈见鬼!他每天都在羊圈边骂。他还没理解爷爷和父亲为什么一辈子呆在夹修沟这块被山脉围得水泄不通的地方,一辈子养着这些体弱多病的羊。他现在也被这群羊困在方寸之地,他想脱身也不得。他想起了梭罗在《瓦尔登湖》里的话,“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沉默的绝望之中。所谓惯性的绝望便是放弃与命运的搏击,是听天由命。”
真他妈没有出息!他既不指名,也不道姓地骂了一句。
他把这些病怏怏的羊推推搡搡地从羊圈中赶出来,费了很大的力气把它们赶到了夹修沟最陡的坡地上,那里正是夹修沟最早迎接春天的地方。坡地上正冒着一些新芽,坡地周围是浓密的灌木丛。那些灌木还没有十分的春意,地上笼着厚厚的枯叶。如果一直向灌木林的左边走,就是一处悬崖,悬崖下面有一片毛竹林,毛竹林下面有悠悠流淌的小溪。
高鹰站在坡地上喘着粗气失望地看着这些羊,他清点了一遍。他从父亲手里继承来的四十多只羊经过他几个月的饲养,一共还剩下三十五只。
“去寻找你们的命运吧!”他把赶羊的木条甩得很远,做出永别的架势,他不想再被这些羊拖得筋疲力尽。他觉得他成了他家那头被父亲卖掉的黄牛,这些羊成了他脖子上的绳索。继续蹬三轮车卖水果也好,或是去摆摊卖老鼠药……这些都是可以的。他读了这么多年的书也无法定义人生的意义。既然自己都定义不了人生,又何必受人定义。
他还是像小时候一样决绝地要离开夹修沟,他也要继续去寻找自己的命运。想到马上就可以离开夹修沟,他下山回家的脚步都加快了许多。
家里多出一个女人,这件事比父亲的死还让人猝不及防。高鹰认真端详那个坐在炉火边木板床上的女人,丰腴,黝黑,结实得像一匹马。她染红的头发和尖头的高跟皮鞋彰显着她所见过的世面。
母亲用皮包骨的手指着这个女人说:“这是你媳妇!”母亲一脸严肃,全然不像玩笑。
高鹰被吓得直往后退。两只眼睛瞪得像两个离壳的核桃。
“你爸死前就卖了二十头羊给你定下的,你哪里也别去了,在我死之前生个孩子吧。”他第一次在母亲那双枯萎的眼珠子上看到星星。他知道自己在母亲这里已然成了村东头那只专门为配种而生的老公羊。
高鹰脑袋嗡嗡响了起来,像喝了一桶烈酒。还没等他清醒,那个女人闪着东张西望的眼睛开口道:“我也是一直在外面打工,这么多年也不是没有条件好的看上。我是个守承诺的人,这一趟专门回来,你不要嫌弃我没有文化,我也不嫌弃你是个怪人。事成不成就看你一句话。”
可以听得出这是一个果敢的女人,直率地把婚姻当成了乡集上的牛马交易。高鹰不知道怎么答复,他只想尽快离开夹修沟,再也不回头。母亲拉扯着他的衣服,把他往床板上推。高鹰憋足了气,大声地喊出:“走,走,全都走!”
女人咯噔咯噔的高跟鞋才从他家门槛里踏出去,夹修沟又传起了他要当鳏公的流言,更有甚者,说他有某种不可告人的身体疾病。没过多久,就有人聚在他家门口指指点点。
高鹰怒气冲冲地收拾行李。母亲在炉火边哭得死去活来。有几个年长的老辈进来,拿出一种说教的口气说:“你爸妈因为你操碎了心,不曾有一天体面日子,你还要继续这样冥顽下去?你想你妈也因你断了气?”
高鹰只觉得莫名其妙,他好像什么都没有做错,又好像什么都是错的。他成为夹修沟的一坨屎,一个臭屁,一根刺,这更是猝不及防的事,但凡今天他踏出这个门槛,母亲有个三长两短,他就是利刃匕首。
夹修沟的人用道德廉耻又在他的脖子上套了一根绳。他只好委曲求全地蒙着头愤愤地睡下。他想不通他只是一个不按普罗大众的路走的人而已,他究竟是触怒了谁,为什么与他相关的事都被愚弄与谴责,他在众人眼里成了万恶的罪人。
高鹰在被窝里熬了很久,直到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人离去,直到听不见隔壁母亲的抽泣声。他才从被窝里抽出脑袋,他横竖睡不着,立起身借着手机的微光,又去看了一下那双羊眼睛,羊的眼睛像两团紫红的星云。高鹰盯着那无限放大的眼睛昏昏沉沉地睡去了。
他做了个梦。梦到自己变成了一只羊,他是羊族群中唯一一只有名字的羊,他的名字叫多利。他不知道他的名字得于何人,被赋予何意,他也不知道他的母体在哪里。除了与其他羊拥有千篇一律的脸,他几乎没有与羊相似的地方。
他生来就不喜欢吃草,宁愿啃食泥土也不愿意闻青草的味道。他哪怕保持长久的沉默,也不喜欢学羊咩咩叫。他的脖子上没有拴过绳索,但是他不自由。他总是被关在透明的玻璃罩子里运来运去。他的身边围满了人群,闪光灯让他看不清楚太阳。他好像聚焦了世人的目光却感受不到任何快乐。
有一天,他为了寻找母体而出走,他来到了夹修沟。他在那群瞎了眼睛,嘴里流着涎水的羊群中是唯一眼明口净的羊。当然,这些都不是最要紧的,他惹起众怒的事,是他总不跟着领头羊,领头羊走过的路,他都不愿意去走。这不是标新立异或者出于其他什么理由,这是一种来历不明的基因,他自己也决定不了。所以在羊群中,就算他不去抢食,他也总是被排挤,因为在相同的族群里,与众不同就是与生俱来的罪恶。
在夹修沟的斜坡上,他想安静地躺一会儿。有一朵云吸引了他,他觉得那绵软的云像极了他记忆中母亲的胎盘。他忍不住高兴地叫出了声:“看,我找到我母亲的胎盘了。”
从古至今,羊族都说天上的云是他们的神明,这是祖祖辈辈形成定论的事,没有人敢说其他。何况胎盘在羊群的认知里是肮脏到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物体。多利不仅不知天高地厚地捅破了约定俗成的规矩,还亵渎了神明。羊群容不得这样特立独行的存在,他们更不需要刨根寻底的同伴。正如习惯了混沌宇宙的天体最害怕闪耀的流星。
于是羊群中两只秉持正义与律法的公羊就用犄角来顶他。他不知道那些路都认不清的瞎眼羊,怎么能在伤害同伴的时候那么准确无误。他没有反抗,因为他还没有长出犄角,他不知道拿什么反抗。那两只不怀好意的羊把他顶到了悬崖边,他的脚跟一下没有立稳,就掉到了悬崖下面。
他莫名其妙地接受了羊群的审判,他想他是必死无疑了。可是悬崖下面有厚实的草木叶,他重重地摔在绵软的枯叶上,并没有感到疼。起初他沮丧极了,他不知道为什么同伴将自己置于死地,他躺在树叶上想了一天一夜也没有想明白。但是他明白他是不属于夹修沟的。
他的辘辘饥肠把他从沮丧中唤回。他在晨曦中走呀走,天上那些绵软的云在指引着他,他要去寻找一些松软的泥土。那些沾着晶莹露珠的嫩草朝着他摇头摆尾,他俯下身就完全能够饱腹。但是饥饿中的他仍然对草没有任何食欲。他顺着太阳照耀的地方继续走,他遇到了山谷里开放的野百合,在荒无人烟的早晨散发着香气。他遇到了在树上吃野果子的尖嘴鸟,告诉他早起的鸟儿并不是都喜欢吃虫子的事实。他也看到才冒芽的新笋长在夏天,慢节奏地生长着,不怕春笋的嘲笑……
泥土散发着厚实的香气,他吞了一口又一口,就像人类依赖的米饭,醇香厚实。青草吃进羊群的肚子里,只能消化成粪便,而泥土融进多利的肚子里,他相信能够长出千百万的内容,这就是他一直不吃青草的原因。
他顺着泥土湿润的空气走,坚信能遇到水源。果然没走多久,他就听到了泉水叮咚声。他饱饱地喝了好几口,相信水土是相互成就的,他的身体一定能长出树来,开出花,结成果。他顺着云朵的方向走呀走,一直走到了山巅,在离天最近的地方,他终于睡进一朵云里,舒适安稳,温暖自由。
在这片新的土壤上,没有一点质疑和嘲笑,鸟有不飞翔的自由,树有不生长的权利,小溪可以向西流——只要它愿意。多利是一个新的物种,但是他并不孤独,他从掉下悬崖的那一刻开始,就没有再打算回归羊群。
【作者简介】文富丽,生于1990年,贵州省赫章县人,彝族;自由写作者,《失群的多利羊》系作者小说处女作;现居贵州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