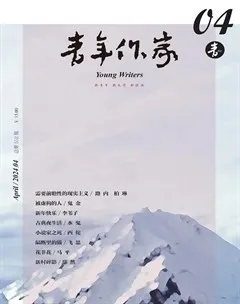风与太阳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有可能是虚拟的。包括熊熊燃烧着的太阳。
一个人的一生,也很有可能是一场看似漫不经心的刻意表演。
农历癸卯年闰二月的某一天,在太阳西北方,一条成形的日珥正渐渐凸起,随后,悄无声息地向太阳系内空间抛射。
那些带电粒子、射线,宛如梦境,不能被人的肉眼所直接看见。
二月兰已经从泥土里冒出来。小小的紫色花瓣,一簇簇开在青嫩的草叶之间。大风呼呼地刮着。天气预报说,从内蒙古阿拉善沙漠吹来的黄沙,已于昨晚入境。
前方,那个熟悉的身影又出现了。我心想:是她吗?那个总是穿戴整洁,每回都会推着一个塞满纸壳的超市手推车,远远望去,显得特别干瘦的拾荒老人——说得俗一点,那个捡垃圾的老太太。
就在我不确定之际,一只野猫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突然窜到脚底。我摘下眼镜,下意识地用手擦了擦右边模糊的镜片,当我再戴上时,视线反而更加不清不楚了。
霎时,一个小男孩儿用手帕认真擦拭地球仪的背影,浮现于脑海。与此同时,我还听见了一个年轻女人刺耳的催促声:别擦了,别擦了,上学都要迟到了。
女人左手握着一听易拉罐啤酒,右手扶了扶左侧肩膀耷拉下来的吊带。
那是年轻时的母亲,与父亲刚离婚不久。那一年,我十一岁,即将小学毕业。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手中擦拭的那枚地球仪非常袖珍,只需用手指轻轻扒拉一下,它似乎便能迅速带我去往远方,暂时忘记发生在身边的一切烦恼。旋转的地球仪,像是吉普赛女巫的水晶球,双手在球体两侧神秘挥动,我便能催眠般地进入到一种自我对话中:
沉沦简直易如反掌,譬如花钱买醉,并将夹着一根廉价香烟的手指靠近嘴边吞云吐雾。
那,什么才最难呢?
人间清醒呗。准确讲,试图活在清醒的常态里,将清醒视为一种人生至高无上的选择,难上加难。
何出此言?
你想啊,多数人根本就无法做到永远保持清醒。一个人想要活得快乐些,明白里总得揣些糊涂嘛。
在突然使劲蹬了一脚后,我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
莫非,是又做梦了吗?是醒着,还是仍在梦中呢?
我把头一歪,望向紧闭的窗外,隔着玻璃,看见疯长的杨树叶片,哗啦哗啦,没有声响地快速抖动着。
心想:这风,得有多大啊!
我开始犹豫还要不要出门。每逢周末,去北京周边走走,已经成为我的一个习惯。就像有人去奥森公园跑步,有人选择到植物园逛逛是一样的。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还是爬起床,以最快的速度洗漱完毕,揣上钥匙,下楼。
今天是星期日,在一条通往近郊铁路的小径上,许是时间太早,除了我,尚无一人。我一边踢着马路牙子旁的碎石子,一边无所事事地吹着口哨疾行快走。
咦?奇怪!道路两旁的树干,上一周还光秃秃的,今天怎么就突然窜出来几片嫩叶了呢?
恍恍惚惚中,只见一个年轻男人正站在墙沿,踮起脚,用一把头上绑有弯刀的长木棍去钩它。
按照儿时的经验,这几棵树,应该是香椿树。
我怎么又回到了小时候。那时的父亲,身形健硕,也热衷生活里的小趣味。
他是从何时开始性情大变的呢?就像是一棵香椿树,在一个春季里陡然发生的变化。
我停下脚步,站在树下,这才意识到是人生第一次仔细观察它。刚刚长出香椿叶的枝丫,像瘦长的手臂,伸向天空。它们离地面都太远了,我只能逆着光,眯起眼睛,把右手弯成一把遮光的小伞,挡在额前。我又进一步细细打量着那些光秃秃的枝丫,仰着脖子,就这样看啊看。忽然间,竟然觉得好饿,紧跟着口腔里开始分泌出一股充盈的唾液,我下意识地清了清嗓子,只听咕咚一声,那些黏稠得都能拉出丝的口水,经过喉咙,被我咽到肚子里。
难道,是我又下意识地想起了许多年前点外卖的那一晚?
此时,我再一次看见她的脸。布满褶子的脸,像极了时下年轻人酷爱吃的千层蛋糕。尤其是嘴角,更加细小的皱纹抽到一起,宛如弥勒佛手中布袋子的束口处。
我想了想,真是好久没有见到她了。
看见道路两侧长势喜人的香椿树与二月兰,我确定,困扰我一整个冬天的梦魇,已悄悄地消散了。毕竟,只有自己知道,为了摆脱病症,我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喝酒,戒酒,然后再喝,再戒。这和当年酗酒的母亲又有什么不同呢。然而就像每一个整天口头上喊着要减肥的人一样,戒酒总是以失败告终。但是这一回,我庆幸自己又成功上岸了。
走着走着,脚尖好像踢在了什么钝物上。低头一看,竟是一颗圆溜溜的松塔。
共享单车的轮子、井盖,此时风中一轮灰呛呛的大太阳,无一例外,它们在某种层面讲,都是一个圆圈。我的脑海中隐隐地浮出“怪圈”这两个字。紧接着,更加离奇的一幕发生了:只见捡垃圾的老太太突然停下脚步,从手推车里翻出一把利剑,独自一人,陶醉地舞起来。而且地上不知是谁用树枝摆出飞机格,连大风也没能把这些干枝子吹跑。我想,没准儿是一对儿神经错乱的喜鹊干的吧。不知怎的,冥冥中,我感觉推车的纸盒里还养着两只蚕,中间用一张卡片隔开,另一半里,住着一窝密密麻麻的蚂蚁。
视线渐渐模糊,我仿佛看见了一个老头在小区公共健身器材上伸懒腰,并问我:对了,你还记得我的长相吗?还有,你觉得我今年有多少岁了?
……当当当,一阵金属的敲击声持续传来。不知是谁家的熊孩子在没轻没重地敲着暖气片。我坐在卫生间的马桶上,这才回过神来。
他很淘气。可以说,与我的性格截然相反。
第一次见到他,是离婚后的母亲再嫁,法官把我判给了她,她带着我来到新家。
开门的正是他。母亲轻轻推着我的后背,试图让我向前迈一步,并催促道:叫哥哥,快叫哥哥。
我看着那个没用正眼瞧我一眼的男孩,根本无法叫出口。
他比我年长五岁,名叫王少祎。
渐渐地,俩人熟了后,他才告诉我,我们初次见面时他那张臭脸背后的故事。
一年前,他发现了平日里那个在他心中威严的父亲和一个陌生女人的私情。他从安装在手机里的一款家用监控App里发现了这事。原本,他只是要查看一下小猫的动态。
App里陌生的女人不是别人,正是我的母亲。
是母亲先提出来,要与父亲离婚。
开庭前,父亲叮嘱我:记住喽,如果法官问你想跟着谁,就说妈妈。
于是,十一岁的我,变成了十六岁的王少祎的弟弟。
那时,他已无心再继续读高中,而是选择到小城郊外的一所技校上学。学校是寄宿制,他寒暑假也不怎么回家。
一次偶然间他发现,把同学拆开后的快递纸盒当球踢非常过瘾。当寝室其他人都去上课时,旷课的他坐在别人的床铺上,将脚下的小纸箱踢来踢去。发泄得还不够尽兴,便双脚站在纸箱上,狠狠地往下踩。伴随着一股无以名状的快感,既解压,又开心。
于我自己而言,我们初次见面,因刚刚接触,彼此并不熟络,那个暑假里,我大都闭门不出,关在新家看电视。其实也不是真的在看电视,而是把手机视频里一部非常古早的电视连续剧《再世情缘》投屏到继父家客厅的一面墙壁上观看。故事讲述了玉琳国师与皇宫里一位格格前世今生的爱情故事。当其他男孩子在户外疯玩时,我却更喜欢安静地坐在家中,看悲悲戚戚的爱情肥皂剧。
出于宅,或是懒,饭点儿一到,我总是点外卖。
从陌生人变成兄弟的最初半年,王少祎住校,他的房间、他睡的单人大床,便由我独自霸占。
次年春天,他回家的频次倒是比往常要多得多。
关了灯,我们俩挤在一张床上,各盖着一条被子,天南海北地神聊。几乎都是他在说。说着说着,没有了声音。我并无睡意,在没有全黑的房间里睁着眼,感受着躺在我身边的这个少年的呼吸。窗外路灯的光亮打进并未拉上窗帘的房间,微微照在他立体的脸庞上。我轻轻地翻过身,将脸枕在手臂上,静静地看着那副轮廓,不知不觉间,沉沉睡去。
天一亮,他便起床,牙不刷脸不洗,穿上紧身的运动衣裤与跑鞋,出门沿着小区外圈,开始跑步。据他讲,天气好时,迎面就是一轮璀璨的大太阳,倘若杨树叶挡在眼前,阳光便在树叶间来回地跳荡着,显现出好看的星芒。
没过几天,他开始怂恿我跟着他一块儿跑步。我说:我是运动白痴,别说跑,走路走多了都得呼哧带喘的。他说:那就走。走不快,就慢走。
我竟然真的开始跟着他一起晨练。
今天空气质量指数494,空气极差。然而我并没有犹豫,因为他说:今天要是再不去看,泡桐花准保被这大风全部吹掉。
原来,小区不远处有两棵泡桐树,在一连几日的浮尘天气里,淡紫色的泡桐花正在怒放。平时最讨厌写作文的他形容说,简直是花香扑鼻。
站在当年凝望过的同一棵花树下,已长得高挑帅气的王少祎蹲在地上,随便捡起一块儿小石头,又随手画了一个圈,指着问我:你知道这代表啥吗?
我表示不解,摇了摇头。
圈子!当然是圈子了。
人想要弄出个名堂来,就得在圈子里混。
此时,时间已经走过了整整十二年。他二十八,我二十三。
这一年春季,沙尘席卷着整座城市,包括我们俩十二年来所驻足的这处僻静之地。
不得不感叹,在天气面前,真是人人平等。在漫天的黄沙中,太阳的轮廓散发出一种幽蓝的冷光。
风太大了,沙尘蔽日,十二年来,太阳始终呈现出一种略带穿越感的冷蓝光。
我说:当学生多累啊!唉,可如何是好呢!
他问:咋了?年纪轻轻的就唉声叹气,这可不好。
我道:你说,人咋就会变老,变得不中用,越来越不自信了呢?!
他:就为这?
我:嗯。
我太向往自由了。越长大,越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我不喜欢被束缚,不论是进体制内,或是进朝九晚五的商业公司,周旋于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地度日,都不是我所热衷且擅长的。
本科毕业后,我选择在一家民营书店打工。准确说,是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带自习室的书坊。不知何时,书坊式的自习室在京城小区周围开设成风。我就在这家名为“上自习吧”的书坊兼职。办会员卡,整理书架,打扫卫生,偶尔在周末组织迷你型的读书活动。之所以称之为迷你,是因为前来参加活动的人数少之又少,常常是三五个人,或者干脆一个人也没有。
这不,今天又是无人参加。为了驱赶内心再次滋生的挫败感,我把自己所有钟爱的作家的书,全都藏在了柜子里的第二排。书架每一层的厚度都很深,为了节省空间,能够摆更多的书,我会在一前一后都码上。每次沮丧袭来,只有前排那些对于我来说可有可无的经管类图书,才会露在最外面。
工作之余,除了照顾书,我也偷偷写作。
他曾对我说:文人相轻。
而我还记得自己当时的回答:王少祎,你很危险!这一点,你自己清楚吗?
他并不清楚,我所认为的危险,是指哪个方面。
我说:是Mood(情绪的意思),是咖啡摄入量超标,是你每周去健身房的次数过多。
然后我又重申:莫非你不知道,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个度吗?
这不,他刚刚健完身,咖啡因在健硕的身体里依然后劲十足,加上他从小学一年级就变得越发古怪的坏脾气,他更加肆无忌惮地说着话。
说着说着,他甚至干脆骂起来,像是某天逃课,一个人待在技校的寝室,一边骂,一边狠狠地脚踩废纸箱。
咖啡的确是一种神奇的饮料,可以让人暂时亢奋。健身也有类似的效果,只是它是一种先苦后甜的奖赏机制,在经历一番自虐式的力量训练后,大脑分泌内啡肽,让人感受到快乐。
这就再一次佐证,所有的喜怒哀乐、嬉笑怒骂、迷狂疯癫,都是化学性的。当然,也包括偷偷地喜欢上一个人。
回想起自己的十一岁,那时真是特别不爱讲话。一说话脸就红,不知道是不是所谓的社恐。我一直认为,人一旦张开嘴巴,打开喉咙开始说话,肚子里提着的那股元气,便会一泻千里。
王少祎质问我:可是,你既然是人,不可能永远都不讲话吧。
他抱着好大一摞不同尺寸、形状各异,被他踩得歪歪扭扭的纸盒,没人知道,他靠着日复一日偷偷变卖这些废品,在一个学期即将结束时,竟然存下了足够买一个手机的钱。
没有人注意过,京城的柳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纷飞的。人们大都会在意工资的涨幅,鲜少会有人在意那些如雪纷飞的种子。
随风黏在一起互相抱团的飞絮,与挂满树叶的一排排杨树形成鲜明的对照。
颇为神奇的是,杨树底下虽然也有一条条宛若绿色毛毛虫的东西,但它们并未炸裂开,而是乖乖地服帖于树干四周,安静的状态像是一些不动声色的小动物。这些温顺的坠落物,是杨树的穗状花序。
我曾在书坊的一本书中读到,杨树花序开始掉落,就表示树要开花了。
我也曾在跟着他跑步的路上,注意到那些笔直向上生长着的大树,粗大的树干上,不知被谁标记上了“♀”这个符号。
相传,此符号源自古罗马神话,维纳斯是美神,容貌娇美,十分注重仪容,常常随身携带一把小镜子。
从技校毕业后,王少祎一直在一家健身房当私人教练。对此我曾表示过不解。按照专业对口,他不是该从事汽车修理的工作吗?
我甚至指责他:你该把你悸动的心用在正道上。这话说得或许不中听,但这是我真心想对你说的。假如正道这个词你不爱听,那就换成正途吧。真的,这的的确确是我想对你送出的最深祝福。
还没等我把话讲完,他却递给我一部新手机。
我傻傻地杵在原地。
就在我随母亲来到继父家半年后,她的一个秘密被我发现了。
那天,我正宅在家继续看《再世情缘》,后背突然感受到一股凉意,于是我站起身,想要把搭在椅背上母亲的外套披上,谁知从口袋里掉出了一包干瘪的香烟盒,又从盒子里,飘出了一张留有手机号码的小纸条。
我紧张地抽出最后一支烟,慌慌张张给自己点上。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抽烟。在经过好一番思想斗争后,我还是拨出了那个号码。令我万分诧异的是,这个手机号竟事先保存过,备注着:外卖,牛肉饭。
我一想,前天晚上大约十点,母亲说饿,让我帮她点一份土豆牛肉饭。而这个号码,不正是前来送餐的外卖小哥的吗?
我还记得,在我下单二十分钟后,手机铃响。母亲打开门,看见身穿黄色外卖服的年轻小哥,愣了好一阵。
走廊灯坏了,楼道漆黑一片。借着她打开的半扇门,屋里的灯光微微照在小哥的脸庞上,让头戴黄帽盔与口罩的他,看上去具有一种朦胧的氛围感。
过了半天,母亲这才接过他手中的外卖袋,吞了一下口水,颤颤巍巍地说了声:谢谢你。
他没有说话,转过身便匆匆下楼。
听着他下楼的脚步声,过了好一会儿,母亲才将门关上。坐到沙发上,母亲并没有撕开外卖封条,而是让我把手机递给她。
当时我还纳闷儿,后来我才搞清楚,原来她拿到我的手机后,顺着App的外卖订单,点开了联系骑手的对话框,打出:小哥,能加你微信吗?
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过去……发出去的消息一直显示未读。无奈之际,只能先撕开包装吃饭。饭早就不热乎了。她也已经没有了饥饿感。但心,却更加火烧火燎起来……
她把外卖一推,推到我面前,说:我不想吃了,你吃吧。
于是我带着一种说不上来的复杂心情,把那六个生煎包全都吃了。
如此,让我更加看清生父与母亲破败不堪的婚姻中存在的隐疾。
据我从小观察,父亲与母亲的婚姻,简直就是稀里糊涂地凑合,是一场互相伤害的自毁闹剧。
父亲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朝母亲嚷嚷,指责她没文化,说话不够温柔。
母亲确实没怎么念过书。高中毕业后,进厂当工人,直至下岗大潮来临,她被买断工龄,提前退休闲赋在家。有一阵,小区妇女时兴扭秧歌,她只扭过一次,回家后便被父亲一番奚落。她哭着说:我不去了还不行吗。我哪里也不去了,就挨家待着。
父亲不以为然,继续斥责她:瞧你那副德行!
无论她自己承不承认,你的母亲都长了一张老脸。这是王少祎的结论。他从来没有喊过她一声妈。他说:我这辈子,就只有一个妈。
他的妈妈在他上小学一年级时,罹患乳腺癌,晚期。她似乎预感自己可能随时会走。有一天,她把他叫到床边,从钱包里掏出三张一寸照片,故作淡定地用看似轻松的口吻嘱咐他道:来,来,小祎,把妈妈的这三张照片都收好喽。
母子连心。他何尝不知,妈妈这看似不经意赠送一寸小相片背后的潜台词:儿子,你把这些照片留好,以便日后不时之需。
果然,没过几天,三张小相的其中一张,被放大洗出来,作为遗像高悬于她的灵柩之上。
他说:后来我才发现,曾经读过的书,做过的各种积极的心理建设,当第一次真真正正面对至亲离开时,根本丝毫不起作用。于是我想,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就要力所能及地好好珍惜,不再试图去改变他们的天性。
王少祎的闪婚,令我措手不及。新娘是健身房老板娘,他们是奉子成婚,结婚后便关闭了健身房,办妥了出国手续,移民去了新西兰。
我的母亲说,他就是傍富婆。二十多岁,跟一个快四十岁的女人结婚,丢不丢人。
我虽然心里难受,但不许任何人诋毁他,情绪异常激动地驳斥她说:都啥年代了,啥丢人不丢人的。更何况,有人早在十几年前就丢人现眼过了。
她似乎心有所察,或许也并不明白我所说的丢人现眼暗指什么。
春天的风,自始至终刮个不停,让人的心乱糟糟的。
飞往南半球的飞机腾空而起。母亲与生父进京的火车即将进站。
怎么说呢,其实,我一点也不盼望着他们来。
话说,虽然快三年没有见过面了,心里总时时想念,那种轻轻地,像蝉翼一般轻薄的想念,淡淡地,却也郑重其事。但一听说他们要来,就感到一阵阵的心慌。
继父发现母亲与外卖员的事后,毅然与她离婚。她后来又与生父复婚。我却一直留在王少祎家,直至考上大学。
我想,一个人可以跟命运抗争,但他无论如何也没法违背自然规律。年纪是,身体的机能是,脑袋里面对往事钩沉的起起伏伏亦然。
人之所以需要睡觉,是因大脑会在睡眠时清除其中的垃圾,否则,人便会昏沉迟钝。
恍惚中,我好像置身在一处昏暗的卫生间。狭小的空间很干净,并且有一股好闻的味道,那应该是一款很高级的熏香。一股淡淡的松木味儿,若有若无,像是那年挤在同一张床上睡觉时王少祎身体散发出的味道。
一个半小时后,我乘坐的周边游的列车到站。
居庸关站。现在这里之所以闻名,除了长城,春天漫山遍野的山桃花也吸引了不少游客。铁轨沿山麓铺设,拐弯时,列车呈S型,广告词中有一句话这样写道——开往春天的花海。如此来看,并非徒有虚名。此时,许许多多的摄影发烧友,在远处瞭望台架起长枪大炮般的镜头,对准弯道,咔嚓咔嚓按下快门。
与快门声一道响起的,还有一阵唰唰的机械声,由远及近,渐渐清晰。
我抬头望向长城,一架有着格外硕大的螺旋桨的直升飞机,正掠过居庸关长城的一处烽火台。这场景似曾相识,好像是儿时在游戏厅打过的一个游戏中的画面,又像是梦中所感知到的一场星际战争来临前异常平静的前奏。谁知道呢!
风刮了整整一个白天,直到晚上才慢慢止息。
我似乎都要忘记,地球上的风,是因何而产生的了。
我只依稀记得地理老师讲过,是大气的水平流动,带来了风。
霎那间,我的脑海再一次浮现出那个推着超市购物车的老太太,小车里塞满了折叠整齐的纸盒,仔细辨识,像极了王少祎狠狠踏平的那一个个纸箱子。
捡垃圾的老太太嘴周密密匝匝的皱纹团缩着,往一处挤着。那是地心引力的方向。是不可拖拽的时间轴的一个瞬间。有一天,我也会跟她一样老,老到细胞端粒无法再复制,老到生命终结。
注意到她,是在一个海棠花开的春日,我出门倒垃圾,因粗心大意,把手中攥着的家钥匙一并丢进了垃圾桶。垃圾桶就在那棵怒放的海棠花树底下。正是她,不嫌埋汰,一句话也没说,低下头帮我寻找起钥匙来。
海棠花让我不禁想起粉紫色的泡桐花。那天清晨的天特别美,或许是刚刚刮过风的缘故,天上的云,呈现出一条条长长的丝带状,让人误以为这是站在木星仰望天空。
无论对地球来说还是木星而言,它们,无非只是一颗寂然转动的星球。无论上面有没有人类,植被繁茂还是荒芜贫瘠,它仍旧在某种原动力的驱使下,亘古不变地转动,似乎被游戏玩家设定了程序一般,以致我常常感觉此刻脚踏实地的星球,以及伸出双手所触摸到的人类的光滑肌肤,都是虚拟的。
虚拟?虚拟又如何。面对爱,不还是一团糟。
不,并不。
只要你做好准备,遇见对的那个人的那一天,迟早会到来。
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人吧。温暖你,照耀你。
还有,暂时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就去感受风。
Day Dream,Day Dream,我一边哼着歌,一边仍旧做着我的白日梦。
我有一种隐隐的预感,觉得自己的人生不会太糟。
我躺在沙发床上睡着了。睡得特别酣畅,以至于在入睡时,身体深深记下了这份高质量的睡眠。当我醒来,脑袋里有一种如同机械大修,被扳手拧过松动的零部件之后,既紧实又迟钝的感觉。应该是做了许多梦,在即将醒来的时刻,密集地梦了又梦。有医学家说无梦才表示大脑得到了充分的休息。我不以为然。
就在宛若宿醉一般疲惫又清醒的状态里,我迎接着新一天的到来。
【作者简介】鲍磊,蒙古族,1982年出生于内蒙古赤峰市;文学硕士;作品发表于《民族文学》《小说选刊》等刊,著有长篇小说《夜照亮了夜》《青春是远方流动的河》《幻海》,短篇小说集《飞走的鼓楼》;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