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音乐出发,走到文学尽头
洪高瑶
音乐和文学的结合实际早已司空见惯,无论是何种文化背景的音乐。这实际上代表着两者本同源。古希腊音乐是神话的反映与写照,后来的许多西方作曲家的作品中也得见于文学作品的浸染与取材选用。回望中国音乐的历史,从诗歌到戏曲,千百年来文学与音乐始终自成一体。
后来随着艺术发展,音乐与文学的含义分割为不同的对象和领域。艺术学科的细化分类揭示着艺术门类的发展,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进步也意味着某种联系的弱化与倒退,即音乐与文学内在联系的消减。所幸,两者的联系并未因此被完全忽略。
此前,作曲家黄安伦根据王立平为1987年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所作的同名配乐改编的小提琴协奏曲《红楼梦》,由上海爱乐乐团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进行了世界首演。同场上演的还有黄安伦的《塞北舞曲》以及施尼特凯的《(非)仲夏夜之梦》[(K)ein Sommernachtstraum]与《果戈理组曲》(Gogol Suite)。
这是一场以文学经典为主题、以文学作品为缘起的古典音乐会。通过将传统的文本经典转化为听觉的音乐形式,实现文学与音乐符号媒介的跨越融合,从而带来对经典文学故事的诉说与身临其境的体验。从民族韵味底蕴浓厚的《塞北舞曲》开始,到缠绵悱恻的《红楼梦》别具一格的倾诉,再到施尼特凯《(非)仲夏夜之梦》中似梦非梦的“双关”以及《果戈理组曲》对乞乞科夫灵魂的叩问……“言有尽,意无穷”在每一个音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弦乐通过揉弦振动描绘着《红楼梦》中缠绵悱恻的念想;乐器及音区的转换渲染着情绪的突变,预示着文学故事高潮来临之际的紧张加剧;大鼓巨响后的余声轰鸣呈现着《红楼梦》最终一切皆空的悲剧。音乐交织出哀恸与悲思,诉说着繁荣似梦而过的空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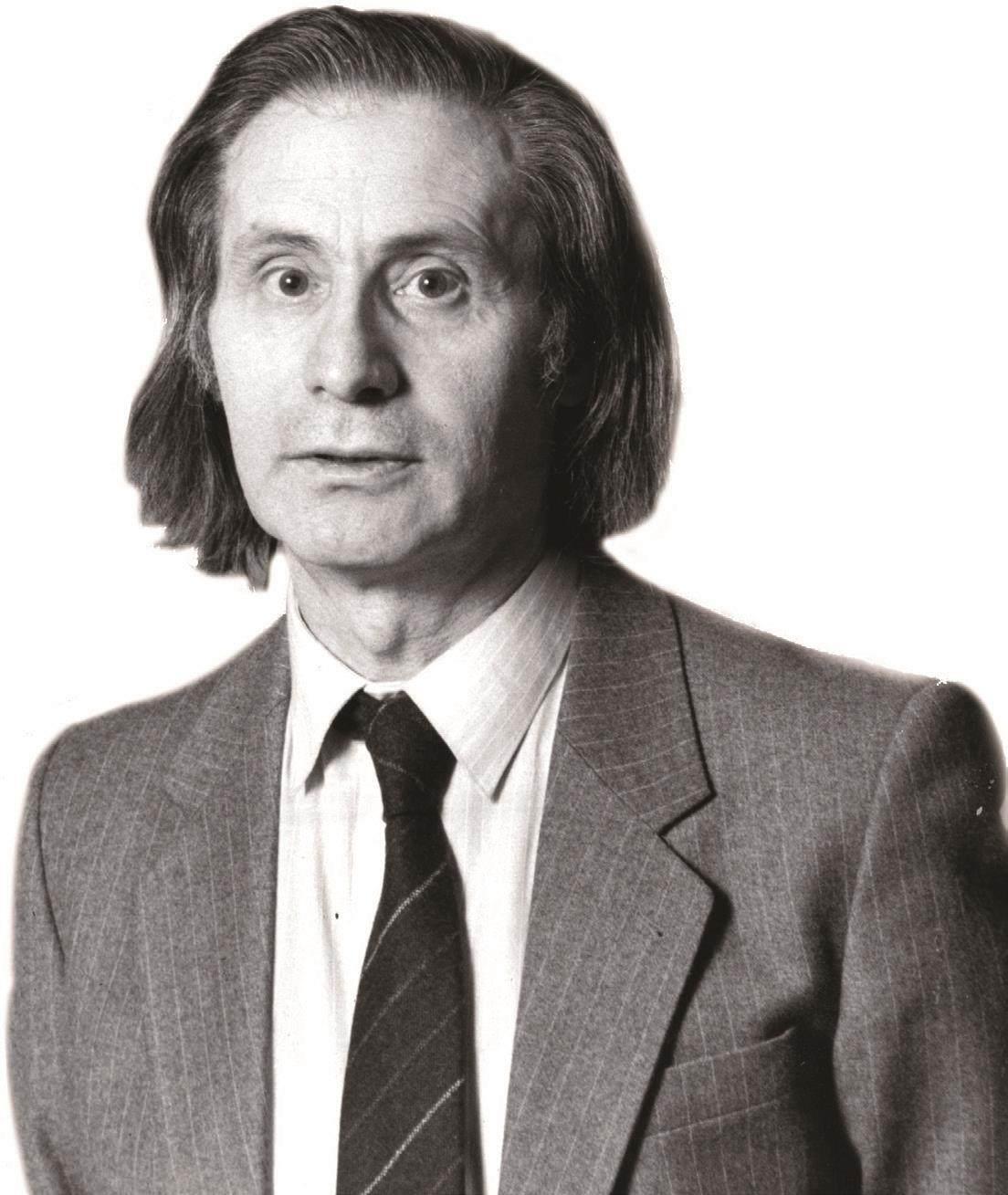
音乐是一种主观性的产物,因而对音乐的解读没有标准答案。正如英国音乐评论家科林·麦卡尔平所说:“音乐可以被视作一种表达情感的感性语言。”用音乐诠释文学作品,用抽象的乐音将小说文本具象、特定化的描述转化为独具朦胧美感的时间与空间的意象画面,既将文学意象和文字中的情绪传递给了听者,又在很大程度上释放了听者主观性的想象空间。
听者对于音乐符号的直觉性感知,有时比语言符号来得更为冲击与深刻。施尼特凯的《(非)仲夏夜之梦》似乎与莎士比亚并无直接关联,其开篇时的诡谲音响好似在极力撇清其与充满浪漫喜剧色彩的《仲夏夜之梦》之间的联系,但我们仍然可以从色彩幽暗的旋律中依稀窥见莎士比亚主题的内涵。
《死魂灵》(Dead Souls)的戏剧配乐《果戈理组曲》一开始便用刺耳的小提琴音响将听众带入了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巴洛克音调与现代主义音乐素材交融在小调无声无息的呼救中,交织出那个年代的黑暗与荒诞;哀鸣性的不协和音响嘶吼着,这是对时代和命运的挣扎……施尼特凯通过音乐的不断进行描绘出了一个古怪扭曲的超现实主义世界,映照出《死魂灵》中混乱横行的时空,也投射出果戈理作品中对现实的批判。
《红楼梦》与《死魂灵》是两部完全不同的文学作品,它们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文化背景,但当它们从有国界的文字语言被演绎为无国界的音乐语言后,国界与文化的界限以及东西方的语言隔阂在音乐中被打破,实现了文化的跨越与理解,使世界所共通的情感弥漫在音乐中,无声无息。
事实上,整场音乐会一直在试图模糊音乐与语言的界限、打破文学与音乐的边界,试图返璞归真,回到音乐与文学一体的形态。比如《果戈理组曲》中的第五部分是一段带有旁白的插曲,作曲家在此处的音乐中加入了一段无意义的念白,如同渗透在乐队中的一种人声织体,既是一种语言,也是一种音乐。音乐和文学的本质实际相同,都是叙事、写景或抒情的人为表达产物,只是书写织体不同,因而当音乐走到文学尽头时,呈现文学语言的音符便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与文字界限的模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