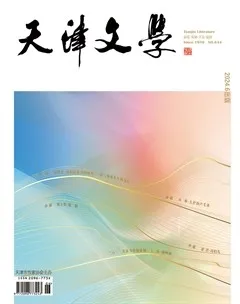失控的芦苇荡
一眼望去,芦苇荡像在天边,影影绰绰一个团。
父亲下巴扬了一下,说,那边。天色微明,父亲缓慢骑着自行车,我坐在冰冷的自行车大梁上。路上不见一个人,太阳还在地平线下,没有人这么早出来。车架上捆着两根鱼竿,后车架上夹着一个帆布包,里面装的主要是鱼饵及我和父亲的午饭,午饭是烙饼夹粉肠。
今天父亲允许我钓鱼。以前都是他一个人钓,我在旁边看,偶尔给父亲递个鱼饵、香烟、水壶什么的,屁颠屁颠很乐意干,一直待着无事可做,无聊得很。今天钓鱼不是往常去的那个地方,我觉得很陌生。空气中飘荡着一股呛鼻的气味,越往前走,气味越重。相距不远,与芦苇荡平行的一条线上,有一片建筑群,几根大烟囱,高耸入云,大烟囱下,若干庞然大物高炉般矗立,呛鼻的气味就来自那里。那片建筑群比芦苇荡清晰多了,但我和父亲不去那里,是奔向并不清晰的渺小的芦苇荡。过了不长不短的时间,我闻到了水草的腥味,呛鼻的气味也更重了,我知道离芦苇荡不远了。父亲没钓鱼。到了芦苇荡,他从后车架的帆布包里,拿出的没有一件是钓鱼的工具,鱼钩、鱼漂、鱼兜都没看见,只有鱼线和钓鱼有关。不钓鱼来干什么?父亲把一只筷子粗细的蚯蚓,穿在一根铁丝上,吊在长长的鱼线和鱼竿上,向芦苇深处走去。父亲的身影隐没了,鱼竿在芦苇尖梢上,一上一下钟表似的摆动,摆动一会儿,停住,过一会儿,继续摆动。太阳悬在半空,父亲从茂密的芦苇荡出来,两个裤管湿了,把一个面口袋一样的兜子扔到地上,拿起帆布包再次钻进芦苇荡。兜子里像有很多只拳头向外击打,不用看就知道,肯定是蹦蹦跳跳的青蛙。青蛙很耐活,到了家也死不了,不像魚,到家后剩不下几条活的,所以,不用太费事,简单刮刮鳞,清除肠肚就可以上锅烹饪了。青蛙烹饪得剥皮,像香蕉一样,剥掉皮,露出里面鲜嫩的果肉。给活蹦乱跳的青蛙挨个剥皮,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父亲每次钓青蛙回来,都一个人关上门,在厨房自己鼓捣,我不敢看,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大烟囱和高炉一样的庞然大物近得如同在眼前,吐着清幽幽的蓝烟,奇怪的是,如此之近,那种呛鼻的气味,却没那么重了,仔细闻才闻得到。父亲半天没动静了。面口袋躺在地上,里面的青蛙一跳一跳仍很欢实。我盯着浓密的芦苇荡,一直盯着,想象着父亲从里面出来,帆布包里肯定又有不少活蹦乱跳的青蛙。四周静得很,只有风吹过后,芦苇互相撞击的哗哗声。我有点儿紧张了,伸长脖子向远处张望,想在芦苇梢儿上,看到父亲一上一下摆动的鱼竿,看到了心里才会踏实。我好像听到父亲喊我,声音来自较远的地方,夹杂着风声,声嘶力竭的。我向芦苇深处跑,坑坑洼洼,深一脚浅一脚,几次摔到水坑里,呛得晕头转向,浑身都湿透了。越急越找不到,我高声喊父亲问他在什么地方。父亲声音飘忽,几近失真。我跑得过猛,没收住脚,险些扑到水里。父亲趴在水边,双臂已浸进水里,头奋力向上扬,双手紧紧攥住鱼竿,鱼线笔直地绷着,像一根细铁丝,插入水下。父亲的身体一点儿一点儿继续向水中滑去,一只鞋从脚上脱落。我慌忙从后面抱住父亲的双腿,用力向后拽。父亲就势调整了一下姿势,往后收鱼竿,鱼线与鱼竿拉成了一条直线,我和父亲一起拖拽水下那个疯狂的家伙。我从未见父亲如此紧张和狼狈。以前父亲钓着大鱼,都沉稳得很,站在岸边,双手握住鱼竿,顺势来回遛,无论多大的鱼,都有精疲力竭的时候,到那时,用抄子轻而易举就把鱼抄上来了。这次情况与以往截然不同,鱼线不是上下前后左右移动,而是像个秤砣,直直地往下坠,这让我和父亲既紧张又恐惧。很快,我和父亲全身都沾满泥水,尽管拼命往后拉拽,可泥泞湿滑的河岸,使我们徒劳无益,原地打转,甚至慢慢滑向水里。我抬头看父亲,父亲没有放弃的意思,他大声喊道,抓住,别松手,千万别松手!我抬头看父亲的时候,看到了天空,有朵朵白云,白云下面有一缕蓝烟,比刚才厚了浓了。看情形,如果这样下去,我和父亲会不可逆转地被拖进水里。我不敢想象,被拖进水里是个什么结果,父亲不会游泳,我只会一点儿“狗刨”。但在我心中,比溺水死亡更大的是恐惧,难以言状的恐惧。我们遇到了什么?我希望父亲放弃算了,不过一根鱼竿和一段鱼线。可父亲就是不撒手。我不知道父亲到底是舍不得鱼竿鱼线,还是好奇心驱使,非要一睹水下这个家伙的真容,还是吓蒙了,完全是下意识的自我保护动作。
父亲上半身差不多全浸在水里了,呛了好几口水,剧烈咳嗽。绝望之际,我有过撒手的念头,但只是一闪,我怎么可能置父亲生死于不顾,眼看他滑向恐怖的深渊?我用更大的力气,向后拉拽。右大腿突然一阵疼痛,一块锐利的石头,硌在大腿上。我像一下抓住了救命稻草,紧闭双腿,用力夹住石头,我和父亲止住了下滑。但疼痛加剧,疼出了冷汗,冷汗和泥水搅到一起。水下的家伙遇到了强有力的阻力,更加拼命挣扎,这个畜生每挣扎一下,我和父亲都在泥沼中抖动一下,顺着鱼线,从黑漆漆、深不见底的水底,传导着势能,也传导着恐惧。我和父亲精疲力竭了。这个时候,我和父亲随时有可能被拖进水里,和被遛得精疲力竭的鱼相同的命运,只不过一个被拽出水面,一个被拖进水里,同样毙命。这块裸露的石头救了我和父亲的命。父亲的一只脚触到了石头。这于我是个极大的鼓舞。我用尽全身力气,拉父亲的腿,父亲的那只脚勾住了石头,石头是个牢固的支点,我和父亲稳稳地撑住了。父亲回头看了我一眼,双手往后拽鱼竿,我心领神会跟着父亲往后拽,仍很费力,但比刚才省力多了,这畜生也乏了。鱼竿缓慢往后退。在鱼竿与鱼线交界处,费了一番周折,似乎它在水下清晰地观察到上面的情况,眼看时日无多,做最后的挣扎。鱼线再度绷紧,像琴弦一样,猛烈震颤起来。我和父亲措手不及,险些脱手。我们迅疾反应过来,我抓牢鱼竿,父亲抓牢鱼线,并缠绕在手上。有石头做支点,我和父亲不再担心被拖入水中,可以全身心地拖拽那个畜生了。我竟可以慢慢往后挪动了,四肢也活泛了,一只胳膊抱住了石头。父亲的一只脚仍然勾着石头,不是被动地勾,是主动用力撑,这样做有明显的效果,另一只脚也有了站起的趋势。
下雨了,噼里啪啦,疏疏落落,雨滴却大,沉重地砸在水面上,溅起密集的水柱。水下似乎平静了。鱼线仍沉甸甸的,少了些狂躁,似乎心平气和了。我从地上蹲了起来。父亲半蹲着,一只脚卡在石头后面,一只脚撑在地上,与我平行了。我和父亲对视了一下,一起往后退,力道持续减弱,渐渐脱离开岸边,到后来,几乎可以站立起来了。看来,不会遇到像样的抵抗了,也许上岸前,再做最后一次挣扎,但强弩之末,不会造成多大麻烦。快出水面了,很快就会上岸。父亲的感觉很准,每当这个时候,父亲一边盯着水面,一边弯腰拿起抄子,瞄准机会一蹴而就抄起“战利品”,干净利索,一气呵成。父亲提醒我抓牢鱼竿,他腾出一只手,弯腰抓起刚才忙乱之中险些被踢进水中的抄子。到最后时刻了。没有出现翻滚的水花和哗哗的水声,这是离开水面前最明显的标志,什么都没出现,它已经毫无抵抗之力,一切应该很快就会结束。我甚至松开一只手,那只手的掌心勒出数道血印,血肉模糊,我竟没觉出疼,除了麻木没有任何感觉。我在空中甩着那只伤痕累累的手,又看到了蓝烟,比刚才又浓重了一些,几个大烟囱同时冒烟了。父亲拿抄子的那只手伸向了岸边,已经着手做收尾工作,他侧头在肩头上蹭了一下,雨水和汗水让他的视线有些模糊。
雨停了。水面如镜。四周寂静无声。
长长的鱼线,逶迤拖曳在岸边,潜在水里的一截,已经很短了,无声无息,像坠着一个本就无生命的物体。想不到,危机这个时候发生了。没有任何迹象和征兆,地上的鱼线急速向水中蹿去,发疯似的,像空中的风筝,突然断了线,风筝和线瞬间随风飘走。我和父亲重新被拖回岸边,父亲险些栽到水里,像是谁在背后踹了一脚,我啪地摔在湿滑的地上,鱼线脱手了。我慌忙爬起,抓住鱼线,如同有一把刀子从手中划过,火辣辣地疼。我顾不得那么多了,我想好了,哪怕被拖入水中,也不松手。我有点儿喜欢上这个畜生了。我和父亲摆开决战的架势,最后一搏,双手攥紧鱼线,岔腿,后仰,像拔河一样,再努一把力,中心点就过来了。它没有多大尿了。胜利在望。预想中的情况没有发生,鱼线忽然松了,手上的劲道一下泄了。我和父亲顺势往后退,退的速度跟不上鱼线松的速度。令人惊异的一幕出现了:一个黑家伙慢慢爬出来,嘴先拱出,扁平状,张开,井口般大小,似刚睡醒,打个哈欠,又像憋闷久了,喘口粗气,瞬间闭上,喷出满嘴腥臭。小炕桌大小,通体黑亮,如同裹了一层沥青。我大骇,张着嘴,呆住了。黑家伙眨了一下眼,看见了我和父亲,父亲也呆愣在原地。黑家伙微微动了一下,突然跃起,将我和父亲掀翻,从我们身上踏过,腥臭的黏液劈头盖脸落下,几乎让人窒息。黑家伙向后蹦去,一跳一跳,水花四濺,大地发出沉闷的声响。它渐渐远去,我和父亲方缓过神,是只青蛙,小炕桌大小的巨大的青蛙。
我坐在飞奔的汽车里。车速肯定非常快,窗外的景物是光和影,飞速向后闪。我眩晕得要吐。我搞不清坐在车的什么位置,只记得拼命踩刹车,腿伸直了,脚也绷直了,却怎么都够不到刹车踏板。我在车里前仰后合,东倒西歪,像个元宵被摇来摇去。整辆车就我一个人,驾驶座是空的,方向盘无人操控,左右旋转,灵活自如。我惊骇得要命。街道很窄,密密麻麻挤满行人和车辆,车飞速穿行其间,如入无人之境。我听说有一种无人驾驶汽车,没有司机,汽车自行在马路上奔跑,遇行人和车辆自动躲避,遇红灯停,该拐弯拐弯,该调头调头。我的车不是这样的。我的车有十多年了,是个老车,快报废了,有若干处剐蹭和伤痕,发动机声音越来越大,仿佛猛兽的低吼,怎么可能突然变成无人驾驶这种高度智能化的车呢。记得十多年前提车时,刚坐到驾驶座上,钥匙还没打着车,方向盘就开始旋转,向一边旋转,转速非常快,车却纹丝不动。我吓坏了,赶紧跳下车,说不要了,要求退款。卖车的老板不说话,眼睛直直盯着我。他胳膊上文着一条青龙,看着挺凶,我不敢再说什么,把车开回了家。说来奇怪,方向盘竟老实了,没再瞎转。以后十几年里,车一直正常,哪儿都正常,当然方向盘也正常。
车在飞奔过程中,我在想一个问题。我肯定想了,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在想我什么时候上的车,为什么没坐在驾驶座上,想了半天,什么都没想起来,前面那段记忆是空白,我从一开始就在飞奔的汽车里。我什么都没想起来,与当时的情形不无关系,人在惊吓中的思维是不专注的,很难集中精力想清楚一件事。遗憾的是,那以后的事我也什么都没记住,车就那么一直飞奔着,像一匹狂奔的野马。我惊恐万状。我在直冲地面的过山车里,我在失控下坠的电梯里,我在万米高空即将坠落的飞机里。心悬在半空的感觉,我算是真正感受到了。物理学上的自由落体运动,重力加速度,就这样坠向无底无边的深渊。
我和老张被轰出门的时候,我感到极大的耻辱。堂堂两个警察,没受到热情招待便罢了(哪怕表面装出热情),连个好脸都没有,竟明目张胆地冲我们喊,可着这条胡同哪家待见你们?赶紧滚出去!我和老张就出来了。我非常吃惊,老张竟然一句话不说,也没有任何表示。我刚分到派出所,老张带我,以后就接管他这片居民区。上面来了通知,要求收缴管制刀具,老张说王进这小子经常打架,保不齐有“货”。没想到碰了这么个钉子。我确实感到了耻辱。如果当时老张一声令下,哪怕给我使个眼色,我都会毫不犹豫把王进扭到派出所,我相信老张和那些老警察,有的是招儿“教训”这样的狂妄之徒。老张平时咋咋呼呼,这会儿却毫无作为,我一下看低他了。我记住了王进。也就是说我盯上了王进。我相信,就王进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总会让我抓住什么把柄,到那个时候,还不定谁滚出去呢!机会来了。治保主任向我反映王进抢了一辆自行车,还踹了骑自行车的一脚,踹到裆上,那人躺在地上半天动不了。是一个居民向治保主任反映的,这个居民和王进住一条胡同,斜对门。那一年正“严打”,这可是个重要线索,非同小可。老张已经调到分局,我开始独立工作了。就是老张不调走,我也不想找他,“包”一个。我立刻向所长老程做了汇报,老程非常重视,派了一个有经验的老民警配合我办案。先调查走访,掌握了一定证据后,王进被传唤到派出所,无论问什么,无论怎么问,死鱼不张嘴。我死盯着他,他死盯着我,彼此心里明镜似的。我忍不住想上前“教训”王进,老民警看出来了,冲我使眼色,在纸上写了一行字:他正等着你动手呢。我真该感谢老民警,那天我要是真动手打了王进,一切就全完了。最后,王进熬不住了,撂了。接着,判刑,注销户口,遣送劳改。走的那天,我到火车站“送”王进。我不是专程“送”王进,市局统一组织押送一批犯人,我和派出所的几个同事,被临时抽调协助工作。一队犯人从汽车上下来,被押上火车,两边是荷枪实弹的战士。王进在犯人队伍里,我们几乎同时看到了对方。他直勾勾盯着我,我直勾勾盯着他。王进登上火车,在车厢门口,回头又望了我一眼,嘴角翘了一下,好像是在笑,然后隐没在车厢里。
王进走了以后,我去过他家几次,他妈在家,问他给家来过信没有,他妈说没有。我和老张第一次去王进家,就是他和他妈在家,王进对我和老张的态度,很让他妈过意不去,给了王进一巴掌。我和老张出来时,他妈把我们送出大门,一再道歉,这王八蛋不懂事,缺家教,别跟他一般见识。我听治保主任说过,王进的父亲早就死了,在焦化厂上班,出了事故,炼焦炉爆炸,连尸首都没找到。
以后,我也调到分局,王进家那片又换了一个民警负责。偶尔,会碰到老张,有一搭没一搭聊两句,也聊到过王进。老张问我,王进判了多少年?我反问,你不知道吗?老张说,我怎么会知道?他被抓时,我已经走了,是你办的案子啊。我说,王进的案子我调查完,就送分局了,分局预审完报检察院,检察院起诉到法院,最后判多少年,我还真没打听。老张不满地看着我,说,怎么可能?
天黑很长时间了,我爱人还没回来。午觉后,她带着孙子一起出去,说是到河边玩一会儿,晚饭前回来。今天休息日,儿子、儿媳带着三岁的儿子回来,进门比较晚,近十一点,做饭来不及了,随便叫了点儿外卖,对付着吃了午饭。午休后,儿子、儿媳说要吃饺子,开始剁馅儿忙活,对我爱人说,妈,您带孩子出去玩吧,省得他在家折腾,晚饭之前回来就行。我坐沙发上抽烟,看电视,电视节目没意思,关掉,下楼看下棋。看棋的比下棋的人多,围得水泄不通,谁都想支招,出主意,结果每走一步都十分困难。就这样闹闹哄哄不知不觉三个小时过去了,我赶紧往家走,该吃饭了。我以为我爱人和孙子早回来了,进门一看没见着人,问儿子,你妈他们还没回来呢?儿子正往桌子上端凉菜,说应该快了吧,工夫不短了。爸,要不咱俩先喝着。我说,再等等吧。
我们谁都没吃饭,都出去找人。先到河边找。三个人分头向河两边找,走出很远了,也没找到。回来继续在附近找,大街小巷、商场公园都找遍了,不见踪影。儿媳咕咚坐在地上,呜呜哭了。儿子说,爸,咱报案吧!
报案后一直没消息。我打电话问了几次,所长说已经布置下去了,您放心,有消息第一时间跟您联系。所长是个不到四十岁的年轻人,他的前任的前任和我是同辈。半个月后,所长来电话了。在焦化厂附近的河边,发现了两具尸体,一老一小,一男一女。那条河从我家门前经过,绵延数十公里,至焦化厂附近,形成一个阔大的水面,水面周围生长着茂密的芦苇。我叫上儿子一块儿去辨认尸体,我怕我一个人扛不住。几十年了,这地方没什么变化,小时候父亲带我钓鱼时就是这个样子。焦化厂废弃多年,河边那片建筑群早已锈迹斑斑。尸体腐烂得不成样子。离尸体还挺老远,我就瘫软在地上了。尽管有思想准备,还是没扛住。两具尸体相隔不远,一具趴在水里,一具躺在岸上。
过了几天,分局那边给出了结论:失足坠河,系意外死亡。排除了自杀和刑嫌。我不相信。我当过警察,感觉没那么简单。我出了家门,走到河边,沿着河岸一直走下去。几十公里长的距离,我走走停停,边走边想,边走边看,想象着我爱人和小孙子在河边游玩的情景。河岸的栏杆不低,与一般成年人齐胸,这样的高度,对于一个个子不高的老年妇女和一个三岁的孩子,足够安全了。他们或走或跑,无论如何都不会失足坠入河里。那就是小孙子嚷嚷着要上桥栏杆玩,我爱人拗不过,抱他上了栏杆,失足掉进河里,她跳下救他,一起溺亡……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她怎么能任凭孩子任性,做出这种昏头的事情?我留意观察了,没有一个家长把小孩子抱上桥栏杆玩耍,谁都不敢在刀尖上跳舞。
河流像一道伤疤,从城市中间划过,蜿蜒向郊外流去。我沿着河岸,继续向郊外走,总觉得能发现点儿什么,以解心中疑惑。下午从家出来,太阳还老高呢,现在太阳已西斜,我没发现这条河与平时有任何异样。我一无所获。我知道河流的尽头,是有几根大烟囱和一片建筑群的焦化厂,我从未沿河步行去过那里。前面还有多远到尽头,我不知道,岸边有闲散遛弯的行人,但我不想向他们打听,我不想说话。我累了,腿发酸,大胯疼,岁数不饶人,退休后,明显感觉身体日渐衰弱。我转身往回走。还没到终点,就走回头路,原路返回,极度不适。但我确实不想继续往前走了,心中那个强烈的愿望,突然间寡淡了,索然无味。或许是我恐惧了。河流尽头,两具高度腐烂的尸体好像还在,难闻刺鼻的气味并未散去,噩梦般挥之不去。回家的路很熟,但我走得很慢,我不知道,回到家干什么。那个家现在就剩我一个人,出来进去都是一个人。儿子偶尔还来看看我,儿媳一面都不露了,因为那件事,两个人差点儿离了婚。不能怪儿媳,事搁在谁身上都受不了。
我进不去小区了,小区路口设置了路障,下面有轮子的那種,三角形,黑黄条纹,轻轻一推就挡在路中央。小区路口有几个戴袖标的人,天还不太黑,我能清清楚楚看见他们在路障前晃悠。我紧走几步,想尽快进入小区回家,还差两三步就进去了,几个戴袖标的人,慢悠悠开始推路障,长长的路障横在了路中央。我进不去小区了。我急切地说,我住里面,我要回家。几个戴袖标的人好像没听见我说话,双手交叉抱胸,站在路障旁边溜达。我问,出什么事了?什么时候放行?他们还是那个样子,好像我根本不存在,如同空气一样。我不想跟他们废话了,再说什么都没有意义。我抬起一只脚,想跨过路障过去,一只脚刚搭到路障上,另一只脚正要抬起,两只大手就从后面伸过来,粗暴地把我拽下来,我站立不稳,一屁股坐到地上。我愤怒地站起,要冲向那个把我拽到地上的人,那个人根本不看我,继续在路障旁边来回溜达,无所谓的样子。很多人围着我,冲我笑,路障两边的人都冲我笑,不是善意地笑,是恶意地嘲笑。没有人要通过路障,小区里面的人没有出来的,小区外面的人也没有进去的,里面外面,两边的人谈笑风生,对路障熟视无睹,旁若无人地走来走去。我知道他们为什么笑了,只有我一个人想通过路障,我是个异类,异类被嘲笑是很自然的。一开始,我对被粗暴地拽到地上,感到无比愤怒和羞辱。拽我的人非常粗壮,留着平头,而我身材瘦小,被拽到地上的时候,要不是我一只手用力撑着,肯定会翻一个滚。倘若我直接冲上去,不会占到任何便宜,会再次被拽到地上,等同于自取其辱。排遣窘境和自我解嘲的最好办法,是与羞辱你的人同流合污。我冲向那个戴袖标的壮汉,冲到一半,停住了,不再充满攻击性和敌意,我向他露出了笑容,温柔的笑容,那个人毫无反应。于是,我向围住我的人群笑,他们见我笑,笑得更厉害了,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我能感到我在笑,脸上有强烈的抻拉感,我还从未有这种感觉。突然,我周围的人不笑了,戛然而止,像没弦的挂钟,走着走着,咯噔一下停住了,笑容倏忽消失。我来不及反应,他们已经转身走开了,我有追上他们的冲动,我想对他们说,怎么走了?我还想笑,我还没笑完呢。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想笑,就是觉得他们都走了,心里发慌。周围恢复如常,路障两边的人相安无事,各走各的,谁也不搭理谁。有一个人在路障那边,也就是小区里面,闪了一下,就不见了。他本不会引起我的注意,他与小区里的所有人一样,溜溜达达地走过去,唯一不同的是,他的嘴角掠过一丝笑容,让我一惊,仿佛触电,身体震颤。那个笑容深深印在我脑子里,怎么可能会忘呢?我不管不顾又要跨过路障,进到小区里,去追那个嘴角掠过笑容的人。无疑,我又被那个戴袖标的壮汉拽到地上,这次摔得比第一次重多了,在地上打了两个滚。没有一个人笑,更没有人看我。我狼狈地爬起来,一头扎进拥挤不堪的人群。
刚进水里的时候,感觉很舒适,温度适宜,味道寡淡,稍有芦苇和鱼的腥味。我不敢睁眼,在水里睁眼,眼睛会淹得很难受,又涩又疼。平时游泳都戴泳镜,对眼睛是很好的保护,能很清楚地看到水里的一切。说老实话,我对进水里这件事,没有任何印象,是被人推下去的,还是我失足掉下去的,真的说不清。我倾向有人把我推进水里,我是很谨慎的人,不可能失足掉进水里。这样说来,我应该感谢那个人,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我都得感谢他,因为我在水里很舒适。我还是忍不住想睁眼,觉得不踏实,黑咕隆咚地在水里游荡,总担心撞到什么危险的东西。我试着睁开一只眼,没问题,没有任何不适之感,我又睁开另一只眼,感觉很好,如同傍晚的景象,余晖把世界染成金黄色,光晕下的一切是流动的。不解的是,我的呼吸也很正常,没有丝毫憋闷感,同其他浮游生物一样,在水中自如游弋。水中有各种生物,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在上面根本看不到。从上面看水下,混沌一片,是一个死气沉沉的整体。那些生物在我身边游走,有的在我身边逗留,用柔软的嘴一下一下“吻”我的身体,个别的也就算了,权当解闷,我觉得很有趣。成群结队蜂拥扑向我的,我就挥动双手把它们赶走,不然,我会感到紧张。我赶它们时,它们像一个云团,一阵风刮来,云团立刻淡了,瞬间四散而逃,无影无踪了。我虽不像它们那样自由自在地游动,但也没固定在一个地方,我漂浮在水中,手脚并用,像一只大螃蟹,把周围的水都搅浑了。我没有任何目的性。我不知道到底要去什么地方。
我努力回忆落水前的情形。我肯定是被人“弄”下水的,这点确定无疑,至于是被推下,踹下,撞下,都不重要,我关注的是落水前我在干嘛。是在钓鱼吗?好像不是,我对钓鱼已经失去了兴趣。那么,一定有比钓鱼更重要的事情,不然,无法解释我一个人何以来到这种荒凉的地方。我一边挥动双臂赶走身边的鱼群一边想,这不是多难的问题,可我就是什么都想不起来。算了,想不起来不想了。我把注意力转移到水中,像观赏风景一样四下张望,我看到了活物,也看到了死物。活物太多了,从长期钓鱼的经验看,我以为我都认识,现在看来,都不认识,水下的世界是奇妙的,水中的生物是奇形怪状的。死物呢,就更多了,死树,死芦苇,死鱼。是的,我在水中看到了死鱼,漂浮在水中或沉在水底。鱼在水中也会死吗?在水底我还看见了鱼钩,断了线的鱼钩,有好几个,鱼线拖曳在鱼钩上面,袅袅漂于水中。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水下总体还是清净的,安静的,超乎我的想象。我沉浸在愉快的享受当中。我想到别的地方看看。我活动一下身体,从立姿变为卧姿,开始做“远途”的准备。我这才意识到,我还穿着厚重的冬衣,里里外外很多层,紧紧将我裹住,奇怪的是,我没有感到行动不便和肌体寒冷,和刚入水时的感觉一样,舒适度丝毫不减。我从容伸展双腿,滑动双臂,看似臃肿不堪的身体,轻盈地游动着,或疏或密的鱼群,与我擦肩而过,悠闲得很,有跑单的,匆匆一闪,像一道光,不见了,匆匆忙忙的样子。我观察着水中的情况,偶尔仰起头,窥视(我能在下面很隐秘地看到上面,而上面却看不到我)一下上面的情況,试图从岸上发现点儿什么,特别是把我从上面“弄”下水的人。从暗处向明处张望,是容易发现问题的,因为对方毫无警惕。
我落水这么长时间,都没浮上来,肯定死了。可我仍自如地在水中游弋,这让我非常困惑。我顾不得多想,处境也不允许我多想,我用力伸展四肢,划水、蹬水,向远处游去。从岸上看这片水域,墨绿色水面与茂密的芦苇间杂,斑斑驳驳,一点儿都不豁然。水下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开阔得无边无际,似乎可以通向世界的任何地方。我看到了更多的水中生物,它们很友好地从我眼前游过,彼此互不打扰,并不陌生,仿佛原本就十分熟悉。突然,一阵风刮来,一切皆乱,大鱼小鱼惊慌失措,四散而逃,水瞬间浑浊了。我不知游向何方,胡乱舞动着,和鱼们四散而逃一样,也是惊慌失措的。我本能地向上游,赶快游出水面上岸,逃离危险境地。开始很顺利,没费什么劲,只划了几下水,身体迅速上升,眼看头将冒出水面,却无论如何都游不动了,遇到巨大的阻力。一片黑漆漆的阴影在天空颤动,影像模糊,那是焦化厂高耸的烟囱和巨大的建筑群。我恐慌至极,拼命向上拱,推,敲,撞,顶,扒,挖,撬,无济于事。水其实柔软得很,无须上述动作,根本用不上力。我如同陷在泥沼里,拼命挣扎,越陷越深,精疲力竭,几近绝望。我躺在水中不动了。味道很不对,呛鼻、腌嗓子、熏眼睛,欲翻身查看,一股水流,巨大的红褐色水流将我吞噬,我失去了知觉。我想我可能真的死了。反正也出不去了,我愿意就这样死去。
我再次沿河岸向芦苇荡方向走去。那是一个下午,天气不冷不热,我下楼出了小区,腿不自觉迈向河边。我本不想去,可心里有事,被什么牵引着,阻挡不住,心有不甘,总觉得能发现点儿什么。河岸两边零零星星有人散步,每个人都心不在焉的样子。我害怕看到那双眼睛。细琢磨一下,那双眼睛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日子不短了。我曾顺着可疑的方向,一路追去,想要确定那双眼睛的来源,最终找到它,结果归于徒劳。现在,我边走边观察,前后左右,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那双眼睛随时会出现。由于过于专注,我几次与河边散步的人相撞,他们无不向我投来异样的目光。越往前走,人越稀少,快到芦苇荡了,已见不到一个人,只有我自己了。
老张竟在芦苇荡钓鱼,这让我非常诧异。老张死了好几年了,就是不死也不大可能,从来没听说过老张钓鱼。可老张的确端端正正坐在河边钓鱼,煞有介事地捏着鱼钩上鱼饵,往水里甩竿,盯着鱼漂,等鱼上钩。抬了几次竿,一条鱼都没上钩。我知道,不是水里没鱼,肯定是老张的钓技太操蛋。我在河对岸,隐藏在芦苇荡中,可以非常清楚地观察到老张的一举一动,我很得意,能这样肆无忌惮地看他,而他却毫无察觉。老张一动不动坐在那里,连手里举着的鱼竿都一动不动,像一具雕塑。看了一会儿,我不淡定了,老张可能真的死了,一个死人还有必要受到关注吗?我从芦苇荡里钻出来,伸个懒腰,想转身离开,心里犯起了嘀咕,停下脚步,老张确实死了吗?我再次凝视对岸的老张,仍旧一动不动,我忽然有一种冲动,想大声呼叫他,说不清是给自己壮胆,还是检验他到底是死是活。我把双手撮成喇叭状,举到嘴边,深吸气,胸腔腹腔急剧收缩,蓄满势能,这一嗓子冲出口,就是死人也能叫醒。老张后面冒出一个人,从哪儿冒出来,我丝毫没注意,连声音都没有,像一个电影镜头,突然一个人闯进画面。那个人穿着雨衣,那种军人样式的雨衣,厚重肥大,帽子把头罩得严严实实。天气晴好,他为什么要穿雨衣呢?他抬腿踹了老张一脚,老张像一截木头一样,“扑通”一声掉进水里,鱼竿也跟随老张掉进水里,漂浮在水面上。我吸进去的一口气,险些噎在肚子里,眼前发黑,头一阵眩晕,后脖颈子瞬间冒出一层汗。我退回芦苇丛中,一动不动,大气都不敢出。那个人根本就不看我,或者看到我不在意,在他眼里我已经是个死人了。他抖了一下厚重肥大的雨衣,雨衣发出黏稠的哗哗声。
大地忽然传来沉闷的响声。由远及近。
从林,男,北京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在《啄木鸟》《青年文学》《北京作家》《天津文学》《创作》《特区文学》《厦门文学》《山西文学》《延河》《芙蓉》《鸭绿江》《地火》《星火》《阳光》《都市》《佛山文艺》《北京晚报》等报刊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若干。另著有长篇小说《天堂之约》。
责任编辑:王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