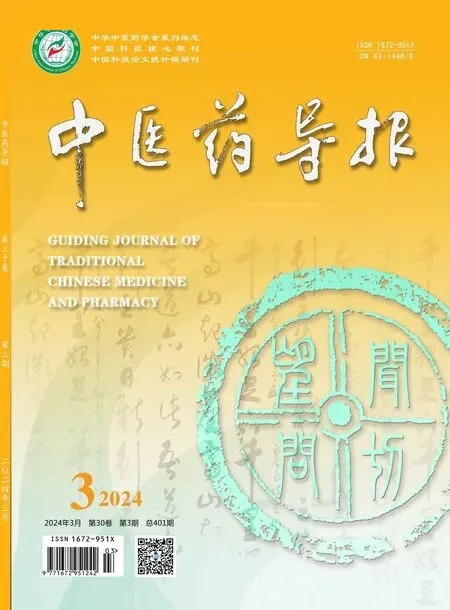傅青主与陈士铎辨治喘证*
俞 邦,覃庭威,张津铖,张洪春,2
(1.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029;2.中日友好医院,北京 100029)
傅青主(以下简称傅氏)与陈士铎(以下简称陈氏)是明末清初有着师承关系的两大医家。世人皆知傅氏尤擅女科,实则傅氏对内科亦有造诣,其所著《傅青主男科》非专论男子疾病,而以探讨内科杂病为主,有独特的临床价值。陈氏勤于著述,《辨证录》是其临床经验的专著,书中善用五行生克理论阐释医理,对脏腑辨证亦有特色。有学者[1]研究认为,傅氏与陈氏为同时期人,在陈氏自述“遇仙传书”时故意将时间错位,实则陈氏经引荐拜访过傅氏,傅氏为陈氏辨疑解难,有师承关系。亦有学者[2]认为傅氏与陈氏为一个学术流派,其学派医学理论和学术体系相当完备,在中国医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学术地位。
喘证是以呼吸困难,甚至张口抬肩,鼻翼扇动,不能平卧为特征的病证[3]。傅氏与陈氏对喘证细辨虚实,重视五行与脏腑理论,遣方用药谨查病机。目前尚未有研究者梳理归纳其对喘证的辨治特点,笔者主要对傅氏所著《傅青主男科·喘证门》和陈氏撰写的《辨证录·喘门》中喘证相关内容进行研究,浅谈二者对于喘证的辨治,试为临床治疗喘证提供参考。
1 虚实错杂,肾为喘根
1.1 喘证多为虚实夹杂证 傅氏与陈氏认识到正虚与邪实皆可致喘,并将邪实与正虚紧密联系,正虚是本,邪实是标,正虚方致邪实,往往导致虚实夹杂之证。临床中辨喘证的虚与实正如“察色按脉,先别阴阳”一般,对于喘证的治疗用药有重要指导意义,若虚实不分,在此基础上的论治将错上加错。《素问·阴阳别论篇》曰:“阴争于内,阳扰于外,魄汗未藏,四逆而起,起则熏肺,使人喘鸣。”[4]金代刘河间言:“寒则息迟气微,热则息数气粗而为喘。”[5]二者分别从外邪犯肺、内生火热角度阐释邪实引起肺脏宣发肃降功能失常的病理过程。
傅氏与陈氏从病程长短切入,区别虚实两类喘证,《傅青主男科·喘证门》有言:“喘有初起之喘,有久病之喘,初起之喘多实邪,久病之喘多气虚。”[6]其认为新发之喘多为实邪外扰,或从风府直入于肺,或经皮毛、口鼻犯肺,使肺失宣肃,肺气胀满而喘,表现为喘息咳逆,胸部胀满,息粗鼻扇,难以平卧,且多剧烈急促,如傅氏所言“气大急,喉中必作声,肩必抬”[6];病久之人则多因正虚而肺气耗散,气难归于下而作喘,表现为喘促短气,气怯声低,或动则喘甚,呼多吸少等,亦可如书中所述“气少息,喉无声,肩不抬”[6]。
区分正虚与邪实在理论上是辨喘证的关键步骤,但临证中,纯实纯虚之喘证往往少见,傅氏与陈氏认为喘证患者多是虚实夹杂之证。傅氏提出“气实者,非气实,乃正气虚而邪气实也”[6],认为气实之喘大多存在正气虚的因素,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如平素体质虚弱,怕风易汗,纳食不佳,腰膝酸软,二便不调之人,肺脾肾亏,稍有劳作不甚,或寒暑不调,或贼风邪气,便外感实邪而喘,气息上逆,不得归元,本体之虚加上邪气之实而形成复杂的虚实夹杂之证。相比于单一实邪致喘,虚实夹杂之喘更为多见,故在治法上“当用补正之药,而加祛逐之品,则正气足而邪气消矣”[6]。故其气治法总方以白术、人参、甘草补肺脾之虚,麻黄祛在表之邪,柴胡疏利气机,白芍养肺金而收敛,半夏祛痰邪而降逆,一润一燥,共收气息归下元,正可谓祛邪而不伤正,扶正而不恋邪。陈氏也认为“邪气之实,亦因正气之虚而入之也”[7],论述邪实的原因是有正虚之象,多为虚实夹杂之证,故在外感风寒所致喘证中,虽告诫不可当做内伤喘证而用纯补之药,但可配以清补之药于解表之味中,作平喘仙丹,专消肺邪而不耗肺之正,顺肺气而不助肺之火。
喘证可见于多种肺系疾病,现代医学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以下简称慢阻肺)的主要症状之一就是喘息。王鹏等[8]对慢阻肺稳定期患者的中医证型进行统计,发现慢阻肺稳定期具有本虚标实的特点,本虚以肺脾肾气虚为主,标实以血瘀、痰阻为主。亦有研究[9]对慢阻肺稳定期患者的中医证型进行聚类分析,5个新命名的证型中有4个是虚实夹杂的证型。可见慢阻肺单纯证者少,兼夹证者多,以虚实相兼、复杂多样为病机特点。现代临床对于慢阻肺的证型研究结果与傅氏和陈氏对喘证的虚实认知较为一致。
1.2 善用攻补兼施剂 攻补兼施剂常用于正虚兼邪实者,明代陶华在所著《伤寒六书》中拟黄龙汤治阳明热结、气血不足证,药用大黄、芒硝、枳实、厚朴泻热通便,人参、当归、甘草、大枣益气养血,为攻补兼施、邪正兼顾之代表方。
傅氏与陈氏治喘亦多攻补兼施,善用麻黄与人参配伍。《古今录验》以续命汤治中风痱,方用麻黄、桂枝发汗,当归、人参、川芎等补虚,攻补兼施以治中风。而历代对于此方争议颇多,应用甚少,后世方书中也较难窥得麻黄与人参配伍者。盖医家多以麻黄发汗强,若本里虚而再用发汗峻剂,则易汗暴出而亡阳。而傅氏在治疗时,辨证明晰,用药有度,以麻黄、半夏、柴胡祛实邪,此为治其外感之标,然其人素有自汗畏风、纳食不佳、气短乏力等肺脾两亏之象,此其感邪之本,故用人参、白术、白芍、甘草而补其脾肺之虚,为治其里虚之本,攻表补里,标本兼治,邪气除而正气安。再如陈氏治疗外感风寒兼肺阴虚夹痰饮之喘时,方用解表和清补兼施的平喘仙丹,以紫苏叶解表宣肺,黄芩、白薇清解肺热,麦冬清补肺虚,半夏、射干、山豆根、茯苓、桔梗化痰祛饮通咽喉,乌药温肾纳气。
目前有较多关于苏黄止咳胶囊治疗慢阻肺的临床报道[10-11],可改善肺功能和炎症因子指标,提高有效率等。苏黄止咳胶囊由麻黄、紫苏叶、牛蒡子、枇杷叶、地龙、蝉蜕、五味子等药物组成,有宣肺平喘、补肾生津之效,是现代攻补兼施治疗喘证的代表方剂之一。
1.3 肾分水火论正虚之根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即有“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4]的记载,从脏腑气机角度来看,肾脏失其封藏则会有气机逆乱的表现。《类证治裁》提出了“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肾主纳气”[12]的观点,强调了肾在呼吸运动中的重要作用,若肾的生理功能出现异常,则不能正常摄纳呼吸之气,便可能出现喘证,多表现为喘促日久,呼多吸少,动则喘甚,气不得续,脉多沉弱细数。
傅氏与陈氏继承前世医家对肺肾二脏有紧密联系的思想,在此基础上着重探讨肾水肾火与肺气之间的关系,将肾虚水竭归纳为虚喘的根本病因。《辨证录·喘门》云:“肾水太虚,而后肾火无制,始越出于肾宫,而关元之气不能挽回,直奔于肺而作喘。”[7]陈氏将肾水与肾火以主次关系进行论述,认为肾水竭是根本,而肾火不制是肾水虚所致的病机过程之一。肾主水,肾水虚则不能制肾火,肾火携元气脱离关元,气冲上焦影响到肺气,最终导致喘证的发生。
现代医家也有不少从肾水与肾火角度阐释病机。如张怀亮等[13]认为,肾中之相火宜潜藏而化无形之元气,不宜僭越,肾中水涸会使相火无藏身之位而伤有形之脏腑。吴荣祥[14]对肾精、肾气、肾阴、肾阳进行研究,认为四者存在互根互用的关系。
2 金水相生,久嗽致喘
傅氏与陈氏善用脏腑辨证、五行生克理论[15],肺属金,肾属水,肺金气虚甚则母病及子影响到肾水,并提出“嗽喘”的概念。《素问·本病论篇》中就有嗽与喘密切相关的论述:“民病寒热鼽嚏,皮毛折,爪甲枯荣,甚则喘嗽息高。”肺失宣肃而发为咳嗽,久嗽耗伤肺之气阴,金为水之母,肺气清肃下行才能助肾生水,肺阴亏耗则津液不能下濡于肾。肺主呼吸,肾主纳气,肺主行水,肾为水脏,肺肾二脏在气机升降与水液代谢方面都关系密切。
陈氏更关注“嗽”与“喘”出现的先后顺序,并论述了背后蕴含的肺伤与肾伤孰轻孰重的病机。“久嗽之后,忽然大喘不止,痰出如泉,身汗如油”[7],若患者只嗽而未出现其他症状,此尚未及肾;但若忽然出现大喘不止,痰出如泉,身汗如油的症状,则为久嗽伤肺累及肾脏,汗出亡阳之证,是为“嗽喘”。久嗽伤肺累及于肾,是先伤肺而后伤肾,乃先伤气而后伤精,以肺伤为本,故嗽喘肺气伤重,肾精伤轻;无嗽只喘则是先伤肾,后以伤气,以肾伤为本,故其肾精伤重,肺气伤轻。《傅青主女科》中亦论述了肺与肾之间的关系:“惟是肾水不能遽生,必须滋补肺金,金润则能生水。”[16]可见傅氏与陈氏都深谙五行生克之理,对肺肾二脏之间的联系阐述详尽。
在遣方用药上,陈氏用生脉散滋肺润燥,但不同于《医学启源》中生脉散的人参、麦冬用量相等,陈氏则是重用麦冬1两为君,人参5钱为臣,五味子2钱为佐。陈氏熟习金水相生之法[17],补肺气以生肾水,气足则肺脏得安,肾得水而火不上沸,正所谓“无形者补气可以生精,即补气可以定喘”[7]。嗽喘及肾之证倘大量用人参补气则恐肾水更亏而火愈盛,故重用麦冬以润肺,金为水之母,金水相生,补肺而肾水自生,人参适量入上焦生肺气而不助火,佐以五味子益气生津,三药合用大补肺之气阴,急救其津液。或用归气汤亦妙,麦冬3两、五味子3钱滋阴润燥,加熟地黄3两、白术2两补肾祛痰。陈氏反对熟地黄多用助痰生喘的观点,认为熟地黄“不生痰且能消痰,不滞气且行气”[18],补肾阴同时亦可消痰,一举两得,白术健脾化痰,脾健而津液自生;四药合用,嗽喘可平。
“嗽喘”大喘不止,汗出如油等亡阳之证可出现在现代医学中慢性肾衰竭合并呼吸衰竭等急危重症中。慢性肾衰竭时肾脏排泄和代谢功能下降,导致水、钠潴留引起气短、气促,或因严重代谢性酸中毒引起库斯莫尔(Kussmaul)呼吸。刘清泉曾以参附汤合补中益气汤加减治疗西医诊断为心功能不全、慢性肾功能衰竭急性加重、Ⅱ型呼吸衰竭,中医辨证为喘脱的患者[19]。
3 金木交战,详论郁喘
历代医家鲜有论述气郁致喘者,傅氏与陈氏独辟蹊径,阐发气郁而喘,并从肝胆论治,为后世提供参考。肝喜调达而恶抑郁,七情内伤,情志不遂,影响肝之疏泄,肺气闭阻,通调水液失常而生痰,“结滞痰涎,或如破絮”[7],若再遇外感实邪犯肺,肺气被束而上逆,以致“痞满壅盛,上气喘急”[7],则形成七情内伤和外感兼而有之的“郁喘”。此时治内伤而外邪不能出,治外感而内伤不能愈。陈氏辨治翔实,从肝胆论治,其所著《外经微言》有言:“肝胆交郁,其塞益甚,故必以解郁为先。”[20]肝胆作为阴阳之会、表里之间,枢机不利则多易生变,故以解郁而平喘息。
陈氏方用加味逍遥散治郁喘。柴胡疏肝解郁,陈氏谓之“治郁证之要剂”[18],且泻肝胆之邪,“入于肝者半,而入于胆者亦半”[18],将表里相通,开其郁塞;白芍利肝气,肝气利而郁气亦舒,陈氏认为芍药解郁之妙在益肝,加味逍遥散中用白芍5钱以达其效;当归走血分滋阴柔肝;陈皮、白术理气健脾;半夏、厚朴、茯苓、紫苏叶效仲景半夏厚朴汤之法以治状如梅核。阴阳会通则内外皆解,诸症得安,喘息可平。
郁喘可对应现代医学里由于心理精神因素引起的哮喘[21]。发生机制可能为抑郁心理使胆碱能神经活性增加导致支气管平滑肌收缩,或使患者的膈肌驱动减弱而加剧呼吸困难[22]。有现代临床研究[23]表明,运用柴胡疏肝方联合孟鲁司特钠片治疗小儿咳嗽变异性哮喘有较好疗效,可改善临床症状及肺功能,安全性好。亦有疏肝补肺法论治支气管哮喘慢性持续期的临证经验[24],收效甚佳。
4 细察兼症,精准辨别
傅氏与陈氏认为不同病因所致之喘的兼症会有差异,并进行了细致而形象的补充。以“喘证”二字测症,必以喘、呼吸困难为主。《灵枢·五邪》云:“邪在肺,则病皮肤痛,寒热,上气喘,汗出,喘动肩背。”[25]明代医家王肯堂在《证治准绳》中对喘证的主症进行了描述,“喘者,促促气急,喝喝息数,张口抬肩,摇身撷肚”[26]。傅氏与陈氏则通过对痰色与痰量、咽部症状、汗出情况等兼症的判断进行精准区分。
4.1 兼症之痰色与痰量“喘甚有吐红粉痰者”[6]可见于肾火挟肝上冲之喘,突出了痰色的异常。肾火上炎,肺为娇脏,肺金被肾火所灼炼液为痰,肺热亦不能克肝木,肝气疏泄失常,肝火亦蒸腾肺金,肺络被肝肾二火灼伤而出血,故可见红粉色痰。在治法上当清肾火、泄肺热、养阴平肝,用药以地骨皮清骨中之火,沙参、牡丹皮、白芍养阴平肝,麦冬清肺,芥子化痰,甘草、桔梗引药入肺,消痰而定喘。现代医学中左心衰导致的肺水肿也会出现喘憋、咳粉红色泡沫样痰的表现[27],在病变脏腑上不同于傅氏与陈氏认知范围的肝肾二脏,临床中应当注意鉴别。
“气喘不能卧,吐痰如涌泉者,舌不燥而喘不止,一卧即喘”[6]为肾寒气喘之证,强调痰量多,发作时间长,影响平卧。肾中寒气盛而肾火衰,水火难以相济,阴阳无以互生,水无所养而生肾寒水气,水寒射肺,肺失宣降,故喘不能卧;肾水不安于下而泛滥于上,故痰多如涌泉且舌不燥。方用六味地黄汤加肉桂、附子,大剂饮之,祛肾寒而温肾阳,使肾气与肺气皆安,方可止喘平卧。
4.2 兼症之咽部症状 郁喘可见“或如梅核,咯之不出,咽之不下”[7],相比于其他喘证,郁喘咽喉不适的症状较为明显。《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曰:“妇人咽中如有炙脔,半夏厚朴汤主之。”[28]用比喻的方式形象地描述了咽部的症状。《仁斋直指方》首次提出了梅核气的概念:“梅核气者,窒碍于咽喉之间,咯之不出,咽之不下,如梅核之状者是也。”[29]后世医家也多从肝气郁结等情志不畅角度进行辨治梅核气,故喘证若由情志因素引起,仔细询问是否存在类似症状有助于明确辨证。
4.3 兼症之汗出情况 嗽喘可见“身汗如油”的兼症,体现了陈氏关注患者全身汗出的情况。见汗出,一要判断汗出的部位,但头汗出可能由上焦热盛,迫津外泄导致,半身汗出多见于中风病人痰瘀阻滞经络,阴部汗出多为下焦湿热;二要判断汗的性质,若汗出沾衣,色如黄柏多究之于湿热,若大汗不止,则需判断是否为亡阳或亡阴的表现。故当喘证见身汗如油者,需考虑患者汗出亡阳的情况。
以上可见傅氏与陈氏对各种喘证的症状观察入微且描述详尽,丰富了中医的症状学内容,但都没有涉及舌象脉诊的描述,难以四诊合参,为白璧微瑕之处。
5 虚实之中,妙用气药
病因不同,治法各异,但逐外之标实、补脏之本虚的思想贯穿于傅氏与陈氏治疗喘证的始末。傅氏提出喘证的治气法原则为“用补正之药,而加祛逐之品”[6],正气充则自以御外邪,诸症可平,陈氏亦认为应解表与清补兼施治疗外感实喘,“以期消肺邪而不耗肺之正,顺肺气而不助肺之火”[7],以达到祛邪而不伤正的目的,两者不谋而合。
5.1 治气法的多种变化 傅氏不仅在治疗妊娠病时重视气的作用,主张“血非气不生,是补气即所以生血”[16],亦通过气的虚实之辨对喘证作出描述,“气虚则羸弱,气实则壮盛”[6];陈氏则认为“气旺则升降无碍,气衰则阻,阻则人病矣”[20],阐明气之旺衰对人体健康有重要影响。
傅氏与陈氏基于对气的认知,提出了气为病而致喘的多种治法。如:“气陷,补中益气汤可用”[6],症见气短乏力、纳差、久泄不止,可用补中益气汤补气升提;“气寒,人参、白术、附子汤可施”[6],患者可有畏寒、痰多色白等表现,治以温气散寒;“气热,用生脉散”[6],可见气短声低、干咳少痰等症状,方用生脉散养阴清热;“气壅塞,用射干汤”[6],表现为喉中水鸡声,不得平卧,治以温肺化痰,降气除壅。
现代医家亦有从气论治各类呼吸系统疾病的学术观点。夏小军等[30]立论于肺癌从气论治的观点,提出补气固本、补气消痰、补气行瘀、补气祛毒等治法。殷莉波[31]认为慢性咳嗽的治疗应从气论治,调畅一身之气机,使“气血冲和,万病不生”。邵长荣从补肺气、健脾气、纳肾气、疏肝气4个方面论治慢阻肺,临床疗效较好[32]。
5.2 虚喘重用人参 诸多医家在认识和使用人参时多考虑其大补元气、回阳固脱、补脾益肺之功效。如《伤寒论》用四逆汤加人参治霍乱脉微而亡血,四逆汤暖补肾水脾土,加人参补气生津而复脉;《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四君子汤中人参补脾益气,配伍白术、茯苓、甘草等治疗脾虚食少;张元素论人参有“治脾肺阳气不足,及肺气虚促,短气少气,补中缓中”[33]之效。
陈氏所著《本草新编》对临证使用人参有独到的见解,“味甘、气温、微寒、气味俱轻,可升可降”[18],认为人参作为补气圣药能入五脏六腑,当遇肾气欲绝之气喘,必用人参,能回元阳于顷刻,且用量宜大,需用到一二两,方能使人参下行,“生气于无何有之乡,气转其逆而喘可定”[18]。陈氏定喘神奇丹和参熟桃苏汤中重用人参下达关元,加之熟地黄、山萸肉、牛膝、麦冬等品,辅佐相济,挽回关元之气而救其肺喘。若病甚下元寒极者,成假热气喘之真寒假热证,当在熟地黄、山药、麦冬、牛膝等补其肾水的基础上,再加附子、肉桂以填命门之火,救之以危急。
傅氏在治疗肾水大虚所致虚喘时重用人参3两为君,取人参重用下行,“下达病原,补气以生肾水”[6]之意,以熟地黄、山萸肉、枸杞子、牛膝、麦冬、胡桃为臣,充肾水、补元气、益肺金,佐以五味子收敛肺气,以生姜为使引入肺经,组方严谨,配伍巧妙,共奏补肾平喘之效。
有学者[34]对现代医家临证使用人参用量进行总结,结合疾病、证型、症状,现代临床用量从3 g到55 g不等。亦有较多关于大剂量使用人参治疗急危重症的报道,如:用独参汤50 g浓煎成100 mL分2次服可改善透析性低血压[35];独参汤可改善脓毒性休克患者的血流动力学,减轻炎症反应,提高血小板数量,阻止其向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发展[36-37]。
6 病案举例
一患者有痰气上冲于咽喉,气塞肺管作喘,而不能取息,其息不粗,而无抬肩之状。陈氏判断此患者为气虚而非气盛,乃不足之症,认为不可作有余之火治之,其方用定喘神奇丹:人参2两,牛膝5钱,麦冬2两,北五味子2钱,熟地黄2两,山萸肉4钱。作汤煎服,1剂而喘少止,2剂而喘更轻,4剂而喘大定[7]。
按语:患者症见喘而不能取息,可归属于中医的“喘证”范畴,喉中有痰,息不粗,无抬肩状,可辨为虚喘。肾水虚而不制肾火,使关元之气上冲于肺而喘,喘又更耗散人体正气,故需纳回关元之气而补肾水。方用人参、牛膝使气下回关元,配伍五味子收敛耗散之气,让上冲之气归于原位。以麦冬润肺金,熟地黄、山萸肉补肾水,肾水充润则易制肾火使其安于关元。诸药共用使水火既济,气不上冲,故服药后喘息可定。
7 结语
在傅氏与陈氏的辨治体系下,首先应辨别喘证患者正虚与邪实的情况,且临证以虚实夹杂者为多;其次在五行生克与脏腑理论的指导下,结合患者的兼症,精准辨别患者的病变脏腑;在治疗上,逐外之标实、补脏之本虚的思想贯穿于治疗的始末,善用攻补兼施剂,遣方用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配伍精巧,且常在方后点明用药内涵,同时提出虚喘应重用人参等多种治气法思路。傅氏、陈氏所著为后世治疗喘证提供了用药思路与临证参考,使中医学对于喘证的辨证论治更加翔实。喘证作为中医病名,常对应现代医学中慢阻肺、肺源性心脏病、心源性哮喘、肺炎等疾病,笔者通过辨析探讨傅氏与陈氏对于喘证的论治思路,以期对喘证诊疗提供借鉴,发挥中西医结合治疗疾病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