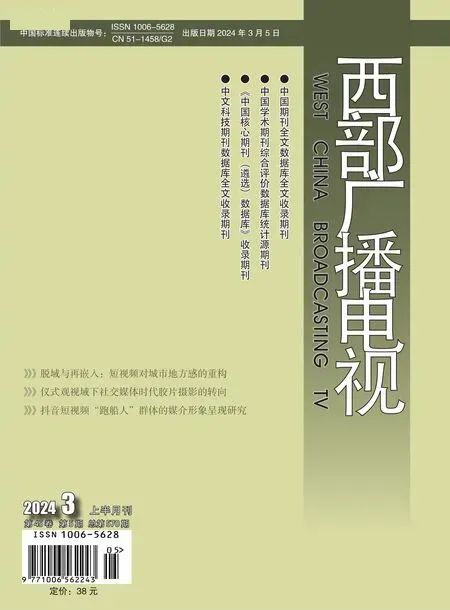共享和互动:网络圈群背景下网络舆论的群体极化传播现象研究
刘 旸 段 玉 曹朋朋 刘语林
(作者单位:四川传媒学院融合媒体学院)
1 研究的主题及传播学背景
回溯过去,传播学界对新的技术发展以及传播形态的描绘大多表现出乐观和一定程度的期待。从技术特征上来看,作为万维网开发者之一的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曾充满雄心地描绘互联网将给人们带来“新的自由”。然而“去中心化”的互联网传播,似乎正在以另一种方式传递着隔阂、误解和圈群化。正如韦龙所说:“互联网没有成就一个理性、包容、可理性沟通的协商空间,反而放大了现实社会的撕裂……形成群体中的极化现象。”[1]互联网舆论的群体极化并不会止步于此,它将现实地转移到社会的公共舆论领域,并对其造成切实影响。
互联网传播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互动性”。在亿万个独立的个体以信息交互的方式穿梭于互联网时,互联网信息传播的发展方向亦不言自明。皮埃尔·莱维(Pierre Levy)将此种交互性定义为“在信息交易中受惠一方的主动性参与”[2]。传统大众媒体时代的受众从未被赋予过如此强大的权利——一种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由角色时空不确定性所带来的传播自主。这也是莱维所关心的“主动型受众”。在实践中,交互的强化产生了多种多样的观点,继而形成舆论。至于舆论的极化,这是一个在传统社会中就存在的现象。例如,人类社会自诞生以来产生的宗教狂热、种族歧视、极端女权等现象。然而,“随着当下媒介环境的智能化与数字化,各类前沿技术重塑着新闻生产过程与媒介生态构成”,使得“观念和行为的同质化与圈层化表现出比‘前智能时代’更为复杂的面貌”[3],这种“技术介入”在多角度推进着极化的发展。
正如丹尼斯·戴维斯等在书中所写,“受众不会被动地去接受……而是主动对信息进行处理和加工,而后只把顺乎文化需要的那一部分保留下来”[4]。传播的文化取向不仅暗含强烈思辨色彩的关于主体性确定的意味,也包含文化传播视域下对“共享”本质的见解。
2 网络圈群和群体极化的逻辑梳理
2.1 网络圈群
国内对网络圈群概念的研究起步较晚,在研究早期,学界出现过诸如“网络社群”“网络圈层”“圈层化”等表达,且尚未明晰区别所在。近年来,关于“网络圈群”相关研究成果较为突出的是王仕勇等人的论著,他们认为“网络圈群的主体、网络圈群所处的环境”是不同角度之下的两个关键要素[5]。通过梳理相关文献,本文认为网络圈群是以现代网络技术为基础,以微信、微博等平台为载体,因某种特定原因或结合个体现实社交圈而建立的网络聚合空间。
在特征方面,国内学者普遍提出网络圈群在直观结构上所具有的排他性和相对封闭性[6]。在严密的进入壁垒的背后不断塑造着圈群“强议程设置”和“沉默螺旋”共存的交互景象[7]。在治理方面,对策主要聚焦于网络圈群舆情蔓延至现实社会的不良影响,将治理思路由亡羊补牢转换为防患于未然。
2.2 网络舆论的群体极化
相较而言“群体极化”的概念则显示出较为蓬勃的活力。笔者在知网以“群体极化”为主题进行搜索(搜索日期:2023年6月10日),得出2 090条结果。其中,相关学术期刊文章1 525篇,学位论文447篇,其他文献118篇。其中,有关传播及媒介的论著达到了268篇。
在概念方面,关于网络舆论的群体极化的相关研究往往将其概括为“舆论极化”,但对其概念的解释尚未统一。国内学者普遍认为,群体极化指的是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8],而国外却更侧重于政治两极化。本文认为“极化”是理解网络舆论的群体极化概念的关键,群体极化即群体观点的两极分化现象。在改善策略方面,主要分为两种视角:一是法律等方面的强硬措施,二是针对不当言论进行引导的软性方法。
2.3 对既有文献的检讨
国内外的网络圈群研究都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学科视角相对单一。在未来的网络圈群研究中,应更加关注共情、互动、分享的作用,网络民粹主义解构等议题,提出更多有效的化解策略和有益的研究视角与课题。在经验主义的实证方面,国外关于网络舆论的群体极化研究主要采用量化的方法,而国内尚处起步阶段,相关研究没有就如何缓解和消除舆论两极分化给出明确回答,抑或给出的解决方法过于主观。具体策略的适用和效果分析多建立在印象式的治理视角,缺乏更为客观的实证。同时,研究更多展示了宏大理论下舆论引导以及政策规制等视角,较少从经典传播学理论角度阐明传播学视域下的“网络圈群”与“群体极化”现象及相应问题的解决方案。
本课题试图着墨于传播学文化理论层面,对网络圈群舆论所引发的群体极化现象进行规律性阐释。在互联网“去中心化”特征的影响下,媒介传播方式和效果有了极大的变化。传统线性的、一对多的、面向“原子化大众”的传播特征一再被消解,取而代之的则是文化研究领域有关价值、共享和互动式的传播。如何在这样的实践背景下找到行之有效的传播模式,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是极其重要的,而这也是消除网络圈群乃至群体极化现象带来的负面影响的重要出路。
3 共享和互动视域下的网络舆论
人文社会科学视角常把文化描述为一种成员间符合社会需求的生活方式和文明传统。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以符号结构来表现的具有实际意义的模式,是一种历史遗产。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在文化路径上审视传播,认为传播的本质就是一个符号过程。现实世界的意义在这个程序中被创造、维持和改变。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内嵌于日常生活,不但指导人们认识和理解事物,更塑造着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看法。传播在交互中获得了对客观现实在解读上的同一性。传播中持续不断的信息交互如流淌的血液穿梭于社会肌理,为整个文化的构建提供源源不断的营养。
3.1 网络信息获取层面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多媒体技术的进步和大数据算法的突飞猛进,媒介技术本身正在以形式的变化直接影响受众内容的获取。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直接将媒介称为隐喻和认识论。这些观点无疑都是将传递信息的媒介本身作为产生意义的原点——某种意义的原话语。
在这种大规模个体直接参与从而建构内容的传播时代,媒介技术却在信息流动上为用户“制造”了一系列现实,并继续“制造”下去。今天的网络传播内容对个体的趋同,是在大数据及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的技术宰制下揭示了用户的被动、无意识状态。于是“信息茧房”的概念在算法技术层面被深化到“过滤气泡”效应领域。互联网“去中心化”的信息收发模式使得信息获取如是,观点和价值判断(在互动过程中所协商出的)亦如是,“回音室效应”解释了这种现象。
互联网开放式、多样化的信息媒介特征却在技术原话语中不断为用户塑造着“窄化”、片面的信息形象。根源在于互联网信息的过载。巨量信息内容如不能被有效筛选,那么这种场域必然将因其所表现的不可操作性而被舍弃。然而,这些技术方式却同时在不断造就着用户的认知偏向和观点极端化。
3.2 网络交互层面
如上文所述,信息过载的问题在信息获取层面以互联网技术来解决。而在交互层面,信息过载依然存在解决的需求。
互联网“去中心化”的特征核心在于信息收发的自由化和匿名化。这些基础特征使得互联网充斥着“混杂了事实、情感和意见”的信息。首先,互联网的交互本质不可避免地造成用户情绪化表达的结果。在情绪化交互的过程中,对于议题的本源——“事实”造成削弱。匿名化等账号人格化的特征使得交互情绪化被放大,群体心理被逐步建立。在圈群边界内的群体中,极致化的舆论传播同一性被构建起来。随之而来的就是圈群的某种既不开放、包容,也不整体化、社会化的“文化同一性”,被一个个中心化的具体核心议题,或意见领袖所建立和维系。其次,意见逐步极化的另一结果就是对议题事实的疏离。这彰显了一种信息获取和交互需求的阶段性矛盾。以事实本源为基础的信息在大量交互中逐渐被“再阐述”,后真相时代便以此得名。其中大量的观点、立场、情感在多次、多轮阐释中逐步释放,并替代事实的一部分。在不断交互的过程中,随着信息获取的机会增多,选择性接触机制将发挥作用。众多对于互联网交互的实证研究发现,信息种类越多,用户根据预设立场进行观点筛选的行为越显著。可见,文化理论视角下,避免舆论的群体极化最直接方法是采用具有同一性的社会文化来进行理解。
4 共享和互动打破群体极化的交流僵局
互联网个体的互动式传播基于“去中心化”的信息传播模式,发展于个人意见的表达和对事实的多次再阐述,形成于具有明显边界性群体的聚集。但是,互联网这个在麦克卢汉眼中造就了“内爆”式的差异消除的场域,却没有重新“部落化”,反而整体性地跌入“脱部落”境况。“差异”由于技术发展竟然同时达到最大规模的“弥合”和“分裂”。前者是互联网“元媒体”式的弥合,后者是互联网舆论群体极化的分裂。媒介延伸了身体,消除了印刷时代和电气时代的鸿沟,却无法逃脱后现代的极端流动性。在社会文化的传播和建构规律面前,如果人们无法有效地依靠媒介先进技术进行共享和互动,不断发展中的社会文化就不能得到持续有效地构建和发扬。
4.1 “再中心化”的工具性
笔者在上文中曾论述网络信息获取的技术发展导致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的飞跃。在共享及互动视角下,这是信息过载的必然结果。个体自发地通过技术方式规避过量信息的入侵。信息这一概念本身是中性的,对其进行价值判断则是文化行为。圈群化的交互同一性使得极化的舆论以群体为主体。此时群体意见成为关键。学界在对互联网舆论的长期研究中,经常聚焦于其“去中心化”的现实,并将其视之为挑战。而我们需要了解的是,一方面,互联网圈群的文化同一性已经实现了理想化的共享与互动,继而应该试图在更大的社会文化范畴内得到实践。所以,我们要“利用批判素养的培养打破圈层藩篱;普及技术素养纠正信息偏食;提升数字素养提高圈层信息质量”[9]。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再中心化”,使我们能够在个体的层面之上再次找到治理落脚点,从而引导个体走向健康向上的公共讨论之中。核心在于,“再中心化”的“中心”,那个“两级传播”中的意见领袖,必须是具有共享和互动精神的“守门人”。它既是开放包容的中心,又是理性文明的中心,而对这个位置的占领是主流文化得以传播和发展的关键点。
截至2023年6月底,在累计下载量过亿的自有应用程序(Application, App)产品中,有11款由8家主要中央媒体拥有。这些中央媒体拥有超千个第三方渠道活跃账号,440余个头肩部账号(百万级以上粉丝或季阅量)且形成矩阵,累计生产2.7万篇爆款[10]。在这样的互联网传播新形态中,主流声音持续占领两级传播的阵地,普遍成为“再中心化”的舆论“守门人”。而他们以共享和互动为基础实现的网络信息传播,会以更大的黏性增强受众的认同。
4.2 分享视角下的充分协商
我们的文化帮助我们理解周围的客观自然。然而,我们对客观自然的表述有赖于每一个互联网参与者在信息共享和互动下有效地彼此协商。审视文化理论的脉络,我们在符号互动的理论支撑下认识到“在参与者之间不同程度地分享含义和价值而引起的符号行为”[11]。
在这种视角下,我们需要主流文化始终不懈地以合适的方式主动融入互联网交互中。王仕勇、余佳琦认为主流文化和圈群文化是一个由对抗向对话,即争斗转为争鸣的过程。概念化、形式化且单调的主流描述难以融入网络圈群这种戒备森严的场域。我们应具备先进的媒介理念、素养以及巧妙的表达方式。从文化的观点来看,共享与互动需要的“互联网语言”可以被视为一种“亚文化话语”的修辞。其在传播上的效果不可被忽视。新修辞学的关键概念是身份认同。修辞具有认知性,我们通过与他人的修辞和交流来获得共识,共享不同的主观经验。主流文化介入互联网传播,如果想要产生良性的共享和互动,则必须在修辞上符合互联网文化表达的形式。
比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新媒体中心在2019年7月29日正式推出的短视频栏目《主播说联播》,就是为顺应“去中心化”的互联网传播新特征,以符合互联网文化表达的修辞形式而发展的舆论宣传样。在2019年8月19日的《主播说联播》视频里,《新闻联播》主持人康辉和欧阳夏丹为观众揭秘了主播手稿的样子。这实质上便是向互联网话语或谓“亚文化话语”的主动靠近,从而达成有效共享和互动。其内容密切关注热点,结合当天重大事件和热点新闻,用通俗语言传递主流声音,有效推进“同温层”舆论共鸣。根据新浪微博话题数据统计,截至2024年2月27日,央视新闻微博账号的“主播说联播”话题总阅读量已达138.6亿,相关讨论250.4万条。
总而言之,主流文化对互联网的介入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可以润物细无声。互联网不仅在共享和互动的基础上,以共同文化为依托,持续不断地传播主流社会的声音,也在这种信息流动的过程中不断塑造、丰富着我们的文化。在这种共同理解的基础上,极化的声音将持续不断地被削弱。互联网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世界,我们在不断交互和共享中认识、改造这个世界,并一刻不停地与我们的客观现实进行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