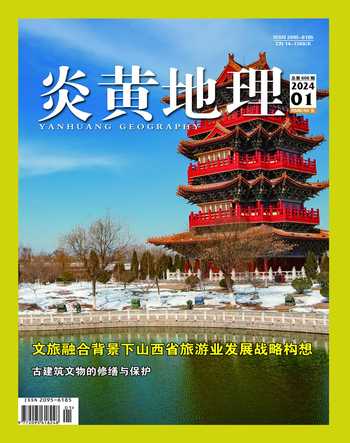文本视角下云南民族村火把节的表演呈现
张敏



作为可被接收者创造性阅读,由封闭、自足、静态走向多元、对话、动态的文本,火把节从原生地走向旅游场域的时空变换就经历如此过程。云南民族村火把节在旅游舞台上以“传承文化,引领欢乐”为宗旨,焕发出了勃勃生机,紧扣“火”这一线索展开分析,从历史角度看到了火把节的前世今生。而处于表演语境之下的火把节,经由作为表演者的村民与作为观众的游客之间的协商,与文化真实与表演的妥协,利用符号代码的方式得以在旅游前台构建出认同空间,于此极富生命力的表演文本得以呈现。
文本一词,经历了传统观念中基礎的文学作品表象,别于被符号或属于某项艺术的材料组织起来的整体的作品,到20世纪70年代,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将作品与文本的关系完全翻转过来,作品只是一个不断重复的出发点,读者可以不受拘束地加以利用,进行种种文本实践,而这种实践中的文本,不再是作品的精神价值的物质承载物,而是更加神秘的语言革命中的实践行动,它并非具体的文字,而是一种永远变动不居的过程。节日文本的研究也从传说、故事这一书面文本挣脱,更关注于节日文化整体。部分学者们从节日的不同语境中,探讨传统与发明的并存以及相互间的权利关系。民俗文本从作为一种交流实践的表演模式来看,文本是情境化的交流实践的新生性结果。
本研究着眼于旅游前台的展演,对云南民族村欢庆的火把节紧扣“火”为线索展开分析,先从表演主体出发,探究此表演文本对参与其中村民与游客身份的影响。再抽离出火把节中各民族共享的符号语汇,以觉察传统与现代发明之间的纠葛,究其根本是多主体的协商与妥协的结果,是新旧文本的链接与碰撞,于此兼具娱人娱神功能的火把节得以呈现。
景区火把节的“前世今生”:从原始崇拜到旅游展演
火把节是我国西南地区彝族、白族、纳西族、普米族、藏族等少数民族一年一度欢庆的传统节日。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现代意义上的火把节,其形成经历了从单一到多元,从小范围到大范围的发展过程。
祭火与祭祖、祭天融合。欢度火把节的民族同属氐羌族系,氐羌族系各民族在文化早期阶段,受原始宗教信仰的影响,较其他族系极为重视祭祀天地、祖先。不仅如此,火崇拜与祖先崇拜叠合的现象在各民族神话中有迹可循,如哈尼族的取火神话——《阿扎》。阿扎的阿爸向魔怪取火,被魔怪化成了石头,于是阿扎决心替阿爸完成取火的使命。火是魔头上的眉心灯,除非摘取时拔下魔鬼头上的金鸡毛,否则就会被追杀。阿扎在其死去父亲的神助下,拿下眉心灯上的火珠,却没有来得及拔下金鸡毛,情急之中吞下火珠。因此,魔鬼把阿扎心中的火珠变成一团燃烧的烈火,一路追赶。最后阿扎虽然把火带回家中,自己却被火烧死。从此哈尼族人就把火叫“阿扎”,于是这个原来祖先的名号就被赋予了火的神灵。让祖先与火同名,让祖先继续以火的形态留存。人们认为人类火种就是祖先用智慧和生命换来的,与大自然的抗争获得了胜利,既合理解释了火的由来也获得自我的肯定,为生活寻找到了力量。火崇拜作为火把节的原动力,与祖先崇拜的叠合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要。祭祖即为祭天,天地祖宗,本为一体,至为神圣,在各民族的祭天仪式上,充满着浓厚的敬祖寻根的意识,通过仪式,以祈求祖先神灵保佑,以祖遗训,规训族人。火把节时以磨秋作为沟通天界与人间的途径,哈尼族人认为天神就是沿着磨秋杆从天上降临人间,因此对立磨秋、祭磨秋极为重视。
氐羌民族随着从游牧生活转为农耕生活的过程中,火把节中也增添了诸多农事要素。
农祀节日到综合性节日的转变。彝族《火把节》神话,天上的大力士斯热阿比要和地上的大力士阿提拉比武,结果,天上的大力士被打败了。天神大怒,便派大批蝗虫来吃地上的庄稼,地上的大力士砍了许多松枝,带领大家在六月二十四晚上点燃火把,把蝗虫统统烧死,保护了庄稼。这则神话解释了火把照田的由来,同样也包含对天神的震慑,望他不再为祸人间。此外,还有火烧松明楼、皮逻阁火烧松明楼杀五诏、孔明擒孟获、父老设燎相迎等说法,无法辨别原型为何,更是无法考据神话解释仪式,还是仪式由神话而来,只能理解为神话与仪式互相解说,互相肯定。
对于火把节的由来各执一词但其风俗已相沿成习。农事生产的丰收对于以此为生的人们来讲就是最大的祈愿,因此火把可灭虫害的功能自然为人所重,将火把节视为农祀节日也符合其脉络。
在旅游行业助推之下,现已形成的官办火把节有凉山彝族国际火把节、楚雄彝族国际火把节、石林彝族国际火把节,火把节作为文化旅游商品,在遵循农历六月二十四传统节日庆祝时间的基础之上,依据不断丰富的节庆活动所需,延长了整个节庆时间,继续举行祭火仪式、斗牛比赛、摔跤比赛,延续传统活动的同时,衍生出了开幕式、主题晚会、火把狂欢、招商引资项目推介会、民族文化艺术展、各乡镇街道分会场等内容。于民众来说是集祭天、祭祖、交游、歌舞、商贸等功能的综合性节日。
作为表演文本的表演者与观众
民族村火把节虽为彝族、白族、纳西族、普米族、藏族、摩梭人、哈尼族、拉祜族共同的欢庆,但通过笔者观察,其隆重程度依次为彝族、白族、纳西族。舞台上的火把节由作为表演者的村民与作为观众的游客共同演绎,但事实上村民与游客都经历着心理认同的困惑。
村民:“名副其实”。民族村过节的八个民族中,当属彝族最为隆重,白族、纳西族次之,其他民族村寨中无特别活动标识火把节的欢庆。对于过节的具体内容,民族村相关部门给出整体方案,主会场——团结广场,分会场——彝族、白族、纳西族村,活动的策划充分尊重过节民族村民的意见,尤其是分会场各民族村寨的活动,经协商后得以呈现于表演前台。
农历六月二十四是彝族正节,这天彝族村举行祭树神仪式。祭神仪式并非所有彝族地区都举行,甚至不是在火把节时举行。
“树神,这个是我们这边有,姚安这边,姚安其他地方有没有不知道,但是我们村子那边有,就像我们的祖坟,上完祖坟,然后专门有棵树神,要在那里点香。”
祭树神仪式被整合于火把节程式之中,体现彝族人民对自然物树的崇拜,同样在春节期间也举行了祭树神仪式。民族村作为旅游地在呈现民族文化时独具开放性与包容性,村民作为文化持有者,给予他们一定的话语权,共同打造节日这一旅游产品;另一方面,村民充分且深入参与节日的全过程,以解思乡愁绪。
农历六月二十五是白族正节,这天早上各民族兄弟姐妹齐聚本主庙前为竖火把做准备,大家将贡果、贡香都插于火把上。随后在本主庙进行了祭拜本主的仪式,贡品奉上,奏乐鸣炮。紧接着将火神牌位抬出至崇圣寺三塔(仿制)前进行祭佛,后返回戏台广场进行敬火神仪式,火神上座、貢献祭品、祭师呈诵祭文,接着长者敬香叩首、敬献祭品。祭师抱公鸡于火把前念诵祝词并模拟鸡血涂抹于火把上的动作(实际未杀)以祈求竖火把仪式的顺利与来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民族村内纳西族的火把节较彝族、白族程式简单,农历六月二十五16点在纳西族村三多广场举行。开始前大家忙碌着摆放贡品,装饰火把,在火把上栓起一根根红布绸,插上松毛,燃起松毛堆。面对三多塑像,东巴手执经文诵读,祭天祈福,村民站立其后。东巴示意开始竖火把,于是村民合力抬起将火把竖起,东巴继续诵读经文,不时蘸取祭品撒向远处,朝松毛堆做抛洒动作,诵经结束后,村民将香插在火把节上,竖火把仪式就算结束。
村民在拥有民族文化基础之上参与各项活动,开展相关工作,存在自我与他我的纠葛与困扰,“这项仪式我们没有”“我们不是这样过的,这里就是给游客看的”,两种声音的交织影响着村民的文化适应的程度,于此村民历经心理挣扎才得以将展演呈现。
游客:借村民之名。民族村的火把节为游客提供了成为俗民的机会。游客与民族村的村民因火把节之机相遇在同一时空下,从而结成了群体关系。
火把节期间,民族村举行了火把拍卖活动,拍下火神火把的游客,将成为当晚的点火嘉宾,一齐点燃团结广场场中的天神火把。参与欢度火把节的八个民族各自准备了一支火神火把,每支火神火把都象征着不同的含义,每支火把从装饰到含义赋予都展现了本民族特色。对于此项活动,部分游客积极参与竞拍,且通过笔者的观察,五天节期内,每天彝族火神火把都拍出了当日最高价,可反映出游客对于彝族火把节的认同心理;另一方面,居首位出场的藏族火神火把也拍出当日的次高价,“特意来过火把节,想要第一份祝福”,可见博得头彩或许是游客出行的动力,也是对今后生活的祈盼。十支火神火把竞拍结束后,游客与少数民族姑娘小伙返回舞台,逐一接受毕摩的诵经祝福,随后点火嘉宾借神龛之火点燃各自火神火把,最后共同将场中天神火把点燃。在毕摩的诵经声中,熊熊火焰包围着火把,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这一时刻,游客借火把传递着自己美好的祝愿,希望能够实现。
形塑表演文本的符号代码
圆圈舞。圆圈舞是我国西部民族特有的一种歌舞形式。西部地区民族民间舞蹈的群舞中最多的运动路线就是围圈而舞。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的聚集地,民间广泛流传少数民族兄弟姐妹“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火把节是民众除旧布新的节点,夜色撩人,借火把的光亮人们拉手围圈,踏地为节。圆圈是天体神界的象征,是人生和万事万物生存与发展的轨迹。圆圈运动,是宇宙循环和人生轮回象征。男女老幼在周而复始、通宵狂欢的舞蹈中,尽情宣泄、交流他们的情感以求得心理平衡。面对面,围着火把向心运动,给民众带来极大的安全感,齐整的步伐,齐整的挥动,在他人的确证与自我生命真实的体验之下,群体意识在这狂热之中悄然扎根。村民与游客共同进行圈圈打跳,经过短暂的模仿学习,游客也可做出与他人整齐的动作,这个时刻,无谓男女,无谓职业,大家都为同跳一支舞而兴奋。
火把。火把节中出现的火把因其所属不同,分为四类,团结广场中央为点火嘉宾点燃的天神火把;过节民族各自装饰的带本民族特色的火神火把;供游客参与火把狂欢的吉祥火把;彝族、白族、纳西族村寨内所竖火把。不同类别的火把,有不同的所指含义。团结广场作为活动的主会场,上演的节目集各民族之长,融现代与传统为一体,场中的天神火把,一为团结各族人民欢度节日,二为祭祀天地祖先,是民族村内最大的火把,此火把由游客竞拍所得的各民族火神火把来点燃,是为民族融合的体现;各民族的火神火把被寄予多种祝福之意,竞拍所得的游客博此彩头,并借这个机会为自己的心愿达成辅以神力;游客所购买的大、中、小型号吉祥火把,可看作参与节庆的标志,左手持火把,围成圆圈舞动,是狂欢之夜最欢乐的时刻。彝族、白族、纳西族村寨内火把,由各族村民自己点燃,相较团结广场内的大场面,村寨内部更具家的感觉。火把燃起,欢歌打跳也开启,节日的喜悦溢于言表。火把是火存在的载体,火彻底结束了先民茹毛饮血的时代,火带来了安定、和平的生活,人们借火把燃烧的熊熊火焰以示对天地神灵最虔诚、最热烈的崇敬,以期得其庇佑。
民族村火把节是经交流协商的表演文本。民族村火把节在其文本化过程中,结合旅游地的特点,因地制宜地进行再生产、再创造。作为旅游产品的火把节一方面为增加其吸引力而深挖民族特色,整合相关文化要素经舞台化处理后进行展演。另一方面遵循风俗旧制,保留部分不可公之于众的内部活动,为民族节日留有隐秘的自我空间。真实与表演之间的取舍以原生文本为基准,管理者征求本民族村民的意见,以期呈现出既符合游客要求又可充分调动村民工作积极性的表演。在此过程难免出现“我们不是这样过的,这里就是给游客看”的妥协。旅游舞台上的火把节是一种动态性的表述,不仅指其文化表演的过程,而是指表演的呈现通过交流实践来实现,是村民与游客之间协商的结果。从心理认同上看,村民通过分离的方式实现文化适应,游客则在火把节这一场域中获得了别于观众的俗民身份。村民呈现的表演前台与游客的旅游前台在旅游空间中相遇,双方在互相凝视中作出选择,游客依提供的环节结合自身兴趣有所取舍,村民依游客的反应适时调整,共同努力之下构建出旅游的认同空间。在此空间之下,火把节这一表演文化获得新生,展现出独特的文化魅力。
此时的火把节,在其文化功能上是兼具敬天祭祖,交游娱乐的综合性节日。毕摩参与的祭火仪式、祭树神、祭火神,白族的祭本主等仪式活动是火把节最核心的要素,即使时空转变,从原生地到旅游地,其神圣性也深刻影响着村民,“我本来想在竖火把时许愿的,但是没空回去啊,没赶上”。火把狂欢为游客与村民提供了释放压力的机会,围圆打跳,纳西三部曲、彝族阿细跳月、摩梭人的甲蹉舞等,身处其中,尽情感受。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