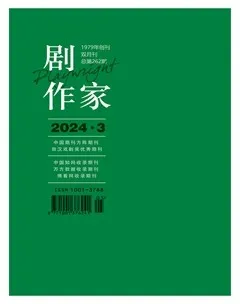话剧《萧红》的人物塑造与艺术特色
徐丽松
摘 要:由齐齐哈尔市话剧团创作并演出的话剧《萧红》,是国家艺术基金2023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它以抒情写意的风格塑造了中国近代女作家、“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萧红的人物形象。萧红坎坷的人生、漂泊不定的命运和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都昭示着一个时代的悲歌。该剧在人物塑造、戏剧结构和表现手法等方面都独具特色。本文将试论话剧《萧红》的艺术风格和艺术特色,以探析该剧的舞台阐释与戏剧脉络。
关键词:话剧《萧红》;人物塑造;艺术特色
《萧红》是齐齐哈尔市话剧团的原创话剧,由知名学者叶君编剧,著名导演邢友江执导。该剧首次以话剧的形式书写了女作家萧红的传奇人生,填补了中国话剧舞台没有萧红传记的空白[1]。被誉为“三十年代文学洛神”的萧红一生坎坷、颠沛流离,历经战乱和情感的羁绊,最终生命定格在本该灿然绽放的31岁。面对这样复杂而丰富的生命个体,话剧《萧红》以诗化的叙事风格和细腻灵动的表现手法对人物的性格和心灵进行深入的挖掘,着重表现了萧红“一生漂泊,一路抗争”的人生经历和短暂的生命过程,通过对人物塑造和舞台美学的积极探索,实现了情真意切的戏剧表达。
一、饱含深情、细腻生动的人物刻画
话剧《萧红》以萧红的情感经历为主线,刻画了萧红与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之间的情感往事,以深情的笔触描写了她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短暂而鲜活的一生。从小生活在呼兰河畔的萧红在爷爷的呵护下长大,但在她9岁时母亲去世后她开始经历人生的苦难,父亲不断阻挠她读书,并把她许配给地主的儿子汪恩甲。21岁被未婚夫汪恩甲抛弃、怀着孩子的萧红流落到哈尔滨,因为交不起房钱、饭钱面临着被卖到青楼抵债的窘境。在道外区东兴顺旅馆的储藏室她遇到了作家三郎(萧军),两个同样有着文学梦想的青年相遇,从此开启了他们彼此纠葛的另一种人生。话剧《萧红》以精神写照的方式提取了萧红不同的人生片段进行人物塑造,戏剧性深层延展,从青春少女到成熟女性,在家国动荡、饥寒病弱、感情挫败及理想与现实的交错中,作家萧红的形象一步步走向观众,逐渐立体和丰满。
如何让人物具有感染力和生命力?这是话剧《萧红》着重处理的问题。在剧中萧红有着鲜明的性格特征,她善良勇敢、敏感多情,同时也热爱自由、充满叛逆精神。和萧军初相遇,即使被未婚夫抛弃、身怀六甲,但萧红仍然有着青春少女的率真,她与萧军一见如故迸发出炽热的感情:“我想热热烈烈地爱一次,但我知道我这辈子注定要跟那些我不爱的东西们周旋,这是我的命。”这样的台词既表达了萧红宿命的清醒,也抒发了她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的勇敢。充满激情的萧红在这个时期创作出了深刻揭露社会现实的小说《生死场》。在上海,萧红得到鲁迅先生的提携,鲁迅对小说《生死场》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许,在他面前萧红仍像初入世事的年轻女孩一样活泼热情。萧红和鲁迅讨论文学作品也讨论穿着打扮和食物,萧红跟许广平说“萧红”笔名的由来——希望自己和萧军的名字永远连在一起,以后可以被别人称为“二萧”。这时的萧红依然充满憧憬和希望地沉浸在爱情里。而随着萧军的出轨和背叛,二萧之间的关系也岌岌可危。“爱便爱,不爱便丢开”,萧军曾经看似洒脱的感情宣言正是最终斩断他们情感的利剑。为了躲避战乱,一路辗转,在临汾火车站萧红与丁玲、聂绀弩一行要前往西安,萧军却要留下来打游击,这意味着他们的爱情也将就此终结。这时的萧红已经从青涩到成熟,独立坚强的女性意识开始觉醒,她努力抗争着自己的命运。当萧军来西安找她时,她勇敢地提出“三郎,我们永远地分开吧”,并与仰慕自己的端木蕻良结婚,开始了人生的又一段旅程。日军入侵香港时,病重的萧红对陪在身边的骆宾基回顾了自己的人生——“无边的流亡,无尽的伤痛,一口箱子就是我的一生”,这样的总结让人唏嘘。在戏剧中创作者没有简单地書写萧红的人生经历,而是通过散点式的情节萃取萧红生命历程中的情感节点,注重用细节来刻画和展现人物形象的复杂多面,描述人物内心的痛苦与挣扎,多条情感线索的链接让萧红的人物塑造细腻生动,真实可信。
话剧《萧红》实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戏剧内容充满人文情感,在人物塑造上投入了创作者的悲悯情怀,以对萧红情感、生命饱含深情的书写勾勒出真实的戏剧空间,使观众在情感和审美上得到共鸣。
二、充满张力、彼此映照的戏剧结构
话剧《萧红》含蓄抒情,剧中多次以人物独白的方式引用萧红的作品,包括《呼兰河传》《回忆鲁迅先生》和组诗《砂粒》。这样的设计增加了剧作的文学性,充分还原了时代背景,更深入地开掘了人物的精神世界,让萧红的人物形象鲜活真切。该剧的另一大艺术特色就是采用了“戏中戏”的戏剧结构,使剧作节奏起伏、充满张力。
萧红的一生都在追寻文学理想,视写作为生命,在颠沛流离、短短的31年的生命里她留下了九十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她的文字清新、质朴、温暖而悲凉,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宝库中的经典。在话剧《萧红》中创作者多次运用“戏中戏”的形式将小说《生死场》的片段展现在舞台上,并与萧红的人生彼此映照、形成互动。这样的戏剧结构避免了话剧情节平铺直叙的发展,以戏剧性的手法呈现了文学的神韵,在虚实之间烘托出萧红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2]p64。剧中,在鲁迅读萧红小说《生死场》的书稿时,舞台上出现了书中人物金枝与成业约会的情景,那时的他们甜蜜、激情,可以为了彼此勇敢地面对周围的一切,这映照出萧红与萧军初相遇时浓郁美好的情感。剧中第二次出现《生死场》的情节时,金枝和成业已经成婚,因为穷困潦倒、困苦饥饿的生活,成业暴露出自私暴躁的本性,他和金枝激烈地争吵,把一切怨气发泄在女人身上,甚至在盛怒之下摔死了他们的孩子,让一个小生命猝然消失。在这里金枝的人生遭遇仿佛是萧红的侧影,也预示着萧红悲剧的命运。因为在与萧军的情感中萧红始终是被动的,她的深情迎来的是一次次的背叛,即使怀着萧军的孩子,她也没有得到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回答。两人在临汾分别后,萧红的女性意识开始觉醒,二萧从此走向了人生不同的路口。之后萧红和端木蕻良结合,但婚姻并没有成为她庄严的约束,没有担当的端木蕻良多次不告而别,让她的情感又遭遇新的伤痛。日军攻打香港的炮火燃起,病床上的萧红说:“这几天我常想起生死场里的金枝。”“我的痛苦源于我是一个女人,金枝也一样,女人的天空是低的。”这时舞台上又出现了《生死场》的片段,逃离乡村的金枝回到故乡,王婆在叠纸钱,面对王婆对日本侵略者的控诉和恐惧,金枝却已经麻木和平静,她说:“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了……俺当姑子去。”此时的萧红病重在身,经历了不断的流亡和情感的挫败,她已经能够平静地接受所有的经历与遭遇,她和她笔下的金枝互为镜像,在她们的彼此呼应里生命的悲凉具有深意,实现了人物塑造的内在逻辑构建,也引发观众深层次的思考与同情。
剧中还以萧红的作品《呼兰河传》为依托,以“戏中戏”的形式将童年的萧红和成长后的萧红相互映照,以诗化的叙事风格增加了人物的质感和剧作的审美意蕴。在剧中被汪恩甲抛弃、身陷小旅店的萧红梦见了自己的爷爷,舞台上荣华(萧红小名)在家里的后花园和爷爷嬉闹,爷爷对她非常疼爱,荣华用玫瑰花装饰爷爷的草帽。在生命的终点,萧红思念家乡和亲人,这时童年的记忆再次出现,爷爷教荣华背诵唐诗《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散文诗般的片段投射着萧红的心理情感,实现了戏剧性和文学性的共生,让叙事情节更加富有哲思与回味。
同时,话剧《萧红》还采用了首尾呼应的方式升华主题。序幕,农历七月十五爷爷领着荣华到呼兰河边放河灯,并告诉她“死去的人如果能顶着一盏河灯,就可以找到回家的路”,尾声魂归故乡的萧红从皮箱中拿出荷花灯与爷爷还有儿时的自己一起“回家”。白山黑水、漫天飞雪,这条回家的路是如此哀婉艰辛,意境深远的画面烘托出这颗耀眼的文学星辰悄然陨落的悲剧结局,不禁让人潸然泪下。
三、深邃简约、彰显内涵的舞美设计
舞台美术是戏剧重要的审美要素。优秀的舞美设计能够营造戏剧氛围,烘托人物情感,增加叙事的张力,传递出“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意蕴。话剧《萧红》的舞美设计化繁为简,以深邃简洁的色彩布景展现时代气息,彰显戏剧的主题内涵。
话剧《萧红》以黑色背景、深棕色道具为基调,营造出含蓄深沉的意境,无言地诉说着萧红沉重的生命和她所经历的痛苦与挣扎。话剧的开篇,在哈尔滨道外区东兴顺旅馆二楼的储藏室,萧红与萧军相遇,舞台上斑驳的黑灰色墙壁后露出俄式教堂的葱头圆顶,简陋的桌椅、床铺,意象性的大块方砖的堆积,空灵的舞美设计彰显了舞台的写意性,让戏剧空间呈现出诗化的情境,在不知不觉中把观众拉回了20世纪30年代哈尔滨的夏天,和演员一起走进萧红的生命与情感。经过一次次的情感冲突,萧红与萧军渐行渐远,这对曾经的有情人终于走到了分离的节点。由于战乱他们一路辗转,在临汾火车站,二人面临去与留的选择。一个“临汾”火车站的站牌、一个悬挂在半空的钟表就是这场重头戏的布景,站牌是地点,钟表是时间,这些都显示和记录着萧红这段最为伤痛的记忆,也隐喻着他们二人的感情再也回不到从前。舞台的戏剧空间和人物内心的矛盾彼此观照,渲染出凝重忧伤的环境氛围,彰显了话剧《萧红》叙事诗剧的唯美风格。“戏中戏”在展现小说《呼兰河传》和《生死场》的情节时,舞台上基本空无一物,只用燈光来烘托人物的表演,他们的出现仿佛是萧红对自己一生情感和创作的回眸,舞台具有抽象的象征意味和震撼心灵的艺术效果。
在话剧《萧红》中还巧妙地运用软幕和舞台的流动来完成剧情的起承转合,形成的意象性的时空呈现了诗化的内在表达。在表现鲁迅阅读萧红小说《生死场》的戏剧情境时,舞台用软幕分隔出前后两个区域,幕后是鲁迅翻看手稿的影像,幕前是成业与怀孕的金枝约会、成业和村里的老妇人对话及获知金枝生产的段落情景。这样前后视觉的重叠,隐喻着人物的命运,同时也表现了萧红文学创作深刻的内涵。在上海,萧红来到鲁迅的寓所探望并接受先生对自己作品的指正,在和鲁迅、许广平的谈话中萧红不小心说出了萧军的本性——“他是一个随性的男人”,这句话暗示着二萧之间隐藏的危机。这场戏结束时,鲁迅和许广平在书房中的身影和布景一起移动消失在黑暗中,接着空旷的舞台再现了《生死场》的片段,只是这时曾经和金枝如胶似漆的成业,已经变得偏执和暴躁,他把对生活的绝望都怨在女人身上,甚至摔死了孩子。舞台的流动,让场景变化自然紧密,同时让戏剧故事超越了表面的情节,将思想内涵和外化表达推向心灵的层面。
鲁迅先生曾为小说《生死场》写下的序言“生的坚强,死的挣扎”何尝不是萧红自己人生的写照。作为为萧红立传的戏剧作品,话剧《萧红》通过多元化的人物塑造和舞台表达挖掘了女人萧红和作家萧红的人性深度,做到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和谐统一,相信通过国家艺术基金的扶持和全国巡演的历练,创作者们将不断雕琢细节,扩展创作空间,让这部剧真正成为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精品力作。
参考文献:
[1]吴泽涛:《话剧〈萧红〉别具诗心》,《光明日报》,2018-7-17
[2]郎春燕:《话剧〈萧红〉的创作特色研究》,《知与行》,2020年第2期
(作者单位:吉林省艺术研究院)
责任编辑 岳莹 王巍
——一本能够让你对人生有另一种认知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