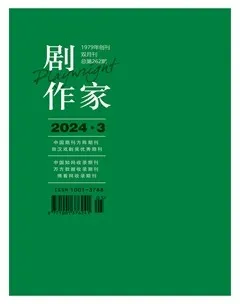权力的博弈
于星华 李言实
摘 要:《费城,我来了!》由爱尔兰知名剧作家布莱恩·弗里尔创作于1964年,剧作中加尔移民美国在即,却陷入不同空间之下的权力争锋而进退两难。本文结合列斐伏尔空间理论及福柯权力理论,分析精神空间中内外加尔之间、物理空间中加尔与父亲,以及社会空间中加尔与美国姨妈之间的权力博弈,并进一步探究其背后所分别映射的爱尔兰与北爱尔兰、英国与美国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揭示作品所反映的爱尔兰个体乃至民族的精神困境。
关键词:《费城,我来了!》;布莱恩·弗里尔;空间理论;权力博弈
布莱恩·弗里尔是爱尔兰当代杰出的剧作家之一,被誉为“当代爱尔兰戏剧之父”。弗里尔一生笔耕不辍,四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共创作各类作品三十余部。《费城,我来了!》(以下简称《费城》)系弗里尔第一部成功之作,一经上演便大获成功,更被评论界视为当代爱尔兰戏剧的分水岭[1]P36。剧作聚焦主人公加尔·奥唐纳移民美国前夜的心理斗争。加尔向往美国物质生活的同时又不舍家乡的传统,在回忆与现实的交织中陷入去留两难的挣扎彷徨。
《费城》创作时期正值爱尔兰实现民族独立并建立共和国之后迎来的第一波移民潮之际,同时也处于二战之后美国迅速崛起之时。在如此特殊的内外历史节点写就的佳作,相较于《翻译》《卢纳莎之舞》等名作却未获得我国内评论界的足够关注。国内现有研究中,学者林玉珍从爱尔兰移民经验出发,对剧作中所涉及的“美国丧礼”特殊的操演性时空进行探究;雷馥源分析了二战后美国强权文化主导下爱尔兰民族的身份认同危机;刘艳芳在其博士论文中用沃尔夫的媒介间性理论,对《费城》进行了音乐叙事研究。既有研究从历史、文化及艺术手法等方面对剧作中所涉及的移民主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但尚未有研究触及移民主题背后蕴含的多方面权力斗争与博弈,更未将其与空间表征相结合,探析人物之间权力之争背后所隐喻的爱尔兰与北爱尔兰、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复杂关系。
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空间转向使空间逐渐回归研究者视野。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在其著作《空间的生产》中指出,空间本身是一种社会生产模式和知识行为,任何空间都由相互关联的三个母体构成,即“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空间”[2]P33,分别对应物理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本文意在探究剧作在上述三大空间层面人物之间存在的权力博弈,以及背后所映射的爱尔兰与北爱尔兰、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复杂关系与权力争锋,从而揭示20世纪60年代爱尔兰民族的精神危机以及剧作家对此的敏锐捕捉和深切关怀。
一、自我还是本我:精神空间中的内外加尔
剧作中第一对权力博弈表现为精神空间之下加尔的“本我”与“自我”之争。加尔在现实生活中一事无成:母亲早亡,父子关系紧张,大学辍学后在父亲的杂货店打工,薪水微薄而前途渺茫,心爱的女友也弃他而去。这让加尔在潜意识中始终存在着远走高飞、离开偏僻落后的家乡、在新的天地改头换面有所作为的“本我”渴望,但因迫于现实规约而在“自我”的抑制下始终蛰伏。移民前夜,加尔仿佛已然置身于美国新生活之中而情绪高涨,“自我”的阀门发生松动,象征“本我”的内在加尔就此产生,和现实中“自我”的外在加尔同时呈现于舞台。在开场前的舞台提示中弗里尔便指出:“虽然外在加尔可以跟内在加尔交流,但是外在加尔看不到内在加尔,正如人不可能看到自我的内心世界。”[3]P26如此设定将“本我”的精神世界分离出来并赋予其实体形态,“本我”和“自我”拥有同等地位;内在加尔对于外在加尔而言看不见摸不着,却能被观众和读者所感知,内在加尔由此获得一定程度的全知视角,并通过对外在加尔的“凝视”将其一举一动始终置于自己的权力监视之下。福柯曾以边沁设计的“全景敞视监狱”为例指出,监控者通过“权力的眼睛”的注视实现对被监控者的权力控制[4]P88。一如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所指出,被监控者在目光的压力之下自觉成为自己的监视者,从作为主体的人的自为存在降格为对象性的自在存在。
“本我”释放之初,潜意识中压抑的对于成功的渴望和对自己所受不公待遇的反击最为强烈,内在加尔因此构建了一个“本我”的精神想象空间。在这里,加尔·奥唐纳不再是默默无闻、四处碰壁的小镇青年,而成为超人般的存在:拥有“魔幻之足”的巴里贝格足球队中卫,能够边演奏边指挥门德尔松古典音乐的音乐家,还是准备接手全球最大连锁酒店的商业奇才。内外加尔更是一改往日面对父亲的敢怒不敢言,对其进行肆意嘲讽和戏谑。他们幻想老奥唐纳各种出糗,还“以汽车评论员的油腔滑调”[3]P44如同介绍时装秀般描述父亲的日常着装,尽情发泄自己的不滿和愤恨。作为加尔整体,内外加尔配合完成的想象式场景模拟是对自己权力的行使和对既定权力框架的反抗;而面对内在加尔的盛情邀请,生活失意的外在加尔自然乐见其成并积极配合,任由内在加尔指挥和摆布,在完成对精神空间的建构和物理现实中的操演的同时也自愿与被迫参半地让渡个人意志,由此为自己的“本我”所支配和控制。第一幕结尾博伊尔老师造访后外在加尔内心的动摇在内在加尔的注视中被察觉,后者不惜中伤诋毁博伊尔,并强迫外在加尔唱出“费城,我来了”的旋律,以坚定其移民决心。
内在加尔由个人意识所衍生,独立于既有的现实社会规约范围之外存在,言行举止皆为其自由思想之体现,且不为除外在加尔之外的人物所感知。原本平静的移民前夜正是由于内在加尔的存在而暗流涌动:内在加尔翻出过往的回忆片段并进行情景再现,自己置身其中对外在加尔当时的表现品头论足;记忆片段本就是外在加尔不愿回首的往事,既要忍受伤疤被重新揭开的痛楚又要努力抵御内在加尔的冷嘲热讽,外在加尔左支右绌,其移民美国的计划也随之摇摆不定。当外在加尔唱着“费城我来了”编织着自己的美国梦登场之初,内在加尔便不断提醒他,移民意味着和家乡的过往一刀两断,从此踏上陌生未知的土地:“离开这片育有鸵与鹬的土地,离开阿兰毛衫和爱尔兰赌彩吗?你准备去一个世俗的、无宗教信仰的、粗鄙的唯利是图的异教国家吗?”[3]P29萨特的“注视理论”认为,他人的注视通过其关于“我”的存在的认识影响“我”,使得注视中的“我”意识到作为注视对象的自己,但与此同时,他人的目光令“我”产生的骄傲或羞耻本质上都是对他人认识的屈从。美国姨妈丽姬来访时加尔不明不白地便认亲并接受其一起生活的邀请,事后面对内在加尔的百般奚落,外在加尔最后竟夺门而逃,留下内在加尔在其身后道:“承认吧,你不想走。”“本我”与“自我”之间的权力博弈并无赢家,诚如管家麦琪所言:“明天他会很难过,也许这周,甚至下一周都会这样。”[3]P92
内外加尔的分裂不仅是个人精神空间中的自我权力博弈,还有政治历史隐喻,即爱尔兰与北爱尔兰之间的历史、政治、宗教等多方面的纠缠和博弈。两者之间的冲突矛盾根源于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对爱尔兰殖民统治。17世纪英王亨利八世改英国国教为新教,为圣帕特里克长期传教之下的爱尔兰国教天主教所不容。伊丽莎白一世为巩固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将大量新教徒迁徙至爱尔兰北部阿尔斯特省等地区并分配土地,在实施垦殖计划的同时却未强制推行新教。土地纷争和宗教差异致使矛盾升级,最终于1641年在阿尔斯特爆发大叛乱(The Great Rebellion)。新教徒被当地天主教徒武力驱逐。新教势力随即进行反击。1649年“护国公”克伦威尔武力镇压爱尔兰天主教,教徒被剥夺土地并被驱逐至偏僻荒凉的爱尔兰西部康诺特省。及至世纪末天主教支持者詹姆斯二世在博因河战役(Battle of Boyne)中战败后流亡爱尔兰,使后者真正成为英国殖民地。爱尔兰境内日益分化为两派:拥有土地和权力,背靠英国支持英爱统一的新教徒少数派,以及被镇压心怀不满、渴望爱尔兰摆脱英国统治实现民族独立的天主教徒多数派。两派势同水火,彼此冲突不断,直至1948年爱尔兰宣布脱离英联邦,北部阿尔斯特六郡仍归英国统治,成为北爱尔兰,爱尔兰正式实现南北分治。爱尔兰独立后两教派之间纷争并未缓和,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势。面对爱尔兰政府独立后对南北和平统一的诉求,北爱尔兰境内天主教徒大多赞成,而占人口多数的新教徒则拒绝脱英。英国当局政策和法令的推行更是使北爱尔兰天主教徒长期遭受多方面歧视。爱尔兰共和军以推动南北统一为名义在北爱尔兰发动一系列袭击事件,北爱尔兰问题最终于1960年代末爆发。
透过《费城》的“小家”题材,弗里尔充分展示了其作为本土作家更加广阔强烈的家园意识。自1964年上演《费城》以来,弗里尔大部分戏剧场景都设在一个虚拟的名为“巴里比格”(Ballybeg)的村镇,它是爱尔兰语“BaileBeag”(小镇)的英语化形式,也是弗里尔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巴里比格位于多尼戈尔郡的西北部,“位于德里、多尼戈尔和蒂龙交界的边缘地带,一个以天主教为主的社区。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迫下,这里的人们过着一种堕落的生活”[5]P70。通过对位于边缘地带的边缘人物内外加尔的刻画,弗里尔再现了自己物理和精神家园的矛盾和分裂。弗里尔出生于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家庭,却在信奉新教的城市德里(Derry)长大。他“既不认可南方的保守主义,也不赞同北方的霸权主义”[5]P84。长期的社会氛围和文化身份的割裂使他反思自己“非南非北”不知何去何从的漂泊流亡状态,其精神的迷茫彷徨即体现在剧作中内外加尔两人去留两难的境地。偏僻落后的巴里比格在弗里尔看来,“在这样随和氛围下成长是件挺好的事,但从精神层面来说,这不是一个太好的地方”[1]P40。其笔下的加尔正是处于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流亡之中:家乡巴里贝格在物理空间中位于爱尔兰与北爱尔兰交界处,自己的精神空间更是处于传统与现代、熟悉与陌生、希望与失望、怀疑与肯定的边界地带。通过加尔“离家”的失败,弗里尔再现了1960年代移民潮之下爱尔兰民族物理空间的居无定所和精神家园的颠沛流离,其于1980年成立的户外日戏剧公司(Field Day Theatre Company),更是致力于打造一个“没有分界线的、完整的”爱尔兰“第五省”(The Fifth Province),从事重塑爱尔兰精神家园的伟大尝试。
二、顺从还是反抗:物理空间中的父子之争
《费城》中所体现的第二对权力博弈则是物理空间下父子之间的权力相争。全剧共三幕四场,基本集中在厨房和加尔卧室两个物理空间。厨房是爱尔兰戏剧舞台惯用场景,用以区别于城市文化特征。一方面,熟悉的场景画面拉近了观众与舞台的距离;另一方面,该剧的舞台表演突破厨房作为原型地位(archetyPalstatus)的框架,改变了爱尔兰农村剧的前景惯性,添加了以往舞台上不常见的卧室场景,产生陌生化的效果。李成坚指出,爱尔兰戏剧场景中常用的厨房空间和炉火意象是家的物理固化形象,代表着温暖和团聚,是心灵的栖息之所,更是自我认同的最终归宿[1]P48。然而,《费城》中的家庭既不温暖更非团聚,本应温馨的厨房和卧室异化为父子权力博弈之下的双方阵营,两人身处其中行使权力明争暗斗,物理空间由此成为福柯笔下的“权力空间”。
剧中“内在加尔”原文为PrivateGar,可另译作“私密加尔”。卧室作为加尔的阵地,所行使的权力正是来源于物理空间的私密性。剧作中未见有除加尔之外者踏足其卧室,即便强权霸道如父亲也未曾进入过儿子的卧室,在楼下与奥伯恩神父下棋时听到楼上卧室传来的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及而并不多加过问。亲如生母的管家麦琪每当给加尔送去茶水和换洗的衣物,也只是站在房间门口同其交谈。精神空间的建构离不开物理空间的基础,正是在绝对安全私密的卧室空间,内在加尔才能最大限度地展现“本我”个人意志,反抗父亲既定的规则框架。卧室由此成为父亲缔造的权力空间之外的“伊甸園”,成为弗吉尼亚·沃尔夫笔下真正意义上的“一间自己的房间”。身处自己的阵营,加尔随心所欲,畅所欲言,一切规则和秩序在独属于自己的物理空间中都短暂失灵,一切精神空间的奇思妙想在私密的物理空间中都能美梦成真。他可以将工作服卷成一团当作足球来射门,也可以对着门框立正敬礼,假装回答移民长官的问话,还能“驾驶战斗机掠过海面,头伸出窗外朝老奥唐纳吐口水”[3]P29。然而,正如前文所言,加尔对于权力的行使仅仅局限于自己物理空间相对独立的维护和精神空间中的想象式操演,“由于双方权力的不对等,只能隐藏情绪,通过角色切换来操演其权力”[6]P65。现实中的加尔在父亲长期的权力压迫之下始终处于失语、失权和被动处境。
厨房作为家庭里的公共场所,本应是家庭成员欢聚一堂、交流沟通之地。《费城》却一改常规,厨房成为父亲对儿子行使权力压迫的物理空间,因此成为父亲的阵营并为父亲所掌控。剧作中老奥唐纳对于权力的运作来自三方面:经济上的压迫、言语及行为上的规训。经济控制奠定了权力控制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将经济视作社会生活的中心,认为权力关系来源于并服务于经济生产,用以维系一定的生产关系及经济运作。父亲正是首先以经济手段实现对加尔的控制。加尔出生不久母亲的去世,对于加尔父子而言不仅是家庭的破碎更是权力关系的失衡。父亲在独自抚养加尔的同时也获得了对他的绝对控制权,在其辍学后用杂货店的繁重工作绑住加尔,还只付给他微薄的工资,甚至没有管家麦琪的多。面对父亲的经济压迫加尔曾有过微弱的反击,在与女友凯蒂商讨结婚事宜时曾透露过自己在农场卖鸡蛋的“投资”并得到了赞许,然而这样的努力终究是杯水车薪。经济条件的困顿和无望的前途是加尔生活失意的主要来源,更是其计划移民美国的直接诱因。在对美国的幻想中加尔毫不掩饰对于出人头地的渴望。面对凯蒂身为参议员的父亲,窘迫的经济条件使加尔语无伦次乃至仓皇而逃。凯蒂最终嫁给门当户对的金医生。在前来道别的朋友面前加尔缺少地位和话语权,即将移民的事实也一度遭到忽略。他更是被美国姨妈反复强调的富足物质生活所轻易吸引,不明不白地便同意其共同生活的邀请。
在完成经济控制的基础上,父亲进一步从言语和行为上对加尔进行规训。“规训”,即“规范化训练”。它不同于借助暴力、酷刑等手段使人服从,规训是通过日常的规范化检查、监视和训练来支配、控制人的行为,制造出驯服的肉体,以微妙和非接触的方式得以实现。加尔平日里并无交流障碍,但每当面对父亲时就变得口吃或沉默不语,只有内在加尔在一旁为之打抱不平。更有甚者,加尔原本清晰的工作記忆也在父亲劈头盖脸的质问之下变得模糊,一回到卧室便又恢复如初。这种“习得性”失语和失忆正是长期言语规训的结果。纵观全剧,父子间未曾出现过肢体接触或冲突,但加尔的行为却表现出本能的服从性和训练痕迹。内在加尔曾嘲笑父亲一成不变的日常行为,称其为“我见过的最听话的父亲”[3]P45,却不曾发觉自己才是父亲精心规训下训练有素的产物:面对老奥唐纳登场之初对自己的召唤,内在加尔表示“让那个家伙继续叫”,外在加尔却“本能强于理智”,冲出去开门[3]P31;加尔对父亲深恶痛绝,却仍尽职地重复每日的工作,在杂货铺进货钢丝卷并放置捕鼠夹,对出了差错而受到责备也习以为常;刚发了工资的加尔问父亲是否再来一杯茶,却没有注意到其询问超出了既定的规训范畴,自己的殷勤讨好也被父亲“我确定你知道我从来不喝第二杯茶”的回复泼了冷水[3]P47。父亲长期的经济控制及日复一日的规范化训练和机械性工作重复成功将加尔训练为驯化服从的肉体,使之如同编写好的程序按部就班行事,了解权力发出者的习惯和偏好并听从其安排与吩咐。
权力作为交错流动的关系网络,不为任何个体所拥有,也不简单表现为控制与被控制的二元对立。控制的对立面也经常以反控制的形式呈现。博弈双方一旦突破边界,被控制者便会处于上风,转而成为反控制者甚至控制者,从而实现双方关系的转换。剧作中,由于双方权力关系不对等,暴力型直接斗争断不可行,在内在加尔的释放和农场卖鸡蛋的投资等无声的间接斗争接连失败之后,加尔最终通过移民美国计划成功实现反控制,自己也一度成为控制者。父亲的经济手段和言语行为规训需要以被控制者的物理在场为前提而生效,而加尔正是借助物理空间的转移来巧妙躲避权力网络的规约,其缺席使一切控制手段无从谈起,不攻自破。在加尔的反控制下,父亲的权力控制逐渐松动瓦解,是夜老奥唐纳一夜无眠,与同样未眠的加尔在餐桌前相遇,安静倾听加尔走后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嘱托,并笨拙地询问其明天的日程安排,试图对加尔进行挽留。父子之间的权力博弈同样没有赢家,临走前对于缓和彼此间紧张关系的尝试因两人对于童年泛舟回忆的巨大出入以失败告终。
弗里尔通过对父子间权力博弈的刻画,巧妙映射了爱尔兰与其前殖民宗主国英国之间的复杂关系。一如剧作中的加尔,爱尔兰处于英国殖民统治长达几个世纪之久,遭受来自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全方位压迫:12世纪英王亨利二世率军援救爱尔兰并自封“爱尔兰领王”(Lord of Ireland),从此拉开英国对爱尔兰殖民统治的序幕;16世纪亨利八世创立英国国教新教并与罗马天主教廷决裂,随后在爱尔兰正式称王(King of Ireland);1604年英爱金赛尔之战(Battle of Kinsale)中爱尔兰战败,盖尔秩序和文化日益没落;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克伦威尔对爱尔兰岛上的天主教村庄大肆屠杀。最终在率先进入工业革命的“日不落帝国”的武力逼迫下,爱尔兰被正式纳入英国版图,成立“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王国”,便是剧中加尔大学辍学后来到杂货店打工,自此屈居于父亲的权力压迫之下的真实写照。19世纪中期,爱尔兰主要粮食作物土豆严重歉收,英国政府却坐视不管并拒绝赈灾,最终引发“大饥荒”(the Great Famine),爱尔兰人口锐减约四分之一,并迎来第一波移民高潮。饥荒的惨剧让爱尔兰人民深刻反思英国政府的殖民统治并激发了民族意识的觉醒。正如加尔对父亲多方压迫的抗争,面对英国强大的综合实力,几百年来爱尔兰人民前仆后继,始终不曾放弃过争取民族解放的努力,最终于1949年成立爱尔兰共和国,真正实现民族独立;1973年加入欧盟后经济取得迅速发展;90年代随着大量外资涌入,国内工商业、旅游业及信息产业迅猛发展,爱尔兰进入“凯尔特之虎”时期(Celtic Tiger,1990—2005),实现了经济腾飞和各方面的迅猛发展。
三、此岸还是彼岸:社会空间中的加尔与姨妈
权力博弈在社会空间中集中体现在第二幕中移民美国的丽姬姨妈一家的造访。姨妈移居美国多年且小有成就,年近六十却膝下犹虚,遍寻美国名医仍然无果,此行便是专程来向加尔抛出橄榄枝,希望他能同他们夫妻二人共同生活并继承家产,却在奥唐纳家备受冷落:妹夫老奥唐纳借故参加同乡晚辈凯蒂·杜根的婚礼,对小姨子避而不见,应绝非偶然;管家麦琪推脱不开,却对客人生硬冷淡,始终没有好脸色。爱尔兰人对准移民的未来抱持过度期望之余,会以文化传统为准则检视已受物质文明“污染”的归人[6]P63。姨妈浓妆艳抹,个性冲动,说话时走来走去,喜欢搂着倚着甚至亲吻谈话对象,频繁的肢体接触令生性保守的加尔局促不安。姨妈自以为对家乡的一切了如指掌,拒绝被视作外乡人,却没听过加尔女友凯蒂的名字。餐桌上,姨妈较平时更加亢奋,喋喋不休,甚至时哭时笑,前言不搭后语,几乎丧失理智,一言一行背后却是美国文化的强势特质及对家乡爱尔兰落后贫瘠的鄙夷。她不仅拒绝别人的纠正和反驳,并且强势地不允许别人插话。虽然身为加尔亡母莫拉的亲姐妹,但在美国社会的充分浸润下身上的爱尔兰传统已消失殆尽,姨妈由此成为社会空间之下美国强权文化规训影响下的产物。
细观姨妈劝说加尔移民的说辞,正是以别墅、装着空调的汽车、彩电和“一万五千美元的联邦债券”等优裕丰厚的物质条件为筹码,并暗示加尔留在家乡没有前途:“你还在等什么?等老奥唐纳跳海?等天气变好?”晓之以理的同时更加动之以情,一言一行尽显对美国物质生活的推崇,以为仅凭经济上的许诺就能吸引外甥。而加尔同意其邀请的背后则是社会空间之下多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社会空间对应“表征性空间”,是由人的日常生活所构建起来的场域,不同于物理空间中的地点空间呈简单的并置,社会空间中的空间概念则可以重合、叠加甚至彼此冲突。面对美国优渥的物质生活加尔自然心向往之,但加尔的出走“并非源于与父亲争权失利,而是丧母之痛”[6]P62。作为亲姐妹,姨妈丽姬宛如亡母莫拉的中年版,加尔“目不转睛,无法从她身上移开目光”[3]P57,脑海中母亲的空洞符号得以填补,加之姨妈对母亲生前的回忆,加尔的移民一程由此成为认亲之旅。然而,姨妈在美国文化异化之下夸张的举止,以及父亲和麦琪对姨妈的厌恶又与自己想象中的美国大相径庭,加尔对此颇为疑惑而失望,面对其邀请也因此犹豫不决。姨妈来访当日正是女友凯蒂成婚之日,“加尔在重获失去多年的母亲的同时又失去意中人”,凯蒂嫁给条件更好的金医生,更让加尔将自己爱而不得归咎于其困顿的经济状况。出于对女友的报复,更是在姨妈“以语言执行认养心愿”的百般劝说下,加尔半自愿半被迫配合其完成“认亲”剧目,表面上欣然接受其邀请,内心却不停地表示“承认吧,你并不想去”[3]P64。
建国之初的爱尔兰面临民族身份认同的转型,而战后美国的强势文化无疑影响着民族身份的塑造,弗里尔正是通过剧中美国姨妈的造访表达对民族身份认同危机的忧虑。瓦格纳、迈克·克朗等学者将身份认同理论融入其空间研究中,提出了“他者空间”的概念,文本中的空间因此和人与社会一样具有了身份和主体性。正如瓦格纳在对康拉德《吉姆老爷》研究中所指出,吉姆无法融入现代生活,却因帕图森岛远离欧洲的影响,不受欧洲帝国的准则约束,小岛成了他的庇护地,吉姆也从一个失败者变成了受人尊敬的英雄[7]P48。加尔眼中的美国也是区别于爱尔兰岛的“他者”空间,他相信自己在那里能够放下过去的一切失意,开启崭新而成功的人生,自己一心构建的美国梦却因姨妈的造访而支离破碎,去留无意,加尔的身份认同面临危机。
对于爱尔兰民族身份的探讨和思考由来已久。20世纪之前,长期“去爱尔兰化”的殖民统治使民族身份的声音始终处于“失语”境地。20世纪前叶,叶芝和格雷戈里夫人发起的“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聚焦凯尔特神话和英雄传说,以“绿色田园”区别于英国城市风貌,试图构建单一凯尔特民族的“爱尔兰性”,则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有产物,因囿于对民族觉醒意识的偏重而在战后日益多元复杂的背景之下过时而狭隘。身处后殖民时期,面对战后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格局,以及国内不断升级的北爱尔兰危机,弗里尔在作品中更多表现个体的精神困顿和彷徨挣扎。百废待兴的共和国迎来的不是年轻人留在家乡建设祖国,而是爱尔兰历史上人口外流最为严重的1960年代。不同于老一辈爱尔兰人出于生计,被迫背井离乡的同时对故乡心怀眷恋,家乡在战后新生代眼中不再被理想化,先辈建国的筚路蓝缕他们无从得知,只见家乡的萧条破败和太平洋彼岸美国的繁荣昌盛,年轻一代选择主动出走。受地理位置和地形影响,爱尔兰长期以农耕生活为主,被称为“欧洲农村”。四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弗里尔坚守家乡德里,其笔下虚构的巴里比格小镇再现了家乡的田园风光,“一个有两面性的地方,有时它是一个温柔沉睡的村庄,但也是一个让人沮丧的地方,这里的人们是文化无根的一群。”如同面对前来道别的凯蒂,加尔的心声流露:“我被困在这里太久了,这是一个沼泽地,是一潭死水,死胡同!……我恨这地方,恨每一块石头,每一株石楠,恨,恨!”[3]P75巴里比格宁静闭塞,精神贫瘠,美国繁荣富足的物质生活对于加尔这样内心躁动、有志难申的小镇青年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美国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背后则是其霸权主义与强势文化。战后美国迅速奠定世界霸主地位,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经济秩序,并在冷战政治思维之下辐射全球,在推行“马歇尔计划”援助西欧恢复战后重建的同时也将其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爱尔兰作为传统欧洲阵营自然难逃其手。1960年代爱尔兰政府为摆脱经济低迷和英国的束缚,将目光转向美国,从经济到文化一切改革措施皆唯美国马首是瞻。政府曾尝试改贸易保护为自由开放,却换来美国消费主义的长驱直入。淳朴的小镇青年加尔对美国物质生活曾有所警惕,称之为“粗俗的物质至上的异教徒之地”,却仍禁不住对“接手连锁酒店,进军好莱坞,成为美国总统”的美梦,以及“别墅,汽车彩电和联邦债券”的许诺浮想联翩,其心境更是从“加州我来了”改编而成的“费城我来了”的美国流行音乐中可见一斑。弗里尔对此敏锐意识到,爱尔兰不过是从英国的殖民地变为美国文化帝国的众多殖民地之一,“我们甚至不再是西部的英国人,我们是东部的美国人”[5]P73。
《费城》中,看似宁静的移民前夜背后暗含复杂的权力博弈和历史隐喻。一分为二、去留两难的内外加尔象征着爱尔兰民族精神家园的动荡与迷茫,在交织的过去、现实和未来之间寻找出路。精神空间中内外加尔的人格之争背后是对解决爱尔兰与北爱尔兰之间“相煎何急”的北爱尔兰危机的探索;物理空间下的父子之争所反映出的亲情的缺失和家园的迷失表现出弗里尔对爱尔兰与其前宗主国英国之间复杂关系的反省;而社会空间里加尔和美国姨妈之间的拉扯和博弈,则是剧作家对1960年代民族身份转型之下美国战后强势文化入侵的警惕与忧思。
参考文献:
[1]李成坚:《当代爱尔兰戏剧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
[2]Lefebvre,Henry.The Production of Space,Malden:Blackwell Publishers,1991
[3]Brian,Friel.“Philadelphia, Here I Come!”in Brian Friel Plays One,London:Faber&Faber,1996
[4]陈炳辉:《福柯的权力观》,《廈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5]刘艳芳:《布莱恩·弗里尔戏剧研究》,山西师范大学,2021年
[6]林玉珍:《“明天他会很难过”:“美国丧礼”与傅利耦的〈费城,我来也!〉》,《外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3期
[7]吴庆军:《当代空间批评评析》,《世界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作者单位:太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 岳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