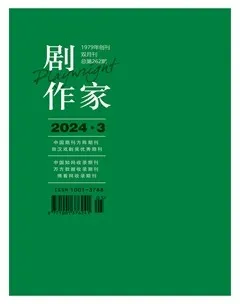一道关于不确定性的菜肴
顾宙寅
摘 要:张慧自编自导的话剧《杂拌、折罗或沙拉》包含了与疫情紧密相关的三则故事,该剧以“不确定性”为戏剧核心,运用现代舞台的影像手段,昭示了疫情之下的百态世相,也充分地契合了当代话剧受众的审美倾向。
关键词:疫情;间离效果;影像;装置艺术
杂拌、折罗、沙拉,三道中外菜肴的名称并置,作为一部戏剧的名字,或许它已在标题层面上对观众做出了明确的暗示:这部戏是杂糅的、浑然的,是艺术的和市井的,是象征的和触手可及的,同时也兼具概念性和景观性。2023年年初,由张慧执导、编剧的戏剧作品《杂拌、折罗或沙拉》,受疫情影响,几经波折,终于在上海兰心大戏院成功上演。恰如名字所暗示的那样,《杂拌、折罗或沙拉》由三个片段组成,它们或多或少回应了一种时代情绪,触及国人隐秘的集体记忆,呈现了现代生活的某一截面与某一时段人间的百态世相。
《浒墅关》:感觉的稻草
在第一个片段《浒墅关》中,由于疫情隔离的机缘巧合,一对已经离异多年的夫妻再次不得不共处同一屋檐下。伴随着两人日夜的攀谈和争斗,往事逐渐浮出水面,观众可知男人曾经为追求考古梦想而抛弃家庭,二人离婚的原因是男人多年前的出轨。“浒墅关”三个字频频出现于对话之中,成为男人和女人、历史和当下、事实和想象、偶然与必然等对立物交织、汇合的焦点所在。
浒墅关为何物?它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历史遗迹景观,而是被赋予了强烈的象征色彩。当两位北方口音的演员谈及远在苏州虎丘区的古镇浒墅关之时,不确定性如雪花,伴随着回忆纷纷飘落。一场没有胜利者、以悲剧结尾的两性战争序幕拉开:男人从浒墅关归来后提出了与女人离婚的诉求,因而,女人揣度在此地必然发生了什么让两人关系产生质变的事。她愈追问,男人愈躲闪,缄口不言。几次三番无果的龃龉之后,男人终于忍不住说出真相,那便是他已死去多年,舞台上栩栩如生的他不过是女人在精神困境中产生的、聊以自慰的幻象。由此,导演将不存在的男人和观众一同拉入了女人的想象世界。“追问”是女人主要的舞台动作,她将此与考古类比,后者衍生出了死亡意蕴。女人的追问必然是一场徒劳,男人不过是她梦中的形象与自我意识的延伸,他无法诉说浒墅关的秘密,其容止言行、一颦一笑皆为幻象,其行为逻辑自然无法超越女人有限的经验范畴。在广大的想象宇宙和狭窄的知觉世界中,诚如怀疑主义者休谟认为的那样,所谓“自我”是感觉的聚合,其结构犹如一束稻草。稻草只是稻草,女人正是凭借记忆的力量怀念过往、追悼故人,一个基础性的“自我”方才水落石出,得以显形。
《浒墅关》还是一个关于“误读”的故事,它发生于男性和女性、北方和南方、自我和他者之间,具有陌生化效果和错位的诗意。剧中的女人永远不理解男人,亦无法探究婚姻溃败的根源,只在重复着一个永远找不到答案的问题:“那天在浒墅关发生了什么?”她在余生中无数次回忆男人,并对回忆进行着创造性却也许偏离事实的校正(但事实本身又包含几分真实?)。观众无从得知舞台上那个狡黠、调皮而感伤,会揉面、做早点但不知司康饼为何物,乒乓颠球技术一流、总是一脸无奈的男人,其身虚实究竟各占几分?回忆是月光,无形无状,见者各异,皆能自我定义与描绘;爱情也是不确定的,往往引出个性与共性的悖论。往日衣衫与笑颜已矣,唯有不确定性将在生者的生活中继续蔓延。
《阿齐》:依恋与自由
第二个片段《阿齐》根据网络红人“‘窃·格瓦拉”的犯罪事例改编:阿齐以偷盗电动车为生,屡屡身陷囹圄,当他在看守所中面对采访的女记者时,竟说出了离经叛道的“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一辈子都不可能打工的”之语,引得台下哄堂大笑。女记者前来的目的便为探寻阿齐不愿打工的理由,观众也伴随她的追问进入阿齐的内心世界。
依恋和自由是破解阿齐心灵秘密的关键词。恋物是对失去之物的追慕,所以盗车何解?其中必有恋物的原由。阿齐迷恋电动车上散发出城市、青草、汗味、泥土等物混合的气息,他将电动车视为马,作为失落情感的外在投射对象,以为倚靠在车上沉沉睡去便能与此产生亲密的情感联结。因此,阿齐认为盗窃一辆电动车,便等于放生一匹马。他如受诅咒而自知的西西弗斯,又颇有几分与尼采在大街上拥马而泣相似的味道,意图将电动车从现代社会无意义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演员以一段诙谐的广西彩调演绎盗车关目后,屏幕上放映着阿齐仰面而睡的黑白影像,如剥洋葱一般,观众得以窥见阿齐的社会边缘人格和创伤心理,以及人物孤独和敏感的情状。对自由的追求是阿齐更深层次的心理动因。出身农村的他曾做过一份给貉剥皮的工作,日久这份工作令他恐惧,一度惊觉自身跑进貉的身体中,貉被剥皮,重伤濒死前那无法描述的眼神成為萦绕其心头久久不去的梦魇,透过貉的眼睛,感觉渐失自由的自己也成了貉,也被看似坚固的集体理性剥去了尊严的皮囊。
阿齐是一个社会化程度较低的边缘人,无法践行众人认同的社会规范和价值。然从另一方面看,阿齐是坚守本真与心中一方净土的人,没有全然被“社会化”。如阿齐所言,“自由”是一道伤口,远不及无拘无束的自在彼岸。“自由”如所有被定义的事物,似都有第一层次、第二层次乃至于更深的层次的不同含义,第一层意义正确,其实似是而非,随着认识的深入,第一层意义往往经不起推敲而烟消云散;第二层意义随之浮现,第二层意义消解后又产生第三层次的意义,以此类推。阿齐用积极的行动不断否定自由的意义,践行着内心的纯真,用一种被社会规范所排斥的个性“错误”推翻另一种坚固的“平庸化”的“错误”,在此过程中重估被认同的价值,自我定义着这不确定的“自由”。
另一位角色,女记者头戴VR眼镜,坐于一隅聆听着阿齐将往事娓娓道来,并慢慢进入阿齐内心的隐秘角落。观众亦随着女记者的视角,任氤氲的微妙感情融于视觉影像中,一同漫步在阿齐自由的臆想世界,剧场中有了几分浪漫恋爱般的暧昧情愫。阿齐的广西方言难以理解,女记者则重复阿齐的只言片语,充当了将广西方言“翻译”成普通话的功用。阿齐的广西方言难以理解固然是听众理解剧情的一个障碍,女配角起到“翻译”的作用也相当有限,但阿齐倏尔正色,易广西方言台词为普通话,也具有瞬间拉近与观众心灵距离的别样诗意。
《一个哑剧》:杂沓的隐喻
《一个哑剧》的表演如一场令人哑然失笑却又大汗淋漓、光怪陆离的大梦,融合了疫情前后人们的想象、情绪和集体记忆。阿齐与女记者双双戏谑退场,一名男子左顾右盼接踵而至。其来到舞台中央,与卵形的装置精彩互动,或又打破第四堵墙与台下观众交流对话,做出各种滑稽动作引人发笑。男子拿着键盘敲出一个个汉字,舞台上的沙拉(杂拌、或折罗?)的盖碗里幻化出电脑的屏幕。屏幕上,一个个好笑又发人深思的问题层出不穷,观众还被无情地归类分群,个性丧失殆尽;互联网记录下14天内观众的踪迹与相关数字,却没有记录这些观众的姓名与个人特征。
身披双翼、手执素棒的白衣者的不期登场,是为诸多意味的杂糅:他可以是AI的无穷化身、全知全能者,抑或操控权力者、病毒的实体、邪恶之客体等等。然唯有一点可以确定,白衣者的存在与行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他挥动手中的指挥棒,一男一女便被完全控制,做出各种动作。这一舞台事件具有多重含义,或许可视为人类集体被数字化裹挟、被科技樊笼囚禁、被困于疾病隐喻的迷宫的事实。男子意图抵抗白衣者的缠斗,几番之后,终于化成唐丧,与白衣者融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表明人类的主体性最终在科技控制下悉数丧失的悲剧情境。
最终,在白衣者的指挥下,三人于一抹昏红的灯光下机械地翩翩起舞,仿佛物我合一。这或许宣告了人类的黄昏,也与当下时代情绪有了巧妙的应和。它表现了人类将与新冠病毒长期共同生存的社会现实,乃至具更多杂沓的不确定意味。这款结尾既带给人希望,也予人警醒:现实既赋予人们希望,又让人失望,两者并存而呈雙螺旋状交叉。回望群星闪耀的人类历史,纵使瘟疫、天花、疟疾、黑死病等疾病曾百般肆虐,人类精神宁折不屈,于逆境中飘扬起高昂的旗帜,可谓逢大疫尽有“克终之美”。然而技术时代到来之际,悬而未决的科技伦理似乎预演了另一种未来:人类渐失主体性,迈入异化的怪圈而不自知,终被异化,与客体融合,为社会、机器与人工智能等外物所牵制、奴役的趋势不可避免。是伏地不起、降志辱身还是崛起抗争?台上传来了一声婴儿的啼哭,在机械世界中又一个生命诞生了。对观众而言,这是一记在真实生活中应何去何从、捍卫自我的致命拷问。
结语
这出混合了装置艺术、数字媒体影像、间离效果的精彩大杂烩,通过导演与编剧以一种“不确定性”为佐餐的“色拉酱”而大放光彩,也由于演员的努力演出而增色不少,但该剧整体结构的平衡性稍有欠缺,人物情感的内在逻辑也有生硬之处,然瑕不掩瑜。正是这种焕发出重重异色的“不确定性”,将三个意味隽永的故事串联成一款夺目的珠玑。
(作者单位:上海戏剧学院)
责任编辑 姜艺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