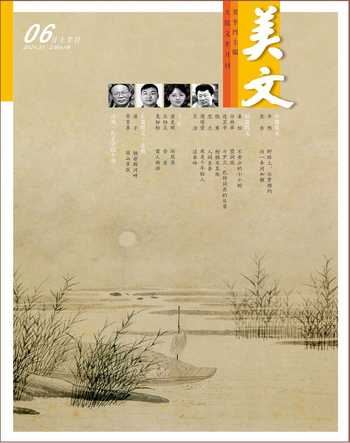柑橘及其他
晓角
柑 橘
所以我们开始将橘子用做花式台球。
——伊曼·梅瑟尔
我还记得那一箱箱柑橘,永远都记得它们叠在一起的橙色,箱子从车上搬下来,一路颠簸有些还沾着白色灰土,穿着灰黑军大衣的小贩把遮在柑橘上厚厚的旧衣服揭开,一箱箱整齐码放在路边,肃杀寒冬里,柑橘的伤口散发香味,硬而清新。
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姑娘,只能看到三箱柑橘叠起来那么高的世界,我够不着大人,不能分清柑子和橘子,村里上过学的燕子姑娘教了我“柑橘”这个词,教完深深印在我脑子里了,于是我坚持叫它们柑橘。我小,村里的东西在我眼睛里都很大,高大的土房子,坚硬漫长的路上坚硬的石头,小贩也很高大,他躲在柑橘后,冬天又白又灰,好多年了我记不住他的脸。
柑橘是好东西,抓破它冻伤的皮,就会像人一样流出味道来,人是血味,它是柑橘味。
最后的一箱柑橘总是卖不完的,小贩站起身,使劲立起箱子把冻得铁硬的剩柑橘倒在路边,它们台球一样滚了满地,滚进雪堆里,牛糞里,天再黑一点时,快要摸不见路时,村里一个女人先于牛羊出现了,她个子应该很高,一张脸有什么样的鼻子、嘴、耳朵,我怎么也记不起来,我记忆里只能泛起她从来不洗的污黑的脸,还有夜那样黑的眼睛。这女人就这么穷苦着来了,每年冬天她都只穿一件烂毛裤和一件烂棉祆,四面漏风,油黑油黑,她弓着腰,捡起雪堆里牛粪旁的柑橘,夜黑雀雀,她也黑雀雀,远远看着,像是柑橘自己跳到黑影上了。
这女人是我们村子的外来者,我那时以为村子大得很,够一座小岛那么大,外面的人活不下去就跑来了。
第一次看到她捡柑橘我新奇得很,那时我还是个小姑娘,不知道她要用这些冻硬的水果干什么,就悄悄趁夜色跟在她身后要去她家,她走得很慢,肩膀一摇一摇,柑橘被她包进棉袄里,我看见她和一头抱着冻水果的黑熊没有两样,我就笑起来了。她听到我笑了,转过身。
“嘿,你个女女笑啥了?”
“我笑你抱着柑橘往树洞走,都快掉在路上了。”
“嘿嘿,柑橘是啥,俺为啥要往树洞走,俺又不是熊。”
我有点为这个装模作样的词不好意思了,我听见她在黑暗里也笑了笑,我就更不好意思了,可是那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对别人道歉。
“姨,我是想跟你回家,想看看你咋吃这么硬的冻橘子。”
她沉默了,但我总觉得她又笑我了。
“俺家冷,你别冻着了,你是村里哪个人家的孩子?”我没有回答她,但她允许我跟着她了。
走了一会儿,我们走到村子的尽头了,也看到她的家了。那是一处院墙倒了的住处,院里乱堆着些木头,木头凉丝丝的,窗户没有亮灯,黑洞洞的。
我有点害怕:“姨,你家真有点像山上的洞,是不是窑啊,我见过窑。”“不是洞,俺家还有孩子睡着呢,都比你大。”
她又弓下身子,把柑橘叮叮当当地落到门口,从毛裤腰里摸到钥匙,开了门,我干站着不好意思,就抱起几个柑橘往门里送,这时她点着蜡了。橘色的火光飘散开来,照见她黑糊糊的墙,墙上掉了好多块皮,世界地图似的,炕头的墙上还立着柱子,柱子也裂开了,屋里种了棵死树似的。我顺着这些往炕上看,炕上铺着块黑蓝色的油布,油布很破了,炕脚睡着两个男孩子,用同一张被子埋着头,其中一个大的听见灯亮了醒来了,坐起来看着我们,橘色灯光里他脸红堂堂,像发烧,我看见他长得不好看,脸窄,眼下有很深一圈灰色,嘴角劈着一条疤,他身上穿着一件背心……不是背心,像是袍子,渐渐我看出来了,那是件给别人戴孝的丧服,但并不脏污,他看来没睡多一会儿,白布还展展着。“姨”点了蜡烛把柑橘拿回来台球样滚在炕上,滚醒了她的小儿子,小儿子缓缓坐起来,烛光也在他脸上染满橘色了,他和我差不多大,下巴尖尖的,眼角也尖尖的,我趴在炕沿儿上看他,他也直直看着我。“姨,这个哥哥为啥不和我说话?”我问道,边用柑橘碰他从脏污被子伸出来的纤瘦的手。“他不会说话,天割了舌头。”我吓了一跳,天割了他的舌头,柑橘一松手滚到他身边,他受烫着那样躲开。“你们俩去院里捡点柴来。”大男孩下了炕走到门外去,我也跟着他出去,外边黑洞洞的,有点怕人,回来时我只拿了几个玉米芯棒,他抱了一小抱木头。
他进来就着烛光把炉子搅旺,填上木头,姨不像熊了,屋里亮了,屋里渐暖了,黑夜退出了家里,柑橘又叮叮当当落到炉子上。
柑橘受了烫,嘶嘶哑哑着呻吟起来。
过了好一会儿,柑橘皮都烤黑了,一个小—点的柑橘软下来了,姨把它拿起来剥皮,一剥水流了一手,柑橘里面全冻虚了,柑橘已然死去,果肉塌在一起。姨先把这个柑橘给他大儿子,男孩拿在手中看了看,嘴唇动了动像是要吃,我才看见他嘴唇全干裂了,红红的血柑橘水那样渗出来,我在想他嘴边大伤疤旁以后会不会多出小伤疤。他没有吃,伸手把柑橘递给我,我那时小,怎么知道谦让,就赶紧接过来把嘴咬上去。
好苦,一个冬天的苦全在这一个柑橘里了。
我那时小,吃不下,赶紧把柑橘又递给姨炕上坐着的小儿子吃,他迫不及待接过去,咬下一大口,汁水流到他脏兮兮的手上,他小狗那样舔干净。
我该走了,我一个人在黑夜里往家走,路上风很大,天幕上星星冻得一摇一摇。
过了几天,村里有个老光棍犯急病死了,他外地的侄儿回来给他办丧礼,办得挺正式,墙头早早立起了白纸,响了好几个两响炮,因为我们家欠这光棍的礼钱,我爸就带我来送礼了。我正坐在塑料椅子上饿着肚子等大人们开始吃饭,这时,两声哭号从不远处扑过来。
等我找到哭的人时,他们已经跪在地上了。
正是那两个吃冻柑橘的男孩,一大一小跪在灵堂前,跪得板直哭得脊背发颤,身上白布袍在白天粗糙脏污,衣身显得过于肥大,此刻也随着痛哭中的身体颤抖,他们像两个大风天扔在地上的烂布口袋。我仔细一看,发现他们哭声最刺耳的那部分居然是那天夜里不会说话的弟弟发出来的,他没有眼泪,只是扯着嗓子喊出惨叫,他哭不出一个完整的音节,哭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只能惨叫,累得脸色铁青,要吐出血但流不出眼泪来。而大儿子则是相反的,他哭得极心痛,但声音不大,眼泪从他闭着的眼睛不停冲下来,一遍遍淌过他嘴角的伤疤又流进嘴里,泡咸他尽力喊出的每一声“爸爸”。
我呆呆着在他们身边站了好久,把吃饭的事都忘记了,好像我也是个守灵的小孝子,在陪着他们哩。直到我爸叫我,我才离开他们,但那哭声响得让我嘴里发苦。吃完菜后饭桌上摆了切成牙的柑橘,我拿起一片放进嘴里,其实我也没吃过几次柑橘,那天夜里的苦柑橘算一次,这次不苦了,算作另一次。
人们离场时我终于看到熊一样的女人来领她的儿子们了,丧礼的管账先生用塑料袋装了些柑橘给他们,女人接过来,又习惯性地要往她脏棉袄里卷,大儿子拉了她一下她才明白要提在手里。
我回家了,大人们说各种话,有说他们俩是那光棍的儿子,那女人乞讨多年才找到这个村,就让儿子痛快哭一哭,有人反驳不是。有人又说他们是外村来的著名哭丧的,到处给别人当孝子,看见遗饭盆子就能掉泪,小哑巴看见灵堂就学会叫唤。有人又说不是。
我长大了,另一个小贩拉着柑橘来到村里,又把橙色的水果整整齐齐码在路上,我买了一点带回家吃,好多年过去了,我看到大人看得出来的东西了,但还是有一点分不清柑和橘。
后來我离开了村子,一个人去了很远的地方。
飞行的夜
也许某一天你还会看见我,也许永不会。
最后一次,在夜空里飞过这小小的村庄,在我童年时它大如迷宫,怎样也走不完,如今,它却小如一只伸开的手。
天黑蓝黑蓝,星宿又如灯笼点起,空气黑蓝沁水,我最后一次察看它们,如多年来每一夜。翅膀下小小农舍里的人夜间羊般安静,但房子里有人就能在静夜里发出味道,发出颜色,人的味道,人的颜色。村东头第一家,玉兰婶子呼出她每年都呼出的烂树叶味,在夜里看是一股残火的细烟,且白且细,在我小时候肺结核便住进她体内,没人愿意站在顺风头和她说话,她一只手上没有小指,她一个人过。一个人种地,收粮食,有时候也会夜里哭,在深秋的树林恸哭。我飞过时听过那哭声。村西头是周老汉的家,今夜他被梦困住了,鼻息哗啦哗啦响。他今年也许活了八十岁,也许活了九十岁,我常在飞过时听到他迟迟不肯动身的死亡。人老了房子便朽到心了,飞过时,我看见后墙会在明年的一天倒他的炕上,我已听到朽塌的声音。他的呼吸在夜里是绿的,草色,有股凉味儿,苦菊味,他是个不说粗话的小老头,手指枯长,每天看新闻捧报纸读,他是唯一常在地里发呆自言自语的人,他的田地永远收成荒凉,这么多年后我终于明白我和他很像,我们只有过去。村南起数第五家,我的翅膀又蹭到一股孩子味儿,孩子味儿不好闻,是我曾经身上的味道。想一想心底痒痒的。屋里有一个六岁的孩子,手掌柔嫩,还没找到铅笔或农具握,此时正握着奶奶枯老的拇指,他一呼吸,呼出我小时候的味道。
我飞过最后一家,又闻到那缕花香,粗糙的花香,格桑花向日葵的香,属于村庄的花香,又苦又浓,我马上便要永远飞走了,临行前让花香拍抚翅膀。
临行前,让我最后一次怀念这一切。
我的四季是四位孤独的鬼
在我的村庄
他们流着眼泪
轮流拥抱我
临行前,我要向你细述深夜的一切,和我最后的诗篇。
逃出雨季
村里每年有一个月是属于大雨的,每一两天就会下一场,时间却从不稳定,人走在路上,或者在地里做活,总是提心吊胆,也许刚才天还蓝瓦瓦的,见不着一丝儿白云,甜脆的黄瓜还在手里吃着,心里正悠闲,乌云就在这个时候轰隆隆赶来了,烂棉花一样遮满天空,日头还想再暖和一会儿,可它的光很快也淹没在烂棉花样的乌云中,悠闲吃黄瓜的人还来不及听见几声雷,北方急急的雨便下来了,打在脸上啪一声,也不知道雨点子具体有多大,只觉得又凉又痛,一天就结束了,赶紧拉上孩子拿上黄瓜往家跑了,跑得慢的只好挨了大雨的毒打。
雨来前孩子们其实是另一个状态,他们人小,但天性乐观,脑子里总想着各种事情,下雨前,村里有几个孩子正在别人的后墙底下玩蚂蚁,那蚂蚁窝当然就在他们脚边,此刻一大群蚂蚁正忙着搬东西,它们用细弱的胳膊把草叶举过头顶,硕大疲倦的眼睛可能也看了天,也许它说了声:唉,一下雨领导催,忙上加忙。说完赶紧又赶路了。孩子们看着蚂蚁们,为它们想象各种故事,有一只蚂蚁走得太慢,快被队伍甩出去了,一个小女孩伸出手指轻轻把它捏起来放到队伍最前面,蚂蚁被吓着了,它心里暗说神显灵了。如果不下雨孩子们能这么看一下午,可雨还是来了,乌云还是来了,一滴雨打在一个孩子头顶,打得“当”一声,他赶紧喊大家回家,好多孩子便跟着他跑,跑啊跑,蚂蚁也被雨打散了。但是雨来了总有孩子是不跑的,他们天性乐观,找地方躲,躲在废门楼下,躲到草棚里,有的躲在树下也不怕雷劈下来。雨停了后接着做游戏,找水花踩,找小鱼抓,从不提自己那个家。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和她都是躲在废门楼下等待大雨结束的孩子,等待去踩水花的孩子。雨季雨水如注,恨不得把地面冲薄一层,雨最大时天是白的,雨幕朦胧万物远离,四周喧哗而安宁。现在的我伸起手往雨幕里探一探,试图再抚摸她小小的脸,却只摸到满手时光的模糊。
我比她大,第一次见面时她几乎是个婴儿,不知道世间的形状和人生的味道,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整天流口水,饿了便吸手指,她母亲小儿麻痹,抱着她一边偏头一边抖,母亲浑身烂衣脏污她也浑身烂衣脏污,母亲发抖时,她也轻轻发抖,那天她进门了,在炕上向我爬来,边爬边笑,露出小小的牙齿,好像我们上辈子认识。
时光在一个一个雨季里被冲掉,化成污泥流进地底。很快她长大了,能站了能走了长成一个机灵的小姑娘穿着烂衣服朝我跑来,我也跟上她一起跑。那是个夏天的下午,是不是雨停的下午我不记得了,太久了,只是回忆深处还有一片片当时生活的阳光倒影,那时也不是没有难过,只是孩子会选择记不住难过。她拉我穿过整个村子,在阳光里走进她家,那家真破,过去的时光里有人看了叫它窝棚,有人叫它危房,我后来知道世间有无数赤贫的房子,只有那一个住过她。我们走进去,地上没有铺砖,是一个坑一个坑的土,炕上斜铺着一块烂油布,油布全是污泥,也许还有血迹,窗户是纸封的,她妈妈坐在炕边一摇一晃。我记得她给我找了糖吃,我们在院子里用糖纸剪了窗花。
妹妹,我有和你一模一样的家,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我自己。
她长大了,整个村子有了我们的笑声,我们爬到山上采花,用锄头挖香得呛人的“地焦焦”,采辣辣的“册茉茉”做饭,抓住蚂蚱又放走,我们用一下午时间清除全村的蜘蛛网,救下三只蝴蝶。最难忘是雨季,雨大了,河水有了,生出无数湿凉小鱼来,游来蝌蚪,长出水草,渐渐河边彻夜蛙鸣。她会在垃圾堆里找最结实的瓶子洗干净,挽起裤腿下河捞鱼,小鱼狡猾,我全身湿透也捉不到,可是她一弯腰就会捧出一条小鱼给我,我们养小鱼,养河螺蝌蚪,每一天窗前都放着一瓶晶莹剔透的鱼儿,小鱼湿冷,在瓶中却可爱。雨季河里起了大水,常有大水趁夜漫进村子淹进农田,冲垮土房,我和她的家整个雨季在屋里下小雨,我们找到所有可以接水的东西来接漏雨,满屋响起叮当声,像是坐在佛堂听木鱼。雨多到这地步时我们只好远离河边,河里也失去了小鱼,但是孩子怎么会失去玩乐呢,我们转身去了树林,大树每一棵都遮住我们,于是藏在每一棵树后面喊对方的名字,在一棵棵树干后旋转。
然后时间在雨中一天天流走,大雨的蛮力也一天天用尽,秋天来了。树叶落向地面,草籽飞到空中,第一层白色霜花长满屋檐时雨终于小了,又细又冷,整天整夜不停淋着人淋着草侵魂蚀骨无极无止,就在这么一个秋天,这么一个永不能再寻回的秋天,我被寒冷雨水困在家里,突然听到有人推门而入,我坐起身看见了她,她浑身湿透了,旧衣服紧紧贴在皮肤上,她青白的脸上污渍被秋雨冲干净了,连嘴唇也发白。可是她看见我没有哭,尽量露出了一个笑,我问她冷吗,她笑了,不冷。在那个秋天,她小儿麻痹的妈妈受不了她父亲的殴打趁夜一个人跟一群乞丐走了,她跟着他们在秋雨中摇摇晃晃,爬过山涉过河,走过一个又一个村子,父亲追了一天,什么都没有找到,连一只鞋都没有找到。
于是她成了没有妈妈的孤儿,她怕父亲打她不敢待在家里,但又不知道去哪里,站在门口淋了半天秋雨,然后来找我,冲我努力着笑,说不冷。
她妈妈走了她却没有哭,如今我多想伸手穿过雨幕给她添件衣服,可是不行了,多年已逝,太远了。日本歌谣唱道:这儿离故乡有几百里。这儿离我们的童年也有几百里。村里从此多了个没有妈妈的孩子,她真的没哭,因为她知道眼泪是没有用的,没有人会可怜她,她不哭,闭上眼睛逼泪水往心里流,妈妈走了几天后她约我到河边,秋雨令河水涨了,涨上河岸清澈见底,那个雨季后她也长大了,我们轮流把脚伸进水里,她拍拍水花,抬头认真看着我:“你知道吗?我想念书了,真的想。”
“我也想念书,但我去不了,你准备咋个念,去什么地方念,咱们这边连个小学都没有,你能去县里吗?”
她用力眨了眨眼,嘴唇动了动没有说出话来,那时她八九岁,我十一或者十二岁,我们周围的村子年轻人走光了,只剩下老人以及为数不多的我们这样没上学的孩子,最近的一所小学只有三个学生听一个老师讲所有课,在她妈妈逃走的那一年这所小学决定解散,她生平第一次的上学梦想也解散了。
除了急雨,我们的村子里还有蓝天,蓝瓦瓦的,意思是人头顶还有蓝色的瓦。没有一丝儿云,蓝色又成为头顶的海,天空每飞过一只燕雀,飞过一只蜻蜓蜜蜂,都是从海面泛向大地的水藻涟漪。
那一年,我们发现天蓝得让人绝望。
因为我比她先陰差阳错识了几个字,我开始教她写字,她手里抓住铅笔,我抓住她的手,努力在烟盒纸上写我们的名字,写了她的,又写我的,她的手很僵,我的手也很僵,文字对我们是陌生的东西,陌生而遥远,不知道怎么能把握它,也不知道把握了能不能进学校去。学着学着,当时的我发现她很笨拙,经常把我宝贵的铅笔芯弄断,把纸也刺穿,歪歪扭扭什么都写不成。
我渐渐生起气来,如今想想多么可笑,我好像要做她老师似的,好像我就懂什么似的。
我越来越不耐烦,时间过得极快,转眼冬天她还是学不会写字,我竟然烦她了,烦这个悲惨笨拙的小妹妹,我那时看不到她有多努力,看不到她多么渴望文化,哪怕我那一点点可笑的“文化”。直到今天,我才明白我和她是一样的,她别别扭扭蹲在地上用木棍学写字,一遍一遍怎么也写不会,抬头偷偷看我,小心翼翼思考我的表情,直到自己哭出来,多年后经事,我和她又有什么不一样。
终于那个冬天,我外婆要搬离村子去县城住了,我以后也没必要再去那个小村子,也当然很难再见她了。分别那天我很难过,很后悔,我第一次知道离别的伤痛。整天我在院子里转,犹豫怎么和她道别,要不要为那些傲慢道歉,我该怎么说?妹妹,对不起,我其实也不会写几个字,这些铅笔和纸都留给你,你不要忘了我。还是说妹妹你不要再担心你妈妈了,她肯定过得很好,肯定很好,村子外的世界都很好,你会上学的,会上中学上大学,会衣锦还乡荣归故里,比我好一千倍一万倍。最后我在冬天的小河边找到她,冬天,河里没有小鱼了。我看着她,她看着我,我们并没有对对方说出什么,也许内心觉得还会再见?我掏出一包格桑花种子,送给她:
“妹妹,立了春你拿去种,就有花看了。”
她接过,竟又笑了,她并没有怪我,从没有怪我,她接下花种塞进自己冬天穿的旧毛裤里,告诉我不要难过,以后有空就回村里来,她会种的,种满她的小院子,等我回来看。
我们就此分别。
然后我再没见过她。大概分别后的第三四年,外婆去老家办事回来告诉我竟然又见到她了,女孩长大了,个子变高,脸上没有泥了,她已经上了学,已经开始变得漂亮,她妈妈也回家了,走路还是一摇一晃,村里人都传这女人给乞丐生了孩子才被放回来。
外婆认出了她,她和外婆寒暄了几句,她没有提起我。
我多希望我的回忆就从这里结束,让她在与我相反的人生大道上远走,走过冬天,走过村子,走过雨季,脚不停歇一路顺风,她不会回头看,我再也追不上她。
可是没有,又过了好几年,时光把她的样子冲淡到我几乎想不起来时,她的命运又变了。
今天,外婆和舅舅回老家给八十多岁的外公提前修墓,给我带回了她最后的消息。去年,这个捉鱼写字的小女孩,我曾经的好妹妹,在去年的雨季一个人趁雨夜黑深离家出走了,她不怕滑,翻过墙,雨还不大时,她开始狂奔。从此后再无她的音讯。
亲爱的妹妹,格桑花种子还在吗?你还好吗?雨最急时这坚强的花会在泥土最深的黑暗中发芽,给最荒寒的村子开出血沁沁的花。
野兽到来
他听见它了,像火车一样叫,就在山后面。
好多年前黑洞洞的夜里,我第一次想象它的样子,想象它在山后面生存的样子,它脊背应该魁梧,走势如山行,毛皮黑蓝如月夜森林,它的眼睛应该是锐利的,聪明的,什么都看得见,夜视如白昼,它用爪子在黑暗中抓一把,大地的皮肤紧了紧。我整夜想象着,直到失眠到来,直到我在想象中一个人去了山后,一个人见到它,被它追赶到天明筋疲力尽。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是怎么知道山后有头野兽的了,我努力地想,但记忆零碎如河底的沙子,找不到源头,但是我想回忆肯定要有一个起点,就把起点定在村庄一个黑暗的夜里吧。我们村子特别小,夏天经常在风雨大作中停电,本来远远看村里窗户还像动物眼睛一样亮着,一道响雷后就全部沉在黑暗中了。我们点起蜡,听着外面巨大的雨声不敢睡觉,我爸爸就讲起野兽的故事了。
当年第一次见到野兽前他还是个孩子,还没有听过他父母给他讲野兽,也没有想过世上是不是真有这么个东西,当然也谈不上怕,那时他很顽劣,每天都在外面游荡,找一点什么东西取乐,他经常爬到树上找乌鸦的窝,把那些柔软的小乌鸦扔进河里,如果找到一些别的小鸟窝也是这样,幼鸟沉进河底了,它们的妈妈却正叼着几只虫子飞回来,整个下午都能听见鸟儿围着树梢呼喊的声音。有时我爸爸还会捕鸟,他在雪天用一把玉米捕到了一只美丽的啄木鸟,那鸟儿关在纸箱里整天闭着眼睛,直到把自己饿死。我爸爸还会去套野兔,套野鸡,这些动物总是饥饿且脚步匆匆,很容易踩进圈套里,他带别的孩子们上山去捡,这些动物们总睁着眼,保持最后的姿势。不过这些是可以吃的,山后的野兽肯定也要吃东西,无可厚非。
直到有一年,我爸爸十八岁那年,他把一只小猫头鹰用绳子绑住吊在空中,他多么幼稚!希望它能飞起来,可这小东西诡异的大眼睛直直看着他,他松手想把小猫头鹰扔掉,可一松手,这小东西却在瞬间消失了,吓他一大跳。
“不是飞走,不是掉在草丛里,是消失了,一下变没有了。”我在烛光邊听得背后发冷。
回家当晚,我爸爸发了高烧,躺在炕上什么都不知道了,外面正下着雨,哗啦哗啦什么也听不到,他在高烧中第一次看见了野兽,野兽到来。
“那东西非常大,非常壮,它就在黑暗里看着我,眼睛特别亮,但是我分不清哪里是它的爪子它的脖子它的腿,它黑蓝黑蓝的一大团,伏在那里,我好像是在跑,又好像是在朝着它走,我躲不过,可周围的山都是我熟悉的,不过是后山。直到它火车一样鸣叫起来。”
烛光动了动,我就从记忆的源头走进现实里来了。
从小,我总感觉村子山后边真的有野兽,我在深夜里给它编出一个个传奇,我有时认为它是正义的精灵,看到山里众生被残害就显个灵,去顽劣之人的梦里吓他一吓,它又多么善良,从不真的伤人性命,我有时又认为它未必真的是野兽,也许它只是一个躲在山后的人,不知从何处流浪而来,与草木同居,它会戏法,有必要时变成火车一样的野兽。
直到那一天,我在一个下午逃离所有人的眼睛,一个人走向后山。
我一步一步往前走,野兽就在我前面,我脚下地面被它一寸寸抓紧,它正火车般向我靠近,可是我终于走到了,却发现什么都没有,后山长满草,中间是洪水冲出来的大伤口。
野兽在哪里?我捡起石子想砸它,最后丢进草丛中。
但是我在后山认识了一个男孩子,他那天正在几棵树后面割草,还提着一篮子,我没有找到野兽,只好和他交朋友,他身量纤细,头上光光的,我决定请他坐下来听我讲野兽的故事,他快活地笑起来,沾满绿色草汁的手在裤子上擦了擦,我发现他的手有割伤的地方,草里多了一点暗红色。
“你知道咱们山后面的野兽吗,我爸爸见过,它蓝瓦瓦的,会火车那样叫,动起来也跟个火车似的。”
“野兽听人说过,我天天见各种牲口见多了,其实更想见见火车。”
“你难道没见过火车从远处滑过去吗?”
“见过,可我想近近地见见,近近见了才是见吧,你说嘞?”
这句话后他害羞地笑了,低下了头,我心里已经失望的野兽莫名变得又有意思了,一个奇妙的念头在我心中升起,我也没近近地看过火车,我爸爸说野兽叫起来像火车,也有火车的气势,会不会火车其实就是野兽呀,那我再找一个人一起等多好,野兽或是火车来了,我们就都看清楚了。
于是那天过后我们经常约在后山,一起割草,一起看野兽和火车有没有来。
“你喜欢捉鸟捉虫不,我爸爸小时候捉了鸟常弄死,后来他有一天发烧了,就在幻觉里见到野兽了,野兽吓唬他哩。”
他还是害羞着笑一笑,有点难堪似的:“不,我不喜欢,我讨厌虫鸟,花蝴蝶都不喜欢,毛乎乎的,我只是想看看火车。”
“为什么你一定要看火车呢?”我忍不住问。
“坐上火车去别的地方,游山玩水,没人找得到我,我就不用割草了。”
我当时赞同了他,我也不愿意待在村庄里,我也想坐上火车逃走,我当时多么理解他。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个人从村子里坐火车跑出来了,其实人不用割草也要割很多别的东西,但是我不后悔,我更理解他了。
一个人在梦里幻想野兽变成了火车,还有一个人在梦里幻想火车变成了野兽。我们幻想着,也对比着对方的梦,又一起把幻想推倒重新描绘,他给我的野兽加上了风一样的轮子,能把不想割草的人拉到远方,纳进天差地别的生活中,当然第一个要拉着他。我给他的火车安上了两只大眼睛,长在车头,月亮一样亮,一眨一眨,铁路上就一明一暗。
后来又过了几年,我和他都长大了,我不再天天梦见野兽,而开始忧虑自己的生活。时间再往后一点,后山又一年长满草的时候,又一年下起大雨的时候,我听说那个男孩去铁路边做什么事,被近近的火车撞死了。
车灯没有眨一眨。
油菜花散在风中
那时我们家一过年,气氛就变得紧张起来,窗户上窗花红红着,门口对联也红红着,日头也温和了,但是就是不对,我把地扫得干干净净,把炕上油布也擦得干干净净,要过年了,都说好要过年了,又究竟有哪里不对。
这紧张的感觉越来越浓,终于浓到一个点,我爸爸妈妈就打起来了,他们从炕上打到地上,从家里打到院子里,我爸爸把磨好的菜刀飞到大门上,大门摇了摇,他还把铁锹朝着我妈妈铲,我妈妈机灵地跳开了,铁锹擦着她飞过,直插进柴堆,柴堆就散了,他还是很生气,看看手里没有东西了,他突然有点伤感,张嘴便骂起来,有时还叉着腰:
“这年我决定不过了,一会儿就把肉扔进茅坑里去,吃你妈的吃,一帮讨吃的东西。”
他骂了这句又觉得不解气,又从脑海里想起了另一句:“我看你们都活不过今天,等晚上我就村里找几个打墓坑的人,多借几张铁锹,你们肯定活不过晚上十点,到时候我让人埋你们的尸首,再做过年菜下酒。”
这句是比较解气的,他骂出口后脸不红了,手不再叉着腰了,放下来在身后一晃一晃的,他慢慢又想起了什么:“老子我快被你们妨碍死了,妨碍死了。”
他终于蹲下了,他嘴里的我们是我和我妈妈。
年年常在這时,大门就开了。有人摇摇晃晃着进来,春节还冷清的风吹着他黑黑的苍老的脸,吹得他一身脏衣服扇乎乎,他把菜刀捡起来朝我们走过来,是我大伯回来了呀。
然后我爸爸暂时顾不上和我妈妈打架了,他去烧水让我大伯洗脸。大伯走进屋里,撩开脏棉祆取出一只刺骨冰冷的鸡架来:“看,大伯给你带了什么。”我接过去,他就在炉子边坐下,他的右腿残疾,只能斜斜着坐,在我记忆中他好像能被炉子一点点烤化掉。
新年夜他去了他的房间烤火,那是一间像他一样黑的仓房,墙上没有墙皮,只是泥土被烟熏黑了,斑驳粗糙,常落黑色的土下来,炕上一小半打扫出来供他放被褥,剩下的地方堆积破衣服,堆积各种垃圾,我爸爸不会去扔的垃圾。大伯转过头睡下前,我听到他和我爸爸说话:“过了年不放羊了,在家和你们种一年地,我身体实在难受。”我没听见我爸爸有没有答应,我睡着了。
年后的春天,大伯不知从哪里带来一包油菜种子,他摇摇晃晃地扛上锄头,领着我去种油菜。那时春天多么好,风淡绿淡绿的,地淡绿淡绿的。他站在我前面,锄头歪歪斜斜把翻过的地划开一道沟,他抬头看看天,天老是那个样子,他把地抹平,又重新划,划着划着汗渗出来。我往他划开的地里撒上油菜种子,他叫住我:“哎呀,你怎么能撒这么多,这么多全长出来,会把人吃得撑死。”我被他逗笑了,就少抓几颗种子,撒得少了。种完了,他看着我:“去把行行踩平了,走小步。”我一扭一扭地踩平埋下种子的地方,留下小小的脚印,大伯没法踩,他站过的地方很大的脚印。
慢慢地,油菜就长出来了,小小的叶子哆哆嗦嗦着,风吹风吹,哆嗦到夏天,开了小小的黄花。日子油菜叶一样哆哆嗦嗦长出来,大伯每天去看,我也每天去,我爸妈还是打架,很快大伯病重了,我们从三天去一次,变成十天去一次,小小的油菜花哆哆嗦嗦着落了,日子也哆哆嗦嗦着枯萎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大伯去世了,那天我爸妈没有打架,没有铁锹被扔出门外,他住的房间也没有再落下黑色的土来,那天天气很坏,云黑压压的,快下起雨的时候,大伯住进棺材里了。
我站在今天看当时的我,她哭着跑出家门去找油菜花,油菜花已散在风中。
(责任编辑:李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