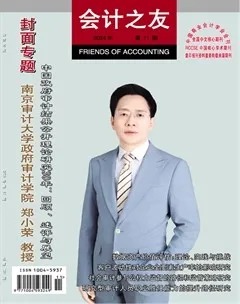黄河下游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与实现路径研究
王晨辉 邓昌斌 高国策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要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支持地方探索开展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计量;依托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提高破坏生态环境违法成本。黄河流域跨越我国地势三级阶梯,横穿四个地貌单元,是我国主要经济区域和重要生态屏障[ 1 ],而黄河下游地区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和生产核心区之一[ 2 ],相较黄河中上游地区,其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与破坏更加突出。因此,系统科学地开展黄河下游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进而实现流域内生态产品价值最大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从宏观层面上利于深入贯彻以“两山”理念为核心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充分践行绿色发展观;从中观层面上可持续助力整个黄河流域经济社会的统筹谋划、协同推进,为制定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规范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从微观层面上可为生态产品交易变现、生态补偿制度落地、生态文明绩效考核提供有力抓手。
一、关于流域生态产品价值的研究述评
生态产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表述,于2010年由国务院发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发〔2010〕46号)提出,国际上与之最为相近的一个概念是联合国制定的《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生态系统核算》[ 3 ](SEEA-EA)中的“生态系统最终服务”,指生态系统为经济活动和其他人类活动提供且被使用的最终产品,包括物质供给、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国家发改委联合国家统计局于2022年针对行政区域单元制定的《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试行)》(以下简称《规范》)中对“生态产品”的定义与SEEA-EA中的“生态系统最终服务”的定义在内容上基本重合,细微不同之处在于《规范》中将最终产品细分成货物与服务。同时《规范》将生态产品总值(GEP)定义为:一定行政区域内各类生态系统在核算期内提供的所有生态产品的货币价值之和。虽然生态产品价值不能简单等同于生态产品总值(GEP)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4 ],但从国际通用核算体系以及国内政府制定的技术规范(指南)来看,三个概念对应的实质内容基本一致,所以对三者的关系不再做进一步厘清与界定。
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可追溯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研究,张林波等[ 4 ]将我国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研究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科学探索阶段(1997—2012年)、实践推进阶段(2012—2021年)、深化铺开阶段(2021年至今)。划分三个阶段的两个中间节点分别是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及2021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这与我国实际情况基本相符。
流域是自然生态要素、社会群体及人与自然间形成的共生共存关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流域空间尺度内的具体表现[ 5 ],关于江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相关的学术成果集中发表于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根据具体研究内容,可分为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与评价、生态产品價值实现机制与路径两大类。一方面,江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是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研究分支,其研究模型、核算方法大多参考欧阳志云等[ 6 ]、谢高地等[ 7 ]、赵庆忠[ 8 ]等先驱学者借鉴国外研究基础上对国内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不同生态要素和不同空间尺度下的学术成果,再根据不同流域的生态环境特点、生态产品类型、生态功能定位等构建GEP核算指标体系,选取科学合理的核算方法,计算并评价三江源[ 9 ]、雅鲁藏布江[ 10 ]、河南省黄河流域段[ 11 ]等江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最后基于分析结果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另一方面,雷硕等[ 12 ]、彭振阳等[ 13 ]、张颖等[ 14 ]分别基于长江流域、浠水流域、黄河流域分析其生态价值实现过程中的难点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促进流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实践路径或保障机制。
整体来看,第一类研究相对侧重生态价值核算指标体系构建与核算结果的定量分析,但受特定研究区域影响,部分核算指标个性强、共性少,核算过程的复制性及核算结果的可比性较差;第二类研究相对侧重生态价值实现机理与措施对策的逻辑分析、定性总结,但对生态产品核算的操作过程和方法选择涉及较少,实操性和应用性相对薄弱。尤其是现有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相关研究与《纲要》这一重大国家战略的总体要求、发展目标联系不够紧密,有待学界在国家战略指导下,联系黄河流域生态实情,进一步深入探究黄河下游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明晰流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以丰富生态产品价值理论研究,助力黄河重大国家战略实施到位。
二、黄河下游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思路与程序
黄河下游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将遵循“实物量核算先行,价值量统一转化”的总体思路展开。实物量是生态系统所提供各类生态产品的物理量,例如农产品产量、水源涵养量、土壤保持量、固碳量等,其优点是直观、易理解,但因其计量单位不同,不同生态系统提供的生态产品实物量无法直接加总。因此必须借助市场价值法、替代成本法等核算方法将实物量统一转化为货币价值,方可加总得到黄河下游不同生态系统对应的生态产品价值。
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主要程序一般包括以下七个步骤[ 15 ]:确定区域范围、明确区域内生态系统类型、编制生态产品目录清单、确定核算方法模型与适用技术参数、收集数据资料、开展各类型生态产品实物量与价值量核算、计算区域内生态产品总值。
黄河下游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也将遵循以上程序,具体见图1。首先,核算范围从地理空间上是以河南省荥阳市的桃花峪为起点,于山东垦利县注入渤海,下游全长785.6km;从行政范围上主要涵盖河南、山东两省20个地级市133个县区(含市辖区),总面积达14.81万平方千米。其次,黄河下游生态系统类型确定主要依据《纲要》的总体要求以及对黄河下游的战略定位。《纲要》的总体要求是重在保护、要在治理,其对黄河下游的战略定位是推进下游湿地保护和生态治理,具体包括保护修复黄河三角洲湿地、建设黄河下游绿色生态走廊、推进滩区生态综合整治,这就划定了黄河下游核算的主要生态系统类型是湿地、森林、城市。而剩余步骤中生态产品的目录清单、数据资料的收集与调查方式、生态产品实物量与价值量核算、生态产品总值计算将结合黄河下游区域特点与实际条件,主要参照《规范》不同章节对应的方法指引进行操作,这使得最终核算结果相对科学、规范,而且便于实现不同区域单元间开展横向比较、同一区域单元实现跨期纵向比较,最大程度做到了核算结果可追溯、可核查、可比较。
三、黄河下游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指标体系构建
在明确核算的直接目标是全面且准确计量黄河下游生态产品总值的前提下,黄河下游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指标体系的关键在于两部分:生态产品核算指标的确定、相应指标核算方法的选择。结合《纲要》对黄河下游的发展定位,确定了黄河下游核算的三类生态系统类型分别是湿地、森林、城市。这三类生态系统在共同一级指标物质供给、调节服务、文化服务的指引下,充分融合黄河下游三类生态系统的生态产品输出、生态功能定位、城市整体规划等具体因素,确定其二级实物量指标与二级价值量指标,并根据每一项二级指标选取确定相应的核算方法(见表1)。
(一)黄河下游湿地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指标体系
针对黄河下游湿地生态系统,《纲要》提出保护修复黄河三角洲湿地。黄河三角洲地区是黄河下游重要的国际湿地,于1992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建立了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因此,黄河下游湿地生态系统生态产品核算指标将充分结合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生态实情、经营现状,因地制宜筛选。
一是在物质供给上,黄河三角洲以农产品、渔牧产品输出为主。农产品可细分小麦、水稻、玉米、高粱等粮食作物,以及棉花、花生、大豆等经济作物;而渔产品和畜牧产品则分别以黄河口大闸蟹、黄河口滩羊为典型代表。二是在调节服务上,基于湿地生态系统发挥的生态功能,选取水源涵养、土壤保持、防风固沙、海岸带防护、洪水调蓄、空气净化、水质净化、固碳、局部气候调节作为二级指标。三是在文化服务上,鉴于2022年体育总局牵头印发的《户外运动产业发展规划(2022—2025年)》在其主要任务中明确提出,推动自然资源向户外运动开放,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价值转换,打造黄河文化户外运动带,加上黄河口(东营)马拉松连续多年成功举办,建议在《规范》原有湿地生态产品核算二级指标旅游康养的基础上,补充休闲游憩此二级指标(见表2)。
(二)黄河下游森林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指标体系
针对黄河下游森林生态系统,《纲要》提出:建设黄河下游绿色生态走廊,加强下游黄河干流两岸生态防护林建设;因地制宜建设沿黄城市森林公园,发挥水土保持、防风固沙、宽河固堤等功能。《纲要》的要求主要体现了黄河下游森林生态系统的调节服务一级指标下水源涵养、土壤保持、防风固沙、洪水调蓄等二级指标对应的生态产品。除此之外,森林生态系统对应的空气净化、固碳、局部气候调节等通用二级指标也应补充体现。而在物质供给上,除了森林生态系统能够直接提供野生林产品和集约种植林产品等多类林产品外,黄河下游还积极发展林下经济,打造林下种植中草药、林下养殖家禽畜等经济模式,因此还应涵盖农产品、畜牧产品等二级指标。最后在文化服务方面,按照《规范》指引仅吸纳旅游康养此二级指标(见表3)。
(三)黄河下游城市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指标体系
针对黄河下游城市生态系统,《纲要》提出:推进滩区生态综合整治;因滩施策、综合治理下游滩区,统筹做好高滩区防洪安全和土地利用。事实上,由于滩区防洪标准低,洪水淹没概率高,使得农田保收能力低且长期收益不高,致使滩区群众生活水平低下[ 16 ],而滩区内经济不发达將直接制约黄河下游城市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滩区治理是黄河下游城市生态系统的特色重点任务。在调节服务一级指标指引下,除了计量水源涵养、海岸带防护、空气净化、水质净化、固碳、局部气候调节、噪声消减等共性二级核算指标对应的实物量与价值量,更应注重核算土壤保持、洪水调蓄这两项二级指标,以针对性地反映黄河下游滩区治理的质量效果。在物质供给上,黄河下游城市生态系统选取由其他生态系统产生并为人类最终使用的物质产品,即生物质能源等其他物质作为二级指标。最后在文化服务方面,按照《规范》指引吸纳旅游康养、休闲游憩、景观增值作为二级核算指标(见表4)。
在核算方法上,黄河下游三类生态系统除了物质供给相关二级指标价值量核算过程中使用了残值法,核算基础数据来自GDP核算及投入产出数据集外,其他二级指标在价值量核算过程中都需要实物量指标提供基础数据,并辅之以相关部门提供的价格、成本等统计监测数据或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规定的征收标准才能完成其价值量的核算。在核算出同一生态系统的各类生态产品对应货币价值后,汇总相加即可得到该生态系统的生态产品总值。
四、黄河下游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选择
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是黄河下游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价值核算是必要抓手,只有将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弄清楚,才能将资源环境变成一种可衡量、可比较的生产要素[ 17 ],进而精准定位生态产品的发展方向,为生态保护补偿和生态绩效考核提供科学依据。但若要切实推动黄河下游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仅靠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是不够的,应区分流域内不同生态产品的产权性质与管理形式,精准施策,合理保障,方可最大程度助力黄河下游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基于生态产品供给方式不同,参照经济学公共品领域的基础概念,将黄河下游生态产品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包含黄河下游国家自然保护区、城市绿地的纯公共型生态产品,其运营管理主体一般为行政事业单位,价值构成以非市场价值为准。第二类是包含建设黄河下游绿色生态走廊过程中着力打造的城市森林公园、郊野公园、公共水域、公共林地在内的准公共型生态产品,其运营主体相对多元,兼具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第三类是包含沿黄下游个体或组织所有的私人生态产品,其管理主体以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为主,主要遵循市场导向,强调市场价值。本文依据上述三类不同生态产品分别提出黄河下游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可行路径。
(一)强化流域内部门协同联动机制,突出过程监督与结果应用
政府被赋予的公共管理职能及纯公共型生态产品的强外部性决定了黄河下游相关行政事业单位第一责任人的主体地位,虽然政府调节手段利于破解生态产品供给的“外部失灵”[ 18 ],但仍存在政府部门间权责不清甚至权力“寻租”现象,这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流域内纯公共型生态产品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针对此问题,可考虑从两方面入手解决。一方面,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落实的工作机制,服从流域内重大规划、重大政策、重要工作安排,细化工作方案,强化区域联动,落实主体责任,务求责任落实到位、措施实施到位、监管覆盖到位。另一方面,畅通人民群众监督举报渠道,让政府部门对黄河下游生态产品的监管置于阳光下,充分接受流域居民的监督与建议;同时,强化生态产品核算结果的有效运用,完善生态文明绩效考核体系[ 19 ],可将核算结果纳入各级政府、各层官员的考核评价和巡视审计中,对任期内造成流域生态产品总值严重下降的,依规依纪依法追究有关党政领导干部责任。
(二)引入民营资本深度参与,协调各类组织协同运营
相较纯公共型生态产品,准公共型生态产品的管理运营主体更为多元,涵盖了行政部门、企事业单位等。但从资本来源来看,主要还是以国有资本为主,特别是大型公园、景区多由地方国企主导经营,民营资本参与机会相对少、介入程度低。因此有必要鼓励和引导民营资本参与到黄河下游生态产品的建设与运营之中,充分发挥营利组织与非营利组织的各自比较优势,形成高效协同运营模式,强化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这既符合国家“放管服”改革纵深推进的趋势,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更好发挥政府监管和调控职能,又能够部分解决黄河下游生态产品保护和治理过程中资金短缺问题,减轻地方财政压力,推动流域内生态福祉共建共享。
(三)拓展生态产品产业链,构建流域生态产品交易服务平台
市场交易是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主要渠道与发展方向[ 20 ],而物质供给类、文化服务类以及调节服务类中碳排放权等私人生态产品产权相对明晰,便于流通、交易。为最大程度实现黄河下游私人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应将流域内分散的生态产品整合起来,深挖文体、休闲、康养等全新生态方向,大力发展“品牌+”“互联网+”,延展生态产品产业链和价值链,着力打造黄河下游特色生态精品,提高私人生态产品经济附加值。在生态产品自身价值深挖与提升的同时,构建黄河下游生态产品交易服务平台,对接国内外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推进生态产品供需精准对接,扩大经营开发收益和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流域内生态产品整体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增强黄河下游用于生态保护的造血能力,切实推动黄河下游实现高质量发展。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表象在黄河,根子在流域”的科学论断,这为黄河流域综合治理指明了改进方向,亦为黄河下游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与价值实现找到了有力抓手,即不能片面就水论水,要做好流域内各类生态系统、各種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紧紧围绕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 21 ],及时修正、完善价值核算指标和方法,充分发挥核算数据对综合治理的决策支撑与效果反馈作用,进而在根子上推动破解黄河下游生态难题,实现流域生态产品价值提升,协同推进整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让黄河真正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参考文献】
[1] 刘晶晶,王静,戴建旺,等.黄河流域县域尺度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和需求核算及时空变异[J].自然资源学报,2021,36(1):148-161.
[2] 张鹏岩,耿文亮,杨丹,等.黄河下游地区土地利用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时空演变[J].农业工程学报,2020,36(11):277-288.
[3] United nation,European commission,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World bank group.System of environmental-economic accounting 2012:experimental ecosystem accounting [M].New York:United Nation,2014.
[4] 张林波,陈鑫,梁田,等.我国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研究进展、问题与展望[J].环境科学研究,2023,36(4):743-756.
[5] 徐瑞蓉.生命共同体理念下流域生态产品市场化路径探索[J].学术交流,2020,321(12):102-110.
[6] 欧阳志云,王效科,苗鸿.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生态经济价值的初步研究[J].生态学报,1999,19(5):607-613.
[7] 谢高地,甄霖,鲁春霞,等.一个基于专家知识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化方法[J].自然资源学报,2008,23(5):911-919.
[8] 赵庆忠.生态文明看聊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68-70.
[9] 李芬,张林波,舒俭民,等.三江源区生态产品价值核算[J].科技导报,2017,35(6):120-124.
[10] 张籍,邹梓颖.雅鲁藏布江流域生态产品总值(GEP)核算及其应用研究[J].生态经济,2022,38(10):167-172,227.
[11] 任杰,钱发军,刘鹏.河南省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22,498(4):130-132.
[12] 雷硕,孟晓杰,侯春飞,等.长江流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与成效评价[J].环境工程技术学报,2022,12(2):399-407.
[13] 彭振阳,黄金凤,高华斌,等.流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探索:以黄冈市浠水流域为例[J].水利水电快报,2022,43(2):94-99.
[14] 张颖,徐祯彩.黄河流域多元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J].水利经济,2023,41(1):89-93,106.
[15]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统计局.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16] 张金良,刘继祥,李超群,等.黄河下游滩区治理与生态再造模式发展:黄河下游滩区生态再造与治理研究之四[J].人民黄河,2018,40(10):1-6.
[17] 李佐军,黄俊勇.做好核算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奠定基础[N/OL].光明网,(2020-10-09).https://m.gmw.cn/baijia/2020-10/09/34250332.html.
[18] 詹琉璐,杨建州.生态产品价值及实现路径的经济学思考[J].经济问题,2022,515(7):19-26.
[19]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A].2021.
[20] 李忠.长江经济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20(1):124-128.
[21] 习近平.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中国水利,2019(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