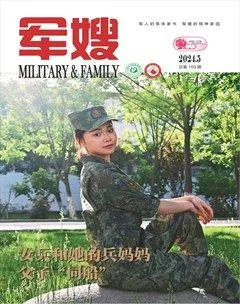长城,长城
郑蜀炎
一
诗人激情击筑的吟咏,歌者鼙鼓声动的旋律,画家旌旗蔽日的丹青,学者究微考据的疏证……无论长城是怎样地进入你的视野,都请记住,长城首先是城——“城者,所以自守也”。
在古代历史框架中,长城的定义从来没有改变——国之防也。如果要形容,它是因战争而诞生的英雄史诗,以无言的庄严见证着华夏大地2000多年的凛冽沧桑;如果谈到记忆,它可能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大的古战场,冷兵器时代无可比拟的杰作、极具价值的军事文化遗产……
“因地形,用险制塞”的战争理论,促成春秋战国群雄不仅争霸割据,还争着修“边墙”(“土气”却很形象,直到秦始皇改叫长城)。一时间,“修城以备”成为诸侯“风尚”。是个国,便少不了一段拥关固防的城墙。于是,就有了楚长城、魏长城、燕长城……
尽人皆知的“烽火戏诸侯”,虽然其真实性一直在被质疑,但至少可以表明,长城及烽、燧、垛等,在西周时已相当完备,并传之以诗文。
比如,绵延于1500多座大小山峰的齐长城,可以从《诗经》中领略其巍峨气势——“泰山岩岩”。
再比如,总长度超过200公里的赵长城,是中国北部最早的长城。《史记》中以“筑长城”“立长城”历历罗列。当然,太史公更为青睐的是主持修长城者——推行“胡服骑射”军事改革的赵武灵王。
至公元前215年,统一了中国的秦始皇也开始“统一”长城——把此前战国时期诸国的“边墙”该拆的拆、该修的修、该连的连。由此,真正意义上的万里长城出现了,从甘肃至辽东,横亘万里。
对“最早”的长城,大家各有说辞,可有一点百喙如一——长城产生于服务于战争的本质从未改变。中国长城学会编纂的《中国长城志》对其有明确定义:“由连续性墙体及配套的关隘、城堡、烽燧等构成的巨型军事防御工程。”
《水经注》曾这样描写战国时期的赵长城:“连山刺天、峨然云举”。我们判读秦长城的走势、地形就不难看出,它是典型的借山势进行防御威慑的自守型建筑。这非常符合中国古代的战略理论——减缓敌人进攻的速度,依靠城堡墙堞分割地理空间,增加防御层次。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公元前3世纪,东西方国家都开始大兴土木。东方是秦始皇开始修长城,而西方的罗马人则开始修用以输送战力的路,其干道加支线总计15万公里。从这个角度看过去,“不到长城非好汉”和“条条大道通罗马”,亦可谓中西文化早期在观念上的某种分野与辉映。
二
“以崇国防”——我们今天所说的“国防”一词,始于汉代。
“能作三军气,当为万里城。”长城见证着汉武帝开阔的防务视野。游牧民族来去如风的袭扰,把这位雄才伟略皇帝的目光吸引向了西域。公元前119年,汉王朝开始在河西走廊修“高城深堑”的长城。这时,长城的意义已不仅仅是固守中原的防线,而成为拓展国家生存空间的延展线。
当然,以建筑材料而论,汉长城没法与凿岩砌石的秦长城相比。修建在沙漠瀚海里的漢长城基本是就地取材,墙体多由红柳、芦苇加沙砾石混筑,被称为“百衲褴褛之躯”,亦有“红柳长城”之谓。
但这并不影响它构成一个总长度在两万里以上完善的国防体系。“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汉朝军队屯田于此,牧马于此,兴兵于此。经略西域战略的成功,使长城突破了地域限制,开始建立起与其他文明的认知与互动。
“横风高弓弩,笙伴箭矢鸣。”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汉长城的绵延曲线就是古丝绸之路的路线。换言之,守护、拓展丝绸之路,是其重要功能。也可以说,名满天下的丝绸之路,其兴其衰,在很大程度上与长城或强或弱,彼此依存又相互解读。
长城的兴建时间,正处于青铜兵器向铁兵器过渡的时期。长城上的每一次厮杀,都闪烁着金属兵器的寒光,撞击着剑戟的铿锵。为了抗击善用弓矢的骑兵,汉代戍边军队开始了战略转变——依托坚实稳固的长城,以步兵坚守要塞的战法与飘忽不定的骑兵周旋,将流动战场转化为固定战场,以高墙深壕来衰减骁勇之骑的速度优势,从而充分发挥中原步兵的兵器、阵法优势。
长城的重点是关隘,几乎所有烽火战事都发生于此。镇远关、插箭岭关、将军关、杀虎口堡、狼牙口、败虎堡、铁门关……几百个关口重镇的名称,记载了长城下的刀光剑影、厮杀呐喊。
秦长城也罢,汉长城也好,“以崇国防”战略构想,让粗糙雄浑的墙堞下见证着鸣镝烽烟、矛戈喋血的峥嵘岁月。而黄沙百战的铁血,泼洒出稻麦飘香、驼铃遥远的安宁。“将军白发征夫泪”换来了长城内外相对稳定和平的生存环境。所谓“入塞者络绎不绝”,便是当年对此的真实写照。
尽管有“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叹息,但亦不乏“劝君更尽一杯酒”的潇洒。长城,最不缺的是豪情与诗意。
三
很多人一直有个疑问: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为什么在他的“游记”中,竟然没有提及长城呢?
回答历史的疑问,要找到历史的逻辑,而“国防”往往是蕴含其中的密码。唐朝,国势强盛,“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完全不需要借靠长城设防;宋朝,则因“四海升平,并无大事可叙”的时局判断,忽略了包括修筑长城在内的国土防御;元朝,在其所开拓的庞大疆域上,长城已然构成内墙,修之何用……
所以,马可·波罗年代的长城,已是深嵌荒岭古道的“东方老墙”。长城似乎终结于某个辉煌的时刻,或者说悬空于一种未完成的时态。
沉默了几百年的长城故事,到了明朝,情节陡然进入了“高潮”。朱元璋“高筑墙”的战略,如同说书人的“惊堂木”,在历史的书案上骤击而响。
元朝既败,可退回漠北草原的游牧军队又怎忘得了中原粉墙黛瓦、水净山绿的富庶。于是,在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战守攻防中,长城的防御作用再度凸显出来。这个时期,明朝的生产力发展到了一定水平,不仅有钱,而且有了更好的工艺和建材。因此,依据“筑边”“建堡”等重要国策,至明中期,通过20次大规模的增修和重修,已经淡出历史许久的长城,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一代名将戚继光曾经负责金山岭600公里沿线防务。他任职的16年间,将长城的防御体系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九边十三镇”成为经典之作。
昔日马萧萧,今日花灼灼。明长城由此知名,八达岭、嘉峪关、金山岭等成为千年长城的代表,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最美最壮观的“历史现场”……
四
与长城有关的一切都是大气磅礴的。
从自然地理来看,总长度达两万多公里、分布在中国北方15个省市的历代长城,有相当长的部分都蜿蜒在北纬40度上下这条地理带上。
从地图上可以清晰看到,方角折曲的长城符号竟与自然界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基本吻合。农业社会的降水量,决定着农业的产出。所以,“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实际上就成为半干旱与半湿润地区的分界线,而农耕和游牧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和文明,也由此产生。
如果从人文方面看,长城不只是一道砖石土木筑起的军事屏障,而且是华夏大地上特殊的人文地理地带。由于其核心是长城,因此可以称为长城地带。这个地带上的农耕和游牧两种文明,由于长城的“缘分”,开始了交错、相融。
长城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智慧结晶。长城沿线的千年战事与烽烟,恰恰演变着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渐行进程。事实上,长城不仅是汉民族修建的。披览史书,北魏、西魏、东魏、北齐、北周、辽金等,都有在其属地上修筑、连接、修复长城的记载。
关隘并非只有金甲战阵、溅血尺寸。随着边疆的相对稳定,明朝廷开始推行“以屯养军”之策。长城的军事属性开始渗入社会属性。一方面,守城兵士和家眷的生活依靠社会商贸活动支撑;另一方面,长城南北老百姓的商贸交往日益兴盛,长城开始有了类似海关的“市舶”“榷关”等功能。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具体详细地描述了18世纪发轫于张家口长城的草原“茶马古道”。显然,为武备而建的“张家口堡”,当时已然成为闻名遐迩的商城。
“雄关存旧迹,形胜壮山河。”1691年,清康熙帝否决了请求修复长城的折子,在一番“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的感喟后,说“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防自固,所谓‘众志成城是也”。
2000多年的長城修建历史,由此画上了句号。
五
1933年3月至5月,中国军队在长城喜峰口、古北口等地,打响了抗击日寇的“长城抗战”。“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旋律激荡在长城沿线。
1937年,八路军在长城首战告捷,平型关大捷振奋国人之心。捷报一个接一个,雁门关大捷、阳明堡之战……我军以长城沿线的三战三捷,激励着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和勇气。在整个抗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仅在长城一带,就进行了数百次与侵略者的激战,标志着我军成为抗日战场的中流砥柱……
《汉书》中喻长城为“弓弦”,谓之“长城之歌至今未绝”。这古老而浑雄的历史弓弦,在山河临危之际,拨响了贯穿万世而不绝、气吞山河而震撼的慷慨壮歌。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诞生于抗战时期的《义勇军进行曲》,以其铿锵、以其悲壮、以其雄烈,使长城升华为一个伟大民族的伟大精神、谱写出一个伟大国家的伟大旋律。
回望千年古长城,怆然、慨然、凛然的心境交织于心;放眼今天新长城,巍峨之间铺展万里画卷,雄峙之巅吟诵浩荡长歌。
2019年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古老的长城作为中国符号,再度绽放出中国瑰宝、世界奇迹的风采。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这是守护民族文化记忆、延续民族文化根脉、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举措。
“望长城内外”,一代伟人所“望”之长城,当然不只是地理概念上的长城;而今天的“长城学”所探寻的,也决不仅仅是长城的建筑工程。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建筑能像长城一样,在时间和空间上如此影响和塑造着一个民族;也没有哪一项工程,如此和谐地塑形了中华文明,书写下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交流交融的史话。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载文明与烽火于一体,系光荣与梦想于一身,负苦难与沧桑于一城。仰望长城,守望历史,展望未来,万里长城的辉煌不只在过去,更在现在和未来。
(转载自2023年4月25日《解放军报·长征副刊》。作者为解放军报社原高级记者)
编辑/李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