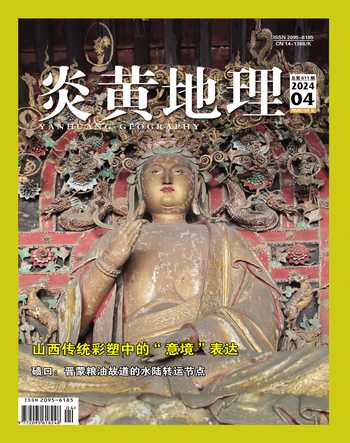既仁且智
刘东祥 王鹏


荀子之学术传承自孔子,为儒者无疑。《史记·儒林列传》说:“孟子和荀子这些儒者,都遵行孔子的事业并对其发扬光大,凭借他们的学问显赫于当世。”荀子对儒学的贡献主要是:完善了儒学思想的“智性”,使其“内圣外王”的主张具备了极强的可操作性或者说实践性。但荀学也因此遭受后儒之非议。
荀子儒学思想的“仁”性
唐代的韩愈认为荀子谈性恶,已不是“醇儒”,所以将其排除在儒家“道统”之外。韩愈在当时政坛和学界的地位都很高,影响力很大,他提出的“道统论”,直接影响到了后世学者对荀子的评价。如宋代的程颐便说:“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实际上荀子论性恶是从“生理欲求”的角度,认为人的“生理欲求”在没有外力干涉的情况下,会使人天然倾向于索取无度,从而成为“恶”,因此荀子将“人欲”天然趋恶的属性称之为“性恶”。
“人的本性是恶的,人性中善的东西是后天培养的。如今人的本性,生来就有喜好利益的因素,顺着这种因素,争夺就会产生而推辞礼让就会消失;生来就有嫉妒和凶恶的因素,顺着这种因素,互相残杀就会产生而忠诚信实的品质就会消失;耳朵和眼睛生来就有喜好声色的因素,顺着这种因素,淫乱就会产生而礼义文化就会消失。因此说顺从人的本性,顺从人的性情,一定会产生争夺,违犯本分,扰乱公理,最后导致暴虐。所以必须有师法的教化和礼义的教导,然后才能使人们的行为从谦让开始,合并于礼仪文明,最后使社会达到稳定。”(《荀子·性恶》)
在荀子看来,生理欲求,无善恶的属性,但这种生理欲求却有一种使人天然趋恶的倾向,这表现在“顺是”所导致的结果上:争夺生而辞让亡、残贼生而忠信亡、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可以说荀子“性恶论”的本意并不是指人的生理欲求本身是邪恶的,而是指人的生理欲求有使人天然趋恶的倾向。荀子的“性恶论”本质上是“人欲使人趋恶”论。荀子正是意识到了“人欲”这种天然使人趋恶的倾向,所以才用“人欲”来定义“人性”并极力宣传“性恶”,用以警醒世人,使世人注重外在的礼法约束与内心的主动修养。“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可以说,荀子虽然论“性恶”,其目的却是使人弃恶从善以“成仁成圣”,在这一点上,他与孟子并无不同。后儒因荀子论“性恶”,便以为荀子不是“醇儒”,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理解荀子“性恶论”的实质。
既然“性恶论”只是荀子对“人欲”即人的生理欲求的认识,那么“性恶论”就不足以代表荀子完整的人性论。事实上,荀子的“人性论”是十分完整的,不仅包含对“人欲”的认识,也包含对人的“先天德性”的认识。只是这种认识往往隐藏在《荀子》的相关句意中,并不如“性恶”那样明显。
“人虽然有质地美好的性情因素,心也有辩知的能力,但必须寻求贤德的老师跟从他,选择良友来友爱他。这样才能使自己所听见的是尧舜禹汤的大道;所看见的是忠信敬让的行为。”(《荀子·性恶》)
荀子认为人有“质美”之“性”,有“辩知”之“心”,因此才能够通过求师访友而闻见“尧舜禹汤之道”与“忠信敬让之行”。换言之,荀子认为人如果没有质美之性与辩知之心,是无法通过后天努力形成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的。“性质美”即人性的素质或本质是美好的,“心辩知”即人心有辨别道德是非和认知外物的能力,可以看出,荀子所言“性质美”与孟子所言“人性善”并无不同,荀子实际上是承认人性中有“善”的素质的。荀子同样认为人性中“善”的素质是人区别并高贵于其他一切物种的本质属性。
“水火有气息但没有生命,草木有生命而没有认知能力,禽兽有认知能力但没有道义,人有气息、有生命、有认知能力,而且有道义,所以是天下最高贵的物种。”(《荀子·王制》)
荀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具有道德观念,人之所以比其他物种高贵,在于人具有道德行为。在先天道德素质与后天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的关系上,荀子与孟子的观念也是一致的。
“君主把仁义之心放置于心内,把认知能力作为仁义之心的仆役,用礼来使仁义之心发挥完全。因此王者先寻求仁而后寻求礼,这是天然的情况。”(《荀子·大略》)
“君子培养内心没有比诚更好的,达到了诚就没有别的事了。只有仁能够守护内心,只有义能够成就行为。”(《荀子·不苟》)
荀子认为“仁心”是上天设置给人的,“知”(即认知能力)是为“仁心”服务的,“礼”是为了保障“仁心”得以最大程度发挥。对于“知”如何为“仁心”服务,荀子提出了“致诚养心”的观点。“诚”就是将原本具有的东西发挥出来,既然只需“致诚养心”便能实现“仁心设焉”,那么荀子显然认为“仁心”先天就内在于人心,是上天赐予人类的德性,故荀子称“诚心”所成就的德性为“天德”。可见荀子在论证儒学思想的正当性方面仍然与孟子一致。
综上所述,后世学者批评荀子不是“醇儒”,批评荀子思想缺乏“仁性”,是因没有准确理解荀子完整人性论而造成的,并不符合事实,荀子的人性论不仅有“性恶”(实际上是“人欲使人趋恶”),更有“性质美”(人的先天德性)和“心辩知”(人的道德分辨能力和认知能力),实际上是由这三部分共同构成的。荀子在“仁性”方面对儒学的理论贡献并不亚于孟子,实为“醇儒”。
荀子儒学思想的“智”性
除表現出传统儒学的“仁”性之外,荀子的儒学思想更表现出迥别于传统儒学的“智”性。传统儒学也有“智”的概念,但其“智”更多是从对伦理道德境界的体悟,即“思”的层面上讲的,如思孟学派便认为:“仁义礼智根于心”,因此心之“思”不是指向外物,不是追求关于外物的知识,而是人作为认知主体对自身的内在道德本性的体认。换言之,在思孟学派那里,“思”作为“智”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为人内在的“道德心”服务的,其主要任务是孟子所说的“尽心”,因此传统儒家虽也有“智”的概念,但并不具备认识论和实践性意义上的“智”性,因此传统儒学一旦应用于实践,便多被人诟病为“无用”“迂腐”。荀子儒学则不然,它极为注重对外在于人的客观世界的规律(“道”)的认知与把握,具有强烈的认知理性和可实践性,这就是荀子儒学的“智”性。大致来说,荀子儒学的“智”性主要体现在《荀子》书中对“天”“欲”等对象的理性认知与利用上。文章仅以其“天论”作为举证。
“天的运行有它的常法,不会因为尧就存在,不会因为桀而消失……所以明白了天和人的区分,就可以叫做至人了。”(《荀子·天論》)
荀子认为,天的运行自有其规律,不因人事而有所改变,人间的治乱并不是“天”直接作用的结果。为此,荀子提出要“明于天人之分”即区分好“天”和“人”各自的职责。
“不用做就能成,不用求就能得到,这叫做天的职责……天有他的时节,地有它的出产,人有它的治理,这就叫做能够参考的东西。舍弃了人用以参考天地的治理,却想要明白天地,就会产生困惑。”( 《荀子·天论》)
荀子认为:使包括人在内的世间万物,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和努力就能获得丰富的馈赠,这是“天”的职责。这种职责,人是无法参与其中的,也不必费心劳神地去参详它,否则就是妄图与天争职。天有四时,地有出产,人有治理能力,治理能力才是人能够用以效法天道的凭借。舍弃了人的治理能力而妄图直接参与到天道本身,就会使人产生迷惑。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荀子·天论》)
荀子认为人对待天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在区分好“天职”与“人事”的基础上,放弃“大天而思之”(孟子)与“从天而颂之”(庄子)的两种极端态度,既不妄求知天,也不消极顺从,而是充分发挥“天”赋予人的认知能力和治理能力,在可认知、可操作的经验世界范围内,通过顺应和利用自然规律,来敬修人事,而不是像孟子一样,把人和天的关系放置在神秘德性主义的立场。
简而言之,荀子的“天论”认为,“天命”与“天意”作为先验世界的宇宙规律是潜移默化、不为而成,可以被人感觉存在,却又无法捕捉的,人无法参与其中或者对其施加任何影响,因此任何妄图在先验世界层面“知天”的努力都是毫无意义的。但“天命”与“天意”在经验世界是留有痕迹的,如天象、地理、四时、阴阳和人类,因此人类又可以通过认知这些自然造物的规律在经验世界“知天”,特别是对人类自身的认知,更是人类在经验世界体察天道的最佳途径,因此荀子主张“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从而达到“知天”和“制天命而用之”的目的。
《荀子》全书都充满着齐文化的理性认知与利用精神,从而使其儒学思想有着迥别于传统儒家的理论风格。有学者指出,“如果说,孟子思想所体现的是一种典型的道德实践理性的话,那么,荀子思想则具有认知理性的倾向。”此论颇为切中肯綮。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荀子儒学思想的理论特征的话,“既仁且智”无疑是贴切的,“仁”是其儒家之体,“智”是其齐文化之用,荀子儒学正是“儒学为体,齐学为用”的产物,“智”是齐文化赋予荀子儒学的重要理论特征,这一理论特征不但没有妨碍荀子儒学的“仁”,反而使儒学之“仁”有了真正落实与应用的可能性。荀子“既仁且智”的儒学思想是先秦儒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对秦汉以后的中国统治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课题项目:本文系2023年度淄博市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荀子思想与稷下学关系研究”(23ZBSK05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1.齐文化研究院;2.淄博市张店区文物事业综合服务中心(张店区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