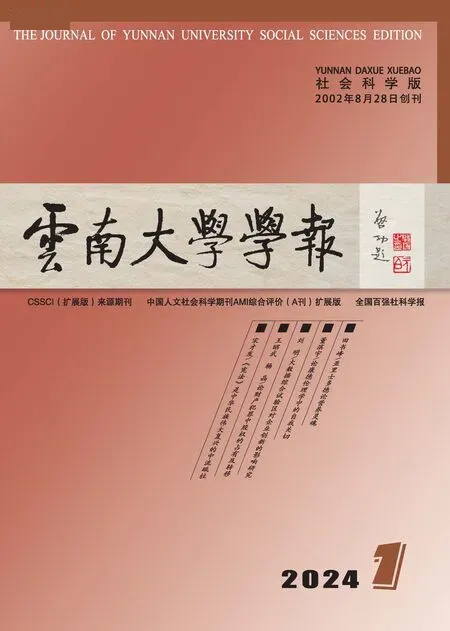论康德伦理学中的自我关切
董滨宇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 100044]
在一些学者们看来,康德伦理学并不关心理性存在者个人的幸福与利益,因为正如康德所说,促进自己的幸福不属于德性义务,因为这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自发的,而只有促进他人的幸福与利益才应该被视为一项义务,而且是道德主体所应该承担的主要责任。当代美德伦理学的代表斯洛特对此展开了激烈的批评,他认为这种观点将导致康德伦理学中“自我—他人的不对称性”,也就是说,康德在过度地强调一种利他主义,而严重忽视了行动者追求自身幸福的重要性。从不同的角度,威廉斯、安斯康姆等当代美德伦理学学者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本文将对此展开深入的分析,通过反驳这种批评,表明康德的义务论保证了自我关切的重要性,并能够为实现每一个人的幸福提供完整的理论支持,而且,其前后期的观点是一贯的,斯洛特的质疑在于其并未全面而准确地把握其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及其关系。
一、自我—他人的不对称性
自当代美德伦理学兴起以来,以理性的普遍性与自律性为中心的康德伦理学一直饱受诟病。在这一派学者们看来,康德主义者们以追求道德规则为宗旨,作为理性的产物,它以其纯粹性而剥离了作为质料的快乐与幸福,尤其是将个人的福祉置于一旁。斯洛特指出,由于以理性法则为中心,不偏不倚的公正性原则成为康德伦理学的基本特征,然而,这种不偏不倚性容易导致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在人的利益或者幸福方面出现了“自我与他人的不对称性”,也就是说,作为义务论的代表,康德伦理学缺少自我关切的维度:
根据康德,不存在关于自我利益的绝对命令,也不存在追求一个人自己的福利或幸福的绝对理性义务或道德义务,这种义务是康德相信能从与他人的关系而非与行动者自己的关系中给予证明的。……可以说康德主义实践理性产生了涉他或偏爱他人的绝对道德命令,但并没有产生合理的自我利益的绝对命令。(1)迈克尔·斯洛特:《从道德到美德》,周亮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年,第34-35页。
在斯洛特看来,无论是常识性伦理学,还是康德伦理学,都不将个人的幸福与利益放在重要位置,更不把实现这种幸福和利益视为道德义务,因此,二者都是“贬低了道德行动者的价值”。究其原因,首先是康德将个人幸福理解为一个主观性概念,康德“认为一个人自身的幸福概念是过于不确定、过于个别地多变的,从而不适合作为命令的基础,这种命令得具有那些从绝对命令衍生出来涉他道德命令所具有的那种深度和力量。”(2)迈克尔·斯洛特:《从道德到美德》,第35页。其次,在康德看来,一个人没有义务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因为每个人都会自发地去做这一点,而职责或者义务只是适用于那些人们不太情愿地采纳的情况。(3)迈克尔·斯洛特:《从道德到美德》,第56页。现实生活中,相对于追求自己的利益来说,我们往往容易忽略他人的利益,因此,康德只是将促进他人的幸福作为一种义务。与此同时,在康德那里还存在关于“完全义务∕不完全义务”的分类。“完全义务”是指道德法则所要求的基本的义务,而“不完全义务”是在此之上人们如果去履行则值得赞赏的义务,其中包括促进我们自己的道德完善和促进他人的幸福。可是,即便在这个范畴内,康德仍然不认为存在着促进自己的幸福的义务和促进他人的道德完善的义务。斯洛特对于这样的主张表达了严重的怀疑,一方面,他并不认为幸福是一个完全主观性的概念,而追求这种个人幸福同样属于道德要求:“幸福、福利或个体利益的这些要素是足够确定的,它们能将关于自我利益的命令赋予我们,而这种命令是康德所明确否定的。”(4)迈克尔·斯洛特:《从道德到美德》,第35页。拉塞尔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康德认为并不存在追求自己幸福的义务,这导致了一种宽泛的意义,即从行为者自身幸福的角度来说,我们不会理解义务。”(Daniel C. Russell,Virtue ethics,happiness,and the good life,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Virtue Ethics,ed. Daniel C. Russell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25)另一方面,一个人也并非像康德所断定的那样是自动地关心自己的利益的。相反,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人在过一种漠视自我、伤害自我的人生。例如那些吸毒者、禁欲者以及那些以牺牲自己的健康换取他人的福利的人。当然,斯洛特注意到,康德也曾指出,我们有义务去发展自己的自然天赋,不去做伤害自己的事,以及施行自我保存,但“除非对完成其他义务有必要,否则我们就没有道德理由去让自己幸福或过得好。(而我们助益其他人的幸福的义务,则在这个意义上并不是衍生的。)”(5)迈克尔·斯洛特:《从道德到美德》,第14页。
总之,在康德的道德义务的排序表中,以个人幸福与利益为宗旨的自我关切始终处于次要位置,它是在保证他人的幸福与利益的前提下获得其合理性的。在斯洛特看来,这是犯了“自我—他人不对称”的错误,而且康德伦理学(包括日常伦理学)将由此导致自身理论的不一致,因为“一个人有义务帮助别人追求幸福,但一个人却没有义务追求他自己的幸福(除非是作为一种派生出的手段,如果追求个人幸福能作为追求他人的幸福或个人的人格或道德成长的手段的话)。然而,康德的道义论(在它的某个方面)对于如何对待人却又要求自我—他人的对称性:一个人不能把自己或他人仅仅当作工具。”(6)迈克尔·斯洛特:《从道德到美德》,第58页。可见,在康德的理论体系中,同时出现了“自我—他人不对称”和“自我—他人对称”两种要求。如果完全依据康德所主张的这种绝对的利他主义,那么其实是将自身完全作为他人的工具而非目的,而这与康德的定言命令之一,即人性论公式是相互冲突的。斯洛特进一步指出,有的人或许会提出以“完全义务∕不完全义务”的模式来解决这一问题,但康德却明确地否认了用这两种义务来进行说明。因为一方面,康德认为追求个人幸福由于是每个人不可避免地去做的,因而不可能是“完全义务”,而另一方面,即便是在“不完全义务”的范畴内,康德仍然没有给个人幸福的谋划留出空间,除非这样做是为了自我完善或者帮助他人。(7)迈克尔·斯洛特:《从道德到美德》,第133页。
康德的“完全义务∕不完全义务”分为对自己与对他人两种类型。在“对自己的完全义务”中,康德列举了以下完全应该禁止的伤害自己的行为,包括因为内心沮丧而自杀、酗酒、自残等等,在斯洛特看来,这些其实都属于对于自身利益与幸福的维护,是康德理论中“自我—他人的对称性”的表现。而康德如果依据其“不存在追求自身利益的义务”这一前提,那么就同样会承认“不存在不得故意自残的义务”。也就是说,按照康德的基本理论,不应该存在有关“对自己的完全义务”的概念设定。(8)迈克尔·斯洛特:《从道德到美德》,第59页。
在康德伦理学中,定言命令是基石,但是,否定追求自身的幸福与利益是一项义务,却是对于定言命令的巨大冲击,也导致了康德伦理体系内部严重的不协调。相反,在斯洛特看来,美德伦理学要求将行为者个人的幸福放到至少与他人平等的位置,因为只有在个人幸福获得保障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去更好地帮助他人。他引用福特(Philippa Foot)在《道德信念》一文中的话说:“如果一个品格特质不能有益于其拥有者或满足其拥有者的需要,这一特质就不能在严格意义上被视为美德。”(9)迈克尔·斯洛特:《从道德到美德》,第9页。即便是康德意义上的理性主体,也不能对自己的健康和免于未来的痛苦漠不关心。同时,追求自身的幸福与利益并不是一种利己主义,因为后者也是不对称的。我们认为,斯洛特所提出的以“自我—他人的对称性”为典型特征的美德伦理学,确实符合亚里士多德所确立的基础性定义—幸福是最高的善。强调这一观点的理论背景是,在经历了现代道德哲学的长期统治之后,人们普遍认为当代伦理学的重心应该从他人的幸福调整到自我的幸福上。
通过对于康德主义的分析与批判,斯洛特揭示了所谓“道德”概念本身所具有的弊病。在他看来,“道德”一词已经被人们视为以利他主义为根本属性的概念,而关心自己的福利往往被视为“非道德的”。斯洛特主张抛弃这种导致 “自我—他人不对称”的常识性道德,而代之以“美德”作为行动的基本规范,它是以“好”或者“卓越”为核心,而不是义务论中的“道德上的错误”、“应该”以及“正当”。在斯洛特的美德体系中,“个人利好”与“可赞赏性”是最为根本的两个原则。
其实,在斯洛特的这种质疑之前,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就表达了类似的见解。在《个人、品格与道德》一文中,他主要批评了康德、罗尔斯等人的理论对于“个人完整性”的忽视与破坏。他指出,康德主义代表了一种典型的“道德的观点”,它是以不偏不倚的绝对命令为表征的,无视特定的人与特定的关系,从而也不关心个人利益的实现。(10)伯纳德·威廉斯:《道德运气》,徐向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2页。不过,斯洛特则发展出了更加完善的论证,在他眼中,康德主义以他者的利益为中心,并且将普遍性的义务视为“道德”的本质,这显然是错误的。与此同时,斯洛特也强调美德伦理学并不因此就是抛弃利他主义道德的,因为帮助他人始终是美德者值得赞赏的重要标准之一。“平心而论,可以说我们的美德伦理学对他人的关心并不比常识道德或康德主义差多少,但对付出行动或拥有可赞赏的特质的行动者自己的幸福的关心,却比两者要多得多。”(11)迈克尔·斯洛特:《从道德到美德》,第10页。
强调个人幸福的重要性,是当代美德伦理学区别于其他理论的突出之处。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生最高的善就是“幸福”或者“好的生活”,而达到它的途径就是“德性”或者“美德”:“幸福是灵魂的一种合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12)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2页。而所谓的“德性”,其基本定义就是“使得一个事物状态好并使得其实现活动完成的好的品质”。(13)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xxvi.然而,基于规则的现代道德哲学,尤其是康德的义务论,只是以其严厉的理性形式为人们设定规则或者目的,就其主要内容来说,是以牺牲自我关切为代价的利他主义。相比而言,以个人幸福为核心的美德伦理学,则是以最适当的方式维护着人格的完整性、一致性以及健康性,并且围绕着每个人的特点与需求规划着其整体性的人生。究其原因,在于从理论的根源上来说,相比于“道德”,“美德”更多地关乎个人的情感、欲望等自然主义诉求,它们构成了个人的特殊性品格,也是实现一个人“好的生活”的主要途径。(14)正如当代美德伦理学学者斯万顿对“美德”的定义:“依据一种亚里士多德的视角,我将‘美德’概念本身视为理性与情感完美结合的性情,在美德状态中,主体通过其行动与正确的情感状态表达了实践智慧与正当目的。”(Christine Swanton,Virtue Ethics-A pluralistic View,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8-9)
二、定言命令与自我关切
在斯洛特看来,康德否定或者忽视了自我关切的重要性,这与其基本的道德法则,即定言命令有所矛盾。初看起来,这种质疑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在此前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里,作为定言命令的“普遍性法则”与“人性论法则”,都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了“自我—他人的不对称性”。然而,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明确地表示不存在“追求自身幸福的义务”。(MS:388)(15)本文所使用的中译本为李秋零主编的《康德著作全集》。为方便起见,《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简写为GMS(《全集》第4卷,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实践理性批判》简写为KpV(《全集》第5卷,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道德形而上学》简写为MS(《全集》第6卷,张荣,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本文主要参考了英译本Immanuel Kant,Practical philosophy,trans. and ed. Mary J. Gregor,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中译本与英译本都是依据普鲁士王家科学院版《康德全集》译出。正文中所用引文仅标出康德著作的简写形式及其编码。可见,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其理论自身的这种严重的不协调。本文则认为,自我关切在康德的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作为“对自己的义务”,这种自我关切不仅包含着作为“不完全义务”的“道德的完善”,也包含着作为“完全义务”的对于自身的尊重以及“自然的完善”,这在其《道德形而上学》的“德性论”部分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康德的这种观点不仅并不与其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所确立的定言命令相冲突,而且还是在后者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必要的推论。
有的学者已经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例如,丹尼斯就指出,康德表明了自我关切的重要性,它体现在“对自己的义务”这一概念中,而这一观点是以其定言命令中的“人性论法则”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在任何时候都要把人视作目的自身而不仅仅是手段,意味着包括行动者个人在内的任何人的幸福与利益都应该成为我们道德义务的目的。(16)Lara Denis,Moral Self-Regard-Duties to Oneself in Kant’s Moral Theory,New York:Routledge,2012,pp.76-77.不过,丹尼斯同时认为,就这一点而言,相比于“人性论法则”,定言命令中的其他法则却并不那么重要。对此,我们并不完全赞同。作为道德法则的最高形式,定言命令并不是一种仅仅意在实现道德义务的强制性模式,更是为了所有人的自身幸福与利益而应该被接受的最为一般性的规则,而且,其中的每一项法则都发挥着同样重要的功能。
首先,应该承认的是,康德确实在其“人性论法则”中明确地提出了“人是目的”的理论,而这也意味着康德的义务论同时也是一种目的论,即康德要求每一个理性存在者应该遵守的道德义务,其实也是一种以保证每个人的利益得以可能的基本的约束性条件。在《奠基》中,他这样说:“用来作为意志自己规定自己的客观基础的东西,就是目的。”(GMS:424)这里的“目的”也就是“法则”,如果它是由工具理性或者慎思理性赋予的,那么就是经验性目的;而如果是由纯粹理性赋予的,那么就是对于一切人都有效的道德目的。康德表明:“实践的原则如果不考虑任何主观的目的,那它们就是形式的;但如果它们以主观目的、从而以某些动机为基础,则它们就是质料的。”(GMS:424)可见,道德行为有其目的,也就是要实现普遍的道德法则,与经验性目的不同,它是具有绝对价值的“目的自身”。人是世界上唯一的理性存在者,而道德法则就是由人来建立的,因此,人就是“目的自身”:“如果应当有一种最高的实践原则,就人类意志而言应当有一种定言命令,那么,它必然是这样的一种原则,它用因为是目的自身而必然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目的的东西的表象,构成意志的一种客观的原则,从而能够充当普遍的实践法则。这种原则的根据是:有理性的本性作为目的自身而实存。”(GMS:428)由于是把自身当作目的,它是一个主观原则,但由于每一个人都是作为理性存在者而把自身当作目的,因此,它同时也是一个客观原则。
通过“人性论法则”,康德向我们正式地提出了他的“目的论”。科斯嘉与伍德都认为,康德全部伦理学的论证起点其实就在于这里所说的“人性”(Menschheit,humanity),作为理性本质的“设定目的的能力”,它不仅是主观价值得以建立的前提,也是一切客观价值或者绝对价值产生的根源。(17)Christine M. Korsgaard,Creating the Kingdom of End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128-131;Allen W. Wood,Kant’s Ethical 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124-132.这也就意味着,人既是设定目的的主体,同时也是目的自身,而且也是作为目的的手段。人不仅必然将自己,而且同时也将他人设定为目的与手段。而在具有最高意义的道德法则中,人不能被限定在这一层面,否则既是对人的整体性福利的削弱,更是对人的尊严的损害。只有在终极价值上将人视作“目的自身”,才能够有效地避免这种不好的结果。
与一般的目的论不同的是,这种“目的论”的内核同时也是“义务论”,因为最终目的本身就是道德义务。作为典型的义务论者,康德固然强调了“为义务而义务”这一根本性原则,但是,这种“义务”的实质却是“以人为目的”,这其实就意味着,人的幸福与利益是其道德理论的核心。正如伍德在论述“人性论法则”时所说:“在康德的理论中,道德的最高原则要求我们产生两种基本目的:我们自己的幸福与他人的幸福。”(18)Allen W. Wood,The supreme principle of morality,ed. Paul Guyer,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nt and Modern Philosoph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354.在《奠基》中,康德并没有过多地探讨作为最终目的的人的“幸福”以及“至善”,但在《实践理性批判》与《道德形而上学》中,这一问题被不断地展开与充实。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康德真正做到了“义务论”与“目的论”的统一。不过,并不是像丹尼斯所认为的那样,“人性论法则”是康德表达“对自己的义务”的唯一的理论基础,实际上,康德已经指出,定言命令的三个主要公式其实只是一个公式,而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是对于另外两个公式的结合。总之,它们都以一个总公式为基础,即“要按照能使自己同时成为普遍法则的那种准则而行动”。(GMS:436)
虽然一般而言,人们按照康德的阐述将定言命令分析为三个主要的分公式:普遍性公式、人性论公式以及自律性公式,但另一方面,康德也一再表明,定言命令其实只有一个。(GMS:421,436)它最为一般性的表述就是:要让自己的行动准则也同时成为其他人所能够接受的普遍性法则。“人性论法则”由于将每一个人作为目的,因此,在康德看来就符合这种普遍性要求。为此,它成为第一个分公式——也就是“普遍性公式”所自然导出的结果。(19)人们普遍认为,定言命令的第一个分公式—“普遍性公式”是由这句话所表达的:“要这样行动,就好像你的行为的准则应当通过你的意志成为普遍的自然法则似的。”(GMS:421)它与正文中所说的总公式几乎表达着相同的意思。当然,一些学者也致力于深入分析各个公式之间细微的差别,本文由于并不牵涉这一主题,因此将不做过多的讨论。
道德义务的客观性首先在于它的绝对的普遍性,而尊重每个理性存在者自身的利益,就成为这种形式化要求所应该具有的实质性内容。每个人的利益都是特殊的,但是,先验的理性推理能够超越于这种特殊性而寻找到最为一般性的目的,这就是“人性论公式”为道德法则所确立的“一种质料”,也就是“一个目的”,即“理性存在者就其本性而言作为目的”。(GMS:436)当每一个人作为理性存在者,都是以自己与他人的利益为目的而建立起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法则时,那么,这样的理性存在者就必然是给自己立法并且自愿服从的立法者,由此,康德导出了“自律性法则”:
一切实践立法的根据客观上在于规则和(按照第一条原则)使规则能够成为法则(必要时成为自然法则)的普遍性的形式,但主观上则在于目的;然而,一切目的的主体就是每一个作为目的自身的理性存在者(按照第二条原则)。如今,由此得出意志的第三条实践原则,来作为意志与普遍的实践理性相一致的最高条件,即每一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都是一个普遍立法的意志的理念。(GMS:432)
严格地说,“自律性公式”的衍生公式“目的王国公式”,是道德法则的最后一种形式。伍德认为,这一公式是之前所有法则的结合,是“定言命令”最充分的表达。(20)Allen W. Wood, Kant’s Ethical Thought,p.166.我们认为,借助这一法则,康德进一步表明,促进自己与他人的幸福,属于每一个理性存在者的道德义务,同时也是人生目的:
就对于他人的可嘉义务而言,一切人所怀有的自然目的就是他们自己的幸福。现在,如果没有人对他人的幸福有所贡献,但也不故意对他人的幸福有所剥夺,人性固然能够存在;但如果每一个人也并不尽自己所能去力图促进他人的目的,则毕竟只是与作为目的自身的人性的一种消极的、而非积极的一致。因为如果那个表象要在我这里产生全部影响,则作为目的自身的主体,其目的就必须也尽可能地是我的目的。(GMS:430)
“人性论公式”要求“人是目的”,它表明每个人都是目的自身,而所有目的的联合就形成了“目的王国”,科斯嘉指出,它意味着人们要对自己负有义务,同时也要承担“交互性”义务:
交互性关系存在于自由与平等的个体之间。如此,出于两个原因,他们要求彼此间的责任。为了产生另一个你自己的目的与理由,你必须将她视为价值源泉,她的选择赋予了她的对象以价值,并且有权利选择自己的行动。为了确保你自己的目的和理由得到他人的关注,你必须认为她也会同样关注你,并准备采取相应的行动。进入交互性关系的人们必须准备共享他们的目的与理由;联结在一起,并且一起行动。交互性是理由的共享,而且,你会希望只有在以理性的方式对待这些理由的情况下,你才会进入这种关系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交互性要求你对他人负有责任。(21)Christine M. Korsgaard,Creating the Kingdom of Ends,p.196.
康德的“目的王国”就是一个相互以对方的利益为首要目的的“伦理共同体”,而实现它的基本途径就是在根本层面上将每一个人都视为“目的自身”。如果每一个人将促进他人的幸福作为自己的义务,那么在这种“相互关切”的体系之中,每个人自身的幸福就将为他人所促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康德将“道德性”定义为“一个理性存在者惟有在其下才能是目的自身的那个条件”。(GMS:435)而只有在每一个人都作为立法成员的“目的王国”中,这一最高目的才能够得以实现。以这样的论证方式,康德消除了人们各自的利益必然相互冲突的难题。
以上的分析是要表明,定言命令的每一个公式其实都是“自我关切”的理论前提。因为康德已经指出,每一个公式在根本意义上都是同一的,正如阿利森所说,它们只是在不同角度对于同一个基本公式的阐释而已。(22)Henry E. Allison,Kant’s Groundwork for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A Commenta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256.斯洛特质疑康德一方面坚持定言命令的至上性,另一方面又排斥自我关切在其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从而导致其内在理论的不一致,其实是一个缺少深入分析的武断的结论。康德的“人性论公式”显然是其目的论的最为鲜明的表达,它要求将每一个人的利益与幸福作为目的,而它与定言命令的其他公式既是相互同一又是相互阐释的关系。同时,在“目的王国公式”中,康德从交互性意义上确立了所有目的的“系统性结合”,在这里,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在整体性目的中获得了一致性。(23)国内学者们也注意到了“目的王国”概念在康德的定言命令中的重要意义。刘凤娟指出:德福一致的至善的实现正在于“目的王国”中各成员之间互为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一个“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幸福社会得以实现。(刘凤娟:《康德的目的王国理念——对Katrin Flikschuh的莱布尼茨式解读的批判》,《道德与文明》2013年第4期)宫睿则主要强调“目的王国”中每个理性存在者特殊利益的重要性,康德是在以个人利益为支点构建一种“准形而上学”式的共同体,也就是说,多元性是一致性的前提。(宫睿:《康德目的王国公式绎解》,《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三、对自己的义务:直接的与间接的
虽然澄清了定言命令与自我关切的关系,我们仍然面临着斯洛特所提出的一个疑难:在康德那里,他一方面声称不存在“促进自己幸福的义务”,另一方面,则又闪烁其词地承认了个人幸福的重要性,但相比于“促进他人的幸福”,促进个人幸福仍然只是一种“间接义务”,在价值追求中,只占有次要的附属地位。应该说,在文本中,这种表述上的含混确实存在,但我们仍然可以结合康德的整体性表述得出这样的判断:在根本意义上,义务论认为存在着促进自己的幸福的义务,这一点已经为定言命令所规定。不过,首先,在“不完全义务”的意义上,这种幸福主要是指包括“自然完善”与“道德完善”在内的更高一级的幸福;其次,在“完全义务”的意义上,这种幸福是指包括避免自残、酗酒、暴饮暴食等在内的基本的身心健康。而且,后者是保障前者能够实现的前提。另一方面,康德认为个人幸福只是“间接义务”,是基于定言命令中所具有的“交互性逻辑”所提出的观点,即只有在主观意向上以关爱他人为首要动机,才能在客观上形成提升所有人利益、从而达到各种特殊目的相互统一的局面。也就是说,在价值排序上,所谓的“直接义务”(促进他人的幸福)与“间接义务”(促进自己的幸福)并没有高低之分,只是在实践的意义上,二者才存在这种先后的差别。
在康德那里,义务是指“通过法则来强迫(强制)自由任性的概念”。(MS:379)可见,一切非强制的自愿的行为对象,都不能成为义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认为由于每个人都自动地寻求个人的幸福,因此它并不能算作义务。不过,在这里,需要我们结合文本针对所谓的“幸福”作进一步的分析。实际上,这种“幸福”仅仅是作为“个人主观性喜好”的概念,例如一个人爱喝酒、爱旅行等等,由于不具有客观必然性而不能构成任何一种道德义务。但是,康德随即提出了客观性的幸福概念,而它才是能够作为共同目的的真正的义务(无论是完全义务还是不完全义务)。
在《道德形而上学》中的《哪些目的同时是义务的目的》一节,康德将德性义务的一个基本维度确定为“促进他人的幸福”,而且,康德将其称为“直接的义务”。相比而言,德性义务的另一个基本维度则是促进自己的完善而非幸福。不过,对于这一观点,康德随即做了补充:“为自己谋求富裕,并不直接地是义务,但却间接地能够是这样的一种义务,亦即防止贫穷,贫穷是恶习的一大诱惑。”(MS:388)可见,追求自己的幸福也成了主体所应该肩负的义务,虽然是间接的,不过,这种幸福更准确地说是世俗性的“自然幸福”。康德接下来说:“但这样一来,它就不是我们的幸福,而是我的道德性了,保持道德性的完美无疵是我的目的,同时也是我的义务。”(MS:388)也就是说,原来的“自然幸福”,现在变成了“道德幸福”,或者说“道德完善”。本文认为,道德完善虽然属于“不完全义务”,即它是超出基本义务的更高的目的,但是,在康德那里仍然属于“直接义务”,这样一来,作为实现自己德性义务的保证,尤其是道德完善的必要条件,促进自己的幸福实际上也属于直接的而非间接的义务。也就是说,在与道德目的相关的前提下,主观性幸福提升为客观性幸福,由此,对个人幸福的追求也正式地属于一项德性义务。
这样的解读并不是没得有道理的。首先,康德在“对自己的义务”中,首先强调保持生命和身心健康是“完全义务”,即主体应该达到这些基本要求,如应该避免自杀、酗酒、暴饮暴食等恶习。在讨论作为“不完全义务”的“自己的完善”时,则区分了“自然的完善”与“道德的完善”,前者实际上相当于我们通常所说的肉体上的健康与完善,而后者则属于更高阶段的精神上的完善。由于理性无法对于任何一种完善的程度做出准确的规定,所以二者都属于对自己的“不完全义务”。重要的是,前者是保证后者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MS:392-393)在自然完善阶段,康德提出要发展个人的天赋:“培植自己作为达成各种可能目的的手段的自然力量(精神的、灵魂的和肉体的力量)……人对自己(作为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负有责任的是:不让自己的理性有朝一日可以利用的自然禀赋和能力不被利用。……培养自己的能力(在这些能力当中,根据其目的的不同培养一种能力比培养另一种能力更多),并且在实用方面做一个与自己的生存目的相适合的人。”(MS:445)具体而言,首先要培养精神的力量,也就是锻炼理性运用的能力。它最典型地体现在数学和哲学的学习中,只有借助于这种智慧之学,人们才能够达到其目的;其次,培养灵魂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记忆、想象力之类的东西,是知性规则和经验之间的相互配合,据此,人们能够获得博学与鉴赏的特质;第三,培养肉体的力量,这是“人对自身的目的”。人们应该照料身上的质料,因为没有这些东西,人就不可能实现自己的任何目的。通过有意识的、持续不断的体育锻炼,人能够保持这种动物性。(MS:445)
在追求自然完善的过程中,康德要求给予主体充分的自主选择的权利,即要以个人的愉悦为准则,这一点集中体现了他对个人自身幸福的关切:“这些自然的完善中哪一种是优先的,在相互的比较中以什么样的比例使它们成为自己的目的而是人对自己的义务,这一点依然听凭在对某种生活方式的愉快方面对它们自己的理性思考和同时对人为此所必需的力量的评价,以便从中做出选择。……因为且不说自身不能建立任何义务的自保的需要,人对自己的义务就是做一个对世界有用的成员,因为这也属于其自己人格中的人性的价值,因而他不应当贬低这种人性。”(MS:445)
以自然完善为基础,人们将继续追求道德完善,即主观上达到纯粹的道德意向,此时,人的内心中不掺杂任何感性要素,“法则独自就是动机,而行动不仅是合乎义务地,而且是出自义务作出的。”(MS:447)同样作为“不完全义务”,它只是人生的一个崇高理想,因为人们无法真正完全地了解自己,而只是应该朝向这一目标不断地努力。
这样一些论述表明,自然完善不仅是道德完善的前提,而且,由于道德完善是人生的最高目的,所以我们应该同时追求自然完善。当然,自然完善并不必然导出道德完善,但是,蕴含着愉悦与幸福体验的自然完善,应该成为通向道德完善的主要途径。据此,追求世俗性的个人幸福也是具有道德价值的,康德清楚地说道:“令人讨厌的事、痛苦和匮乏是违背自己的义务的重大诱惑。因此,富裕、强大、健康和一般而言的福祉,是和那种影响相对立的,它们看起来也能够被视为同时是义务的目的;也就是说,促成其自己的幸福,使它不仅仅为了他人的幸福。但这样一来,这种幸福就不是目的,而主体的道德性才是目的,为这个目的清除障碍,只是被允许的手段;因为没有其他人有权要求我牺牲我那并非不道德的目的。”(MS:388)依据这一思路,康德虽然接下来就说谋求自己的福祉属于“间接义务”,但随即又将其归入个人的道德性之中,并最终认为,保持这种蕴含着个人幸福的道德完善,既是我们的目的,也同时是我们的义务。
当澄清了理论上的复杂关系之后,我们就可以针对斯洛特所提出的问题给予更为充分的回应。首先,斯洛特认为康德只是从主观性角度理解“幸福”概念的,然而,在斯洛特看来,“幸福”具有客观性内容,而追求幸福应该成为人的道德命令,一个人应该关心自己的利益与福祉。对此,我们认为,其实,幸福的涵义在康德的理论体系中有所变化。在《奠基》中,幸福主要属于一种经验性概念,而这是因为康德此时要着重强调道德行为的纯粹性与普遍性,从而否定将任何与感性偏好有关的要素作为这种行为的根据。但是,即便如此,康德在有些地方仍然表明,“幸福的理念”是“绝对的整体”,是“未来的福祉的最大值”。(GMS:418)到了第二批判中,幸福的涵义则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康德认为它是“自然与理性存在者的整个目的以及本质性规定根据的协调一致”(KpV:124)据此,我们认为,康德提出了一种先天的、形式化的幸福概念。与仅仅作为感官满足的幸福不同,它具有一种普遍的客观性,在这个意义上,追求幸福也属于人们所应该服从的道德义务。不过,在《道德形而上学》中,这种“主观性幸福”与“客观性幸福”在康德的论证过程中都同时存在。和很多研究者一样,斯洛特并没有注意到幸福概念在康德伦理学中的多重内涵,而仅仅将其视作经验性的满足或者世俗性的愉悦状态,从而不明白康德所要求的规范的只是这种世俗的幸福,但同时却高扬精神层面的“道德幸福”,它意味着人的整体性价值的实现,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内在和谐的体验,很大程度上,它接近于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至善。我们认为,它也接近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作为美德最高目的的“幸福”。(24)一些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了康德与亚里士多德在对“幸福”与“德性”的理解上的一致性。可参见Stephen Engstrom,Happiness and the Highest Good in Aristotle and Kant,eds. Stephen Engstrom and Jenniffer Whiting,Aristotle,Kant and the Stoics-Rethinking happiness and Dut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102-138;Allen Wood,Kant and Virtue Ethics,eds. Lorraine Besser-Jones and Michael Slote,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Virtue Ethics,New York:Routledge,2015,pp.307-320.在这一形式化的概念之下,康德认为,每个个体可以有不同的关于幸福的理解与感受,但只要这种幸福从道德角度是主体有资格享有的,那么这就是最高的目的,是每一个人值得去追求的目标。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对于有利于道德培养与完善的任何一种世俗的幸福,比如身心健康以及生活充足,都是我们应该去履行的义务。
在斯洛特眼中,康德还犯了一个认知性错误,即认为由于每个人都是自动地关心个人的利益,因此,不应该把追求自己的幸福视为义务。但是,斯洛特指出,这种理解是不符合实际的。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并非像康德所认为的那样会自动地关心自己的福利,而是往往会有意或者无意地做出伤害自己的事情。针对这样的人,应该将关怀自己的身心健康以及人生完善作为其首要的义务。
的确,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未必像康德所认为的那样理性而且乐观,我们看到太多的悲观厌世或者有心理疾病的人做出损害自己的行为,我们也看到正常人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丧失理智而自残,同样,即便是清醒的理性存在者,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也很有可能做出在旁人看来对自身并不有益的谋划。所有这些现象都证明一点:人们并非自动地关心自己的利益与幸福。然而,我们认为,这并不能真正构成对康德观点的威胁。因为首先,康德在其论证中始终都将行为主体限定为“理性存在者”,即具有一般的理智性推理能力以及能够形成道德观念的人,这也就将那种不具有正常精神状态的人排除在外。而对于正常的理性主体,虽然从客观角度人们可能判断其对自己所做的谋划或者行为其实是有害的,但是,这在具体的实践中是一个缺少确定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正常的理性范围内,旁人并不能保证拥有充分的、明确的信息,能够针对一个人所要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行动做出准确的断言,“判断的负担”要求他人慎重地对待个人的选择,最好是将这种选择权在道德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地赋予行动者本人。正像康德在《奠基》中的第一章中就指出的,对于具体的幸福,人们很难取得一致的意见,而只把它当作个人的特殊目的。可以设想这样的情况:当一对父母要求已经具备理性能力的孩子通过各种方式努力成为一名商业精英时,这个孩子可能坚定地认为自己最大的幸福就是做一名足球运动员。现实昭示给我们的更加确定无疑的经验是,人们对于价值与目的的理解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而这种丰富的人生样态恰恰是人类得以持续发展的动力。康德在这个意义上不将个人的特殊的幸福视为义务,其实能够避免他人以“为了你的幸福”作为名义而对你的选择进行自以为是的武断的干涉,这恰恰是基于道德法则对于个人权利与尊严的有利的保护。而如果遵循斯洛特的思路,那么就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这对父母认为孩子应该对他自己的个人幸福负责,但是他们坚决不认可孩子对于幸福涵义的理解,由此,他们进一步认为,自己能够站在孩子的立场上,为其个人幸福做出“合理的”谋划,但是,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减少了孩子个人的幸福,甚至是损害了整体性的幸福总量。
对此,反对者们或许仍然能够提出质疑,因为即便是接受康德的观点,即以他人的幸福为己任,那么同样将产生类似的问题。例如,这对父母可以认为自己正是将孩子的幸福作为道德义务,因此才强制性地对其做人生的规划。我们认为,这种误读在于并没有真正理解康德的真实意思。以他人的幸福为目的,前提是必须尊重他人的个人选择,也就是说,尊重他人的自主,而人的尊严正是基于这种自主。所谓的“幸福”,无论对任何人而言,必须首先符合道德法则的要求。尊重人的尊严,这是康德所确立的最高意义上的道德法则的核心内容。
四、结 语
由于总是强调道德义务的利他性,在斯洛特看来,康德伦理学犯了严重的“自我—他人不对称”的错误,然而,这种批评并不能令人信服。以他人的幸福为义务,并不意味着与具有绝对普遍性的道德法则相冲突。实际上,如果每个人都在德性义务的要求下致力于促进他人的幸福,那么由此产生的效果将是他人也会促进自己的幸福,因为主体在他人的眼里也变成了客体。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以促进他人的幸福为义务”,作为一个命题将同时导出“每个人的幸福都将获得提升”,借用康德的术语来说,两个命题可以是分析的关系。相反,如果将“以促进自己的幸福”为首要义务,那么不仅导不出后一个命题,而且可能会由于助长了人们的自我中心主义观念,从而致使每个人的幸福都受到损害。正如克莱格尔德所总结的:“在一个道德世界中,我促进他人的幸福,而他人也促进我的。每个人的幸福在他人的眼中都是善的,反之亦然。这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中,美德者们集体地致力于所有人的幸福。以这种方式,包含了幸福的至善应该得到辩护,因为道德法则要求促进这样的幸福。反过来也意味着,由美德行动产生的幸福不仅仅是愉悦的,而且也确实在道德上是善的。”(25)Pauline Kleingeld,Kant on ‘Good’,the Good,and the Duty to Promote the Highest Good,ed.Tomas Höwing,The Highest Good in Kant’s Philosophy,Berlin:De Gruyter,2016,pp.40-41.
斯洛特注意到,康德通过“对自己的义务”,也涉及了对于个人利益和幸福的维护,然而,康德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自己理论中所蕴含的这种“自我—他人的对称性”,相反,无论是关于对自己的完全义务还是不完全义务的论证,康德始终都是将他人的幸福作为道德义务的首要目的。对此,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康德在“对自己的完全义务”中其实既强调了维持生命、保护健康这种基本的义务,又在“对自己的不完全义务”中强调了发展自然禀赋、从而达到道德完善这种更高层次的目的。当然,按照斯洛特的理解,所有这些与对自己的关爱和发展有关的义务,在康德那里都属于自然的完善,而它们都是为了服务于最终的目的——自我的道德完善,这种完善的核心内容仍然是促进他人的幸福。对此,我们可以依据《道德形而上学》中的相关论述表明,实现个人的自然完善或者幸福,在根本意义上就具有道德性,因为就像康德所表明的,作为实现道德完善的必要条件,我们必须将其也视为义务,只不过是为了服务于道德完善的间接的义务。但是,这种“间接义务”并不意味着相对于“直接义务”而言是不重要的,只是说它在道德实践中并不处于在先的位置。但是,就义务论的整体性范畴来说,康德仍然是将幸福(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体)确立为以道德法则为基础的德性义务。因此,我们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种“间接义务”其实仍然能够被转换为“直接义务”,只不过康德认为只有在动机与行为上以他人的幸福作为首要目的,才能够真正实现包括自我幸福在内的每一个人的幸福。
作为当代美德伦理学的代表,斯洛特的观点体现了这一流派对于康德主义的一种普遍性的怀疑。然而实际上,康德伦理学以其义务论为核心,能够包容“自我—他人的对称性”,它不仅表达着一种自我关切,而且同时避免了滑向利己主义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