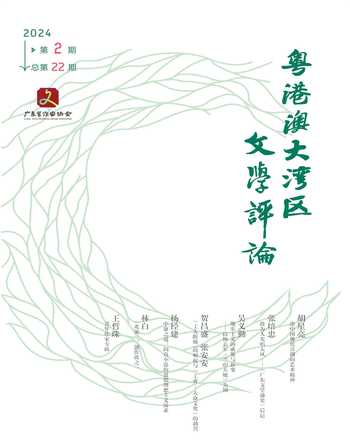“工人阶级”的崛起与“工业—大众文化”的勃兴
贺昌盛 张安安
摘要:就“现代”世界而言,真正主宰整体社会之演进趋向的核心力量,其实是由产业革命而催生出来的新兴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在持续推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衍生出了以“工业产品”为主要依托的消费型文化形态,由此才使得源自“工人”底层的“大众文化”成为了自20世纪至今一直被关注的热点话题。如同其他的文化形态一样,“工业-大众文化”同样存在着利弊参半的问题。一方面,法兰克福学派以“文化工业”为切入口,对工业社会的技术理性所造成的人的“同质化/异化”现象给予了全面的批判;另一方面,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启发下,伯明翰学派则从“工人阶级”所特有的“群体意识”中寻找到了以“文化政治”引导社会趋于良性发展的“左翼新路”。“大众文化”绝非一个可以无限泛化的概念,脱离了“工人阶级”主体和“工业生产”基础,现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将始终无可定位。
关键词:工人阶级;大众文化;文化工业;文化政治
自20世纪中期以来,“文化研究”一直是欧美学界所关注的焦点话题之一,它也直接影响到了1990年代至今中国学界的学术转向。但在多数的论述中,作为核心范畴的“大众文化”概念始终处于含混未定、语焉不详,甚至包罗万象的状态。尽管“大众文化”的涵盖面确乎极为宽泛,但事实上,这一概念的出现与凸显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的。“大众文化”与“工人”这个完全新兴的“阶级”群体有着深层的关系,更与产业革命所激发出来的全新生存方式密不可分。与之相对应的,“大众文化”的实际蕴涵还曾出现过从法兰克福学派以“同一性”为前提的“mass culture”批判,到伯明翰学派所强调的“公共性”的“popular culture”的动态变化过程。所以,某种意义上讲,脱离了“工人阶级”主体和“工业生产”基础,所谓“大众文化”恐怕仍旧只能是一种飘忽不定的幻影。
一、作为新生动力的“工人阶级”
从总体上说,“现代”世界的基本标识可以作如下概括:在器物层面,所谓“现代”主要显示为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的日趋完善;制度层面则体现为“契约/法”的体制化理论与实践的基本实现;思想层面的“现代”意识主要是指平等、权利等等观念的普遍认同。以此作为参照,农耕或游牧形态下的等级社会形态可谓之“前现代”,而以“差异性”来对抗“同一性”的“多元/非中心”取向则可谓之“后现代”。当然,此种概括只能是一种宏观的表述,目的只在为“工业/工人/大众”等貌似习以为常实则一直处于被遮蔽状态的诸多问题的剖析划定一种整体的知识构架。
“现代”世界发生革命性的巨变,应当是始于“机械生产”的大规模推广。最早出现产业革命的英国,即是在纺织机和蒸汽机等机械的广泛应用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社会的整体转型的。雷蒙·威廉斯曾指出,工业革命“是对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技术革新及其相应的生产方式变革的认可,同时也是对由此所引发的整体社会变革的一种默认,因为社会也经历着同样的变型期。”1机械的广泛使用在替代繁重的人力劳动的同时,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的效率,却也为扩大生产和再生产提出了新的问题,那就是能够正确操控“机械”的“人”的需求量在不断扩大。与前现代时期手口相传的手工技艺不同,从事大规模机械生产的“人”既需要掌握熟练的技能,更需要拥有最为基本的一般“知识”——藉此以避免各类错误操作引发事故以至造成重大的损失。所以,“工人(worker)”最初指的就是具有基本机械知识并且拥有机械操作的专门技能的“人”,其与传统意义上的“手艺人(craftsperson)”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差别。汤普森即曾指出:“工人階级并不像太阳那样在预定的时间升起,它出现在它自身的形成中。”“劳动人民的新的阶级意识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一方面,不同职业和不同文化水平已经意识到他们有着个体的利益。……另一方面是意识到工人阶级或‘生产阶级自身同其他的阶级的利益相对立,而且其中还包含着日益成熟的建立新制度的意识。”2
进一步说,传统的“手艺人”大多是以“个体”的形态而出现的,“工人”则以其相似相邻的特质成为了一种群体性的新兴阶层,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发掘出了这一特定阶层前所未有的深层价值。恩格斯在1845年专门撰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对产业革命发生以来“工人”这一新兴阶层的基本生存境况作了全面的分析。恩格斯认为,尽管工人有自己的劳动保障并改善了自己的生活,但他们在本质上依旧是一无所有的“无产者”。“我们已经看到,机器的使用如何引起了无产阶级的诞生,工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人手的需要;工资提高了,因此,工人就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人口以令人难以相信的速度增长起来,而且增加的差不多全是工人阶级。”3马克思概括认为,“工人阶级”之所以可称为“无产阶级”,实质在于这一阶级并不拥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而只能靠出卖自身的体力和脑力劳动来获得生存所需,而且绝大部分的劳动成果是被“资产”拥有者所占有的——其彼此的矛盾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矛盾。换言之,一种本该“主宰”社会发展趋向的“力量”——积极生产能推动经济繁荣而罢工停产则能导致社会生活的瘫痪——却被迫蜷缩在社会的底层作无望的挣扎。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弱势的“工人阶级”其实恰恰是可以改变整个社会机制的潜在而巨大的力量,真正彻底的社会变革也只能以“工人阶级”为主导,但前提是,“工人”必须切实地“自觉”意识到自身这一群体性力量的存在。如恩格斯所言,“在欧洲各国,经过了许多年的时间工人阶级才完全相信,他们是现代社会中一个特殊的阶级,而且,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下,是一个固定的阶级。”1作为一种设想,《共产党宣言》中所倡导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理论逻辑上,是能够以一种“革命”的方式从根本上改变既有“资本社会”的压迫与不公,进而实现公共生产和公共享用的自由与平等的“共产社会”的。对于“工人阶级”这一新生的特定群体的发现,也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魅力所在之一。
当然,作为某种本质提炼,“工人阶级”确实具有其相对同一的共同属性。但在具体境遇中,这一阶级自身内部的差异性也是十分明显的。恩格斯对于这一点也曾给予过准确的剖析,比如,除了工人与资产者之间的矛盾之外,工人与外来者、工人们彼此之间,以及工人与机械劳动之间等等,也都存在各式各样的矛盾。汤普森也强调,“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e)是一种复数而不是单数,复数的“工人阶级”是在不同关系的交往甚至冲突中由共同经验和利益联合而成的同盟体。“集体的自我意识实际上是工业革命的伟大精神成果,它是针对工业革命而产生的一种裂变,而且也是一种较为古老的、较能为人性所能理解的生活方式。”2雷蒙·威廉斯也肯定地认为:“团结观念把共同利益定义为真正的自我利益,认为个体的复杂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得到检验,因此这种观念是社会潜在的真正基础。”3历史的实践表明,“暴力革命”的方式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某种甚至根本性的矛盾,却也需要付出可能极为惨重的代价。正因为如此,当伯明翰学派反观“工人阶级”这一群体之时,他们的目光才会从“暴力革命”转向“文化协作”,尝试从“文化政治”的角度走出一条能够循序渐变的“新路”。
二、“工业-大众文化”的兴盛
“文化研究”之所以会引发全球范围的普遍关注,其关键就在于,它在走出以阶级矛盾为核心的对抗性“意识形态”思维模式的同时,为“文化”自身的包容、交流和对话开辟了一条可行的全新路径。
应当承认,产业革命的发生的确在物质层面上彻底地改善了人类的基本生活,它也同时刺激了作为生产主体的“工人”自身生存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所谓“文化”,在现实层面上指的其实就是人的生存方式。如保罗·威利斯所言:“文化的特性在于社会能动者‘意义创造的积极过程,尤其是在理解自身生存处境,包括经济地位、社会关系以及为维护尊严、寻求发展和成为真正的人而构建的认同和策略的过程中。”4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工人阶级”与生俱来的“斗争性”有所不同,伯明翰学派更加突出“工人阶级”这一特定群体的全新生存方式对于“现代”社会所蕴涵的深远意义。或者说,正是“工人阶级”的崛起,才创造性地生成了一种根植于底层民众却又完全区别于此前所有文化形态的“新型文化”;惟其产生于更为广泛的“大众”之中,且随着产业革命在世界范围的持续扩张,其世俗性和普适性也更为明显,所以才被提炼称之为“大众文化”。在马克斯·韦伯的意义上,“大众文化”可以说正是趋于理性化和世俗化的“现代”世界的最为显著的标志。
具体而言,与前现代时期相对封闭的自然型生存形态相比,工业化时代的“大众文化”有如下几个突出的特质:首先,大众文化的载体是“城市-市民”。这里的“城市(City)”与前现代的城邦、城堡、市集、封地、公国等等由分封及传承或自然形成的特定“属地”有着根本的区别;现代的“城市”是随着产业革命的扩张,由来自不同地域的“工人”共同协商规划完全重新建设而形成的全新的“聚集地”。因其“汇聚”,其各自不同的文化遗留才有了碰撞、借鉴、互融、转变的可能。由此,以城市为“聚合体”的“大众文化”也才有了相对共同的“共享型”文化取向。有别于以少数人群为主的“贵族/精英”文化或农耕、游牧式自然形态的文化,大众文化是一种在异质文化彼此渗透和磨合的基础上取其“最大公约数”而人为构建出来的新型世俗文化。其次,“大众文化”形成的根基是现代工业的发展,其所依托的是工业技术的持续革新,这就使得大众文化自身也会始终处于不断创新和变化的动态过程之中——所谓“时尚/新潮”也即源自此。以产业革命为基础的“大众文化”自身即带有先锋和开放的特征,包括对精英文化的吸纳与改造或对传统自然文化的复活与转化,这一点实际也正是“现代”世界的特质。如威廉斯所言:“在新兴的都市文化发展的同时,在和传统的文化形式的复杂联系中,城市中的工人阶级和贫困阶层对于文化的趣味和质量也发展变化了。”1再次,在工业化社会中,“工人”无论其产业“分工”有着何种的差别,他们都同样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这就使得他们所“共享”的“文化”也必然地会受到“生产-消费”经济循环模式的制约,进而使“大众文化”本身带有了以“商品”意识为导向的“消费主义”的明显色彩。“大众文化是人们从文化工业产品中创造出来的。文化工业生产的只是群氓文化,而人们主动从中提炼、再创造出来的才是大众文化。这原本是个消费的过程,但人们在消费的同时对商品和商品化的实践加以利用。”2英国产业革命初期,所谓“工人阶级”还只是一种较为涣散的聚合体,“工人”自身也都保留着其各自的信仰、习俗、嗜好及传统生活惯性。但随着产业革命的迅猛推进,越来越多的“工人”被纳入了工业社会的规范系统之中。除了物质生活上对于工业产品的日趋依赖之外,精神层面的“文化”生活也同样被卷入工业化和商品化的漩涡。如约翰·斯道雷所指出的那样,“无论采用何种方式来为大众文化下定义,有一个前提都是毋庸置疑的,即大众文化只有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才能出现。……无论文化还是大众文化,都深深根植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土壤中。在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英国毫无疑问地成为大众文化的诞生之地。”3进入20世纪以后,由英国的产业革命催生出的这种全新品质的“工业-大众文化”,开始在全球各个区域蔓延兴盛。一方面,英国式的“工业-大众文化”在不同国度(或者以殖民的方式)得以“复制”;另一方面,它也激发了各式“文化”形态的变异,比如对于“丑”的艺术的欣赏,对于超现实主义或未来主义等现代主义艺术的极度张扬,以青年“亚文化”为突出表现形式的对于既有生活样态的激烈反叛,甚至视“商品价值”为判别一切的最高且唯一的价值尺度,等等。如果说如何定位“现代性(Modernity)”迄今依旧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的话。那么,“工业-大众文化”也许确实可以看作是“现代性”问题发生的真正起点。
三、从“文化工业”批判到
“文化政治”引导
无可否认,由作为新生力量的“工人阶级”所生发出来的“工业-大众文化”,确实已经造就了“现代”世界最为普遍的全新生存方式;它不仅渗透进了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直接主宰了人们的思维与选择。
事实上,早在产业革命兴起之初,马克思就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过劳动生产过程中“人的异化”的问题,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中则进一步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物化-商品拜物教”的问题。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一系列论述直接启发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思想,他们从无处不在的“文化工业”现象中透视到了现代世界深层的精神危机。
尽管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将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与单调乏味的精神生活中解脱了出来,但在机械重复与繁荣变幻的表象之下,人们其实已经“异化”成为了其生产对象的“奴隶”,其核心的本质就是对于“工业化/商品化”生存方式的高度依赖。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看来,工业社会的所谓“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在以“工业”的方式来大规模批量生产“形态同一”的“文化”,进而塑造“面目一致”的“人”。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即认为,当资本拥有者借助同一化、平面化的策略诱导大众沉迷于各式纷纭的“虚假需求”之中,或者通过各种娱乐媒介来蛊惑大众时,普通民众最终将丧失其独立自主的判断力和否定力,“大众文化”在此不过是“文化工业”的代名词。“文化工业的每一个运动,都不可避免地把人们再现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种样子。”1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也曾针对以工具理性为标识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所造成的现实生存境况指出,“单向度”的社会体制结构必然导致“单面人(One Dimensional Man)”的出现;工业社会的“消费控制”助长了人们的物质及享乐需求,同时会强化工具理性成为解释整个社会生活的唯一合法的逻辑,鲜活的富有感性的“人”最终就被“技术理性”驯化成为了其自身理性的工具。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尽管认为工业化的机械复制使得曾经为少数人所拥有的“高雅”艺术真正具有了普遍的“民众共享”的色彩,但“光晕”(Aura)的消失也同时消解了艺术自身的独特魅力与深层的精神价值。当技术理性所推动的文化工业高速发展而单维社会结构的固化逐步趋于日常化时,人们往往会把大众产品中所传播的文化等同于常态的“真实的”现实生活的延续;大众文化为满足市场消费的需要,向人们提供标准化、没有思想深度的、平庸的通俗产品,以迎合在机械劳动中的工人阶级群体的初级精神需求,使其在无意义的娱乐消遣过程中得到放松。久而久之,就会促使工人阶级群体对社会的不合理视而不见,习惯于“技术理性规范”对其思想的垄断,进而形成普遍的现实逃避与社会认同。其中所隐含的恰恰是“大众文化”对于大众的广泛欺骗性与操控性。
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工业-大众文化”的批判有其相当的启发与警醒意义,马尔库塞所提出的“审美救赎”和本雅明的“弥赛亚式”拯救等也都同样不失为某种走出困境的可行的方案。但同时也不应忽略一个关键的事实,那就是,纯粹“个体”的自我反思(辩证性否定)与感性复活(审美创造或信仰回归)固然是某种积极的策略,但是在面对以“群体”方式出现的“工人阶级”之时,此种策略的有限性也就随之显露出来了。即此而言,葛兰西所提出的有关“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的构想或许是一条更加切合于“工人阶级”求得真正解放的现实路径。
葛兰西并不否认“工业-大众文化”中所隐含的种种弊端,但他认为,造成此种弊端的根源实际在于“资本”拥有者对于“文化权力”的全面操控;反过来说,如果“文化权力”能够真正为“工人-无产阶级”自身所掌握,那么,其所造就的无疑将是一种彻底摆脱贵族精英、资产阶级及一切陈旧没落思想的全新的“文化”形态。“工人-无产阶级”的真正解放不能只是单纯地寄托于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改变社会体制,更重要的是,必须通过对于“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与掌控,来实现其自身从物质生存到心灵自由的全面解放。
葛兰西的思想对于伯明翰学派产生了多重向路的影响与启发。由于伯明翰学派诸人大多出身于工人阶级,他们自身的生活环境与平民大众联系紧密,所以比仍旧保留着浓郁学院精英色彩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学人更加具有平民的经验与视野,对于大众文化为社会带来的积极推动作用以及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更为关注。相比于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否定”,伯明翰学派更多的是从“建设”的角度出发看待大众文化的,其所注重的正是大众文化的平民性和普泛性。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aggart)曾描绘过大众社会鲜活生动的文化生活图景,他认为,工人阶级实际上并非全然是被动地在消费着资产阶级提供的大众文化,他们同样能够自由地选择自然而淳朴的生活方式,充实且快乐。“城市工人阶级能积极应对自身环境变化和廉价大众产品入侵的双重挑战”。1汤普森也敏锐地指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教育的普及,由“工人阶级”所主导的“大众文化”形态其实一直都在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得以改造、提升和传承。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相对左倾,对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抱有同情,他们对自己的父兄曾用汗水浇灌了工业革命之花的普通劳动者追忆缅怀、又充满崇敬,同时又有一种神秘的好奇感,想在他们的经历中寻找自己的来源。这是一种‘寻根热。”2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已经关注到了“工人阶级”文化的“群体”特性与阿诺德式或利维斯式的精英主义文化的根本差异,他认为,与资产阶级文化注重由个人思维决定的制度、方法、思维习惯和意图不同,工人阶级注重的是集体思维。“工人阶级文化,以其历经的阶段而言,基本上是社会性的(在于它创造了机构),而非个体性的(特别是在智性或想象性作品上)。如果把这些置于具体语境中进行考虑,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非凡的创造性成果。”3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则更是直接将“工业-大众文化”的特定生存方式推向了以“文化政治”来引领和革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机制的向路上。
在英语语境中,尽管“mass culture”和“popular culture”都指代“大众文化”,但“mass culture”主要是与“high culture(精英文化)”相对而言的。“mass”意味着数量众多(群众),“massculture”所指的也主要是以“工业技术”方式所生产出来的如电影、广播、电视、摄影、广告和流行出版物等一系列由商业利益驱动的通俗文化产品,而这类产品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缺乏个性及其标准化、齐一化的趣味与审美取向。这也正是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对象(与他们对于精英意识的坚守密切相关)。不过,在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家们看来,“工业”时代的“大众文化”更多的是应当回归其源自“民间/民众/民有”的“popular/of people”的“自发生成”的“本位”。唯其是一种“自发”的文化,它才有可能摆脱被动地“接受改造”的现实境遇(成为对抗资本社会的潜在的力量);也唯其是一种“生成”出来的文化,其自身才会充满了活力与创造性(以此消解现代世界的“同质化”趋向)。这也许才是由伯明翰学派兴起并最终引发全球学界关注的“文化研究”能够作为热点问题持续至今的根因。
“文化研究”能够在中国逐渐得到肯定和延续,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已经处在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之中,国人也已经初步品尝到了“工业-大众文化”的滋味。但也应当看到,中国的“工人阶级”及其“工业-大众文化”尚处于相对稚嫩的“初期”,且带有明显的“外源/效仿”的特性。加之由中国历史所形成的农耕-乡土文化形态的遗留,传统文化的多元取向,以及不同空间-地域文化的差异性影响,我们所理解的“文化”就更增添了诸多的复杂性与混融性。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混融与复杂其实也正为新的“文化创生”提供了可资吸纳、延续、汇流、利用和转化等的有利基础。如果能够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式创造出真正富有自身特色的全新文化形态,也当被视为对现代人类世界所作的独特的贡献。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1 [英]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第2页。
2 [英]约翰·B.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第951页。
3 [德]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0页。
1 [德]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页。
2 [英]约翰·B.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979页。
3 [英]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第343页。
4 [英]保罗·威利斯:《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秘舒、凌旻华译,译林出版社2013版,第2页。
1 [英]雷蒙·威廉斯:《出版业和大众文化:歷史的透视》,严辉译,见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15页。
2 [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第五版)》,常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
3 [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第五版)》,常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页。
1 [德]霍克海默、[德]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页。
1 [英]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工人阶级生活面貌》,李冠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55页。
2 [英]约翰·B.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994页。
3 [英]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第3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