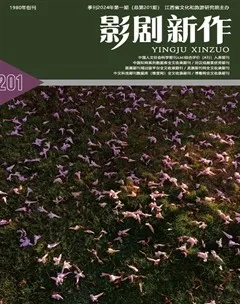经典戏剧的新阐释
陈杰
摘要:契诃夫的四幕剧《海鸥》充终,体现的是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分裂后对现代人造成的,在艺术作品中则是人的精神孤独感和人们之间的隔膜疏离感。通过舞台化地呈现戏剧场面失衡、人物彼此的理解、人物的自我封闭等状态,让观众意识到现代人面临的精神困境。
关键词:现代精神 情感潜流 状态性事件 戏剧性场面
北京人艺2023年版《海鸥》由濮存昕导演,青年演员李越饰演科斯佳,李小萌饰演妮娜,不仅演员阵容呈现出年轻化的特点,观众也趋向年轻化、青春化,剧场中有半数以上的观众都是青年人(包括高校学生、高中生等)。这种新的变化,特别是观众趋向年轻化的趋势,导演和演员通过舞台演出是怎么应对的?导演和演员是怎样向今天的青年人阐释契诃夫剧作的?本文尝试通过对北京人艺《海鸥》的分析,回答这两个问题。
一、舞台风格:冲突性的增强和喜剧性的呈现
《海鸥》为四幕喜剧,讲述了一个具有艺术革新精神的青年人特里波烈夫(科斯佳)为他倾慕的女孩妮娜创作了一部形式上具有创新意义的戏剧,演出失败后,科斯佳和妮娜各自走向了自己的艺术追求之路,最终科斯佳陷入了精神痛苦之中而自杀,妮娜被作家特林果林遗弃后艰难地走出了困境。契诃夫在艺术创新上和特烈波列夫具有相同的旨趣,即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和戏剧类型,《海鸥》的演出成功也证明了这种新的戏剧类型的建立。契诃夫开创的戏剧新形式,可以归结为戏剧场面生活化、去事件(情节)化、注重人物内在情绪的体现和内心潜流的开掘。
因为契诃夫的戏剧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体现,所以他用惯常的日常生活取代了曲折离奇的戏剧情节,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观众因过多关注戏剧情节而忽视对戏剧人物内心潜流的体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契诃夫的戏剧很少在舞台上直接体现冲突,但是北京人艺的这版《海鸥》有意地增加了外部冲突,比如,在第一幕将特里波烈夫创作的那段“人,狮子,鹰和鹧鸪……”的台词提前到了第一场戏,将剧本中本来是第一场戏的玛莎与麦德维坚科的对话后置,这样将两个戏剧场面置换,虽然增强了戏剧冲突和戏剧效果,也确立了该剧的主题,但是却减弱了剧作原有的抒情性色彩所营造出的一种诗意的气氛。第二幕结尾,北京人艺版《海鸥》将特里波烈夫开枪自杀设计为明场戏,这虽然制造了舞台事件,影响接下来戏剧情节的发展,但是原剧中之所以将特里波烈夫第一次开枪自杀设计成暗场戏,就是为了避免舞台上强烈的事件引发观众过多关注外部情节而忽略对人物心内世界、内在情绪的感受。特里波烈夫第一次开枪自杀未遂在原剧中是作为一个“状态性事件”出现的,即开枪自杀未遂这件事,具有戏剧事件的形态,但不具备戏剧事件的作用,因为,特里波烈夫这一举动,既没有改变他与其他人物的关系,也没有造成大的影响。因为这个事件没有改变妮娜依然深愛特里果林的事实,阿尔卡基娜和特里果林要离开庄园是因为特里波烈夫自杀未遂后提出决斗,从而捍卫他所追求的文艺新形式的理想。所以,北京人艺版《海鸥》将特里波烈夫开枪自杀变成明场戏呈现,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剧中人物的情绪,不利于体现人物内心的情感。
北京人艺版《海鸥》前两幕戏节奏感不明显,因为留白较少,原剧中的停顿基本都被取消,舞台上没有明显的停顿,那也意味着导演需要借助另外一种手段,来体现人物内心的情感潜流。喜剧性戏剧场面的处理即是体现人物内心情绪的重要方式之一。
契诃夫明确提出四幕剧《海鸥》是喜剧,但契诃夫创作的喜剧显然与古希腊以来的喜剧类型有显著区别。契诃夫不完全以讽刺性情节、幽默式语言、滑稽性挑逗、怪诞式逻辑等方式制造喜剧效果。正如他所创作的戏剧是一种崭新的戏剧类型,他所制造的喜剧效果也是这种新戏剧形式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在这种新类型的戏剧中充满了现代精神,这种现代精神在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剧创作中贯穿始终,体现的是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分裂后对现代人造成的痛苦,在艺术作品中则是人的精神孤独感和人们之间的隔膜疏离感。契诃夫的喜剧则是对这种现代人精神状态的一种舞台化呈现,让观众因戏剧场面失衡、人物彼此的不理解、人物的自我封闭等状态引起观众大笑的同时,也让观众意识到现代人面临的精神困境。在人艺版《海鸥》的舞台呈现上就在着力表现这些喜剧性的场面。比如,剧中的索林在倾听别人说话时会沉沉睡去发出打鼾声,这是戏剧场面失衡的一种体现:麦德维坚科问玛莎为什么总穿黑衣裳,玛莎的回答和麦德维坚科的理解南辕北辙,这是人物因不理解对方而造成彼此孤立隔绝,从而造成了对话的错位:从头至尾,管家沙姆拉耶夫都在高谈多年以前莫斯科歌剧院演员的事迹,可是大家没有一个人接话,他看似在向众人诉说,其实和自言自语没有区别,这可以理解为人物自我封闭状态的一种舞台化展现。
二、人物形象:海鸥的象征意味
《海鸥》创作于新旧世纪之交的19世纪末,契诃夫在剧中并没有拘泥于当时的现实主义规范,他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极大地扩充了现实主义戏剧的表现范围,在剧作中他把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等流派巧妙地与现实主义结合为一体。《海鸥》在创作上也打破了契诃夫之前创作的“只有一个主角”的戏剧(如《伊凡诺夫》《林妖》),进入到了有多主角的剧作时期(如《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文学性的增强和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和含蓄性也是契诃夫戏剧的重要特征。契诃夫戏剧的这些特征,也给导演和演员阐释剧作,在舞台上表现剧中人物增加了困难。北京人艺版《海鸥》在对剧作象征意象的处理及人物阐释上颇具特色。
在对剧作象征意象的处理上,北京人艺版《海鸥》主要借助凸显台词、舞台布景、道具服装等手段来完成。大幕打开,特里波烈夫便站到自己搭建的舞台上朗诵他所创作的剧本中的那段台词,妮娜也一再重复朗诵以下这段台词:
人,狮子,鹰和鹧鸪,长着犄角的鹿,鹅,蜘蛛,居住在水中的无言的鱼,海盘车,和一切肉眼所看不见的生灵——总之,一切生命,一切,一切,都在完成它们凄惨的变化历程之后绝迹了……到现在,大地已经有千万年不再负荷着任何一个活的东西了,可怜的月亮徒然点着它的明灯。草地上,清晨不再扬起鹭鸶的长鸣,菩提树里再也听不见小金虫的低吟了。只有寒冷、空虚、凄清。
[停顿。
所有生灵的肉体都已经化成了尘埃:都已经被那个永恒的物质力量变成了石头、水和浮云:他们的灵魂,都融合在一起,化成了一个。这个宇宙的灵魂,就是我……我啊……我觉得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和莎士比亚,拿破仑和最后一只蚂蟥的灵魂,都集中在我的身上。人类的理性和禽兽的本能,在我的身上结为一体了。我记得一切,一切,一切,这些生灵的每一个生命都重新在我身上活着。
对这段台词的重复构成了一种复调意义,当这段台词被在舞台上不断重复时,它的象征意义便会自然浮现在观众的脑海中,让观众理解了特里波烈夫对一种新的艺术理想的追求。这版《海鸥》舞台布景具有象征意味。舞台布景是借助现代多媒体投影出的蔚蓝水塘,而不是一个大湖,一眼便能见出湖的边际;借助两个虬曲着的古老而干枯的树木搭建起来的临时舞台,都显露出了剧中的象征色彩同时也暗含着特里波烈夫的不幸。舞台道具和人物服装上也具有象征意味,舞台上堆积着的旅行箱,它代表着人物的不拘与流动,同时也意味着特里波烈夫和妮娜精神上的放逐与追求;那只被特里波烈夫开枪打死的海鸥则象征了人物的命运:妮娜的服装前三幕都是白色裤子和白色连衣裙,最后一幕她出现时,已是一个饱尝辛酸、历经磨难的人,她穿着红色裙子、黑色披风和白色外套。是啊,妮娜依然纯洁纯净,但她此刻的洁净是她历经苦难折磨后淬炼出来的,她已尝味过红色情爱的浓烈,黑色幽暗的屈辱。
在剧作人物形象阐释上,北京人艺版《海鸥》也颇具特色。特里波烈夫是一个理想化的角色,他身上有哈姆莱特的忧郁气质,就像特里波烈夫所说的那样“哈姆莱特害怕思考,我害怕做梦”。哈姆莱特的痛苦源于他的深思,而特里波烈夫的痛苦则源于他的艺术理想,他认为“表现生活,不应该按照着生活的样子,也不该照着你觉得它应该有的样子,而应当照着它在我们梦想中的那个样子”。生活在梦想中的样子,是特里波烈夫的艺术追求,为此他探索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不惜否定与诋毁以母亲阿尔卡基娜和作家特里果林(阿尔卡基娜的情夫)为代表的庸俗。也可以说,特里波烈夫的痛苦,是一种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所产生的精神痛苦,这种痛苦源于他无法忍受周围人的庸俗生活。这也是理解玛莎狂热地追求特里波烈夫,最终还是不被接受的关键,瑪莎有对爱情的理想追求,但是她不理解特里波烈夫的精神追求,她本身虽然可爱但距离特里波烈夫的精神理想还太遥远。这次北京人艺版《海鸥》里特里波烈夫的扮演者李越,能呈现出人物狂烈的一面,但忧郁感和内心的情感节奏没能有力地表现出来,使人物略显漂浮,若能沉浸到人物的情绪潜流中,把握人物的情感基调,相信演员能创造出一个更加鲜活的特里波烈夫。
妮娜则是一个天真纯洁的人,一心要做女演员的狂热追求,让她对艺术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她崇拜艺术创作这一神圣的活动,并由此爱上了作家特里果林。跟随特里果林的两年里,她在生活上和精神上受到了双重磨难,她从痛苦和屈辱中重新振作起来,领悟到了艺术和生命的真谛。在第四幕即将结束时,她对特里波烈夫讲“在我们这种职业里一不论是在舞台上演戏,或者是写作——主要不是光荣,也不是名声,也不是我所梦想过的那些东西,而是要有耐心。要懂得背起十字架来,要有信心。我有信心,所以我就不那么痛苦了,而每当我一想到我的使命,我就不再害怕生活了”。此刻的妮娜不再为虚名和荣誉而做演员,她在为一种坚定的内心信念而演出,这种坚定信念正是支撑她活下去的精神力量。妮娜的这种转变,造成了她在前三幕和第四幕中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性格状态,如何体现出入物性格上的变化是塑造人物形象成功的关键,同时这也为演员构成了不小的挑战。同时妮娜这一形象也充满了象征意味,她就是那只翱翔的海鸥,由天真纯洁狂热追求艺术到认清现状继续坚守,仍然纯净如初。北京人艺版《海鸥》中由李小萌饰演的妮娜,比较成功地塑造了这一人物形象,特别是第四幕,李小萌把妮娜内心中的那种伟大而坚强的信念,受难后的觉悟以及对特林果林的深爱等复杂的情感,都层次清晰地在舞台上展现了出来。美中不足之处是第一幕妮娜出场时,舞台上妮娜的性格奔放有余而内敛不足,不太符合剧作中妮娜刚出场时的性格。
三、舞台创新:由唯美象征到空荡舞台
《海鸥》不仅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现代性,在主题思想上也具有现代性,这就是这部戏常演常新,适合不同时代、不同地域观众观看的重要原因。北京人艺版《海鸥》在舞台上也有革新,一为在舞台上增加了乐队:二为变唯美象征的舞台布景为空荡裸露的舞台。
北京人艺这版《海鸥》在舞台一侧增设了乐队,根据剧中人物、情节、场面的需要而进行现场伴奏。音乐最能表现人物内心微妙复杂的情感和情绪的变化,使用乐队是可以增强对契诃夫剧作中人物内心情感潜流的音乐展现,使人物的内在情绪变成有声的音乐形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舞台创新。其实,契诃夫的戏剧和小说创作都侧重人物情感的含蓄深沉,同时在创作中他也注重音乐性和抒情性的运用。早在1888年,契诃夫28岁时,他便创作了中篇小说《草原》,侧重体现“人与自然”两种力量,大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看到小说后赞誉“《草原》也许是俄国文学中最有音乐感的一部小说”。这次,北京人艺舞台上将《海鸥》剧作中最能揭示人物内心情感潜流的停顿取消了,而契诃夫剧作中最有力量的部分便是隐藏在停顿这一外部静止动作背后的人物内心情绪,怎么展现这一有力的情绪?把人物情绪音乐化,以流淌的音符取代剧作中的停顿,把人物复杂微妙的内心情绪用音乐形象直观体现出来,这未尝不是这版《海鸥》的一个大胆而勇敢的革新。
按照斯氏体系演出的戏剧本来就是幻觉戏剧,需要在第四堵墙内的规定情境中演出。但是,北京人艺这版《海鸥》在戏剧结尾时有意打破了舞台幻觉,原本靠电子投影在舞台幕布上呈现的蔚蓝湖水、舞台上的两棵古老枯树和临时搭建的戏台,在戏剧即将结束时,随着特里波烈夫站在湖岸边朝向湖水自杀的枪声,枯树和戏台倒塌,舞台幕布轰然陨落裸露出纵深的后台,湖水和梦想的戏台统统消失,一幅残忍的真实图景呈现在观众面前。这也许是特里波烈夫抗拒的庸俗世界,也许是他不敢面对的世界,这同时也是妮娜在其中觉醒后变得坚强的世界,更是我们每个人消除美好幻梦后要面对的真实世界。
舞台幕布的突然陨落,让观众看清了失去梦想和幻觉后的世界真相。我们是庸俗地生活在其中还是像特里波烈夫说的那样“照着它(生活)在我们梦想中的那个样子”去创造?这个问题叩问着剧场中的每一个心灵,也许这就是北京人艺版《海鸥》给观众特别是给青年观众最有价值的启迪吧!
注释:
1896年10月17日夜,一个孤独而失落的身影独自踟蹰在寒冷的彼得堡街头,他忘记了寒冷,因为此刻他的内心盛满了更加酷烈的严寒和极度的失落,他精神沮丧到了极致,这种失落情绪裹挟着他,急于想逃离的想法压倒了一切,他不顾一切地乘坐早晨第一班火车逃离了彼得堡,甚至把随身的行李都遗落在了火车上。这个仓皇逃离的人就是契诃夫,这年他36岁,创作了世界现代戏剧史上伟大的、富于革新精神的剧作——《海鸥》。首演失败给契诃夫带来了极大的打击,以至于使他一度认为自己不适合创作戏剧,就像不久前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奉劝他的一样“写小说你是个高手,写剧本则完全是外行”。就在契诃夫内心陷入深深的矛盾与纠结的时刻,俄罗斯剧坛上著名的舞台艺术革新家涅米罗维奇一丹钦柯发现了《海鸥》的价值,在丹钦柯一再的劝说下契诃夫才勉强同意重排《海鸥》,后经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钦柯的全新阐释,借助新的导演手法营造出了契诃夫戏剧中的情绪潜流,才使演出大获成功。《海鸥》在莫斯科舞台上的演出成功,不仅宣告了一个崭新的戏剧类型的诞生而且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创立新的演剧体系(斯氏体系)的重要标志之一。
责任编辑:伍文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