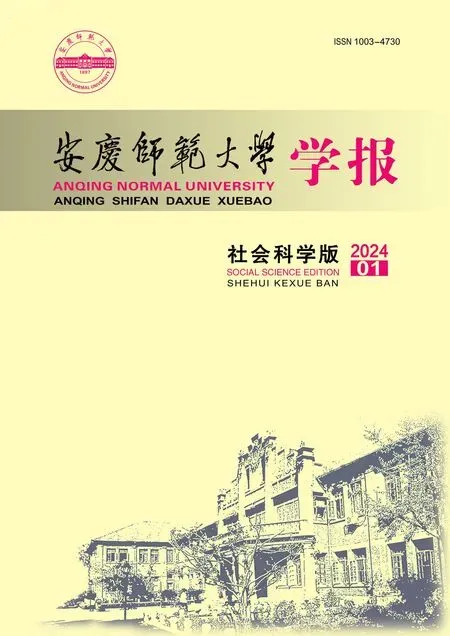由“合”趋“离”:小学和赋关系的学理问题
王飞阳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 550001)
论小学和赋,最早当属扬雄,将“作赋”比诸“雕虫篆刻”。而至晚清,章太炎提出“小学亡而赋不作”[1]129,足见小学和赋关系密切。时贤方家于此鲜有论述,殊为遗憾。小学和赋的关系,要在学问发端,识字为本①赋主学问,是易师闻晓的观点,其《汉赋为“学”论》中认为:汉赋学问的表现在于学的流行,词章的学养,博物的取资、字词的僻难。其中亦涉及小学和赋的论述。本文即本易师观点,论小学首先注目学问和识字。。中国文学成于汉字的运用,辞藻乃是其根基[2]。而赋家用字之富、词藻特丽,最见学问。小学和赋,洵息息相关,这于汉赋最为彰显,其突出表现在用字僻难、同旁联贯、殊方异物。自晋而下,用字率从简易,小赋和赋由“合”趋“离”。中唐以降,小学衰落,赋体式微,二者愈呈背离。所谓“小学亡而赋不作”,实际宣告小学和赋彻底分途。“五四”以还,文学和语言渐而分道扬镳。这背后的学理问题,令人寻思。论赋和小学的关系,必须本诸创作,方可深切体认其中的内在理路。
一、学问发端:一子之学和识字为本
赋和小学的关系,首在学问相关。赋主学问,章学诚谓赋为“一子之学”,最为探本。其云:
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虽其文逐声韵,旨存比兴,而深探本源,实能自成一子之学,与夫专门之书,初无差别[3]。章氏所言,除辨别赋家源流,更强调赋家重学。无论《庄》《列》《战国策》,还是《储说》《吕览》,赋家必须熟读,多温原典,以滋学养。而比之“专门之书”,实确认赋为“专门之学”。谢榛亦云:
汉人作赋,必读万卷书,以养胸次……又必精于六书,识所从来,自能作用”[4]。读万卷书,可见学问之大,而所有的学问必始于识字,“精于六书,识所从来”,赋家唯精通小学,方可“自能作用”。汉赋四大家,皆通小学,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皆著有字书,而张衡亦有《周官训诂》,赋家学问之深,首见于小学功夫。“小学”本初之义,是关于识字的学问。古人以识字多、识见广为博学之征,而赋体名物之多、难字之富,最显学问之大。唯多识字,才可博识名物,此为唯一途径。因此赋家博物,究在识字之多;赋资博物,则是字类之富;赋称为“学”,也以文字之学为主[2]。
扬雄悔赋,比之“雕虫篆刻”,而言“壮夫不为”。长期以来,执着于“劝百讽一”的视角,而忽视扬雄所指“雕虫篆刻”之本义。近有学者揭示“雕虫篆刻”实指小学,进而论述小学和赋的关系,认为扬雄“三步通经”,由童子“小学”之学,渐入辞章之文,后根柢在弘道之儒业[5],具有启发性。“雕虫篆刻”,是为八书之体,汪荣宝疏云:
虫书、刻符,尤八书中织巧难工之体,此皆学僮所有事,故曰“童子雕虫篆刻”[6]。
扬雄精通小学,将赋比之“雕虫篆刻”逻辑合理。当然扬雄立志弘道,以辞章为下,小学又次之,但将赋与书体比拟,洵为小学和赋关系密切的体认,而这体现在赋体创作最考究用字。“夫文字者,篇章之始也”[7],汉字为中国文学的根基,其独体单音的特质,加上音形义、声韵调的变化,予以造字组词种种可能,非其它语言所能项背。而较诸其他文体,诗主性情,不宜以文字、学问为诗;词曲通俗,实为白话文学,无所谓学问多寡。唯赋主学,要在铺陈,故“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赋中博物取资,用字僻难,诚为知识的类聚,学问的展示。
如《子虚赋》写山:
其山则盘纡茀郁,隆崇嵂崒,岑崟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土则……其石则……其东则……其南则……其高燥则生葴菥苞荔,薛莎青薠。其卑湿则生藏莨蒹葭,东蔷雕胡,莲藕觚卢、菴闾轩于,众物居之,不可胜图。其西则……其中则……其北则……其上则有鹓雏孔鸾,腾远射干;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8]119-120。
各类名物,应有尽有。而就某物铺陈,亦搜罗殆尽。如写土:
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坿,锡碧金银[8]119。
共计10种;写石:
则赤玉玫瑰,琳琘昆吾,瑊玏玄厉,碝石斌硖[8]119-120。
共计8种。而《上林赋》写猴:
玄猨素雌,蜼玃飞鸓,蛭蜩蠼猱,獑胡豰蛫,栖息乎其间[8]126。
共计10 种。一物即一字,名物铺陈实为字类的排比。赋家不通于小学,洵难操觚。除铺陈名物,赋家用字往往临文创制,而显僻难。如《上林赋》形容水势:
沸乎暴怒,汹涌澎湃。滭弗宓汩,逼侧泌瀄,横流逆折,转腾潎冽,滂濞沆溉。穹隆云桡,宛潬胶盭。逾波趋浥,涖涖下濑。批岩冲拥,奔扬滞沛。临坻注壑,瀺灂霣坠,沈沈隐隐,砰磅訇礚,潏潏淈淈,湁潗鼎沸[8]123-124。
这些语词,罕见典籍,仅“瀺灂”出自《高唐赋》,其余或为异形,或为转写,或为自创,系于声韵,本于音义,故多为联绵①关于赋中联绵字的分析,参看易闻晓《汉赋为“学”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辞赋联绵字的语用考述》,《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凡此,都是赋家精于小学的明证。而“搜寻适当字以就四言,才是相如‘含笔腐毫’的艰辛所在”[9]。
汉代极重字学:
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10]1720。
而以赋见赏的词章之士,识字则愈过之,四大家且不说,汉代赋家多兼为史家②参看王焕然《汉代赋家与史家关系论略》,《河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学问博,识字广,自无异疑。
辞赋创作实际上就是字词的运用,汉大赋的繁复名物、繁难僻字、大量异体字,来源于古、今及六国文字的复杂性,未正复字的存在、“书同文”的不彻底,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的遗存,反而成为赋家选字、堆砌名物、排比形容的文字渊薮[2]。
而正因“字无常检”,故汉赋中大量使用“玮字”,简宗梧就汉赋“玮字”问题,从多方面探讨,举列异文、剖析成因,详矣备矣③参看简宗梧《汉赋源流与价值之商榷》,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年版,第47-49页。。而谙熟各类文字,无疑滋养了赋家的学识和胸襟。汉代赋家精于小学,为历代所公认。董正功云:
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子云作《训纂》,皆欲同文也。相如、子云能辞赋,本精小学[11]。
阮元云:
古人古文,小学与辞赋同源共流。汉之相如、子云,无不深通古文雅驯[12]。
凡此,皆是强调赋和小学关系密切,唯以识字为本,精通小学,方能为赋之方家。至于王鸣盛所云:
《凡将》字既有出于《仓颉》之外,则知相如本赋家,性尚浮夸,必不精当[13]。
则实不知赋家用字旨在追新求确、炫耀学问,不然若按字书填砌,作赋又有何难:
案头多置类书,掇拾填砌,便可成章,无惑乎来俳优之讥、雕虫之诮也[14]。
洪亮吉云:
汉文人无不识字,司马相如作《凡将篇》……隋唐以来,即学者亦不甚识字[15]。
可见汉大赋之所以无法逾越,或非后世赋家才不可及,而是学不逮也。
赋和小学的关系,以学问发端,落实用字。汉代赋家通于小学,作赋精于用字,最能彰显二者关系紧密。自晋而下,用字率从简易,小学和赋由“合”趋“离”。中唐以降,小学衰落,赋体式微,二者愈呈背离。清代小学虽一度复兴,却无法弥合裂缝,终至于“小学亡而赋不作”。
二、双向背离:赋体式微和小学衰落
逮至中唐,赋和小学都发生重要转变。汉代献赋频仍,然非真正意义上的“考赋”,考赋源自唐代,一般以高宗麟德二年(665)试“寒梧栖凤赋”为端。但及中唐,考赋制度才正式确立,所谓“不试诗赋之时,专攻律赋者少。大历、贞元之际,风气渐开。至大和八年(834),杂文专用诗赋,而专门名家之学樊然竞出矣。”[16]孙梅所云:
自唐迄宋,以赋造士,创为律赋[17]。
此说并不确切,其实自唐迄清,都是以赋取士,宋代虽曾罢赋,但考赋仍是主流。明代科举虽以八股,但亦有试赋之举,其中制科、礼部、吏部、庶吉士、翰林院馆课均试赋①参看孙福轩《明代科举试赋考》,《科举学论丛》,2010年第1辑。,同样以赋造士。可见从中唐开始,考赋成为制度,而赋变为仕进之具。士子趋之若鹜,无非是为功名,视赋多存鄙夷,一旦登第,再不复为。强至《送邵秀才序》云:
予之于赋,岂好为而求其能且工哉,偶作而偶能尔。始用此进取,既得之,方舍而专六经之微,钩圣言之深,发而为文章,行而为事业,所谓赋者,乌复置吾齿牙哉[18]?
赋之于读书人,无法跟六经圣言相比,仅为利禄津梁,一旦进取,则弃如敝屣。在执于经义的历史进程中,赋体价值慢慢走向消解,至律赋兴起,“赋亡”之说出现。毛奇龄所云:
至隋唐取士,改诗为律,亦改赋为律,而赋亡矣。登高大夫,降之为学僮摹律之具,算事比句,范声而印字,襞其词而画其韵,既无忼慨独往之能,而称名取类,就言词以达志气,亦复掩卷殆尽[19]。
此论最为切痛。虽清人表现出明显的尊体意识②参看拙作《清代赋论的赋体书写》,《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却无法挽救赋体衰亡之命运,诚如章太炎所言:
承千年之绝业,欲以一朝复之,固难能也[1]129。
但作赋却愈演愈盛,清人自诩:
国家昌明古学,作者嗣兴,钜制鸿篇,包唐轹宋,律赋于是乎称绝盛[20]。恐怕只能从数量着眼。对于帝王而言,试赋是一种政治手段,而对士子来说,作赋是为稻粱谋,各取所需,疯狂作赋,从而营造“明盛实衰”的假象。
当赋成为仕进之具,习之愈久,遂为程式。律赋限以八韵,犹如八股之文,多以经义为题,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而各种指导之书,亦因之兴起,学子只需按部就班、依样画葫,又怎会顾及学养、留心小学。所谓:
《说文》训诂之学,自中唐以后,人多不讲。宋以后,说经尤不明故训[21]。
确切指出小学衰落的事实。小学长期为经学附庸,自五经立于学官,经学成为仕进通途,控制经学的解释权,实则掌握政治话语,而小学是通经之具,故小学昌盛。当小学和政治失去联系,仕进之途转而为诗赋文章,小学注定走向衰落。同时科举取士,规定:
进士考试必用正字,不能用俗体[22]123。
也加速了小学衰落的进程。清代是传统小学光辉终结的时代[22]14,曾使小学一度复兴。然而清代儒者致力小学,多为现实所迫,埋首故纸堆是为学术之争,而钻研重心在于文献辑佚、考证及重建经学师承源流,似乎重回经学传统,所谓:
今日言小学者,皆似以此为经学之附属品[23]13-14。
清代小学大师无暇顾及文学,多羞于作赋,故小学虽在清代复兴,但赋体衰亡仍在所难免。章太炎所云“小学亡而赋不作”,不仅针对中唐以来小学衰落的事实,还在于他认为清代“小学”并非真正的“小学”,其云:
此种学问,《汉·艺文志》附入六艺。今日言小学者,皆似以此为经学之附属品,实则小学之用,非专以通经而已。周、秦诸子,《史记》《汉书》之属,皆多古言古字,非知小学者,必不能读。若欲专求文学,更非小学不可。汉时相如、子云,唐时韩、柳,皆通小学,故其文字闳深渊雅,迥非后人所及。中间东汉、六朝诸文学家,亦无不通小学者,一披《文选》便可略知梗概。然自中唐以后,小学渐衰。韩退之言:“凡作文字,宜略识字。”可知当日文人已多不识字者。自宋以来,欧、曾、王、苏诸家,皆于此事茫然无省……自元以下,此风亦绝。明时,七子宗法盛唐,徒欲学其风骨,不知温醇尔雅之风,断非通俗常言所能支配。清时王、朱二子,则又运用僻典为能事,造字遣辞,不能由己,更佣猥不足道矣。要之,文辞之本,在乎文字,未有不识字而能为文者。加以不明训诂,则无以理解古书,胸中积理,自尔匮乏,文辞何由深厚[23]13-14?
在章太炎看来,小学和文学息息相关。善为文学者,未有不精于小学。此论之于诗词,或不适用,但之于赋却极有见地。赋主学问,赋家须多温习经典及诸子百家,以滋学养,否则“胸中积理,自尔匮乏”,文辞必然浅显,焉能显露赋家广阔胸襟!而唯谙熟小学,故能识字众多,知所从来,故造字遣辞,才能由己,方能闳深渊雅。此扬、马、韩、柳过人之处,而“近世徒有张惠言,区区修补《黄山》诸赋,虽未至,庶几李、杜之伦”[1]129,安能项背!“小学亡而赋不作”,应作如是观。反言之,“赋亡而小学不作”,亦可融通。小学和赋,洵形影相附,彼此难分。然自中唐以降,赋体式微,小学不振,二者渐趋背离,殊为可叹。
小学衰落,而志书、类书却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成为文人“案前宝鉴”,遂使作赋无难。袁枚说:
今志书、类书,美矣、备矣,使班、左生于今日,再作此赋,不过翻撷数日,立可成篇[24]。
因作赋不复呕心沥血,以赋显才则大打折扣,加速消解赋体的价值。而因字书、类书的方便,也使士子无暇钻研小学,如王楙《古文奇字》所言:
后世大夫读书作文,趣了目前,他不甚求解,所谓古字之学,漫不复得[25]38。
这种双向的背离,自中唐一直迄至清季。章太炎提出“小学亡而赋不作”,其实是“雕虫篆刻”的变向回归,只不过跳脱了经学的藩篱,而将视角立足革新致用。
三、变向回归:通经讽喻和革新致用
小学和赋长期背离,却在强调“有用”的观念上于清代实现变向回归。汉儒将先秦经典列为儒家专书,依经立义,旨在美刺讽喻。由于六义之一为赋,故汉儒视赋为“古诗之流”,其实赋体和《诗》体并无本质关联。
《诗》的赋比兴作为表现手法固与风雅颂的内容相表里,《诗》之“赋”不离风颂,只是一种表现手法[26],而非赋体。赋体源自楚辞,屈骚抒情漫衍,流为汉代骚体赋,而宋玉去情主物,衍为汉大赋[27]。至于“赋”的称名由来,蒋晓光指出:
赋体文学的立名源于祭祀过程中的“献赋”活动[28],也非六义之“赋”。只是汉儒执持经义,将骚、赋之祖同归于《诗》,而着眼在于美刺讽喻。扬雄作为学者型文人,自然立足于经,视小学为通经之具,而视赋为讽喻手段。赋体价值,全凭经义衡之。赋之有用与否,全系之讽喻有无。“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之说,虽不够客观,然在当时却振聋发聩。
汉代虽然小学昌盛,但由于和政治挂钩,故门户之见颇重,师法、家法谨严,不能越雷池一步,以致解经繁琐万言,或失之谶纬荒诞,扬雄于此深感不满。其撰《训纂》《方言》,旨在纠正当时的偏颇。申小龙认为《方言》:
推动了汉代小学研究的范式革命,对当时儒学经学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弊端起到纠偏与导向的作用[29]。
“雕虫篆刻”其实是“字本位”,唯有精通八体方言,扬雄才能“博极群书,于小学奇字无不通”[30]358,作赋才能得心应手。如《蜀都赋》所写“山”类,山字旁异字逾三十个,均罕见典籍,这是善用古字、奇字的明证。而“所谓奇字者,古文之变体者也”[25]38,然非精于小学,焉能转换自如?虽然扬雄作赋有炫学一面,但旨在讽喻。《汉书·扬雄传》载:
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还,上《河东赋》以劝……其十二月羽猎,雄从……故聊因《校猎赋》以风……是时,农民不得收敛。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10]3522-3557。
作赋因由,无一不是经历实事而旨在讽喻。至于黄承吉质疑子云:
晚年作序乃自讬于讽谏,是其巧于作伪也[31],显然不顾赋文,实属偏见。扬雄作赋,用意在讽。这较之相如凭虚夸谈,无疑呈现征实的转向[32]。但由于赋“立体在颂”,要在铺陈,以颂体追求讽喻之旨,唯致“讽颂同构”的两难境地[33]。扬雄因赋讽效果微弱,故决不复为,可见小学是通经之具,讽喻才是立言之旨。扬雄前期拟赋,后期转而治经,实际是由赋家“尚文”转向儒家“言道”①参看安生《诠赋与宗经:扬雄悔赋批评下的“三步通经”思想》,《古代文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2辑。,其“壮夫不为”之说对后世产生久远的影响。
中唐以降,经学不振,小学式微,但“赋者古诗之流”的思维却根深蒂固,以经义衡赋的藩篱始终没有破除。对赋的评价高低,往往系之于讽颂的多寡,尤以讽喻为重。赋之有用与否,则决于讽喻有无,扬雄视赋为“雕虫篆刻”,而悔“壮夫不为”,实为肇端。但当以赋取士成为制度,士子作赋唯有歌功颂德,讽喻殆尽。而当考赋成为仕进之具和政治手段,那赋的价值也仅限于此。逮至清季,经世之风兴起,论赋跳脱经学的束缚,不执讽喻,多主致用。章太炎提出“小学亡而赋不作”,首在反思小学和文学的界定。其论小学:
非专为通经之学,而为一切学问之单位之学[23]15。
视小学为所有学问的根本。章氏学识渊博,而学养的根基也在小学。当然精通小学,不是为学问而学问,而是旨在致用,所谓:
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岂专引笔画篆,缴绕文字而已[1]6。
在此之前,论小学多注目于学问、解经、用字,而章氏将小学提升到致用的高度,较之许慎所言“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34],犹如隔代响应,但章氏跳脱了经学视角,打破小学为经学附庸的成见。扬雄撰《训纂》《方言》,是为纠偏,而章太炎立足革新,实现超越。
关于“文学”的思考,章太炎十分独特。其云:
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1]73。
以文字为文之本,而旨在挑战道咸以降的声气说(以声音为文之本),亦反对阮元的文言说(以骈偶、用韵为文之本),极大地扩大了“文学”的边界,从而将考证文字纳入文学的领域,这当然离不开自身小学的修为①参看胡琦《言文之间:汉宋之争与清中后期的文章声气说》,《文学遗产》,2022年第1期。。而章太炎视赋为“有韵的句读文”,又云:
文辞之繁,赋之末流尔也[1]128。
而将疏证类推为上乘,盖其:
文皆质实而远浮华,词尚直截而无蕴藉[1]128。
显然是以文字为本,以致用为纲。章氏论文学不主性情,所谓“论文学者,不得以兴会神旨为上”,而“气乎德乎,亦末务而已矣”[1]81,诚有失偏颇。而其认为“赋之亡盖先于诗”[1]129,将隋之后的赋一概抹杀,也是出自致用之旨。“小学亡而赋不作”的考量,不唯学问、文字,更为重要的在于致用。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压迫,章太炎坚守文化自信,以自己淹贯的学养探索中国文化革新之路,即:
以文字为基础,由文献、文学而上升到文化,最终建构起了一套以“文”为中心的革命的文明论体系[35]。
这份壮志,殊为可敬!章太炎作赋不多,而其《哀山东赋》紧扣实事,记录列强欺压百姓的惨状,抒发不平之气,然相信天道轮回,佑我中华。其骨子里的义愤填膺和民族自信,洵为动人,亦属实有用。
汉时扬雄亦主“革新”,处处与前贤争胜,然囿于时代,困于经学,所论不出通经讽喻之藩篱。赋之有用与否,在扬雄看来唯在讽喻多寡,而至章太炎则以致用为标尺,无论是讽喻还是致用,均是强调赋须有用,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变向回归。但本质上,小学和赋已然彻底分离。而在今天文学和语言又分道扬镳,这背后的学理问题令人寻思。
四、学理反思:本诸创作和文学本位
汉人作赋,赋和小学紧密相关,突出表现在学问的展示、博物的取资、字词的繁难。然自中唐以降,小学和赋渐趋分离,虽然执持“有用”的观念,小学和赋在清代实现变向回归,但终究还是逃不过“小学亡而赋不作”的命运。时至今日,文学和语言又呈分离之势,各有壁垒,难以融合。这背后的学理问题,需要说明。
小学在汉代几为“显学”,乃因现实需要。“书同文”不彻底,八体互见,汉廷以识字多为吏,乃出自统一规范的动机。而古今文之争甚嚣尘上,古文家的政治诉求直接推动了小学的繁荣②参看杨兴华《古文学家的政治追求与汉代“小学”的繁荣》,《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通经可任博士,小学为通经之具,故太学生趋之若鹜,甚而逾万人,足见小学在汉代的普及性。然时移世易,魏晋六朝通经者多为世家大族,寒门弟子难以染指。中唐而后,科举定型,以诗赋取士,通经者廖若无几,小学自然鲜有问津。及至清代,小学虽然复兴,但称为大家者亦不过段、王、钱、戴,小学渐成专门之学。而今日之语言学,几为“独门绝学”,旁人难睹秘笈。小学从一时“显学”变成独门“绝学”,主因在于失去了现实价值。而在很多人眼中,小学成了“无用之物”。章太炎提出“小学为一切学问之单位之学”,想必也是欲挽狂澜于既倒。然“五四”以来,传统小学已然成为专门人士的“谋生手艺”,传诸子弟,亦多茫然,遑论他人。当然,客观言之,不通小学就无学问?也不尽然。只是就赋而言,洵需小学滋养,可叹的是当小学衰落,赋中本见学问的难僻之字竟成了嘲讽对象,诚如刘勰所云:
自晋来用字,率从简易,时并习易,人谁取难?今一字诡异,则群句震惊,三人弗识,则将成字妖矣。后世所同晓者,虽难斯易,时所共废,虽易斯难,趣舍之间,不可不察[36]。
后人不学,全然不顾汉时君臣“素名古字之学”[25]38的事实。而随着字书、类书的涌现,作赋妄自堆砌:
仿效汉人赋颂,繁声僻字,号为复古,曾无才力气势以驱使之,有若附赘悬疣、施胶漆于深衣之上,但觉其不类耳[37]。
犹如今日识字不多,亦可为文,无病呻吟。较之扬雄“一物不知,君子所耻”[30]357,岂啻天渊!
小学衰落的同时,赋体文学也呈消亡之势。“赋亡”之说始于明人,明人所论是针对唐赋,持论者视律赋为科举程文,毫无价值。当然也有反对之声,如王文禄云:
李太白《大猎》《明堂》、杨炯《浑天仪》、李庚《两都》、杜甫《三大礼》、李华《含元殿》、柳宗元《阂生卢》、《肇海潮》、孙樵《出蜀》,岂曰无赋[38]。
其实,明人有关“唐无赋”之争是诞育于复古与反复古之时代氛围和文化心理的[39],表现出种种矛盾和挣扎,而歧见的焦点在于是否将律赋等于唐赋。虽看法不同,然均注目经义,并没有道出“赋亡”的本质。赋体最根本的特质在于铺陈,一旦赋没有了铺陈,就是“赋亡”的开始。
魏晋南朝乃至唐代律赋,赋题愈小,篇幅益短,牵合骈偶,巧构属对,致使语势顿断,愈减铺陈,体物为多,主于描写,略于名物,寓情托物,辑比事类,愈近诗境[40]。
“赋亡”之征,不在经义有无,而在铺陈多寡。本诸体制,“赋亡”之论才显融通。当然从数量而言,赋并没有亡,相反愈演愈盛。今日作赋之风炽热,如党圣元所言:
当代辞赋创作的“合体”情况,实际上并不多见,不用说根本在于读书少,学识不足支持辞赋的创作,铺天盖地的是当代白话俗语或标语口号的不烦罗列,其中无物,苍白空洞,难以符合赋体铺陈的要求[41]。
赋作虽夥,然赋“名存实亡”。当赋和小学均呈式微,若想紧密相系,显然再无可能。
小学和赋关系的失落,还在于“文学”观念的错位。在整个中国古代,其实没有“纯文学”的观念,而所谓“文学”离不开“原道”,涵括经史子集①参看李建中《中国文学观念的兼性特征》,《湖北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而“文学”立足点在于切实有用。扬雄、章太炎论赋绝非以“纯文学”的标准,扬雄视赋为词章,旨在弘道,用以讽喻。“赋者古诗之流”,将赋纳入经学视角,是汉儒的普遍认知,显然不是以“文学”视赋。尽管汉赋辞藻华丽,铺张扬厉,但若说是“文学自觉”的起点②龚克昌先生早就提出“文学自觉”的起点应在司马相如的时代,参看《论汉赋》,《文史哲》,1981年第1期;《汉赋——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文史哲》,1988年第5期。,仍有商榷的余地。至于章太炎,将“竹帛文字”皆视为文学,而赋仅“文辞末流”,可见“小学亡而赋不作”的关键点在于小学,小学是章氏学问的根基,故其将小学归于文学之中,以彰小学。只是章氏的“文学”观念是错位的,论小学和赋并非真正落到创作之中,只是强调学问和致用。而今天的“文学”观念来自西方,注重虚构、唯美、抒情和创造,虽云“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落实到具体创作,语言是语言,文学是文学,西方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在关照”往往水火不容,遂使语言和文学分为两途。其实,西方的语言完全不符汉字的特性,西方的文学也非中国传统的文学,双向的错位导致文学研究偏离创作。就赋而言,赋不主情,而是主物③赋是“主物”的文学,亦是易师的观点。参看其《主物的文学:赋体分别与题材交互》,《中山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故在西方“文学”归类中找不到应有的位置,故论赋多侧重于外部观照,而非立足文学本身。
忽视文学本位,自然会漠视创作。中国文学成于汉字的运用,辞藻乃是根基。而赋辞藻特丽,最见“字本位”的语用考量。赋体的形成和发展当然离不开礼制,而赋中的物事往往也有“象喻”,从外部考察赋无疑是必须的。但只有本诸创作,立足“字本位”,赋学研究才能探本。易师多次强调:
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语用是为根本。赋学研究必当具有语用的维度,由于汉字之于汉语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大赋创作的语用就以用字为本。“字本位”的语用研究不唯通合文学和语言的领域,而且表现为深细的文本考辨,具有实学的品格[9]。
而就赋和小学的关系来说,最为根本的即为学问发端和识字为本,不然汉赋中的“玮字”从何而来?若仅从“有用”的观念介入,那赋和小学的讨论只能游离在外部。文学研究必须回归文学本位,而且不是以“西方文学”为本位,而是以“中国文学”为本位,落实到汉字本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绝不能“崇洋媚外”,匍匐在西方文学的脚下。章太炎的文学观念虽然存在偏颇,但其背后的文化自信却值得尊敬和效仿。若研究中国文学者鄙夷中国文学,研究汉字者痛恨汉字,皆是文化自卑的心理作祟,中华文化复兴又从何谈起?小学和赋,皆是中国文学的独有特色,小学被誉为“一切学问之本”,而赋则是“中国文学的石楠花”[42],绝非西方语言所能造就,更非研究西语者所能诋毁。诚然,小学一去难返,大赋亦成过往,但汉字仍在。只有本于汉字,小学和赋才能发生联系。章学诚云:
扬、马诸赋非通《尔雅》、善小学,不能为之。后代辞章之家,多疏阔于经训[43]。
不通经训,则不明小学;不明小学,又岂能通字书?今日学者多不创作,偶有创作者,写诗不合格律,作赋粗俗不堪,善为赋者洵凤毛麟角。学者若不创作,研究再夥,赋也只是陈列“干尸”,终会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