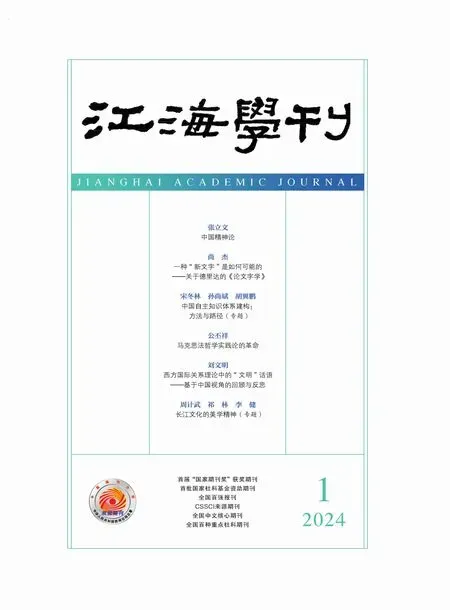“世界”的媒介:胡适与商务印书馆的早期合作*
张仲民
1936年5月4日,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著名文字学学者杨树达在日记里记载,他之前打算将个人论文集《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交由著名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结果被拒绝,“托辞不肯印行”,杨树达愤慨“商人全不辨白黑也”,“不得已”,“托北京大学某君言之”。此处的某君即胡适。杨书在胡适推荐下,商务印书馆才“允许出版”。(1)参见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诗文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页。由此不难窥见该馆与胡适关系之密切程度,而胡适之所以同商务印书馆建立起如此密切的关系,固然在于其能力和声望,但同新文化运动期间张元济、高梦旦等商务印书馆主事者对胡适的看重与信任,以及此后双方在诸多合作中建立的互信关系密切相关。只是有关这一过程的梳理,既有研究并不充分。(2)既有研究比较关注胡适与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王云五的关系,但讨论比较简单。参见陈达文:《胡适与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73—600页;季惟龙:《胡适与商务印书馆》,安徽大学胡适研究中心编,沈寂主编:《胡适研究》第3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77—401页;柳和城:《挑战和机遇:新文化运动中的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97—118页,等等。有鉴于此,本文拟钩沉索隐,重建史实,或可藉此深化有关胡适和商务印书馆关系的研究。
与商务印书馆结缘
作为近代中国经营最成功的出版商,向持“营业主义”的商务印书馆一直紧跟现实形势,关注思想界动态,注意挖掘新出现的政学两界人才为其服务,尤其看重有留学背景且中外文均比较优秀者,先后援引了如郑贞文(月薪一百五十元)、蒋梦麟(二百元)、朱经农(二百元)等多位有留学背景的人为其服务。而在好友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以后,身为商务印书馆经理兼编译所所长的张元济希望加强同北大的联系并在出版方面进行合作,出版章士钊的著作即是嚆矢。
在民初以办《民立报》《独立周报》《甲寅》而名声大噪的章士钊,“学术文章皆有时誉”,(3)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吴虞日记》(上册)(1914年6月21日日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4页。初入北大读书的顾颉刚得知文科聘请的教师名单中有教逻辑兼图书馆主任的章士钊后,即在致好友叶圣陶的信中说:“是中尤以章行严先生最为惬心餍望,非震其名也,闻上课而外尚有特别研究。”参见顾颉刚:《致叶圣陶(1917年10月21日)》,《顾颉刚书信集》第1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2—23页。能打造出一种逻辑严密的章派文言文体,(4)胡适1919年在接受采访时曾高度评价章士钊一派的文章风格及影响,视其为梁启超新民体的接续者:“章行严做‘文言的文章’的本领,实在不小,因为他的文章,能达极繁密的思想,能把思想一层一层的剥进……因为有了章派的文体,很能达极繁密的思想。”但胡适此处表扬章士钊的意图在于为接下来自己倡导白话文运动做铺垫;“因为章派的文章不是人人能做的。就是能做的人,做一篇文章,也要费很大的气力。再就看的人方面讲,要看得很明白,也不容易。有了这两种困难,所以章派的文章,还是不适用。章派的文章,既不适用,所以我们不能不提倡白话文学了。”真心:《关于新文学的两个问答》,《大公报》1920年1月16日。只是“未能忘情政治”,(5)顾颉刚:《致叶圣陶(1917年12月17日)》,《顾颉刚书信集》第1卷,第28页。但仍然接受刚接任北大文科学长的好友陈独秀的邀请到北大担任教授,讲授逻辑学,一度兼任北大图书馆馆长。1917年10月26日,张元济致信章士钊,邀请章氏为商务译东文书,“每千字二三十元,发行可由我担任一切”。(6)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6卷《日记》(1917年10月26日日记),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71页。张元济给予章士钊的这个稿费待遇极高,可能仅次于当时中华书局给予梁启超的“千字三十元”待遇。(7)据吴虞记载潘力山语,中华书局当时为梁启超开的稿费待遇为千字三十元,而四川学者谢无量在中华撰文的待遇仅为千字四元,因而不平辞职。参见吴虞1917年1月21日日记,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吴虞日记》(上册),第281页。稍后(12月3日),章士钊到访商务,“请以其所著文字由本馆印行”,张元济和高梦旦决定参照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前例,版税按照书定价的十分之一支付。(8)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6卷《日记》(1917年12月3日日记),第287页。
因为向《甲寅》投稿而与章士钊结识的胡适最初与商务并无多少关系,之所以产生交集大概出自章士钊的推荐。据胡适自述,此前张元济和章士钊曾邀请他为《东方杂志》撰稿(当系张元济委托章士钊邀约),“吾久许张菊生、章行严两先生为《东方》作文,而苦不得暇。此次乞假归娶,新婚稍暇,因草此篇”。(9)胡适:《惠施公孙龙之哲学》,《东方杂志》第15卷第5号(1918年5月),第87页。当《惠施公孙龙之哲学》一文完稿后,胡适直接寄给了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张元济决定予以发表。(10)胡适:《惠施公孙龙之哲学》,《东方杂志》第15卷第5号,第87—93页;《东方杂志》第15卷第6号(1918年6月),第88—97页。按照之前与章士钊“千字六元”的约定,张元济决定从优给予胡适稿费也是千字六元,(11)张元济为范源廉(静生)介绍的著名记者刘少少在《东方杂志》上发文所给稿费为“千字四元,他种千字三元,月先以一万字为率”。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6卷《日记》(1918年1月25日日记),第316页。“此连空行在内。与梦翁(即高梦旦,引者注)商送五十元”。1918年2月15日,胡适收到张元济2月5日的来信后即回信表示感谢,“谢收到润资五十元”。(12)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6卷《日记》(1918年2月2日、5日日记),第323、324页。此次交道大概是胡适同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订交之始。3月1日,胡适又寄《庄子哲学浅释》一文给张元济,让张氏发表。(13)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6卷《日记》(1918年3月1日日记),第338页。胡适:《庄子哲学浅释》(连载),《东方杂志》第15卷第11号(1918年11月),第81—88页;《东方杂志》第15卷第12号(1918年12月),第91—98页。
1918年6月下旬,张元济有北京之行,拜访了很多在京名流和旧友,包括蔡元培在内的多位北大教师,如夏元瑮、马幼渔、叶瀚、章士钊、秦景阳、屠寄、沈尹默、陈独秀、朱希祖等,也于7月2日拜访了胡适。(14)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6卷《日记》(1918年7月2日日记),第378页。
7月8日,蔡元培专程回访老友张元济,商讨北京大学同商务印书馆合作改良教科书事。(15)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6卷《日记》(1918年7月8日日记),第381页。9日下午,张元济赴北京大学同蔡元培及陈独秀、马幼渔、胡适、李石曾、钱玄同、李大钊等北大教授讨论双方后续的合作事宜,重点围绕三事:世界图书馆事、编辑教育书事、改订本版教科书事。之后张元济又参加了北大举行的“编译会茶话”,胡适、章士钊、陈独秀等均在座。其中陈独秀、胡适等人还向张元济提出商务出版北大学者之书的一些建议(即出版“大学丛书”)。细心的张元济在日记中对此有记载,“胡适之言,拟用四号字横行,书照‘科学’式”,胡适还认为只印刷五百部太少,并就设立世界图书馆和编辑教育书事提出看法。(16)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6卷《日记》(1918年7月9日日记),第381—382页。
8月23日,张元济离京返沪,行前特意到北京大学向陈独秀、胡适等北大教授辞行,因诸人未到校,张元济只能“留刺”而别。(17)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6卷《日记》(1918年8月23日日记),第395页。为了发展同北京大学的合作关系,“更坚大学之信,可博得后来生意”,张元济还舍弃了代北大买外文书所获得的“特别折扣”。(18)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6卷《日记》(1918年8月27日日记),第396页。
此后江苏教育会的沈恩孚(信卿)、黄炎培劝商务印书馆“宜多出高尚书,略牺牲营业主义”,被张元济采纳,表示商馆打算印行的北京大学丛书和尚志学会所编撰之书即“高尚之书”。(19)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6卷《日记》(1918年10月18日日记),第424页。
这期间,新文化潮流日见盛行,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销量“大减”,(20)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6卷《日记》(1918年12月25日日记),第458页。这让一直追随时代风气和重视吸纳新学人才的张元济及接替他担任编译所所长职务的高梦旦不得不主动改革《东方杂志》,减价销售自家出版物,积极投入新思潮这个文化市场,加强同北大的合作,还在《新青年》杂志上刊登商务印书馆出版物广告。(21)有关情况可参见柳和城:《挑战和机遇:新文化运动中的商务印书馆》,第7—93页。
1919年2月,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作为“大学丛书”之一由商务出版。该书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两个月后即再版。这让张元济更加关注融新学旧学于一体而又温文尔雅的胡适。故当他听到坊间有胡适将离北大别走以不愿太卷入北大内部新旧之争的传闻,张元济立刻致信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经理孙壮(伯恒)打听情况:
闻大学风潮近日更甚,新旧之争势所难免。并闻人言,胡适之诸君将离去大学,免惹成新旧之争,不知果有其事否?胡君能融贯新旧,至可钦佩。昨与梦翁商,如胡确有暂时韬晦之意,拟邀入本公司办事。在社会上办事,总不至如在大学之易招诽谤。虽有时亦不免有所顾忌,然外界干涉之力总比在北京为轻。此时未得确信,不敢冒昧直陈。闻筱庄先生与胡适翁极熟,可否请其代达此意。倘惠然肯来,敝处极为欢迎。如何之处,鹄候示复。(22)《张元济致孙壮函(1919年4月5日)》,转自柳和城:《挑战和机遇:新文化运动中的商务印书馆》,第100页。
4月8日,张元济发出此信,他在日记里写道:“托伯恒转托陈筱庄约胡适之,月薪三百元。”(23)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7卷《日记》(1919年4月8日日记),第50页。这个薪水应该是商务为留学生乃至自己员工所能开出的最高薪酬,稍高于胡适在北大的280元月薪。(24)据胡适1921年7—8月间所做调查,为商务印书馆最重要机构的编译所有成员一百六七十人,其中一百零八人月薪在五十元以下,百元以上的也才三十七人,而月薪为二百五十元以上者仅三人。参见胡适:《商务印书馆考察报告》,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19页。关于胡适这时在北大的薪酬,参见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中(1917—1927)》(上篇),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3页。
1919年4月底,胡适到上海迎接即将由日本抵沪的他的美国老师杜威。5月1日,胡适同张元济有过一次会面,当系为回应此前张元济的入馆之邀。张氏日记记载:
胡适之来谈,闻筱庄言,拟在京有所组织。余答以前闻大学风潮,颇有借重之意。胡又问,此系前说,后筱庄又托人往谈,似系托搜罗人材。余言亦有此意,京师为人材渊薮,如有学识优美之士,有余闲从事撰述者,甚望其能投稿或编译。(25)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7卷《日记》(1919年5月1日日记),第61页。
5月4日,张元济又约胡适和蒋梦麟一起午饭。(26)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7卷《日记》(1919年5月5日日记),第64页。从胡适此次上海之行访问张元济的情况看,少年老成的他当对商务加盟邀约回应积极,只是没有遽尔应允。然而经过这两次见面,胡、张两人由此前的仅仅是业务往来关系更进一步,由之前借助时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陈宝泉(筱庄)联系变为直接联系,这让张元济和另一商务高层高梦旦对胡适可能的加盟充满期待。之后,两人均同胡适建立了更为密切的联系。如张元济日记记载,1919年11月7日,他奔赴北京祭奠高梦旦次兄“高子益(而谦)(1863—1919)”,16日返沪。(27)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7卷《日记》(1919年11月4日、17日日记),第150、152页。胡适1919年11月14日日记记载了两人见面事,“张菊生约在大学会谈”。(28)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日记(1919—1922)》(1919年11月14日日记),第10页。复据时在教育部任职的蒋维乔记载,不论是张元济或是高梦旦,两人赴京均会拜访旧日商务同事、当时依然在商务兼职的蒋维乔。1919年10月8日,蒋维乔拜访时在北京的高梦旦,(29)林盼等整理:《蒋维乔日记》第3册(1919年10月8日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163页。此后蒋维乔日记中有多次在北京同高梦旦、张元济会面的记载。可以想见,在这一段逗留在京照顾兄长高而谦病情和处理后事期间,高梦旦应该与胡适有过会面和接洽,所以他之后才会向张元济推荐胡适帮商务主编小丛书。
制订“世界丛书”之计划
1920年1月4日,人在上海的张元济同高梦旦交流了“仍编小丛书”的计划,高建议该小丛书每册约三四万字,给作者二百元。两人原本属意的主编人选为哈佛大学数学博士、中国科学社社长、大同大学教授胡明复,“拟先约胡明复一谈”。5日,张元济对高的建议提出了异议,认为原来设想“字数较多,恐题目有限”,希望“仍以小种为宜”;高则坚持认为,“小本另是一事。大本者可分哲学、教育科学,选西人名著,仿《文明协会丛书》(日本明治时代出版的一套译介欧美政治情况的丛书,引者注)之例,即托胡适之等人代为主持”。张元济则认为“只以新思潮一类之书选十种八种,至小丛书可仍托胡明复担任试办”。(30)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7卷《日记》(1920年1月5日日记),第173页。两人争论的结果大概是张元济接受了高梦旦的建议,先请胡适主编一套新思潮类书籍,高梦旦为这套书定名为“二十世纪丛书”。(31)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7卷《日记》(1920年1月14日日记),第177页。从书名不难看出,这蕴含着高梦旦等商务主事者希望译介20世纪世界的现实和介绍“先进”文明入中国的心愿。
1920年1月14日,身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高梦旦专程赴北京。(32)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7卷《日记》(1920年1月14日日记),第178页。此行目的当是同胡适洽谈双方的编译合作计划,即约请胡适等北大同人为之编辑“二十世纪丛书”。一直关注世界大势的胡适自然同意了高梦旦的邀约。经由双方商量,原计划的“二十世纪丛书”被改名为更具开放性的“世界丛书”。1月26日,胡适开始撰写《世界丛书》条例。(33)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日记(1919—1922)》(1920年1月26日日记),第66页。1月27日,高梦旦再次拜访胡适。(34)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日记(1919—1922)》(1920年1月27日日记),第67页。
1月26、27日,在上海的张元济收到高梦旦北京来信,(35)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7卷《日记》(1920年1月26、27日日记),第181页。1月29、31日,张元济又收到两封高信。(36)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7卷《日记》(1920年1月29、31日日记),第182页。这四封信中高当有讲述同胡适接洽“世界丛书”的情况。
2月2日,胡适在自己经常惠顾的东兴楼餐馆宴请高梦旦,继续与其谈“世界丛书”事。(37)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日记(1919—1922)》(1920年2月2日日记),第73页。之后高梦旦返回上海过春节,向张元济讲述北京之行与胡适等人交流的成果。张元济在2月9日日记记载:“编译《廿世纪丛书》,梦翁在京与蔡、蒋、胡拟有办法。余意可以订定,惟专史不宜译,又人地名概用原文,本科专门译名应附对照表。”(38)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7卷《日记》(1920年2月9日日记),第185页。
为了不影响同北大及胡适的合作,张元济和高梦旦一度不愿代印另外一个宣传新思潮的刊物《国民杂志》,除其“文字不佳”外,还因其“与《新潮》杂志各为派别,恐启争端”。(39)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7卷《日记》(1920年2月28日日记),第190页。但因代印业务是商务营利的重要来源,加上该杂志背后有梁启超的支持,高梦旦认为“难于拒绝”。(40)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7卷《日记》(1920年3月3日日记),第191页。
不仅希望胡适主编“世界丛书”,张元济和高梦旦还有更为宏大的计划,即在北京新设商务印书馆第二编译所,请胡适主持。3月4日,张元济和高梦旦“谈拟设第二编译所”事。(41)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7卷《日记》(1920年3月4日日记),第191页。3月8日,张元济和高梦旦决定在北京设立商务印书馆第二编译所,“专办新事”,“以重薪聘胡适之,请其在京主持。每年约费三万元。试办一年”。(42)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7卷《日记》(1920年3月8日日记),第192页。3月9日,张元济将此事告诉商务总经理高凤池。(43)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7卷《日记》(1920年3月9日日记),第193页。
但与此同时,事情有了新的变化。3月5日,一直享誉思想界的梁启超访欧归来抵达上海,身为梁氏好友的张元济亲自到码头迎接,(44)大概此举当时曾引发一些争议,因很多时人认为张元济算是梁启超的师叔辈,“任公是师侄辈,以师叔而迎师侄,未免太过否?”而据说张元济回应道:“我为商务印书馆多得几部好文稿,为中国文化多出几部好书,并非以师叔地位去迎任公。”《张屏翰、朱景张献辞》,柳和城整理,张人凤校订:《张元济先生九十生日纪念题辞》(下),《历史文献》第1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5页。并让梁住自家。(45)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7卷《日记》(1920年3月5日日记),第192页。3月13日,梁启超向张元济提议“拟集同志编辑新书及中学教科书”,这与此前张元济、高梦旦敦请胡适设立第二编译所的计划有所冲突。故张元济约高梦旦、陈叔通等商务印书馆高层一起“细谈”梁启超的建议,决定修改之前计划给胡适的待遇,将梁启超与胡适一并看待,“拟拨二万元预垫版税,先行试办一年。胡适之一面,亦如此数”。(46)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7卷《日记》(1920年3月13日日记),第194页。稍后,高梦旦到天津同梁启超会谈后,知道梁“欲更为久大之计画”,张元济4月10日又致信梁启超表示商务愿意再追加二万元支持梁启超试办两年。参见《张元济致梁启超函》,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3卷《书信》,第221页;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1页。该日下午,三人又一起与梁启超晤谈具体的计划,初步达成合作意向。
3月19日,由上海赶到北京的高梦旦为双方合作事再次拜访胡适。21日两人又面谈,代商务在北京办第二编译所的事情胡适应该没有应允。24日,胡适在大陆饭店为高梦旦践行,显示双方关于“世界丛书”的合作协议当已达成。(47)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日记(1919—1922)》(1920年3月19、21、24日日记),第119、121、124页。返回上海之前,高梦旦还在天津短暂停留(据张元济日记记载,高3月29日回到上海),应该是他去拜访梁启超续谈之前达成的合作计划,并于天津寄胡适一封信,“在津寄奉一书,计已达览”。(48)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1册《高梦旦来函(大约1920年4月初)》,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265页。引用文字参考了夏寅整理:《高梦旦致胡适信三十八通(附一通)》,胡适研究会编:《胡适研究通讯》2019年第4期。下同。
3月26日,人在上海的张元济收到高梦旦的北京来信,附有胡适所撰《世界丛书》翻译条例。(49)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7卷《日记》(1920年3月26日日记),第199页。同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胡适所撰《〈世界丛书〉条例》,之后上海《时事新报》、北京《晨报》等报刊也相继刊登该条例。
该条例虽标为“商务印书馆谨启”,但实际出自胡适之手而又未被收入《胡适全集》,为大多数学者所不知,这里全文迻录于此:
(一)本丛书的目的在于输入世界文明史上有重要关系的学术思想,先从译书下手;若某项学术无适当的书可译,则延聘专门学者另编专书。
(二)无论是译是编,皆以白话为主(惟浅近文言亦可),一律用新式标点符号,以求明白精确。
(三)本丛书无编辑部,只设审查委员会,会员五人或七人(不必限定在一处),由发行人聘定。
(四)审查委员会之职务:
(甲)商定要编译的书目及先后次序。
(乙)担任委托胜任的编辑人分任各项书籍。
(丙)每书成五千字以上时,得由审查委员分任或转托人初读一次,以定编译人能否胜任此项书籍。
(丁)书成后,审查委员或亲自审查或转托专家审查。审查之后,由审查人署名负责,始付印。
(戊)审查委员会除委托编译的书籍之外,随时亦可收受已成之稿。审查合格后,亦可作为丛书之一部。如系译稿,须与原本同时交与审查委员会。
(五)审查人(无论是否委员会中人)每审查一书,应得相当的酬报。
(六)每书的编费或译费,略依本书的难易为标准,分为两种办法:
(甲)依售稿办法,约以每十万字稿费三百元为率。其版权为发行人所有。
(乙)依版税办法,以定价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为版税。其版权为著作人所有。遇需要时得先垫付版税若干。
(七)本丛书由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发行,现已委托国立北京大学蔡孑民、蒋梦麟、陶孟和、胡适之诸先生组织本丛书审查委员会。
(八)国内外学者有愿担任编译者,望将所愿编译之书名或已成稿件寄交北京大学第一院胡适之先生,或由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转交,以便通函接洽。
商务印书馆谨启。(50)《〈世界丛书〉条例》,《时事新报》(1920年3月30日,第4张第2版)、《北京大学日刊》第572期(1920年3月26日第1版)、《晨报》(1920年3月26日,第6版)及这里所引之《时事新报》均无此条落款,只有《时事新报》(1920年4月28日,第2张第2版)有“商务印书馆谨启”字样。
从条例内容看,该丛书以翻译编写同世界文明有关的书籍为主,包含着学习世界“先进”文明、译介新知的期待,文体采用白话文,加新式标点,这也反映胡适一贯的世界主义追求和白话文主张。《条例》极大程度上保障了作者或译者以及审查人的权益。胡适这里拟定的审查委员人选,则全部出自北京大学,由在北大举足轻重的蔡元培、蒋梦麟、陶孟和和他本人担任,四人均为欧美留学生。
条例公布后,高梦旦致信胡适讲明后续事宜。信中表示“世界丛书”审查委员的酬金,“每人年五六百元”,询问胡适是否已经告知其他审查委员,并告诉胡适所拟《〈世界丛书〉条例》发表后,“此间舆论甚赞同,后此接洽事必多,非有专员办理不可。如一时难得适当者,鄙见可先请助手一人,后来专员聘定亦可,令其管理杂务。先生甚忙,事事躬亲,鄙怀甚不安也”。(51)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1册《高梦旦来函(大约1920年4月初)》,第265—266页。高梦旦这里还不忘附上张元济的问候。稍后,高梦旦还应同时致函胡适等四位审查委员,通知其每年的酬金情况。接下来,他又致信胡适送上报酬:“适之先生大鉴:‘世界丛书’审查委员会事,承俯允担任,同人不胜感佩。兹送上年金六百元,乞詧入为幸。”(52)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1册《高梦旦来函》,第264页。实际上,除胡适外,其余三位审查委员仅是挂名,(53)蔡元培稍后致胡适的一封信很明确提及此情况。他向胡适推荐北大学生陈迪光翻译的《科学与上帝》一书时说道:“鄙意可收入《世界丛书》,此事想仍由先生主持,特奉上。”但此书最后并未收入丛书中。类似情况亦见于蔡元培之后向胡适推荐的张蕴霭所译《人类的人格》一书,也未被列入丛书中出版。《蔡元培致胡适函(1921年12月26日)、(1922年1月4日)》,高平叔、王世儒编注:《蔡元培书信集》(上册),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05、508页。他们所得酬金如此之高,自然隐藏着胡适拉同盟的心理和商务对胡适极高的期待。
此后胡适即开始为商务工作,推荐了一些书目——包括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续编和陈衡哲的《西洋史》,还推荐“戴君”专门负责具体的联络工作,薪水由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承担。胡适旧友马君武大概看到“世界丛书”广告,自告奋勇寄信与商务表示自己有书稿提供。这些情况在高梦旦致胡适之信中即有显示:
戴君月薪拟按月由京馆迳送戴君处。书目稍缓发表,甚是。如能于二三个月出书数种,竟不发表,亦无不可,因外间所发表者未必即出书,不必与争竞也。《中国历史》事,拟即依尊意,就夏穗卿之书为蓝本,但要求其审定,未必做得到耳。《西洋史》草案,敬悉。此间同人另有意见书一纸,请詧阅,草案附还。……马君武来函寄阅,此间拟为出单行本,亦不必标明某某丛书字样,现稿子亦尚未寄来。(54)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1册《高梦旦来函(1920年6月7日)》,第267—268页。
经由这次合作编书,此后张元济、高梦旦和胡适来往不断,双方关系明显密切起来。1920年7月14日,直皖战争在北京一带爆发,皖系兵败在京郊南苑一带抢劫,一时北京人心惶惶。(55)林盼等整理:《蒋维乔日记》第3册(1920年7月18日日记),第1226页。胡适也当致信高梦旦报告自己的近况与即将有南京之行的计划。高梦旦8月2日复信胡适表示关注,还表示自己可能将有北京之行:
近畿战事发生,尊寓不免惊惶。现在幸而无事,殊可慰也。南京讲习事,是否仍须一行?如有到沪,幸见告。弟拟八月末或入京一行也。前所云苏君甲荣编辑《中学本国地理》事,未审已否接洽?如能将编辑条例草示,尤幸。(56)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1册《高梦旦来函(1920年8月2日)》,第270页。
由高梦旦8月17日复信可推知,对高氏8月2日的来信,胡适也应很快进行了回复,说及即将纳入“世界丛书”的陈石孚所译《经济史观》出版事宜和自己将到上海事,同时询问了《东方杂志》发表文章中几个笔名系何人的问题。高梦旦复信表示:
前谈甚快。《经济史观》计五万九千字,如何办法,有复信即见示。现已赶紧付排矣。(57)该书1920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主要是介绍马克思的经济史观,序言出自陶孟和(履恭)之手。美国塞利格曼原著:《经济史观》,陈石孚译,陶履恭校,定价大洋五角。所询《东方》之“蠢才”,系胡君愈之别号。此君刻在馆中,《东方》译件最多。“愈之”“蠢才”“罗罗”及“W”,皆其手笔,但用“蠢才”时较少耳。从者何日来沪?先期示知,以便趋谈。(58)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1册《高梦旦来函(1920年8月17日)》,第271页。
但高梦旦原计划的北京之行并未成行,倒是稍后张元济的北京之行,至少同胡适见了两次面。1920年10月9日,张元济在北京访问了胡适。(59)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7卷《日记》(1920年10月8日日记),第231页。10月26日又见了胡适、陶孟和等人。
1920年下半年,胡适开始患病。(60)关于胡适此次患病及其治疗乃至后续情况,参见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中(1917—1927)》(下篇),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119页。他遂在1921年1月16日致高梦旦信中讲述病况,信中还应向高提出了《中国哲学史》版税等事,希望能预支千元。故高氏1月22日立即回信,除提出医疗建议外,还逐一答复了胡适的提议,表示愿意给予胡适特别待遇,但请其不要将之随意公开:
一月十六日手书已收到。尊体因工作又有不适,甚为念念。此等病,其来源甚远,断非旦夕可愈,尤不宜用峻剂以求速效。鄙见仍以有经验之西医详为诊治,并多多休息,俟完全复原之后,再行办事。每日黄芪十两,是否适宜,仍须斟酌。弟不敢谓中国无方药,但有奇效者,必有一部分之危险,不如科学的治疗为稳妥,愿三思之。《哲学史》版税,据出版股查复,另纸附阅。虽间有因兵乱阻碍,及分馆存储,以致迟迟;实则此间范围过广,督催不力,亦无可讳言。现已嘱主者力加整顿,以后不至更蹈此弊,尚祈鉴谅……承嘱拨付千元,遵即由兴业银行寄奉,但不便以垫付版税为名。因有版税之书甚多,恐他人援以为例,尚希秘之。(61)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1册《高梦旦来函(1921年1月22日)》,第273—276页。
考察商务编译所
随着双方关系的日趋密切,张元济和高梦旦对胡适的期待也愈发高,希望胡适最终能到商务担任编译所所长一职。1921年4月,前往北京出差的高梦旦屡次拜会病后复原中的胡适,代表张元济直接提出希望胡适到商务任职的建议。胡适在4月27日的日记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高梦旦先生来谈。他这一次来京,屡次来谈,力劝我辞去北京大学的事,到商务印书馆去办编辑部。他是那边的编辑主任,因为近来时势所趋,他觉得不能胜任,故要我去帮他的忙(他说的是要我代他的位置,但那话大概是客气的话)。他说:“我们那边缺少一个眼睛,我们盼望你来做我们的眼睛。”此事的重要,我是承认的: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但我是三十岁的人,我还有我自己的事业要做;我自己至少应该再做十年、二十年的自己(的)事业,况且我自己相信不是一个没有可以贡献的能力的人。因此,我几次婉转辞谢了他。他后来提出一个调停的方法:他请我今年夏天到上海去玩三个月,做他们的客人,替他们看看他们的办事情形,和他们的人物谈谈。(62)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日记(1919—1922)》(1921年4月27日日记),第218页。
高梦旦还劝胡适在暑假带家眷一起去上海,但胡适没有同意。
从返沪的高梦旦那里得知胡适愿意赴商务任职的消息,(63)据王云五回忆说,胡适当时已经答应高梦旦去商务任职,“但以先行尝试几个月为条件,如果尝试后自己认为于性情尚无不合,固可勉为应命,否则务请原谅”。结合当时情况,王之回忆当属实。参见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第77—78页。张元济非常高兴,立即致信胡适表达喜悦和欢迎之意:
高梦翁返沪,询知贵体复元,起居康吉,至为欣慰。敝公司从事编译,学识浅陋,深恐贻误后生。素承不弃,极思借重长才。前月梦翁入都,特托代恳惠临指导,俾免陨越。辱蒙俯允暑假期内先行莅馆。闻讯之下,不胜欢忭。且深望暑假既满,仍能留此主持,俾同人等得常聆教益也。弟来月拟入都一行,或可先在北方相晤。(64)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2卷《书信》张元济致胡适(1921年5月15日),第536页。
不过,事后因张元济计划的北京之行未成,两人再见面要到胡适7月中旬到访商务印书馆了。
对此前高梦旦邀请他到商务任职一事,胡适比较犹豫。1921年6月15日,胡适写了一封长信给高梦旦询问商务要他去任职的目的。(65)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日记(1919—1922)》(1921年6月15日日记),第308页。但高的复信仍然模棱两可,只是让胡适准备移眷到上海安家。胡适稍后在日记中有所记载:
我前写信给商务印书馆,问他们究竟要我做什么事。今日梦旦先生来信,仍是不明白的答复。他说:“此间关于编译事全赖先生主持。一切情形,非笔墨所能尽,可俟到沪面详。惟有一节不能不预定,则移眷是也。”(66)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日记(1919—1922)》(1921年6月23日日记),第318—319页。
与此同时,上海《时报》社老板狄葆贤也在打胡适的主意,希望胡适能担任《时报》主笔,让昔日的北大学生张培风即张煊先行说项,(67)关于张煊情况,可参见炯炯:《张培凤遗事》,《晶报》1927年4月30日,第2版。按:炯炯为钱芥尘笔名,丹翁:《千号纪念新闻篇》,《晶报》1927年7月3日,第2版。张煊(寿昆)当年与钱穆先后在常州府中学堂和南京钟英中学为同学,钱穆晚年亦曾回忆及张煊,参见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台湾东大图书公司2013年版,第60—62页。并亲自致信邀请胡适:
昨晚得上海《时报》狄葆贤先生的快信,说《时报》附出的七种周刊将停止,改出一个“星期讲坛”,前已由张培风君向我说过,已得我的允许,担任主任,他不日将登广告发表此事,并云“从此敝报仗先生法力,将由九渊而登九天矣!”——这事太突兀!张君来说过,我并没有答应他。我怕狄君真如此发表,故急托张君发电阻他。我也写了一信给他。(68)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日记(1919—1922)》(1921年6月26日日记),第322页。
6月27日,胡适又写信给高梦旦。(69)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日记(1919—1922)》(1921年6月27日日记),第323页。由此后情况看,此信当系胡适通知高梦旦自己接下来商务之行的具体时间安排,信中应也拒绝了高梦旦提出的“移眷”要求。7月10日,胡适拜访了到北京出差的商务印书馆东文部主任陈慎侯(承泽),进一步了解了商务邀请他的内情,“大概商务想我去做编译所主任的事”。(70)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日记(1919—1922)》(1921年7月10日日记),第355页。7月15日上午10点,胡适乘坐火车去上海,16日晚上10点,胡适到站。张元济、高梦旦、李拔可等一帮商务高层亲自到车站迎接。(71)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日记(1919—1922)》(1921年7月16日日记),第362页。7月17日,高梦旦、高凤池、鲍咸昌、张元济、李拔可、杜亚泉等商务“主要职员”陪胡适午餐,席间闲谈提到商务印书馆正在悬赏征文,胡适认为也可以用悬赏征书方式征集所需要的书稿,“可悬赏五千元(或三年留学经费),以一年或年半为限,当可得许多好稿子”。(72)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日记(1919—1922)》(1921年7月17日日记),第363页。
7月18日上午十点半,胡适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考察,并与高梦旦交流:
我问梦旦,他们究竟想我来做什么。他问我能住几时,我说,北大开学时我即须回去,此已无可疑。至于半年以后的事,那是另一问题,大概我不能离开北大。他说,他们昨天看我的情形,已知道不能留我。但此时他们很望我能看看编译所的情形,替他们做一个改良的计划书。我说,我也是这样想。议遂定。(73)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日记(1919—1922)》(1921年7月18日日记),第365—366页。
抱此目的,胡适展开调查工作。他发现编译所有一百六十人,于是访问编译所的老熟人了解情况,征求内部各人对编译所现状的意见和改革办法。其中,郑贞文等人率先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和改造计划。(74)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日记(1919—1922)》(1921年7月18日日记),第366—367页。
7月19日上午,胡适再次到编译所与众人会面交流,并顺道参观了商务涵芬楼的藏书。此次会面中,高梦旦对胡适表示了他希望彻底改革编译所的愿望,胡适则认为“编译所是不能完全不要的。革命也只革得一部分,毕竟还免不了立宪的改革”。(75)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日记(1919—1922)》(1921年7月19日日记),第367页。
7月20日,胡适又到编译所旁听了编译会议。会上胡适感觉有关中学教科书的讨论太散漫,忍不住劝各人做一个计划后再开会讨论,“便可不致如此散漫了”。胡适还在大家讨论《国文读本》时,劝商务“多设法编一些‘中学国文参考丛书’”,并提出自己的计划。而在与商务职员杨端六交流后,胡适了解了更多编译所的弊端,知道“改良编译所不容易,因为须从全部的组织改良起”:
现在馆中事权不统一,馆中无人懂得商业,无人能通盘筹算,无人有权管得住全部……馆中最大的弊是不用全力注重出版而做许多不相干的小买卖。编辑所中待遇甚劣,设备(图书、房子)甚不完备,决不能得第一流人才(终年无假期,暑假名为可以自由,而又以加薪之法鼓励人不告假)(薪俸也极薄)。
胡适非常认可杨端六指出的这些问题,认为“极中肯要”。(76)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日记(1919—1922)》(1921年7月20日日记),第373页。
7月21日,编译所员工“华超”提供给胡适一篇《改革编译所刍议》,详细提出了具体改革措施。(77)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日记(1919—1922)》(1921年7月21日日记),第374—375页。7月22日,郑振铎也给胡适提供了一个改革意见书。(78)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日记(1919—1922)》(1921年7月22日日记),第380页。7月27日,高梦旦邀请了一些编译所“新人”,如杨端六、郑贞文、郑振铎等人到家吃饭和胡适会谈,期间郑贞文又提出学者在编译所难以发展的问题,胡适当即有所回应,设想了解决办法。(79)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日记(1919—1922)》(1921年7月27日日记),第387—388页。8月8日,杨端六又给了远游返沪的胡适一个《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改组办法大要》。(80)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日记(1919—1922)》(1921年8月8日日记),第408—409页。三人所提建议大部分为胡适在9月30日撰成的《对商务印书馆的考察报告》所采纳。(81)胡适:《对商务印书馆的考察报告》,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0卷,第513—536页。在这万字报告最后,胡适也批评商务印刷忙着赶印“教会之经典及其他外来之印件”,导致“世界丛书”出版太迟。10月1日,胡适将报告交给了到北京治病的张元济。(82)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日记(1919—1922)》(1921年9月30日日记),第473页。张元济当面对胡适表示,其提议“都是很切实可行的,没有什么大难行的”。(83)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日记(1919—1922)》(1921年10月4日日记),第476页。不过,稍后正式出任编译所所长的王云五又提出一个更可行和具体的改进意见,并付诸实施。(84)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第79—80页。
7月22日当天,张元济和高梦旦还同胡适交流了编辑《常识小丛书》的计划,请胡适出谋划策,第二天下午,胡适即拟了一个新的计划和“二十五个题目”。(85)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日记(1919—1922)》(1921年7月23日日记),第382页。但对正式担任编译所所长一职事,胡适觉得于自己个性“不很相宜”,(86)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第78页。至于替代人选,胡适非常反对由文化立场比较保守的刘伯明——高梦旦属意的替代人选担任:“梦旦问我,若我不能来,谁能任此。我一时实想不出人来。他问刘伯明如何,我说决不可。”(87)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日记(1919—1922)》(1921年7月18日日记),第367页。胡适此前认为刘氏所译杜威《思维术》一书“错误甚多”,“此书前经印出一次,中有许多错误,我曾指出几处,托知行转告译者。今此等处仍没有改正”。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第327页。但事实上,胡适翻译杜威的著作也是错误百出,江勇振先生已有指正,而徐佳贵教授指出刘伯明此书中的翻译错误其实没有那么离谱。参见徐佳贵:《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与新文化运动——以刘伯明为线索的再考察》,《学术月刊》2022年第6期;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中(1917—1927)》(下篇),第221—307页。在胡适看来,商务印书馆太重要了,不能轻易将之交到敌对者手中。
1921年8月13日,高梦旦又劝胡适明年来商务接办编译所。胡适虽然认为“这个编译所确是很要紧的一个教育机关,——一种教育大势力”,但他自己有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书和写作的计划,“不应该放弃自己的事,去办那完全为人的事”。(88)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日记(1919—1922)》(1921年8月13日日记),第416—417页。因此,“迟疑”的胡适只能寄希望于自己认可的人接手此职,所以向高梦旦推荐了为商务印书馆不熟悉、且尚无太高知名度的王云五出任此职,并亲自邀请王云五到商务与张元济、高梦旦等人见面。(89)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日记(1919—1922)》(1921年7月23日日记),第381页。8月19日,胡适、王云五与商务重要职员一起见面吃饭。(90)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日记(1919—1922)》(1921年8月19日日记),第426页。
8月31日(阴历七月二十九日),张元济和王仙华代表商务聘请王云五,“条件都已提出”,王云五答应中秋节前回话。对此,作为居间人的胡适非常满意。(91)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日记(1919—1922)》(1921年9月6日日记),第446页;胡适:《高梦旦先生小传》,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9卷,第666—669页。关于胡适此次考察商务印书馆的情况,还可参见柳和城:《挑战和机遇:新文化运动中的商务印书馆》,第97—122页。
在胡适即将启程返京之前,高梦旦代表商务致送酬劳一千元。胡适只愿意接受五百元,返回了五百元。(92)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日记(1919—1922)》(1921年9月3日日记),第443页。9月7日,胡适离沪返京,张元济、高梦旦等商务高层和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原放等都到车站送行。(93)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日记(1919—1922)》(1921年9月7日日记),第448页。
10月25日,到北京探视侄子病情的高梦旦去见了胡适,高度肯定了王云五的能力。(94)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日记(1919—1922)》(1921年10月25日日记),第488页。11月10日,胡适收到王云五表示不愿就任商务编译所所长的来信。次日下午,高梦旦拜访胡适,请其致信王氏劝他就任编译所所长职务。胡适允诺。(95)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日记(1919—1922)》(1921年11月11日日记),第498页。最终王云五于1922年1月1日正式接替高梦旦担任编译所所长。
此后胡适深得张元济、高梦旦信任,两人对胡适的各种要求与推荐也基本予以满足。在他们考察期间,胡适向高梦旦推荐了周建人入职商务印书馆,并致信其兄周作人,告知他为其弟争取到的月薪为六十元。(96)《致周作人(1921年8月18日)》,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3卷《书信(1907—1928)》,第324页。1921年底北大欠薪风波仍未解决,高梦旦代表商务印书馆致信胡适,直接赠送一千元现金以帮助胡适渡过难关:“读报知中央教育费仍属无着,北京教职员多在窘乡,先生自不能从容。此间同人甚为念念。且以先生为此间尽力甚多,兹致送千元,尚乞察入。区区之诚,必蒙鉴及,故不多赘。”(97)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1册《高梦旦来函》,第282页。张元济后来甚至说只要胡适看中的书,可以随时开列名单推荐给商务,“不妨随时想得,随时开示,敝处出版,本无限制也”。(98)《张元济致胡适(1923年9月8日)》,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2卷《书信》,第537页。
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早在双方确定合作出版《世界丛书》后,胡适就开始帮商务印书馆招徕作者、译者。如胡适日记记载:“校读潘介泉(家洵)译的易卜生的《国民公敌》完,又略看他译的《娜拉》。此两剧与他译的《群鬼》将归《世界丛书》出版。”(99)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日记(1919—1922)》(1921年4月27日日记),第218页。再如1921年8月9日,李季来见胡适,表示有稿子给《世界丛书》。胡适便让商务印书馆直接支付李季千元路费资助其出洋。(100)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日记(1919—1922)》(1921年8月9日日记),第410页。胡适还希望鲁迅兄弟将所作小说汇集起来列入“世界丛书”出版,他专门致信周作人说明此事。除此之外,他还希望周氏能将正在翻译的日文小说放到自己主持的商务印书馆“世界丛书”中出版,因为商务不但排印错误少,且所给稿酬也高。(101)《致周作人(1921年8月30日)》,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3卷《书信(1907—1928)》,第325页。周作人遂答应胡适的邀约,将自己翻译自日人的《现代小说译丛》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胡适还约请黄凌霜为“世界丛书”翻译华德的《应用社会学》一书,三年后翻译工作完成,胡适请黄附序文与目录,致信时为编译所所长的王云五征询是否可以继续出版此书,而胡适自己态度是觉得“此种名著,大可出版,稿费可送一整数,或不甚昂贵”。(102)《致王云五》,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3卷《书信(1907—1928)》,第393页。但不知道何故,此书后来似未列入“世界丛书”中出版。
为商务辩护
由上述史实重建情况可知,在胡适与商务印书馆建立密切关系的过程中,编辑“世界丛书”之提议成为双方开始合作的契机。在胡适这边,他借助主持“世界丛书”的机会同商务高层建立起紧密的合作关系,获得了商务印书馆的充分信任和不时的经济援助,故之后他非常注意为后者出谋划策,帮助搜罗作者、译者,也将自己的著作《章实斋先生年谱》等送交商务出版(1922年1月出版),时时维护和援用商务印书馆这个平台。这种情况通过他对好友高一涵的驳斥可以明显看出。
当胡适决定将原由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努力》周报交由商务改为月刊出版后,甫(1923年)在商务出版过《欧洲政治思想史》(上卷)一书的高一涵觉得这是商务打算包办《努力》谋利,遂产生不满,借代人在北戴河养病的胡适回应两读者批评《努力》杂志之际,以“摇旗呐喊的小卒子”身份在影响甚大的《晨报副刊》发文,公开批评商务高高在上的“资本家面孔”,表示自己要持“不合作主义”,高进而还把为《努力》写稿的人称为“文丐”。(103)高一涵:《关于〈努力月刊〉的几句话》,《晨报副刊》1924年8月28日。高文是在表面借批评胡适与商务合作出版《努力》之举,批评商务在借胡适和《努力》赚钱,实际是“酸葡萄心理”,批评商务只“敷衍”胡适这样的“有名人物”而忽略自己这样的“小卒子”。胡适读到高文后非常生气,除私下致信高一涵外,次日,又给《晨报》写信为商务印书馆辩护,同时回应了其他人对《努力》的质疑。(104)《致高一涵(1924年9月8日)》《致晨报副刊(1924年9月9日)》,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3卷《书信(1907—1928)》,第379—384页。
在1924年9月8日致高一涵的信中,胡适批评高一涵为了证明自己清高,“就不惜把一切卖文的人都骂为‘文丐’”,这是缺乏道德的表示。接下来,胡适激烈地反驳高一涵:
拿尽心做的文字去卖三块钱至五块钱,不算是可耻的事。献寿文,作瞒心昧己的谀墓文,那是文丐。借文字敲竹杠,那是文丐。用抄窃敷衍的文字骗钱,那是文丐。迎合社会的恶劣心理,制造下流读物,那是文丐。但拿不苟且而有价值的文字换得相当的报酬,那是一种正当的生活。
反驳高一涵之余,胡适也向高氏解释了自己为何与商务印书馆联合出版《努力》,主要在于看重商务雄厚的经济实力,可以实现自己“办一个有资本的杂志”的梦想。“无钱而办杂志办报,全靠朋友友谊的投稿,那是变态的现象,是不能持久的。《努力周报》不出稿费,连发行部的人也不支薪,这是我最不安的事。所以改办《月刊》时,我极力主张,非集点资本,正不必办……所以我主张《月刊》每月应有最低限度的编辑费。”胡适继续披露内情,他在同亚东图书馆和商务商量之后,加上陈独秀的协调,决定交给愿意支付出版费的商务办,而胡适和陈独秀的文字不要酬劳但保留版权,“此是‘商务’承办此报的事实,并无如你说,‘商务印书馆于是便板起资本家的面孔’,说:‘给你们做文字的人三块钱至五块钱一千字’的情形”。随后,胡适又向高一涵解释了商务与《努力》的关系,绝非是商务意在借此赚钱,商务这样一个大公司不会在乎这几个小钱,而且其所办杂志,几乎没有盈利的,考虑到办刊成本,商务接办《努力》月刊是存在风险的,如果每期销量得不到八千册,肯定会赔本,而月刊类杂志是极难达到八千这样销量的,而达不到胡适他们也无须赔偿商务印书馆,“这种单方的条件,我们能说他们是谋红利吗?”胡适教训高一涵有欠忠厚,误解商务好意,导致自己不得不出面亲自解释,向高披露双方合作内情。(105)胡适:《致高一涵(1924年9月8日)》,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3卷《书信(1907—1928)》,第379—381页。
胡适在给《晨报》社的信中回应对《努力》的质疑,解释《努力》出版停滞的原因和继续出版的必要,同时针对之前高一涵的文章,进行重点说明。因胡适该文出言激烈,为商务背书色彩明显,高梦旦担心会被别有用心者炒作,于胡适和本馆名誉不利,特意致信胡适委婉提醒。(106)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1册《高梦旦来函(1924年9月20日)》,第309页。之后,时在商务担任史地部部长、同为胡适与高一涵朋友的朱经农也致信胡适,解释高一涵迁怒于商务的缘由:高自认为在同商务关于《欧洲政治思想史》后续内容的出版交涉过程中受到轻视而产生不满与误会。(107)《朱经农致胡适(1924年11月30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03—204页。朱经农稍后认为,商务为了出版《努力》周刊,其实也冒着一定政治风险,因为《努力》中的时论会批评当局和政治,会得罪有权势者,这样势必牵连到出版商和资助者商务印书馆,故他建议胡适:“《周刊》与‘商务’的关系,最好仍是代定、代售。”(108)《朱经农致胡适(1924年12月9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05页。的确,参照商务印书馆以前的做法,对于涉嫌盗版或犯禁的书刊,商务印书馆一直采取秘密印刷不署印刷者之名的做法。但此做法对于《努力》这样同人化、公开出版的定期刊物,显然不适用。由此可见商务印书馆为了笼络胡适所冒的风险,但此后《努力》并未如愿复刊,朱经农这个担心并没有成为现实。
实际上,像高一涵这样批评商务重利的学者颇有不少。1918年时,罗振玉积极图谋为在哈同处工作不愉快的王国维找一兼职机会,他致信张元济(菊笙)希望商务能聘请王国维为之校勘古籍,(109)《罗振玉致王国维》(1918年5月26日),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集》,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371页。但为张回信婉拒。罗振玉为此颇为恼火:“菊笙复书已来,附览。此人卒不可与为善,颇悔前函为多事也。”(110)《罗振玉致王国维》(1918年6月11日),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集》,第376页。身为海上名流、富商兼藏书家的蒋汝藻平常与张元济交往甚多,互相借书刻印也为常事,但蒋氏破产后,所藏珍贵书籍被张元济强买,故他向好友王国维抱怨道:“即以菊生论,当时彼出《四部丛刊》时来商借,弟无书不允,绝无条件……论情论理,公理何在,友谊何在?然犹可诿为见利而动也。”(111)《蒋汝藻函》(三十六),马奔腾辑注:《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3页。
身为罗振玉和蒋汝藻好友的王国维对商务印书馆之出版事业也有评论。他曾批评商务所出书籍“无用有害”。(112)《致罗振玉(1917年12月31日)》,房鑫亮编:《王国维书信日记》,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93页。1919年8月中旬,王国维将自己翻译的伯希和的文章《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送登《东方杂志》,该文有六七千字,但商务印书馆仅答应给其稿费二十元,让原本期待能得到四十元酬劳的王国维很是不满,“竟遭点额,索四十元还二十元,怒而索还原稿”。(113)《致罗振玉函(1919年9月10日)》,房鑫亮编:《王国维书信日记》,第396页。受胡适介绍为商务编辑教科书的顾颉刚对该馆不重视学问而急功近利的做法也非常不满,一度产生“恶感”,曾直接致信商务印书馆史地部主任朱经农,抱怨“商务印书馆是充满着商业气味,与学问格不相入”。(114)顾颉刚:《致朱经农(1923年6月3日)》,《顾颉刚书信集》第2卷,第134—135页。
不仅以上这些学者批评商务重利,即便是同商务印书馆和张元济有密切合作关系的蔡元培也曾有过类似看法:“商务之纯粹营业主义,不肯稍提赢余以应用于开辟风气,且为数年以后之销路计,亦可谓短视矣。”(115)蔡元培:《复吴敬恒函(1914年4月23日)》,高平叔、王世儒编注:《蔡元培书信集》(上卷),第208页。
以上诸人对商务的批评虽各有立场,未必尽当,但他们对商务过于坚持营业主义立场的认识却所见略同。凡此种种,均可见商务印书馆崇尚营业主义甚至为此不惜冒犯风险的一面,这或许正是该馆得以壮大成长为近代中国最成功的企业原因所在。只是过去我们在研究中过于强调商务印书馆、张元济为中国文化建设所做的贡献和功劳,而相对忽视其重利、逐利、冒险的面向,这显然不利于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商务印书馆的历史。
结 论
吊诡的是,当初双方寄予厚望的“世界丛书”刚发布征稿广告之时,尽管获得了学界较好的响应,但所收来稿质量一般。胡适自谓:“著书的人没有,勉强找几个翻译人,总该还有。所以我们上半年,弄了一个‘世界丛书’,不想五个月的经验结果,各处寄来的稿子虽有一百多种,至今却只有一种真值得出版。”(116)胡适:《提高与普及(1920年9月17日)》,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0卷《教育语言杂著》,第67页,引文标点有所更动。其后该套书虽先后编撰翻译了多种,(117)有关“世界丛书”的目录、译作者、出版信息等情况,可参见上海图书馆编藏:《中国近现代丛书目录》,上海图书馆1979年印,第320—321页。但引起的反响总体不是很大,从商业经营角度上来说不算太成功。较之同时期商务推出的梁启超主持的“共学社丛书”——与世界丛书同时注册,(118)1921年9月23日,张元济得到内务部传来的消息,“共学社及世界丛书不能总共注册一次,须分种注册”。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7卷《日记》(1921年9月23日日记),第266页。其影响当逊色不少。
事实上,“世界丛书”及其所蕴含的现代性——“文明”追求和“世界”想象不过系商务印书馆结好胡适的一个媒介而已。为了争取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尽可能长期为己所用,该馆并未在意该丛书在商业上的得失。稍后为了维系同胡适的合作,同时与亚东图书馆竞争胡适这个金字招牌,商务印书馆甚至愿意不惜贴钱资助胡适办《努力》月刊,打算“无论什么条件都可遵依”,(119)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30卷《日记(1923—1927)》(1923年10月17日日记),第73页;《致高一涵(1924年9月8日)》,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3卷《书信(1907—1928)》,第379—381页。并答应给《努力》作者千字“三块钱至五块钱”的稿费。张元济和高梦旦等商务主事者对同胡适合作的热衷度,可见一斑!
概言之,双方当时顺利建立的这种密切合作关系对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对胡适学术声望的扩张与再生产,对商务印书馆新思潮书刊的出版销售,乃至对后来整理国故运动的开展及其后一系列学术事业的推进、学术书籍的出版,均意义重大。因之,这里对胡适与商务印书馆早期关系的重建,当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胡适之所以为胡适,以及商务印书馆的“营业主义”和与时俱进的一面,进而更好理解胡适同商务印书馆建立密切合作关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