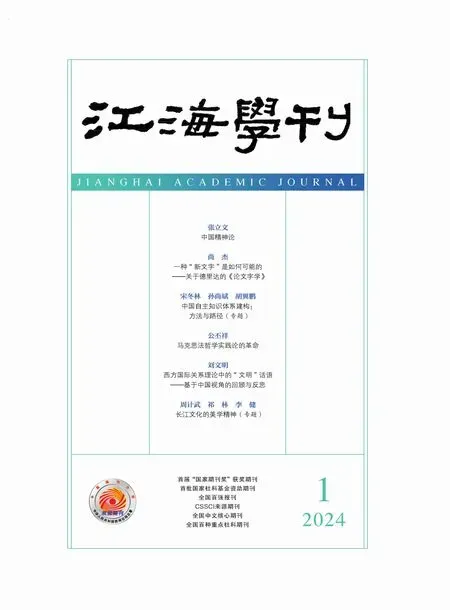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文明”话语*
刘文明
20世纪90年代之前,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流派均强调以国家为中心来思考国际关系,“文明”作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并未受到重视,仅英国学派对此有所涉及。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文明冲突”论,改变了这一状况,他的观点引起了广泛回应。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国际关系研究由主要强调国家行为体扩大到关注各种非国家行为体,“文明”问题也日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文明间的关系成为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中的一个热点话题。与此同时,由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崛起和世界多极化发展,世界迎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和不同文明之间平等交流互鉴在构建国际新秩序中显得日益重要。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指出:“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我们应该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68—469页。这意味着,建构新的国际秩序不仅要尊重各国主权平等,还要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的国际新秩序。然而,现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是基于西方历史经验和知识建构起来的,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倾向。基于此,国际关系学迫切需要来自不同文明背景及不同学科的学者展开对话,从全球历史经验和知识体系出发,构建一种尊重文明多样性和倡导不同文明和谐共生的新型国际关系理论。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在此尝试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文明”话语——包括19世纪以来的“文明国家”观念和围绕“文明标准”“文明冲突”的讨论,作一回顾和评述,并从中华文明视角出发进行反思,为构建全球化时代倡导不同文明和谐共生的新型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一点思考。
19世纪以来国际政治中的“文明国家”观念
依据现有研究成果,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出现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此时欧洲的自由主义、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等意识形态中,都包含了有关国际关系的思想,而且这种思想明显受到“文明”观念的影响。(2)参见[英]巴里·布赞、乔治·劳森:《全球转型:历史、现代性与国际关系的形成》,崔顺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加]阿米塔·阿查亚、[英]巴里·布赞:《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刘德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19世纪国际政治中的“文明”话语,可从“文明国家”概念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文明”标准、“文明”等级观念体现出来。
西方的“文明”概念出现在18世纪中叶的启蒙运动中,在19世纪欧洲得到广泛使用,尤其被用来描述一种先进的社会状况,以区别于那些落后的社会,“文明国家”也由此成为19世纪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关键概念。首先对此作出较为系统阐述的是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基佐(François Guizot)。他在1828年完成的《欧洲文明史》中提出,“文明的基本理念是进步和发展,一个民族或国家是否‘文明’,取决于其社会和个人是否表现出了进步和发展,‘文明’包含着两个事实……社会活动的发展和个人活动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性的进步。哪个地方……只要看到了这两个标志,虽然社会状况还很不完善,人类就大声鼓掌宣告文明的到来”。(3)[法]基佐:《欧洲文明史》,程洪逵、沅芷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1页。基佐的阐述实际提出了“文明”的标准,即具备上述两个“标志”的国家才称得上是“文明国家”。这一观点对后来的欧洲思想界影响很大。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就认为,正是文明所代表的进步,将富裕、强大的国家与蒙昧人(savages)或野蛮人(barbarians)区别开来,他在1859年一篇关于国际干涉的文章中提出,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应根据文明程度不同而区分不同的情况,把“同样的国际习俗和国际道德规则,既适用于一个文明国家和另一个文明国家之间,也适用于文明国家和野蛮民族之间,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野蛮人没有作为一个‘国家’的权利”。(4)John Stuart Mill, Dissertations and Discussions: Political, Philosophical, and Historical, Vol. IV, Boston: William V. Spencer, 1867, pp.171-172.因此,密尔从“文明国家”观念出发,认为国际规则不适用于“野蛮民族”,西方列强有权干涉“野蛮民族”的事务。
19世纪的国际法学者在讨论国际关系和国际权利时,对“文明国家”的阐述比政治思想家们的表述更加具体和趋于实用。他们提出,“文明国家”构成一个“国家大家庭”(family of nations,后来英国学派称之“国际社会”),国际法只适用于这个“国家大家庭”中的成员,“非文明国家”要加入这个集体,必须首先成为“文明国家”。这实际上是将政治思想家们提出的“文明”标准运用于现实中的国际关系,提出了一种“国际社会”准入的“文明”标准。例如,英国法学家托马斯·厄斯金·霍兰德在1886年的《法学原理》中明确提出:“‘国家大家庭’是一个由众多国家组成的集合,这些国家由于其历史传统而继承了一种共同的文明,在道德和政治观点方面也处于相似的水平。这个术语可以说包括了欧洲基督教国家及其在美洲的分支……根据国际法理论,这个排外性圈子里的所有国家都是平等的。圈子之外的国家都不能被看作是正常的国际法人。”(5)Thomas Erskine Holland, The Elements of Jurisprudence,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886, p.322.可见,霍兰德借助对“国家大家庭”这个“排外性圈子”的阐述,把“文明国家”具体界定为“欧洲基督教国家及其在美洲的分支”,其他国家都不具备“正常的国际法人”资格。拉萨·奥本海在1905年出版的《国际法》中,明确提出“国际法是指文明国家在相互交往中那些被认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习惯和常规的总称”。(6)L. Oppenheim, International Law: A Treatise, Vol. 1,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05, p.3.英国法学家詹姆士·洛里默在1883年出版的《国际法概要》中,明确将整个人类社会根据文明程度分为三种情况:“作为一种政治现象,人类在其目前状况下将自己分为三个同心区域或范围——文明人类区、野蛮人类区和蒙昧人类区……按照法律都属于由文明国家承认的三个阶段——完全的政治承认、部分的政治承认和自然的或仅仅作为人类的承认。”(7)James Lorimer, The Institutes of the Law of Nations, Vol. 1, Edinburgh and London: 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 1883, p.101.他接着解释了这三种国际承认的范围:完全政治承认的范围,包括全部欧洲国家及由欧洲移民构成的殖民地附属国;部分政治承认的范围,包括波斯、中亚的独立国家、中国、暹罗和日本;世界其余地区属于自然的或仅仅作为人类承认的范围。他认为国际法学家只需处理第一个范围的国际事务,没有义务将国际法适用于蒙昧人或野蛮人。
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欧洲思想家和法学家们所谓的“文明”,是基于欧洲文化传统和欧洲历史经验的“文明”,布鲁斯·马兹利什(Bruce Mazlish)称之为“欧洲意识形态”和“殖民意识形态”。(8)参见[美]布鲁斯·马兹利什:《文明及其内涵》,汪辉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然而,以这种“文明”程度不同来处理国际关系和划分国际权利的思想,成为19世纪欧美国际法学界的普遍观念。这样,在欧洲“文明”话语影响下,世界按“文明”标准被划分成了文明和非文明(蒙昧和野蛮)两个部分,或者文明、半文明、蒙昧或野蛮三种类型的国家或民族,只有“文明国家”是国际社会成员并享有国际法权利,由此形成了两种性质不同的国际关系:文明国家之间的关系、文明国家与半文明或野蛮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显然,由这些关系构成的是一个以“文明国家”观念为基础的不平等国际体系。阿米塔·阿查亚和巴里·布赞称之为“西方-殖民主义全球国际社会”,“主要特征是特权中心和附属外围之间层次分明,特权中心适用一组规则,附属外围则适用另一套规则”。(9)[加]阿米塔·阿查亚、[英]巴里·布赞:《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第19页。可见,19世纪西方有关国际关系的思想,实际上是西方列强相互争霸和进行殖民扩张在知识建构层面的反映,明显打上了欧洲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烙印。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9年巴黎和会后,以“文明”为标准的等级制国际秩序虽然受到“民族自决”观念的冲击,但未得到根本改变。1945年之后,随着殖民地民族独立和新兴国家建立,联合国框架下的各国均成为国际社会的合法成员,这就终结了以往殖民主义世界体系中被“文明”标准排除在国际法之外的“殖民”关系。但“文明国家”观念在战后国际关系理论中并没有消失。1945年6月26日通过的《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c款中仍称国际法院裁判时应适用“文明国家所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10)刘颖、吕国民:《国际法资料选编(中英文对照)》,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438页。当然,国际法学界也开始了对“文明国家”观念的反思。1949年5月19日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在起草《国家权利义务宣言草案》第三读时,有人提出应避免使用“文明国家”这一表述,委员会主席最后同意了这个提议,表示“不应使用‘文明国家’一词”。(11)United Nations, Year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1949, New York, 1956, p.170.1955年,H.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8版,将国际法定义修改为“国际法是指各国在相互交往中那些被认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习惯和条约规则的总称”,(12)L. Oppenheim, International Law: A Treatise, Vol. 1, H. Lauterpacht ed.,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55, pp.4-5.删除了句中“国家”前的定语“文明的”。由上可见,19世纪镶嵌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和国际法中的“文明国家”观念,以及它对国际关系实践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叶。不过,在20世纪下半叶,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显性“文明”标准虽然在现实国际政治中出现了退潮,但有关“文明国家”和“文明标准”的思想,作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渊源之一,并没有被西方国际关系学界遗忘,而是通过对“文明标准”的讨论出现了“回归”,并得到新的阐发。
关于“文明标准”的讨论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政治学界关于“文明”问题的探讨,基本上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是以英国学派为主的一些学者围绕国际关系中的“文明标准”展开讨论,二是一些学者对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进行回应,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国际关系中的“文明”问题。
国际关系理论的英国学派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他们认为,源于17世纪威斯特伐里亚体系的欧洲基督教国家形成了一个“国际社会”,它随着欧洲的扩张而不断扩展,并在19世纪明确形成了将广大非西方国家排除在这个“国际社会”之外的“文明”标准。因此,“文明标准”成为英国学派讨论“国际社会”扩展的一个重要概念。(13)如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亚当·沃森(Adam Watson)1984年主编的《国际社会的扩展》和亚当·沃森于1992年完成的《国际社会的演进》,都考察了欧洲国际社会形成及其发展成为全球性国际社会的历程中“文明标准”扮演的角色。参见[英]赫德利·布尔、亚当·沃森:《国际社会的扩展》,周桂银、储召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英]亚当·沃森:《国际社会的演进》,周桂银、王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版。其中,江文汉在1984年出版的《国际社会中的“文明”标准》是英国学派讨论“文明标准”的代表作,不仅从理论上探讨了“文明标准”的内涵、出现及其与国际法的关系,而且还从“文明标准”视角考察了中国、日本、暹罗等国进入“国际社会”的历程。
江文汉认为“文明标准”有助于界定19世纪“国际社会”的内部身份和外部边界,也承认非欧洲国家在被迫接受“文明标准”时经历了“文化的屈辱、错位和调适”。但他把欧洲强加“文明标准”给非欧洲国家视作“文化体系的对抗”,是“无法调和的‘文明’标准的冲突”,认为“从非欧洲国家的角度来看,该标准既是一个指导方针,也是一个改革的促进因素”。这一看法似乎有为“文明标准”辩护之嫌,不仅以“文明冲突”论掩盖欧洲扩张的本质,还声称这种标准“指导”和“促进”了非欧洲国家的“改革”。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相信“某种文明标准仍将是任何国际社会的一个特征”。(14)Gerrit W.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pp.xi, 239, 248.赫德利·布尔也反思性地认为19世纪的“文明标准”是一个“名声不好”的概念,“如今在我们看来是不公正的统治和剥削制度的一部分,亚洲和非洲人民有权反抗这种制度”。而他也为之辩护:“在20世纪的进程中,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列强明显地未能遵守他们在19世纪为自己和他人宣布的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标准本身是错误的,也不意味着我们今天不需要这些标准。”(15)Hedley Bull, “Foreword”, in Gerrit W.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p.viii, ix.
江文汉和布尔对“文明标准”的矛盾论述,表明处于20世纪下半叶西方霸权衰落和第三世界兴起这一大变局时代的英国学派,在反思“文明标准”具有殖民霸权一面时,又抱着难以割舍的心情希望这一标准延续下去。这实际上反映了英国学派面临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国际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如何重新阐发传统的“文明标准”并使之适用于变化了的国际关系?从有关著述来看,英国学派对“国际社会”变化的理解,开始从以国家主权为中心的多元主义,转向强调人权的社会连带主义,试图通过强调人权、民主、发展、善治等价值观,确立起“新文明标准”。例如,文森特在1974年的《不干涉与国际秩序》以及1986年的《人权与国际关系》中的观点变化,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在《人权与国际关系》中,文森特在承认尊重国家主权的同时,提出个体作为一个独立于国家的行为体,享有作为人类一员的“基本权利”,国家必须尊重和保护这一权利。如果它受到国家的严重侵犯,国际社会就可以进行人道主义干涉。(16)See R. J. Vincent,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由此,“人权”逐渐成为国际关系中“新文明标准”的一个重要因素。
1998年,美国学者杰克·唐纳利发表文章《人权:一种新的文明标准?》,认为“文明标准”在国际社会中具有延续性,“对文明行为的呼吁一直是19世纪和20世纪国际关系的一个不变的特征”,而“人权”为当代国际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包容性标准”。(17)Jack Donnelly, “Human Rights: A New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74, No.1, 1998, pp.1-23.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人权”标准具有塑造国家身份和国际政治空间的作用,亦即可以通过“人权”标准来划分国际阵营和排斥异己。美国学者大卫·菲德勒则在2001年明确提出了“文明标准的回归”,认为19世纪欧洲的“文明标准”有助于将一个文明多样性的世界转化为一个“以西方的规范、规则、制度和价值观为特征的威斯特伐里亚文明。它的回归标志着威斯特伐里亚文明有可能转变为自由的、全球化的文明”。(18)David P. Fidler, “The Return of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2, No.1, 2001, p.139.显然,他提倡“文明标准的回归”,就是要把“威斯特伐里亚文明”发展成为“全球化的文明”,以源于“威斯特伐里亚文明”并代表西方价值观的“新文明标准”来规范当代世界。澳大利亚学者布雷特·鲍登(Brett Bowden)在2009年《文明的帝国》一书中,虽然批评欧洲“传统文明标准”是“自诩为‘文明’的民族对‘不文明’的民族强加的一种法律和政治工具”,但却赞同“复兴”文明标准,并提出要不断提高修订后的新文明标准,“包括人权与法制、代议制民主治理、允许开展国际贸易并对外资持开放态度的自由主义经济和自由市场、宗教与文化多元主义以及高效能的科学与技术水平”。(19)[澳]布雷特·鲍登:《文明的帝国:帝国观念的演化》,杜富祥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59—160、233—234页。无疑,这些标准仍主要基于西方价值观。正因如此,他也像杰克·唐纳利那样,把“文明标准”当作影响国际关系实践的重要工具,主张以此区分不同的国家然后进行排斥或胁迫遵守,使一些国家基于西方理想的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而组成“国际社会”。(20)Brett Bowden, “To Rethink Standards of Civilisation, Start with the End”,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2, No.3, 2014, pp.614-631.荷兰学者塔尼娅·阿尔伯茨也认为,国际法中始终隐含一个根深蒂固的“文明标准”,它并没有因为当代世界倡导主权平等而消失。它作为一种国际权力工具,具有生产性力量,即通过它可以创造出新的“国际社会的成员”。(21)Tanja E. Aalberts, “Rethinking the Principle of (Sovereign) Equality as a Standard of Civilisation”,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2, No.3, 2014, pp.767-789.巴里·布赞也在2014年的一篇文章中,对“文明标准”作为英国学派的一个重要概念进行了回顾,提出如何将其从一个19世纪具有欧洲中心论的古典概念,发展成为一个21世纪基于现代性定义的新概念,包括人权、民主、资本主义、环境保护、发展等新形式。(22)Barry Buzan, “The ‘Standard of Civilisation’ as an English School Concept”,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2, No.3, 2014, pp.576-594.
由上可见,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对“文明标准”的讨论,都没有脱离19世纪西方传统“文明标准”这一思想渊源。尽管他们当中一些人对19世纪西方“文明标准”有所反思或批评,但大多数人对当今国际社会中“新文明标准”的设想,主要基于西方传统“文明标准”的“回归”或“复兴”,把“新文明标准”看作是西方传统“文明标准”在全球化时代的延续和发展,其中以西方价值观来衡量的“人权”成为主要标准。因此,他们的有关讨论未能摆脱西方视角的局限,仍然是从西方文明来看待世界并将其价值观强加于非西方国家。
围绕“文明冲突”论的争鸣
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杂志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提出冷战结束后世界面临的危险将主要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1996年,亨廷顿出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自己的观点作了进一步补充扩展,全面阐述了所谓“文明冲突”论。他把“文明”看作文化实体,认为冷战后的全球政治是多极的和多文明的,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将其引向与其他文明(尤其是与伊斯兰和中国)的冲突。(23)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由此可以看出,亨廷顿基于本质主义的文明观,以现实主义的权力关系来思考文明间关系,并在“文明—野蛮”二元对立和冷战思维的影响下,得出了“文明冲突”的结论。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冷战思维的延续,试图为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寻找或制造一个新的假想敌以取代苏联的位置,而这个假想敌是代表儒家文明的中国,或者是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联盟。
国际政治学界许多学者对亨廷顿的观点进行了回应,由此推动了对国际关系理论中“文明”问题的讨论。
有一些西方学者部分认同亨廷顿的观点并提出了修正。例如,美国学者唐纳德·J.帕查拉也将文明视为“文化实体”,并认为文明具有生命周期,经历了从早期发展到充分发展的“成熟文明”,探讨文明间关系要考虑到文明处于的不同发展阶段。由此他提出了成熟文明之间必然发生冲突的观点,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修改成了“成熟文明的冲突”,并表现出对现实世界中文明间关系的忧虑:“如果历史可以阐明未来,那么21世纪的世界很可能充斥着成熟文明,而且从历史上看,这可能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情况。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成熟文明之间的相遇在推动人类走向更高的道德成熟或文化融合方面并没有什么成效。一些成熟文明之间的相遇是悲剧性的。”(24)Donald J. Puchala, Theory and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141.
总体上看,亨廷顿的观点受到国际关系学界的广泛质疑与批评。有的学者借鉴后殖民理论解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例如,英国学者马克·索尔特(Mark B. Salter)通过梳理西方历史上“野蛮”与“文明”二分的传统及其话语,指出这种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观点在亨廷顿的著作中仍然有所体现:“在西方与其他这一范式的具体化上,亨廷顿再次运用了‘两个世界’的二分法。即使世界其他部分是多样性的,它也是根据二元结构来进行界定。亨廷顿把文明/野蛮论用到了这种区别上。他用野蛮成见定势来描述‘其他’文明,认为其他文明是非理性,原教旨主义和倾向于暴力的,这种观念自19世纪以来就一直流传着。他把西方看作是惟一真正‘开化的’(‘发达的’)文明。”(25)[英]马克·B.索尔特:《国际关系中的野蛮与文明》,肖欢容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82页。
有的学者借用社会学理论阐述文明间关系,以此批评亨廷顿的文明本质主义观点。例如,美国学者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持一种建构主义的多元文明观,认为“文明”并非一种文化实体,而是兼具属性和话语的基本模式,可以描述为一种“组合体”或“复合体”,并且是多元和多维的。他提出:“文明是动态的,是充满内部政治论争的”,“多元性和多维性这两个概念是对当今文明政治的最好概括……如果真有文明冲突的话,这种冲突更易于发生在文明内部而不是文明之间,这与亨廷顿的理论是大相径庭的。”(26)[美]彼得·卡赞斯坦主编:《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秦亚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4、42—43页。瑞典学者马丁·哈尔和美国学者帕特里克·撒迪厄斯·杰克逊认为,亨廷顿简单地把世界划分为具有本质差异且相互排斥的不同文明,表现出一种本质主义的文明观。而他们主张从非本质主义视角来考察国际关系中的文明,将文明看作一个持续的过程,建议“停止把文明当作结构或事物来思考,而开始把它们当作过程和关系来思考”。(27)Martin Hall and Patrick Thaddeus Jackson, Civilizational Identity: Th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Civiliza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8.加拿大学者罗伯特·考克斯也反对将文明视为实体,提出文明是物质生存条件和主体间意义之间的契合,在一个多文明的世界中,世界组织的作用是从作为文明组成部分的不同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中寻求一种超主体性,以此为多文明的世界秩序提供某些共同原则。不过,他在谈到如何寻求通过不同文明中的公民社会达成“对基本人权的一致理解”时,其思路便体现出了西方霸权思维。“在一个多文明的秩序中所面临的挑战是,寻找方法以鼓励民众力量在‘他们的’社会中为巩固人权而斗争,而不显得是将一种文明的规范强加给另一种文明。一个外部强加的秩序将仍然是脆弱的,容易被指控为帝国主义。”(28)Robert W. Cox, “Thinking about Civiliz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6, 2000, pp.217-234.的确,如何以“人权”名义干涉他国内政而又不被指责为“帝国主义”,是西方国家所面临的“挑战”。
在回应亨廷顿的观点中,以“文明对话”取代“文明冲突”是国际政界和学界许多人的共识。1998年,伊朗总统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倡导通过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以避免国际冲突,并在第53届联合国大会上提议2001年为联合国“不同文明间对话年”,这一提议得到采纳。为构建文明对话理论,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组织来自19个国家的20位学者合编了《跨越鸿沟: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一书,强调文明对话有助于建立新的国际关系范式,联合国对于促进文明对话具有重要作用。(29)See Giandomenico Picco, eds., Crossing the Divide: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South Orange: Seton Hall University, 2001.基于此,意大利学者法比奥·佩蒂托把“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作为世界秩序的一种替代模式”。(30)See Fabio Petito, “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 as an Alternative Model for World Order”, in Michális S. Michael and Fabio Petito, Civilizational Dialogue and World Order: The Other Politics of Cultures, Religions, and Civiliza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p.47-63.美国学者弗雷德·达尔迈尔发掘西方传统思想资源以思考文明对话,一方面从理论上讨论了文明对话的含义及意义,另一方面考察了不同历史时期和各种文明背景下文明内部和文明之间对话的具体例子。(31)See Fred R. Dallmayr,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Some Exemplary Voic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另外,德国学者哈拉尔德·米勒(Harald Müller)和保加利亚学者亚历山大·利洛夫(Александър Лилов)等人也从“文明共存”与“文明对话”视角批评了“文明冲突”论。(32)参见[德]哈拉尔德·米勒:《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郦红、那滨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保]亚历山大·利洛夫:《文明的对话:世界地缘政治大趋势》,马细谱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由上可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以“文明”为文化实体甚至是国际政治中的行为体,强调文明间的本质差异与冲突,是后冷战时代美国为了维护霸权、强化西方文明认同而建构起来的一套话语,它建立在想象和“预言”的基础上,缺乏历史和事实的依据,因而受到西方国际关系学界一些人的批评。然而,这些学者虽然不赞同“文明冲突”论,但未摆脱西方话语和西方思维的影响,其思想资源和理论基础仍然来自西方,例如达尔迈尔关于文明对话的思考主要来自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人的思想。因此,他们对国际关系中“文明”的阐述仍然是西方视角的,或者说阐述的仍然是“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尽管他们批判并解构了亨廷顿的观点,但对“文明”理论的建构却显不足,缺乏具有说服力的理论取代亨廷顿的观点,这是“文明冲突”论在现实国际政治中一直具有影响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基于中国视角的反思
为何冷战后的西方国际政治学界出现了关于“文明”问题的热烈讨论?一方面,冷战后的国际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重新获得了世界的主导权,乐观的“历史终结论”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西方国家的心态。他们相信,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又回来了,他们有责任为“新世界秩序”规划制定一个“21世纪的文明标准”,这是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热衷讨论“新文明标准”的重要影响因素。伊朗裔丹麦学者迈赫迪·莫扎法里曾指出,冷战后的西方国家“找到了一种新的自信”,他们不仅要求国家之间要以“‘文明’的方式”相待,“还要求国家对自己的公民(各种少数群体:宗教的、种族的、世俗的等)采取文明行为,因此在经典的文明标准中加入了一个新维度(人权)”。(33)Mehdi Mozaffari, “The Transformationalist Perspective and the Rise of a Global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1, 2001, pp.247-264.另一方面,冷战后的世界也是一个国际力量平衡被打破之后动荡不安的世界,冷战掩盖下的许多矛盾和问题暴露了出来。同时,全球化的加速及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也促使了文化和身份认同意识的强化。这样,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第三世界内的国家、种族、民族、部族之间,矛盾和冲突有所上升。这在一些西方人看来,既是世界政治中“文明的冲突”,也是第三世界国家中“文明的倒退”。例如美国记者罗伯特·卡普兰的著作《正在来临的无政府状态:打碎后冷战时代的梦想》,就以西非国家为典型描述了一个充斥着贫困、疾病、犯罪、暴力的非西方世界,而另一面则是一个发达的西方世界。(34)See Robert D. Kaplan, The Coming Anarchy: Shattering the Dreams of the Post Cold Wa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0.这实际上类似于西方传统上把世界分为“文明”与“野蛮”,其间的矛盾也就变成了不可避免的文野冲突。因此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仅在西方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不乏赞同者,在美国政界也不乏支持者,尤其是9·11之后美国开展“反恐战争”及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 Bush)的一些言论,似乎“验证”了亨廷顿的“预言”。
然而,从前述西方学界关于“文明标准”和“文明冲突”的讨论可以看出,西方国际关系学中的“文明”理论,存在两个明显的缺陷。首先,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无论是主张“文明标准回归”还是“文明冲突”的学者,他们思考和阐述文明间关系的共同出发点,就是基于近代以来欧洲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的西方文明优越论。正是抱持西方文明优于其他文明的看法,以英国学派为代表的一些人才会把当代国际社会视为19世纪欧洲国际社会的延续和扩展,才会把当代全球化文明视为威斯特伐里亚文明的转型,才会把他们当下构想的“新文明标准”看作是欧洲传统“文明标准”的回归与复兴。同样地,也正是基于欧洲扩张的历史经验和对西方文明优越地位丧失的担忧,以亨廷顿为代表的一些人才会将其他文明的发展视为对西方文明的威胁,而大肆渲染“文明冲突”,以此维护西方文明霸权。其次,对“文明”持本质主义的看法。“文明”作为国际关系学中一个思考问题的范畴,有助于我们从国家行为体之外的其他维度来理解和阐释国际关系。然而,亨廷顿等西方学者却把“文明”当作“文化实体”,将其属性本质化,由此将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矛盾解释成“文明冲突”。英国学派在阐述国际社会中的“文明标准”时,也存在本质主义倾向。他们把“人权”当作一种西方价值观下个体享有的绝对权利状态并将其普遍化,而不是把“人权”视为不同社会条件下与其社会状况相一致而呈现出来的个体相对生存状态,因而否定了人权的社会相对性和人权文明的多样性,作为国际社会中“新文明标准”的“人权”,也就成了在本质上具有西方文明特性和价值观的人权。
当代国际政治的实践表明,西方国际关系学中具有西方中心主义和本质主义倾向的“文明”理论,难以合理地解释国际政治中的文明间关系,由此也不可能构建起一种不同文明间平等、和谐、共生的国际新秩序。
当然,一部分西方学者也看到了上述不足,并由此进行了反思。例如,澳大利亚的滕娜·祖瓦拉从资本主义与文明的关系入手讨论“文明标准”,认为西方人对“文明标准”的排斥与包容表现出相互矛盾的立场,即一方面反对非西方国家被平等地纳入国际社会,另一方面又表示可以有条件地接纳,条件是非西方国家必须进行改革以确保其符合西方标准。因此“文明标准”在实践中表现出排斥和有条件的包容之间的矛盾。(35)See Ntina Tzouvala, Capitalism As Civilisation: 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近年来,随着全球史的兴起,一些学者也试图突破西方视角的局限,从全球视野出发思考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文明”。例如,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和巴里·布赞等人主张由不同文明背景的学者参与构建“全球国际关系学”,从而避免这门学科中的西方中心论,“使国际关系学适应一个业已全球化的、深度多元化的、后西方的世界”。(36)[加]阿米塔·阿查亚、巴里·布赞:《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第292页。约翰·M.霍布森将全球史视角和方法运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指出近代西方文明是在大量借鉴和吸收东方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谓“先进的”西方,实际上是“东方化的西方”,他进而批评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文明的捍卫者,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构建。(37)See John M. Hobson, 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s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The Eurocentric Conception of World Politics: Western International Theory, 1760-201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不过,西方学者在反思“西方中心论”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超越自身的知识结构和思考视角?有学者对此表示了怀疑。(38)董欣洁:《难以超越“欧洲中心论”的西方通史类全球史》,《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6月24日。本文的考察也表明,尽管一些西方学者对19世纪以来的“文明标准”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持批评态度,甚至其中不乏具有建设性的观点,但对相关理论阐述仍然不同程度地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西方文明优越论以及“文明冲突”论思维,仍然充斥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与西方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文明”观及其思维方式有关。西方“文明”观的形成与其“他者”观念密切相关。古代希腊人将外族视为“蛮族”的观念,奠定了后来西方“文明”观中“文明-野蛮”对立思维的历史文化传统。而犹太教和基督教中的一神信仰,强调信徒与“异教徒”之间的身份差异和对立,进一步强化了西方文明观念中的“文野”二元思维方式,以致到19世纪“文明”概念在西方流行之时,很快发展成为一种“文明—野蛮”话语和文明等级观。这种“文明”观影响下的思维方式,将“文明”的西方与“野蛮”的非西方区分开来,形成一对孪生概念范畴,由此造成西方学者潜意识中的西方文明优越论和西方中心论,将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对立起来。对此,秦亚青指出:“如果我们看一下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如古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为代表的权力理论、文明冲突理论,以及英国学派所代表的社会理论,这种冲突性思维几乎无处不在。”(39)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8页。因此,西方学者在讨论国际社会中的文明间关系时,往往以西方文明为“标准”,它与非西方文明的关系也就成了非此即彼的“冲突”关系。
由上可见,要正确阐述国际政治中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关系,避免西方文明优越论和西方中心论,仅仅由西方学者对以往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反思是不够的,需要由具有不同文明背景的非西方学者参与到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中。重视非西方视角和非西方思想,倡导尊重不同文明的传统和价值,对于构建“全球国际关系学”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新西兰学者罗比·西利亚姆曾批评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对非西方思想的忽视,指出“非西方思想可以为现代世界秩序的空间建构提供新视角”。(40)Robbie Shilliam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Non-Western Thought: Imperialism, Colonialism and Investigations of Global Modern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p.24-25.的确,非西方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亚洲国家,可以为发展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
在先秦儒家的文明观中,“中庸”与“和谐”是重要内涵,而将这些思想运用于“天下”,便形成了一种处理对外关系的世界观和外交思想。因此,古代中国与周边各国及各民族的相处之道一直遵循着“和”的价值取向。《易经》中所说的“同人”,大概是中华文明中对“和同于人”价值观的最早表达。“同人”卦中说:“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41)王弼注,孔颖达疏,李申、卢光明整理:《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页。这表明,文明与刚健并行的中正之道,是一种和同于人的美德,君子由此能够通达天下之人的心志。关于这种思想,《礼记·中庸》里有更明确的表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42)郑玄注,孔颖达疏,龚抗云整理:《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2页。因此,“中”在儒家思想中被视为世界万物蕴含的一种终极目的,而“和”便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普遍法则,通过“致中和”,就能实现世界万物的秩序井然和繁荣昌盛。当把这些主张运用于人际和国际关系时,便有了《论语·子路》中“君子和而不同”和《尚书·尧典》中“协和万邦”的思想。因此汤一介认为,“儒家思想中的‘普遍和谐’观念无疑将会对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作出特殊的贡献”。(43)汤一介:《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哲学研究》1994年第3期。
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中庸”与“和谐”的思想,不仅体现了一种有别于西方的文明观,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世界的“中庸之道”——一种不同于西方二元对立思维的包容式思维方式,秦亚青称之为“中庸辩证法”。他说:“在国际关系领域,从诸多主流理论可以看出,西方的思维方式更多地建立在黑格尔冲突辩证法的基础之上。而中国虽然经过了与西方互动的动荡过程,但中国人基本的思维方式依然更多地建立在中庸辩证法的基础之上。”(44)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第79页。正因为如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构建不同文明和谐共生的国际新秩序而言,不仅提供了创新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资源,也为建构这种国际新秩序指明了可能的实现途径。因为它从思维方式上化解、克服了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由西方文明视角造成的困境和局限。例如,中国古代在“中庸”与“和谐”基础上形成的“天下”观,就体现了一种不同于西方文明的世界观,由此出发来阐释当今世界不同文明间的关系,有可能克服西方文明视角的局限而构建起一种具有包容性的和谐国际关系和“全球国际关系学”。赵汀阳认为,在西方思想中,即使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及其当代变形版“民主和平”理论,也无法应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因为其提倡的和平有效条件是“同质国家”(或者说所谓“民主国家”)之间的国际联盟,将那些在文化、价值观和制度上异质的国家排除在外了,而中国的“天下观”所蕴含的“天下体系”思想,则能够为世界“提供共存基础的新普遍主义,一种‘兼容的普遍主义’,以普遍有效的关系去兼容和协调各种不可归化的异质价值观和文化,在协调合作的关系中,各种异质文化仍将是异质的,但普遍的兼容关系可以有效抑制相互冲突……因此,天下体系被设想为一个能够解决康德理论所不能解决的亨廷顿问题的永久和平理论。”(45)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再版序言”,第2页。
结 语
19世纪欧洲知识分子赋予“文明”以西方价值观并将其运用于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使“文明国家”观念及其标准在西方霸权下成为服务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由于这种具有价值取向的政治化“文明”概念为当代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所继承,使得他们所讨论的“文明标准”带有强烈的西方价值观取向,也无法全面反思和批评“文明冲突”论。
基于此,从中国视角出发,强调中国学者参与到国际关系学的理论构建,克服单一西方文明视角的局限,剥去国际关系理论中附着于“文明”之上的西方价值观外衣,从而构建有助于促进世界各国各民族和谐共生的新型国际关系理论,显得尤为重要,甚至可以说已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一项紧迫任务。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先秦时期形成的儒家思想蕴含着丰富的处理内政外交的政治智慧,并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得到传承。不仅如此,由于古代中国在东亚世界中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儒家思想中的中庸和谐之道是19世纪中叶以前维系整个东亚区域国际秩序的准则。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我们反思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构建一种体现“全球文明”和人类共同价值的“全球国际关系学”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这也意味着当代中国对于构建全球化时代尊重文明多样性和不同文明和谐共生的新型国际关系理论都大有可为。
总之,当代世界要构建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新秩序和“全球国际关系学”,需要在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消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西方中心论,要由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参与,通过文明对话和交流互鉴来实现。而在当代中国发展起来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建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相结合的基础上,有可能破解西方文明观中的“文明—野蛮”二元思维和“文明冲突”论,并且随着中国日益扩大的世界影响力,通过文明交流互鉴而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贡献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由此在实践上为推进构建一个不同文明和谐共生的国际新秩序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