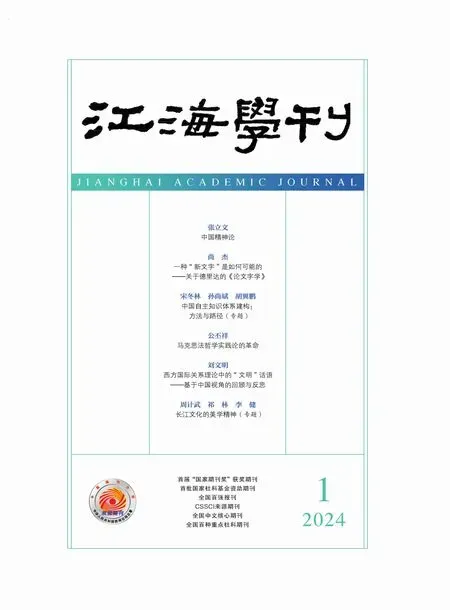生命尊严与法律权利范围的扩展*
朱 振
自二战之后,人的尊严或人性尊严已经成为法律和人权的价值基础。以后的相关学术讨论,关注的重点基本都在对“尊严”的挑战上。这些挑战包括二战中纳粹对人性尊严的系统性侵害,以及此后对人性尊严的各种社会性和制度性的侵犯。它们都属于外在挑战,催生了国家对人性尊严和基本权的保障义务。但现在我们日益面临另一类挑战,它们是来自科技的,指向了对“人”本身的挑战。与上述第一类挑战相比,科技尤其是和人体有关的科技(比如基因技术)的挑战则属于内在挑战,因为它指向对“人”本身的界定,触及对人和人的生命形态之法哲学意义的不同理解。这种挑战既是哲学上的,又是法律上的,而且前者构成了后者的基础。在哲学层面上,康德的尊严观,即以理性和自由为基础的人格理论,是突破这种挑战的障碍,因为在这种尊严观看来,不具有理性能力的人可能不是“人”。但同时它又潜藏着突破的契机,因为尊严的现代范式发展了康德的人性公式,把尊严改造为一种绝对价值,这又强有力地辩护了人的生命尊严。尽管这种主张绝对价值的尊严观不一定能够支持生命权意义上的法律主体,但其可以有效辩护法律权利保护范围的扩展。
传统/现代范式中的尊严观演变
在思想史上,尊严观有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大体上,我们可以区分出古代的尊严观与现代的尊严观,或称之为尊严的传统范式与尊严的现代范式。在传统范式看来,尊严意味着一种较高的位阶,或统治阶级中的较高位置,比如执政官或元老。这种尊严观和价值无关,人处于某个位阶并不意味着其在道德上匹配这个位阶。与上述范式相关,尊严的传统观念要解答的问题是:人在宇宙中的位置。
传统尊严范式的代表人物有西塞罗、大良一世、米兰多拉等。西塞罗认为,人比其他动物优越,因为人有思维,而且沉思培养了人类的心灵。这是说,与动物相比,人具有优越的地位。而根据米兰多拉的论述,即使人在宇宙中居于优越的地位,他也有可能堕落到低等的生活中,人有义务摆脱这种堕落。这就是传统尊严范式的双重意涵,我们也可因此将这种范式称为双重尊严论:第一,人由于具有一种自由或理性的能力而高于自然中的其他事物,这里的自由或理性的能力指向源始尊严;第二,道德性和充分实现我们的源始尊严相关,我们负有实现它的义务,即人对自身的义务。在这一阶段,尊严并不是普遍的,且尊严并不与权利相关,而是和义务相关。(1)[德]奥利弗·森森:《康德论人类尊严》,李科政、王福玲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227—240页。
当代的尊严观(或尊严的当代范式)变革了看待尊严的角度,尊严不仅和道德紧密相关,而且和权利关联起来。尊严的当代范式的核心主张是:人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具有一种固有的价值。当代范式的产生具有独特的背景,它来自对二战的反思。在这之前,尊严在思想史或法哲学上并不具有重要地位,甚至《世界人权宣言》也并未赋予尊严以特别重要的地位。可以说,这时尊严还不是人权和权利的基础。随后尊严在人权公约和各国宪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两份联合国人权公约都是从人的固有尊严来推导人权。尊严是人权和权利的基础(人因尊严而享有权利,其他人对其负有义务),现在几乎已成定论。可以说,直至20世纪中叶之后,基于纳粹暴行和对二战历史的深刻反思,尊严重新获得了理论和实践上的重视。(2)沃尔德伦指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自然权利观念声名扫地,但二战后在“人的尊严”这一新标签下轻而易举地复兴了。Jeremy Waldron, “Is Dignity the Foundation of Human Rights?”, in Rowan Cruft, S. Matthew Liao and Massimo Renzo, eds.,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Human Righ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126.
那么,对法哲学尤其是民法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康德尊严观属于其中的哪一种范式呢?对此,学界存在很大的争议,出现了两种对立的立场。一种以康德哲学专家科尔斯戈德和伍德为代表,认为康德尊严观预设了一种绝对价值;另一种以森森为代表,认为康德尊严观基本属于传统范式,尊严的现代范式在20世纪之前并不存在。根据森森的总结,传统尊严观的核心是:第一,尊严并没有被设想为一种独特的形而上学的价值,尊严对应一种较高的位置,而非固有的价值;第二,尊严有两层意涵(对应两个阶段),即源始的尊严及其实现;第三,尊严本身并不是权利的基础;第四,尊严主要关乎对自己的义务。(3)[德]奥利弗·森森:《康德论人类尊严》,第241—244页。经过对康德哲学文本的细致解读,森森认为,康德的尊严观是传统范式的,理由在于:第一,对康德来说,尊严指的是一种高度,而不是一种价值本身;第二,康德的尊严观包含两个阶段:一个源始的阶段和一个得到实现的阶段;第三,对于康德来说,尊严和义务相关,且尊严本身不产生权利;第四,康德主要用“尊严”一词来指对自己的义务。(4)[德]奥利弗·森森:《康德论人类尊严》,第244—257页。森森的这些看法招致了许多反对意见,当然他也明确说,其目的并不是要证明康德不持有现代范式,而是要表明,康德会理解并赞成尊严的传统范式。
无论如何,区分这两种尊严范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这表明:第一,尊严的现代范式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事情,即使康德的尊严理论可以孕育出尊严的现代范式,它也有着文本上的模糊之处以及传统范式的遗迹;第二,尊严在法律上(尤其是在人权公约和宪法上)具有重要地位是尊严的现代范式的标志,而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尊严在法律上并不具有重要地位。关于这两点,哈贝马斯有一个总结:“作为哲学概念,人的尊严早在古代就出现过,并由康德得出了其现今的含义,但它直到‘二战’结束后才进入国际法以及之后生效的各国宪法文本中,自相对较短的时间以来,它也在国际司法裁决中发挥核心作用。与此相反,作为法律概念,人的尊严观念既未曾出现在18世纪经典的人权宣言中,也没有出现在19世纪的法典中。”(5)[德]尤尔根·哈贝马斯:《欧盟的危机:关于欧洲宪法的思考》,伍惠萍、朱苗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3页。
生命尊严观对法律主体理论的挑战
综上可知,康德的尊严观带有传统范式的痕迹,而深受康德伦理学影响的德国民法典在某种程度上改造了康德的理论立场,实现了主体的普遍化,但也依然带有传统范式的痕迹。新的法律实践挑战了法律主体理论,我们需要改进对尊严的理解。
(一)法律主体的普遍化与固定化
拉伦茨认为,康德的人格主义伦理学深刻影响了那个时代法典制定者的精神世界。(6)[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邵建东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5—46页。这种影响是观念上的,也是制度上的,比如关于责任的规定。实际上康德的尊严或人格理论并不必然内在地支持人格的普遍化,因为他以理性能力为人格的属性,并不是经验意义上的所有人都具有这种属性。因此,根据康德的人格主义主体理论,人格有可能只属于特定的主体。从民法的制度实践来看,法律上主体的范围相较于康德哲学中主体的范围来说实际上已经扩展了,没有自由意志的人也是法律上的平等主体。这就是民法中关于权利能力的制度设计,它持有的是一种普遍平等主义理念。
在民法的制度构建上,普遍平等主义是通过权利能力来实现的。“权利能力”首见于《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18条,《德国民法典》将其发扬光大。权利能力具有两种功能:一是形式性的,相当于法律上的人格(主体地位),自然人和法人都享有;二是实质性的,体现了自然法“人生而平等”的思想。由此可见,虽然权利能力是一个规范上的形式概念,但也负载了一定的伦理内涵。(7)朱庆育:《民法总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79—381页。这种伦理内涵决定了权利能力虽然是法律制度的创造物(制度性事实),但也具有一定的先验性,实证法不可将其剥夺。朱庆育特别指出:“自然人的权利能力乃是人性尊严的内在要求,并不依赖于实证法赋予,毋宁说,实证法不过是将自然人本就具有的权利能力加以实证化,权利能力先于实证法而存在。”(8)朱庆育:《民法总论》(第二版),第383页。朱庆育还把这一点进一步诉诸康德关于“先天的权利”和“后天的权利”的区分,认为权利能力不是实证法所赋予的。实际上实证法是观念的规范化,权利能力的普遍化来自启蒙时代的平等观念,权利能力概念的发明及其实在法化只是落实了占主流地位的平等观念。拉伦茨等人更进一步地将这种无差别的平等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能力追溯到人性尊严:人性尊严有着相同的本质,所有人的生命、健康与人格自由发展具有同等的不可侵犯性。(9)Larenz/Wolf,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 9. Aufl., 2004, § 5 Rn. 7. 转引自朱庆育:《民法总论》(第二版),第383页。
法律主体的普遍化确实是对康德人格理论的一种改进,但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固化。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这限定了人在法律上存在的时间。根据权利能力理论,出生之前或死亡之后的“人”的存在形态都不是法律主体,不能以存在者自身的名义享有权利。这显然是以人的理性能力(人是自由、理性的存在者)为判断标准,在思想观念上同样受康德人格主义伦理学的影响。但现实中很多司法案例已经对这一界定模式提出了挑战,比如出生之前的存在者,如胎儿和冷冻胚胎,都被认为依然具有规范性法律地位。人的生命是一个逐步形成、延续的过程,划分一个必然的阶段来断定是不是法律主体,并是否从而享有权利、承担义务,这是武断的。这就需要我们改进对尊严的理解,即从具有等级性的人、到普遍的人再到人的生命本身,尊严的范围是不断扩展的。
(二)人的生命的连续性及提出的法哲学问题
人的生命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出生、死亡当然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之前和之后的人的存在状态都是没有法律意义的,否则很多现实的难题无法在理论上得到融贯的解释。对于这种生命的连续性,哈贝马斯指出:“在受精或细胞核融合与出生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界线,每一次这样的尝试或多或少都是武断的,因为从有机起源到有感知能力的生命再到个人生活的发展,其中充满了高度的连续性。”(10)Jürgen Habermas, The Future of Human Natu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3, p.32.于是哈贝马斯提出了“人的生命的尊严”这一概念,以与“人的尊严”这一概念相区分:“人的生命作为我们义务的参照点,甚至在它进入公共互动语境之前,就享有法律保护,而其自身无需成为义务或人权的主体……当然,我们出于胎儿本身而对他负有道德和法律的义务。而且,出生前的生命——尚未处于被赋予第二人称的先赋角色之阶段——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伦理意义上建构的生命形式具有一种不可或缺的价值。正是在这一方面,我们感觉有必要区分人的生命的尊严和法律赋予每个人的人之尊严——顺便说一句,这种区分也反映在我们对待死者的高度情绪化态度这种现象之中。”(11)Jürgen Habermas, The Future of Human Nature, p.35.
“人的生命的尊严”这一概念的提出,并不是要辩护比如胎儿(或更早期的冷冻胚胎)、婴儿是潜在的人,这一点无需辩护,因为它是一个生物学事实;而是要辩护人的生命本身具有重要的规范性地位,不能以随意的方式对待它。人格具有时间性,人的存在和延续不可能有一个绝对的起点和终点,不能认为出生之前或死亡之后的人的存在形态都是没有规范性意义的。德国哲学家施佩曼的看法是,“对于婴儿,我们绝不能说,他潜在的是人格……人格性不是一种发展的结果,而是一个发展的构成性的结构。永远不存在一个潜在的人格。人格是贯穿整个发展的,蔓延了整个时间的统一性”。(12)这是贺念在翻译施瓦德勒的一本书的译者导言中对另一位哲学家施佩曼理论的总结。参见贺念:《对“人的尊严”的追问与保障:从康德到德国宪法精神》,[德]瓦尔特·施瓦德勒:《论人的尊严:人格的本源与生命的文化》,贺念译,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译者导言”第14页。这些论述都表明,人格性是一个构成性结构,依据的是生命本身在时间上的统一性。但这一点需要哲学理论的证成,尤其需要考虑怎么解决康德尊严理论自身所面对的一个根本难题。
现代尊严观与人的生命的尊严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对尊严有一段有名的论述:“在目的王国中,一切东西要么有一种价格,要么有一种尊严。有一种价格的东西,某种别的东西可以作为等价物取而代之;与此相反,超越一切价格、从而不容有等价物的东西,则具有一种尊严。”(13)[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译,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3页。要理解这句话就必须先理解康德意义上的“目的王国”和“人格”的概念内涵。根据贺念的界定,人依赖于自由意志能够遵守自我立法,从而人自身成为目的;每个人都是如此,那么所有理性存在者的道德世界就是一个目的王国,这样的道德主体就是康德所理解的人格。(14)贺念:《对“人的尊严”的追问与保障:从康德到德国宪法精神》,[德]瓦尔特·施瓦德勒:《论人的尊严:人格的本源与生命的文化》,“译者导言”第4页。之所以存在人格和目的,就是因为人作为理性存在者能够摆脱自然律,从而具有尊严;其他物只具有交换价值,可以被通约或替换。
康德的论证遗留了两个难题:一是时间性(或经验性)难题,二是平等性难题。限于本文讨论的问题,下文重点论述第一个难题。时间性难题起因于人的经验性存在,即人(Mensch)和人格(Person)并不具有统一性。正是人格界定或规定了尊严,那么有些人或人在某些情形下就可能没有尊严,因为他(们)不拥有理性能力从而不能满足人格的条件。理性能力的欠缺来自人是一种经验性、时间性、生物性的存在者,而康德的人格理论却是纯粹理论的建构,二者之间出现不匹配是必然的。贺念指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理性能力,比如胎儿、婴儿、精神病患者等;而康德的整个尊严思想都建立在人的纯粹理性能力上,这样就会产生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即“一旦康德承认某些人不具有人格,而人格又是尊严的基础,从而就必将推导出:某些人是不具有尊严的”。(15)贺念:《对“人的尊严”的追问与保障:从康德到德国宪法精神》,[德]瓦尔特·施瓦德勒:《论人的尊严:人格的本源与生命的文化》,“译者导言”第8页。根据前面的论述,不具有尊严的人就只有价格,只能作为手段而存在,而不是目的本身。
这是康德哲学自身遇到的难题。如果说民法就建立在这一套理论基础之上,那么民法中的主体的涵盖范围也会出现问题。根据学界的研究,可将不具备尊严的情形分为几种类型:第一类是人暂时失去理性,比如睡着或因医疗原因被麻醉;第二类是人尚未具备理性能力,比如胎儿、婴儿等;第三类是人因疾病而(永久)失去理性能力,比如身患老年痴呆等。(16)贺念:《对“人的尊严”的追问与保障:从康德到德国宪法精神》,[德]瓦尔特·施瓦德勒:《论人的尊严:人格的本源与生命的文化》,“译者导言”第8页。其实我们还可以往其中加入好几种新出现的不具有理性的存在者,比如因辅助生殖技术而产生的冷冻胚胎,可被归入第二类;死者可被归入第三类,因为其都属于曾经具有理性能力,但现在都失去了。
因人的存在的经验性而被提出的这一难题,可以被归结为一种时间性难题,即需要面对如下几种情形:在某个时间内暂时失去理性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具备完全理性能力、曾经具有理性能力而现在永久地失去了。当然并不是其中的所有情形在法哲学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冷冻胚胎、基因编辑、死者名誉权等难题的解决,都要依赖在理论上彻底解决康德尊严理论面临的上述难题。只有解决了这一哲学难题,才能在根本上解决民法学上所面临的难题。
面对这个难题,德国哲学家罗伯特·施佩曼提出了一个系统的解决方案,其核心思想是所有人都有人格。施佩曼认为,对人格的承认是一种无条件的承认,这就表明实践真理是被承诺的,而不是被证明的。实际上施佩曼就取消了理性在人格中的地位,因为理性还是一种属性。不能说,只有拥有这种属性才有人格;而是说,只要是人就有人格。这里的“人”是生物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于是施佩曼的结论是,一种“人”的存在形态只要在生物性上归属于人类这个家族,便拥有人格。因此,“人格”是在人类共同体中被承认的概念。
施佩曼的理论是对人格与尊严学说的一个很有意义的发展,能够有效回应生命伦理学对法理学或民法学的挑战,尤其是能够突破传统民法理论对法律上的人的理解和界定。民法严格坚持人/物二分,即一个存在者不是人就是物,很难赋予一些有争议的存在者(冷冻胚胎、胎儿、死者、动物等)以规范性地位。即使有相关规定,它们也只是在不动摇人/物二分的基础上作出的一些例外规定,比如关于胎儿权利的规定。施佩曼的尊严理论实际上是关于人的生命的尊严理论,宪法学与民法学虽然也把尊严人格平等化或普遍化了(即权利能力一律平等),但对人的理解也不会迈向对人的生命的理解。民法上的人是一种受到严格时间限制的“生物人”,即始于出生,终于死亡。因此严格来说,这一标准既不是以理性能力为标准,又不是以人格的某种属性为标准,也不是以“生命或人格共同体”为标准,因为它武断地消除了人在出生之前和死亡之后的存在意义。
作为价值的尊严与法律权利的扩展
现代尊严观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人的尊严的时间性难题,但适用于新科技下的法学领域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改进。由此,下文先概述主张绝对价值的现代尊严观的基本理论,然后再提出本文的反思与一个初步的解决之道。
(一)尊严的现代范式及其内在困境
在考虑尊严的谱系时,哈贝马斯指出,起初为身份差异而设置的尊严概念被悖论地普遍化了。也就是说,尊严这个概念一开始是与等级、身份等联系在一起的,而后来所发展出的普遍主义的尊严概念与前者是存在悖论的。因此,尊严观念的平等主义或普遍化是现代范式的核心内涵,解释这一普遍化的动因和过程就成为一个关键的课题。哈贝马斯认为,这一普遍化需要两个前提。一是“确立个体在人与人之间的横向关系中的价值,而不是‘人类’在与上帝或与低存在等级之间纵向关系中的地位”;二是确立每个人的无与伦比的价值,“以个人的绝对价值取代人类及其单个成员的相对优等性”。(17)[德]尤尔根·哈贝马斯:《欧盟的危机:关于欧洲宪法的思考》,第18页。绝对价值也是康德的哲学文本中明确提出来的,康德定言命令的第二条表达式是:“你要如此行动,即无论是你的人格中的人性,还是其他任何一个人的人格中的人性,你在任何时候都同时当做目的,绝不仅仅当做手段来使用。”(18)[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译,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第437页。这就是科尔斯戈德所总结的康德的“人性公式”。(19)Christine Korsggard, Creating the Kingdom of En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06-132.
把现代尊严范式应用到生命伦理学与法学领域,就需要坚持康德义务论伦理学。比如,施佩曼反对从理性主义解读康德的尊严观,因为这种解读会导致胎儿、婴儿、精神病人等不具有人的尊严。这一解读模式实际上等同于把尊严作为内在的和绝对的价值,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对人格的承认是一种无条件的承认。与此类似,另一位哲学家施瓦德勒还区分了对待生命的两种文化,即规范文化和实用文化,并把这两种文化与伦理学的两大传统对应了起来。规范文化对应着康德式的义务论伦理学,即某些原则是绝对要坚持的;实用文化对应着边沁式功利主义,也就是对生命进行目的/手段的衡量,只要收益足够大,没有什么原则是不可放弃的。根据这一区分,施瓦德勒描述了对待生命的两种态度或维度:“一方面是充分有效的人格的生命,这些人格必须受到相同的其他人格的尊敬和保护;另一方面则是一些人的生命不属于人格地带,而是能够当作一种被真正的人类生物支配的为了拯救、改良和构形生命而准备的‘原材料’。”(20)[德]瓦尔特·施瓦德勒:《论人的尊严:人格的本源与生命的文化》,第154页。前者相当于完全的人格主体,而且是相互平等的;后者作为原材料基本是工具性的,是为其他生命变得更好而被利用。施瓦德勒持有一种严格的义务论立场,即对人的生命的保护和尊敬是绝对的,不能将它们作为手段来使用。
显而易见,施佩曼和施瓦德勒的理论虽然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也能够为我们融贯地理解并解决一些法律难题提供有益的理论资源,但他们的立场都是比较激进的,他们几乎赋予胚胎等以完全的法律人格或主体地位,即认为生命的尊严具有康德意义上的绝对价值,各种生命形式不能以任何方式被工具性地利用。这实际上等于赋予了胚胎以生命权,从而面临着学理上和法律实践上的诸多困难。关于对人类胚胎等存在形式的法律保护,存在两种学说。一是生命权保护说,其主要认为,从受精卵、胚胎、新生儿到成年人,是一个连续的生命过程,人从受精卵开始就应该享有生命权。二是人性尊严说,其认为宪法与法律上的人性尊严原则应及于人出生之前的存在形态,包括体外胚胎。这两种学说显然存在交叉的情形,比如施瓦德勒就综合了这些学说,提出对生命权的保护正体现了人性尊严。但它们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即使有人赞同人性尊严原则溯及胚胎,但也不必然赞成生命权保护说,因为后者存在明显的学理与实践困境。
综合来看,生命权保护说的主要困境有:第一,从受精卵到完全意义上的人的产生,中间有一个较长的生命过程。在其中的不同阶段,这些生命形态与完全的人之间存在很大程度的差异,如体外胚胎与即将出生的胎儿差异很大。第二,统一的生命权保护说难以解决不同主体(比如母亲与胎儿)之间的权益冲突,这是最常见的一个反对意见。第三,基于以上两个理由,即使赋予胚胎以生命权,也不得不规定许多例外措施。而这样做其实违背了生命权的性质,因为生命权是全有全无式的,要么存在生命权,要么不存在,承认了生命权再规定诸多限制,这有违生命权的本性。第四,生命权说将使得一切关于体外胚胎的研究都不再可能,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生命科技的进步,而科技发展和公共健康也是一种重要的公共善。(21)邱玟惠:《“人类尊严”法学思维初探——从人类体外胚胎谈人性尊严之另一面向》,《台北大学法学论丛》2009年总第69期。
摆脱这些困境的一个可行方式就是在方法论上采取一种综合的进路,即放弃生命权或法律主体的思路,同时保留或改造尊严的概念,把尊严仅仅用在辩护胚胎等具有一种规范性地位上。这既可以消除因人性尊严保护的绝对性而产生的学理与实践悖论,又可以在另一种意义上辩护权利的存在。下文致力于探寻将人性尊严原则适用于人类胚胎等的合宜方式,并揭示现代尊严观的权利哲学意涵,而上文所讨论的强调价值的一系列尊严观也能找到其合理运用的场所。
(二)现代尊严观的权利哲学意涵
邱玟惠在探讨人类胚胎的人性尊严问题时,区分了“个人尊严”和“人类尊严”这两个不同的术语。前者和个体性的法律主体联系在一起,而后者确保了一种特定的人类形象,以免受与其尊严不符的侵害。邱玟惠认为,将人性尊严区别为“个人尊严”和“人类尊严”后,即使学界对体外胚胎的权利主体地位缺乏共识,我们也可用“人类尊严”的名义有效地保护体外胚胎。其中的要义是,胚胎享有人类尊严的地位,并不在于其作为权利主体而存在或受尊重,而在于应尊重人类不同于其他生物、不同于一般物的特性和本质。此外,这样来理解胚胎的人类尊严地位,还可对这种尊严与某些共同善(比如由科学研究自由所促进的科技进步)或其他主体权利等,进行法律意义上的衡量,而不至于因人的尊严的绝对性而陷入学理与实践的悖论中。(22)邱玟惠:《“人类尊严”法学思维初探——从人类体外胚胎谈人性尊严之另一面向》,《台北大学法学论丛》2009年总第69期。邱玟惠的主要目的是区辨不同种类的尊严,以赋予胚胎某种规范性地位,从而辩护我们对胚胎负有的义务。这里的“人类尊严”就是本文所使用的生命尊严,胚胎因分享了人类物种成员的身份而具有了规范性地位。但本文进一步认为,这种生命的尊严可以辩护胚胎等人类生命存在形式享有某些权利,即使它们不具有法律主体地位。
现代尊严观构成了人权和权利的基础,在人权话语中,人的尊严这一概念发挥着重要作用。从时间上看,人的尊严的出现要远早于人权或权利的出现,其中康德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尊严观。于是就有很多学者认为,二者之间不存在概念上的关联,只是出于对大屠杀的恐惧,才将人的尊严概念加到人权或权利的概念之上,并使其构成后者的理论基础。而哈贝马斯反对这一看法,认为二者自始在概念上就存在紧密关联:尊严是“所有基本权利内涵赖以汲取营养的道德‘源泉’”,“人权从一开始就被隐性赋予了某种东西:它在一定意义上就表达了人人具有同等的人的尊严这个规范性实质”。(23)[德]尤尔根·哈贝马斯:《欧盟的危机:关于欧洲宪法的思考》,第5、6页。哈贝马斯从尊严提供了道德源泉这一定位出发,深刻论述了尊严在人权或基本权利发展中的地位,以及在实在法(尤其是宪法)中的作用。他指出:“人的尊严好似搭起一个平台,道德的平等普遍主义内涵皆由此输入法律之中,人的尊严观念是概念的铰链,它将对每个人的平等尊重与成文法及民主立法联结起来。”(24)[德]尤尔根·哈贝马斯:《欧盟的危机:关于欧洲宪法的思考》,第10页。哈贝马斯的这一判断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尊严起到的是中介作用,“概念的铰链”联结了平等尊重与成文法。哈贝马斯的论述反驳了那种基于思想史的解释而认为尊严与权利之间不存在概念性关联的看法,从而建立了二者之间的价值性关联。那么,生命的尊严或人类的尊严能推导出什么权利呢?
埃德蒙森提到了一个扩张圈(expanding circle)的概念,即权利在范围上的扩展。(25)William A. Edmundson, An Introduction to Rights,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53.在埃德蒙森看来,能否将权利扩展到人类胎儿、永久昏迷的人等存在者,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去定义人权(或权利)。如果人权意味着“属于生物人(human beings)本身的那些权利”,那么这些存在者就享有权利。如果人权只是意指“由于生物人拥有某种重要特征和能力而典范式地归属于他们的那些权利”,那么上述存在者就不必然拥有权利或人权。(26)William A. Edmundson, An Introduction to Rights, Second Edition, p.154.根据第一种界定,胎儿或永久昏迷者等就可以拥有权利,因为他们属于生物人,尽管他们存在显而易见的能力缺陷。但根据第二种界定,他们就不必然拥有权利或人权,因为其显然缺乏某些典型特征。其实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以某种属性(比如能力、理性等)来界定尊严,那么与此相关的权利范围也会受到影响。二者在界定标准上存在相似之处,对尊严的理解和对人权或权利的理解在某种意义上是同构的,因为这些理解都会涉及对人本身的界定。
由此,可以对“尊严构成权利的基础”这一命题作一种更为普遍化和理论化的阐释,即取消“人权”(human rights)这个术语中“人”的要素的重要性,而更加突出“权利”要素的重要性。同时,尊严还能以另一种方式进入权利之中,比如尊严可能构成权利利益中的一种重要利益。埃德蒙森基本采用了这一进路,他着重指出了人权中的“human”所具有的方法论困境,即对于什么可以“成为人”(being human),不同的标准会导致不同的权利范围。比如,强调人的生物学意义,就会排除动物、人工智能体等拥有权利;强调人的行动能力,就会排除胎儿、精神病患者等的权利地位。于是埃德蒙森提出了从权利的角度来理解权利扩展的边界,这就是权利话语的承认功能。埃德蒙森对这种功能的界定是:“通过表明权利持有者(right-holder)的某些特定利益具有一种特殊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足以将不干涉的义务强加给他人——即使要是允许这种干涉,将会带来一个更好的结果或更令他人满意的结果,亦是如此——这时,权利话语就可以起到一种承认的功能。”(27)William A. Edmundson, An Introduction to Rights, Second Edition, p.158.这一论述显然是权利利益论在方法论上的一种延伸,这种延伸超越了对权利主体的执念,而着重关注权利持有者的利益。(28)William A. Edmundson, “Do Animals Need Rights?”,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Vol.23, No.3, 2015, p.349.其中在权利享有的范围上,权利人也变成了更为中性的权利持有者,就像在权利思想史上“男人的权利”被消除性别色彩而让位于“人的权利”一样。
我国《民法典》第16条关于胎儿权利的规定就是此类权利扩展的一个立法典范。该条的内容是:“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其中的“胎儿”并不是医学意义上的术语,而是法律意义上的界定,即人出生之前的所有生命存在形态(甚至体外胚胎)都属于第16条所说的“胎儿”。《民法典》第16条的规定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生动体现了我国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对人的生命尊严的接受和维护。生命尊严辩护了胚胎的有限权利地位,因为该条的核心思想是“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民法中的“视为”即“拟制”的意思。关于该条规定及相关案例的判决与生命尊严间的关系,石佳友等指出:“在21世纪科技时代下,法律应该积极应对科技挑战,采纳并发展新的法律思想,兼顾人类辅助生殖程序中自然人生命发展的特殊性,强化人文关怀。将人类辅助生殖背景下的体外胚胎纳入第16条的保护范围体现了民法典的时代精神,体现了对人的尊严和自由的保护。”(29)石佳友、曾佳:《死后人类辅助生殖生育子女的权益保护》,《法律适用》2023年第7期。这一判断与本文的主要论证理由是一致的,也应当代表了我国民法学的主流价值立场。
这就使得权利的范围在权利理论内部进行了自然而然的扩展,即只要利益足够重要,就可以承认享有利益者拥有权利。而利益重要性的判断标准实际上来自权利利益论的一个经典定义,即拉兹把权利定义为:“当且仅当X能够拥有权利,而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X福祉的一个方面(他的利益)是使得其他人(们)负有一项义务的充分理由,那么‘X就拥有一项权利’。”(30)Joseph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66.这既是对权利的一个义务角度的解释,也是判断利益重要性的标准。同时,也在技术层面解决了法律保护的难题,即法律可以凭借义务来保护权利持有者的权利,并根据权利观念自身的变化(31)这就是权利的生产性,即随着社会共识的改变,新的保护要求(即义务)就会被提出,这时权利主张的内容就会不断扩展。也就是说,权利可以不断产生新的义务,而无需不断创设新的权利。这是权利本身所蕴涵的一个更为技术性的要求,也是从义务角度解释权利的一个优势。Joseph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Chapter 7.来扩展义务的范围,而无需时时创设新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