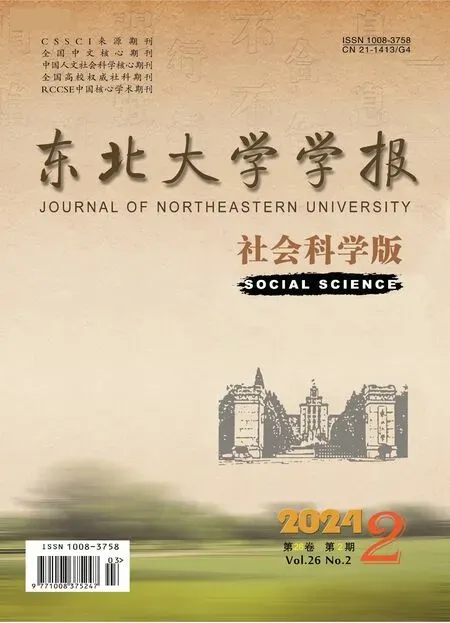《诗经》风诗叙事及其传统
——《诗经》研读笔记之二
董 乃 斌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一、《诗经》风诗的叙事
研究《诗经》,除了其文本以外,可以利用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从汉人开启到此后历代学者的注疏、专著,不胜枚举(1)参见刘毓庆:《历代诗经著述考》,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现在除了许多单本的专著外,又有了一些注疏和研究著作的汇编本,如鲁洪生主编的《诗经集校集注集评》、黄霖等主编的《诗经汇评》等等。
此外,多种文学史著作的《诗经》部分也是重要参考资料,因为它们综合而又精简地展示了《诗经》的研究成果,对《诗经》的内容、思想艺术、文学史地位等都有简明扼要的阐述。
我们现在关注《诗经》风诗的叙事问题,首先要问风诗究竟涉及哪些事情,接着要问风诗是怎样叙述这些事情的、有些什么特点、是否形成某种传统等等。前人论述对此曾多有涉及,虽各有短长,均很有参考价值,当然最根本、最重要的还是《诗经》文本自身。这是我们的入手处,也是着力处。
《诗经》风诗,旧称十五国风,总计160首。统观这160首诗,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也可以说风诗写了四个方面的事情:第一是恋爱家庭;第二是农事生产;第三是战争徭役;第四是对统治者的美刺。这四大类包括不进去的,暂列为其他,数量仅占全部风诗的十分之一,涉及社会生活和心理的各方面,但数量稀少(2)有的文学史概括《诗经》内容,大分为六类:(1)祭祖颂歌和周族史诗;(2)农事;(3)燕飨;(4)怨刺;(5)战争徭役;(6)婚姻爱情。(见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一卷第一编先秦文学第二章《诗经》之第二节)其中一、三两类内容在雅颂中,其余四类见于风诗。我们采用了这种说法,在具体介绍时按作品的多少排次并按实际情况对提法略做修改。。
恋爱婚姻家庭是风诗写得最多的内容,全部风诗的一半以上属于这个部分。
兹列举篇目如下:
《关雎》《樛木》《螽斯》《汉广》(周南)
《鹊巢》《草虫》《行露》《殷其雷》《摽有梅》《江有汜》《野有死麕》《何彼襛矣》(召南)
《柏舟》《绿衣》《燕燕》《日月》《终风》《凯风》《雄雉》《匏有苦叶》《谷风》《旄丘》《简兮》《泉水》《静女》(邶风)
《柏舟》《桑中》《蝃蝀》(鄘风)
《考槃》《硕人》《氓》《竹竿》《芄兰》《伯兮》《有狐》《木瓜》(卫风)
《中谷有蓷》《采葛》《大车》《丘中有麻》(王风)
《缁衣》《将仲子》《叔于田》《大叔于田》《遵大路》《女曰鸡鸣》《有女同车》《上有扶苏》《萚兮》《狡童》《搴裳》《丰》《东门之墠》《风雨》《子衿》《扬之水》《出其东门》《野有蔓草》《溱洧》(郑风)
《鸡鸣》《著》《东方之日》《甫田》(齐风)
《椒聊》《绸缪》《有杕之杜》《葛生》(唐风)
《蒹葭》《晨风》(秦风)
《宛丘》《东门之枌》《衡门》《东门之池》《东门之扬》《防有鹊巢》《日出》《泽陂》(陈风)
《素冠》《隰有苌楚》(桧风)
《候人》(曹风)
《伐柯》《九罭》(豳风)
以上82首均属婚恋家庭题材,除了婚恋,还包括家庭生活的其他方面,故数量甚多。除《魏风》缺席外,其余十四国风均有分布,而以邶、鄘、卫与郑风为多。这显示出此类诗歌反映的是《诗经》时代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内容,也是民间歌谣最喜表现的方面。这些诗的主人公多半是女子,多以女子视角、女性口吻叙述,而所表现的感情则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俱全。《诗经》风诗的叙事因素,在此类诗中表现得集中而突出,像《邶风·谷风》《卫风·氓》虽抒情色彩极浓却已相当接近叙事诗,其余所有作品的抒叙结合也均达到上佳水平。此类诗篇的数量居于风诗之首。
农事生产也是《诗经》时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但《诗经》风诗中对之做正面叙述描写的作品,其实不算太多,总共只有7首,就数量而言,只能算是风诗的殿尾。其篇目有《葛覃》《芣苢》(周南)、《采蘩》《采蘋》《驺虞》(召南)、《十亩之间》(魏风)、《七月》(豳风)。
虽然数量少,但仅《豳风·七月》一首即可一以当十百,其长度、所涉具体内容、写法和总体分量足以与《大雅》的《生民》《公刘》《绵》等史诗相颉颃和媲美,使其在《诗经》整体中占据重要地位。从诗歌叙事的角度来看,《七月》也是极典型的代表作。
另两类内容的作品,在《诗经》中分量比较接近,也都是《诗经》风诗的重要内容。那就是百姓美刺统治者的32首和战争徭役题材的21首。美刺类中,实以怨刺为主,美、刺之比是1∶3。若将战争徭役类中怨刺为主的诗篇加上,那么对统治者不满的讽刺之诗数量就更多,这也是风诗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
下面仍列出各类的篇目,以方便讨论。
赞美统治者的有《麟之沚》(周南)、《甘棠》(召南)、《定之方中》《干旄》(鄘风)、《淇奥》(卫风)、《羔裘》(郑风)、《车邻》《驷驖》(秦风)等8首。
讽刺鞭挞统治者的有《羔羊》(召南)、《新台》《二子乘舟》(邶风)、《墙有茨》《君子偕老》《鹑之奔奔》《相鼠》《载驰》(鄘风)、《黍离》(王风)、《南山》《敝笱》《载驱》(齐风)、《硕鼠》《汾沮洳》(魏风)、《扬之水》(唐风)、《终南》《黄鸟》《权舆》(秦风)、《墓门》《株林》(陈风)、《羔裘》(桧风)、《鸤鸠》《下泉》(曹风)、《狼跋》(豳风)等24首。
刺诗明显多于美诗,叙事色彩也以刺诗较为鲜明,涉及阶级矛盾、贫富悬殊和反抗意识的内容,这类内容历来在一般文学史著作中都受到重视。
反映战争徭役的作品有21首,其中有少量凯旋之歌,更多的是战争徭役重压下抒发悲苦伤痛之情的怨刺之歌。具体篇目有《卷耳》《兔罝》《汝坟》(周南)、《小星》(召南)、《击鼓》《式微》《北门》《北风》(邶风)、《河广》(卫风)、《君子于役》《扬之水》《兔爰》(王风)、《清人》(郑风)、《东方未明》(齐风)、《陟岵》《伐檀》(魏风)、《鸨羽》(唐风)、《小戎》《无衣》(秦风)、《东山》《破斧》(豳风)。
最后是18首难以分入以上各类的作品。如同情孤独者的《卫风·有狐》《唐风·杕杜》、赞美乐师舞者的《王风·君子阳阳》、流亡者之歌《王风·葛藟》、猎人射手之歌《齐风》的《还》《卢令》《猗嗟》(这三首似可列入农事生产,但较勉强)。还有《魏风》中愤于社会不公、忧虑时事的《葛屦》《园有桃》,《唐风》中叹息时光流逝、讽刺吝啬、批判傲慢、劝勿信谗、睹物思人的《蟋蟀》《山有枢》《羔裘》《采苓》《无衣》,以及外甥送舅的《秦风·渭阳》、书写游子乡愁与悲慨人生的《桧风·匪风》《曹风·蜉蝣》,乃至托物寄情的禽言诗《豳风·鸱鸮》,等等。这些作品的存在,说明风诗内容的丰富性。
对于风诗,也可按别的标准划分组合,比如将怨恨讽刺统治者划为一类,则上述战争徭役与怨刺统治者两类便可归并,以鞭挞怨刺统治者为标题。这样做,亦有其合理方便之处。
此外,若对诗篇内容的理解、阐释有分歧,则各诗分类位置亦会不同,此中争议不可免。为讨论方便,以上姑作试分,大体如是而已,尽可商榷调整。
上面将《诗经》风诗所涉之事,按我们的理解做了大致归类,即婚恋家庭、美刺统治者、战争徭役、农事生产。这既是《诗经》风诗的四大内容,也是《诗经》风诗所叙事情的四大方面。这些事情都是各篇风诗所叙述的,虽然各篇的叙述方式、抒叙二者的含量分配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是一种叙述文本,只有通过诗人(作者)和事件中人物的叙述,读者才能了解到其中的种种事情(3)中国诗歌,以《诗经》作品为代表,都可以称作“叙述文本”,与西方文论习惯所分的“抒情文本”“叙事文本”“戏剧文本”不同。叙述文本是包含着抒情成分和叙事成分的综合性文本,其抒叙结构则需要分析。。历代研究者之所以对风诗文本有此基本共识,具体解说虽有小异,但大体方向并无扞格,关键在于风诗所叙、所涉之事的确就是这些内容。根据文本,人们从“事”与“情”两方面对它们做出说明,结果大致便只能如此。
我们再读前人对《诗经》风诗叙事的解说,又发现这些诗所反映和表现的内容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其事与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相联系;一种则仅与无名大众相联系。因此,前者与历史记载有关,其本事于史有证,可以考订印证,可以比较切实地“诗史互证”。当然,因所指具体,也容易见仁见智而有所分歧。后者虽也是历史(社会)生活的反映,但无本事可考,诗的史性弱于前者,对之施行诗史互证,只能在时代氛围、社会心理或历史趋势等较大较笼统的层面进行。对于诗歌叙事学研究来说,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作品,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是有差异的。我们拟分别讨论之。
二、风诗与诗外之事
在风诗的上述四大内容中,美刺统治者一类里有较多与历史人物相关的作品,《召南·甘棠》颂念召公仁政,《卫风·淇奥》颂美君子人格,据说指的是卫武公,《鄘风》的《定之方中》《干旄》赞美卫文公复兴强国的事迹等。这类作品不多,多的是怨刺之诗。
如《邶风·新台》和《鄘风》的《墙有茨》《君子偕老》《鹑之奔奔》是一组讽刺卫宣公及其后人荒淫乱国的历史。相传许穆夫人所作的《载驰》(属鄘风),也与之有关(4)何楷的《诗经世本古意》认为《邶风·泉水》《卫风·竹竿》也是许穆夫人作品,魏源《诗古微》亦持此说。《诗经原始》和《诗经通论》中怀疑是许穆夫人妾媵所作。。
从《诗序》《毛传》起,历代研究者基本无异词,认为这些诗对应于《左传》的纪事以及卫国后续诸君的更替变换:
(桓公十六年)初,卫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属诸右公子。为之取于齐而美,公取之,生寿及朔。……宣姜与公子朔构急子。公使诸齐,使盗待诸莘,将杀之。(5)《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758页。
(闵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及狄人战于荧(荥)泽,卫师败绩,遂灭卫。……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齐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生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文公为卫之多患也,先适齐。及败,宋桓公逆诸河,宵济。……立戴公以庐于曹。许穆夫人赋《载驰》。(6)《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87—1788页。
司马迁《史记·卫康叔世家》据《左传》梳理叙述此段历史,与上述诸诗有关的人物主要有卫宣公、伋(急子)、顽(昭伯)、宣姜、子寿、子朔(惠公)、戴公(名申)、文公(名燬)、许穆夫人等。
这里与诗篇有关的基本情节是:卫宣公为太子伋娶齐女为妻,见女美,乃于河上筑新台,夺媳为妻,是为宣姜,生子寿、子朔。宣姜、子朔谗害太子伋,宣公亦欲废太子,乃令伋出使齐国,安排杀手在界上伏击。子寿获悉阴谋,追救伋,被误杀。伋后到,亦被杀。宣公卒,子朔立,为惠公。齐国强迫宣公另一子顽(昭伯)与宣姜同居,生三子二女。此后卫国动乱多年,国弱,以致被狄人灭亡。宋桓公接济卫之难民,并立戴公为卫君。许穆夫人(顽与宣姜所生次女)亦欲前往奔唁,并为卫谋划,受到许国大夫阻挠,心情激愤,乃作《载驰》。后在齐国帮助下,卫得以复国,戴公卒后,文公继立。
以上简述的情节是从史书得来的。《诗经》风诗的研究者以之为《新台》《墙有茨》诸诗的本事。如《邶风·新台》的《小序》云:“刺卫宣公也。纳伋之妻,作新台于河上而要之,国人恶之而作是诗也。”《二子乘舟》的《小序》云:“思伋、寿也。卫宣公之二子争相为死,国人伤而思之,作是诗也。”《鄘风》的《墙有茨》《君子偕老》《鹑之奔奔》诸诗和《小序》《毛传》也这样叙述。《载驰》作者因有《左传》明言,当然更无疑义。朱熹在《诗集传》中对《小序》《毛传》似不尽信,但仍称其为“旧说”,并特地声明:“凡宣姜事,首末见《春秋传》,然于诗皆未有考也。诸篇放此。”(7)朱熹集注:《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7页。总之,前人就这样将风诗与史事联系了起来。但正如朱熹所言,这些史事仅凭诗歌文本是无法考实的。
《新台》诗云:“新台有泚,河水弥弥。燕婉之求,籧篨不鲜。新台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渔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从诗的字面,看不出卫宣公夺媳为妻故事。籧篨,据朱熹注,本意是指竹席,人或编以为囷,其状如人之臃肿不能俯仰,故借以比喻丑陋的形象(如鸡胸、驼背之类)。戚施,朱注曰:“不能仰,亦丑疾也。”闻一多则认为“籧篨”与“戚施”都是癞蛤蟆一类丑物(8)参见闻一多:《天问释天》《诗新台鸿字说》,《闻一多全集》第二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2年。。燕婉之求,本想得到个理想的人,不想来了个丑怪物,真是事与愿违。诗中再三言之,可见大有切肤之痛。但如仅看诗内,其题旨便只能如高亨所说:“诗意只是写一个女子想嫁一个美男子,而却配了一个丑丈夫。”如此而已。可是如果考虑到此诗属于《邶风》,邶、鄘、卫三风所写皆为卫国卫地之人事,而其创作时限则在卫国被狄人灭亡之前(《载驰》才涉及卫亡),题曰《新台》,与卫宣公在河上筑“新台”以迎娶齐女事正合,故《毛传》所云能够得到公认。从《诗序》《毛传》《郑笺》《孔疏》到唐、宋至清与现代的《诗经》研究注释者,如苏辙、姚际恒、方玉润、高亨、程俊英等均同意此说,看来并非无理。
就《新台》诗而言,《毛传》指出的《左传》所载之有关史事,对于解读诗意、说明诗旨是非常有用的资料,甚至可说是不可或缺的参证。虽然这些史实并未具体表现于诗内——诗的字面并未写到,即并未直赋这些事——按其实际地位,它们应该称为“诗外之事”。但这个“诗外之事”对于诗歌的解读和叙事分析却十分重要,应视为作品叙事之有机组成部分。
当然,绝非随便找点什么历史记载就可以充当这个“诗外之事”。“诗史互证”既有其成立的合理性,也存在发生错误的可能,故必须严肃缜密,使之可信可靠,才能具有说服力,并且应当允许质疑讨论和证伪的可能。而一旦认定此事与作品确实有关,就不仅可将其作为诗歌创作的背景,甚至不妨将其当成诗歌内容的一部分,在对其做叙事分析时予以充分利用。
“诗史互证”可以说是《诗序》和《毛传》的核心概念和基本方法,在此基础上说本事、解诗意、揭题旨、析作法,可以说是《毛传》对《诗经》研究的重大贡献,也是后人研究《诗经》的一般思路和轨范。虽然陆续有人发现《诗序》《毛传》观点有牵强附会、说服力不强之处,但总体说来还是不能完全否定,只能零星具体地商榷或另立新说。在论《诗经》史诗时,《诗序》《毛传》的价值已充分显示,现在论风诗,又获得再次证明。
既已发现并确信诗歌内容与某些诗外之事有关,古人自然据以阐释诗篇。他们虽无叙事学之名,但实际操作有时却暗合其理。如《毛传》谓《新台》系国人厌恶卫宣公夺媳为妻之事,故作此诗讽刺,将诗的内容与史实做了明确联系,并认定此诗为卫国人所作,奠定了阐释诗意的基础。朱熹更具体论此诗为“言齐女本求与伋为燕婉之好,而反得宣公丑恶之人也”。沿此思路可知,《新台》诗描述的主人公乃是初嫁卫国的齐女,诗的叙述者以齐女视角观察感受,以齐女口吻叙述抒怀,诗面略过事实,直诉对婚姻对象的极端憎恶,狠狠讽刺咒骂了卫宣公其人其行,这种阐释一直传承至今(9)值得注意的是,《新台》女主人公是无法掌握自身命运的古代女性、无辜的受害者,该被同情。但她后来成了宣姜,卫宣公死后又与宣公次子顽(昭伯)同居(据《左传》记载,此事与齐国唆使诱迫有关,或与当时父死子继的婚制有关),成了卫公室乱伦荒淫的参与者,也成了《墙有茨》诸诗的讽刺对象。古今之人不齿于此,今人更从阶级意识批判之,皆无可厚非,但宣姜作为一个女性的不幸却很少被考虑。请参阅黄霖主编:《诗经汇评》上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118—121页。。
《新台》是一首本事可考的风诗,但具体本事在诗外(只能算是此诗的背景),诗歌所表现的不是有关的故事(即所赋非故事),而是故事女主人公的一腔怨恨之情(即所赋为情感)。因此,这是一首抒情诗、一首包含叙事因素的抒情诗,确切地说,是一首咏事诗。在诗与事关系密切程度的等级(含事、咏事、述事、演事)上,可列第二级(10)关于诗与事关系疏密远近的不同及其区分,请参阅董乃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后世的咏史诗与之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这种情况在《诗经》风诗中相当普遍。《邶风·新台》颇为典型,且无意见分歧。但像《邶风·二子乘舟》,诗面仅有挂念远行者之意,《毛传》引《左传》桓公十六年事为说,解为“思伋、寿也”,就有很多人并不相信。
《鄘风》的《墙有茨》《君子偕老》《鹑之奔奔》,情况与《新台》相同。当初产生时是对社会现象的讽喻,后世看来,则为咏史。这三首诗也是以卫公室故事为背景的抒情诗。由于“诗史互证”法的局限(不确定性带来证伪的可能),以及“不淑”一词的不同理解(不善抑或不幸),《君子偕老》的题旨就有多种说法。
《齐风》的《南山》《敝笱》《载驱》讽刺齐襄公乱伦荒淫,鲁桓公未能采取有力措施阻止,以致被害,后来鲁庄公亦未能防闲其母。此事见于《左传》桓十八年、庄二年的记述(齐襄公与嫁给鲁桓公的妹妹文姜私通,并因此而谋杀了鲁桓公。鲁庄公继位后,未能设法阻止,文姜继续与齐襄公晤会)。
《秦风·黄鸟》的有关史实见于《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司马迁《史记》也有记录。
《陈风》的《墓门》《株林》二诗分别与陈国的君主桓公、灵公相关。《左传》桓公五年载,陈桓公之弟佗,杀太子自立为君,国人因之作《墓门》,批评陈桓公不能早除陈佗。《左传》宣公九、十年载,陈灵公及大夫孔宁、仪行父与夏姬(大夫夏御叔之妻)淫乱,夏姬之子夏征舒杀灵公自立,楚出兵诛夏征舒,立灵公之子,是为陈成公。
以上诸诗所咏之事皆有历史文献可考,涉及的人物有名有姓。但这些诗歌本身并不是直接叙述其中某个历史事件,而多是以其事为背景而发表议论或抒发情感的。对这些诗歌进行叙事分析,离不了“诗史互证”和从史籍考证所得的“诗外之事”,也离不了读者(研究者)将诗面内容与诗外之事通过充分联想所进行的综合分析。在这里必会产生不同意见,所以为证伪留有余地是必要的。
《邶风·击鼓》是一首记有历史人物名字、诗内诗外叙事均颇分明的作品。诗中提到的孙子仲,即公孙文仲,字子仲,其生活年代与州吁同时。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11)朱熹集注:《诗集传》,第18—19页。
此诗的“诗外之事”即背景,是篡权的卫公子州吁联合陈、宋、蔡三国伐郑(见《左传》隐公四年)的战争。孙子仲是卫国的统帅。此诗以卫国一个兵士第一人称叙述口吻出之。首章叙击鼓出征,二章叙战而无归,三章叙战争失利,四章叙危境思妻,五章叙悲哀叹息。全诗从击鼓出征起,写出一个时空转换与心绪波动的过程,虽概括精简却非常具体:别人守土,我则随军出征不得回家。战争失利,生死难卜,危难中想到妻子,想到当年与她的誓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堪称神来之笔,令人如闻如见。现在愿望落空,使我孤独,也使我失信!诗内所述如立体画面,征人及其妻遥思而无奈之情满溢纸上。《击鼓》可谓诗内外之事呼应增色、诗歌含义丰茂的典范。
三、抒情诗的叙事分析
《诗经》风诗还有更多是无法与具体历史人物联系的作品,对这些诗歌进行叙事分析,基本上只能利用诗面的文字。
有的作品叙事色彩鲜明,如《邶风·谷风》《卫风·氓》和《郑风》的《将仲子》《女曰鸡鸣》之类,虽长短不一,但诗内之事写得生动明晰,已略具叙事诗性质。《谷风》《氓》是两位弃妇在娓娓诉说婚姻的变故;《将仲子》表现男女的热恋,有活泼的行动和亲昵的话语;《女曰鸡鸣》则是新婚夫妇家常生活一景,既现实又充满憧憬。这些篇章不但有顺时或逆、倒、追、补诸式的叙事,还有人物语言和戏剧性场面的展示,叙述内容的多面多层及由之而来的丰富含义,均非常值得注意。
《诗经》风诗的叙事常常是与抒情(含议论感慨)成分的溶渗结合。文学叙事无不含情,或者说,文学中本没有无情的叙述。同样,世上没有凭空而来、与事无关的情,诗之抒情亦必含叙甚至有赖于叙。当然,为艺术之委婉含蓄,诗歌往往将所因与欲叙之事置于暗处、隐处、远处,而以抒情感慨议论为诗之明面、近景、主声。这种含事之诗往往给人专在抒情言志的表象,叙事一翼遂易于有意无意间遭到忽视。中国诗歌被笼统称为抒情诗,以为中国诗歌只有一个抒情传统,今日我们则要纠正这种误解和偏颇,对抒情诗做一番重新审视和分析:一是要探寻揭示其中的叙事因素;二是要分析它们的抒叙结构;三是要论证其与抒叙传统的关系。总之,是要发挥读者参与的能动性,运用叙事视角来看抒情诗,以发现诗歌中那些被“抒情传统唯一”的偏见遮蔽的现象与表现,而以“抒叙两大传统贯穿”的观点取代“抒情传统唯一”的观点,并努力使之成为文艺理论和文学史知识中的共识乃至常识。
探寻诗篇的叙事因素,一般可从叙述视角(人称)入手。以前的习惯性认识是对抒情诗的作者、抒情人、叙述者和作品主人公不做区分,而将其浑然等同,将抒情诗内容简单地看作作者本人的真实自白(12)不是没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如钱锺书先生就曾多次强调诗歌创作的虚构性和语言的修辞特征,指出诗语的不可尽信。但旧习影响很深,说诗者仍不时陷入泥淖。。而从叙事学引进叙述视角的概念,则可改善这种粗疏囫囵的弊病。
风诗的叙述视角至少有两种:一是第三人称叙述;一是第一人称叙述。
第三人称叙述,主要由赋体构成,亦可称赋体叙事,其特点是叙述的客观性,作者与叙述者、抒情人有别,诗歌叙述的基本上是他人故事,而并非自己之事。如《关雎》,虽用兴法开篇并连缀,所兴亦是作者之所见,叙述者实处于客观地位。诗中“寤寐思之”“辗转反侧”是对君子行为的描述,“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云云,则是拟君子之思与言。《葛覃》第三章有“薄污我私”“薄浣我衣”之句,但前两章造成的总体印象客观性颇强,仍不妨为第三人称叙事。《卷耳》首章即云“嗟我怀人,置彼周行”,直到末章“我马瘏矣”“我仆痡矣”,都是“我”在叙述,那是典型的第一人称叙事,或称独白叙事。这两种叙事占了风诗叙事的绝大部分。
属于第三人称叙述的,如《周南》的《樛木》《螽斯》《桃夭》《兔罝》《芣苢》《汉广》《麟之沚》,《召南》的《鹊巢》《采蘩》《采蘋》《甘棠》《羔羊》《野有死麕》《何彼秾矣》《驺虞》,《邶风》的《凯风》《式微》《旄丘》《简兮》《新台》《二子乘舟》等皆是。
而《召南》的《草虫》《行露》《殷其雷》《摽有梅》《小星》《江有汜》,《邶风》的《柏舟》《绿衣》《燕燕》《日月》《终风》《击鼓》《雄雉》《谷风》《泉水》《北门》《北风》《静女》等,则均是第一人称叙述。
第一人称叙事的极致是独白叙事,即全诗每句话都是主人公自己在叙述,犹如戏剧中的独白,而诗人(作者)则如剧作家一样隐身幕后。除上举《郑风·将仲子》在语言表达上是独白叙事,《魏风·硕鼠》也很典型。此外实例尚多,大抵未明写背景、场合而能靠抒情人独白见出事情者皆是。
由上可知,区分风诗的叙述人称,主要看其叙述是“有我”还是“无我”,有我为第一人称,无我多为第三人称,无论何种人称,叙述事情都是一致的,区别仅在具体事件之隐显而已。读者同时需要体会琢磨诗歌叙述的语感。有的独白是真的自说自话,无须受述者,仅诉诸内心。有的独白则不然,说者虽是独白,但实有确定的受述者,此人虽未出场,但却是重要的存在,如《郑风·将仲子》诗中的青年仲子,《硕鼠》诗中贪婪无度的巨鼠。述者与受述者共同构成一个叙事场,二者在诗中的存在虽有隐显明暗之别,但却是相互依赖的关系。
区分人称的目的在于判断叙述的视角,分辨诗歌的叙述者、抒情人和故事主人公。比起小说的叙事视角,诗歌可能较为简单,但也不能把诗歌的作者与抒情人、叙述者乃至主人公完全画等号。诗歌的叙述视角也是有变化的,而这对理解诗意和题旨关系重大,故应细心分辨,不可忽略或笼统视之。
这里再举《豳风·东山》一诗,说明人称、视角的变化以及读者对此理解的不同对诗意解说的影响。其诗四章,每章十二句,原文如下: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果臝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蟏蛸在户。町畽鹿场,熠耀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怀也。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仓庚于飞,熠耀其羽。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13)朱熹集注:《诗集传》,第94—95页。
《豳风·东山》是《诗经》风诗中创作年代较早的作品,应是作于西周,周公东征平定管叔、蔡叔与武庚之乱以后。《诗序》说:“《东山》,周公东征也。周公东征,三年而归,劳归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也。”这是认为《东山》系周大夫所作,主题是赞美周公东征及其慰劳归士之举。后更有人干脆将诗的作者直接定为周公本人,如朱熹谓“成王既得《鸱鸮》之诗,又感雷风之变始悟而迎周公。于是周公东征已三年矣,既归,因作诗以劳归士。盖为之述其意而言曰:我之东征既久,而归途又有遇雨之劳,因追言其在东而言归之时……”,明确将《东山》解为周公之词。看法类似的尚有王质、戴溪、严粲诸人,当然后代持不同观点的研究者亦甚多。
其实,诗作者是谁并不重要,也很难真正弄清并证实,关键是要对作者与诗的叙述者/抒情人加以区分。即使《东山》一诗的作者真是周公或周公麾下的大夫,但从活跃于诗中的人物,从这个人物的所为、所思视之,其叙述者/抒情人都应该是作者的代言人,诗中频繁出现的“我”应该是东征军的一位将士,这样才能把全诗讲通、讲顺、讲深。如果做了这样的区分,整个诗的意义和题旨也会产生不小的差异。古代有些解诗者,自觉不自觉地站在礼教立场,强调此诗的政治意义。从假托孔子所言“于《东山》,见周公之先公而后私也”(《孔丛子·记义》)到《诗序》所谓“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闵其劳,所以说(悦)也;悦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东山》乎!”,到朱熹引述《诗序》后的发挥——“愚谓完谓全师而归,无死伤之苦。思谓未至而思,有怆恨之怀。至于室家望女,男女及时,亦皆其心之所愿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发而歌咏以劳苦之,则其欢欣感激之情为如何哉。盖古之劳诗皆如此。其上下之际情志交孚,虽家人父子之相语,无以过之。此其所以维持巩固数十百年,而无一旦土崩之患也”(14)朱熹集注:《诗集传》,第95—96页。,们都大力强调此诗是周公对东征将士自上而下的慰问体贴,目的则在于让他们和更多的民众心悦诚服,既不怕苦也不怕死地听从统治者(“上之人”)的驱遣,使国家和政权得以巩固。他们的政治目的很清楚,这指导了他们对诗的分析,使他们把《东山》解释为周公对将士的慰问。可是,如果把《东山》读成征戍者之歌,那么我们听到的就是从征者的声音,就能体味到他们心中的悲苦和怨恨,这些苦恨的矛头恰恰是指向包括周公在内的统治者。解读者的立场和感情与作品内涵的关系极大,而他们对作品叙述视角、叙事声音的理解和判定则可以说是一个敏感的切入口。
除第一、第三人称视角的叙述外,风诗还有一些特殊的叙述方法。
对话叙事,通过对话表现出某种情节和故事,并激活人物形象。有全盘对话,如《郑风·女曰鸡鸣》,如果用新式标点可以写成这样:
女曰:“鸡鸣。”
士曰:“昧旦。”
“子兴视夜,明星有烂。”
“将翱将翔,弋凫与雁。”
“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
《齐风·鸡鸣》也是一对夫妇的床上对话,具体内容与《郑风·女曰鸡鸣》不同,而且形式也有区别,连开头的“女曰”“士曰”都省略了,两个人的声口却听得明明白白:
“鸡既鸣矣,朝既盈矣!”
“匪鸡之鸣,苍蝇之声!”
“东方明矣,朝既昌矣!”
“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
“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
“会日归矣,无庶予子憎。”
两篇都是夫妇起床前的对话,没有另外的叙述,所言之事不同,形成了情节的差异,夫妇情浓则两篇一致且表现得很充分,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戏剧性场面。这个场面看似真实,实乃虚构,但很典型。这样的篇章抒情色彩当然浓厚,但情是从对话和人物行为中表达出来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主题的揭示也是在这其中完成的。朱熹的解说颇中肯綮,他说前一首是“此诗人述贤夫妇相警戒之词”,后首是贤妃闻苍蝇之声而心存警畏,提醒君王莫耽逸欲,“诗人叙其事而美之也”。两处用了“叙述”字样,显示他对诗歌叙事的艺术感受(15)朱熹集注:《诗集传》,第51、58页。。若以叙事学术语言之,这两首诗的对话,前者因点明是谁所说,有如间接引语,而后者则是未曾点明说者的直接引语,小说中最常用之。二者均是诗歌作者借其塑造的人物之口所表达,对话具有表演性、场面感,是诗歌语言戏剧化的表现,也是两种值得注意的诗歌叙事手法。
也有诗歌用部分对话、片段对话来叙事。
如《邶风·击鼓》先叙从军赴战,后言“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在回忆中引出当初的誓言,昔日情景可见。
如《王风·大车》末章“榖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皦日!”是在客观叙述之后的加强表达,这四句是女子未必说出口的强烈心声。
如《郑风·溱洧》先写春日游玩,男女相会,再写“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同游士女开心说笑,如在眼前。接下去便是“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了。
如《魏风·陟岵》,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上慎旃哉!犹来无止!”以及“母曰”“兄曰”的类似话语,此为诗歌主体,但均在游子登高眺望的叙述之后。
至于《魏风·伐檀》则在描述辛劳伐木后,道出“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狟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的怨言。
这些对话既是故事中人物的声音,也是人物行为的一部分,从而也就构成了整个故事情节的一部分——抒情诗中的叙事部分。
更有戏剧性场面的营造,使叙述向表演发展,显示了抒情诗叙事主体的非单一性以及人物的多样性。《郑风·将仲子》《魏风·硕鼠》皆以主人公独白及其未出场的受述者一起构成戏剧场面,如画面,亦如影视。上面已涉及,不再赘论。尚可另举《魏风·园有桃》一例,其诗云:
园有桃,其实之殽。心之忧矣,我歌且谣。
不知我者,谓我:“士也骄!”
“彼人是哉?”“子曰何其?”
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
园有棘,其实之食。心之忧矣,聊以行国。
不知我者,谓我:“士也罔极!”
“彼人是哉?”“子曰何其?”
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16)朱熹集注:《诗集传》,第64页。
这首诗的抒情人“我”是一位落魄士人。他生活潦倒,饮食难继,却还在忧国忧民,不满现实,自我清高(所谓“我歌且谣”,内容应与此有关),于是为一般人所不理解,遭到揶揄批评,被说成骄傲、荒唐。处境如此,不能不引起他的思想斗争。“人们说得对吗?”“你自己认为怎么样?”这样的问题纠缠于心,反复折腾。想来想去,既无知我者,只有抛开不想拉倒!当然,完全不想是办不到的,这只是恨极无奈之词而已。诗意大致如此,事情原委是由士人的自述道出的。叙述中引用了外界的批评语,写到了自己内心的无声语——抒情人化身为另一人与自己对话——抒情诗经由叙事发生了向戏剧小品的变化,内容和表现方式都得到一定程度的丰富。
从时间、空间的转移变化来观察,也是对风诗做叙事分析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转移变化,有时表现得比较清晰明显,如《邶风·谷风》《卫风·氓》叙述恋爱婚姻的变故,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均有所呈现;特别是《氓》,事态的演变很有层次感,女主人公生活境遇日趋恶劣的叙述与时间地点的变化扣得很紧。这是对时空关系的直接表现。
有的则通过景物、环境的描述加以婉曲地表现。如《王风·丘中有麻》,从第一章的“有麻”,到第二章的“有麦”,再到第三章的“有李”,借植物的生长显示时间的变化,而人物故事即发生在这过程之中:先是请刘子嗟帮忙种麻,继而请其父吃饭,次年李熟时节,乃有女主人公接受刘子嗟赠送佩玉之事。诗虽短小,却将季节之变、植物之变、人事情感之变融汇在一起。
例如《齐风·著》,描写一个女子接受亲迎的过程和心情,便通过地点的变换来表现。“俟我乎著乎而”,著是古代大门和屏风之间的地方,前来迎亲的新郎先在这里等待,新娘初次窥见了他。“俟我乎庭乎而”,新郎来到了中庭。“俟我于堂乎而”,亲迎者已进入中堂。空间的渐变与新娘怦怦的心跳就这样应和着。叙事笔墨简洁,但人、事、情都描绘出来了。
风诗中多“叙中抒”现象,叙述尽管朴素平实但感情倾向明显,典型的例子如《豳风·七月》在客观叙述一年农事过程中,抒发了农人劳作的沉重、物质生活的艰苦,乃至农家女人身无保障的忧恐。的确,没有不带感情的文学叙事。凡叙述,或含褒扬赞美、同情怜惜,或含讽刺鄙夷、厌恶诅咒,虽可不着一字,倾向却难掩抑。不带感情色彩的叙述,除非那些非文学的说明性文字,如药物或用品的使用说明书之类。
风诗的诗面中亦有纯抒情的现象,表面看来未说何事,或言之模糊隐晦,或所言只及其他,读来难以确指其事。但即使如此,也不会真的绝对无事,而都是隐含事由之作。像《邶风·式微》《唐风·采苓》以及《陈风》的《月色》《衡门》《豳风·伐柯》,诗面均是直抒,然背后之事(服役操劳、谗言为害、男女相恋等)还是隐约透露着而并非完全不可捉摸。
总之,就一首诗整体而言,其所用语非叙即抒,完全可以分辨清楚。叙者,叙事;抒者,抒情(包括诉说主观情绪的感慨议论)。抒叙相互支撑、相互补充加强,是一种互惠关系,但抒叙也形成博弈(闻一多谓为“对垒”)。
互惠好理解,博弈则需略说。
首先,如果从一首诗来看抒叙博弈,那就是抒叙语言成分的分配。假设全诗的总分量是“十”,那么抒叙各占几分,必是你多我少、此重彼轻。抒叙转换交接的方式和重心的安排是诗歌结构的关捩。一首诗是叙事成分多还是抒情成分多,其总体色彩和风格特征是不一样的。由于抒叙各具独特功能,诗的艺术效果亦由此而有别。叙多者往往具体可见、质实沉重,抒多者的好处是易于清空灵动,其弊则是易流于浮泛空洞。若从诗作内容的充实厚重程度而言,则往往存在抒不如叙的情况。比如《邶风·谷风》《卫风·氓》《王风·中谷有蓷》三诗均为弃妇之词,但三诗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却并不一样,这里的差异即与各诗抒叙成分与结构的不同有关。章培恒先生认为《谷风》是西周后期作品:“由于这是我国的早期诗篇,在艺术上自不可能成熟,加以篇幅较长,叙述有些杂乱,这大概是诗人在感情的激动下,思绪纷沓,想到什么就倾诉什么,因而多少影响了别人的理解。”(17)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 第二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0页。这是说《谷风》的抒情有点多而乱,造成叙事不够丰满不够清晰的缺陷,从而削弱了它的表现力。章先生又指出,《氓》产生于东周,“与《谷风》相比,《氓》的结构显然优于《谷风》,其叙述层次分明。……像这样的在各章之间具有明晰逻辑关系的结构,在《诗经》的较长诗篇中是很少见的。在《谷风》的章与章之间,我们就很难找到此类逻辑关系”(18)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 第二版),第64页。。精辟地点出《氓》在叙事上大有进步,其优越之处主要就在于叙述层次分明、逻辑关系清楚,特别是叙事与抒情融汇结合得好,所以读者容易理解,并且深受感动。程俊英先生在解说《王风·中谷有蓷》时也有相关论述。她说:“同样反映弃妇的不幸,此诗和《谷风》《氓》相比,在表现手法上有较大的差别。后者含有比较完整的叙事成分,前者则是单纯的抒情。同样是控诉男子的负心,后者是通过琐琐屑屑的诉说,前者则只有慨叹悲泣。主要原因在于《谷风》《氓》是自述,《中谷有蓷》的作者是一位同情弃妇者。”(19)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上),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04页。程先生明确地指出《中谷之蓷》的单纯抒情比不上《谷风》《氓》的叙事加抒情,并且涉及诗歌叙述人称的问题。《谷风》和《氓》是第一人称叙述,作者与抒情人并不是同一人;《中谷有蓷》是第三人称叙述,作者或抒情人从旁观角度表达了同情,其感染力稍小是很自然的。章、程两位先生在著作时恐怕并无扬叙事贬抒情之意,但却实事求是地触及、论证了抒叙博弈的问题。这样的例子在为数甚多的诗词赏析文章中不难发现。
其次,抒叙博弈是作者个人风格形成之因。每位作者的擅长都不相同,有的善叙、有的善抒,即使处于同样场合,面对同样景致,以相同题目作诗,他们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动用和发挥所长,从而写出抒叙比重不同、风格各异的作品来。抒叙博弈就渗透在这个过程之中。
再次,抒叙博弈表现于整个文学过程,往往体现于文体的盛衰变化。古人曾云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而所论无非是各文体在不同时代的兴衰起伏,所谓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直至近代小说戏剧类叙事文体占领文坛主流地位,都包含着抒叙博弈的结果。故抒叙博弈实乃文学创作发展的一种动力,由读者作者共同操纵左右,使文学史、诗史呈变化无穷、波澜壮阔的面貌。
这后面两点涵盖的内容超过本文论题,兹不展开论述。
《诗经》风诗乃至全部作品都可以按抒叙成分的比例排成队列,形成一个谱系。此意闻一多先生早已揭示,见下文引述。我们试借光谱来比喻这个队列,具体论述另有专文。简言之,此队列可分为含事、咏事、述事、演事四个段落,划分的原则是诗与其有关之事的远近、疏密、多少之关系和表现方式。寻找并论定某诗在此队列中的位置,则可以成为对其进行叙事分析的第一步。
四、《诗经》与中国诗歌抒叙两大传统
《诗经》风诗每一篇都是抒叙结合体,《诗经》总体则是中国诗歌抒叙两大传统的源头。抒情、叙事在这个源头不分先后地共生着,从开始它们就是互动互惠,同时也互竞博弈。
以前把《诗经》说成是一个“抒情诗传统”,仅强调“情志”是诗歌之源,这是对《诗经》风雅颂三类作品和《诗大序》的误解。其实,无论从《诗经》作品还是从《诗大序》都能够清楚看到古人对诗歌叙事及其传统的认识。但是在二者的既互惠又博弈的传统中,抒情一端被某些人强调到了不合适的程度,而叙事一端则受到压抑遮蔽。事实上,在中国漫长的文学史、诗史中,叙事传统从未消泯断绝,叙事及其传统与抒情及其传统始终共存同在,而且二者不时互有起落升沉,形成波动不息的浪潮,涌现出杰出的代表人物。最为民众所熟悉的,便是被称为“诗史”“诗圣”的杜甫。杜甫在新乐府运动之前,就弘扬了《诗经》风雅和汉代乐府的传统,直接启发引领了元稹、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运动。以后历代诗坛均回响着以老杜元白为代表的抒、叙共荣传统与单纯抒情传统的博弈之声,直到今日这种博弈仍在走向深入而未曾止歇。
闻一多先生八十多年前在《歌与诗》一文中阐发论证的观点,涉及诗歌的抒叙对垒、抒叙的互惠博弈、诗歌抒叙博弈的发展变化及其历史意义,至今没有人把问题说得如此明晰、如此深刻透彻,完全可以作为我们继续深入研究的理论纲领。兹引录闻先生所论与本文有直接关系的两段文字如下:
第一段,讲清楚了歌与诗、抒与叙二者原初的区别与关系:
上文我们说过“歌”的本质是抒情的,现在我们说“诗”的本质是记事的,诗与歌根本不同之点,这来就完全明白了。再进一步的揭露二者之间的对垒性,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古代歌所据有的是后世所谓诗的范围,而古代诗所管领的乃是后世史的疆域。……原来诗本是记事的,也是一种史。在散文产生之后,它与那三种(指《书》《礼》《春秋》)仅在体裁上有有韵与无韵之分,在散文未产生之前,连这点分别也没有。(20)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一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187页。
第二段,更精粹深刻地论述了《诗经》,特别是风雅二体作品抒叙博弈演变的历史过程和巨大意义,为中国诗史与文学史的变迁勾勒了角度独特、视野开阔而线索鲜明的轨迹,给我们以无穷的启发:
诗与歌合流真是一件大事。它的结果乃是《三百篇》的诞生。一部最脍炙人口的《国风》与《小雅》,也是《三百篇》的最精彩部分,便是诗歌合作中最美满的成绩。一种如《氓》《谷风》等,以一个故事为蓝本,叙述方法也多少保存着故事的时间连续性,可说是史传的手法,一种如《斯干》《小戎》《大田》《无羊》等,平面式的纪物,与《顾命》《考工记》《内则》等性质相近,这些都是“诗”从它老家(史)带来的贡献。然而很明显的上述各诗并非史传或史志,因为其中的“事”是经过“情”的泡制然后再写下来的。这情的部分便是“歌”的贡献。由《击鼓》《绿衣》以至《蒹葭》《月出》是“事”的色彩由显而晦、“情”的韵味由短而长,那正象征着歌的成分在比例上的递增。再进一步“情”的成分愈加膨胀而“事”则暗淡到不合再称为“事”,只可称为“境”,那便到达《十九首》以后的阶段,而不足以代表《三百篇》了。同样,在相反的方向,《孔雀东南飞》也与《三百篇》不同,因为这里只忙着讲故事,是又回到前面诗的第二阶段去了,全不像《三百篇》主要作品之“事”“情”配合得恰到好处。总之,歌诗的平等合作,“情”“事”的平均发展是诗第三阶段的进展,也正是《三百篇》的特质。(21)《歌与诗》,文后署“二十八年六月一日”,初刊于《中央日报》1939年6月5日(昆明版)副刊《平明》第16期。文末注云:“这是计划中的一部《中国上古文学史讲稿》的一章。关于‘歌’的问题,不是与浦江请先生那一夕谈话,我几乎完全把它忽略了。论‘诗’部分,则得益于朱佩弦先生的《诗言志说》(载《语言与文学》第一集)者不少。谨此向二位致谢。”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一册,第190页。
今日重读,真是感慨万千。闻先生曾对《诗经》下过大功夫,以上所论则为深入浅出之言,也可以说是真正“回归到文学”的研究,值得我们结合闻先生的《诗经》研究做系统认真的学习,而不应该无端将此文设为“公案”,甚至树为批判的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