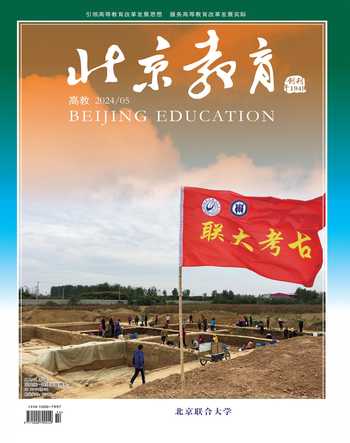世界一流大学发展鲜为人知的经验
洪成文 张博林 王佳明 张峰铭
摘 要:2035年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宏伟目标就是如何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实现高等教育强国,为成就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铺垫坚实基础。虽然很多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经验做了大量梳理和总结,但鉴于一流大学建设要素的繁多及其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大学发展受政治、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的不可避免性以及一流大学发展所体现的策略个性化,仍然有一些成功之道少有探讨,抑或是研究不够深入,甚至为决策者和实践者所疏忽。因此,探究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鲜为人知的特殊经验,不仅有探讨的必要性,而且有很大的研究价值。通过以一流大学为研究对象,试图从六个方面探讨一流大学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有何种独特而非广为人知的经验。在此基础上,联系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实际需求,展开分析和反思,以便为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提供些许参考。
关键词: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路径;鲜为人知的经验
在探讨何谓鲜为人知之前,让我们思考一个基本问题,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功建设经验是普遍性大,还是特殊性大?笔者认为,特殊性应该大于普遍性。毕竟每一所大学的遗传与环境都有很大的差异,遗传与环境决定了一流大学发展和成就的可能性。從遗传上看,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不同;从环境要素看,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不同。可见,大学之间的特殊性不可忽视,正所谓有一百所世界一流大学,就会有一百个不同的故事。因此,探讨一流大学背后那些独到但又鲜为人知的发展经验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迫切的。
何谓“鲜为人知”?众所周知的常识和认知不是“鲜为人知”,少有研究且很少传播的,为人少知或不知的,才是“鲜为人知”。对于一流大学而言,坐拥一流的师资队伍、产生一流的科研成果、依赖一流的建设资金等,都是老生常谈的经验,自然不是鲜为人知,所以也不是我们的研究对象。那么,“鲜为人知”的经验如何判断呢?一是没人研究或少有人研究的;二是与研究一流大学成功经验完全相反的研究,也就是说,重视研究大学为什么没有成功,或者先成功了而后再次坍塌的教训;三是只看到单方面的价值,却没有看到另一方面的价值。例如:重视立德树人,却没有认识到培养大学“铁粉”的重要性。①要做好这些研究,既要有对熟知的“通识”有全面的认知,也要有过程研究的精神,不断开拓研究新视角,用比较的视角,获取比较的新材料,才有可能出现一点研究新进展。本文主要从引才与养才、培养校友和“铁粉”、一流专业与学派、募钱与生钱、招聘与设置讲席教授、名校长和输送校长六个方面展示部分一流大学建设以及确保大学可持续发展的特殊经验。通过对这六个方面的深入分析和反思,结合我国“双一流”建设的现状,产生反思并提供对策建议,以期为同行的进一步研究铺垫基础。
一流大学引才重要,养才更重要
一流大学、一流专业无不重视人才引进工作,是不是人才只要引进到学校,工作就可以告一段落呢?肯定不是。因为对人才的“服务”或者“养护”更加重要。如果“服务”“养护”工作没有做好,人才潜力发挥不出来,或者有潜力,但却待不长久,甚至很快离开学校,一定会降低引智工作的效益。说得更严重一点,就是将引智工作做反了。放眼国际,将引智工作做到极致的是普林斯顿大学,在人才服务方面贡献最为突出的案例莫过于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和他的高等研究院了。弗莱克斯纳从组建到打造再到服务高等研究院发展的全过程中,均强调与突出一个基本观点:人才引进是学校校长的责任,但是为科学家们服务并与他们朝夕相处的院长,才是关键之关键。校长们在引进人才上的作用固然很大,但是“养护”工作却更多地落在了院长的肩膀上。因此,院长们应该有何权责,需要什么样的人格特点,对待教授应采取何种态度,都是需要探讨的。从弗莱克斯纳的经验中看,院长首先应当具有包容性,要不拘一格看待不同的人才。弗莱克斯纳引进的部分科学家(诸如赫尔曼·威尔教授、爱德华·厄尔教授)不仅处于其人生低谷期,还患有重度的精神抑郁,尽管如此,他依然为其主动争取权益。[1]联想到今天,鲜有大学敢于录用精神抑郁或者患有其他疾病的教授。其次,弗莱克斯纳从来没有压制过天才的薪资和待遇,反之,他创造性地做出了很多创举。与爱因斯坦谈工资待遇时,他将爱因斯坦提出的工资标准提高了六倍之多,并解释道,普林斯顿大学必须提供与他的水平相当的待遇,否则就是普林斯顿大学的错误了。在他任院长期间,美国经济大萧条还没有完全结束,大学也很拮据。尽管如此,他还是为教师设立了养老金制度,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创举。在弗莱克斯纳看来,大学者都是“宠出来的”。最后,弗莱克斯纳正确地处理好自己与教授们的位置,在他眼里,这些教授就是他“崇拜的偶像”。一方面,这些人才确实从实力和潜力上看都是不可估量,值得为人所尊敬与崇拜的;另一方面,学者本身具有成长期,在被“宠”的环境下工作,会滋生更多积极情绪,进而创造更多研究成果。虽然弗莱克斯纳本人没有发表过一篇像样的论文,但他的伟大就在于他能将世界顶尖的学者笼络在一起。积极的服务态度和对知识和大师们的“崇拜”无疑是他成功的关键经验,没有弗莱克斯纳的奉献和支撑,高等研究院难以实现培育出33位诺贝尔奖和32位菲尔茨奖得主的辉煌,也难以成就20世纪中后期的普林斯顿大学的一流发展之奇迹。[2]由此可见,引进人才重要,“养护”人才更为重要啊!
当然,弗莱克斯纳院长到底拥有多大自主权,也是值得探讨的议题。联想到我国大学的内部治理现状,可能有人在羡慕弗莱克斯纳的同时,会产生疑问:中国大学能给二级学院的院长们那么大的自主权吗?我国大学提供给院长们的自主权能支撑他们做好服务和“养护”工作吗?显然,我们无法提供答案,但是这个课题却值得探讨。只要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内部治理的优化问题就是绕不开却又必须解决的大课题。
毕业生重要,培养“铁粉”更重要
立德树人是大学的根本任务,每年大学都会产生一批新的校友,但是校友当中有多少“铁粉”?“铁粉”是怎么培养出来的?“铁粉”对于大学的一流发展有什么作用?这些都是鲜有人探讨却又十分关键的课题。“铁粉”是成就与情感的复合体,光有成就没有对母校的情感,是校友但不是“铁粉”,成就与情感兼具才是学校“铁粉”的关键所在。一般而言,我们可将学校的“铁粉”分为三个类别。一是毕业后大展宏图、潜力充分发挥且取得巨大成就的校友,母校同他们一荣俱荣。[3]二是毕业后自主或合作创业取得巨大财富的,且自愿为母校捐款甚至反复捐款的校友。[4]三是与母校不离不弃始终同甘共苦的校友。他们或是周转数校、最终返回母校做校长或董事的校友;或是在母校担负学术工作且面对他校“挖角”而不动心的校友;抑或是学校的管理者,坚守母校,且始终秉承一个信仰:能为母校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就是一辈子最大的荣幸。[5]总而言之,一流大学必然有自己的“铁粉”,毕业生之中“铁粉”多,大学自然就一流了,而如若毕业生之中鲜有或者不存在“铁粉”,那么这所学校的一流性就值得怀疑了。
那么“铁粉”是如何锻造出来的呢?让学生有过感动的经历和体验,是“铁粉”形成的基础。读书和拿学位好比大学生活的普通凡事,被母校感动过且一辈子难以忘怀的感受才是形成“铁粉”的关键。家庭贫寒获得经济资助、前途渺茫获得导师智慧引导、毕业后就业困难获得母校支持,都是培养“铁粉”的具体表现。如果大学只关注于招生、缴费与教学,而忘记了对学生身心健康和理想的引导;如果大学只是满足于在校期间的照顾或“看护”,而忽视了对毕业生毕业后可能面临的窘境提供适时的帮助,那么“铁粉”的培养就会面临困境。由此不难看出,一流大学对学生的服务不仅仅停留在学位和学位课程的修习上,也不仅仅局限于四年本科学习和六七年的博士研究生活。世界一流大学往往秉承并倡导“感动您的学生”以及“为校友服务一辈子”的理念,这对于我国正在创建一流学科或一流大学的同行,启发一定是莫大的。
一流专业重要,形成学派更重要
何谓学派?《辞海》对“学派”的解释为: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同样,因以某一地域、国家、民族、文明或问题为研究对象而形成具有特色的学术传统、对全球学术进程和发展方向产生根本性影响的一些学术群体,同样可称为“学派”。例如:牛津大学的历史学派、剑桥大学学派(数学或者经济学)、哥廷根大学的数学学派以及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学派等。早在17世纪,剑桥大学就产生了影响全球数学研究的数学学派,亦引领着剑桥大学数学研究的卓越发展;20世纪初,哥廷根学派的诞生使其引领着当时世界的数学研究;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学派随着高等教育研究院的崛起和发展,为该校数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可见,如果没有政治、经济和外交因素的影响,学派一旦形成,不仅能为一流大学的建设提供支柱,而且还会深远地影响大学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
学派之所以重要,主要原因是学派具备了建设一流大学的全部特征:有最新的研究和思想;有最伟大的教授和学科带头人;有对学科产生根本性影响的研究成果;当然也相应产生了人聚人的效应,即“高人”吸引“俊才”的效应,人才汇聚于学派,是科学发展的规律。以剑桥大学和哥廷根大学为例,前者产生了牛顿、莱布尼茨和伯努利兄弟等数学家,创造了微积分及其分析方法,后者產生了高斯、黎曼、克莱因和希尔伯特等数学家,[6]他们探索了数学与应用数学、理论自然科学与控制工程技术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对数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同时,学派内部学术自由、平等交流,学术风气十分和谐。例如:20世纪初的哥廷根大学,学者们重视学术交流,形成了一种平等和自由的学术讨论氛围,学者之间共同打造了相互配合密切合作的学术风气。如果没有出现希特勒反动政权这颗毒瘤,哥廷根大学世界数学中心的地位不会戛然坍塌,美国大学的数学辉煌也有可能延迟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出现。
聚焦学派形成原因的研究在高等教育领域几乎未有涉猎,所以我们很难直接归纳和提炼学派的发展经验。然而,科学史研究在世界科学中心转移上有了一些实证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规律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一是要有史无前例的思想大解放,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和启蒙运动时期的法国。二是要有本国人才快速成长的环境、制度以及汇聚其他国家人才的手段和吸引力。三是要有科学理论紧密联系社会实践的机制,确保科学成果的转化和应用能够落到实处。[7]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为我们研究学派的产生提供了间接的参考,尽管学派和科学中心之间还是存在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区别;但由此我们可以尝试性地得出结论,大学要形成世界级的学派,不仅需要有极大的人才汇聚能力,而且要有思想的史无前例的解放。有了思想解放,才能有学科创新的爆发。联系到当下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现实,我们至少要思考三个问题:一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我们已经有了思想解放,然而我们的思想解放之于学派的形成是否充足?二是我们在哪些学科上,更有可能较早地形成世界级学派?是否能够找寻相应的苗头?三是学派的构建需要考量世界级科学家分配的问题,即名师是分散到各个大学好,还是有组织地集中到两三所大学?②
募捐重要,基金投资生财更重要
募捐是一流大学的工作常态,高水平大学在筹资方面也具有普通大学难以企及的优势,甚至在一流大学中,校长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筹资。从部分大学大额筹资项目的公布来看,筹资就是一场运动(campaign),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在发起筹资运动,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的运动更加宏大。大额筹资运动的兴起一定程度上表明大学在资源竞争上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动辄就是几十亿美元的大额筹资,不仅实现了筹资金额的大幅提升,还实现了筹资周期的逐渐缩短,过去需要十来年的筹资项目现今只需三五年便有可能提前实现,如耶鲁大学的“为了明日的耶鲁”和斯坦福大学的“斯坦福挑战”等大额筹资运动都是提前实现的。[8]由这些运动开始,逐渐有了各院系全员动员、聘请专业团队负责筹资项目设计、校友年度捐款和讲习教授制募捐等多种大学筹资模式。可以说,多元的募捐文化已然成为一流大学校园文化的一部分。
募捐的意义是不证自明的,然而在一流大学之中,另一个同样重要的事项正在发展,这就是所谓的基金投资,基金投资的意义在于使得社会募捐的硬筹资变成了软筹资。传统的硬筹资是一种筹资所得与实际募捐相等的募捐,而软筹资则能将应筹资的效益倍数化,通过有效的安全投资,使筹资所得获得增值。例如:哈佛大学积累了509亿美元的大学基金,耶鲁大学也积累了414亿美元的大学基金。③对于世界一流大学而言,基金的竞赛始终是存在的,如果斯坦福大学在筹资上超越了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那一定不是这两所老牌大学所愿意看到的,因为基金是大学确保一流事业发展的根基之一。根据两所大学的基金报告来看,其年化收益率平均约12%,基金投资的收益每年就高达61亿美元和49.7亿美元。与此同时,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进一步发起了大额募捐运动,计划在五到十年内募捐到50亿美元,以促进学校自身长远发展。[9]由此不难看出,基金投资的本质就是“钱生钱”,从效益上远比大学筹资的价值大,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也比筹资要少得多。
概而言之,基金对于一流大学的发展有三大作用。一是能够实现大学筹资所得的增值。如上所述,名牌大学的基金增值已经接近大学的日常性经费总和,当然这里是指少数一流大学,且基金总量超过两百亿美元以上的学校。声誉越好,筹资能力越强,基金总量越大,所产生的效益就越高,这就是一流大学资金“滚雪球”的现象。二是大学基金可以起到避税和避险的双重作用。所谓避税,指的是大学的基金投资收益因为大学的非营利性而获得免税资格;所谓避险,指的是这笔基金可以对大学运行中的财政风险起到平衡作用。大学基金可以保障大学遇险而不险,帮助一流大学在危机之中化险为夷、渡过难关。三是大学基金的构建将学校的经营从校园范围扩大到市场范围。一流大学的基金投资使其具备了从市场取得红利乃至巨大红利的能力,将大学的筹资所得投入市场中,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实现进一步的增值,就是将经营范围扩大到市场的具体表现。
当然,大学也相当关注资金的安全问题。很多人可能会好奇,市场中存在风险,如何对其进行控制?如果大学基金投资遭遇风险,责任谁来承担?要回答这些问题,可以从耶鲁大学的首席投资官大卫·斯文森(David F.Swensen)那里找到答案。[10]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的学生,大卫应恩师之邀于1985年出任耶鲁大学首席投资官,并在耶鲁大学商学院教书育人,其开创的“耶鲁模式”使他成为机构投资的教父级人物,也正是在他卓越的基金管理能力之下,耶鲁大学的基金得以屡创佳绩。联系到我国的“双一流”大学建设,对我国大学基金的发展,我们应该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不仅要提高认识,而且更要解放思想,以多种方式促进大学基金不断增值,只有迎头赶上,我们才有可能赶超世界一流。否则我们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会被进一步放大,难以实现赶超与飞跃。
补充年轻教员重要,引进讲席教授更重要
一流师资是一流大学的标配。师资队伍建设无外乎两大路径:一路径是补充新教员,内部培养,最后发展到挑大梁的位置;另一路径是外部的人才引进,俗称“挖角”和“挖人”。本文无意区别和探讨这两大途径,而是将目光聚焦于第三条鲜有研究者关注的师资建设路径,即通过捐赠教席来吸引和选拔人才。
在人才引进的过程之中,利用捐赠教席来吸引和选拔优秀人才,是一流大学独有且十分有效的手段。一般而言,捐赠教席就是通过社会募捐获得资金然后以私人或名人姓名设立的教授席位。讲席教授在大学中不仅冠名教授,而且往往由本学科学术水平最高的教授担任。最早的讲席教授,可以追溯到剑桥大学的卢卡斯数学讲席教授。五百年前,谁能担任卢卡斯讲席教授,谁就是数学界的泰斗。[11]到了德国,讲席教授演变成了讲座教授,一个专业只有一位讲座教授,讲座教授具有学术权威和部分行政权力。有了讲座教授,就不再新聘教授,除非讲座教授退休或者身体不适。20世纪初,德国科学的兴旺发达与讲座教授制就可能存在某种微妙的关系。[12]美国更是“滥用”讲席教授的典型,讲席教授的制度广泛存在于美国名牌大学和诸多普通大学之中。以加州大学为例,自1980年代开始20多年的时间里,加州大学的讲席教授从80个增至1,695个,足见捐赠讲席教授制在美国高等教育领域之中的重要影响力。[13]对于美国学者来说,如果头上没有一顶讲席教授的帽子,都不好意思开口说自己是大学教员。
从效果来看,捐赠讲席制让一流大学获得了一石三鸟之效。一是大学设立讲席教授,是取才于社会,且一劳永逸。二是讲席教授对于解决教授后期的职业倦怠起到了极大的刺激作用。三是通过讲席教授的平台来“挖人”,是提升自我、击败竞争对手最有效的武器。讲席教授相互之间也存在平台高低区别,讲席教授的声誉越大,对学者的吸引力更大,一流大学的讲席教授从声誉和待遇上都能够更好地获得优秀学者的青睐。
当然了,讲席教授制度不仅仅在大学的科学研究方面发挥作用。十多年前,MIT的霍克菲尔德校长就巧妙借用了讲席教授制来缓解大学教授之中普遍存在的教学科研不均衡的问题。校长通过讲席教授制度引进了上百名教学专职型教授,令其专门从事教学相关的工作,而邀请教授的资金又全部来自于募捐。通过这种方式,麻省理工学院零成本聘用了百余位卓越的教授,解决了很多名牌大学长期面临但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
所幸的是,国内部分大学也开始建设种类不同的讲席教授,或者以名人或名校长命名,或者以捐赠者的名字命名,或者以“某某江”或“某某山”来命名,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值得鼓励,但仍有不少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例如:讲席教授建设资金是依靠事業经费,还是依靠捐赠资金?这样的讲席教授的学术声誉如何快速地提高?讲席教授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
拥有名校长重要,向外输送校长更重要
大学要发展离不开名校长。哈佛大学因为艾略特而确定了美国领头羊大学的地位,西南联合大学因为梅贻琦而奠定了联大的历史性辉煌。有什么样的校长,就有什么样的大学。尽管这一判断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上,很多国家的大学还是将选聘一流校长放在了相当举足轻重的位置之上,这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但我们往往忽略了一点,即卓越校长的聘任是绝对的关键,但是向其他大学输送校长同样是一流大学的成功秘籍之一。为其他大学输送校长,能够给源大学带来什么效益呢?④概括起来有两点:一是成就了源大学一个“校长培养所”的荣誉称号。以耶鲁大学为例,美国很多名牌大学的创校校长均来自耶鲁大学,如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达特茅斯学院、佐治亚大学和伯纳德学院等。[14]这会给美国社会留下一个耶鲁校友拥有支持教育事业善心的共同印象。同时,诸多大学的创建和成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源大学添加了不少荣耀。二是向外校输送大学领导人间接肯定了源大学的理念和先进管理。21世纪初,耶鲁大学集中向世界一流大学输送了众多大学校长,再次宣传与弘扬了耶鲁大学的管理智慧。剑桥大学的爱丽森校长、牛津大学的哈密尔顿校长、MIT的苏珊·霍克菲尔德校长、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朱迪·罗丹校长、达特茅斯学院的布劳德海德校长等,均出自耶鲁大学。如此集中地向外输送校长,不仅能够更广泛地向世界传播耶鲁大学的办学理念,而且还能收获同行的认可与感激,形成了一个双赢的良性循环。
那么如何才能形成集中向外校输送校长的情景呢?笔者认为大致有两点。一方面,打铁还要自身硬。大学想要向外输送校长,首先应当提升自身的综合水平,保证大学自身的世界一流,才有望培养出卓越的教育领导人才。耶鲁大学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文化引领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为其成为“校长培训学校”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校长培训学校”的诞生与源大学的主观能动性也密切相关。大学自身应当有意识地向外界输送自己培养的卓越人才,让所有人才都能够在最适合自身的位置发挥才能。主动推荐或许不能保证校长输送这一行为的确定成功,但一定程度上能够为毕业的优秀人才扫除职业生涯发展道路之中的障碍。耶鲁大学向外输送校长的成功实践是否与其领导层有意识的推荐行为相关尚未可知,但有一点可以明确,那就是从结果来看,耶鲁大学具备了向外界输送校长的主客观要素,这是我国大学所欠缺并亟待提升的。
囿于篇幅限制,本文仅从上述六个方面探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之中的那些鲜为人知的经验。需要厘清的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独到经验远不止于此,还有待研究者进一步地探索、发掘与丰富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
注释:?
①所谓的“铁粉”,是对母校有最高忠诚度的校友(作者注).
②近十余年,我国引进了相当数量的顶尖科学家,这些科学家首次多为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所聘任。但是几年后,他们又纷纷被礼聘为其他大学的校长。从科学发展的角度看,名教授分散在多所大学,人才集中度就被稀释了。笔者认为,科学家分散到各个大学,是不利于学科或学派的发展的.
③数据来源于各高校官方网站.
④所谓源大学,指的是原来的大学,或原先就职的单位.
参考文献:
[1]罗伯特·赫罗马斯,克里斯托弗·赫罗马斯,林子萱.爱因斯坦的老板[J].现代班组,2022(7):48.
[2]杨立军.从十大名校看美国式精英教育[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62.
[3]洪成文.世界一流学科发展有哪些国际经验[J].中国高等教育,2018(5):1.
[4]牛欣欣,洪成文.美国一流大学年度捐赠的理念与实践——普林斯顿大学的经验[J].高教探索,2021(3):88-95.
[5]许晨.立足现代 追求卓越——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理念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建立[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4):78-81.
[6]刘沛清,杨小权.哥廷根学派的发展历程[J].力学与实践,2018,40(3):339-343.
[7]张云龙,马淑欣.论科技发展与人文精神的内在勾连——基于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视角[J].自然辩证法研究,2022,38(2):86-92.
[8]李洁.斯坦福大学捐赠基金管理策略研究与启示[J].现代教育管理,2015(8):124-128.
[9]林成华,洪成文.美国一流大学“顾客导向”大额捐赠管理模式[J].比较教育研究, 2015,37(12):48-54.
[10]大衛· F ·斯文森.机构投资的创新之路[M]. 张磊,杨巧智,梁宇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4.
[11]杨庆余.近代科学建制史上的丰碑——卢卡斯数学讲席教授的设立、意义及其影响[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30(11):99-104.
[12]王保星.德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发轫及其意义映射——基于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创校实践的解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8(9):41-46.
[13]张和平,沈红.研究型大学引资与引智同行:加州大学捐赠讲席制度的特征[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3(5):152-158.
[14]耶鲁大学:美国学院之母[EB/OL].(2017-05-26)[2024-03-08]. https://www.sohu.com/a/143795332_380470.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责任编辑:于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