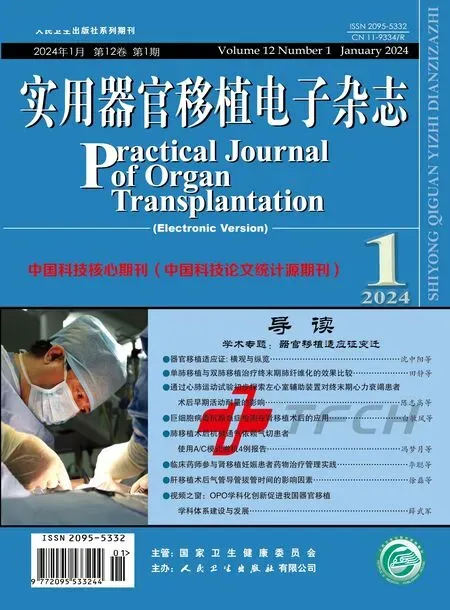实体器官移植禁忌证的变迁
康一生,刘懿禾,王兵(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外科ICU,天津 300192)
实体器官移植(solid organ transplantation,SOT)是现代医学最成功的进展之一,对于患有终末期器官疾病的患者,SOT 是延长生存或改善生活质量的重要机会[1-2]。自从1955 年的首例肾移植的成功[3],随后肝移植[4]、心脏移植[5]、肺移植[6]、胰腺移植[7]、小肠移植[8]、面部移植[9]以及子宫移植[10]的成功,将SOT 带入了一个新的篇章。
然而并非每位患者都适合接受器官移植,有一些禁忌证使他们无法被列入器官移植名单。常见的禁忌证包括高龄、病态肥胖、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e-dificidncy virus, HIV)血清阳性、酗酒或滥用药物、其他器官终末期衰竭、活动性感染、某些癌症、精神疾病以及预期生存时间有限等。
1 禁忌证与适应证的辩证关系
器官移植的禁忌证和适应证是辩证的,二者之间犹如阴阳二极,是相对的和动态变化的。适应证是基于对患者的病情评估和治疗目标的综合考虑,以最大程度地提供治疗,改善患者的生存或生活质量。禁忌证则是给予手术风险或治疗获益更深入的理解和对特定患者群体的选择,以确保治疗的安全性、适应性甚至是社会的公平性。在医学技术与研究的推动下,禁忌证会随着患者的整体情况和治疗目标进行不断调整和更新,会动态转化为适应证。器官移植禁忌证和适应证都需考虑患者/供者的心理状态、社会资源、社会公平等,具有很强的个体化和社会性。
2 禁忌证的时代性
在SOT 发展的历史中,禁忌证是随着时间、技术、社会变化而一直在不断变化的。初期阶段禁忌证主要涉及器官功能状态,如脏器功能严重受损以及存在严重心脏疾病或活动性癌症的患者被认为不适合进行器官移植手术。20 世纪50 年代,免疫抑制剂的引入使得器官移植手术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从最初使用6-巯基嘌呤,到后来联合使用硫唑嘌呤与类固醇,避免了排斥带来的问题,显著改善了患者的预后[11]。1984 年环孢素开始用于临床,显著提高了肾移植和肝移植患者的生存率[12]。现代免疫抑制剂(他克莫司、西罗莫司、麦考酚酸和依维莫司)的发展改善了移植手术,减少了不良免疫排斥反应。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的进步,SOT 技术改进及经验的积累,某些禁忌证,如高龄、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等,也开始变成相对禁忌证。同时随着技术的进步,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也不断拓展。除了亲属和非亲属供体之外,过去被认为禁忌的异体器官(例如跨物种移植)和互助器官也逐渐接受移植手术。这为一些特殊情况下无法找到合适供体的患者提供了新的机会。最后,社会观念的转变也在推动禁忌证变迁。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观念的变化,人们对SOT 的认识和接受度逐渐提高。这种转变使得原本被认为禁忌的情况接受到更多关注和探索。
3 重要的SOT 禁忌证的变迁
3.1 高龄:长期以来,基于手术风险、术后并发症及社会公平性等,高龄移植作为SOT 的一个禁忌证而存在。在早期,肝移植的年龄上限为45 ~ 55 岁[13],年龄超过70 岁被视为肝移植的绝对或相对禁忌证[14]。中国台湾的一项为期14 年的肝移植患者研究发现,60 岁以上的患者在移植后3 年内的病死率明显增加,而且年龄的影响在伴有合并症的患者中更为明显[15]。但一项包括 UNOS 和欧洲的研究结果发现,60 岁以上患者的肝移植患者或移植物存活率与年轻患者相比没有区别[16]。美国的一项单中心研究发现,70 岁以上的肝移植患者与50 多岁的患者的10 年生存率没有区别[17]。另一项纳入了22 项研究,共涉及242487 例患者(老年人:23660 例,年轻人:218827 例)的荟萃分析显示,相对于年轻受者,老年受者(>65 岁)围手术期死亡、技术性并发症、重大感染率、移植物和患者的生存率并没有差异[18]。一项关于SOT 禁忌证的调查中发现,大多数心脏移植(83.7%,n =41)、肺移植(76.9%,n =30)、和肝脏移植(68.4%,n =39)项目将80 岁以上的患者视为绝对禁忌,但只有29.2%(n =26)的肾脏项目会对80 岁以上的患者视为绝对禁忌证。多数心脏移植研究 (69.4%,n =34) 和肺移植研究(59.0%,n =23)对75 ~ 79 岁的患者有绝对禁忌,但没有一项SOT 研究将年龄低于75 岁视为绝对禁忌证[19]。 由于老年患者接受移植的总体结果与年轻受体相当,美国老年患者(>65 岁)肝移植比例明显增加,已由2007 年的11%[20]增长到2019 年的23%[21]。可见高龄作为移植禁忌证在逐渐变化,作为绝对禁忌的年龄上限可能会随着科学技术、社会年龄结构等改变,但谨慎选择供体和受体,并在术后对风险因素进行最佳管理,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该人群的移植结果。
3.2 病态肥胖:病态肥胖(BMI >40 kg/m2)在很早就视为大多数SOT 的绝对或相对禁忌[22],来自UNOS 的数据显示肥胖患者的移植物原发无功的发病率和术后病死率更高,更多围手术期并发症如更多的输血、更长的手术时间、更多的伤口并发症和胆道并发症、更长的重症监护室和住院时间,甚至是出院到专业护理或康复机构的比例增加等[23-26],一些指南已经确定,BMI >40 kg/m2是SOT 的相对禁忌证[24]。但近期也有研究显示BMI ≥40 kg/m2的患者的移植物存活率与BMI <40 kg/m2的患者相当,甚至从移植中的获益反而更多[27]。一个对234 项移植研究的调查发现,56.4%的研究视BMI 40 ~45 kg/m2为绝对禁忌证,而当BMI ≥45 kg/m2时比例达到73.5%[19],其中肺移植项目有最严格的基于BMI 的绝对禁忌,大多数肺移植项目认为BMI ≥35 kg/m2就是移植的绝对禁忌证。在此间梅奥诊所的研究小组证明了对病态肥胖者行袖状胃切除术与肝移植相结合(SG-LT)的可行性。与单独的肝移植相比,SG-LT 患者在随访3 年后的总体重下降比例更高,高血压、胰岛素抵抗、肝脂肪变性的发生率也较低,需要的降压药和降脂药也较少[28]。后续更多的研究也得出相似结果,而使术中的袖状胃切除术逐渐被应用于病态肥胖的患者中[29-31]。与其他一些适应证不同的是,肥胖是一种潜在的可改变的合并症,应更加强调通过有氧运动和热量限制的预康复方案,警惕合并症和糖尿病的围手术期管理,以及潜在的移植前减肥手术,以减轻围手术期风险,改善这些患者的结果。BMI >40 kg/m2的患者应根据他们的合并症,如冠状动脉和肺部疾病,而不是绝对的数字BMI 值来评估肝脏候选资格。
3.3 人类免疫缺损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血清阳性:HIV 血清阳性(HIV+)受体接受器官移植后有出现突破性感染,超级感染,即感染第二种不同的HIV 菌株、机会性感染,恶性肿瘤如卡波西肉瘤,HIV 肾病等多种可能,长期以来HIV+被视为器官移植的禁忌证。早年的一项对加拿大和美国肝脏移植中心的调查发现,1/3 的加拿大和1/2 的美国移植中心认为HIV+是移植的禁忌证[32-33],2010 年南非的Elmi Muller 博士首次报告了成功地开创了 HIV+之间的肾移植案例[34],4 例HIV+肾移植患者1 年内无死亡、移植失败或 HIV病毒学失败,后续研究显示27 例阳性受者和移植物的 5 年存活率分别为 74% 和 84%[35]。这些成功的经验导致美国了《国家器官移植法案》(1984 年)禁止使用 HIV+ 捐献器官的修正,并于2013 年11 月,国会通过了HIV Organ Policy Equity(HOPE 法案)。2015 年11 月,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发布了HIV+供者的选择标准[36]。2016 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完成了美国首例HIV+受者与HIV+供者之间的移植手术[37]。目前多数中心已经开始施行HIV+患者的移植手术,对多达234 项移植研究项目的调查显示,仅有29.5%的项目视HIV+为禁忌,其中主要为肺移植项目(59%)[19]。目前尚未建立针对移植受者的HIV 特异性选择标准,但大多数中心遵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的要求:在至少6 个月稳定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下,病毒载量低于检出低限,并且CD4+细胞计数>200/μl[36]。
3.4 酗酒/未戒酒:酗酒未戒酒通常和药物滥用一样是SOT 的禁忌证,大多数中心要求在移植前有一段时间的戒酒期(6 个月规则,six-month rule)。6 个月规则有双重意义:首先,对于在戒酒后肝功能和一般临床状况有所改善的患者,可进行继续观察;其次,6 个月的戒酒行动可识别在移植后复发风险较大的患者。虽然酗酒导致的急性酒精性肝炎(severe alcoholic hepatitis, SAH)的短期病死率接近70%,其中75% ~ 90%患者通常在2 个月内死亡[38],但由于移植前没有戒酒和移植后酒精复发的潜在高风险,酗酒导致的SAH 长期以来一直被世界上大多数移植中心认为是器官移植的绝对禁忌证。
2011 年,Mathurin 等[39]对SAH 未执行6 个月规则而行早期肝移植进行了试点研究,发现早期肝脏移植组有77%的患者在6 个月内存活,而没有肝移植的患者仅有23%存活(P <0.001),显示出明显的生存优势。这种生存优势在2 年的随访中依然存在:71%对23%。这项研究首次表明,未行6 月戒酒的SAH 患者中进行肝移植有生存获益。Louvet等[40]近期的一项多中心对照研究再次显示急性SAH 的早期肝移植并不劣于标准肝移植。2016 年,西奈山医院公布了他们的经验,在111 例出现SAH的患者中,9 例(9.6%)接受了肝移植。肝移植受者在出现酒精性肝炎之前的戒断时间中位数为30 d。早期肝移植的6 个月生存率与未进行肝移植的匹配对照组相比,是89%对11%。随访中位数为2 年,生存率为89%,2/9(22%)人在肝移植后有饮酒行为[41]。2017 年,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公布了第二项美国单中心研究[42]。未戒酒的患者行肝移植的生存率为88%,与执行6 个月规则戒酒的酒精性肝硬化患者的总生存率相同(88%)。且未戒酒患者与行6 个月戒酒者在移植后饮酒情况相似(24%比29%)。另一项模拟研究显示,未严格戒酒而接受早期肝移植的患者的平均预期寿命为6.55 年,而戒酒6 个月后接受延迟肝移植的患者的平均预期寿命为1.46 年。与延迟移植相比,早期肝移植在所有模拟情况下都增加了生存时间[43]。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酗酒后第1 次发生SAH,对药物治疗没有反应的特定患者,早期肝移植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西班牙肝脏移植协会最近发表了一份共识声明,认为有可能扩大肝移植的适应证,包括对药物治疗没有反应的首次发作的SAH 患者[44]。
3.5 ABO 血型不相容(ABO-incompatible,ABOi):由于ABO 抗原抗体复合物的形成激活补体,促进血小板聚集,引起血管内血栓形成、内皮炎等,有可能导致移植物衰竭,甚而受体死亡,因此血型不相容性曾被视为器官移植的禁忌。1955 年,Hume等[45]在世界范围内首次开展了ABOi 肾移植,然而8/10 例患者发生了超急性排斥反应导致了移植肾失功。早期ABOi 肝移植的2 年移植物存活率也只有30%,且急性排斥反应、肝动脉血栓、胆管炎等并发症明显增加[46]。直到1987 年,Alexandre等[47]采用了脾脏切除、术前血浆置换和联合应用糖皮质激素、硫唑嘌呤、ATG 等,患者术后 1 年的移植物存活率达到了75%。至 2001 年,Tyden 等[48]首次使用利妥昔单抗代替脾脏切除,取得了良好的预后,ABOi 移植才成为了成熟的技术手段。尽管各中心对于ABOi 移植的处理不尽相同,但主要的方法仍为:尽可能降低预存的ABO 血型抗体滴度,通过降低B 细胞或浆细胞尽可能预防血型抗体的反弹,尽可能调整患者的凝血功能等。虽然ABOi 的移植物及受者的生存率相比血型相符偏低,术后发生排斥反应的发生率偏高,如果移植前进行了预处理以降低受者体内抗A/B 抗体滴度,移植术后的存活率能明显提高,但相应的感染或出血并发症可能会增加。ABO 血型相容曾被视为SOT 的先决条件和首要原则,但对于需要紧急移植的受者,ABOi 移植仍是一项能挽救生命的选择,目前肝、肾移植的ABOi移植相对多见,肺脏移植最少。
3.6 严重的心肺疾病:对于不同的器官移植来说,严重心肺疾病可能是禁忌证也可能是某些移植如心、肺移植的适应证。心肺功能是患者手术耐受力的表现,较差的心肺功能明显增加SOT 手术或麻醉风险。严重心肺疾病会减少氧供、氧输送、氧利用,降低移植物灌注压,增加移植物流出压,进而影响内环境、凝血功能,从而增加术中出血量、延长手术时间、增加脏器并发症如术后移植物功能不良或恢复延迟,急性肾损伤、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急性心力衰竭、全身感染等。在心肺功能中,肺动脉高压作为禁忌证其变迁较为突出,早期的研究显示无论是肝肺综合征或是门肺高压受者,当平均肺 动 脉 压(mean pulmonary artery pressure,mPAP)≥50 mmHg(1 mmHg =0.133 kPa)时肝移植的病死率 都 是100%[49-50],故 而mPAP ≥50 mmHg 曾 被视为肝移植的绝对禁忌证。但随着技术的进步、新型血管扩张药物的应用,肝肺综合征或门肺高压的移植效果均得到了改善[51-53]。为此,在2006 年OPTN/UNOS 政策给予了存在肝肺综合征、门肺高压患者在等待肝移植时会给予终末期肝病模型(model end stage liver disease,MELD)例外评分,即每3 个月给予一次标准的MELD 评分增加以尽快帮助此类患者获得移植机会[54-56]。
3.7 恶性肿瘤:在移植的早期,活动性肿瘤常作为一项移植的绝对禁忌证出现。然而随着抗肿瘤治疗等技术的进展,某些活动性肿瘤作为禁忌证已逐渐成为过去,这主要体现在肝脏原发或继发性肿瘤上,在米兰标准、UCSF 标准、up-to-seven 标准、杭州标准下,肝癌肝移植已经成为了较常见的适应证了。其他还包括胆管癌、肝上皮样血管内皮瘤、肝母细胞癌等。如胆管癌(hepato-pulmonary syndrome,CCA)肝切除术后的长期效果不佳,5 年总生存率为40%,50%以上的患者疾病复发[57-58]。20 世纪90 年代的胆管癌肝移植的研究报告给出了令人失望的28%的5 年生存率和51%的复发率,这使得胆管癌成为肝移植的禁忌证[59]。但随着"梅奥方案 "(包括外照射,结合静脉注射5-氟尿嘧啶,然后是腔内近距离放疗和口服卡培他滨)的提出,美国12 个大型移植中心报告了移植后5 年无病生存率为65%[60]。随后更多的结果证实CCA 行移植治疗的有效性[61-63],其5 年生存率为65% ~ 83.3%,5 年无复发率达到50%。目前UNOS 允许将MELD例外分配给不可切除的CCA 以尽早获得移植[64]。
恶性肿瘤伴转移一直以来是项明显禁忌证,近年来在肝移植领域该禁忌证也有所突破,见于结肠癌肝转移(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CRLM)、神经内分泌瘤肝转移等。在此以CRLM 为例见证该禁忌证的变迁。早年的研究显示CRLM 患者行肝移植的5 年总存活率不到20%[65],由于极差的预后和器官的短缺,CRLM 被视为肝移植的禁忌证。2013 年挪威发表的一项前瞻性研究(SECA-I 研究)使人们重新关注这一潜在的治愈性选择[66],纳入这项研究的患者已经完成了原发肿瘤的手术切除,在经过至少6 周的化疗后接受移植。1 年的无病生存率为35%,估计移植后的1、3 年和5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95%、68%和60%。近期发表的开放标签随机对照SECA-Ⅱ试验中,应用更严格的选择标准使移植后1 年和5 年的总生存率显著提高到100%和83%[67]。目前,CRLM 逐渐成为肝移植的适应证,选择标准可参考匹兹堡大学的标准包括[68]:事先切除原发病灶,确认结肠直肠转移到肝脏,无法进行根治性切除,接受至少6 ~ 12 周的化疗,没有疾病进展的证据、 原发肿瘤切除后至少有6 个月的等待期作为肿瘤生物学的评估,在移植评估时,胸部/腹部/骨盆的CT 或MRI、PET 扫描或骨扫描没有肝外转移的证据,评估时CEA 小于100 ng/dl,以及有活体捐赠者。BRAF 突变的肿瘤由于具有侵略性的生物行为而被排除在外。挪威的一项研究[69],纳入2006 — 2012 年间23 例不可切除的CRLM,其5 年和10 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43.5%和26.1%,与药物治疗相比,接受移植治疗的不可切除的CRLM 患者的OS 更长,并与可切除的CRLM 患者的OS 相似。这项研究也可能促使不可切除的CRLM 作为移植禁忌将成为历史。
3.8 活动性感染:患有终末期器官疾病的SOT 受者会发生各种感染,如肾移植候选者可能会发生与血液透析通路或腹膜透析导管有关的感染或者复杂性尿路感染;肝移植患者可能出现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或吸入性肺炎;肺移植患者有时会感染多耐药菌,尤其是囊性纤维化患者;心脏移植患者可能会出现肺炎或与血管内装置有关的感染。未控制的感染是SOT 禁忌,早期的研究显示术前28 d 的感染性休克与术后90 d 的死亡相关[70],甚至导致从等待名单剔除的风险增加[71]。其他一些特殊感染,如组织胞浆菌病、隐球菌病、结核病(tuberculosis,TB)和非结核分枝杆菌也构成移植禁忌证。出于这些原因,指南要求在进行移植前应充分治疗活动性感染[72]。但近期也有研究显示虽然术前感染与术后感染或脓毒症有关,但似乎并不影响术后受者或移植物的存活,即使是多重耐药菌感染[73],这可能受益于日益完善的感染监测体系以及治疗手段、新型抗感染药物的应用,紧急移植前伴有活动性感染已逐渐变得常见。
总之,禁忌证的存在对于患者意味着安全保障、避免加重病情、个体化治疗和医学伦理的尊重,其确定有助于医生制定最佳的治疗方案,以确保患者的健康和福祉。器官移植禁忌证的变迁意味着移植技术、 手术效果、受者获益和安全性的变化,移植受者从最新的医学技术和研究进展中受益,并且随着时间、科学技术、手术技巧、社会进步的改变还会继续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