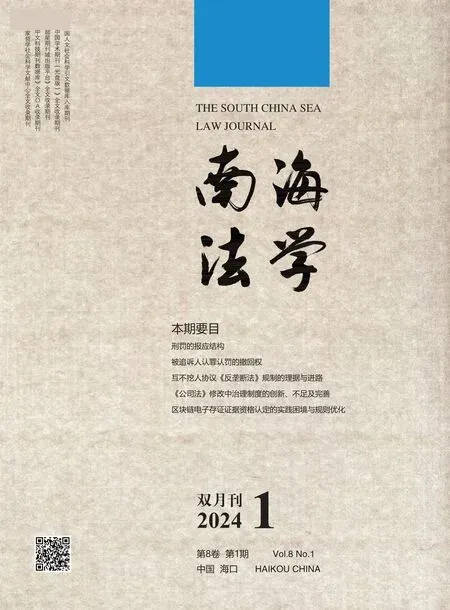互不挖人协议《反垄断法》规制的理据与进路
赵 曦 李 剑
(吉林大学 法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2)
引言
互不挖人协议(no-poaching agreement),亦称互不挖角协议或互不挖猎协议,指经营者之间达成合意,约定互相不雇佣或不招揽对方的员工。作为劳动力市场中的新兴垄断协议,互不挖人协议已引起反垄断执法机构的高度重视,但目前,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来看,对其认定和规制问题,均讨论尚少。“从劳动法到竞争法,是资本内部矛盾演变为外部矛盾,并转化为矛盾解决方法的过程。”①刘继峰:《竞争法学》(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第59—60页。互不挖人协议的出现,正是这种矛盾演变的集中体现,体现了资本将内部压力向外部传导的过程,而探索行之有效的认定方式和规制办法,恰是凝聚劳动法和竞争法合力,找寻矛盾解决方式的过程。有鉴于此,有效认定和规制互不挖人协议成为亟须研究的现实课题。本文旨在找寻认定并规制互不挖人协议的理论依据和理想进路。
2023年9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本年度民生领域反垄断执法专项行动第二批典型案例,“四大猪企业案”位列其首。牧原、温氏、双胞胎、正大四家头部养猪企业联合签署《互不挖人公约》,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精神,有损统一市场构建,涉嫌垄断。①《市场监管总局发布2023年民生领域反垄断执法专项行动第二批典型案例》,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执法一司网:https://www.samr.gov.cn/fldys/sjdt/gzdt/art/2023/art_f49c6fd3b75044cb8d510881e466c7fa.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3年10月20日。这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首次对劳动力市场垄断公开表达关注,也是互不挖人协议在我国首次被纳入反垄断执法范围。互不挖人协议的订立意味着经营者放弃了对特定劳动力的竞争,在限制特定劳动者自由择业权的同时,降低劳动力市场公平发展的可能性。②张素伦:《劳动力市场垄断行为的法律规制》,《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6期。
从目前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来看,对互不挖人协议的认定与规制,主要有两种声音:一方面,学界一般从《反垄断法》规制的条件要素出发,认为互不挖人协议属于垄断协议的范畴,故主张运用《反垄断法》对互不挖人协议予以规制;③聂婴智、张义豪:《劳动力市场的反垄断规制研究:基于对美国公司间“互不挖人”协议案例的借鉴》,《价格理论与实践》2022年第8期。另一方面,在司法裁判中,法院倾向于借用民法上的契约自由原理,认为经营者间达成包含互不挖人条款的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认定协议真实有效。④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01民终844号民事判决书。概言之,对于互不挖人协议,理论界主张适用《反垄断法》,而实务界则倾向于合同法一般原理的适用。在2021年的“台州市驾驶培训公司集体诉讼案”中,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引入了反垄断规制办法,认为驾驶培训公司之间的约定构成横向垄断协议,但法院并未明确指出互不挖人协议的反竞争特征,而是将其与薪酬固定协议一并审判。⑤见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1722号民事判决书。法院在司法裁判中舍近求远,虚置《反垄断法》而诉诸契约自由原理,甚至有意无意地淡化对相关协议的反竞争特征的提及,究其原因,是当下反垄断立法缺失对互不挖人协议的可操作性规定。由此观之,对于严重危害劳动力市场公平竞争的互不挖人协议,理论研究亟须跟进,以促成立法层面的制度完善。
为此,本文首先从互不挖人协议的两种类型出发,梳理和剖析其在反垄断法规制过程中所遭遇的冲突及成因;其次,基于垄断协议的实质判断标准,运用劳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论证对互不挖人协议适用《反垄断法》的正当性;再次,在分析对该协议适用《反垄断法》的可行性的基础上,借鉴域外经验,从短期、长期两个角度进行设计,提炼出适合我国国情的互不挖人协议反垄断法规制路径;最后,对《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反思,从价值目标、分析方法、豁免规则三方面提出具体修订建议,以期促成对互不挖人协议及其他劳动力市场垄断协议的有效规制。
一、互不挖人协议反垄断法规制的困境成因
互不挖人协议反垄断法规制困境的深层原因在于,其受到《反垄断法》中垄断协议二分法的桎梏。一方面,《反垄断法》对垄断协议作出横向垄断协议与纵向垄断协议的类型划分。在理想状态下,《反垄断法》的适用应以垄断协议符合这两种基本形态之一为前提。然而,另一方面,互不挖人协议依据其自身特点被划分为横向互不挖人协议与纵向互不挖人协议。其中,前者属于横向垄断协议,后者兼具纵向垄断协议与横向垄断协议的部分特征。这造成互不挖人协议超出了《反垄断法》的规制框架,甚至可能因此而被排除于《反垄断法》的适用范围。
(一)新兴协议类型:横向互不挖人协议与纵向互不挖人协议
根据协议订立主体之间的关系,互不挖人协议被划分为横向互不挖人协议与纵向互不挖人协议。①Bethany Hastie,“Platform Workers and Collective Labour Action in the Modern Economy,”University of New Brunswick Law Journal,Vol.71(2020):40-60.其中,横向互不挖人协议指在同一劳动力市场中,相互竞争的经营者之间达成的不雇佣或不招揽彼此员工的协议。这一协议本质上与《反垄断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横向垄断协议相同,即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间达成的联合抵制交易协议,其打乱了在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凭借自身技能获得相应薪酬的正常定价机制,具有显著的反竞争效果。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2022修正)第十七条:“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下列垄断协议:……(五)联合抵制交易……”例如,2010年美国司法部曾起诉苹果、谷歌、英特尔等六家科技公司,诉其签订互不挖人协议,因为这六家公司均在各自公司内部的管理条例中明确要求人力资源部门不得雇佣与本公司签订该协议的公司的员工。③Caitlin Somerman,“Recent Cases Caution Companies That Employment Practices May Be Scrutinized Under the Antitrust Laws,”antitrust news(18 January 2011),https://antitrust.weil.com/recent-cases-caution-companies-thatemployment-practices-may-be-scrutinized-under-the-antitrust-laws/.虽然该案的最终结果是美国司法部与被告的六家科技公司达成和解,法官亦未作出事实和法律认定,但是,美国司法部联合联邦贸易委员会2016年发布的《针对人力资源专业人士的反垄断指南》指出:“根据反垄断法,雇主之间赤裸裸的……互不挖人协议,无论是直接订立,还是通过第三方中介机构订立,本身都是违法的。”④Iadevaia & Michael,“Poach-No-More: Antitrust Considerations of Intra-Franchise No-Poach Agreements,”ABA Journal of Labor and Employment Law,Vol.35(2020):151-182.由此观之,横向互不挖人协议具有显著的违法性,是世界公认的严重违法行为。并且,横向互不挖人协议与《反垄断法》中横向垄断协议的构成要件相契合,应被纳入横向垄断协议的规制范围。因此,对横向互不挖人协议进行反垄断法规制较为简单,直接适用我国《反垄断法》关于横向垄断协议的法律规定即可。
与横向互不挖人协议不同,对纵向互不挖人协议的反垄断法规制存在明显困境。所谓纵向互不挖人协议,指在特许经营的情况下,特许人与加盟商之间以明示或者默示的方式达成的,要求多个加盟商不得雇佣或招揽彼此员工的协议。其最常见的形式是辅助性条款,即以约定条款之一的形式存在于特许经营合同中。例如,在“坚欢成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与上海力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案”中,原被告双方特许经营合同的第五条第四款约定,被告的所有直营店和原告的张杨路崮山路店之间不得招用彼此员工。⑤见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4民初9515号民事判决书。一般认为,由于纵向互不挖人协议的订立主体处于生产或经营的不同阶段,且彼此间不具备竞争关系,该协议通常被视为纵向垄断协议,落入《反垄断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纵向垄断协议兜底条款的规制范围。然而,事实上,纵向互不挖人协议与纵向垄断协议之间仍存在本质差异。一方面,就限制对象而言,典型的纵向垄断协议的限制对象为商品价格,而纵向互不挖人协议的限制对象为劳动力的流通;⑥见《反垄断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一、二项。另一方面,就实施要求而言,纵向垄断协议普遍要求在纵向层面履行协议,即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之间共同履行约定,而纵向互不挖人协议不仅要求特许人和加盟商的纵向执行,还要求诸加盟商的横向执行。申言之,纵向互不挖人协议有着横向和纵向的双重实施要求。如果只有特许人和加盟商之间的约定,而没有处在同一市场中的多个加盟商的相互配合、共同执行,就会造成纵向互不挖人协议流于表面,无法落实。在这一点上,纵向互不挖人协议反而与横向垄断协议存在相似之处。可见,虽然纵向互不挖人协议在形式上是纵向的,但其对加盟商具有横向的实施要求。相较于纵向垄断协议,纵向互不挖人协议的实施要求更高,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更加严重。因此,简单地将纵向互不挖人协议视为纵向垄断协议的类型之一,是对纵向垄断协议形式要件的认知偏差,系对纵向互不挖人协议的特征和反竞争效果的认识不足所致。
总之,诚如霍温坎普所言:“在反垄断法中,很少有哪个领域能够像纵向限制那样,更能引起人们对已经确立的规则进行反思。”①[美]赫伯特·霍温坎普:《联邦反托拉斯政策:竞争法律及其实践》(第3版),许光耀、江山、王晨译,法律出版社,2009,第489页。具体而言,对于横向互不挖人协议,适用反垄断法中横向垄断协议的有关规定便可以获得理想的规制效果;但纵向互不挖人协议则不然,鉴于其主体关系与纵向垄断协议相似,但实施要求却更加接近横向垄断协议,这种纵向与横向并存的特征造成其既不属于典型的横向垄断协议,又不属于典型的纵向垄断协议,难以满足垄断协议二分法的形式要求。纵向互不挖人协议与垄断协议二分法相冲突的后果在于,这不仅导致其反垄断法规制路径的选择困难,而且其可能被排除在反垄断法的规制范围之外,落入民法的合同自治领域。基于此,后文将专门探究纵向互不挖人协议的认定和规制办法。在后文中,除非特别指明,“互不挖人协议”一词专指“纵向互不挖人协议”。
(二)既有法律架构:垄断协议二分法
自2008年颁布以来,我国《反垄断法》一直采用垄断协议二分法,以此区分垄断协议的类型,即根据垄断协议形式的不同,将垄断协议区分为横向垄断协议与纵向垄断协议。前者指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的垄断协议,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较强;后者则指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的垄断协议,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相对较弱。垄断协议二分法的优势在于,其简单且清晰,提高了反垄断的执法效率。然而,面对纷繁复杂的经济生活,这一形式区分方法的弊端业已凸显。②张晨颖:《垄断协议二分法检讨与禁止规则再造:从轴辐协议谈起》,《法商研究》2018年第2期。对协议进行简单化和表象化的形式认定,不但难以应对日渐复杂的竞争市场环境,而且尤为重要的是,立法上的二分法极易导致执法实践中的法律形式化运用。过度关注垄断协议应归于横向还是纵向这一形式问题,不仅可能导致执法机关忽略垄断协议之所以违法和有害的实质内涵,形成框架效应,还可能助长规则操纵、选择性执法等不法行为,有损反垄断执法中的程序正义。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企业间的纵向关系和横向关系相互交织。尤其是在平台经济等新业态经济出现之后,层层转包的雇佣模式盛行,无法被简单区分为纵向与横向的商业关系在竞争市场中比比皆是。实际上,垄断协议二分法已无法周延覆盖所有具有反竞争特征的商事协议,亦无法合理评价所有垄断协议的实际反竞争效果,进而难免造成部分违法主体逃脱《反垄断法》的制裁。③郝俊淇:《论我国垄断协议类型序列的立法完善》,《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正是在此背景下,互不挖人协议作为一种新兴的垄断协议,难以得到有效规制。
“过分强调法的确定性,有可能导致一种无法容忍的僵化和刻板。”①[美]本杰明·N.卡多佐:《法律的成长》,李红勃、李璐怡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30页对于互不挖人协议而言,在垄断协议二分法的影响下,反垄断法执法机构必须首先根据互不挖人协议的形式来判断其属于横向垄断协议还是纵向垄断协议,然后才能具体选择如何适用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质言之,对于互不挖人协议的规制问题,形式吻合变成了该协议适用反垄断法的首要条件。
法律具有滞后性。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新产物,互不挖人协议难免与《反垄断法》产生冲突。究其原因,垄断协议二分法这种划分方式,是概括式的,是形式性的;而上文论及的互不挖人协议的类型划分,是依据协议实质特点作出的,是具体化的,是实质性的。当概括式的法律架构设计难以框定新兴协议的具体表现形式,当形式性的划分方式遭遇实质性内容的诘难,我们就必须重新审视甚至调整既定的法律形式设计。恰如美国学者巴拉克·奥巴赫所评论的,“从形式上将垄断协议区分为‘好’的纵向协议和‘坏’的横向协议充其量只是天真的想法。这种形式上的区分应逐渐淡化”②Barak Orbach,“The Durability of Formalism in Antitrust,”Iowa Law Review,Vol,100(2015):2213.。
二、互不挖人协议《反垄断法》规制的正当性证成
将互不挖人协议纳入反垄断法的规制范畴,对认定和规制互不挖人协议、有效遏制劳动力市场垄断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鉴于我国当前的垄断协议二分法桎梏,互不挖人协议超出了《反垄断法》的规制框架,甚至可能因此被排除于反垄断法的适用范围。为证成互不挖人协议反垄断法规制的正当性,应当对现有的垄断协议判断标准进行分析,从事实层面辨明互不挖人协议的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同时周延考虑互不挖人协议中经营者的行为动机和利益需求,兼顾实证分析和价值分析的双重考量。
(一)判断标准的实质回归
互不挖人协议的出现,对我国当下《反垄断法》中的垄断协议二分法提出了挑战。这种挑战的实质是对垄断协议判断标准回归实质化的呼唤。互不挖人协议是否属于垄断协议,以及其应否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或者说,其反垄断法适用的正当性基础何在?判断这些问题的标准,应当是实质性的,而非仅停留于形式层面。
诚然,垄断协议二分法有其合理之处,前文已述,垄断协议依此被区分为横向和纵向两种类型。这是因为,市场中的垄断协议通常存在横向与纵向两种基本形态,在排除、限制竞争的程度上,二者存在差异。与此二分法相对应,在《反垄断法》中,对垄断协议的具体规制路径分为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原则。③本身违法原则指针对企业的某些特定行为,不管事实是否已经产生了限制竞争的后果,均被视为非法垄断;合理原则指对某些行为是否在实质上构成限制竞争并在法律上予以禁止不是一概而论的,而是需要对经营者的动机、行为方式及其后果加以慎重考察后作出判断,予以认定的。参见种明钊主编《竞争法》,法律出版社,2008,第227页。这种形式化的区分方法源于对司法效率需求的回应。就横向垄断协议而言,由于其直接消灭了竞争者之间的竞争,反竞争效果较为明显,且其行为主体缺少行为正当性,故法院一般对其适用本身违法原则。①丁茂中:《现行〈反垄断法〉框架下维持转售价格的违法认定困境与出路》,《当代法学》2015年第5期。本身违法原则的适用可以减少法院的审理和调查程序,提高裁判效率。相比之下,对于纵向垄断协议的认定,则一般较为谨慎。原因在于,纵向垄断协议一般仅适用于限制品牌内部的竞争,而不至于影响整个市场的竞争秩序。同时,纵向垄断协议的签订可能具备合理的商业理由,如增进销售商之间的非价格竞争、减少企业交易成本、促进品牌间竞争等。因此,法院一般会运用合理原则,对纵向垄断协议进行个案分析,以免误判其反竞争效果。总之,垄断协议二分法的合理性在于,其在兼顾实质正义的同时提升司法效率。
然而,垄断协议二分法适用的时代背景早已不同往日。垄断协议二分法成型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美国联邦法院在1963 年的“白色汽车诉美国案”中首次提出了纵向垄断协议的概念。②See White Motor Co.V.United States,372 U.S.253(1963).彼时,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相对落后,商业模式单一,垄断协议的形式亦较为简单。纵向和横向两种形式便可以涵盖几乎所有的垄断协议。但时过境迁,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之间错综复杂的商业利益和合作模式已远非简单的形式化分类所能穷尽。除了互不挖人协议之外,固定薪酬、算法共谋等新兴垄断行为也对垄断协议二分法形成了冲击。因此,当纵向行为关系的竞争效果与人们的既往认识不再一致时,就到了正视垄断协议二分法现实局限性的时候了。
“人的视野是有限的,过于关注细枝末节,难免就会忽略那些具有普遍性的因素,就会忽略更重大的真相本身。”③[美]本杰明·N.卡多佐:《法律的成长》,李红勃、李璐怡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17页。垄断协议二分法仅是对垄断协议进行形式化、简单化区分的工具,实际上,排除、限制竞争才是垄断协议的实质危害,即根本特征所在。④王健:《垄断协议认定与排除、限制竞争的关系研究》,《法学》2014年第3期。根据《反垄断法》第十六条规定,垄断协议指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因此,排除与限制竞争,就是垄断协议的实质特征。垄断协议的实质性判断标准必须依此设立。面对互不挖人协议的反垄断法规制困境,应勇于抛弃垄断协议二分法这一形式上的区分工具,着重分析互不挖人协议的违法本质,即分析其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
(二)劳动经济学视野下的排除、限制竞争行为
“竞争法本质上是法律和经济学的混合体。”⑤Whish Richard & Bailey David,Competition Law(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4.“由于经济学与反垄断法的特殊关系,经济分析方法天然地成为探寻事实或者帮助进行事实认定的重要路径。”⑥孔祥俊:《论反垄断法的谦抑性适用——基于总体执法观和具体方法论的分析》,《法学评论》2022年第1期。我国司法解释也指明,人民法院可参考专业机构或专业人员出具的经济分析报告,对被诉垄断行为进行审查判断。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有鉴于此,本文选取劳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认定互不挖人协议的排除、限制竞争效果。
在劳动经济学视域下,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具有四个关键要素:大量公司相互竞争聘用特定劳动力,大量具有相同技能的人独立提供劳动服务,劳动者具有获取工资行为,具有完善的、无成本的信息和劳动力流动。⑧Davis,“Talent can't be allocated: labor economics justification for no-poaching agreement criminality in antitrust regulation,”12 Financial & Commercial Law,Vol.12(2018):279-310.在此四点要素的共同作用下,企业被迫向劳动者支付均衡工资(equilibrium wage)。如果企业提供的工资低于均衡工资,那么劳动者就可能去其他提供均衡工资的企业寻求工作。同样,劳动者也必须接受均衡工资,因为其工作能力和收入潜力在各企业中是统一的。“这种均衡工资、劳动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平衡状态正是获取工资行为的意义所在。”①Davis,“Talent can't be allocated: labor economics justification for no-poaching agreement criminality in antitrust regulation,”Financial & Commercial Law,Vol.12(2018):301.易言之,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工资是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均衡时的价格。均衡工资实现与否,影响着劳动者的工作意愿和企业的发展方向,亦代表着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状态。然而,互不挖人协议的实施损害了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关键要素,改变了劳动力市场中的均衡工资。很明显,它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现实效果。
首先,显而易见,互不挖人协议消除了经营者之间对特定劳动力的竞争。互不挖人协议所针对的劳动者,大多为具有专业技能的劳动者。例如,浙江省温州市民办教育协会发起的《温州市民办中小学教师流动的自律公约》规定,公约成员单位不得招聘其他学校合同期内的教师;②《温州46 所民办中小学签署教师流动自律公约》,载温州新闻网:https://news.66wz.com/system/2016/10/31/104926692.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3年10月27日。美国最大的代账公司H & R Block内部的特许经营协议要求,加盟商彼此不得互相雇佣经过其他加盟商系统培训的操作人员。③Michael Lindsay&Katherine Santon,“No Poaching Allowed: Antitrust Issues in Labor Markets,”Antitrust,Vol.26(2012):73-77.一直以来,在充分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具备专业技能的劳动者都是经营者竞争的关键。由于具备专业技能的劳动力数量较少,培训、教育成本较高,且专业技能可以为企业获得市场优势提供助力,所以经营者会不断拓宽招聘渠道来广泛吸纳具备专业技能的劳动者,甚至可能通过无预约电话(Cold Call)等方式来挖角其他企业中的成熟技术人员。然而,按照互不挖人协议的内容要求,诸经营者彼此不能互相雇佣或招揽对方的员工。这意味着,经营者主动放弃了对专业技能劳动力的招聘、招揽措施,该类劳动者亦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肆意剥夺了相关就业机会。在劳动力市场中,特定劳动力群体的竞争活跃度因此降低。
其次,互不挖人协议人为改变了劳动力市场中的均衡工资。英国经济学家阿弗里德·马歇尔从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研究了工资水平的决定因素。在他看来,在劳动力需求方面,工资取决于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边际生产力递增,经营者愿意支付的工资水平也会递增;在劳动力供给方面,工资则取决于劳动的生产成本和负效应,劳动的生产成本和劳动负效应愈高,劳动者对工资水平的需求就愈高。④劳动负效应指由劳动引起的不舒适、不愉快程度。劳动负效应需要由金钱或空闲来补偿。鲁品越:《当代理论经济学三大源流的哲学基因剖析》,《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当劳动力供给和需求达到一致时,劳动者获得的工资即为均衡价格工资。如前所述,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劳资关系平衡,且经营者向劳动者支付均衡工资。然而,互不挖人协议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劳资关系的平衡。以“德斯兰诉麦当劳美国有限责任公司案”为例,劳动者德斯兰想要跳槽到薪酬更高的麦当劳餐厅,但遭到拒绝,理由仅是麦当劳集团的特许经营协议中包含了互不挖人条款。⑤Catherine E.Schaefer,“Disagreeing over Agreements: A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of No-Poaching Agreements in the Franchise Sector,”Fordham Law Review,Vol.87(2019):2285-2311.此时,除非彻底离开麦当劳集团,否则德斯兰就只能被迫留在原麦当劳餐厅继续工作,接受更低的薪酬。由此可见,在互不挖人协议的影响下,劳动力需求方面的工资水平已不再取决于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而是受到经营者的主观意愿的强烈影响。即便经营者提供的工资低于均衡工资,劳动者出于稳定、维持生计的需要,也很可能会接纳经营者提供的较低工资。诚然,劳动者也可以选择去互不挖人协议覆盖范围之外的企业工作,但对经过长期培训或具备专业技能的劳动者来说,此举的沉没成本太高。由此可见,“互不挖人协议人为地降低了劳动力供应弹性,提高了经营者的市场力量,使经营者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低于他们的生产贡献”①Alan B.Krueger&Eric Posner,“Corporate America is Suppressing Wages for Many Workers,”N.Y.TIMEs(28 February 2018),https://www.nytimes.com/2018/02/28/opinion/corporate-america-suppressing-wages.html.。
最后,互不挖人协议限制了信息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一方面,互不挖人协议加剧了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劣势。在实践中,互不挖人协议的具体条款不仅包括禁止雇佣行为,还可能涵盖企业对薪酬、福利、员工资料等信息的分享行为。美国《针对人力资源专业人士的反垄断指南》规定,交换关于员工薪酬、雇用条件的特定信息或接收其他经营者内部薪酬数据的文档,均可能被认定为经营者间实施了“互不挖人”性质的行为,属于违反竞争规则的行为。②Cara Bayles,“Animators' Attys Defend $31.5M Fee Bid In Anti-Poach Deals,”Press News(11 April 2017),https://www-law360-com.ezproxy.bu.edu/articles/912024/animators-attys-defend-31-5m-fee-bid-in-anti-poach-deals.通过互不挖人协议,经营者的信息分享行为会抬高经营者的信息优势,加强经营者对劳动者的信息控制。同时,这种行为还可能演变为针对劳动者的信息屏蔽行为,如拒绝向其他企业员工披露福利待遇、联合固定劳动者薪酬等,从而进一步加剧劳资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劳动者的信息劣势会阻碍劳动力的自由流通。劳动者在劳资关系中的天然弱势地位,加之经营者的信息屏蔽行为,会造成劳动者对经营者的从属性大幅增强。换言之,囿于无法获得真实、及时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劳动者只能依赖于企业的单方面通知,无法认识到其薪酬待遇在当下市场中的真实水平,更难主动跳槽以寻求收入更高、福利更好的工作。因此,在信息壁垒之下,劳动者的选择自由权会受到侵害,劳动力难以在市场上自由流通。
总之,以劳动经济学视角观之,互不挖人协议严重损害了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的三项关键要素。虽然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在现实中很难实现,但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不应该是市场参与者人为操纵的结果;相反,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应当是有机的。互不挖人协议人为打破了劳动力市场的完全竞争状态,排除、限制竞争,具备垄断协议的实质特征,应被纳入反垄断法的规制范畴。
(三)合理动机掩盖下的排除、限制竞争行为
从经营者的角度看,其订立互不挖人协议,最主要的出发点是预防搭便车行为。③Michael Iadevaia,“Poach-No-More:Antitrust Considerations of Intra-Franchise No Poach Agreements,”ABA Journal of Labor and Employment Law,Vol.35(2020):151-182.搭便车行为指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受益者无须花费代价。在“威廉姆斯诉费舍尔案”中,美国内华达州法院曾认定,“互不挖人协议的目的是防止特许经营公司在他人花费时间和费用培训管理员工后‘抢夺’对方的管理员工”④Williams v.I.B.Fischer Nevada F.2d 445(9th Cir.1993).。前文已述,互不挖人协议签订的背景是特许经营。在特许经营中,特许人将商号、专利、经营模式等以特许经营合同的形式授予加盟商使用,加盟商则需要按照特许经营合同的要求进行经营活动。由于特许品牌大多具有专有技术和统一的经营模式,所以相较于普通经营者,加盟商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来培训员工,以满足特许经营合同要求。与高昂的员工培训成本相对应,劳动力流失所带来的加盟商利益损失也十分严重。因此,在逐利心理的驱使下,部分加盟商会挖角同一特许人旗下其他加盟商中已经培训成熟的员工,以降低员工培训成本,减少利益损失。此种不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力的行为便是搭便车行为。诚然,经营者防止搭便车行为的目的和动机具有一定合理性,其维护经营利益、规避经营风险的行为似在情理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经营者采取订立互不挖人协议这一限制市场竞争的方法来实现自身利益的做法是合理合法的,更何况,在应对搭便车行为时,订立互不挖人协议并非经营者维护经营利益的唯一途径。在多数情况下,经营者可以通过签订竞业限制协议来替代互不挖人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相关法律已经构建了较为完善的竞业限制协议制度。签订竞业限制协议不仅可以降低员工的离职风险,保护专利技术培训成果,而且于法有据,不至于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经营者还可以通过提升福利待遇来留住劳动者。对此,正如搭便车理论的提出者曼瑟尔·奥尔森所说:“组织的实质之一就是它提供了不可分的、普遍的利益。”①[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第12页。
除预防搭便车行为外,互不挖人协议的另一个目的是控制劳动力成本,提升品牌竞争力。②Clayton J.Masterman,“The Customer is Not Always Right: Balancing Worker and Customer Welfare in Antitrust Law,”Vanderbilt Law Review,Vol.69(2016):1397-1422.互不挖人协议的订立者认为,该协议有助于节省用工成本,进而有助于降低产品价格,从而推动不同品牌在产品市场中的竞争,使消费者获利。表面上,这一观点从产品市场的角度证否了互不挖人协议的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实则具有显著局限性。一方面,工资上涨对商品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有经济学家在汇总多项研究后发现,餐厅价格上涨3%可以抵消工资增长20%所带来的任何损失。③Robert Pollin & Jeannette Wicks-Lim,“A $15 U.S.Minimum Wage: How the Fast-Food Industry Could Adjust Without Shedding Jobs,”Economy Issues,Vol.50(2016):716-727.工资上涨可以提升劳动者对岗位的满意度,从而降低人员流动成本。同时,工资上涨还能够激发劳动者的工作热情,挖掘劳动者的工作潜力,进而减少培训时间和人工成本。虽然互不挖人协议对产品价格的影响是真实的,但这种影响非常小,尤其是与工资增长所带来的社会福利相比。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互不挖人协议同样会对产品市场竞争产生负面影响。如前所述,特许经营商通过订立互不挖人协议来防止劳动者离职,然而市场中的中小企业却无法阻止劳动者去其他企业工作。因此,在互不挖人协议的影响下,中小企业只能被迫支付更高的工资或面临更高的员工流失率,竞争劣势被不断放大,中小企业的正常经营难以维系。中小企业数量的减少乃至消失,从长远来看,会造成产品市场中的寡头垄断或多头垄断,严重削弱产品市场竞争,最终损害消费者利益。
准此而言,经营者行为动机表面上的合理性,不足以赋予互不挖人协议足够的正当性。订立互不挖人协议不属于正常商业行为的范畴。作为排除、限制劳动力市场竞争的行为,互不挖人协议的签订理应得到反垄断法的有效规制。
三、互不挖人协议《反垄断法》规制的路径选择
规制路径的选择涉及当事人的举证负担和执法机构调查的难易,直接关涉垄断协议的法律规制效果。①张晨颖:《垄断协议二分法检讨与禁止规则再造——从轴辐协议谈起》,《法商研究》2018年第2期。下文将在法律适用层面分析互不挖人协议适用合理原则或本身违法原则的可行性。而后,在反思和借鉴互不挖人协议的域外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该协议的特殊性和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特征,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设计适合我国国情的理想规制路径。
(一)适用可行性:合理原则还是本身违法原则
前文已述,与垄断协议二分法相对应,合理原则和本身违法原则是适用《反垄断法》规制垄断协议的两条具体路径。然而,鉴于互不挖人协议既具有纵向垄断协议的主体关系特征,又具有横向垄断协议的实施要求,因此互不挖人协议的反垄断法规制有两种基本方法:其一,从法解释学的角度,通过解读《反垄断法》第十八条,将互不挖人协议纳入合理原则的规制范围;其二,采取类推适用的方法,对其适用本身违法原则。
显然,通过合理解释现有法律规定来解决互不挖人协议的反垄断法规制难题是最为经济的途径。在《反垄断法》中,最具有解释潜力的条款是其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即“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下列垄断协议:……(三)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这一条款是认定纵向垄断协议的兜底条款,落入合理原则的适用范围。如前所述,互不挖人协议在形式上与纵向垄断协议十分相近。特许人和加盟商可以被视为经营者和交易相对人,交易标的物为商标、专利技术等特许经营内容,双方签署的互不挖人协议具有一定的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因此,依据文义解释,只要反垄断执法机构明确将互不挖人协议认定为垄断协议,那么就可以运用合理原则对其进行规制。
然而,合理原则这一规制路径并不全然适合互不挖人协议。一方面,合理原则的运用会加重司法裁判的负担。合理原则的设立本意是保证司法公平,防止因反竞争效果轻微的或不存在反竞争效果的协议被执法机构施以过重处罚。按照合理原则的要求,反垄断执法机构和法院需要综合考量事实影响、潜在效果、救济措施等多方面情况,才能认定协议违法。②Se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v.United States, 246 U.S.231 (1918).对于构成要素相对简单的互不挖人协议来说,此种垄断协议认定方式过于烦琐。申言之,互不挖人协议直接限制了同一市场中经营者对劳动力的竞争,必然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反竞争效果。其表现和影响均相对直观,若严格按照合理原则对其各方面进行仔细、全面考察,实属不合理地加重司法裁判的负担,会降低反垄断执法的效率。另一方面,合理原则的程序复杂性会加重原告的举证负担,造成原告胜诉率低、反垄断实施弱化等问题。③兰磊:《重估合理原则的制度成本——兼评〈制度成本与规范化的反垄断法〉》,《经贸法律评论》2020年第3期。互不挖人协议的反垄断诉讼既可以由检察机关等公权力机关提起,也可以由权益受损的劳动者提起。相较于公权力机关和订立互不挖人协议的经营者,劳动者不仅容易受到经营者的威胁或蒙蔽,而且通常缺乏法律知识储备和收集证据的能力。劳动者天然的弱势地位,加之合理原则较高的证明要求,导致劳动者很可能因证明能力不足而主动放弃对互不挖人协议的追诉。即便劳动者主动提起诉讼,败诉的概率也往往很高。因此,通过合理解释将互不挖人协议纳入合理原则的适用范围,虽然具备程序上的合理性,但在实质效果层面仍存在不足之处。
那么,除合理原则外,对于互不挖人协议,是否可以适用本身违法原则?在我国《反垄断法》中,本身违法原则体现为第十七条针对横向垄断协议的规定。由于互不挖人协议在实施要求、反竞争效果上与横向垄断协议相似,因此可采取类推适用的方法,将互不挖人协议纳入本身违法原则的规制范围。①类推适用指对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争议案件,援引类似案件适用的法律规定。梁慧星:《民法解释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5,第274页。按照本身违法原则的要求,无论互不挖人协议是否产生了排除、限制竞争的现实效果,只要经营者订立了该协议,就被视为实施了垄断行为。
必须承认的是,本身违法原则有助于弥补合理原则在实质层面的适法效果缺陷;但是,运用它来规制互不挖人协议,亦存有实质弊端。首先,并非在所有的互不挖人协议案件中均可采取类推适用的法律方法。事实上,互不挖人协议的反垄断执法分为行政执法和民事诉讼两种情形。在民事诉讼中,法官可以通过类推适用来填补法律漏洞。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第七条。然而,在行政执法中,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受到严格限制,缺少类推适用的法律依据。“法无授权不可为”,这要求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时刻保持谨慎和克制。③马光泽:《论指导性案例类推适用的方法及限制》,《中山大学法律评论》2022年第2辑。其次,运用本身违法原则来规制互不挖人协议,易使部分违法主体免于《反垄断法》的制裁。如前所述,本身违法原则是《反垄断法》中针对横向垄断协议设计的具体规制路径。其规制对象为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即互不挖人协议中处在同一市场中的多个加盟商。作为互不挖人协议的牵头者,特许人的反竞争行为反而易被本身违法原则所忽视。由此可见,本身违法原则缺少对互不挖人协议之纵向形态的有效评估,易使订立协议的特许人逃脱法律制裁。最后,虽然互不挖人协议的反竞争效果较为明显,但直接将其纳入本身违法原则的规制范围,未免有些矫枉过正。本身违法原则适用于总是或者几乎总是限制竞争和降低产出的限制行为。④Mark A.Lemley & Christopher R.Leslie,“Categorical Analysis in Antitrust Jurisprudence,”Iowa Law Review,Vol.93(2008):1207-1270.易言之,本身违法原则的适用范围很窄,仅适用于通过长期经验证明具有持续反竞争性的行为。作为近年来新兴的垄断协议,互不挖人协议的实际效果尚未经过实践和司法的长期检验。同时,互不挖人协议存在于特许经营中,影响范围受限于特许经营的规模。即便该协议的内容直指劳动者,必然对劳动力竞争产生负面影响,但对于其在现实劳动力市场中的反竞争程度,仍需结合主体市场地位、相关市场状况等因素来衡量。当然,这种衡量应当是有限度的,否则又会产生与合理原则类似的负面影响。总之,使用本身违法原则来规制互不挖人协议,在程序和实质两个层面均存在一定弊端。
综合来看,合理原则和本身违法原则皆无法完全满足互不挖人协议的反垄断法规制需求。相较于合理原则,本身违法原则的规制缺陷更甚。因此,对于互不挖人协议的规制路径而言,要么对合理原则进行改良,要么另辟蹊径。
(二)美国经验:从合理原则到快速审查原则
对互不挖人协议的反垄断法规制路径,美国有着较为成熟的司法实践经验。在互不挖人协议纠纷出现的早期,美国法院多采用合理原则。例如,在1957 年的“美国联合流通公司诉联邦贸易委员会案”中,美国联邦法院就曾采取合理原则对互不挖人协议的违法性进行认定。在该案中,美国联邦法院指出:“如果抵制行为对竞争的有害影响从表面上看并不像那些被认定为本身违法的协议那样明显,那么法院或委员会就应考量这种抵制行为对受影响行业竞争的实际或潜在影响。”⑤Union Circulation Co.v.FTC, 241 F.2d 652 (1957).同时,针对互不挖人协议本身,美国联邦法院指出:“互不挖人协议看起来是针对签约组织的内部行为,由于从协议条款中看不出对竞争的有害影响,所以我们认为它与那些本身违法的抵制行为是有区别的。”①Mark A.Lemley & Christopher R.Leslie,“Categorical Analysis in Antitrust Jurisprudence,”Iowa Law Review,Vol.93(2008):1207-1270.这一案件是美国首批涉及互不挖人协议的案件之一。虽然法院最终裁定联合流通公司签署互不挖人协议属于《谢尔曼法》规定的垄断行为,但从裁判方法和裁判理由中不难看出,美国法院早期对互不挖人协议持相当谨慎的态度,对互不挖人协议排除、限制竞争的现实效果亦未达成确信。
随着市场发展和互不挖人协议纠纷的增多,美国法院的主流裁判观点逐渐转向了采用快速审查原则(“quick look”rule of reason analysis)。快速审查原则是介于合理原则和本身违法原则之间的一种垄断协议规制原则,有时也被称为有限合理原则或截断式合理原则。②Max R.Shulman,“The Quick Look Rule of Reason:Retreat from Binary Antitrust Analysis,”Sedona Conference Journal,Vol.2(2001):89-96.美国法院通常将快速审查原则适用于在传统反垄断分析中被认为是不合法的,但发生在新的或不熟悉的市场或环境中的限制竞争行为。③Catherine E.Schaefer,“Disagreeing over Agreements: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of No-poaching Agreements in the Franchise Sector,”Fordham Law Review,Vol.87(2019):2285-2311.换言之,快速审查原则的适用对象是存在一定反竞争表征,但并未经过实践长期检验的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美国联邦法院曾对此类行为的具体反竞争程度进行概括,结论是“对经济学有基本了解的正常人能够判定该行为会对客户和市场产生反竞争影响”④Cal.Dental Ass'n v.FTC,526 U.S.756,770(1999).。基于此,美国法院大多采用快速审查原则来规制互不挖人协议。在快速审查原则下,法院首先假定互不挖人协议构成垄断协议,而原告只需证明其合法权益受到了互不挖人协议的侵害,被告则需承担主要证明责任,证明其行为有利于竞争。如果被告能够提供充分的证明理由,法院将根据合理原则权衡被告的理由与所指控的反竞争损害;但如果被告不能提供充分的理由,其就需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⑤Jay P.Yancey,“Is the Quick Look Too Quick: Potential Problems with the Quick Look Analysis of Antitrust Litigation,”University of Kansas Law Review,Vol.44(1996):671-706.美国法院向来关注互不挖人协议中可能存在的有利于竞争的内容。例如,在2017 年的“保帝斯卡诉卡尔-卡尔奇企业案”中,美国洛杉矶高等法院曾指出,要考虑品牌间竞争的普遍益处和互不挖人协议对品牌间竞争的促进作用,鼓励单一商标企业内部的有效合作。⑥Bautista v.Carl Karcher Enters.LLC,No.BC649777(Cal.Super.Ct.L.A.City.Feb.8,2017).
由此可见,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互不挖人协议的反竞争特征逐渐得到了普遍的认可,法院适当减少了对互不挖人协议的认定程序。同时,由于互不挖人协议的签订可能存在一定的合理事由,所以美国法院保留了对互不挖人协议细节的适当考量,拒绝将互不挖人协议视为本身违法行为。
值得肯定的是,美国法院所采用的快速审查原则打破了垄断协议二分法的桎梏,其能够在督促法官对互不挖人协议进行充分考察的同时,适当减轻法官的裁判压力和原告的举证压力,为互不挖人协议的反垄断法规制提供了一条更为合适的路径。然而,快速审查原则在审查内容上的缺漏,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危及反垄断执法的公正性。具体而言,按照快速审查原则的要求,法官应通过推定来判断被诉行为是否为垄断行为。法院在通过推定得出确切结论后,其以被诉行为构成垄断为前提,仅接受被告提交其行为有利于竞争的目的和理由,而不接受被告提交其行为不具备现实反竞争效果的理由。①Can Erutku,“The Quick-Look Approach in Antitrust Analysis,”Canadian Business Law Journal,Vol.46(2008):50-65.也就是说,即便被诉行为从一开始就不具备排除、限制竞争的实际效果,但在法官作出推定后,被告提出的相关证据对法院的审判结果而言也是无效的。这种审判方式实际上削弱了被告在诉讼中的证明权利。此外,在互不挖人协议的违法性尚未得到司法实践长期检验的前提下,快速审判原则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水平要求较高,可能会使公众对法官审判结果的合理性产生怀疑。
(三)理想路径:基于协议特殊性与劳动力市场特征的双重考量
“法律的本质不在于空洞的原理或抽象的价值。”②[美]尼尔·K.考默萨:《法律的限度——法治、权利的供给与需求》,申卫星、王琦译,商务印书馆,2007,第3页。以规制对象为基础,以社会现实为指引,才能更好地完善立法。如前所述,互不挖人协议的反垄断法规制路径要么选择对合理原则进行改良,要么选择另辟蹊径。但无论如何选择,均需在尊重互不挖人协议特殊性的基础上,充分考量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及劳动者的需求。
互不挖人协议的特殊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形式上的特殊性,即其在主体关系上属于纵向垄断协议,但又在实施要求上与横向垄断协议十分相似,兼具横向垄断协议与纵向垄断协议的部分特征;二是反竞争效果上的特殊性,即从劳动经济学视角观之,其具有较为明显的排除、限制竞争效果,但其实际反竞争效果却尚未经过我国司法实践的长期检验,反而可能存在一些有利于竞争的现实影响。
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人力资本与劳动力经济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本指数报告2023》显示,截至2021 年,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75 年,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仅为23.24%。③《中国人力资本指数报告(中文版)-2023》,载中国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网:http://humancapital.cufe.edu.cn/rlzbzsxm/zgrlzbzsxm2023/zgrlzbzsbgqw_zw_.htm,最后访问日期:2023年11月10日。相比之下,同期的加拿大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4.6 年,美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3.4 年。④吴瑞君等:《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载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网:https://mp.weixin.qq.com/s/oKfP9RVcIK-fKKwn_kTkig,最后访问日期:2023年11月10日。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偏低,导致我国劳动者在面对互不挖人协议时维权能力较弱,且很可能缺少对自身权益边界的清醒认识。其次,工会在我国劳动力市场运行过程中尚未充分发挥作用。工会组织的集体谈判是劳动力市场机制运行的必要条件。通常来说,集体谈判能够增强劳动者一方的议价能力,克服劳动关系中的内在不平衡,是化解劳资冲突的一种重要方式。然而,事实上,我国工会的覆盖范围十分有限,且独立性较差,加之雇主角色不明、雇主组织缺位等问题,集体谈判的作用难以有效发挥。⑤程延园:《集体谈判制度在我国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在互不挖人协议案件中,劳动者的弱势地位无法得到有效矫正。最后,新业态逐渐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新常态。随着新业态的蓬勃发展,一方面,工作灵活性开始成为新业态劳动者择业的主要原因,而互不挖人协议对劳动力流通的负面影响被不断放大;另一方面,三角用工模式在以外卖平台为主的新业态企业中流行开来,这导致劳动力市场中的主体确认和责任分配愈发困难。①王茜:《平台三角用工的劳动关系认定及责任承担》,《法学》2020年第12期。在这一社会背景下,认定和规制互不挖人协议,不仅会造成司法裁判的难度和成本大大增加,还会进一步加重诉讼中原告的举证负担。
总之,结合互不挖人协议的特殊性和劳动力市场的特征,本文认为,对互不挖人协议的反垄断法规制,应当保持相对审慎的态度,同时也应周延考虑弱势群体利益和司法裁判压力。对此,可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着手,确定互不挖人协议的反垄断法规制的理想路径。
从短期来看,可以通过合理解释,将互不挖人协议纳入《反垄断法》第十八条之合理原则的规制范围,同时,在司法裁量中,适当减轻互不挖人协议诉讼中原告的证明责任。如果原告为劳动者、小微企业经营者等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群体,那么司法机关或反垄断执法机构应积极发挥能动作用,为原告提供合理援助。从长期来看,则可以借鉴美国的司法实践经验,在《反垄断法》中增设一条实质性的垄断协议规制路径,以容纳互不挖人协议以及其他可能出现的新兴的非典型横向或纵向垄断协议。在司法裁判中,应首先假定该协议具备一定的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由原告初步证明其权益受到了被诉协议的损害,再由被告承担主要的证明责任。同时,法官应当接受被告提出的不具备现实反竞争效果的理由,考察其提出的有利于竞争的理由是否具备必要性和合法性。例如:被告目的是否合法?被诉行为是否能够实现被告的目的?被诉行为是否存在反竞争性更弱的替代措施?等等。
四、互不挖人协议《反垄断法》规制的制度因应
长期以来,囿于我国《反垄断法》对劳动力市场的忽视,现有的垄断协议规制办法难以为互不挖人协议的规制实践提供有力支撑和具体指导。基于此,应对《反垄断法》进行适当调整,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包括签订互不挖人协议在内的劳动力市场垄断行为的规制需求。
(一)明确《反垄断法》对劳动者利益的保护
竞争是反垄断法的立身之本,而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是竞争市场的“一体两面”。②吴宏伟、金善明:《社会本位观:反垄断法立足之本》,《法学家》2008年第1期。对于劳动力市场竞争和产品市场竞争之间的关系,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言:“经营者利用产品市场力量和劳动力市场力量的获利方式是相同的,都是通过提高价格或降低成本来增加利润。”③Iadam 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Clarendon Press,1976,P.1776.由此可见,在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中,经营者均可能出于逐利心理而实施破坏竞争的垄断行为。而劳动者和消费者正是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中垄断行为的利益受损方。作为市场中的平等主体,劳动者和消费者二者的利益没有高低位阶之分,理应受到反垄断法平等且全面的保护。然而,事实上,依据《反垄断法》第一条的规定,《反垄断法》所保护的特定群体利益仅为消费者利益。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一条:“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鼓励创新,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这一规定从立法上忽视了同样受到垄断行为侵害的劳动者利益。这不仅影响法律解释的边界,间接导致了长时间以来反垄断执法机关对劳动力市场垄断行为的忽视,而且很可能形成负面的示范效应,对反垄断诉讼过程中的法官裁量造成错误指引,使诉讼中的劳动者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针对反垄断法保护劳动者利益的重要性,有学者曾提出反对观点,认为在反垄断法之外已经有足够的保护劳动者利益的有效方法。具言之,在面对互不挖人协议等劳动力市场垄断行为时,劳动者可以依据工会法,通过加入工会和集体谈判来阻止经营者支付垄断性工资;同时,劳动者还可以依据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获得关于最低工资、最长工时、安全工作场所等的具体法律保护。①Shaun Ossei-Owusu,“The Sixth Amendment Facade: The Racial Evolution of the Right to Counsel,”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Vol.167(2018):1161-1240.诚然,劳动法领域的法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但其并不足以遏制劳动力市场中的垄断行为。一方面,就覆盖范围而言,劳动法中的劳动者与市场中的劳动者有所不同。劳动法对劳动者的保护以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与用人单位成立劳务关系的劳动者不在劳动法的保护范围,无法获得劳动法为劳动者提供的各项具体保护。另一方面,就实践效果而言,工会在集体谈判中发挥的作用往往不尽如人意。前文已述,我国工会在市场运行中的缺位状态由来已久。劳动者凝聚力低、经营者拒绝谈判等现实问题造成工会的集体谈判功能难以有效发挥。更何况,在垄断行为中,经营者的优势地位被进一步放大,工会缺少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去“迫使”经营者接受谈判条件。总之,除非《反垄断法》对劳动力市场垄断行为予以专门规制,否则劳动者权益很难得到全面保障。
“立法的本质就是利益衡量的过程。”②梁上上:《利益衡量论》,法律出版社,2013,第95页。劳动者利益和消费者利益都是受到垄断行为侵害的合法利益。对此,《反垄断法》应予以平等对待,提高对劳动者利益的重视程度,明确将劳动者利益纳入《反垄断法》第一条关于价值目标的规定之中。此举既有助于提高反垄断执法机关对互不挖人协议的重视程度,还可为互不挖人协议及其他劳动力市场垄断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提供有力支撑。
(二)重设界定相关市场的分析方法
界定相关市场,是判断经营者的市场行为是否构成垄断的基础,在反垄断案件中常常具有决定性的意义。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济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61页。根据《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界定相关市场可以采取“假定垄断者测试(SSNIP)”的分析方法,即“小而显著非临时性涨价(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这是目前世界范围内界定相关市场的主流方法,也是我国通行的方法。考虑到法的稳定性,对劳动力市场中相关市场的界定可以比照“假定垄断者测试”,并对其分析框架进行适当调整。调整后的“假定垄断者测试(SSNDW)”可被称为“小而显著非临时性工资减少(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 Decrease in Wages)”。④Suresh Naidu,Eric A.Posner & Glen Weyl,“Antitrust Remedies for Labor Market Power,”Harvard Law Review,Vol.132(2018):526-601.为了实施“假定垄断者测试(SSNDW)”,首先要界定一个候选市场,而后,应假定这个候选市场上的所有劳动者都在一个假定的垄断公司内工作。当假定垄断公司将劳动者薪酬持续性地减少5%左右,并且候选市场外其他公司的劳动者薪酬维持原状时,观察是否仍有大量劳动者留在假定垄断公司内工作。如果大量劳动者选择去候选市场之外的其他公司工作,那么就说明候选市场的界定过于狭窄,因为候选市场之外的其他公司对候选市场内的假定垄断公司有着足够的替代性,对候选市场产生了直接的竞争压力。接下来,则需扩大候选市场,将之前的候选市场之外的公司纳入新的候选市场。此后,重复“假定垄断者测试(SSNDW)”,以确定劳动力市场中相关市场的界限。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中相关市场的实际范围可能受到一些特殊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匹配市场。①Lee Goldman,“The Labor Exemption to the Antitrust Laws as Applied to Employers' Labor Market Restraints in Sports and Non-Sports Markets,”Utah Law Review,Vol.3(1989):617-686.在产品市场中,买卖双方的交易只考虑产品的功能和价格;而在劳动力市场中,不仅经营者会根据生产需要寻求具备特定技能和特定身份的劳动者,而且劳动者也会根据工作条件和薪酬待遇,选择符合自身要求的工作岗位。除此之外,劳动者和经营者二者的性格和喜好也会影响彼此的选择。由此可见,相较于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交易需要买卖双方的双向选择,经营者和劳动者之间匹配和协调的难度更大,相关市场的范围也相应变得更加狭窄。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中相关市场的范围还可能受到劳动者流动性的影响。也就是说,劳动者个人的通勤意愿和通勤能力会影响劳动力市场中相关市场的边界。如果劳动者有能力选择速度更快的通勤方式,或者愿意付出更多的通勤时间,那么市场的集中度就会下降,相关市场的范围将得到扩大。然而,事实上,劳动者的通勤意愿和通勤能力参差不齐。比如,青年劳动者的流动性较好,而年长劳动者或已有子女劳动者的流动性则相对较弱。这一现象使得劳动力市场中相关市场的界定更为复杂。
就此而言,可以通过司法解释、反垄断指南或规章等形式,引入针对劳动力市场中相关市场的“假定垄断者测试(SSNDW)”分析方法,以为互不挖人协议等劳动力市场垄断协议的反垄断法规制提供技术支持。同时,还可以考虑借用产品市场中的“临界损失分析法”,来对“假定垄断者测试(SSNDW)”的分析结果进行重复检验。“临界损失分析法”来源于美国《竞争法》,其通过比较假定垄断者的实际损失和临界损失,来确定假定候选市场的边界是否需要进一步扩大。虽然“临界损失分析法”和“假定垄断者测试(SSNDW)”的分析原理都是对需求弹性和可变成本的考察,但前者相对直观,对数据获得的要求较低,且计算简便。②丁茂中:《美国反垄断法中界定“相关市场”的临界损失分析法》,《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因此,倘若在适用“假定垄断者测试(SSNDW)”后仍难以确定劳动力市场中相关市场的具体边界,则可以采取“临界损失分析法”进行佐证。
(三)调整《反垄断法》垄断协议的豁免规则
集体谈判是弥补劳动者弱势地位的重要工具。为开展集体谈判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有助于发挥集体谈判的真实作用,帮助劳动者对抗互不挖人协议的签订等劳动力市场垄断行为。按照工会法的要求,集体谈判的主体应当具备法律上的劳动者身份。所谓“法律上的劳动者”,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规定的、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主体。但是,在现实情况中,集体谈判主体不仅包括法律上劳动者,还包括不具备法律上劳动者身份的广义劳动者。这类广义劳动者通常存在于外卖平台企业中,如外卖送餐员等。该群体虽未与经营者订立劳动合同关系,但受到经营者的严格管控,与法律上的劳动者一样处于劳资关系中的弱势地位,需要借助工会的力量和集体谈判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七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推动建立适应新就业形态的工会组织,积极吸纳外卖送餐员群体入会,引导帮助外卖送餐员参与工会事务。”除此之外,山东省总工会、上海市总工会等地方工会也都带头开展了针对外卖送餐员等不具备法律上劳动者身份的广义劳动者的集体协商活动。①《团结奋斗开新局 喜迎工会十八大|京东、“饿了么”、顺丰……平台企业集体协商从“点上探索”向“面上推开”》,载工人日报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8218376497578289&wfr=spider&for=pc,最后访问日期:2023年11月20日。总之,就主体身份而言,集体谈判的主体与法律上的劳动者有所不同。这既是集体谈判的当下现实情况,也契合各级工会的工作要求。
然而,主体身份的差异造成集体谈判与《反垄断法》之间存在潜在张力。具体而言,由于集体谈判主体并不全然具有法律上的劳动者身份,所以其组建和参加工会,就交易条件与经营者进行谈判的行为,可能涉嫌违反《反垄断法》。依据《反垄断法》第十五条的规定,经营者是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在集体谈判中,若谈判主体被排除在法律上的劳动者的范围之外,则可能会落入《反垄断法》规定的“经营者”范畴。②班小辉:《超越劳动关系:平台经济下集体劳动权的扩张及路径》,《法学》2020年第8期。申言之,尚未成立劳动关系的集体谈判主体可以被视为向经营者提供服务的自然人,而这恰好符合了《反垄断法》对“经营者”的定义。于此情形,这些不具备法律上的劳动者身份的广义劳动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属于民法上的合作关系。如果该类劳动者在工会组织下,通过联合抵制与经营者交易、固定或降低企业服务费提取比例等集体协同行为,与经营者进行谈判,那么这一行为就可能被视为垄断行为。在集体谈判的过程中,如果该类劳动者最终与经营者达成了固定工资价格的集体协议,那么这一协议就可能涉嫌构成垄断协议。因此,从法律适用的逻辑上看,劳动者在不具备法律身份的状态下,与经营者进行集体谈判,有违反《反垄断法》之嫌。
因此,为了增强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实现对互不挖人协议等劳动力市场垄断协议的有效规制,可考虑调整《反垄断法》中的垄断协议豁免制度,巩固集体谈判制度的正当性。一方面,应明确《反垄断法》对合法工会活动的豁免。在短期内,可以借鉴欧盟的司法实践经验,通过颁布司法解释,将工会成员视为其所在企业的一部分。③Marshall Steinbaum,“Antitrust,the Gig Economy,and Labor Market Power,”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Vol.82(2019):45-64.按照单一经济体理论,同一法律实体内部有关工资和劳动条件的集体谈判活动不受反垄断法的调整。从长远来看,则可以通过法律修订,将工会组织实施的有利于保护工会成员合法权益的行为纳入《反垄断法》第二十条之垄断协议的豁免范畴,为豁免集体谈判提供更加直接的依据。另一方面,应修改垄断协议中的消费者福利判断标准。依据《反垄断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适用豁免规则的经营者应当证明所达成的协议不会严重限制相关市场的竞争,并且能够使消费者分享由此产生的利益。这一判断标准,显然不能适用于对互不挖人协议等其他劳动力市场垄断协议的认定。对此,本文认为,可以放弃消费者福利判断标准,将其修改为“能够使市场中其他主体分享由此产生的利益”,以此实现《反垄断法》对劳动力市场中和产品市场中的垄断行为的平等规制。
结语
作为劳动力市场中的新兴垄断协议,互不挖人协议对市场竞争的发展和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均有重要影响,亟待得到《反垄断法》的有效规制。认定和规制互不挖人协议,需从其不同类型出发,关注其特殊性以及法律适用过程中存在的潜在冲突。通过反思垄断协议二分法,透视其限制、排除竞争的现实效果,可证成《反垄断法》适用的正当性。对互不挖人协议反垄断法规制的路径选择,则应在充分考量合理原则与本身违法原则之适用合理性的基础上,批判性借鉴域外经验,结合我国劳动力市场特点及互不挖人协议自身性质,进行探索。同时,应周延考虑《反垄断法》中关于垄断协议认定的制度漏洞,针对互不挖人协议及其他劳动力市场垄断协议,为未来的法律修订做好理论储备。未来,应建立更加全面完善的垄断协议评估体系,甚至可探索建立规制互不挖人协议的专门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