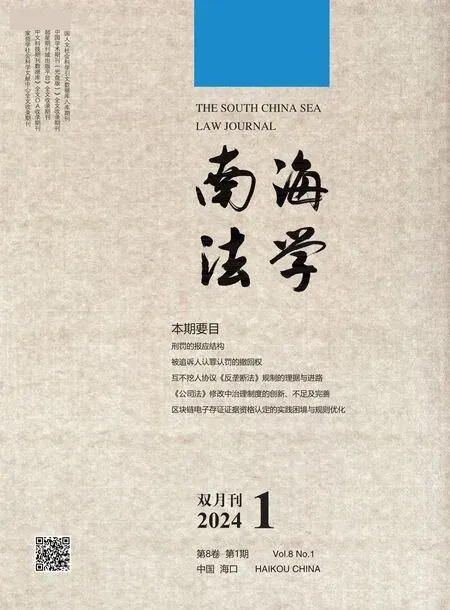刑罚的报应结构
[俄]尼古拉·季马舍夫 著 徐歌旋 译 姚 远 校
(南京师范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一、犯罪与刑罚是条件反射吗?
先有犯罪发生,后有社会反应。这一反应自古以来被冠以“刑罚”之名。就如同个体反射中的“刺激—反应”次序,“犯罪—刑罚”的发生次序似乎是自然且必然的。我们可能会论及惩罚的社会文化反射,“社会文化反射”这一名词是不同个体行为序列的简称,一些个体的先前行为通常会引发其他人的随后行为。
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谨记这些相似性只停留于表面。在所研究的这个行为序列类型中,刺激和反应都不是由自然确定的,而是由社会决定的;刺激和反应之间的联系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社会强制力塑造的;必须有基于社会交往的人类意志的协调处置,才能实现社会反应。
在“犯罪—刑罚”序列中,什么是由社会决定的?首先是惩罚性反应。构成这种反应的那些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一般是由社会预先确定的,而不是由个人好恶决定的:由习惯规则或者法律规则决定社会对于犯罪如何反应。犯罪也是由社会决定的:习惯规则或者法律规则勾勒出应受罚行为的范围,形塑出刑法的“行为内容”。①Michael,J.and M.Adler,Crime,Law and Social Science(New York,1933),p.20.许多犯罪学家没有觉察到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经常有人指出犯罪是以“规范”的形式被决定的,这阻碍了犯罪的因果关系研究。因此,一些学者试图独立于实在法,揭示出犯罪的自然概念。②R.Garofalo,Criminologia(first Italian edition 1855;pp.1-52 of the fifth French edition,Paris,1905).当然,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习惯和法律都是社会现象,因此,通过习惯或法律确定应受罚行为的范围也是一个社会过程。
在先天个体反射的情况下,刺激和反应之间不可能出现失调情况。这种失调情况在后天或条件反射中可能存在:在某些情况下,刺激可能是一个错误的信号,会引起一种没有生物效用的反应。社会文化反射中的失调情况更为常见。为了研究在犯罪—惩罚序列中可能出现失调的原因,我们必须区分其基础结构和非常复杂的上部结构或上层建筑。如果一个结构与人类行为的自然倾向密切相关,那么它就是基础结构。原初结构大体也是基础结构,在原初结构中,自然比文化发挥着更重要的影响;但是基础结构当然可见于后来复杂结构的内核——因为自然只能被文化所改造而不能被根除。
我们这个序列的基础结构如下。个人在社会群体中的持久互动产生了一种群体伦理信念。这种信念的存在表现为个体对群体成员某些规则的认可。一项规则不一定要得到每一个群体成员的认可,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就足够了,因为它能促使其他群体成员在行动时“关注”③T.N.Whitehead,Leadership in Free Society(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6),p.9.“普遍”承认。
当群体成员认可一项伦理规则,他会根据伦理规则的内容调整自己的行为,并试图去影响其他群体成员,使他们的行为也合乎该规则。这种意志倾向是承认的本质。如果行为违反了伦理规则,或者某种违反行为已具有威胁性,那么群体成员就会采取敌对态度,这种态度构成了承认行为复合体(behavior-complex of recognition)的一部分。④G.Humphrey,“The Conditioned Reflexes and the Elementary Social Reactions”,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and Social Psychology,XVII(1922):113-119.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在我们研究的社会文化反射形成之前,敌对的态度往往导致个体报复性敌对行为。集体反应行为,亦即社会文化的惩罚反射,取代了个体反应,这成为文化发展最具有决定性的步骤之一。原初的完全利己的动机,被净化、升华、改造为社会性动机。
尽管发生了这种转变,但违反公认的伦理规则还是会导致敌对态度。这一次序可以被理解为一系列个体反射,在这一过程中,一个行为(即实施犯罪)形成刺激,而不确定数量的群体成员的敌对态度则是反应。这些敌对态度会自然而然地导致个人的敌对行动;但是这一倾向被预期的群体反应所抑制。这存在着一种激动、不满的状态。已经成为第一束个人反射的刺激的那个行为(即犯罪),在以“官员”或集体意志执行者身份行事的人们——因为集体行为在欠缺组织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的——的复杂行为体系中发挥着刺激作用。这些行为序列被调整行为的习惯规范或者法律规范所约束。通常,它们导致犯罪者承受痛苦,而这种痛苦根据社会伦理信念,是犯罪者“应得的”。
知道官员们的活动是为了惩罚罪犯,更重要的是,知道这一目标已经完全实现时,群体成员就会形成一种放松的、心满意足的状态,他们最初的敌对态度因对官方行动的期待而得到抑制。这些敌对态度已经被消除,就像它们真的导致了个体敌对行为一样。我们还可以说到又一束个体反射,其中,对官员惩罚行为的了解构成刺激,而行为则表明信心、和平与安宁的恢复——这是反应。
所有的这些反射束都由后天的或者说条件性的反射形成,而非由先天的或非条件性的反射组成。根据条件反射的规律,该反射的完全表达意味着其得到强化,反之,如若没有表达则意味着该反射遭到抑制甚至破坏。我们链条中的一个要素是对罪行实施者的敌对态度,但是敌对的反应仅仅是承认的一环,从个体的角度看与从社会角度看的群体伦理信念一致。因此,我们所研究的复杂反射系统的实现结果是强化群体伦理信念,即群体伦理信念在其中贯穿始终。我们都身处一个社会—文化性的循环反射系统,它与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个体循环反射类似。①T.H.Allport,Social Psychology,(1924),p.39.犯罪—刑罚次序的基础结构可以被称为报应结构。②刑罚的报应结构在近代德国学术界得到热议,特别可以参见R.Schmidt,Aufgaben der Strafrechtspflege(Freiburg,1895);E.Beling,Die Vergeltung und ihre Bedeutung im Strafrechte(Tübingen,1908); J.Nagler,“Die Strafe,”Leipzig Vol.I,(1918);A.Baumgarten,“Das grundsätzlich Neue im schweizer Strafgesetzentwurfe,”Schweizer Zeitschrift für Strafrecht,vol.43(1929); H.Drost,Das Ermessen des Richters(Berlin,1930).
二、什么决定了刑罚的该当性?
并非每次违反伦理规则都会被施加痛苦,都会产生上述类型的循环反射。有一种该当性的自然法,只有当行为的恶和反应的恶之间符合一定的比例,循环反射才会发生,群体伦理信念才会得以强化。
在比较两恶时考虑哪些因素,取决于群体伦理信念。在一开始,人们是用最原始的方式理解相称性或该当性的:要求犯罪者此前行为与此后命运之间客观对等。这是同态复仇规则(“以眼还眼,以命抵命”)。后来同态复仇被等价复仇(iedal retaliation)所取代:等价复仇不仅要考虑犯罪侵犯的客观价值,还要考虑犯罪者的意图。③J.Makariewicz,Einführung in die Philosophie des Strafrechts(Stuttgart,1906),pp.338-437.另一方面,不再要求两恶之间保持客观对等,而只要求它们在伦理价值和由社会施加的痛苦这两个尺度上保持相似位置:对侵犯较高价值的犯罪应报以更大的痛苦,对侵犯微小价值的行为应报以轻微的痛苦。这就是等价复仇原则。在这种理想的报应结构中,可以观察到许多不同程度的发展;当然,当代刑法属于其中最完善的发展形态。随后可能会进一步演化,以目的刑(a teleological one)取代等价复仇(ideal retribution),即根据罪犯的社会危险性对其进行相应的处理,现代犯罪学的改革运动或许已经表明或预示了这一点。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一种现实。
我们是如何知道这些的?是通过研究自古以来的刑法典。④埃及法、希伯来法、希腊法、罗马法和阿拉伯法的相关历史证据,参见L.Günther,Die Idee der Wiedervergeltung,I(1899),p.24,43,78,65,109.所有的这些刑法典都按照可能的罪行以及相应社会反应的编目进行构建:犯罪损害的社会伦理价值越高,社会反应就越强烈。一些现代犯罪学家否认这一基础结构的普遍性,但在这样做时,他们混淆了两种观点:实在法实际上是如何规定的,以及实在法应当如何规定。当报应结构的反对者正在公允论辩时,他们必须承认这种结构至少在现代刑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①J.Michael and M.Adler,op.cit.p.374.
事实上,除了报应之外不可能有对刑法典的其他解释:刑法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按照报应惩罚的理念构建的。另一种解释或许是这样的:通过不同的痛苦来平衡犯罪后可能产生的各种快乐预期。但是,我们没有理由想象,最“残暴”(最应被严厉惩罚的)的犯罪带来的满足感是最强的,反之亦然,要使这一理论站得住脚,痛苦的分配必须与刑法典所产生的效果大不相同。
事实上,以痛苦制衡犯罪诱惑的思想,总是导致刑罚的严厉程度无以计量地增加。1813年的巴伐利亚法典就是如此,该法典由(针对潜在罪犯的)“心理强制”理论的倡导者冯·费尔巴哈制定②Cf.G.Radbruch,“P.J.A.Feuerbach.Ein Juristenleben,”Vienna (1934);S.Blohm,Feuerbach und das Reichsstrafgesetzbuch(Breslau,1935).;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的刑法也是如此,当时各国政府采纳了以刑罚威慑人的思想,威胁着削弱了刑罚的基础反射。这是发展中的一种反常现象.如果社会发展是通过试错法实现的,那么反常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刑罚的发展也是如此。十八世纪的刑罚哲学和刑事立法的相应调整,③1786 年托斯卡纳刑法典、1787 年奥地利刑法典、1791 年法国刑法典、普鲁士刑法典(位于普鲁士一般邦法中,1794年起生效)。使基础结构重新确立。
克服刑罚的报应结构的可能性是值得怀疑的。首先,如前所述,符合该当性的具体规则是可变的,可以想象一种新的“目的刑”,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着改革者的憧憬。其次,最近的实践已经证明,即使是最莽撞的改革者也不敢完全打破基于报应的传统。
1921年,意大利颁布了一部刑法典草案,该草案是由“实证”学派的领导者们所制定的,他们对报应的理念感到恐惧。④Cf.Sh.Glueck,“Principles of a Rational Penal Code,”41 Harvard Law Review 453 ff.1(1928).该草案只有总则部分,从总体上规定了犯罪和刑罚,通常包含上述编目的分则部分却从未出现过。但是,总则部分的许多条款都允许这样的假设,即在改革者的心目中,分则是由正常类型的编目构成的,只有在这一假设下,草案中涉及正常刑罚增减的那些细致复杂的规则才能得到解释。
1930 年,俄罗斯人克雷连科(Krylenko)详细拟订了一项刑法典草案。⑤该草案已经发表于:“Sovetskaia Justitsia,”No.19(1930).Cf.N.Timasheff,“L’Evolutione del diritto penale sovietico” in Rivista Italiana di diritto penale, Vol.4 (1932): 188-9; Müller,“Die Entwickelung des sowietrussischen Strafrechts,”Archiv für Criminalpsychologie und Strafrechtsreform,Vol.21(1930):650-2.该草案完全取消了该当性和报应性原则:应受惩罚行为的编目不再包括对应每一种行为的制裁;社会反应只需考虑犯罪者的社会危险性。但是,这个草案从未被通过,现在也不可能颁布,因为共产党政府已经对传统作出诸多让步。
涉及该当性的规则可能各不相同,还可能会互相取代。但该当性的一般法则始终有效。它是一种自然法则,试图规避它会导致社会病态现象。如果总体来看,犯罪之后没有压制或者惩罚明显低于该当性规则(就当时的社会伦理评价而言)所指明的程度,那么就会出现恢复个人反应(私力复仇)的倾向——这就是“私刑正义”的根源。如果压制明显比社会伦理评价所要求的严厉,那么惩罚并不会加强群体伦理信念,相反,它所产生的集体情绪会破坏这种信念:罪犯被视为“受害者”,而施加惩罚的政府代理人则被视为暴君。①在俄罗斯,直到19 世纪中叶,刑法仍然极为严厉,罪犯被称作“不幸者”。N.D.Sergeievsky,Russian Criminal Law(in Russian)(St.Petersburg,1911),p.87,173.
三、犯罪与刑罚应如何调整?
在发展初期,犯罪—刑罚序列内不存在欠缺调整的缘由。随着社会演变的推进,原初结构因某些超级结构变得复杂,这有时还会导致循环反射的失调。
对违反伦理规则的行为实行惩罚,成为政治权力的职能之一。一开始政治权力毋宁说是通过选择的方式开展工作的:只有已经被无组织的社会交往所创造和承认的规则,才能得到法定惩罚的认可;立法,如果有的话,只不过是对往往不精确的群体信念的正式确认和澄清。
除了选择之外,很快又出现了第二个过程——同化。原始的政治权力已经拥有了一种防御系统,它包括对每一个侵犯或者危及政权利益的人展示赤裸裸的权力。逐渐地,这种非正式的防御系统被转化成与那些构成群体伦理信念的规则类型相同的规则综合体,并被赋予了实施同样的制裁措施的权力。②在罗马法中,这种演变最为明显。Th.Mommsen,Römishes Strafrecht.(Leipzig,1899),pp.35-54.这样,某些规则被“同化”进了最初的相互交往所创造的规则中。稍后,随着国家及其职能的发展,被同化的规则急剧增长;现在它们构成了所有具有惩罚性制裁的规则的主要部分。就基础结构而言,这些规则只不过是对服从既定权威的命令的放大。这些规则通常以如下不正确的形式表达:法律规则只是部分符合伦理规则;从伦理角度来看,有一部分法律规则是中立的;在极端情况下,一些法律规则甚至和道德规则背道而驰。
当政治权力试图将新规则同化入原始规则时,它的策略是什么?它是在犯罪—惩罚的循环反射中引入新的规则,并以这种方式强化这些规则。在基础结构内,惩罚是社会不认可被惩罚者行为的一种表征;在基础结构内,犯罪与惩罚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短促,以至于社会的憎恶往往从罪犯转移到被惩罚者身上。众所周知,一个被惩罚的个体重新加入已经倾向于将他视作局外人的社会群体是多么困难,罪犯改造是实用犯罪学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对群体舆论来说,已被惩罚就等于侵犯了群体伦理信念。政治权力在创造新的应受惩罚行为时,考虑到了这种置换,并希望民愤能加强新制定的规则的效力。
这样的计算往往会被事件所证实。首先,新规则可能符合群体伦理信念的发展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处理的是持续的选择,而不是同化。其次,政治权力有时成功扮演了社会伦理领导者的角色,它的行为会得到有影响力的团体成员的确证,群体信念也相应地被修改。最后,如果在引入新规则时采取必要的谨慎态度,避免了与现有信念的明显冲突,且新规则的数量不多,那么同化过程也会发生。
四、现代刑罚结构存在什么问题?
但无所不能的错觉很容易跟政治权力联系起来。看起来政治权力具有迫使每个人按照强制力确立的模式行事的强制力,特别是在违法行为得到制裁的情况下。处于改革热情期的革命政府和独裁政府经常在这种错觉的影响下行事,有时民主政府也是如此。他们引入新的行为规则,并赋予其刑罚制裁,希望这些规则能逐渐被纳入群体伦理信念之中,并通过犯罪—惩罚的循环反射得到加强。实际结果有时却大相径庭:以这些规则为基础的专横惩罚行为在群体内被评价为不适当、不公正,它们可能在群体成员的意识中引入恐惧动机,并阻止其中一些人违反新规则,但它们仍然不存在循环反射,有时还会破坏整个群体伦理信念。在这方面,美国禁酒令的经验是非常明确的。①Michael and Adler,p.239.
在这种情形下,循环反射的一个要素是由基本社会群体之外的某个社会群体决定的,这造成了失调:政治权力的拥有者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它固然与更大的“社会”密切相关,但显然被赋予了特殊的群体精神和利益,并按照特殊法则发展。
麻烦和失调还来自另一个方面——确定刑罚的性质和目的。只要基础结构是有效的,惩罚的具体目的就会以一种相当不精确的方式被确定下来:②O.Kinberg.“Über die relative Bedeutung der Generalprevention und der Specialprevention,”Monatsschrift für Criminalpsychologie und Strafrechtsreform,XXI(1930):470.犯罪之后,与其恶大致相称的恶应跟随其后,仅此而已。
随着社会伦理信念的发展和完善,监禁刑已成为惩罚制度的核心要素。必须强调的一点是,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人们确信监禁刑的优越性,而是因为当早先盛行的两种主要刑罚方法——死刑和身体刑分别被大大削减和几近废除时,只剩下了监禁刑。监禁刑突然被放在首位时,群体伦理信念并没有赋予它特殊的目的。
当监禁刑成为惩罚制度的核心时,一个由最优秀、最人道和最有远见的监狱管理员组成的新社会团体应运而生。他们以加强群体伦理信念为历史目标,试图与其他目标结合起来,这些目标首先涉及他们要对待的罪犯:通过监禁改造罪犯的想法就是这样产生的。经验表明,用现有的方法改造罪犯只在某些情况下是可行的。后来(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了一场改革传统惩罚制度的运动,目的是使其成为一种适当的、普遍的改造工具,隔离惯犯的想法也被纳入了这一计划。在许多国家,这一运动得到了知识精英的支持,并对实在法产生了影响。
因此,在当代法律中,刑罚的性质和目的仍然是由社会决定的,但这种决定往往是特定精英(而不再是整个“社会”)商议和确信的结果。③这有时会导致看似被大力推行的措施彻头彻尾的失败。针对“惯犯”特别措施的失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些措施已被写入实在法,但却遭到了表达群体伦理信念的“公众舆论”的反对并在实践中搁浅。关于法国(1885年的法律),参见R.Heindl,Der Berufsverbrecher,Berlin 1927,p.136-7; 关于挪威(1902 年的法律),参见K.Wilmans,Die verminderte Zurechnungsfähigkeit,Berlin 1927,p.322-3; 关于英国(1908 年的法律),参见Report of the Departmental Committee on Persistent Offenders,May,1932,Printed and published by 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London,1932.刻意为之的社会决定已经成为政治权力和特殊精英的一种职能,这不仅是在我们所研究的复杂问题中如此。但是,刑罚的情况较为特殊。应受惩罚的行为类型现在更多地由政治权力而非整个社会决定。刑罚的性质和目的现在由特殊精英决定。但是,整个社会都是受这一决定影响的对象:每个群体成员都是潜在的罪犯,因为一系列不利的环境可能会诱发人们犯罪;(刑罚的)目的是控制普通群体成员的动机,而不是控制活跃的权力中心或精英的动机。此外,整个社会承载着预防犯罪的机制——通过“犯罪—惩罚”的循环反射强化群体伦理信念。强化这种信念,至少不破坏这种信念,应该是理性社会防卫犯罪的首要原则。
结论绝不是主张回到基本结构的旧形式,而是在行动时考虑并理解这一结构。只有在强制施加特定类型的行为①即“刑罚”(译者注)。成为一种明显的社会需要(而不仅仅是立法者的一时任性),而且通过其他手段(即通过所谓的间接诱导)完全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的情况下,才应引入应受刑罚行为的新类型。应谨慎采用对待犯罪者的新形式,并适当考虑到支配“罪与罚”社会文化反射的自然法则。如果我们在改造100 名真正的罪犯时,破坏了集体信念的预防机制,把1000 名潜在罪犯变成了现实的罪犯,难道不是适得其反吗?